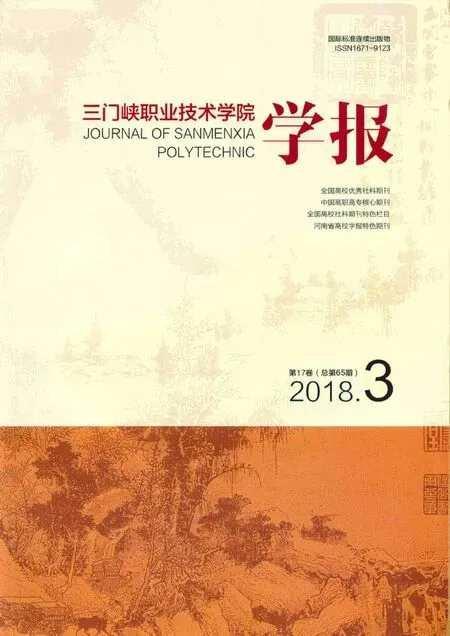联系中的思索
——论卡夫卡式的境遇及独特表现
◎张 曦
(陕西理工大学 文学院,陕西 汉中 723000)
卡夫卡无疑是20世纪最杰出的作家之一。他特殊的生活背景与体察世界的独特眼光与感知方式都使他的作品呈现出深刻的意蕴内涵。学界对卡夫卡的研究多停留于对其荒诞,悖谬的写作风格、异化等精神意蕴分析、叙事特色、某一具体作品进行某个侧面的静止分析等。文章试图从卡夫卡个人与社会、与他人、与自我的动态交往与联系中所体味到的强烈的心理体验入手,结合其具体作品分析其独特文学表现。尝试归纳卡夫卡在思考与反思中所形成的三种特殊的写作意识:无力的虚无、负罪的沉重与悲剧的毁灭,进而深挖出卡夫卡通过这三种独特的写作意识传递的人与世界交互联系中的困境与挣扎。
一、“我”与社会——无力的虚无
再没有人像卡夫卡那样无法将自己的身份有一个明确的定性。作为犹太人,他在犹太人当中不是自己人;作为说德语的人,他在捷克人中不是自己人;作为劳工工伤保险公司的职员,他又不完全属于资产阶级,[1]这种身份的游离总让他有种无所归依的孤寂虚幻之感。但不甘于被边缘化的卡夫卡也从未放弃过融入社会的努力。作为一个合格称职的劳工工伤保险公司的职员,他将自己巨大的热情献给了自己的工作,也获得了巨大的荣誉。但这种双重性格给他带来的却并不是相互影响下的调和,而是随着时间推移日渐激烈的内心冲突与矛盾。他越努力地进入社会,也就越了解社会的本质内核,这带给他的是更深层次的绝望。在这种绝望与试图超越的碰撞挤压下,他无法停止游走在世俗环境中的步伐却又举步维艰。而他这样的惶恐不安与找不到出路的无力感自然也加深了他对虚无的感受,形成了他作品中虚幻颓靡的写作风格。
他将这种在社会中体会到的虚无感投射给了《城堡》中的K。虚无首先来自于身份的模糊与不被认同。K以被城堡雇佣的土地测量员的身份来到村庄,但他却逐渐发现,所有人对于他土地测量员的身份都不予认可,甚至连给他发出任命书的城堡都无法肯定他的身份,这使K的出现从顺理成章变成了扑朔迷离,进入城堡也变成了一种虚无缥缈的目标。虚无也来自身份不明之后的迷茫却又不甘被否定的矛盾追逐。身份成谜的k被否定后并没有离开,而是一步一步地妄图证明自己的身份,从而融入到这个环境之中。K不断尝试:对通往城堡之路不断寻觅;把希望寄予能够给自己向城堡传信的两个帮手中;接近城堡的官员克拉姆的情妇弗里达……K一次次燃起希望却又快速破灭。无论K用何种方式,如何在等待中迷茫,穷尽一生,他也没有得到自己身份的认同,进入城堡。追逐本身是一种有意义的积极行动,但在这里,追逐却只是用死亡献祭的一场荒谬悲剧。卡夫卡将自己在社会中所体验到的虚无感一层一层地加在了K的身上,从身份到目的,再到过程,所有的一切都成为了K周身散不去的幻影迷雾,使他找不到出路,最终只能坐以待毙。虚无感被卡夫卡同样赋予给了《地洞》中那只可怜的小动物。这只小动物与K一样在矛盾中不断追逐,最终却只能体味追逐的虚无、庇护的虚无。它以修建地洞,为自己打造一个谁也无法进入的避难所,获得永久的宁静为生存目标。为了这个目标,它“用手抓,用嘴啃,用脚踩,用头碰。将血渗入到它的那片土地中”。[2]为了这个目标,他的精神总是处于焦虑之中:时而欣喜地观赏着自己的杰作,时而却害怕它因为不可抗的外界因素而崩塌。即使在身体与精神的双重损耗下,它也无法得到它想要的宁静的避难所,外界即使是很小的响声就能令它颤抖,轻易地将它所有的努力打破。于是糟糕的恶性循环就这样困住了它,它越惶恐外界的威胁,就越无法离开自己的栖身之地,但越依赖,自己却越要承受着随时失去保护的担惊受怕之中。他在对于宁静的追逐中永远无法得到宁静。卡夫卡带着悲悯的目光嘲笑着这只小动物庇护之所——无法企及的保护,毫无意义的追求。
就如同卡夫卡在社会中体验到的那样,K与那只建造地洞的小动物,即使再努力也无力改变强加给他们的不安与重压。卡夫卡用荒诞的表现揭示了人类在社会生活中无法摆脱的困境:身份的难以归属、追逐的无意义。这种困境使人与社会永远无法相互融合,而处在一种错置的状态中,让人们的家园感与归属感消失殆尽。面对整个社会的重压,面对看到的或者看不到的重重阻力,人们不停地追逐目标,换来的确是更大的虚无。卡夫卡将他体察到的社会带给他自己的感受投注在了自己的作品中,揭示了人们在社会中身份认同的艰难与始终无法摆脱的虚无感。
二、“我”与他人——沉重的负罪
卡夫卡和他人的关系充满了矛盾,他与父亲的关系尤其如此。“对卡夫卡来说,家庭是压迫开始的地方”[4]。父亲的暴力在幼年的卡夫卡心中留下的不可抹去的阴影,使他对于父亲的压迫敏感而胆怯。这种压迫来自于父亲的暴力行径,也来自于他总是无意识地陷入父亲太过于强大而自己又太过于弱小的对比情绪之中。在父亲强大的权威下,他形成了既不满同时又对自己的反抗情绪充满愧疚的病态负罪心理。这种复杂而矛盾的心理就如同精神枷锁,让他永远沉重地背负着“罪责”的重压。
在卡夫卡的《判决》中,一个儿子因为隐藏了一些无从轻重的事实而让父亲勃然大怒,这本是一种平常的责备,但在儿子这里却如同死神的裁判般不可违抗:父亲的一句让他投河淹死的荒唐“判决”就让儿子义无反顾地选择了服从。与其说父亲的一句话是儿子走向死亡的发令枪,不如说其实当儿子选择对父亲有所隐瞒、挑战父亲的权威时,负罪的重压就已经预示了他的命运。在权威绝对强大时,一个小小的隐瞒都是对权威的亵渎,而当背叛发生后,代表权威的一句话都足以对这种“罪行”进行残酷的审判。
卡夫卡在之后的创作中虽然很少再出现父亲的形象,但他将父亲的形象转变成了各种形式的权威与压迫,与之相随的负罪意识也依然是卡夫卡摆脱不掉的精神枷锁。他将这种枷锁戴在了《审判》中约瑟夫·K的身上。在《审判》中,权威就是法,就是与法有关的一切权力机构与在这些机构中工作的人员,甚至是同样拥护法的普通人。K是在一天早上无端被逮捕的,K就这样成为了权威的被控制者。被捕的毫无预兆,使K无法理解也无法接受,但他还是开始了漫长的申诉。K的负罪来源就是这样对权威即反抗又认同的矛盾心理。权威是压抑的,同样也是强大的,人的自我意识总能从这种权威中感到压迫,从而使反抗的潜意识暗涌,但这种反抗在卡夫卡那里却因为负罪而成了一种徒劳。K没能逃脱死亡的命运,卡夫卡要K为自己对于权威的质疑与反抗付出应有的代价。
应该说,通过儿子和K的死亡,人们可以看到这种负罪意识是有些病态而消极的,童年的心理阴影使卡夫卡消极的将父亲所代表的权威压迫下产生的负罪心理看作是一种命运般的不可违抗,它不一定能代表人类本性中共有的缺陷。但无法否认的是,抛去这种个人化病态的根源,将这种负罪意识的边缘扩大,它在揭示人与他人的关系中人类消极的一面还是有极大的反思意义的。先以K来说,虽然他一直为自己的无罪辩护,但在自我审视的时候,他发现自己也不是那样的“无辜”。作为一个银行职员、政治机关中的一员,他将自己也抽象为权利的代表,运用等级观念压制下属,对待前来办理业务的普通民众,将权力机关的政治暴力具体化。同样背负罪责的还有那两个逮捕K的看守。卡夫卡安排了他们被鞭笞的情节,表面上是在惩罚他们在逮捕K时不恰当的行为,实则谴责了他们为了自己的目的而告密背叛同事的有罪行为。而那些表面以法作为掩护的法庭工作人员就更加“有罪”了。他们滥用权力,在法的伪装下做着荒唐的事,如法官宣读的判决书竟是黄色周刊等。他们就是用这样的敷衍与冷暴力随意地处置本应该被法保护的人。法的维护者却践踏法律,这种强烈的讽刺正是卡夫卡所想要传达的深刻的负罪意识。
卡夫卡作品中的负罪意识在今天应该被更宽泛地理解,负罪其实就是人类应该为人性中普遍存在的阴暗面而承受的谴责。在与他人交往时,人们总会以个人的既得利益为中心而伤害他人:偏见、利用、自私这些人类摆脱不掉的劣性,都是使人类无法逃脱罪罚的根源。卡夫卡作品中的负罪意识足以让人们反思自己,如何恢复人性的纯美,摆脱负罪的重压。
三、“我”与自我——悲剧的毁灭
可以说,在与外界的联系中感受到的绝望与痛苦使卡夫卡自我封闭的同时也造就了他。为了探寻一切人类在社会中产生的不安。消极的本质与根源,他将审视的目光移回人自身。他敏锐地察觉到了人类似乎永远无法解决的矛盾:想要肯定自我的价值,却又往往将衡量的标准让渡于他人而抛弃自我;人类的精神力量总在不断地要求自我实现,但现实却将人类的肉体拖入了静止甚至堕落的深渊,这种分化与矛盾给人类带来的是毁灭的悲剧,这种思考也就形成了卡夫卡作品中的悲剧意识。
悲剧意识在《饥饿艺术家》的身上蔓延,最终摧毁了那个以饥饿为表演艺术的艺术家。悲剧体现在艺术家对于自我价值的转化与抛弃。饥饿艺术家是一个以表演饥饿为生的人,这种看似有些荒诞不经的表演形式却也是艺术家赖以生存的人生价值。但可悲的是,他却将这种价值的裁判权抛到他人的手中,仿佛只有在观众们的赞叹声与惊诧钦佩的眼神中他才觉得自己的艺术得到了认同,自我的价值才得以实现。当饥饿艺术家饥肠辘辘地进行自己引以为傲的艺术时,观众却怀疑他在表演过程中偷吃了东西;他彻夜不睡陪伴看守聊天来向别人证明他的确是在进行伟大的表演,但“诚然,也有人对此举不以为然,他们把这种早餐当做饥饿艺术家贿赂看守以利自己偷吃的手段”[2]。在自我价值已经被自我抛弃,又得不到他人的认同时,艺术家的悲剧已成定局。他最终悲惨地在自己表演的牢笼中死去。卡夫卡向人们展示了当人类对自我价值的认同从对自身尊严的肯定转化为对于旁人近乎无自尊的乞求时,来自于他人的否定必将造成人类自我价值的崩塌与毁灭。
毁灭的悲剧也来自于灵魂与肉身无法调和的悖谬分裂。《饥饿艺术家》中的艺术家为了向世人表达自己对于艺术至死不渝的追求,为了能让艺术的超越成就艺术家的意义,他直到瞳孔扩散的那一刻,眼中都流露着坚定的信念,他要饿下去,达到他所追求的最高的艺术境界。他完成了精神的超越,肉体却也同时陨灭。在卡夫卡的悖谬哲学中从来都不会存在两全其美,更肖说是灵魂与肉体的分裂。肉体是有限的,因为有限的生命,人类往往无法在现实生活中得到永恒,但精神的驱动力与思考的探索却是那样的无边无际。思考总让那些不甘流于肉体平庸中的人们由精神的力量所支配,不断地追求更高尚的灵魂,然后当他发现肉身无法达到灵魂的高度时,便以毁灭的方式达到永恒,实现生命的意义。即使没有毁灭,也游走在极度痛苦与挣扎的边缘。卡夫卡用饥饿艺术家最终的毁灭向人们揭示了人类悲剧的根源:上帝用灵魂的无限以弥补人类肉体的有限,却也让人类永远无法同时拥有二者。
应该说卡夫卡的悲剧意识的真正内涵是人类无法摆脱的生与死的悖谬,其结果虽然是一种悲剧的毁灭,但卡夫卡并非是想用这种悖谬令人类陷入绝望之中,而是唤醒人们更强烈的生的意识,让人们不断自我完善,认识到自我价值。“将‘希望’一词用于卡夫卡的创作并没有任何反讽的意味,相反卡夫卡对悲剧的描绘越真切,对希望生的呼唤就越强烈”[3]。他呼唤人们重新从自我出发,在不断超越中肯定自己的力量。他提出了灵魂与肉身的分裂,并不是让人们悲观地沉溺于生的短暂与永恒追求的矛盾中,以死亡达到永恒,证明人类的价值。而是提醒人类不要使肉体在安逸生活的享受中放弃了前进,使灵魂的不朽与超越离肉身越来越远,他呼唤人类在不断地思考中找到自我的价值,尽力达到使灵魂与肉体的融合,找回并重新确立人的尊严。
卡夫卡曾说过:“其实我就是恐惧组成的。”[5]从出生到死亡,他始终都活在压抑与恐惧中。这些负面的情绪使卡夫卡一生都禁闭在孤独却独属于他的文学世界里,但这并不意味着他的世界是闭塞、与外界完全隔离的。如果没有与外界的联系,只凭借主观的想象与毫无根据的思考,他的世界绝不会那样丰富而又意蕴深远。恰恰是因为他在与世界、与他人的联系中始终保持着独立的思考、清醒的意识,思考人与人、人与世界、人与自我的关系,从而将在与三者的联系中所体验到的情绪放大,外化,从而才深刻的揭示出了人与社会的本质。他在孤独、恐惧与压抑中将自己痛苦的思考无私地呈现在自己的作品中,披上文字的外衣形成一种属于他的独特的文学表现,带给人们以无限的思考。虽然对幻灭、负罪,毁灭的表现使卡夫卡的作品沾染上了一层浓厚的悲剧色彩,但卡夫卡最终的目的并不是让人们陷入绝望,而是告诉人们只有在绝望来临时,人们才能正视绝望,从绝望中燃起希望:面对困境,恢复与重建人的价值与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