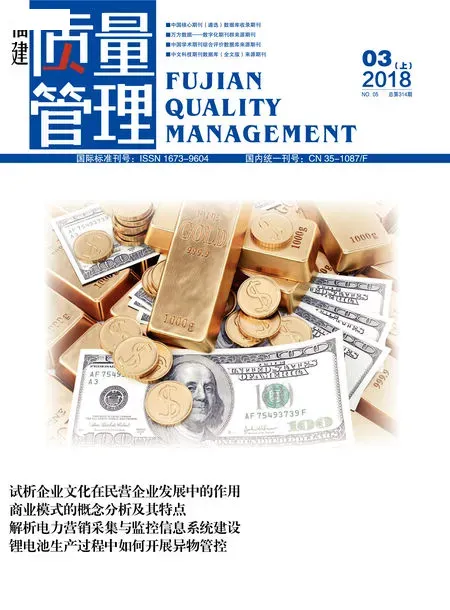销售服务商标的法律保护
(浙江工商大学法学院 浙江 杭州 310018)
近年来,超市、商场、连锁便利店等经营形态持续增长,这使得日渐饱和的国内零售市场竞争更加激烈。为了在市场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各商业企业开始提供差异化服务来吸引消费者,也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商誉,其商业价值体现在所提供的服务而非产品,此类销售服务商标引发的法律问题也逐步显现。在我国现有的商标注册制度下 ,商业企业是无法在“销售服务”上注册商标的,他们往往通过三种方式来寻求法律保护:一是将自己的商标注册在第35类“替他人推销”上来寻求《商标法》的保护,但是对于“销售服务”和“替他人推销”的关系,学术界和司法界都还没有统一的认识;二是通过未注册驰名商标的保护来主张自己的权利;三是寻求《反不正当竞争法》中对企业名称、字号的保护。销售服务商标纠纷日益增多,亟需给予其法律上的保护,本文将结合具体案例分析销售服务商标的保护现状,剖析商标法意义上的“服务”概念,进而分析超市、商场等商业企业的销售服务的性质,破解其法律保护上的困境。
一、销售服务商标的保护现状
(一)“替他人推销”类别注册商标
由于目前我国没有开放“销售服务”这一商标注册类别,所以很多商业企业在第35类“替他人推销”这一在语义上较为相似的类别进行注册,但是“销售服务”和“替他人推销”二者的关系在实践中是一个颇具争议的焦点问题。
1.在商标注册上,商标局认为“销售服务”和“替他人推销”构成不同服务
在使用原版《类似商品与服务区分表》(基于尼斯分类第八版)期间,商标局在商标申字[2004]第 171 号《关于国际分类第 35 类是否包括商场、超市服务问题的批复》中明确指出:“销售服务”与“替他人推销”构成不同服务。理由是商场、超市是主要从事批发、零售的商业企业,而第35类的注释则明确说明,该类别服务的主要目的在于“对商业企业的经营或管理进行帮助”,或者“对工商企业的业务活动或者商业职能的管理进行帮助”,且“尤其不包括:其主要职能是销售商品的企业,即商业企业的活动”。由此可见,第35类“替他人推销”服务的内容是:为他人销售商品(服务)提供建议、策划、宣传、咨询等服务,商场、超市等商业企业的批发、零售活动无法归于该类,即使在该类进行注册,也无法得到有效保护。我国于 2007 年 1 月 1 日开始使用尼斯分类第九版,表中第 35类注释的“尤其不包括”项下已经删除了原版中“其主要职能是销售商品的企业,即商业企业的活动”这一特别说明的文字。2013年1月1日起,依据尼斯分类第十版,商标局在第35类中新增7个医药领域的“零售或批发服务”,指将药品、药用制剂、卫生制剂、医疗用品、兽药、兽医用制剂等商品集中和归类(运输除外),以便顾客看到和购买,但是商标局只是非常有限和保守地在上述医药领域接受了7个批发零售服务。2013年1月,其在《关于申请注册新增零售或批发服务商标有关事项的通知》中明确表示零售或批发服务在此类的注册不予受理。综上,商标局在商标注册环节的态度很明确,“销售服务”和“替他人推销”构成不同服务。
2.在商标侵权纠纷的司法裁判上,法院未达成一致
“销售服务”和“替他人推销”是否构成相同或者类似服务,在司法实践中存在三种不同的观点。
一是认为构成不同服务。在“采蝶轩”商标案中,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合肥采蝶轩服务有限公司在面包店铺门头上使用‘采蝶轩’标识,不是对其注册在第35类‘替他人推销’的服务商标的使用,因而不能构成正当使用。” 但最高院并没有给出明确的原因解释,有观点解读为被告店铺提供的是面包、蛋糕、牛奶等商品的销售并提供场地供餐饮的服务,店铺与消费者之间的交易对象既是面包、糕点等商品也是餐饮服务,所以被告的店铺提供的主要是第43类餐馆、面包店等服务,而不是替他人推销服务。
二是认为构成相同服务。广东高院在“好又多”商标案的判决中给出了明确观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标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中规定根据相关公众对商品和服务的一般认识来综合判断商品和服务是否类似,《商标注册用商品和服务国际分类表》、《类似商品和服务区分表》可以作为判断类似商品或者服务的参考。《类似商品和服务区分表》(基于尼斯分类第九版)中删去了第八版所规定的“替他人推销服务不包括销售服务”的内容,而且,广东高院认为目前大多数零售商家在第 35 类“替他人推销”上申请注册商标,并将注册商标实际使用在销售活动中,零售商家的大量使用使得相关公众将“替他人推销”与“销售服务”视为相同服务。综上,以广东高院为代表的部分法院是将“商场、超市”与第35类中“替他人推销”认定为相同服务。
三是视情况构成类似服务。在“友阿”商标案中,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在本案中认定批发零售服务与“推销(替他人)”为类似服务,考虑了注册背景、现实市场情况、司法解释对类似服务的规定以及知名商业企业在“推销(替他人)”服务上的商标被认定为驰名商标的事实情况。
(二)未注册驰名商标保护
商标局网站上发表的数据显示,商标局和商评委将许多注册在第35类上,但实际用于批发、零首的商标认定为驰名商标,比如“苏宁电器”、“潘家园旧货市场及图”、“红星美凯龙及图”、“银座”等。由此可见,商标局和商评委认可批发、零售的商业企业提供的服务可以归入“替他人推销”。
“Walmarts”商标案是一起零售企业通过未注册驰名商标维权的典型案例。二审法院北京高院认为:根据原告沃尔玛百货有限公司提交的证据,可以证明沃尔玛百货有限公司是全球最大的零售企业。案件中的证据足以证明经过沃尔玛百货有限公司的大量使用,“沃尔玛”和“WAL-MART”商标在中国已成为社会公众广泛知晓的商标,相关公众已将两商标之间建立唯一对应关系。在此基础上,法院认为被异议商标“Walmarts”破坏了引证商标“WAL-MART”与其指定使用服务之间唯一固定的联系。然而,在该案中,原告沃尔玛百货有限公司仅提供了引证商标“WAL-MART”在零售服务知名的证据,却没有提供在“替他人推销”服务上知名的证据。
(三)寻求《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
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对于知名商品的有关规定适用于知名服务。实践中,已有销售服务的提供者寻求知名服务特有名称反不正当竞争法上的保护。原告海宁中国皮革城股份有限公司诉被告卓尔发展(武汉)有限公司、汉口北集团有限公司、武汉汉口北商贸市场投资有限公司侵害注册商标专用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一案中,原告通过大量的举证证明“海宁皮革城”通过宣传和使用具有了显著性、原告提供的“销售服务”知名度高以及被告攀附他人商誉的主观恶意,因此,被告使用“海宁皮革城”标识的行为易使消费者产生误认和混淆,认定其侵权。
企业名称是由行政区划、字号、行业或者经营特点、组织形式构成的,其中字号最具识别意义。企业名称和字号起到了区分不同市场主体、表明商品来源的作用,是企业极为重要的无形财产。《反不正当竞争法》(1993)第五条第三项中有对企业名称的保护。我国从事批发、零售的商业企业可以通过《反不正当竞争法》寻求企业名称和字号的保护。
二、厘清“服务商标”中的“服务”概念
现有商业企业通过不同方式对其销售服务寻求法律上的保护,商标注册行政体系与司法保护体系存在不同,商标注册体系严格依据《分类表》,而司法保护则更重视平衡各方利益、解决客观实际问题。越来越多的学者建议开放“销售服务”商标的注册,明确给予“销售服务”商标有力的商标法上的保护,但是这一做法的前提是,商场、超市等商业企业的销售服务是商标法意义上的“服务”。这就首先要对商标法中服务商标的“服务”概念进行厘清。
关于“服务”概念的定义一直持续却没有定论。亚当 ·斯密认为“服务”是“不产生有形产品的所有活动 ”。国际标准化组织(ISO,1991)对“服务”定义为有形产品的附属物,即由生产过程而产生的结果。当代市场营销学泰斗菲利普·科特勒给服务下的定义是:“一方提供给另一方的不可感知且不导致任何所有权转移的活动或利益,它在本质上是无形的,它的生产可能与实际产品有关,也可能无关。”《服务贸易总协定》第一条范围和定义中第三款将“服务”定义为:包括任何部门的任何服务,但在行使政府权限时提供的服务除外。国际上,美国《兰哈姆法》、《巴黎公约》、《Trips协定》等未提及何为“服务”,我国商标法及司法解释也没有“服务”的定义。可见,由于服务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对“服务”的概念一直缺少明确的定义。要想解决本文中“销售服务”商标的问题,我们首先要从商标法意义上厘清 “服务商标”中的“服务”概念。
在商标法中,商品商标所指向的对象是有形的商品,服务商标所指向的对象是无形的服务。与商品相比,服务具有明显不同的特征:服务是无形的,不可触碰的;服务的产生和消费是同时进行的,二者不可分离;服务上述的两个特点决定了服务是不能储存的,顾客不可能把专家门诊的服务安放起来留着以后使用。当然,并不是所有的服务都值得《商标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保护,立法目的是保护经营者和消费者的利益,维护市场秩序,与不可注册的服务相比,商标法上的“服务”也具有其特殊性,这一方面的区别更值得关注:服务具有交换价值,日本学者纹谷畅男认为“服务”是看不见的商品,即可独立成为经济交易对象的无形商品,作为奖励,企业为内部员工提供的服务就不是商标法意义上的“服务”;服务是为了他人利益的活动,而不仅是提高自身价值,如果企业为销售或宣传自己的商品而提供商业信息、广告宣传、赞助、比赛等,属于对商标在商品上的使用,而非提供服务。
三、超市、商场等商业企业“销售服务”的性质
之所以超市、商场等的销售服务在商标注册和司法实践中被区别对待,究其根本其实是对超市、商场等销售服务的性质界定问题。
超市、商场等的销售服务归属于零售业,从营销学上讲,零售业是指个人或公司从批发商、中间商或者制造商处购买商品,然后直接销售给消费者,是一个历史悠久的经营形态,遍布世界各地,也有着很多知名老字号。商场、超市等商业企业的“销售服务”无疑是零售服务的一种,但这是否是商标法意义上的“服务”。
上文阐述了商标法意义上“服务”的概念,分析了其与不可注册服务的区别,接下来也从这方面进行探讨。
商场、超市等商业企业的销售服务不具有独立的交换价值,是依附于其所销售的商品之上的,如果没有商品,这种服务也就不复存在。虽然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会因为商场或者超市良好的服务态度、便民的商品归类和售后保障而去购买商品,但这些都是商场、超市在销售商品时的正常范围内的服务,仅仅是“加分项”,我们主要目的还是为了获得商品而非商场的服务,超市、商场赚取的也是售卖商品的差价或者提成,与销售服务并无直接关系。商场、超市提供的一些打折促销活动,是为了多卖商品增加自身的收益,与商品厂家无关。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超市提供的所有服务都不是商标法意义上的“服务”,有些线下超市开展线上业务,其通过网络提供的方便顾客浏览、购买的服务就是属于第35类明确列举出的服务,因为自尼斯分类第九版起,在第35类注释“尤其包括”项下,在原说明“为他人将各种商品(运输除外)归类,以便顾客看到和购买”后特别增加了“这种服务可由零售、批发商店通过邮购目录和电子媒介,例如通过网站或电视购物节目提供”的说明。
四、结语
商场、超市等的“销售服务”不符合商标法意义上的“服务”,不能强行纳入“服务商标”的保护范围,但这并不意味着商场、超市在提供销售服务过程中多年来形成的商业价值就无从保护,当商业企业的名称、字号、装潢等受到他人侵害时,除了《商标法》,我们还可以寻求《反不正当竞争法》、《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企业名称登记管理条例》、《民法通则》、《广告法》等的保护。而且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已经修订,其中第六条有多处变化,将原来的“擅自使用知名商品特有名称、包装、装潢”改为“擅自使用他人有一定影响的商品名称、包装、装潢”、在“企业名称”后面增加了“包括简称、字号等”明文解释,并在列举的三项混淆行为之后加上了一条兜底条款,更有利于被侵权方依法提起诉讼,一定程度上减轻了被侵权方的举证责任。学术界和司法界对“销售服务”和“替他人推销”关系问题本就存有争议,纠结于《商标法》上的保护是有风险的,这时转向《反不正当竞争法》等其他法律保护是更好的选择。
[1]王莲峰.商标法[M].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
[2]管勇、王玉杰、王潇鸿.关于零售(批发)服务商标的思考[J].中华商标,2010(12).
[3]邱进前.从Giaomelli Sport Spa’s Application一案看欧盟零售服务商标的可注册性[J].当代国家法论丛,知识产权出版社,2008.
[4]李长宝.“与商品销售有关的服务商标”的可注册性——基于中国与欧盟的司法实践予以评析[J].知识产权,200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