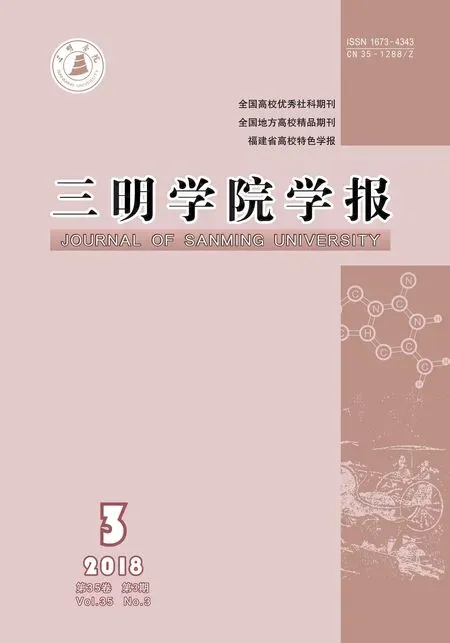朱熹论涵养为格物致知之本
徐 涓
(三明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福建 三明 365004)
朱子学之一重要理论是格物致知论,朱子格物致知论并不等同于一般认识论。朱子格物致知论的形成历经漫长过程,考察其思想之前后变化以及发展成熟,对于研究朱子学有重要意义。
一、朱子哲学之核心:格物致知
南宋杰出的哲学家、思想家、政治家和教育家朱熹(1130—1200),是孔孟以来弘扬儒学的最杰出代表。朱熹弟子黄榦称其师:“继往圣将微之绪,启前贤未发之机,辨诸儒之得失,辟异端之讹谬,明天理,正人心,事业之大,又孰有加于此者? ”[1](P546)黄宗羲称朱熹之学:“致广大,尽精微,而综罗百代矣!”[2](P1495)朱熹一生为学勇猛,学识渊博,著作等身,享誉海内外,其创建的以“理性本体、理性人性、理性方法为基点的理性主义哲学基本结构”[3](P2),或称理性理学,在宋元以后成为官方意识形态并统治中国社会800多年,思想影响波及海外。
若追问朱熹理学的核心思想为何?黄宗羲认为:“其为学,大抵穷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践其实,而以居敬为主。 ”[2](P1504)黄氏认为朱子之学以“穷理致知”为大要。民国时期周予同认为朱熹格物致知中包含有“何以知”“如何以完成其知”这两个问题,而后一个问题“实为朱熹哲学全部精神之所在”[4](P46)。钱穆认为朱子的格物致知理论最值得重视,因这一理论是朱子学乃至宋明理学中的最精彩处,他说:“朱子学之最着精神处正在此。朱子于宋明理学中所以特具精彩处亦在此。其理气两分说之精义,亦于此而见。”[5](P508)陈来认为朱熹 “大力强调并发展了程颐关于格物的思想,使得格物论成了朱子学体系的重要理论特征”[6](P140)。朱熹以“格物致知”为《大学》补传是其最有代表性的思想,且对后世影响最大。[7](P2)确实如此,朱熹的格物致知既有对二程格物思想的继承与发挥,又有对二程以后诸位大儒有关格物思想的甄别与检讨,故而他与前人格物致知有极大不同。格物问题“亦为程朱学派与陆王学派争论之焦点”[4](P46),此也是与陆王心学之根本区别所在。
陆九渊提出 “四方上下曰宇,往来古今曰宙。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宇宙内事,是己分内事。 己分内事,是宇宙事”[8](P273)等观点而创立心学一派,其学“以尊德性为宗”[2](P1885)。其论“格物致知”为“欲穷此理,尽此心也”[8](P149)。朱陆对格物的不同理解,引发后代众多评述,明代王阳明继承并发扬陆九渊之说,批评朱熹格物致知以析“心”与“理”为二物,王氏所谓致知格物,就是“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也”[9](P45)。明末刘辑山说:“格物之说,古今聚讼有七十二家。 ”[10](P771)此处虽不是具体统计数字,但亦可见参与人数之多。钱穆阐述朱熹思想中以“格物致知”最受后人重视与争议,他说:“朱子思想,以格物穷理为最受后人之重视,亦最为后人所争论。其论此之最该括精要语,则见于《大学章句》之格物补传。”[5](P504)
朱熹格物致知论之所以备受争议,乃是因其理论前后不断发展变化,逐渐完善,而且前后思想也并非完全一致,甚至还有相互矛盾处,正是这样,才显示出其格物致知论的复杂与丰富。王阳明曾作《朱子晚年定论》,搜集一通朱熹中年书信为据,以为朱熹晚年已放弃前说,而归入心学之列,“复取朱子之书而检求之,然后知其晚岁固已大悟旧说之非,痛悔极艾,至以为自诳诳人之罪,不可胜赎”[9](P120)。阳明考据错误,前人早已详细指出,但朱熹思想自三十五岁开始至四十岁,有一重大转折,确是实情,而促成这一转折原因有两大方面:一是与张钦夫论已发未发时钦夫提出“敬”字工夫的启发;二是编纂二程遗书过程中对程颐思想中“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的吃透与领悟,而后一方面最终促成了朱熹思想的转变。这一转折表现在重新重视涵养工夫,其中包含了对以前忽略了涵养工夫的愧悔,后朱熹朝着这一方向一直向前,直至六十岁时完成了《大学章句》《大学或问》,朱熹格物致知思想也趋于成熟。
二、朱熹早年之格致思想
朱熹在《大学或问》中将涵养本源提到格物致知之本的高度,说明朱熹对居敬涵养的重要性已经有明确认识,然朱熹在三十五岁前之格物论中未提及涵养,不仅如此,此时朱熹还明显忽视涵养。
(一)以《大学》之序释格物致知
朱熹少时受教于家庭,父亲朱松因与秦桧政见不同而闲居在家,朱松曾师从程门再传弟子罗从彦,与延平李侗乃同门,朱松得伊洛之学不传之遗意,摈弃浮华而趋于本质,“日诵《大学》、《中庸》之书,以用力于致知诚意之地”[1](P175),父亲对朱熹定然产生一些影响,朱熹十几岁时,便于“禅道、文章、楚辞、诗、兵法”[1](P179)都广有涉猎,十七八岁就下大力气诵读《大学》《中庸》,吃了不少苦头,可见这时就已经读过《大学》中格物致知。1153年,二十四岁的朱熹初见李延平,好高谈阔论,李侗只是摇头说不是,朱熹开始怀疑李侗之学,李侗让朱熹先读儒家经典,朱熹后来对学生赵师夏回忆说:“余之始学,亦务为笼侗宏阔之言,好同而恶异,喜大而耻于小,于延平之言,则以为何为多事若是,天下之理一而已,心疑而不服。同安官余,以延平之言反复思之,始知其不我欺也。”[11](P354)
朱熹二十四岁至二十七岁任同安主簿期间作《策问》①三十三条。[5](P529)其中有一条论述格物致知:
问:《大学》之序,将欲明明德于天下,必先于正心诚意,而求其所以正心诚意者,则曰致知格物而已。然自秦汉以来,此学绝讲,虽躬行君子时或有之,而无曰致知格物云者。不识其心果已正、意果已诚未耶?若以为未也,则行之而笃,化之而从矣。以为已正且诚耶?则不由致知格物以致之,而何以致其然也?愿二三子言其所以而并以致知格物之所宜于用力者,为仆一二陈之。[12](P3572)
朱熹从《大学》的顺序上论及格物致知,并勉励学子当从格物致知处用力,同样,二十七岁作的《一经堂记》,也是从这个方面提及格物致知:
曰:予闻古之所谓学者非他,耕且养而已矣。其所以不已乎经者,何也?曰将以格物而致其知也。学始乎知,惟格物足以致之,知之至,则意诚心正,而《大学》之序“推而达之”无难矣。若此者,世亦徒知其从事于章句诵说之间,而不知其所以然者,固将以为耕且养者资也,夫岂用力于外哉
以上两条是现存所见朱熹著作中最早论及格物致知,这说明朱熹在同安为官时,已经在李侗导引下,开始从《大学》中去探讨格物致知。
朱熹三十三岁,李侗阅读了朱熹准备给孝宗上的封事并提出建议:“封事熟读数过,立意甚佳。”[11](P334)朱熹在封事中批评孝宗皇帝讽诵文章、记诵辞藻,非能探寻出治道之要,批评其阅读《老子》《释氏》之书,也不能通贯本末大中,而真正圣贤帝王之学,必始于格物致知,朱熹说:
是以古者圣帝明王之学,必将格物致知以极夫事物之变,使事物之过乎前者,义理所存,纤微毕照,瞭然乎心目之间,不容毫发之隐,则自然意诚心正,而所以应天下之务者,若数一二、辨黑白矣。苟惟不学,与学焉而不主乎此,则内外本末颠倒缪戾,虽有聪明睿智之资、孝友恭俭之德,而智不足以明善,识不足以穷理,终亦无补乎天下治乱矣。[13](P572)
朱熹指出格物致知可探究事物之变,可察觉毫发之隐,做到格物致知,必然能正心诚意,故而他又说:“盖‘格物致知’者,尧舜所谓精、一也。‘正心诚意’者,尧舜所谓执中也。自古圣人口授心传而见于行事者,惟此而已。 ”[13](P572)朱熹此时说“格物致知”就是尧舜所言之“精、一”,其实就是舜所言之“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中的“惟精惟一”,朱熹认为《中庸》一书开始所言正是一理,而其中散为万事,后又归于一理,而此理“放之则弥六合,卷之则退藏于密”[14](P32)。这时朱熹就是在李侗“理一分殊”思想影响下阐释“格物致知”,认为天下万物道理虽各不相同,但事物必各有其理,一理散入万事万物,格尽万事万物终能穷理。朱熹阐明格物致知对于君王治政之重要,兼提及格物致知在于心之精一,但并未阐述何以能心之精一。次年,朱子再次上奏折孝宗,其中论到格物致知:
大学之道,……然身不可徒修也,深探其本则在乎格物以致其知而已。夫格物者,穷理之谓也。盖有是物必有是理。然理无形而难知,物有迹而易睹,故因是物以求之,则应乎事者自无毫发之谬。是以意诚、心正而身修,至于家之齐、国之治、天下之平,亦举而措之耳。[13](P631)
此次是从大学进学顺序来论及格物致知,指出格物致知对于正心诚意、修身治国之重要意义。此段时间内,朱熹有关格物致知之论述,都未提到格物需要涵养功夫。究其原因有二:一是朱熹对章句训诂之偏好,二是朱熹对李侗提倡静坐涵养的方式并不认同。
(二)格致功夫中未重视涵养
李侗是个极有涵养之人,据载:“受学罗公,实得其传,同门皆以为不及,然乐道不仕,人罕知之,沙县邓迪天启尝曰:愿中如冰壶秋月,莹澈无暇。”[1](P180)寥寥数语,一位大隐至人跃然眼前,纯粹洒落,颇具光风霁月之姿。他极力引导朱熹涵养气象,然朱熹依然对文字章句产生浓厚兴趣。
朱熹二十八岁,此年六月,李侗致信朱熹让其要用力涵养,说:“承喻涵养用力处,足见近来好学之笃也。甚慰甚慰!但常存此心,勿为他事所胜,即欲虑非僻之念自不作矣。孟子有夜气之说,更熟味之,当见涵养用力处也。于涵养处着力,正是学者之要,若不如此存养,终不可为己物也。 更望勉之。 ”[11](P309)朱熹二十九岁,李侗致信朱熹,依然敦促其要涵养洒然气象,“大率须见洒然处,然后为得。 虽说得行,未敢以为然也”[11](P313)。然而朱熹对于章句训义非常用力,致书李侗,问《论语》中“亦足以发”之义,李侗引用“起予者商也”为证以启发朱熹,指出二者之不同。朱熹深思再三,认为二者虽有浅深之异,但并未体悟到其完全不同处,请教李侗再详细说之。李侗解释,要体悟这两句之不同,先得从颜回与子夏之气象不同处体会:“先玩味二人气象于胸中,然后体会夫子之言‘亦足以发’与‘起予者商也’之语气象如何。颜子深潜纯粹,于圣人体段已具,故闻夫子之言,即默识心融,触类洞然,自有条理。 ”[11](P313)这里,李侗从颜回与子夏之涵养不同处,教导朱熹当从涵养处用力,颜回因涵养较子夏好,故能发明孔子之道。
朱熹三十二岁,李侗致信朱熹,认为朱熹涵养依然不足:“喻及所疑数处,详味之,所见皆正当可喜,但于洒落处,恐未免滞碍。”[11](P330)朱熹三十三岁时致信说自己处事困扰,李侗让其从静坐中体会:“承谕处事扰扰,便似内外离绝,不相该贯。此病可于静坐时收摄,将来看是如何,便如此就偏着处理会,久之知觉,即渐渐可就道理矣。”[11](P331)同年,朱熹问仁,李侗批注云:“推测到此一段甚密,为得之。加以涵养,何患不见道也。”[11](P336)
朱熹三十四岁,李侗致信朱熹问涵养:“近日涵养,必见应事脱然处否?须就事兼体用下工夫,久久纯熟,渐可见浑然气象矣。”[11](P339)朱熹表弟去世,朱熹心中愧悔忧伤,李侗教诲,责己之心可有,但不能常存于胸中不去,此乃过之:“若来谕所谓似是于平日事亲事长处,不曾存得恭顺谨畏之心,即随处发见之时,即于此处就本源处推究涵养之,令渐明,即此等固滞私意当渐化矣。”[11](P339)李侗指出朱熹愧悔过度乃因为涵养有缺所致。
(三)早年并不认同“静中存养”
通过以上梳理可知,至朱熹三十四岁,李侗去世,朱熹一直都勤于章句训诂,尽管李侗也一直教诲他要增进涵养,李侗对涵养方式解释为静坐:“明道教人静坐,李先生亦教人静坐。看来须是静坐,始能收敛。 ”[11](P345)这一方式并未得到朱熹认同,朱熹晚年就认为李侗以终日静坐的方式来体验天地万物之道,有失偏颇。学生问:“先生作《李先生行状》云:终日危坐,以验夫喜怒哀乐之前气象为如何,而求所谓中者。与伊川之说若不相似。 ”[11](P347)朱熹回答:“这处是旧日下得语太重。今以伊川之语格之,则其下工夫处,亦是有些子偏。只是被李先生静得极了,便自见得是有个觉处。不似别人,今终日危坐,只是且收敛在此,胜如奔驰。若一向如此,又似坐禅入定。 ”[11](P347)因为朱熹并不认同静坐方式,尽管此时有李侗之反复敦促,朱熹依然对涵养不够重视,朱熹晚年也回忆说:“李先生当时说学,已有许多意思,只为说‘敬’字不分明,所以许多时无捉摸处。”[1](P215)朱熹后来认为自己当时缺失涵养,“旧失了此物多时,今收来尚未便入腔窠,但当尽此生之力而后已”[1](P215)。
李侗一直教导朱熹要在静坐中存养,但因朱熹对这一方式不太认同,他一直都在章句中求索。在朱熹二十八岁时,就曾致信李侗询问过对程颐“所谓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之理解,李侗回答不甚分明,以致二人都未对这一问题引起足够重视,李侗回答道:“又见喻云伊川所谓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考之《大学》之序则不然。如夫子言非礼勿视听言动,伊川以为制之于外,以养其中数处,盖皆各言其入道之序如此。要之,敬自在其中也,不必牵合贯穿为一说。 ”[11](P320)李侗认为程颐的所言“敬”与《大学》顺序不同,认为这都是谈入道之序。对于朱熹论述的“所谓但敬而不明于理,则敬特出于勉强,而无洒落自得之功,意不诚矣”[11](P320-321)。 李侗回答:“洒落自得气象,其地位甚高。恐前数说,方是言学者下工处,不如此则失之矣。由此持守之久,渐渐融释,使之不见有制之于外,持敬之心,理与心为一,庶几洒落尔。”[11](P321)李侗只是强调说要存养洒然气象,但如何存养?除了静坐之外,他并不能提供更好方式,说来说去难免堕入虚无缥缈。最后李侗又以自身持守为例,告诉涵养持守之重要:“某自闻师友之训,赖天之灵,时常只在心目间,虽资质不美,世累妨夺处多,此心未尝敢忘也。 ”[11](P321)李侗是极有涵养,但如何涵养,朱熹却难以领悟。
三、朱熹格致思想之转折
朱熹三十五岁至四十岁之间,思想经历两次转折,陈来称这两个转折叫做丙戌之悟和己丑之悟[3](P159,173),丙戌年,朱熹三十七岁,致信张钦夫,主要探讨体用关系、理一分殊等问题。同年在与何叔京的书信中重点探讨天理人欲问题。此年还作《观书有感》出示友人鉴赏,以表明自己悟道有得。朱熹三十九岁时,编成《程氏遗书》,随着对二程书籍的精细研读,领悟了“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内涵后,正式确立涵养为格物之本的思想。
(一)张栻“敬”为格物之道的影响
随着李侗去世,朱熹进学也步入茫然期,其在三十五岁时,致信朋友说:“熹天资鲁钝,自幼记问言语不及人。……竟以才质不敏,知识未离乎章句之间。虽时若有会于心,然反而求之,殊未有以自信。”[15](P1700)朱熹追忆自己求学历程,曾出入佛老十余年,后才亲道,然一直以来都游离于章句之间,虽然时有所悟,但并不自信。又在致信另一位友人时,称自己格物毫无长进,“熹自延平逝去,学问无分寸之进,汩汩度日,无朋友之助,未知终何所归宿。迩来虽病躯粗健,然心力凋若,目前之事十亡八九。至于观书,全不复记,以此兀兀,于致知格物之地,全无所发明。”[15](P1730)此年秋九月,魏公张浚卒,朱熹哭悼,与其子张栻于舟中共处三日。朱熹称赞张栻“其名质甚敏,学问甚正,若充养不置,何可量也”[1](P195)。此后十数年,朱熹与张栻交往密切,书信频繁,1167年,朱熹三十八岁时还亲到长沙造访,二人同登南岳衡山,在诗歌酬唱之余,便是探讨哲学问题诸如已发未发、太极之义等。
张栻说:“盖万事具万理,万理在万物,而其妙著人心。……致知,所以明是心也;敬者,所以持是心而勿失也。故曰‘主一之谓敬’,又曰‘无适之谓一’。”[16](P938)张栻以致知是明心之道,持敬也是持心勿失,故而认为持“敬”也为格物之道。[7](P38)朱张二人频繁论学,张栻思想对朱熹有很大触动,朱熹后来回忆说:“余早从延平李先生学,受《中庸》之书,求喜怒哀乐未发之旨,未达而先生没。余自窃自悼其不敏,若穷人之无归。闻张钦夫得衡山胡氏学,则往从而问焉。钦夫告余以所闻,余亦未之省也,退而沉思,殆忘寝食。 ”[12](P3634)朱熹三十七岁时在对友人书信中说:“某块坐穷山,绝无师友之助,惟时得钦夫书问往来,讲究此道,近方觉有脱然处,潜味之久,益觉日前所闻于西林而未之契者,皆不我欺矣,幸甚!幸甚!元来此事与禅学十分相似,所争毫末耳。 然此毫末却甚占地步。 ”[17](P4748)朱熹此时觉察出张栻之学与禅学相似,其实就是指张栻的心学偏向,体现在格物上便是更多关注心之作用,“格之为言,感通至到也。……所谓格也,盖积其诚意,一动静,一语默,无非格之道也”[16](P461),张栻格物论有明显心学偏向。同时张栻之学因受其师胡文定影响,认为体察在涵养之先,“南轩从胡氏之学,先察识,后涵养,不言未发”[1](P426),因为张栻天资甚高,故其可以略去涵养工夫,但平常学子,却会受到其害,朱熹三十九岁时致信朋友说:“钦夫见处卓然,从游之久,反复开益为多。但其天姿明敏,初从不历阶级而得之,故今日语人,亦多失之太高。湘中学子从之游者,遂一例学为虚谈,其流弊亦将有害,比来颇觉此病矣。别后当有以救之。然从游之士,亦自绝难得朴实头理会者,可见此道之难明也。”[18](P1923)朱熹指出张栻因为天资高,故可以不循序进学,而其从学者,若效仿如此,则会不注重涵养朴实工夫,而沦为虚谈之辈。尽管朱熹后来渐觉张栻有些偏,但当时确受其影响,“这种强调从已发入手,先察识后涵养的方法表现出朱熹当时受到湖湘之学的明显影响,而与李侗用力于未发,重在涵养的方法相距甚远”[3](P165)。
此间,虽有张钦夫等湖湘学子相与论学,又有蔡季通等弟子与朱熹相互启发,但朱熹依然对已发未发、天理人心等问题并非全然冰释,他致信友人问询道:“不审别来高明所进复如何?向来所疑,定已冰释否?若果然见得分明,则天性人心、未发已发,浑然一致,更无别物。由是克己居敬,以终其业,则日用之间亦无适而非此事矣。”[18](P1803)从其所问中,可见朱熹此时对这些哲学问题并未有高明之见。朱熹真正通透这些问题是在《程氏遗书》编成以后。
(二)二程“主敬”思想之影响
朱熹三十九岁编成《程氏遗书》,其中总结二程思想为:“先生之学,其大要则可知已。读是书者,诚能主敬以立其本,穷理以进其知,使本立而知益明,知精而本益固,则日用之间,且将有以得乎先生之心,而于疑信之传,可坐判矣。”[12](P3625)朱熹明确指出二程核心思想是“主敬以立其本,穷理以进其知”。清代王懋竑说:“按程子‘涵养须用敬’二语,庚寅(1170,朱子四十一岁)始特拈出,而戊子(1168,朱子三十九岁)《遗书序》已云‘主敬以立其本,穷理以进其知’,即此二语之指也。 ”[1](P431)可见这时提出的“主敬以立其本,穷理以进其知”就是对程颐的“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的领悟。这终于解决了一直困扰朱熹的“涵养”与“格物”之间的矛盾。朱熹在答友人的书信中论述道:“‘敬’字之说,深契鄙怀。只如《大学》次序,亦须如此看始得。非格物致知,全不用诚意正心,及其诚意正心,却都不用格物致知。但下学处须是密察,见得后便泰然行将去,此有始终之异耳。其实始终是个‘敬’字,但敬中须有体察工夫,方能行著习察,不然兀然持敬,又无进步处也。观夫子答门人‘为仁’之问不同,然大要以敬为入门处,正要就日用纯熟处识得,便无走作。非如今之学者,前后自为两段,行解各不相资也。近方见此意思,亦患未得打成一片耳。”[18](P1923)朱熹指出“敬”字工夫须要体察,也是“为仁”之入门工夫,要在日用中养得,“敬”要贯穿于为学始终,而不能似当时学者,截断为二,行知不一。
朱熹自编《中和旧说》②当作于朱熹三十九岁时[3](P166),此编辑录当年论学书信,朱熹四十三岁时为其作序,回顾自己求学心路历程。关于中和问题,几经曲折,依然不解,后朱熹“则复读取程氏书,虚心平气而徐读之,未及数行,冻解冰释,然后知情性之本然、圣贤之微旨,其平正明白乃如此。而前日读之不详,妄生穿穴,凡所辛苦而仅得之者,适足以自娱而已。”[12](P3635)朱熹体悟后,再致信张钦夫及同论者,只有钦夫深以为然,其余人则或信或疑,故而朱熹感叹:“夫忽近求远,厌常喜新,其弊乃至于此,可不戒哉!……独恨不得奉而质诸李氏之门,然以先生之所已言者推之,知其所未言者,其或不远矣。”[12](P3635)朱熹指出当下学者之病即在于涵养缺失,多好远舍近、厌旧喜新。而这正是当年李侗谆谆告诫自己的,所以朱熹觉得当奉与李门,以示愧疚。
朱熹体悟中和有得后,即致信张栻等湖湘学者:“然未发之前,不可寻见,已发之后,不容安排。但平日庄敬涵养之功至,而无人欲之私以乱之,则其未发也,镜明止水,而其发也,无不中节矣。……故程子之答苏季明,反复论辨,极于详密,而卒之不过以‘敬’为言。”[19](P3130-3131)这里朱熹认为人心之正,乃因性情之德,而全赖平日涵养之功,故程子以“敬”来做涵养工夫。
(三)朱熹持“涵养须用敬”与友论学
朱熹整理《程氏遗书》完毕,经常持“涵养须用敬”致信与朋友论学,他四十一岁在《答刘子澄》书中云:“程夫子曰:‘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此二言者,体用本末,无不该备。试用一日之功,当得其趣。夫涵养之功,非他人所得与,在贤者加之意而已。若致知之事,则正须友朋讲学之助,庶有发明。”[15](P1534)同年,他在《答陈师德》书中说:“示喻格物持敬之方,足见乡道不忘之意,甚善甚善。持敬正当自此而入,至于格物,则伊川夫子所谓穷经应事、尚论古人之属,无非用力之地。若舍此平易显明之功,而比搜索窥伺无形无际之境,窃恐陷于思而不学之病,将必神疲力殆而非所以进于日新矣。 ”[19](P2671)他在《答林泽之》书信中称赞其所举伊川格物说极好:“所举伊川先生格物两条,极亲切。上蔡意固好,然却只是就见处。今且论涵养一节,疑古人直自小学中涵养成就,所以大学之道只从格物做起。……大抵‘敬’字是彻上彻下之意,格物致知乃其见节次进步耳。 ”[18](P1978-1979)朱熹认为古人乃从小学中涵养成就,所以大学才从格物说起,而今人不于涵养上用功,故而只知益思虑知识寻求,其实并无日用根据,没有循序渐进。朱熹受程颐“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的思想影响。
朱熹自整理程氏遗书中“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语,后一直以涵养居敬来论格物致知,晚年与学生论学,更是明确指出“敬”为圣学之第一要义:“‘敬’字工夫,乃圣门第一义,彻头彻尾,不可顷刻间断。 ”[20](P371)还指出“敬”为为学纲领:“‘敬’之一字,真圣门之纲领,存养之要法。 一主乎此,更无内外精粗之间。 ”[20](P371)“敬”如此重要,乃是因为其为涵养本源的基本工夫,一旦缺失,必然误入歧途,《语类》中还记录朱熹以当世之人不曾做小学工夫,而一旦接触大学,便恍惚无措,故而劝慰学者当从持敬开始,做好小学工夫,然后方能致知格物,他说:“明德,如八窗玲珑,致知格物,各从其所明处去。今人不曾做得小学工夫,一旦学大学,是以无下手处。今且当自持敬始,使端悫纯一静专,然后能致知格物。”[20](P422)诚如王懋竑所说:“自庚寅(1170,朱子四十一岁)拈出程子‘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两语,学问大指定于此。”[1](P421)此后三十年,朱熹一直认为涵养为格物致知之本,持“敬”须贯彻于为学始终。
四、朱熹格物思想之成熟
朱熹六十岁时作《大学章句》,将《大学》古本分为“经”“传”二部,他认为《大学》“传”中的“格物致知”释义已经亡佚,为求文本完整,朱熹“取程子之意以补之”,曰:“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也……此谓物格,此谓知之至也。 ”[14](P20)这段文字共 157 字,就是著名的朱熹以“格物致知”为《大学》补传。朱熹唯恐人们不能更好领悟《大学》要领,故以问答方式对《大学章句》作了进一步阐述,这就是《大学或问》,这里有对“格物致知”的详细解释,曰:“吾闻之也,天道流行,造化发育,凡有声色貌象而盈于天地之间者,皆物也……必其表里精粗无所不尽,而又益推其类以通之,至于一日脱然而贯通焉,则于天下之物,皆有以究其义理精微之所极,而吾之聪明睿智,亦皆有以极其心之本体而无不尽矣。 ”[14](P526-528)这段文字共 818 字,在朱熹格物致知论中最严密周备,是其格物思想之成熟表现。这一论述在扩充总结二程格物致知论之基础上提出,为说明格物致知之途径和方法,朱熹引用《二程遗书》所言十条,“此十条者,皆言格物致知所当用力之地,与其次第功程也”[14](P526)。紧接着,朱熹另又引《二程遗书》《外书》所言五条,指明格物致知之本:
又曰:“格物穷理,但立诚意以格之,其迟速则在乎人之明暗耳。”又曰:“入道莫如敬,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又曰:“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又曰:“致知在乎所养,养知莫过于寡欲。”又曰:“格物者,适道之始,思欲格物,则固已近道矣,是何也?以收其心而不放也。”此五条者,又言涵养本原之功,所以为格物致知之本者也。[14](P526)
朱熹引用二程言语,认为格物致知也并非随意就可以去格,须立诚意去格,也并非是任何人都可以去格,需要有一定基础,这就是涵养。朱熹据此明确提出涵养便是格物致知之本,这一涵养就是小学工夫,而小学乃为大学之根基。在《大学或问》中,有人问朱熹讲解大学之道,为何还要考察小学之书?朱熹回答认为:学问固然有大小区别,但是道理则是一致。“是以方其幼也,不习之于小学,则无以收其放心,养其德性,而为大学之基本。及其长也,不进之于大学,则无以察夫义理,措诸事业,而收小学之成功。……今使幼学之士,必先有以自尽乎洒扫应对进退之间,礼乐射御书数之习,俟其既长,而后进乎明德、新民,以止于至善,是乃次第之当然,又何为而不可哉?”[14](P505-506)故而朱熹主张:幼年时经历小学阶段养德收心,主要做法为洒扫应对进退、礼乐射御书数,这便为大学打下基础,而大学阶段主要是考察义理、成就事业,则是对小学之提升,学习必须循序渐进,决不可躐等陵节。
小学之收心养德,亦即涵养本原之功,如何涵养?朱熹认为具体做法就是“敬”,敬以直内,义以方外,敬应贯彻于圣贤学问之始终。朱熹说:“盖吾闻之,敬之一字,圣学所以成始而成终者也。为小学者,不由乎此,固无以涵养本原,而谨夫洒扫应对进退之节,与夫六艺之教。为大学者,不由乎此,亦无以开发聪明,进德修业,而致夫明德新民之功也。 ”[14](P506)朱熹指出,在小学阶段,用敬可以涵养本源,大学阶段,用敬可以开智成德。学者当持敬以守,则能固本达于圣学之域。有人问敬为何要贯穿于为学之始终,“敬之所以为学之始者然矣,其所以为学之终也,奈何?”朱熹明确回答:“敬者,一心之主宰,而万事之本根也。……然则敬之一字,岂非圣学始终之要也哉。 ”[14](P506-507)朱熹以敬为一心之主、万事之根,小学以此开始,大学以此而终,一以贯之,此心既立,则格物致知才得以可能,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不可一日离“敬”。
总之,朱熹格物致知论受到程颐之“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思想影响,认识到 “敬”之“涵养”功夫在进学、进道、成人中的本体地位,是从整个为学的角度审视格物致知,对涵养加以重视,认为涵养当贯穿于为学始终,亦即“涵养为格物致知之本”。
注释:
① 钱穆以朱熹此《策问》作于同安任上的翌年,或第三年,钱氏认为这是朱熹现存所见著作中最早论及格物致知。
② 《中和旧说》当作于朱熹三十九岁时,参见陈来《中和旧说年考》。
[1]朱熹.朱子全书:第 27 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2]黄宗羲,全祖望.宋元学案[M].北京:中华书局,1986.
[3]陈来.朱子哲学研究[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4]周予同.朱熹[M].上海:上海商务印书馆,1929.
[5]钱穆.朱子新学案:第 2 册[M].台北:三民书局,1971.
[6]陈来:宋明理学:第 2 版.[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7]乐爱国.朱子格物致知论研究[M].长沙:岳麓书社,2010.
[8]陆九渊.陆九渊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0.
[9]王阳明.王阳明全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10]刘宗周.刘宗周全集:第1册[M].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1997.
[11]朱熹.朱子全书:第 13 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12]朱熹.朱子全书:第 24 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13]朱熹.朱子全书:第 20 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14]朱熹.朱子全书:第 6 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15]朱熹.朱子全书:第 21 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16]张栻.张栻集:第 2 册[M].北京:中华书局,2015.
[17]朱熹.朱子全书:第 25 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18]朱熹.朱子全书:第 22 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19]朱熹.朱子全书:第 23 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20]朱熹.朱子全书:第 14 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