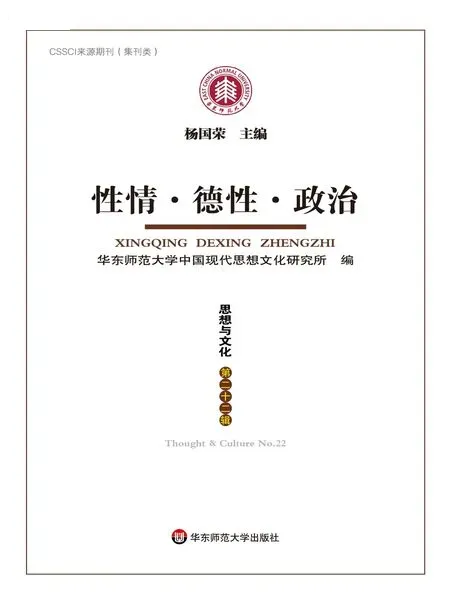文学研究还有未来吗?
——被糟蹋的方法的象征*
●
当今大学的文学系学生如果对该学科的功能究竟是什么感到有些迷惑不解的话,这情有可原。文学研究到底是什么?是历史,是哲学的分支,还是修辞研究?抑或它旨在培养在道德或技术意义上更好的读者?文学研究不是学习如何写作的,那是创意写作项目(MFA)的任务。人们可能求助于该学科的历史来搞清楚这个问题,但这同样会产生困惑。研究和批评方法的历史本身就是文学研究的分支领域,人们能找到的有说服力的论证适用于大部分目的。
事实上,你对文学研究是什么或应该是什么的观念常常取决于你在哪里上大学。某些人物的形象在这所大学的想象中要比在那所大学更为高大。哥伦比亚大学的文学研究历史肯定包括莱昂纳尔·特里林(Lionel Trilling)和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而在耶鲁大学,谱系需要解释从威廉·维姆萨特(William Wimsatt)到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再到保罗·德·曼(Paul de Man)的转变过程。当今在耶鲁大学教书的人几乎没有人想宣称这些前辈还有影响力,但这个事实本身也是故事的组成部分。影响力往往很狡猾,而且很少直截了当。不过,即便完美的谱系也并不意味着,这些人主张的方法和传统会被一代一代传承下去。其实,没有人真正测量过如何阅读、理解文学的方法在文化繁衍和传播中到底有多么准确和有效。现代语言学会(MLA)并没有专利权,也不能垄断阅读实践。变异情况经常出现。大部分人根深蒂固的阅读习惯往往形成于中学教育体系而非形成于大学,这个事实仍然令很多人感到不舒服。
想象“人民的文学研究历史”是像托尔斯泰简要描述的奥斯特利茨战役(Austerlitz,发生在第三次反法同盟战争期间——译者注)和司汤达描述的滑铁卢战役(Waterloo)那样单调乏味和具有反英雄色彩——那是一种混合了各种意图和热诚的民众记事,是充斥着青少年荷尔蒙、误解、怪诞、应征入伍者和平庸者的一百所中学课堂。每位文学批评家如希利斯·米勒(J.Hillis Miller)或米勒(D.A. Miller)都有两百个“幸运的吉姆”和“简·爱”。新学派的创立和新阅读方式的出现等精彩时刻并不比穿梭于学术研讨会、教学例会和考试等数不清的场所更重要。就像传染病的社会史之类,其焦点集中在描述接触和传播的多个要点和途径,以及为传播提供方便和预先阻止传播的条件和实践。
约瑟夫·诺斯的《文学批评的简要政治史》不是这样的书。诺斯的确表达了对伟大人物(或伟大作者)的理论的怀疑,总是警告我们将他们理解为发挥作用的大趋势的“象征”,但是,他的工程仍然是能辨认出名字和学派的思想史。对诺斯的读者而言,书名中的形容词“政治”是在驴子眼前晃悠的胡萝卜。他们是大学内外的左派同志,是在话题转向文化之前就已经丧失理解对方诀窍的人。不过,虽然有精心准备的路标,但诺斯这位耶鲁大学的年轻英语教授的确朝着我幻想的方向迈出若干大跨越,主要是因为他公开表达了对文学学科前进方向的困惑。就像法布里奇奥·德·栋戈(Fabrizio del Dongo)看着在比利时南部城市沙勒罗瓦(Charleroi)一堆被抛弃的沉箱和步枪,不敢肯定自己是否真在战场上一样,诺斯感到纳闷,他和同事们过去这么多年一直被训练要做的事是否真的算“文学研究”。他在探索更大和更重要问题的答案 :文学研究如何逐渐偏离“学院派美学教育项目”,转而拥抱他所说的“历史主义/语境化范式”?
那些最近上大学文学课程的人将本能地明白这种区分,虽然40岁以下的大多数人对于“学院派美学教育项目”在真实生活中到底意味着什么或许并不是很清楚。对那些被排除在学院高额支付墙之外的人而言,历史主义/语境化范式的简单版本可能是这样子 :体裁、风格和叙述的异常情况或许让文学成为特别的记录,用以描绘敢于抵抗、遭受压迫和被边缘化的主体。这正是文学的价值。有时候,文学文本排除或隐藏了这些声音;有时候,它漫不经心地或以编程的方式放大这些声音。对文本阶段的研究能揭露其潜在的或清晰的政治意义。学术研究或文学批评(将这两者合并是诺斯辨认出的问题的一部分)因而是显示在文学内外以具体和特别的方式编码政治欲望的过程。
在历史主义/语境化范式支配下,文学研究已经变成了学习政治史和经济史的另外一种手段而已。
将此称为范式而非项目或者方法的要点是,它暗示,在横跨学院派文学研究的整个纵向和横向范围内,某种基本假设几乎总是在下意识或潜意识里发挥作用。虽然乔尔·法恩曼(Joel Fineman)的心理分析影响下的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研究,米勒的《小说和警察》,保罗·吉尔罗伊(Paul Gilroy)的《黑色大西洋》和李·帕特森(Lee Patterson)对《坎特伯雷故事集》的研究在内容上似乎很少有相似之处,诺斯能够显示——通过引用这些和其他著作绪论的蒙太奇,学者能辨认出过去半个世纪不同文学研究子领域的“经典”或“基础”——所有著作都将文学的形式特征与权力结构分析联系起来。诺斯写到,文学研究旨在制造一种特别的知识或艺术,从而与政治的对话。我们不清楚这种知识最初是不是有关文学的知识,或者该对话是不是在平等地进行。在历史主义/语境化范式支配下,文学研究已经变成了学习政治史和经济史的另外一种手段而已。
虽然历史主义/语境化范式取得了胜利,但诺斯认为,美学教育路径并非被预先规定了的,有可能翻转。20世纪时,大学里曾经短暂存在过一种被称为文学批评的东西,呈现为批评实践和文学形式课程。文学批评与更乏味的学术研究义务平行存在,其中包括档案整理,手稿对比,次要著作的注释性编辑,对阶段、体裁或单个作者的研究等。虽然形式主义和学术研究在当今大学里仍然存在,但过去半个多世纪的支配性趋势一直是,倾向于生产像上文提到的那些将批评与研究结合起来的学术著作,其目标读者群是越来越少的经受类似训练的“本领域专业人士”。
在诺斯的谱系中,我们现在搞文学研究的方式源于主要奠基人物之一——以剑桥大学为基地的“实用批评”的支持者理查兹(I.A. Richards)的一系列误读——有些是一厢情愿,有些是纯粹的错误。将理查兹选为主要奠基人似乎有些怪异。对他的名字稍微有些了解的人可能将他与美国20世纪中期新批评家们所推崇的令人昏昏欲睡的“细读”实践联系起来,或者与英国批评家利维斯(F.R. Leavis)的《细绎》(Scrutiny)小集团联系起来。在电影《死亡诗社》中,令人恐惧的教科书常常扼杀寄宿学校男生的想象力,其名称借自理查兹的新批评对手克林斯·布鲁克斯(Cleanth Brooks)的《理解诗歌》,据说归功于用首字母代表名字的英国人。这些联系和困惑并不仅限于好莱坞。诺斯着手要阐明的是,它们包含了各种各样的固有观念(idéesreçues)和学术速记,它们很深地侵入文学研究中,几乎难以根除。
需要从这个陷阱中挖掘出来的理查兹,是个比后人设想的更为激进的人物。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初期,剑桥大学的辉煌阶段,理查兹感兴趣的是为读者的美学解放奠定经验性基础 :一种文学研究途径,它能将读者从感受到的按特定方式思考和交谈的义务中解放出来。理查兹的《文学批评原理》(1924年)中的很多乏味标题提出了既有嘲弄性却又很吸引人的论证,反对当时碰巧包括美学术语在内的时髦术语。虽然诺斯没有明说,但理查兹提出的往往显得简洁的研究模式,就是对艾略特(T.S. Eliot)咄咄逼人的批评,或者是对瓦尔特·佩特(Walter Pater)和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诱人的风格,以及其他世纪末美学家(fin-de-siècle aesthetes)的解毒剂或所做出的反应。在理查兹到剑桥大学时,这些人仍然是文学界的明星。阅读学生对理查兹的文学练习的反应以及他本人的评论——都收录在1929年出版的《实用批评》中——就是沿着走廊被引领到我们再也无缘拥有的最佳导师面前。我们能听到现在已经消失的对话模式的回声 :对人类智慧的操作所采取的方式,略带嘲讽却并不残酷,语带调侃却没有对立,充满尊重却表示怀疑。
诺斯在自己的研究中并不讨厌某种历史主义/语境化范式,他将理查兹放回到批评和哲学的全球现代主义时刻的基调之中。此时,人们将文学的接受视为思想复杂者的生产形式,而不仅仅是受到压抑和限制的主体的消费。理查兹影响力最大的著作《实用批评》与他亲密的同代人的著作有着共同兴趣,它们都密切关注积极分子和令人充满活力的潜力。其中包括美国实用主义者约翰·杜威(John Dewey)的《经验艺术》、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神秘而异端的《机械再生产时代的艺术作品》以及苏联批评家维克托·什克洛夫斯基(Viktor Shklovsky)的陌生化研究。就其怀疑风格和思想试验方式而言,理查兹有时候也与他在剑桥大学的同事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相似。在理查兹看来,文学批评是两部分组成的舞蹈,被诺斯描述为“诊断”和“治疗”。理查兹将“诊断”部分作为“比较意识形态的现场研究”。他交给学生诗歌和更大著作的片段,但在呈现时没有作者,没有标题,没有日期,也没有其他辅助信息。然后,让学生们写出简单的反应并记录他们阅读片段的次数。接着,他将从语法上描述或分析这些反应以找到趋势、老调重弹、启蒙或者受阻时刻(类似于弗洛伊德的自由联想途径),其勃勃雄心是要提出“人类意见和情感的自然历史”。“治疗”方面则旨在把学生从他们想象中应该采用的文学批评方式的命令中解放出来。正如在心理分析案例中发生的那样,该途径培养了一批学生,他们不加反思地采用理查兹的观察方法和语言,正如他们曾经接受之前批评方法的意识形态一样。任何解放运动都经久不衰地制造自己的教条主义者,但是“实用批评家”至少在理论上是旨在成为“自由人”的同义词,是要自由判断而非愚昧无知地盲从。理查兹相信,人们学习文学不是因为关心已经死亡的文字,而是因为“如果以适当方式走近,艺术应该能提供最好的数据,让我们决定哪些体验比其他体验更宝贵”。
在诺斯的叙述中,这多愁善感的最后一部分似乎已经给理查兹的理论的接受和后来的声誉都带来了很多麻烦。在改编理查兹的练习却忽略或搞乱了其目的的美国新批评学派看来,开放性问题本来是哪些读者经验对特定读者比对其他人更宝贵,现在却变成了哪些著作对一种文化和一个社会比其他著作更宝贵——结果就出现了这样一种观念,即只有那些被认为具有内在价值的作品才能产生宝贵的阅读体验。诺斯指出,这是把理查兹的观点往后扯。从前的阐释性老调重弹再次启动,不过,粘上了理查兹的名字再也揭不下来了(至少直到诺斯或他的粉丝着手编辑理查兹的维基百科网页为止)。
利维斯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英国批评界最具影响力的杂志《细绎》的创办人之一,也是理查兹的学生、同事和他在剑桥大学的继任者。对于利维斯而言,价值逐渐意味着道德价值,体验意味着文本中描述的体验而非读者的文本阅读体验。按照利维斯的思维方式,文学本身就是一种批评,是“人生批评”。如果我们阅读文学首先是发现如何生活,那么,我们阅读也是发现如何不生活。这让利维斯为文本分析实践重新引进了一种伦理清教主义和隐蔽的阶级和种族势利主义,虽然其职业生涯的很大部分致力于提升作家劳伦斯(D.H. Lawrence)的名望,其作品往往被认为是道德败坏的高峰,利维斯则竭力为之辩护。
诺斯暗示,新批评家和细绎群体都试图将文学研究的根源放在文化保守主义基础之上(并非总是政治保守主义),解释美学敏感性的培养等于对其加强限制和管束。虽然理查兹常常发现学生的回应遭到误导或被预先编程,但他对错误的态度要比新批评家威廉·维姆萨特和门罗·比厄斯利(Monroe Beardsley)的态度要宽宏大量得多,他们制订了年轻批评家必须回避的阅读“错误”目录。美国新批评家应该通过遵循正确的阅读实践达到正确的修养水平,这不可避免地意味着正确的道德、社会和美学判断,以此确定文本的价值,从而值得仿效或保存。这种约束性途径不可避免地改造了理查兹的开放性练习,使其转变为有正确答案的考试;一些诗歌和小说被逐渐挑选出来或明或暗地作为经典,用新批评的词汇就是“奏效”。在后来被称为“细读”的实践背后站立着通常的权力关系,无论是课堂之内还是课堂之外,它都排除了本来旨在寻找意义和独立判断的过程。
在这种从方法向教条的转变过程中丢失的是理查兹的研究的某些方面,他的研究在三十多年前就预测到了我们现在所说的文化研究世界观 :
当我们观看一幅图画,阅读一首诗歌或者聆听音乐时,我们做的事与我们在前往画廊途中或者早上穿衣服等事情并没有多大不同。我们身上引发体验的方式不同,作为法则,这种体验更复杂一些,成功的话,还会更统一一些。但是,我们的活动在本质上并没有什么不同。
本质上,诺斯的论证创造出了虚假的二元论,使理查兹与各种各样的反应性“高雅严肃”(high-brow)的美学流派产生失调错位,这些流派与更多关心政治和历史议题的学派尖锐对立。因为实用批评就像细读一样,是被右派和道德化中间派提出的,最终必须遭到左派的否认或者被打入冷宫。最著名的例子是利维斯的学生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的研究。虽然威廉斯在后来的访谈中,描述他那一代接触实用批评时感到“痴迷”和回味无穷,“当时,我们认为有可能将它与我们打算采取的清晰的社会主义文化立场结合起来”,但是,这个观点证明是“可笑的,因为利维斯表现出的文化立场恰恰不是这样”。正如诺斯确立的那样,威廉斯是枢纽性人物,清楚体现了文学研究从剑桥批评派到种种左派历史主义提供的积极参与式批评(《政治与文学》和《新左派评论》、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 Jameson]、后殖民主义理论、女权主义批评和酷儿理论)的转变过程,意料之外地成为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期出现的新历史主义机构性和专业化版本的帮凶。像理查兹一样,威廉斯感兴趣的是他称为“感情结构”的东西,不过,这些是历史研究的对象而非当代分析。艺术仍然提供有价值体验的最好数据,但是,这些体验不是学生自己的生活而是前人的生活。不是为了自己做实用批评,文学的学者型批评家试图解释从前几代人如何做时代的文学和文化批评。
在这些评论中,诺斯对实用批评的命运的描述最具说服力。当他进入四代剑桥学派批评家的论证的细微差别时——包括其美国直接继承人和威廉斯的学生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他就暴露出一些本来可以阐明的可能性和可供选择的道路。如果威廉斯明白,利维斯的版本是对理查兹最初模式的破坏而非其正统形式,情况会怎么样呢?伊格尔顿与其说是通常认为的那种“爱发奇问而无忌讳的儿童”(enfant terrible)倒不如说是“门徒”(bonélève)。如果他用学术生涯更早时更开放的心态去看理查兹,他还会在年老时对批评的命运感到悲观吗?他曾经说过批评“就像茅草屋或木屐舞”,是濒临死亡的艺术。
但是,对理查兹的接受问题仅仅占据了旨在解释上个世纪文学研究短暂瞬间的上半部分。在此范围内,下半部分以飞越风景更高处的方式展开。大块儿大陆的特征更清晰可见——比如有对詹姆逊和莫雷蒂(Moretti)更广阔的鸟瞰——但是,因为很多细节必须通过推测来获得,它有助于人们拥有地上事物的内心地图。这种直接冲上梗概的最高天,并依靠尾注使其充分稳定的做法是一种宏大姿态,很可能令诺斯最博学的读者倾向于做出吹毛求疵的攻击。文学研究的各个独特领域常常充满嫉妒地捍卫自己的领地,为了可怜的课题资助和日益萎缩的教授职位相互竞争,但是它们不过是威廉斯管理下的单个领地的不同方面而已。
无论引起什么样的眩晕,这种观察方式允许诺斯对这个学科的标准历史做出更精彩和更具争议性的修改之一 :文学理论的内衬是通过他称之为“1960年代”的时段而部分完成的。他正确地指出,虽然我们被告知,“理论”被认为是猛犸象,既包括一切又是单个术语,但它指研究文学的各种方法和途径,常常拉扯到相互对立的方向。解构主义和罗兰·巴特式(Barthesian)文本情爱更自然地与批评和细读校准;福柯式以档案为基础的历史和布迪厄社会学(Bourdieusian)则投身于轻易同化训练有素的文学史家和学者。换句话说,当“大陆”理论来到这个场景吹响自己的号角时,历史主义/语境化范式和美学范式之间的分裂已经存在。对于从前的文学研究之历史,如伊格尔顿的或杰拉尔德·格拉夫(Gerald Graff)将20世纪分成三个阶段——理论之前、理论阶段和星云般的多元主义后理论阶段——诺斯建议文学研究遵循同样的政治和文化趋势线,就像更广泛的英美世界那样 :从1919年到1937年是个人和集体解放的长征,此后是遭遇强大反抗的漫长撤退期。诺斯写道 :“既然我们能够调查这个世纪的整体情况,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初期,左派所迈出的一小步到了20世纪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初期成为对右派来说具有决定性的与之决裂的序曲——这次决裂具有决定性的意义,简直等于开启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就像对于解构主义者来说,概念文本之外无物(Il n’y a pas de hors-texte);对于诺斯来说,任何活动都带有全球政治和经济斗争的伤疤。这种坚持也标志着作者沉浸在他竭力反对的支配权力环境中,促使他提出反本能的和令人担忧的主要见解。如果反对实用批评的部分要点是“进行比较意识形态的现场工作”本身就是一种意识形态练习——或者细读让文学系充当了保守主义的堡垒,虽然打着一种幌子,表现出对文本和相关性的讳莫如深和故意的冷漠无情——人们必须承认这个令人感到不舒服的事实,即文学分析的历史主义/语境化范式在当今新自由主义所向披靡的阶段正繁荣发展,无论在大学体系内部还是在整个世界。[注]阅读诺斯的这个章节,让我想起我在1997年申请攻读研究生时的一场对话。受一位教授的影响而爱上波德莱尔、福楼拜、克尔凯郭尔和叔本华,这位教授对我说,不乏真诚的后悔,“你必须准备好变成鄙俗的市侩”。我回答说 :“但是,我已经是不可救药的市侩了。”我的回答太过自信和太不正经,她对我作出警告是正确的。她说 :“还不够。”
用更老一点儿的批评术语,诺斯提出究竟是什么促成了左派内容和新自由主义形式的邪恶共生问题。他在回答这个问题时有很多策略、同情和谨慎,那可以用一篇浓缩的书评表达出来。但是,人们可能将其论证简化为一点,即大学文学批评的“交换价值”,虽然这样说有些不公正。采用历史主义/语境化范式研究文学的学者将自己首先视为学者而非批评家。他们或许根本就不喜欢文学——他们的口味如何与此无关——但是,他们明白其工作是什么,用诺斯从众多当今学者那里借来的非常说明问题的时髦术语来说就是“知识生产”。
用理查兹的同时代人以及他在美国的神交之一肯尼斯·伯克(Kenneth Burke)的话说,文学提供“人生设备”的任务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相反,文学研究这门学科或者专业旨在生产有关文学或过去社会的知识,除了将这种知识传播和传承给一群接受过类似训练的专门人才之外,没有其他明确的目的,而这些专家的资格是根据再生产可接受的“知识形式”的能力来衡量的。即使产生的知识在政治内容上是丰富的,常常故意带有政治性——那种政治内容的使用价值必须被否定或者被遮盖起来,因为在它作为专业著作出现的那个时刻,应该体现出知识与进步之间的模糊启蒙。
这里的模式是科学,但是没有实证性和实践检验因素。从文学研究中产生的知识的可靠性不是被其他机构决定的(在权力的意义上),而是被再生产这种知识的人所决定。这些权威通过公平的和污秽的手段登上本领域的巅峰。这就解释了为什么经过了1960年代的创造冲动之后,最容易复制和最可靠的知识形式历史主义/语境化范式开始占据主导地位,虽然它从来就没有文学性。这也意味着根本没有上帝,只有老板,无论他们是系主任还是院长、教务长、校董或者学校外部的政府机构。这些老板首先是根据生产力判断其研究的价值的。
虽然诺斯发出了对摇摆的或循环的历史研究感到厌倦的信号,但他的读者很难不觉得学界的文学研究已经回到了批评之前(BC)。世界上的“文学”应该仍然存在一个指称对象,它们有内在的价值,只不过这次在本质上是政治的而非美学的。人们研究文学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这些对象。像从前一样,存在经典或者很多经典,虽然古老经典现在更多成为一种索引——要在适当监督下阅读的危险书籍,同时还有用以抵消其影响的反经典论述,而这些论述本身现在也已成为经典。就像从前一样,文本阐释和分析的自由发挥常常被课程内外的权力关系封杀或被附着在上面的经济和地位焦虑而取消。内容姑且不论,我们时代的文学批评原则和实践只是在表面上与新自由主义态度支配下社会的其他情况有所不同而已。
诺斯身陷“游戏中”太多而且太客气了,仅仅对这种显著观察的隐含意思点到为止 :无论内容如何,精英的文学研究都是站在当权者一边反对无权者,只要能维持其“精英”地位就行。贬低美学,并用大数据、知识生产以及其他宏大的文化评估模式取而代之,不过是跟上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发展而已,虽然使用这般方法的大部分教授公开宣称其政治信念如何进步。很多人攻读硕士、博士,一路走来可能怀疑,左派虽然占据大学文学教育的支配性高度,但对整个文化界来说,却不仅没有产生积极后果,反而造成消极的政治后果,最终培养出一代又一代平庸的左派官僚(mandarin),既没有官僚这个词隐含的高深水平,又没有文化资本。
诺斯也不希望以这样阴沉的音符终结他的故事。利用詹姆逊的“政治无意识”,他提出了“批评无意识”,考察了当代学界内外美学教育乌托邦工程的演变轨迹。在这节中谈及的批评家几乎全部是女性或者酷儿,这可能是故意的,也可能只是碰巧而已 :已故的伊芙·塞奇威克(Eve Sedgwick)、伊索贝尔·阿姆斯特朗(Isobel Armstrong,在英国和英联邦之外几乎默默无名,不过是剑桥学派的直接后裔)、劳伦·贝兰特(Lauren Berlant)和米勒(D. A. Miller)。在谈及包括本文作者主办的刊物《n+1》在内的小型杂志竭力为广大读者留下批评空间的堂吉诃德式努力时,作者表现出诊断结论式的成功。更短小的版本是缺乏“强有力支持的机构批评范式”或者与积极的社会运动配合——正如《政治与文学》和《党派评论》早期的情况那样——我们常常过多地发表一些“新闻报道性的”当代作品评论(即故事概要加上某些传统的道德寓意)或者对学术生产的认真解释(像本文)。
在这样的时刻,诺斯工程自我设置的边界暴露出自身的边界本质。我这样说不是因为他批评了《n+1》,若应用到书评部分,其批评还算公正,虽然在规则中可能存在例外情况。而是说,他选择的在政治上属于进步这一边、同时关注个人美学发展的机构批评的例子,似乎因为篇幅而被勒死。这是我们抛弃理查兹批评途径的可感知的最大文化损失。人们必须学习如何做批评,以便知道如何辨认出好的批评家,因为好的批评本身就是文学。诺斯虽然努力在历史主义/语境化范式之外或背景之外思考,但其思考仍然局限在他所描述的范式之内,他的论述能更有技巧地辨认出带有机构性或政治性意义的好思想家,但不是理查兹式的好批评家。
诺斯以从前的“细读”方式,对文学批评的实际文本进行文本风格分析的尝试,正如米勒(D.A. Miller)对简·奥斯丁(Jane Austen)的非人性的精彩把握。那是很好的阐释,但是批评世纪肯定能够产生某种更加激动人心的东西,事实上的确如此。这里有实用批评家的部分名单,他们或者在大学里,或者在大学之外,但书中根本没有提及他们,甚至在尾注里也没有 :兰德尔·贾雷尔(Randall Jarrell)、布莱克默(R.P. Blackmur)、肯尼斯·伯克、哈罗德·布鲁姆、杰弗里·哈特曼(Geoffrey Hartman)、莱斯利·菲德勒(Leslie Fiedler)、诺思洛普·弗莱(Northrop Frye)、玛丽·麦卡锡(Mary McCarthy)、纳托尔(A.D. Nuttall)、弗兰克·科默德(Frank Kermode)、阿尔瓦雷茨(A. Alvarez)、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艾瑞斯·梅铎(Iris Murdoch)、乔治·斯坦纳(George Steiner)、大卫·布罗姆维奇(David Bromwich)、詹姆斯·伍德(James Wood)、阿尔伯特·默雷(Albert Murray)、斯坦利·克罗齐(Stanley Crouch)、韦恩·克斯坦鲍姆(Wayne Koestenbaum)、玛利纳·瓦勒(Marina Warner)、特瑞·卡塞尔(Terry Castle)。这些名字都不是主要与“政治”有关,虽然有些人撰写了政治著作。他们也不像通常设想的那样,从20世纪中期大学里的“机构性批评范式”中受益。诺斯对当今左派的承诺让他们都变成令人讨厌的人是有可能的,但是,我们有理由感到纳闷,忽略这些人的声音的文学批评史是否真的体现出更大的开放心态。
如果人们开始思考诺斯所描述的阶段内大部分文学专业学生乱七八糟的异端教育经验,他叙述的另外一个问题就出现了。“理论年代”或许如诺斯所说被玩得过分了,但仍然真实的是,常见的罗兰·巴特理论、解构主义理论、德国“读者反应理论”等,到现在为止仍然是很多学生对文学批评方法的形式分析和阐释的仅有了解。无论其重要性如何,“理论”现在代表了一整套重要体验,任何新实用批评都离不开它。人们也不能贬低给很多读者的文学和文化体验染上颜色的文本阐释的、宗教的,或隐秘神学方法的持久影响——无论是福音派基要主义类型、《塔木德经》阐释法,还是中西部路德派“更高批评”的残余——它们靠或集中或分散的宗教中学和大学网络维持下来。授予学位的大学加入像现代语言学会这样的机构。过去10年任何看到超级英雄飞舞的人都能告诉你,大部分美国人遭遇了寓言框架内的文化,这种对寓言的口味受到文化产业的滋养,服务于历史主义/语境化范式并得到它的服务。这种范式讲述的是,文学自身就是政治或存在斗争的编码场所。
最后,如果诺斯在回顾这个领域之前接受自己的建议并回到理查兹,结果可能会更好。如果能提出更有说服力的例子,恢复批评家的敏感性仍然是可能的。在阅读《实用批评》时,有两点变得很清楚。一是理查兹觉得好玩儿,或者,如果这个词似乎过于不合时宜,他至少是在开玩笑,既是对学生也是对读者开玩笑。在口吻上,他与诺斯引用的后来的历史主义/语境化范式批评家的对比也非常明显,这或许根本不值得提及,虽然其论证的情感威力取决于我们感受到这种差别的能力。[注]当今的例外是弗朗科·莫雷蒂(Franco Moretti),他的“文学实验室”非常类似理查兹的风格,虽然意图正好相反。在莫雷蒂的练习中,电脑学会思考文学,而学生学会像电脑和计算程序那样思考。理查兹的练习是故意反经典的,也是对学生自认为已经知道的东西的挑战。这是个没有赢家和赌注的游戏,但自己玩得心甘情愿而且非常认真严肃。如果幸运的话,你或许被邀请像这样做些什么。在任何正规教育背景下,这种情况都不大可能会出现。
这个人可能说出他们内心的想法,不用担心分数、晋升、正确答案或者公共舆论。
第二点与学生在对理查兹练习的反应中被揭示出的心理状态有关,虽然理查兹让他们充当在思考文学时颇感沮丧和纠结的例子。这里是标准的亚马逊书评长度的典型例子,主题是不相干的 :
让人想起后伊丽莎白时代的人的抬高声调运动或者故意装腔作势的口音。但是,这是没有思想复杂性的,尤其从隐喻中显示出来。模仿性。这里,运动变得反思更多体验更少;一种故意装填的节奏——受到说教性伪装的影响。华兹华兹?欺骗性的。维多利亚时代中期的诗歌戏剧?有关借来的支柱的常见格言集锦。我冷漠地接受这些命题。它或许是写给《伟大思想日历》的。朗读它,我需要大声说出来,我有些荒诞地感觉到一种道德尊严。
这是1928年或1929年间年轻的英语专业学生(18—20岁)的声音。这里,最令人印象深刻的,除了思考书上若干选择和自我更正的自由之外——与现在大部分学校讲授文学批评的方法相反——是学生对诗歌片段的心理影响的清醒意识,在表达时融合了自我贬损和自信心。这个人可能说出他们内心的想法,不用担心分数、晋升、正确答案或者公共舆论,表达还没有充分形成的个性和敏感性。当今读者已经学会将社会学和文学批评的观察结合起来,他们毫无疑问会怀疑这种口吻是英国上层阶级男性的标志。但是,他告诉我们,选修理查兹实验课程的学生平等地分为男女(其中有我的外婆,她是家族中第一个上大学的人),这种回应是理查兹收集和发表的回应的代表。
若作为历史文献来阅读,《实用批评》显示,一旦社会有了对公共教育的高基线承诺,朝着更大的社会平等迈进,看重个人的成长和发展,不受那些热衷将这种发展用于社会用途和经济用途的观点的影响,为此我们能做些什么来帮助高等教育层次的思想变得更精致、更细腻微妙。它与当今时代的对比实在太明显不过。如果还不算太晚的话,矫正轮船走向的努力在大学文学系的影响范围之外,如果大学文学系(勉强说来还算有)发挥作用的角色空间的话。诺斯的“批评范式”将教学放在学术生产之前。仿佛是命运的捉弄,当今美国高等教育的现状唯一仍然有益的地方是大学附属的针对囚犯的文科教育。像巴德监狱倡议(the Bard Prison Initiative)这样的项目为劳动力市场之外的人提供专业志愿服务(pro bono是拉丁语pro bono publico的缩写,本意是“为了公共利益”——译者注),这些人的需要是获得一定程度的自主性,至少在当时比谋生的需要更大。
应该承认,这些项目的成功是靠师生自我报告的幸福感、成就感和成长来衡量的。应该提出的问题是,为什么这样的教育机会没有在囚犯被抓起来之前给予他们呢?历史主义/语境化范式占支配地位不仅与在最广泛和最抽象意义上的新自由主义占支配地位同时存在,还碰巧与公立学校的私有化、关闭或“瓦解”同时出现。在此方面,约翰·杜威的思想在美国的命运与理查兹的思想同样具有建设性意义。以师生之间集体合作解决问题为基础的教育本来是进步的公共教育蓝图,如今剩下的只是精英中学宣扬的一揽子建议,他们提供杜威式妙方如“教育全面发展的人”、“以解决问题为基础的学习”和“玩中学”。
这显示的是机构重点的变化要比方法或范式上的另一场革命更具紧迫性。我们不仅必须优先考虑本科生教育,而且专业性学位的目标也需要重新设计以便实现对中学教育的承诺。培养公立学校教师的专业“教育”和培养专业人才的“文学”教育的分裂必须沟通融合起来。进入文学院系读研究生、毕业后去当中学老师的人,应该像获得大学终身教授职位或珍贵的研究员身份的人那样,拥有同样多的威望、地位和尊重。研究生录取的选拔方法应该改变,以吸纳那些在性格上和思想上更适合通识教育的人。另一方面,这也要求提升中学教师的地位,要像对待文学教授的著作一样,严肃对待专门讲授文学的老师的技能。
这种情况在非英美国家和社会民主国家已经出现。诺斯的案例说明,新自由主义更多解释了美国和英国当今文学研究的状况,而不是给愿意加入者展示其模式的尝试。《文学批评的简要政治史》不是《人民的文学研究历史》,如书名所示,诺斯指出了一种把文学研究和批评真正以文学的名义与民众结合起来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