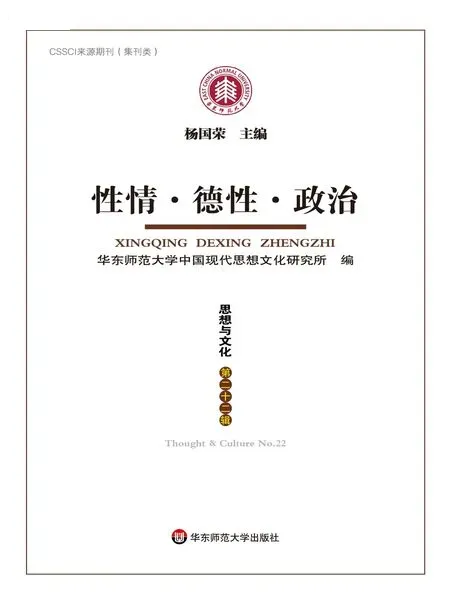论《孟子》中“命”的观念
●
“命”是《孟子》中极为重要的观念,但这一观念在前人的
研究中似乎并未得到足够的重视。试举一例 :戴震《孟子字义疏证》选取了理、天道、性、才、道、仁义礼智、诚、权等诸多概念[注]戴震 :《孟子字义疏证》,北京 :中华书局,1982年,第1—52页。,却没有对“命”进行专题化的讨论。诚然,在《孟子》的文本中,并没有规范化地对“命”进行概念式的规定,因此也没有现成的概念或原理可供直接采纳,但与其相关的思想在文本中却清晰可见。接下来,本文将尝试着分析并归纳出《孟子》中“命”这一观念中所蕴含的思想,并进一步说明,从“命”的观念出发去理解《孟子》的思想具备哪些理论上的优势。
傅斯年先生在《性命古训辩证》中考证了“命”字的来源 :“命之一字,作始于西周中叶,盛用于西周晚期,与令字仅为一文之异形。”、“据此诸器,足征令、命二字之为互用,且为同时并用者。”[注]傅斯年 :《性命志训辩证》,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9、36页。“命”与“令”本来是一字两形,起初它们指的都是君主或天所发的号令或命令,如 :“归纳上列令字之用,不出王令天令二端……曰‘显令’、曰‘丕显休令’、曰‘天子鲁休令’,皆王令也。曰‘文武受令’、曰‘大令’,则天令也。”[注]傅斯年 :《性命志训辩证》,第28页。而许慎《说文解字》曰 :“命,使也。从口令。”段玉裁注 :“令者,发号也。君事也。非君而口使之。是亦令也。故曰命者,天之令也。”[注]许慎撰,段玉裁注 :《说文解字注》,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57页。由此引出一个问题,既然“命”字所含有的意思“令”已然具备,那么,作为后起之文的“命”字有何独特的含义吗?细究起来,最重要的一点在于 :“令”字只指发号施令的一方,具有强烈的主动性质,而“命”则两方兼具,且偏向于受动的一方,即接受命令的一方。[注]对于“命”、“令”两词之间的差异可参照丁为祥 :《命与天命 :儒家天人关系的双重视角》,载《中国哲学史》2007年第4期,第11—21页。“王命”针对的是除了王之外的官员或平头百姓,而“天命”的对象则包括了世间一切生成之物,人间帝王也在其列,如“性自命出,命自天降”(《郭店楚墓竹简·性自命出》),正表明了“命”虽来自于天,但却要在现实世界中的生命体即受动的一方中显示出来。在《孟子》中,“命”字这方面的意义也体现得很明显。《孟子·万章上》曰 :“莫之为而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无为而自为者,天也;不召而自至者,命也。”前一句强调天不言而化生万物,后一句针对的是天所化生的万物(尤其是人),“命”对天所化生的万物而言,并非主动的选择,而是不期而至的降临和下落,亦无推辞不受的可能性。也就是说,天所赋予一个生成物的一切,都可视之为“命”之内容。而《孟子》一书中着重展现的,正是“命”在人类——这种最为独特的生成物——身上所呈现出来的多种面向的特征。
一、 莫非命也 :“命”在《孟子》中的诸多含义
其一,“生-命”义。《诗经》所谓“天生蒸民”是也。人只有出生了之后才有所谓的“命”,但既已“生”了之后,“生”反过来却成了“命”之最基础的含义。这里的“生”,是一种最单纯的规定性。换句话说,由于“命”是天对生成物的赋予,而后者最基本的规定就是“被生成”,说某人出生了,虽然未对他/她做出任何具体的规定,但却是其他任何可能性的基础。
其二,“死-命”义。死亡也是“命”中注定的事情。有的人从《论语》里“未知生,焉知死”(《论语·先进》)这句话中判断儒家只谈生,不论死,认为他们回避了死亡的问题,这是一种误解。实际上死亡问题一直作为一个思考背景体现在儒家思想的方方面面。无生无死的是无限存在着的天,而有限的生命个体既有其生,必有其死,生死本就是一体两面。例如,《孟子·梁惠王上》曰 :“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杀人者也。如有不嗜杀人者,则天下之民皆引领而望之矣。”朱熹对此的解读是 :“盖好生恶死,人心所同。故人君不嗜杀人,则天下悦而归之。”[注]朱熹 :《四书章句集注》,北京 :中华书局,1983年,第207页。又如“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如何使百姓免于横死,从而使民心归附,是孟子劝说人君施行仁政的重要理由之一;此外,《孟子》中多将生死与仁义(舍生取义)[注]《孟子·告子上》 :“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相对,以阐明其对人生价值的独特理解。总之,“命”观念中的死亡义,是孟子思想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当然,《孟子》文本中并未对死亡进行正面的讨论,本文接下来将根据其文本背后的理路和精神,对孟子的死亡观进行简单的构建。
通常人们对于死亡的态度是“不是今天”,它隐藏在时间的某一处,但不是今天。人们会谈论某某人死了,可这件事现在还事不关己;偶尔也会感慨华发已生,时光如梭,但生活依然会按照一如既往的操劳步调行进,不会去想此生的意义或者意识到死亡的逼迫性。这样的视野,并未真正将死亡纳入自身的生命系统中去,人们明白死亡的必然性,但并未使得这一特殊事件成为选择人生路向的重要标尺;而很明显,儒者是意识到死亡的特殊意义的。在每个生命体的生成之始,死亡的可能性就已经存在。也即是说,生之现实性已然蕴含着死之可能性。死亡是随时随地都可能出现的,对于每个单独的个体来说,死亡是别人无法替代的,任何人都不可能从别人那里取走他的死。在某些艺术作品中可以看到,英雄壮士代替自家主公赴汤蹈火,仁人志士为了保护他人而慷慨就义,似乎死亡是可以代替的;但是,暂时逃脱死亡的那些人,迟早还是要面对自身的死亡。因此,正视死亡的一个重大的意义就在于,个体反思自身存在的意义,并从而真正地成为个体。从某个方面来看,死亡是对生命最大的否定,它意味着生命体的完结;但另一方面,恰恰是死亡的可能性肯定了生之可贵。短暂而有限的生命已然是我之全部,那么,怎能不好好地去珍惜?正是因为死亡的不可逃避,儒者才深知时光的可贵,并将这种理解转化为切身的行动。“子在川上曰 :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论语·子罕》)孟子曰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孟子·尽心上》)孟子如此急切地追寻生命的意义与价值,如此努力地宣扬仁政以保全生民之命,亦是基于对死亡的正视和对短暂生命的珍惜。[注]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儒家并非是由对死亡的惧怕而肯定生之意义。对个体生命的过分执着与关注亦是一种“私欲”;天道流行,个体的生灭存亡本来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但不执着于此并不意味着对此完全不加以理会,毕竟“死”是人类这种生成物不得不面对的一种限制,它构成了个体存在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所以给予某种程度上的体认是必要且有意义的。
其三,“时-命”义。这一点也就是所谓的命运,是某个人出生之后所得到的具体的、实质性的限定。已然成为现实存在的个体不再是一种抽象意义上的可能性,而是一个活在特定环境下的活生生的人。这时,他从天禀受的“命”大致有以下几点。首先,作为自然人的生理上的特性,即“口之于味也,目之于色也,耳之于声也,鼻之于臭也,四肢之于安佚也”(《孟子·尽心下》)。人的感官需要欲望上的满足,人的躯体需要物质上的滋养,因此对于自然界有一定的依附关系。其次,人智性上的禀受,所谓“唯上智与下愚不移”(《论语·阳货》),也就是生知、学知、困知的区别[注]《论语·季氏》 :“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儒者看到了每个人在天赋能力上的差异,但这种差异是智性上的,而非德性上的。第三,特定的自然环境。具体个人所降生的时代,都会有那个时代独特的自然境况。如自然灾害的发生,“富岁,子弟多赖;凶岁,子弟多暴”(《孟子·告子上》)。一方面,人类依赖着自然给予我们的物质上的供给,自然“养育”我们;另一方面,正因为这种依赖关系,自然境况对人类来说是一种限定,它的好坏决定了我们的生存可能性。在大灾之年,“民有饥色,野有饿莩”(《孟子·梁惠王上》)。生存都有威胁的时候,智性或德性也就无从发展。最后,特定的社会环境对个体的影响。家庭是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家庭环境对个体的成长有很大影响,孟母三迁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孟子看来,他所处的那个时代已不同于尧舜周公之世,君王好战,攻城掠地而致黎民于倒悬,人祸引来天灾,率兽食人,天怒人怨。而在读书人中,“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孟子·滕文公下》)。这是一个君子很难有作为的时代。
最后,“使-命”义,也就是“性善”也。《孟子》中明言“性善”者不止一处,如《孟子·滕文公上》 :“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又如《孟子·告子上》 :“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乃所谓善也。若夫为不善,非才之罪也。”人之为恶,不是因为本性如此,性本身的材质都是善的;孟子将道德责任纳入了人的本性之中,人生来如此,因此可以说,“性”是命的一个面向。这一点并不同于当时流行的解释。“天下之言性也,则故而已矣。故者以利为本。所恶于智者,为其凿也。”(《孟子·离娄下》)朱熹对“利”的理解是 :“利,犹顺也,语其自然之势也。”[注]朱熹 :《四书章句集注》,第297页。世人将“性”解释为顺,徐复观先生认为这指的是人在不自觉状态下的反复行为,也就是一种生活习性,这同告子所理解的“生之谓性”类似。孟子曰 :“口之于味也,目之于色也,耳之于声也,鼻之于臭也,四肢之于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谓性也。仁之于父子也,义之于君臣也,礼之于宾主也,智之于贤者也,圣人之于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谓命也。”(《孟子·尽心下》)天下人把感官欲望看作“性”,但孟子认为它们能否得到满足,在天不在我,因此应被视之为“命”;而仁义礼智,世人把它们看作是“命”,孟子却认为人们只要反求诸己,则能实现这些,因此应该被视为“性”。这里可以看出,传统中被视作“性”的内容,在孟子思想中是包含在“命”之中的,而孟子的“性”仅仅用来表示人天赋的道德使命。
而之所以说“性”也是“命”之一方面,首先是因为“性”是天赋予人的,根据前面提到的孟子对命的规定“莫之为而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可判断此观点不虚。其次,孟子曰 :“莫非命也,顺受其正。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岩墙之下。尽其道而死者,正命也。桎梏死者,非正命也。”(《孟子·尽心上》)身陷牢狱而死与知性尽道而死都是命的表现;又有 “天命之谓性”(《礼记·中庸》),“性自命出,命自天降”,都很明确地说“性”从“命”而来,是“命”之一种。
孟子认为人本性是善的,是基于两方面的证据。第一,人的心中皆有善端。“端,绪也”,即头绪,条理。“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孟子·公孙丑上》)见小孩要掉入井中,当下的那种不忍和惊慌不是思虑的结果,也没想着有什么利益好处,而是自然生发的情感反应。可见,人天然地就有善心,这一点足以证明其背后作为基础的善性的存在。“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孟子·告子上》),而小孩天生地知道爱亲敬长,同理也。朱子曰 :“天地以生物为心,而所生之物因各得夫天地生物之心以为心,所以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也。”[注]朱熹 :《四书章句集注》,第237页。人作为天的生成物,具有仁民爱物之心。第二,人不同于禽兽而具有道德能力,还在于人心能思。“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物交物,则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此天之所与我者。”(《孟子·告子上》)心有思的功能,所谓思者,段玉裁在《说文解字注》中说 :“思心曰容,谓五者之德。……谓之思者,以其能深通也。”[注]许慎撰,段玉裁注 :《说文解字注》,第501页。耳目等感官由于不能思虑,因此容易被物所遮蔽引诱,而心通过思虑则能够摆脱物欲的遮蔽,通于天道,参赞天地的化育。“善端”所体现的是仁之本,而思虑之心则是义之路,通过心思之求之,将“善端”扩而充之,从而使得善性得以成就。
此外,上面关于“命”的四个面向,并非彼此隔绝的独立部分,而是相互交织、相互融摄、同等源始的整体。这里之所以分为四个方面,只是为了分析上的方便。换句话说,我们任意截取某个人的一个生活片段,在其中这四者都起着作用,它们共同构成了人的存在结构。在这个结构中,可以看到人既受限制但同时又有自由。《孟子》中有“自暴”、“自弃”、“自取”、“自得”等语[注]《孟子·离娄上》 :“自暴者不可有信也,自弃者不可有为也。言非礼义,谓之自暴;吾身不能居仁由义,谓之自弃也。” 《孟子·离娄下》 :“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则居之安;居之安,则资之深;资之深,则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皆明言人之自由向度。人的自由是由于天赋予人一颗能思之心。动物或植物并不具有思虑能力,因此作为自然生命的它们,若想超越自身,只能靠着外在的力量,诸如死亡;而有意识的人类,其意识本身就有超越性。用黑格尔的话说,“意识是其自身的概念”,它自身含有发展的动力和目标;在孟子这里,人的目标就是达于天道,但同时天道对人来说又是一种命令,也可以说是一种限制。这是一种独特的自由观念。
二、 人如命何 :人对“命”观念不同面向的态度
上文简单地梳理了《孟子》中“命”观念大致包含的向度,它们构成了人的生存结构。而进一步的问题是,面对自身的生存结构,人类应该如何去对待它们呢?
人之生老病死是人所不能把握的,因此,只能顺其自然,等待而已。《论语》中伯牛身患重病,孔子执其手说 :“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论语·雍也》)他面对这些也只能徒呼奈何,而无力改变什么。又如颜渊死,子曰 :“天丧予!”(《论语·先进》)天决定人的生死夭寿,颜回去世是老天给孔子带来的大损失,而人对此是无能为力的。《孟子》中多处提到“俟命”正是基于此 :死生有命,个体无法控制或改变,但没必要怨恨(“不怨天”)或争辩,也不会让它们成为我们正常生活的干扰,平静地等待其到来即可。
人真正能够把握的,是人对道——人的人伦道德——的承担。首先,这是一种应然的道德命令。孟子认为 :“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舜明于庶物,察于人伦,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孟子·离娄下》)人是有能力超越自己自然本能的生成物,与禽兽之间的区别就在于能够行使仁义,守身立命。说禽兽是禽兽,并非一种辱骂,它们自是其所是,但说人是禽兽,则不啻剥夺了人之为人的尊严。当人自暴自弃、为私欲所遮蔽而不知事亲敬长的时候,就失去了人的本性,而不复为人。其次,上文也已经提到,人有成仁取义的实然能力。人心中的善端和思虑能力为人“践仁”、“履义”提供了基础。因此,去成就自己的德性,无需外求,只要回归自己的本心。“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孟子·尽心上》)正因为这一点,个人的道德责任是能够把握的,因为成就的关键在于自己的内心。“由人之性而落实于人之心,由人心之善,以言性善,这是中国古代文化经过长期曲折的发展,所得出来的总的结论。”[注]徐复观 :《中国人性论史》,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第141页。“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是求有益于得也,求在我者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无益于得也,求在外者也。”(《孟子·尽心上》)追求的东西在外部,受到我之外的条件的制约,则极有可能虽求却不得,若追求的东西在我自身,求则能得。具体到实践上,“践仁履义”并非诸如“挟泰山以超北海”(《孟子·梁惠王上》)之类的事情,后者不是有限的人类所能做得到的,而是“为长者折枝”(《孟子·梁惠王上》)、“徐行后长者”(《孟子·告子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之类的人情事变,简单易行,上至君主,下至庶民,人人皆可为,这就是所谓的“人皆可以为尧舜”(《孟子·告子下》)。相比生死和命运的无常,追求道德之善是人生命中的“常”,犹如茫茫黑夜中的一座灯塔,给人以目标和希望。
不过,“人皆可以为尧舜”是就人内在的善性而言,表明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圣贤,至于能否真正实现,则受命运的制约。首先,每个人有其不同的自然禀赋,比如上智下愚的区别,生而知之者不待学而能自明之,而下愚则要付出更多的努力。其次则是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的限定。就自然环境来说,也不是任其天生天长,而是要识农时而不违之。而时代的不同条件会影响“道”的实现,孔子就认为道之兴废是命运的作用 :“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论语·宪问》)个人的成善或许没那么难,但若要平治天下,追求“大同社会”的理想,则不得不面对不尽如人意的社会环境,受命运的摆弄,遭受挫败。是否对命运采取听之任之的态度而毫无作为呢?在孟子这里显然不是。在孟子看来,基于人的不同禀赋,君子可以像伯夷(治则进,乱则退,圣之清者)、伊尹(治亦进,乱亦进,圣之任者)以及柳下惠(不羞污君,不辞小官,圣之和者)那样有不同的成圣道路(《孟子·万章下》),他们虽然因其天赋所限,不能像孔子那样集大成,各有偏颇,但依然是有道之君子,体现了善性的一些方面。“君子和而不同”(《论语·子路》),在“仁”这一普遍的原则之下,存在着多样性的具体表现。每个人应该对自己有充分的认识,并根据自己的禀赋而选择修身的进路和成圣的方向;同样地,对于个体所处的环境也应该加以认识,并依其特殊状况而筹划行为。“禹、稷当平世,三过其门而不入,孔子贤之。颜子当乱世,居于陋巷,一箪食,一瓢饮。人不堪其忧,颜子不改其乐,孔子贤之。”(《孟子·离娄下》)身处乱世与平世不同,虽是同道,但选择的生活方式不同;曾子与子思,面对盗贼攻城,前者躲避而后者与君守城,则是因为身处的位置不同。君子的道虽是一,但处境各有差异,各自的选择因而也是多种多样的,不能只是死守原则而不知权变。又如 :“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权也。”(《孟子·离娄上》)总之,“执中无权,犹执一也。所恶执一者,为其贼道也,举一而废百也”(《孟子·尽心上》)。不根据具体处境进行权衡,是戕贼仁义的一种表现。上述这一方面的意义正是孟子竭力宣扬的“义”之观念,朱熹说 :“仁者,心之德、爱之理。义者,心之制、事之宜也。”[注]朱熹 :《四书章句集注》,第201页。“义则意味着必须与具体的状况、特定的情境、相应的条件相适合、相配合的‘大地上的真理’。”[注]陈赟 :《〈易传〉对天地人三才之道的认识》,《周易研究》,2015年第1期。这并非是说孔子的思想中没有“义”这个维度,只是他不如孟子如此大力地渲染和强调“义”而已。正如朱子在《孟子序说》中引程子所言,“孟子有功于圣门,不可胜言。仲尼只说一个仁字,孟子开口便说仁义”[注]朱熹 :《四书章句集注》,第199页。。明言“义”通过孟子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在文本中孟子经常将“仁义”、“圣智”并提 :德性的成就需要智性上的辅助,最终方能完满。
综上所述,“仁义”的观念都是“命”观念的题中之义,尽性还要知命,方能真正实现人道德上的善。人们提到孟子的思想,大多会用“性善论”这一说法,那固然是孟子思想的一大特色,但性善只是仁之本,而义路这一面向则被遮蔽了;仁本不结合义路,对于孟子来说,不但无助于道,甚至是对道的一种损害。“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处而处,可以仕而仕”(《孟子·万章下》)才是“守善道、识时命”的集大成者,而不是那些只有善心善性、却不知如何结合具体环境去实行的道德空想主义者。因此,也许孟子“命”这一观念更适合作为他思想上的特征。
三、 天地之心 :“命”观念所体现出的天人关系
上文主要对“命”的不同面向分别做了分析,现在则将“命”观念作为一个整体来探讨。由于这里的“命”指的是“天所赋予人的各个方面”,这里必然涉及的是天与人两方 :天发出命令,但“命”本身却要在作为其生成物的人类身上体现出来。身为受造物的人类受“命”的束缚,是有限的,不得不依赖自然物质和社会条件得以存活,且不具备天那样普遍而全能的视角。这里所引出的问题是,天与人之间到底存在着怎么样的关系?传统中有“天人合一”这一观念,而在“命”论的框架之下,天与人究竟是一还是二?如果是“二”,即天人相异,那么,有限的人如何能够认识无限的天道?
从作为追问者的人来说,限于自身有限的视角,天并非如同掌上纹路那样一目了然,因此,这里并不对“天”这一观念下一个确切的定义(《孟子》中也无此规定)。结合“命”这一观念,简单地总结一下“天”的几个特征 :天是万物得以生化的根源;不同于有形的万物,天无形无象; 天是万物之所以显现的原因,换句话说,它在万物背后或“之中”。
接下来,本文将尝试分析《孟子》中所体现出的天人关系。首先,从天的角度来说,世间造化,莫不是天流行发应的产物,因此,无物不是天。如王阳明所说“三光之上天也,九地之下亦天也”[注]王守仁 :《王阳明全集》,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22页。,在此处,天人本来就是一,不必言合。
其次,从人的角度来看,情况则复杂得多。对于尚未达到圣人境界的百姓来说,不但天与人,人与人之间、人与他物之间都被私欲间隔了,自身与外在的一切都是相异的。那么,对于圣人来说,是否天人就是“一”?就“命”观念的几个要素来看,是又不是。之所以说天人是一,是从“性-命”这一因素来看,也就是孟子所谓的“尽心知性知天”。天地生物之大德,只有圣人能够抛弃一己之私而体认之,复归天然之善性,认识到万物本来一体,“民吾同胞,物吾与也”[注]张戴 :《张戴集》,章锡琛点校,北京 :中华书局,1998年,第62页。,从而身体力行,参赞天地之化育。就这一点来看,《孟子》这里的“天人合一”是道德心性意义上的合一。而就“命”观念的其他几个因素来看,无论人再怎么努力,也无法消除自身的一些限制,从而使自身一跃而为天。人有生有死、有病有痛,认知与行事上也要受到诸多条件的局限,所以,从这一角度来看,即使是圣人,与天依然相异。正因为人的这些限制,才有了恶的存在。人承“命”而生,一切的禀赋都来自于天,因此“恶”亦是来自于天,只是这些所谓的恶在“天”的层面不是恶,“天地无心而成化”[注]程颢、程颐 :《二程集》,王孝鱼点校,北京 :中华书局,2004年,第1029页。。天地化生万物是无心之举,本来无所谓善恶,而有心的人由于自身的独特性而产生了“恶”。
最后,本文将处理由“命”观念引出的另外一个问题,即 :有限的人如何能够认识无限的天道?
首先,天在人的眼里虽然无形无象,但世间万物莫不是由天而生。“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故而,通过对天所生之物进行观察,有推断出天道之可能。具体的路径大概有 :观草木生生不已的过程,明了天地生物之心。但这一点在《孟子》中并没有作为重点讨论。其次,观古今兴废存亡,以明治国当以仁政,方能长治久安。中国古代思想历来有注重历史的传统,这一点在《孟子》中也表现得很明显。尧舜禹之圣王之迹,春秋战国时的世衰道微,这些历史事件经过时间的沉积,显露出了自身的规律,这一规律也即所谓天道,“顺天者存,逆天者亡”(《孟子·离娄下》),因此,这也是知天道的路径。最后,则是孟子所竭力强调的,即反求诸己,在自身的内心上用力 :
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孟子·尽心上》)
由心之善端得到其背后的善性,进而知天道 :天道性命一贯。总之,如果想要得知天道,不管是向内反省自己的心性也好,还是向外观察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都必须以人的视角,并从天所显示出的经验证据出发。《孟子》中,“心→命(性)→天”这一路径正是表达了这一种认识顺序。当认识到天道之后,应该明白真正的生成顺序则是与之相反,即“天→命(性)→人”,这一过程是在认识顺序之后,根据对天道的体认而重新建构起来的。这种生成顺序在《周易》、张载《正蒙》等著作中被采纳。但人无法直接洞晓天的秘密,只能通过人道的践行,达到智圆仁熟之后,才能明白天道。所以孔子说 :“下学而上达。”(《论语·宪问》)“下学”是路径,而“上达”是一个不一定必然能达到的目标,因此,我们坚持要做的只是“下学”。需要注意的是,即使通过人的努力而达于天道,但此天道依然是有限之人的努力成果,仍然受限于人,只是“人之天”;至于天本身,也就是“天之天”,则不可得而知也。
人既已明了天道,但如何证明这种明了,是需要反过来向天求证的。而“天不言,以行与事示之而已矣”(《孟子·万章上》),天不会开口说某个人哪里是对的或错的,这种明了仍然要体现在世间的事物之上。利于人民之事,民接受了的行为可视作是天接受的,孟子引《尚书·泰誓》“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例如 :不违农时,让百姓衣食无忧;行使仁政,不草菅人命;父慈子孝,让百姓家庭生活完满,这些都体现了生生之德,都是民众所乐于看到和接受的。君子能够在天下完成这些事情,就算是知晓了天道,且通过自身的行为,辅助上天实现了生生之德。《中庸》所谓“赞天地之化育”、“与天地参矣”是也。
总之,“命”观念中所体现出来的天人关系,最终的重心落在了人道之上。
结语
天地无心而化生万物,但和谐的自然界因人的出现而变得不再平静。人类是万物之灵、天地之心,它不像其他的生物那样,如动物依靠自己的本能生存,渴则饮、饥则食,自然而然,不违天道。人是能够违背天道的生成物,是有能力为恶的,可以说“为恶”虽是一种负面的能力,但这恰恰证明了人的自由。而与恶相对的,人更为重要的自由向度,则是天生的“善性”,这是“天人之所以合一”的最重要维度,也是人唯一能够通过自身的努力而可达成的目标。因此,孟子才会如此重视“善性”。但同时,单纯去强调孟子的“性善论”有对孟子思想进行简单化处理之嫌。本文之所以重构《孟子》中的“命”观念,正是通过这种尝试,去展现出《孟子》中较为复杂精巧的思想,而这些思想,在今天依然具有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