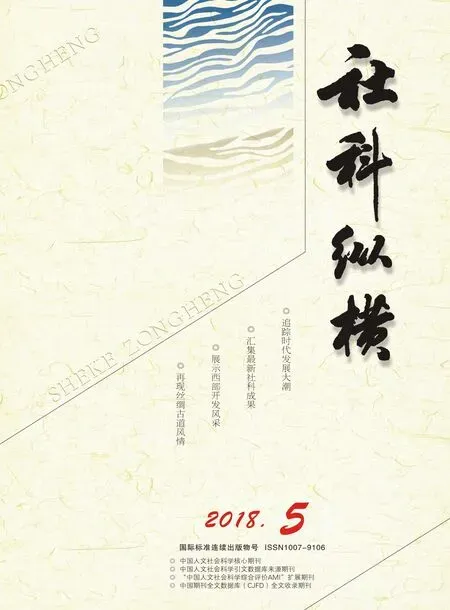探讨施坚雅理论的问题和启示
——重读《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
朱文珊
(中央民族大学 北京 100081)
一、《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和施坚雅的城市研究理论
人类学家施坚雅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下文简称《城市》)并不是一本传统意义上的人类学民族学读本,它甚至算不上一本纯粹的社会科学作品。在这本书中,除了人类学民族学的知识以外,还融合大量的社会学、经济学、历史学、地理学、人口学、统计学、生态学乃至城市规划、航运、建筑等多个方面的理论和方法。因此,有人把这本书划归人文地理学范畴,也不无道理。但是,因为社会和人类的发展——城市是该书的核心,所以《城市》仍旧被列入了多个人类学民族学的书单中,比如王铭铭的《社会人类学与中国研究》。如果给这本书下一个简单的定义,我们可以将它命名为:一本研究中国城市和城市中人的书。
本书主要分为三个部分,分别是围绕着中华帝国晚期城市的三个方面来写的。第一部分的标题为“历史上的城市”,主要论述了城市的建立、拓展,以及影响城市形式和发展的各种各样的因素,比如中华文化传统的宇宙观、农业、运输、宗教等等[1]。第二部分的标题为“空间的城市”,在这一部分里,作者们研究了城市在各自的中心(腹地)和大区域内扎根的过程,并且论证了城市与城市、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关系,在这里,对城市政治功能和经济功能的论述得以展开。第三部分的标题为“作为社会体系的城市”,该部分论述了中国城市内部的种种社会结构,比如驻扎在城市里的行会、神社等等。作为编者的施坚雅为每一部分都做了详细的导言,并尽其可能地将书中这些相互之间关系松散的内容串联在了一起。
实际上,该书为集合了两次美国中国城市研究研讨会成果的论文集,篇幅颇长,内容繁杂,它所包含的课题兼具了研究广度和深度上的复杂性。《城市》大致论著的帝国晚期中国城市及其在当时的大背景下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与会人员的学术背景各不相同,研究方向也无法统一,使得评论非常困难。而且,正如诺顿·金斯伯格所说:“其所以难以评论,是因为此书标志着对中国城市的研究,已经跳出了晦涩难懂的传统汉学的窠臼,开始进入了历史社会科学的比较城市研究的轨道”[2]——这是一本野心勃勃地想要解决关于城市的多项问题的书,或者说,作为一个整体,这本书实际上是一本完全跨学科的、多人合著的,以研究对象而不是研究方法为导向的皇皇巨著。
这种跨学科的另辟蹊径的方式,并不仅仅体现作为整体的《城市》中,更是体现在施坚雅本人的研究趣向里。本书包括导言在内一共19篇文章,施坚雅一人独占五篇。通读全书就不难发现,施坚雅研究的内容充满宏观性,“19世纪中国的地区城市化”涵盖了大部分城市化地区(即是所谓的“汉人地区”),而“城市与地方的体系层级”则将着眼点放在了帝国晚期的城市体系内容,等等。施坚雅的研究(这里还包括章生道的“城治的形态与结构研究”)分析了整个中华帝国晚期城市的状况和发展。与之相比,其他大部分论文(比如牟复礼的“元末明初时期南京的变迁”),多是对于某一或某几个城市进行的案例分析。
除了宏观性之外,施坚雅的研究还兼具了大量方法上的跨学科性。翻开《城市》,首先引人注目,且与大多数传统意义上的人类学民族学著作相左的就是施坚雅对于数据的运用。大量的人口统计、人口级数、城市数量、行政规模百分比等等的数据,乃至城市等级——规模分布图这样的统计学研究方法(暂且不讨论是否适用和使用正确)得到了很大程度上的使用。另外,《城市》一书中也向读者提供了大量的地图。在这里,地图的使用对读者理解中华帝国晚期城市的分布和施坚雅的城市区域理论起到了极大的辅助作用(实际上,仅在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时期,施坚雅本人就收集了约700多张地图,而在那个没有被信息化的年代里,这些地图大多由其本人及其合作者们亲手绘制)。
而这些,体现了本书,乃至施坚雅整个理论体系的人文地理学基础。正如列维—斯特劳斯以语言学研究人类学民族学一样,施坚雅对于人文地理方法和理论的使用极大地开阔了其民族学人类学研究。在《城市》一书中,他对于城市(包括其对于中国西部乡村的研究)是基于德国地理学家瓦尔特·克里斯塔勒(Walter Christaller)于1933年所发表的《南部德国中心地原理》一书中所提出的著名的“中心地理论”(Central Place theory)的概念。这一理论的内容讨论了关于(国家内)城市和城镇的职能、大小以及空间分布结构的学说,适用六边形概括了城市的等级与规模[3]。而是施坚雅将这一理论运用到了人类学民族学对于城市的研究中来,而这无疑是将人文地理学中的数学模型带进了人类学民族学研究的方法之中。
在施坚雅的研究中,他首先分析了中国的几大核心地点的等级和顺序;其次,他对中国的社会空间结构划分了九大区域(满洲并没有进行详细的分析);最后,他论述了除了经济地理因素之外社会因素是如何对于紧急空间进行制约的。在这一套理论里,最重要的是中心地的概念,而中心地是由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所决定的,这里,起到决定的作用的是自然形成城市的经济因素。
二、对于施坚雅和《城市》的质疑
然而,尽管施坚雅对于中国城市的论述充满了具有划时代意味的创见,他的研究里仍旧有不少问题,并受到各路学者专家的质疑。笔者将在下文中列举出几个对于施坚雅的研究中的问题提出的重要挑战:
首先,施坚雅的研究结果存在适用性问题,即他的社会理论是否适用于现实。白思奇认为,尽管施坚雅的城市理论充满了激情和说服力,但是,如果将施坚雅的社会空间模式(尤其是关于城市中商人和士大夫的聚集地在空间上是分离在两个特定的位置的研究结论)运用到北京这座城市中的话,那么就会出现两个严重的问题[4]:其一,尽管核心区存在,但是,根据施坚雅的理论所得出的士大夫的居所位置并不完全等同于现实状况;其二,在施坚雅对于明清时期的中国城市研究中,城市状况的发展和变化——城市的历史——并没有得到充分的考量,简而言之,施坚雅暗示了帝国晚期城市是不变的,然而,这并不是事实。
武雅士认为如果根据施坚雅的理论,并不能够解释中国文化,尤其是城市文化的多样性[5]。根据施坚雅的理论,当时中国城市群的经济状况所导致的应当是社会和文化的同质性。但是,在当时不同的地区,即便是在施坚雅所划分的同一区域里,当地的社会文化也具有多样性。就此,王铭铭干脆直接问出了“西方理性经济人的概念是否适用于传统中国这个非西方、非资本主义社会?”[6]这样的问题。他认为一方面,施坚雅的模型过于理性而忽视了人的存在;而在另一方面,在施坚雅将城市中的经济和政治功能一分为二,从而忽视了城市发展中的经济—政治之间的互动。
当然,也有人直接向施坚雅的论据发起了攻击。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的曹树基教授曾就施坚雅的城市研究中的人口规模估值的方法提出过质疑。他认为,施坚雅对于明到晚清中国城市的人口规模的估计有以下几点不合理之处[7]:
其一,施坚雅在《城市》中曾根据城墙的长度与形状对城市的人口规模作出过估计。然而,从明代到清代,虽然“大多数首府性城市的城墙长度与形状”几乎没有发生变化,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城市人口的居住范围却从城墙内扩展到了城墙外。因此,大部分“城市居民”其实并不住在城墙以内,通过当时城墙的长度对当时的城市人口进行的估计并不十分有效。其二,施坚雅所使用的部分材料(800多个城镇)来自于东亚同文会所汇编的《支那省别全志》(《全志》)。可是,施坚雅并没有清楚地说明(或者说是并没有意识到),日本人在编纂这本《全志》的过程中,并没有进行详细的调查,而仅仅是根据当时(1915年前后)的人口数量对光绪年间的城市人口进行了估计。其三,在施坚雅的研究中,城镇的人口可以根据其邮政级别、航运、铁路等情况进行确认。然而,在近代中国邮政、航运以及铁路逐渐发展的过程中,这些交通通讯方式和城镇体系的变化实际上是相辅相成、互为因果的。因此,根据这些状况来推测城市人口是不合理的。其四,施坚雅所采用的西方来客的游记本身就有不少问题,无论是这些游记的准确度,或者是该类资料的数量都使得该类资料来源不具有可信性。
三、跨学科方法——施坚雅对学科建设的真正启示
虽然施坚雅在《城市》中的研究成果确实存在大量问题,但是,当我们在向施坚雅提出质疑的同时,应当注意到他本人也承认他的这一系列的理论是存在问题的。或者说,施坚雅本人认为他的城市研究理论是建立在一定“假设”基础上的“理想模型”,而并非完全是对真实的城市情况作出分析之后的结论。
因此,当我们尝试去去理解施坚雅的“理想模型”,尤其是六边形等级模型时,就必须首先明白在施坚雅的理论体系内,城市的六边形模型并非是根据中国的历史资料和现实情况推导出来的,这甚至都不是从西方(欧洲传统地理学)里诞生的——它是一个纯粹的数学模型。这个数学模型始于理想的标准圆形模型,然而,当等大的圆形布满平面空间,将重叠的空间进行分割之后,平面上就会形成等大的蜂窝状六边形几何图案。这里的平面几何数学模型,对施坚雅来说并不仅仅适用于中国的状况,也是所有城市的理想模型。该模型是先验的,而非基于资料得出的构建结果。
虽然,在中国的范围内,我们很少能够发现标准的正六边形城市区域(市场区域),但是,这根本不是施坚雅需要面对的问题。他的研究的核心问题实际上是通过建立数学模型去研究和分析社会、空间和历史究竟是不是合理的。之后的学者当然可以否认模型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而使用实证分析来处理中华帝国晚期城市的状况。但是,如果完全否认模型,那么对话施坚雅就成了多余之举[8]——这完全就是不同的游戏规则。如果承认数学模型在社会空间上的合理性,那么假定城市(市场)是圆形比其他的形状,比如三角形、不规则形状,更为合理和有效。一旦将圆形布满空间至没有缝隙,再重新等分等圆既有的空间,那么我们仍旧会得到蜂窝状的正六边形。也就是说,如果承认模型的可能性并建立模型的话,我们最有可能得到的最优结果恰恰就是施坚雅模型。所以,目前,就模型本身提出问题,实际上意义并不大。而通过这一模型,我们可以简化的现实状况,尤其是经济学状况,从而得以研究建立在空间内的社会文化。
这种数学模型的建立在人文地理中比较常见的,但是在人类学民族学里,尤其是今天的学科研究里,却难以寻觅。因此,我们能够从施坚雅的体系里,以及从《城市》里面所能够学到的除了施坚雅理论模式本身,更是这种跨学科的研究方式和视角。
四、结论
“城市”这一个双字词像大多数中文中的多字词一样是由两个具有不同意思的单字——“城”和“市”所组成的。“城”,往往指的是用城墙为起来的地域空间,而“市”,则更多指的是进行交易的场所。在施坚雅的理论体系里,其实谈得更多的,起到决定性作用的是经济的(市场的)市,而政治和社会的因素更多的是收到经济空间的制约。
而经济本身,其实是可以被量化的。因此,这完全有利于施坚雅将基于经济的城市空间以及其结构、社会和文化的复杂性融入简单的数学模型中。
所以,根据《城市》我们可知,施坚雅的理论更多的是启发性的理论,而并非是实践性的理论;从这些理论里面,跨学科可以给我们带来更多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
参考文献:
[1]施坚雅主编.叶光庭等译.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M].北京:中华书局,2000.
[2]诺顿·金斯伯格.叶光庭译.书评一:《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A].庄孔韶主编.人类学经典导读[C].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3]瓦尔特·克里斯特勒.常正文,王兴中译.德国南部中心地原理[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4]白思齐.任吉东译.中华帝国晚期北京城市生态的重新思考:都城社会空间的演变[J].城市史研究,2006(1).
[5]武雅士.社会等级与文化多元性——对施坚雅中国农民文化观的批评[A].庄孔韶主编.人类学经典导读[C].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6]王铭铭.社会人类学与中国研究[M].北京:生活 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
[7]曹树基.王旭等译.清代北方城市人口研究——兼与施坚雅商榷[A].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城市研究——施坚雅模式[C].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
[8]史建云.对施坚雅市场理论的若干思考[J].近代史研究.200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