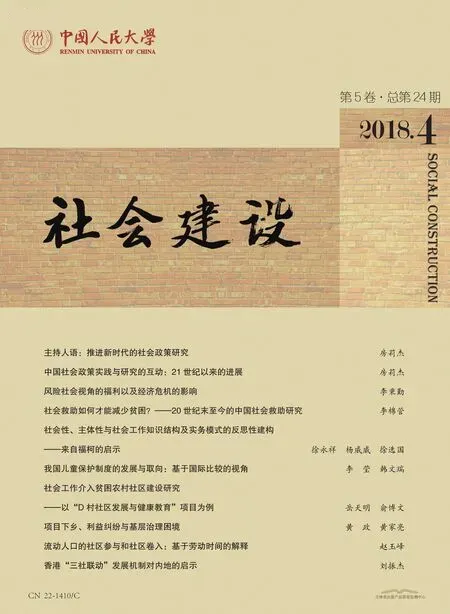风险社会视角的福利以及经济危机的影响
李秉勤
一、从风险社会视角出发的福利国家发展
现代福利制度从本质上看是在维持经济竞争力和维护社会安全感之间寻找一定的平衡。固然,过高的福利有可能奖懒罚勤,但是一个不能给社会成员提供一定程度的经济安全感的国家,所面临的不稳定因素不仅是政治上的,而且很可能就是经济上的。例如:个人在缺乏安全感的情况下迫不及待地投资,甚至投机,本身就有可能成为造成经济和金融危机的根源。Beck①Beck, U. From Industrial Society to The Risk Society: Questions of Survival, Social Structure and Ecological Enlightenment. Theory, Culture& Society, 1992, 9(1): 97-123.在《从工业化社会到风险社会:生存、社会结构和生态启蒙问题》一文中首先发问:“风险难道不是至少和工业社会,甚至是和人类的存在一样悠久吗?难道不是所有的生命都要面临死亡的风险吗?难道不是历史上所有的社会都是‘风险社会?’”但是,他指出:前工业社会的风险往往是和人的运气有关的。人们往往认为自己所面对的风险是“上帝”、“自然”决定的。这类风险在工业化过程中逐步得到降低:婴儿存活率、灾荒、饥饿、流行病、甚至战争的死亡率都在不断下降。而后工业社会的风险往往带 是人为造成的或者由社会建构的。它可能与人的决策有关,是科技与经济决策的产物。 它也可能是人类在开疆拓土,使用新技术的过程中造成的风险。 社会政策领域,提高安全感的措施由来已久。社会保障或者社会保险本身就是从减少人所面对的风险出发。至于哪些风险被纳入到福利国家的范畴内则带有很强的政治色彩。这种防范风险的动机,恰恰成为福利国家发展的动力之一。
以人道主义为出发点的学者认为,福利制度的出现是为了结束社会成员遭受苦难的情况。早在国家福利制度出现之前,就有宗教和其他类型的互助和慈善机构在为帮助人们摆脱困境而提供社会服务。而国家福利制度是更加系统性的需要满足。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应该确定什么是“需要”,Doyal 和 Gough在,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就致力于确立什么是人类需要的研究①Doyal, L., & Gough, I. A Theory of Human Needs. Critical Social Policy, 1984, 4(10): 6-38.。至今很多新的文章都在分析在特定的背景下,新的无法得到满足的需要的形成以及社会政策如何应对。这样的“苦难”也可以视为人类一生中所面临的风险。它可能是健康的损害、人力资本的缺乏或者丧失、收入来源的中断,或者家庭和社会照顾的匮乏。Taylor-Gooby②Taylor-Gooby, P. (Ed.).New Risks, New Welfare: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European Welfare Stat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提出随着欧美福利国家的经济结构和就业模式向着后工业社会的转化,新的社会风险出现,其中包括女性就业、人口老龄化造成家庭照顾的负担和成本增加;后工业化经济的就业机会与人力资源不匹配,同时产生低收入和不稳定就业的岗位。另外一个现象是女性由于就业参与门槛低,比较乐于接受低收入和非全职的工作,反而比男性失业者更容易重返工作岗位。这对过去建立于男生就业为主、终生就业;女性承担家务劳动和养育责任,就业时间和收入都较低的家庭分工模式和收入结构都造成了冲击。也对传统意义上一国人力资本的形成方式带来了影响。欧洲国家上个世纪80年代以后在福利国家范畴内引入家庭政策和养老政策、对基础设施的关注,对年轻人和女性的关注等等都是在不断应对新的社会需求的过程中产生出的新的社会政策,就是政府对经济和社会变化的反应③Häusermann, S. Changing Coalitions in Social Policy Reforms: The Politics of New Social Needs And Demands. Journal of European Social Policy, 2006, 16(1): 5-21.。本世纪初,人的主观需要的满足被提到社会政策研究议事日程上来。虽然仍然存在很多的争议,但是政策制定者已经发现主观指标的重要性。Veenhoven④Veenhoven, R.. Why Social Policy Needs Subjective Indicators.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2002, 58(1-3): 33-45.认为社会政策不应仅限于物质,它也应当针对心态。特别是当人的心态有可能影响到他们的健康、就业和社会交往⑤Dolan, P., Peasgood, T., & White, M. Do We Really Know What Makes us Happy? A Review of the Economic Literature on the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Subjective Well-Being. Journal Of Economic Psychology, 2008, 29(1): 94-122.,而且相关的后果有可能耗费公共资源的时候,其社会政策意义也变得愈发重要起来。
风险是指事件发生的可能性。人类的主客观需要得不到满足的结果可以视为在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中所面临的风险变成了现实。社会政策、特别是社会保障和保险则是社会对这些风险的社会化防范,而社会救助则是对风险造成的恶果的补救措施。
如果人们对社会风险和后果的认知能够达成共识,则福利制度也不会存在很多争议。但是现实世界更加复杂,一个社会偏偏很难就什么是风险、什么风险需要社会政策来防范和什么后果需要社会救助达不成一致的意见。Esping-Anderson 1990⑥Esping-Andersen, G. The three worlds of welfare capitalism,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年在他著名的福利制度分类研究《福利资本主义的三个世界》中,按照劳动力去商品化的程度和影响因素把欧美福利制度进行了分类。其后的十几年中,有学者前赴后继地进行了大量的分类①Ferragina, E., &Seeleib-Kaiser, M. Thematic Review: Welfare Regime Debate: past, Present, Futures? Policy & Politics, 2011, 39(4): 583-611.Esping-Andersen, G. (Ed.). (Welfare States in Transition: National Adaptations in Global Economies. Sage, 1996.Barrientos, A. Labour Markets and the (hyphenated) Welfare Regime in Latin America. Economy and Society, 2009, 38(1): 87-108.Arts, W., &Gelissen, J.. Three Worlds of welfare capitalism or more? A State-of-the-Art Report. Journal of European social policy, 2002, 12(2): 137-158.Aspalter, C. The Development of Ideal-Typical Welfare Regime Theory. International Social Work, 2011, 54(6): 735-750.Gough, I., & Wood, G. Insecurity and Welfare Regimes in Asia, Africa and Latin America: Social Policy in Development Context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Cerami, A.Social Policy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The Emergence of a New European welfare regime (Vol. 43). LIT VerlagMünster, 2006.Wood, G., & Gough, I. A Comparative Welfare Regime Approach to Global Social Policy.World Development, 2006, 34(10): 1696-1712 Brush, L. D. Changing the Subject: Gender and Welfare Regime Studies. Social Politics: International Studies in Gender, State & Society, 2002,9(2): 161-186.Gallie, D., &Paugam, S. (Eds.). Welfare Regimes and the Experience of Unemployment in Europe. OUP Oxford, 2000.Lewis, J. Gender and Welfare Regimes: Further Thoughts. Social Politics: International Studies in Gender, State & Society, 1997, 4(2): 160-177.Trifiletti, R. Southern European Welfare Regimes and the Worsening Position of Women. Journal of European social policy, 1999, 9(1): 49-64.。这些研究有的沿袭了Esping-Anderson1990年的分类方法,有些则补充新的分类变量,还有的把相同的方法论扩大到世界其他国家,其中Gough和Wood的作品甚至把第三世界的国家也纳入到福利国家的分类中来,认为传统社会的非正式的和灵活的福利提供也应当被视为福利的提供模式之一。此外,女性主义学者持续地对Esping-Andersen的分类进行系统性地批判,通过对他的分类模式进行修正使得福利国家分类中包括了对女性作用和家庭政策的分析。Schröder进一步把资本主义的生产组织方式和Esping-Anderson的福利国家的类型结合起来。他认为把福利和生产制度视为一体比将两者分开的方法更有解释力。例如,福利国家的分析有助于解释一部分劳动力市场中的性别歧视,而资本主义多样性的理论有助于说明为什么妇女在获得高层劳动力职位时遇到更多困难。把二者结合可以更全面地了解女性劳动参与的条件。生产和福利结合起来研究也便于体现“自由化”的多种轨迹。如:在自由主义福利国家,自由化更多地体现为广泛的,全面的放松管制。而在福利制度保守,但是强调协调发展的国家,二元化现象则比较突出:比如“体制内”的人地位稳定,而“体制”外的人就业不稳定。而在社会民主福利而注重经济协调发展的国家,“自由化”则意味着强制执行灵活保障。②Schröder, M.Integrating Varieties of Capitalism and Welfare State Research: A Unified Typology of Capitalisms. Springer, 2013.
直到2006年欧洲社会政策期刊发表了专刊,对世界各国的福利制度进行重新考察,多篇文章如Scruggs 和Allan、Bambra都指出发达国家福利制度已经无法按照Esping-Anderson的方法归类。③Scruggs, L., & Allan, J. Welfare-state Decommodification in 18 OECD Countries: A Replication and Revision. Journal of European Social Policy, 2006, 16(1): 55-72.总体上看,对福利国家制度类型的分类,也可以视为通过宏观的社会支出状况来判断针社会就福利制度所造成的社会共识及其实施效果。如果放到风险社会的视角来看,就是探索经由福利国家认可的社会风险和社会困境所决定的福利制度模式。
但是,对于社会共识达成的机制也有不同的解释。按照工业化的逻辑,社会化的福利提供如:公共住房,有助于劳动力、军人、家庭成员把更多的精力放在能够带来经济增长和保护国家的活动中来。这种做法说毕竟是把社会政策视为经济发展的工具和辅助,是功利性的。它对社会政策的定位是以产业以及产业中的就业者所面临的风险为核心的。历史上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工业化进程进行分析,提出资本主义必然走向灭亡的预言。他的思路恰恰是基于资本主义社会难以通过市场机制来达成应对工业化带来的社会风险的共识。但是他在对资本主义提出批判的时候没有考虑到福利国家的出现,即政府意识到市场的缺陷,主动采取防范手段,利用社会保障和社会保险来防范风险,和提供社会救助。从而达到了弱化工业化社会风险对工人阶级生存和尊严的破坏。可以说,恰恰是福利国家的出现,挽救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困境。自由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认为马克思的理论没有考虑到中产阶级的崛起和产权与控制权的分离,从而误判形势。还有的学者认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制度的理解并没有问题,但是他提出需要通过革命才能解决资本主义的矛盾是低估了国家独立于资本经济而发挥作用的能力以及资本主义经济的自我调节能力①Stephens, J. D. The Transition from Capitalism to Socialism. Springer, 1979.。但是,马克思的后继者认为福利制度治标不治本,不过是延缓了资本主义制度走向毁灭的速度②Skocpol, T. States and Social Revolution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France, Russia and Chin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以Harvey为代表的新马克思主义者更进一步把资本主义社会中劳资关系的斗争引入到城市空间范畴来,强调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与城市居民的城市空间争夺③Harvey, D. Social Justice and the City (Vol. 1).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2010.,认为与资本与政府权力的结合进一步剥夺了劳动者在城市中的生存权利。
在生产和贸易体系带来的风险之外,社会政策本身也有可能制造社会风险。Taylor-Gooby认为,包含新社会需求的现代化政策的造成了社会政策制定中的新冲突。它与社会分配中的阶级冲突不同。相反,有可能围绕这些政策形成价值联盟和跨阶级联盟。在实践中,恰恰是社会政策常常人为地制造出各种社会排斥。尤其是在缺乏政治参与的背景下确立起来的社会政策往往有可能导致社会排斥④Sen, A.. Social Exclusion: Concept, Application, and Scrutiny. Asian Development Bank, 2000.。这种现象在福利公民权的发展过程中表现得非常明显。福利公民权体现的是国家政策与公共和私人社会生活领域之间的关系。随着社会现代化的程度越高,福利国家为更多的人授予“福利国家的公民权”⑤Marshall, T. Citizenship and Social Class. Citizenship and Social Class, 1950, p1-85. https://doi.org/10.2307/587460。公民权的扩展包括权利内容与质量的扩展和权利覆盖人群的扩展。例如:单亲父母、老年照护、精神健康等等领域的很多服务和保障都没有包括在最初的福利制度设计之中。随着时间的推移,得到了不断的发展。Turner⑥Turner, B. S. Contemporary Problems in the Theory of Citizenship. Citizenship and Social Theory, 1993, p1-18.认为福利国家的公民权应当与主权国家的公民权区分开来。福利国家的公民权更接近于享有民主权利的公民的概念。它围绕着政治共同体的共同成员来制定公民身份。例如,虽然欧盟已经发展多年,而且在经济领域的一体化势头在90年代以来愈发强大,但是它只是一种政治共同体,各国公民想成为统一的欧洲福利制度的公民却面临着非常大的阻力。这个阻力的来源恰恰是欧盟的公民。也就是说,从福利制度的角度来看,成员国的公民并不具备同等的社会公民权。具有“主流”话语权和选举权的国家公民可以通过对本国政治的影响来排斥共同体内其他国家的公民。这在劳动力自由流动的地区就会带来严重的社会风险。例如:没有所在国福利公民权的人在面对失业和经济困扰的时候就只能回到母国才能够享受到相应的福利待遇,否则就会陷入困境。但是因为他们不是所在国的公民,无法对所在国的社会政策享有发言权,于是只能依靠所在国公民的“同情”获得权益。
新社会联盟往往以社会运动的形式形成推动社会政策变迁的政治力量。早期的社会运动和社会运动组织的研究假设社会活动是因为参加者的集体挫折感或不满形成了社会组织和社会运动。这种思路偏重于社会运动参与者的社会心理学。从这个意义上看,社会组织和社会运动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在方法论上是比较接近的,只不过斗争的组织不是在阶级层面,而是在多样化的社会群体层面;不是由工会或无产阶级政党来组织的,而是由社会组织来组织的。McCarthy和Zald强调资源的多样性和来源的多样性,提出社会运动与媒体、政府和其他各方,以及其它社会运动组织之间的互动形成了对资源动员和调动的影响①McCarthy, J. D., &Zald, M. N. Resource Mobilization and Social Movements: A Partial Theor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77, 82(6):1212-1241.McAdam, D., Sampson, R., Weffer, S., &MacIndoe, H. There will be Fighting in the Streets: The Distorting Lens of Social Movement Theory. Mobilization: An International Quarterly, 2005, 10(1): 1-18.。McAdam等人认为,人们对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以来的社会斗争的关注是扭曲的,使得社会运动总是和以下几个现象联系在一起:(1)在公共环境中进行破坏性抗议;(2)在政治问题上协调松散的国家层面的斗争;(3)基于城市和/或校园的抗议活动;以及(4)在弱势少数群体中提出申诉。他们用1970年至2000年间约1,000次抗议事件的数据对芝加哥都市圈的集体公民参与的趋势和模式进行研究,提出实际的数据并不支持社会运动的刻板印象。他们发现,自1980年以来,社会运动的形式发生了显著的转变,公众抗议基本上是和平的、例行的、郊区化的和本地化的,而且往往是由处于优势地位的人群发起的。从理论上看,在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已经有人开始摆脱用社会心理学来研究社会运动的思路,提出与社会运动的作用应当与反应社会过程的结构理论结合起来。从这个意义上看,社会运动应当是更广义的,它包括了大范围内的基于集体行动的挑战当局权威的抗争,也包括了小范围的、日常性的谈判和参与,意在改变现有政策和政治的格局。与其说他们是针对执政者,不如说是要求社会对由前期的社会排斥所造成的个人风险提供防范和救助。
除了政策带来的风险之外,人们越来越多地关注到政策治理体系和政策过程造成的社会风险。Kasperson等人提出来社会风险有可能因为机构行为而被放大。②Kasperson, R. E., Renn, O., Slovic, P., Brown, H. S., Emel, J., Goble, R., &Ratick, S. The Social Amplification of Risk: A Conceptual Framework. Risk Analysis, 1988, 8(2): 177-187.他们提出原本在技术上评估并不是很大的风险,却有可能以各种方式与心理、社会、体制和文化过程相互作用,放大或减弱公众对风险或风险事件的反应。风险的放大有可能发生在两个阶段:在有关风险的信息的传递过程中,以及在社会的响应机制中。有关风险的信号由个人和社会来放大,其中包括传达风险评估结果的科学家、新闻媒体、文化团体、人际网络等。可以在每个阶段都找到放大的关键步骤。放大的风险会得到相应的行为上的反应,这些反应又会产生进一步的影响。他们把风险放大机制比作音响的放大过程。指出由于人们对风险的认知能力有限,往往倾向于利用简化的思维来评估风险并作出反应。此外,个人和群体往往会因为价值观取向而决定什么样的风险更为重要。这就有可能造成不同价值观取向下的社会群体对风险的理解不同,从而形成不同的政治力量。当某项风险成为不同社会群体的政治运动的核心议题时,就会吸引到公众更多的注意力,其关注度与对相关技术的意识形态解读和风险管理过程有关。很有可能由于极端化的观点和争论的升级而吸引更多的人加入。这些社会路线往往和风险管理相配套,并在这个过程中逐步清晰和坚定起来。由此有可能造成对貌似并不很大的风险的过度反应。由此,他们提出应当关注风险管理。这个管理不仅仅是社会风险的管理(即提供社会保险和保护来防范社会风险),而且包括对风险放大机制的管理。
Hood等人撰写的风险管理报告,确定了七个关键领域的争论和不同的思路:(1)主动预测和避免特定风险与一般抵御意外灾难;(2)系统应该在一定程度上追求减少指责,同时创造一种学习文化;(3)应使用定量或质性的手段来评估风险;(4)采用正统的工科方法来设计复杂的社会技术系统是否可行;(5)降低风险的成本,可能需要与其他目标和其他风险相平衡;(6)风险决策的参与程度 - 决策群体的最佳规模和构成;(7)确定适当的监管目标-结果还是过程?①Hood, C. C., Jones, D. K. C., Pidgeon, N. F., Turner, B. A. and Gibson, R. ‘Risk Management’, in Risk: Analysis, Perception and Management:Report of a Royal Society Study Group. London: Royal Society, 1992.
在过去一些年里,公共服务提供机构过度强调公共部门的风险管理,特别是强调通过公文表格的填写来实现免责。这种做法招致非常多的争议。往往为了避免风险却创造出新风险:增加了专业人员的焦虑和脆弱。使得他们在发现用户生活中的新风险时,采取更加保守的控制方法。避险的本质是社会服务中的保护和自治之间的平衡问题。涉及到应该保护谁的权利和自由,以及谁应该得到控制的决定往往是取决于对社会中不同群体和个人的相对价值的判断。从这个角度来看,关心风险在哪里会比关注需求和资源分配更关键。Alaszewski和Manthorpe对英国福利机构的研究表明,传统的以工作人员为中心而不是以用户为中心的官僚机构和福利机构往往依靠专家建议,惩罚错误并试图通过预测和预防风险来控制环境。相比之下,以用户为中心的机构则更加灵活,权力下放并重视个人判断。他们鼓励更多的人来参与决策,汲取错误的教训,并开发快速反应系统来处理问题,而不是花费大量精力来预测和预防特定风险。对公共机构避险行为的探讨比较多的是在2000年以后,英国出现了多起关于儿童虐待的案件。每一次都是由公共机构开除基层社工为结束。后来开除员工也不足以平民愤,机构的部门领导也一并被开除。导致社工纷纷辞职。Stalker认为社会服务的机构和从业人员的风险加大其实是来源于公众对公共服务体系和专家的信任下降。②Stalker, K. Managing Risk and Uncertainty in social work: A Literature Review. Journal of Social Work, 2003, 3(2): 211-233.
Munro对开除员工的做法提出异议,认为公共服务提供机构寻找替罪羊的避险行为直接导致公共服务人员也寻求自保,使得公共服务愈发变得程式化。这直接造成公众对服务的信任度下降,而不是提高。③Munro, E.. Managing Societal and Institutional Risk in Child protection. Risk Analysis, 2009, 29(7): 1015-1023.这就意味着,只从服务提供者的角度控制风险显然很不够。人对风险的认知本身也可以影响他们的安全感。对风险的认知可以受多种因素影响:文化上的偏见、心理特征、认知结构和所属机构。人们对风险的认识还有可能影响到他们的行为决策。因此,实际的风险,对风险的认识和风险管理三者是相互依存、相互渗透、并且存在互动的。但是对风险的认识不一定能够反应实际的风险。而且人们在判断风险大小的时候不光是考虑事件发生的可能性,而且还把结果放在一起考虑。所以即使某事件发生(再发生)的可能性并不很大,人们考虑到该事件造成的恶劣影响,也会自然而然地感到担忧甚至害怕,从而做出过激的反应。因此,Garland提出,从政策制定者的角度看,不能轻易地认为公众是受到蒙蔽的、非理性的或者是不懂科学的。政府需要倾听这种过激的反应,并创造条件让公民参与辩论和决策。这个参与的环节有助于公民增加对风险的认识。
二、经济危机及其对福利国家的影响
经济危机可以说是现代社会中最为重要的大规模和系统性的冲击。危机的到来充满不确定性,如何防范经济危机是经济学家多年来研究的问题,本文不再赘述。而对于经济危机造成的后果以及如何应对则有
Broadhurst, K., Hall, C., Wastell, D., White, S., &Pithouse, A. Risk, instrumentalism and the humane Project in Social Work: Identifying the Informal Logics of Risk Management in Children's Statutory Services.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Work, 2010, 40(4): 1046-1064.很大一部分属于社会政策的范畴。经济危机的影响有的是确定的,同时也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例如:经济衰退是肯定的,但是衰退的程度和时间长短是不确定的;经济危机必然面临失业增加, 但是其影响的范围和人数则难以确定。这些不确定性的因素使得每次经济危机到来之后会引起很多人的焦虑、恐慌,甚至会影响到人的精神健康①Rodrigues, D. F. S., &Nunes, C. Inpatient Profile of Patients with Major Depression in Portuguese National Health System Hospitals, in 2008 and 2013: Variation in a time of Economic Crisis. Community Mental Health Journal, 2018, 54(2): 224-235.Uutela, A. Economic Crisis and Mental Health. Current Opinion in Psychiatry, 2010). 23(2), 127-130.Gili, M., Roca, M., Basu, S., McKee, M., &Stuckler, D. (2012). The Mental Health Risks of Economic Crisis in Spain: Evidence from Primary Care Centres, 2006 and 2010. The Europe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23(1), 103-108.Roca, M., Gili, M., Garcia-Campayo, J., & García-Toro, M. (2013). Economic Crisis and Mental Health in Spain. The Lancet, 382(9909): 1977-1978.。
对个人来说风险有几个重要的层面。第一:由于经济衰退造成失业,收入减少,与失业困境相关联的健康问题增多。2007年以来的经济危机之后不难看到,中低收入群体在住房上的投资受到很大冲击。危机使得消费者对其他的服务行业,如旅游、商业的需求明显受到打击,并进一步影响到就业。第二、经济危机还有可能影响到人们对现行福利制度的态度。例如,在繁荣时期,人们对失去工作的人抱有比较大的同情心。纳税人并没有感到为这些人支付救济的经济压力。可是,在经济危机到来,财政压力增大的时候,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很多人人是被高福利制度“宠坏了”。从而支持更加严苛的救济制度。第三、国家的财政收入由于经济衰退而下降,导致可供福利国家支配的经费削减,形成经济紧缩。第四、由于福利国家被削减,福利制度的受益者收到进一步打击。上述几点之所以被视为风险,因为这些现象并不必然实现。个人不一定会在危机到来的时候失去工作,这一点并不难理解。而福利国家是否追求紧缩的经济策略和这些策略是否直接影响到社会福利体系,则要取决于各国采取的政策。
经济危机之后,更多的个人面对生活、就业和健康困境,但是他们的需要不一定能够得到满足。福利国家对经济危机的反应各不相同。从2008年的危机开始,有很多学者跟踪各个福利国家支出的变化。在危机到来之初,由于各国的制度惯性,不得不对更多的人提供失业救济金,加上危机之前的预算已经确立,很多国家的福利支出实际增长了。提出经济衰退确实有可能造成财政紧缩,但是福利国家并没有一套固定的应对经济危机的策略。而且虽然受到多次经济危机的困扰,欧洲的福利国家并没有发生质的变化。这些研究为Pierson在上个世纪90年代的理论提供了实证支持。例如:Steinebach等人提出危机对社会监管(sociaregulation)造成了冲击,促成社会政策标准的解体。但是,危机引发的政策解体仅限于对现有政策工具的调整。在不同宏观经济条件下社会政策组合的诸多结构性要素(例如社会政策目标或适用的政策工具)方面没有显著的政策制定模式差异。这表明经济危机不会导致福利国家的深刻转变,而只会导致财政紧缩②Steinebach, Y., Knill, C., &Jordana, J. Austerity or Welfare State transformation? Examining the Impact of Economic Crises on Social Regulation in Europe. Regulation & Governance, 2017.。Armingeon也提出国际金融危机只导致了紧缩,但是并没有带来更为现代化的福利制度③Armingeon, K. Breaking with the Past? Why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led to Austerity Policies but not to the Modernization of the Welfare State, 2013.。一味强调尽所有可能带来直接的社会影响。例如:Mladovsky,等人④Mladovsky, P., Srivastava, D., Cylus, J., Karanikolos, M., Evetovits, T., Thomson, S., & McKee, M. Health Policy Responses to the Financial Crisis in Europe, 2012.认为,2007年开始的全球金融危机可以视为是对健康系统的外部冲击 ,即一个发生在卫生系统外部的事件对健康系统的资金来源造成很大的负面影响,或间接产生巨大的卫生服务需求。经济震荡给政策制定者带来三大挑战:(1)卫生系统需要可预测的收入来源才能规划和投资、制定预算和购买商品及服务。公共收入流的突然中断可能会使其难以维持必要的医疗保健水平;(2)任意削减基本服务可能会进一步破坏健康。Karanikolos等人①Karanikolos, M., Mladovsky, P., Cylus, J., Thomson, S., Basu, S., Stuckler, D., & McKee, M.. Financial Crisis, Austerity, and Health in Europe. The Lancet, 2013, 381(9874): 1323-1331.的研究也发现:希腊,西班牙和葡萄牙采取了严格的财政紧缩政策。随着这些国家的经济继续衰退,保健系统的压力越来越大。传染病和自杀在这些国家日益增多,预算削减限制了医疗保健的可及性。经济衰退影响了健康,需要有社会支出的相应增加,但财政紧缩和社会保护的弱化无法满足更大的健康支出需要,最终加剧了很多欧洲国家的健康和社会危机②Simou, E., &Koutsogeorgou, E. Effects of the Economic Crisis on Health and Healthcare in Greece in the Literature from 2009 to 2013: A systematic review. Health policy, 2014, 115(2): 111-119.。相比之下,冰岛通过民众投票反对紧缩政策,金融危机对健康没有明显的影响。
经济危机和紧缩本身也冲击了社会的凝聚力。而社会凝聚力在过去一向被视为是达成社会政策共识的基础。Taylor-Gooby等人③Taylor-Gooby, P., Leruth, B., & Chung, H. The Context: How European Welfare States Have Responded to Post-Industrialism, Ageing Populations, and Populist Nationalism, 2017.用十个欧盟成员国的经验提出,在全球化、技术变革和人口老龄化的推动下,欧洲福利国家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经济衰退的后果和前所未有的移民水平带来了额外的压力。他们发现各国确实都或多或少地做出了基于新自由主义的紧缩反应,同时提出塑造福利国家发展的阶级凝聚力已经不再强大。围绕老年人、年轻人、女性和男性、移民和居民之间的分歧。在一个新的、更具竞争性的世界中,赢家和那些感到被遗忘的人之间的分歧变得越来越显著。欧洲国家已进入政治不稳定时期。紧缩在几乎所有地方占据了主导地位,但各国的反应各不相同,有的走向社会投资,也有的走向保护主义,还有的采取新凯恩斯主义反击模式。各国福利制度虽然仍然带有一定的传统福利制度模式的影子,但是其实际的政策更多地取决于其当下的政治辩论,从而把单个的国家带离Esping-Anderson的福利国家聚类。Starke 等人则进一步提出了福利国家规模的影响。他们分析了四个经合组织国家(澳大利亚、比利时、荷兰和瑞典)的福利国家对三大经济危机(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90年代的经济衰退,2008年金融危机)的反应。研究的政策范围包括中短期的社会权利的变化:养老金、医疗保健、积极和消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以及家庭转移支付和服务。他们提出,与传统的认识相反,各国对全球经济危机的政策反应差异很大。他们发现,从危机管理的政治角度来看,福利国家的规模很重要。在大型福利国家,危机管理可以依赖规模巨大的自动稳定器。通常针对劳动力市场中的弱势群体有比较一致的调整措施。在较小的福利国家,危机管理更多依赖相机的宏观稳定政策。它面对的冲突更大,因为会直接影响到福利国家的形态。额外的支出需要明确针对福利措施的“危机套餐”来解决。因此,这些措施很可能成为党派斗争的焦点。此外,政党和执政党的构成在危机应对方面有可能发挥关键作用,党派冲突和各方的影响都受现有福利国家配置的限制。在较不慷慨的福利国家中,执政党的组成对社会政策变化的方向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相反,在更为慷慨的福利国家,即那些拥有高度发达的自动稳定器的国家,政策变化的总体方向分岐较少。
这些福利国家的政治冲突更多地关乎扩张或削减是否必要。因此,通常不会显示明确的党派影响①Starke, P., Kaasch, A., & Van Hooren, F. Political Parties and Social Policy Responses to Global Economic Crises: Constrained Partisanship in Mature Welfare States. Journal of Social Policy, 2014, 43(2): 225-246.。这个观点和他们在之前分析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这样的规模比较小的福利国家的反应正相呼应。Starke发现 2008年金融危机后,澳大利亚围绕巨额财政建立了危机管理战略,刺激性政策带有很重要的社会政策色彩,而新西兰政府在实施财政刺激措施时,社会政策部分所占的比重很小,而且政府很快就回归到福利紧缩和以就业为福利的道路上来。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之间福利制度的差异在过去来源于其经济结构差异,比如澳大利亚有持续的矿业繁荣,社会保障资金来源相对稳定。另外,重大事件如新西兰基督城地震有可能影响到社会支出的结构。但是,近年来经济上的差异已经不能完全解释社会支出的差异,党派的意识形态是至关重要的因素②Starke, P. Antipodean Social Policy Responses to Economic Crises.Social Policy & Administration, 2013, 47(6): 647-667.。
紧缩政策本身也存在很大的风险,它不一定会使得经济回到正轨,而是有可能导致进一步的经济衰退,甚至更多的失业。面临偿债压力的政府往往采用紧缩政策,使政府收入更接近支出。紧缩措施也是欠债的政府向债权人和信用评级机构表发出自律的信号。平衡预算是新自由主义的逻辑,在危机后的决策中占据主导地位,并在大多数欧洲国家被选民所接受③Taylor-Gooby, P. Root and Branch Restructuring to Achieve Major Cuts: The Social Policy Programme of the 2010 UK Coalition Government. Social Policy & Administration, 2012, 46(1): 61-82.。甚至有社会政策学者也在探讨发达国家是否还能够承担得起福利国家制度 。④Farnsworth, K., & Irving, Z. Varieties of Crisis, Varieties of Austerity: Social Policy in Challenging Times. Journal of Poverty and Social Justice, 2012, 20(2): 133-147.但是,Clarke 和 Newman认为这样的政策因为得不到政治上的共识,面临道德上的挑战⑤Clarke, J., & Newman, J. The Alchemy of Austerity. Critical Social Policy, 2012, 32(3): 299-319.。即使不从道德角度考虑,紧缩政策是否能够达到预期的目标也是很大的问题。 在大多数宏观经济模型中,紧缩政策通常会增加失业率,因为削减政府开支会减少公共部门就业。此外,增税有可能导致私人企业成本上升,同时也可能通过减少家庭可支配收入来减少消费。因此,对于减少政府开支是否能够帮助经济走出衰退一直就有所争议。因为政府开支本身就是国内生产总值的一个组成部分,减少政府开支反而有可能导致债务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率升高。例如,在大萧条之后,尽管预算赤字减少,但在许多欧洲国家采取紧缩措施后,失业率和债务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不降反升。这就招致对自由主义的反弹。更有甚者,受紧缩政策影响最大的群体往往是社会底层的人,因而被称为是自己跟自己过不去的政策(self-defeating)⑥Holland, D., &Portes, J. Self-defeating Austerity? National Institute Economic Review, 2012, 222(1): F4-F10.Müller, G. J. Fiscal Austerity and the Multiplier in Times of Crisis. German Economic Review, 2014, 15(2), 243-258.。即使存在这些反对意见,紧缩政策还是得到了实施。可是,从后来的发展来看,欧盟国家的极度紧缩政策带来了更为深远的政治影响。在民粹主义盛行的国家,对自由贸易、移民的反对变得日趋明显。可以说,法国的勒庞和欧洲的脱欧运动都与前一时期的极度紧缩有关。它使得居于社会底层的“本地人”感到自己是被政府抛弃了,就业机会或者输出到发展中国家,或者被外国人抢走了。这些异议导致了福利沙文主义的抬头⑦Cavaille, C., &Ferwerda, J. Understanding the Determinants of Welfare Chauvinism: the Role of Resource Competitio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June 2015), 2016, p1-29.。福利沙文主义是一个政治上的概念,即福利应该限于某些群体,特别是一个国家的本地人,而不是移民。这个思路热衷于把一国的居民分为两个极端:掏钱的人和无能的人,强调他们在社会稀缺资源竞争中的矛盾。它被右翼民粹主义政党所利用,认为福利国家问题与本质上是移民问题,以及福利领取者和失业者与其他社会群体之间的矛盾①Jørgensen, M. B., & Thomsen, T. L. Deservingness in the Danish Context: Welfare Chauvinism in Times of Crisis. Critical Social Policy, 2016,36(3): 330-351.。
而另一方面,来自于新凯恩斯主义的思路试图综合扩张性支出的需要与减少“福利养懒”的需要。社会投资沿袭了这套逻辑,强调国家干预,越是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越需要有更多的国家支出来从事社会投资、由政府来扩大机会,促进增长。从某种意义上看,它是与居于主导地位的新自由主义相配合的。社会投资并不是一个新的概念,它较多地与教育联系在一起。所谓“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的理念本身就是社会投资的概念。它强调现在的支出有可能成为将来的回报。为此,教育、培训以及儿童保育领域的社会投资已经由欧盟所倡导,并纳入到2020年欧洲计划以及国家层面的政策中②Morel, N., Palier, B., & Palme, J. (Eds.).Towards a Social Investment Welfare State?: Ideas, Policies and Challenges. Policy Press, 2012.。Vandenbroucke等人③Vandenbroucke, F., Hemerijck, A., &Palier, B. The EU Needs a Social Investment Pact. Observatoire Social Européen Paper Series, Opinion Paper, 2011, p5.分析过去社会投资实践中的问题指出:(1)社会投资应该是一揽子计划,部分实施可能最多可以取得部分成功。社会投资的视角是基于生命机会/生命过程的视角。只有在整个产业链得以保持的情况下才有效,从幼儿教育和照顾到终身教育训练和积极老龄化都需要有相关的政策跟进;(2)虽然社会投资范式没有“挤出”传统福利。过去二十年的项目表明,社会投资战略并不是一个便宜的选择,不会带来大量的预算节省,在短期内更不会得到这样的效果;(3)社会服务的质量是社会投资策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投资功能本身应该是平等主义的,而不是加剧不平等,儿童保育和教育的影响应该是减少社会不平等。只有高质量的儿童保育才能长期发展影响儿童的能力和成功,并有助于减少社会不平等。出于同样的道理,让人们重新回到劳动力市场去接受“任何工作”并不会产生好的结果。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可以被看作是社会投资的要素,应当被视为社会促进的工具。而低质量的就业激励效果会很差;(4)社会投资策略是(必要的)供给侧战略,它不能取代宏观经济治理和健全的金融监管。社会投资策略必须是支持持久性的宏观经济治理和金融监管,以及实体经济均衡增长。但是,从目前很多国家(斯堪的纳维亚国家除外)的做法来看,社会投资并没有像理想中的那样以为人们提供暂时庇护为目标,而是成为新自由主义者借以推行期待回报的福利投资④Nikolai, R. Towards Social Investment? Patterns of Public Policy in the OECD World. Towards a Social Investment Welfare State, 2012, p 91-116.。
三、结论
本文以风险为视角回顾了社会政策领域对风险的认识的不断丰富,即从传统的由“不幸”带来的风险,到工业化社会和后工业化社会制造的风险,再到由社会政策和公共服务机构造成的风险。以对风险的认识和应对为出发点,也可以把社会政策理论的各个流派和视角进行梳理。在此基础之上,本文分析了经济危机(特别是2008年以来经济危机)产生的新的社会风险和各国的应对方式。总体上,无论是从风险的产生还是应对方面来看,这次危机和过去的风险防范和救助的社会政策理论一样,向世界各国提出一个挑战:如何在不妨碍经济竞争力的前提下为社会成员创造更大的安全感。而经济危机全面冲击了社会安全感的基石,使得社会愈发分化。分化又进一步摧毁了福利制度的社会认同基础,从而导致强调群体、阶层和公民身份的福利沙文主义盛行。
社会投资的理念或许是能够把人们从急于自保、相互诟病的状态中解放出来,以更长远的眼光来看待一国经济竞争力的积累和安全感的平衡。但是,从目前实践看社会投资理论无法化解“排外”的问题,而且也有可能被用于其他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