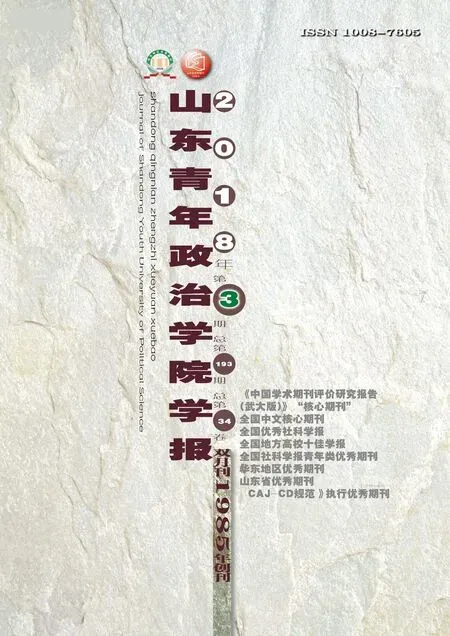融入乡土 超越苦难
——浅析莫言小说《白狗秋千架》
王爱侠
(山东管理学院,济南 250100)
莫言自1981年凭借小说《春夜雨霏霏》登上文坛以后,就在积极探索自己的创作方向,直到1984年与福克纳的作品相遇,他才笃定了要创造一个属于自己的“体系”的决心。此后他进入自己创作的一个重要转捩点,其中,《白狗秋千架》这篇小说就是这一转折时期的重要作品,小说以“高密东北乡”开篇,尽管语言尚未出现莫言后来作品当中那些丰富淋漓的意象,但是可以说,这篇小说是莫言“高密东北乡”文学王国的一个“具体而微”的奠基者,文中涉及到了莫言小说创作的诸多元素,这些元素在他此后的创作中不断丰富和拓展,进而构成了一个属于莫言也属于世界的文学风景。
一、返乡:融入乡土的深度介入
返乡是文学创作中的一个长盛不衰的话题。无论是中国古典文学中浮云游子“近乡情更怯”的返乡,还是西方文学中尤利西斯历经十年坎坷而得以永劫回归式的返乡,都是以故乡为坐标,表达对于远行者的一种召唤。从某种程度上讲,故乡是一种守望,是可以让漂泊者安顿灵魂的家园。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返乡”是小说主人公的渴望,也是文学作品表现的核心主题。但米兰·昆德拉的小说《无知》却对返乡进行了意义解构,主人公阔别家乡多年之后终于得以返乡,却发现自己不认识家乡,家乡也不认识自己了,主人公与留在家乡的亲人共进晚餐时,因为语言和心灵的双重隔膜而产生了沟通的尴尬,这一番寻找精神家园的“返乡”行为显得荒谬,因为这种形式的“返乡”非但不能安顿灵魂,反而使灵魂陷入更深的失落与惆怅。
还有一种形式的“返乡”在文学作品中大量存在——离开家乡的人,在经历了新的生活之后,以“外乡的文明世界”为坐标,通过“返乡”来衡量家乡的文明程度。在二十世纪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知识分子返乡”是精神与思想启蒙的一种重要模式,许多乡土文学的创作者都是走出乡村的城市人,经历了现代性的文化思想及生活方式的洗礼之后,他们所叙写的“返乡”,往往带有浓重的启蒙色彩,对于乡土生活中的愚昧和落后,主人公持同情或者批判的态度,这种置于乡土之上的俯视,可以说并非思想与情感上的深度介入——这也是启蒙话语不能通畅地抵达被启蒙者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鲁迅的《故乡》是“知识分子返乡”的经典文本,在小说中,阔别家乡多年的“我”在返乡后惊诧于家乡的巨变,尤其是闰土和杨二嫂,只能隐约辨别出当年依稀的影子。这种巨大的变化使“我”震惊和悲哀,但究其根源,无论是中年时期闰土的辛苦麻木,还是如今像“圆规”一样的杨二嫂的辛苦恣睢,责任都在社会,是辛亥革命之后农村的日益凋敝使得家乡的人生活日益悲惨,小说在悲凉的氛围中艰难地寻找着希望——“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1]——小说中的“我”凭借知识分子的良知与责任,在绝望与希望中交织着对于新生活的追寻。尽管如此,知识分子与农民之间的隔膜并没有因为这种感情的强烈而打通,如同闰土和“我”之间的厚障壁难以打通一样。
二十世纪百年发展历程中,知识分子(城市)与乡村之间一度转换过不同启蒙角色。新时期文学创作依旧对于“城市与乡村”予以关注,经过奋斗的农村青年成为城市的知识分子之后返乡回望,成为一种书写模式。莫言的《白狗秋千架》虽然也采用了“知识分子返乡”这一叙述方式,但在这一城乡之间的关联结构中,主人公作为城市的知识分子,却以乡村的“在地者”身份进入小说的叙述中,并以身心与情感的深度介入的方式进入了乡土。当然,这乡土是藏污纳垢的民间,是有着沉重的劳作以及寡淡的欢乐的地方,莫言本人在回顾自己乡村生活的时候曾经痛楚地说:
十五年前,当我作为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在高密东北乡贫瘠的土地上辛勤劳作的时候,我对那块土地充满了仇恨。它耗干了祖先们的血汗,也正在消耗着我的生命。我们面朝黑土背朝天,付出的是那么多,得到的是那么少。我们夏天在酷热中挣扎,冬天在严寒中战栗。一切都看厌:那低矮、破旧的茅屋,那些干涸的河流,那些狡黠的村干部……[2]
这样的乡村,就是《白狗秋千架》这篇小说的背景,小说讲述了离开乡村读书工作的“我”十年后回到家乡,遇到了青年时的伙伴——暖。年轻时,暖和“我”都喜欢音乐,梦想参军但是愿望没有实现。后来暖和“我”在荡秋千的时候出现意外,从此失去了一只眼,也失去了歌唱的梦想和进城的希望,成了一个只能在乡间劳作的地地道道的乡村妇女。
作为“返乡”小说,《白狗秋千架》将“我”置于事件之中,主人公暖的不幸,“我”难辞其咎,所以,尽管十年来,我一直生活在远离乡村的城市,家乡的音信皆无,但是我心里总觉不安,这种不安,实际上是对于暖的一种牵挂和亏欠——小说就这样丝丝缕缕地将“我”和暖的命运微妙地连接在一起。
莫言小说中的城市知识分子,以一种深度融入乡土的姿态出现,没有居高临下的俯视的姿态,因为他自己本身就是乡土的一部分。初到家乡,“我”首先见到的是黑色爪子的白狗:
狗眼里的神色遥远而荒凉,含有一种模糊的暗示,这遥远而荒凉的暗示唤起内心一种迷蒙的感受。[3]
从某种程度上说,这只白狗也是莫言小说动物书写的开端,莫言笔下的动物往往有通灵的品性。这只白狗就在小说劈头出现,仿佛是“暖”的生活象征,又仿佛与“我”有着某种内在的联系,遥远而荒凉的眼神里面有无法释怀的忧伤,正预示着将要出现的主人公之一——暖正在过着一种毫无希望的生活。在“背着大捆高粱叶”的人出现的时候,“我”对于劳作有一番真切的感受:
我在农村滚了近二十年,自然晓得……我很清楚暑天里钻进密不透风的高粱地里打叶子的滋味,汗水遍身、胸口发闷是不必说了,最苦的还是叶子上的细毛与你汗淋淋的皮肤接触……
我为自己轻松地叹了一口气。[4]
正因为清楚其中辛劳的苦涩,所以才对背高粱叶的人有一种感同身受的叹息。当然,这叹气声,既包含着对于自己终于摆脱了农村劳作的庆幸,也包含着对于劳作者的深深同情。莫言丝毫不避讳自己心灵中微妙的感情,一声“叹气”,将“知识分子”面对劳苦大众有可能呈现出来的拯救者姿态改变成一个普通民众的姿态,甚至“我”还带有小农意识,为终于摆脱了乡下人的身份而庆幸——这也正是这篇小说与其他小说的不同之处,在鲁迅一代启蒙者的写作中,这样的叹息声是没有的,因为莫言没有把自己定位为“启蒙者”,而不过是一个成功的“逃逸者”。
《白狗秋千架》的故事就这样展开:一个已经拥有一定社会地位的“城里人”,和一个辛苦疲惫邋遢不堪的“乡下人”,在这一时刻相遇。记忆中闪回的是十几年前的生活,那时候的暖是美丽的,是拥有无限憧憬和无限希望的幸福女子,和今天这位从高粱地里背着高粱叶子的暖相比,就如同少年闰土之于中年闰土,“豆腐西施”之于“圆规西施”。但不同之处在于:闰土、杨二嫂的悲剧性遭遇来自社会,暖的不幸,来自我当年无意当中的一次荡秋千的召唤(暖就是此次从秋千架上摔下来掉到刺槐从中而瞎了一只眼睛),也来自我进城之后对她的放弃。
二人相见之后的对话,几乎完全在不对等中展开:一个地位优越者努力低调,却始终无法与地位卑微者进行平等的对话。后者对于艰难生活的怨怼和不满自然是情理之中的:因为前者的出现,一方面唤醒她过去的记忆,另一方面又与自己的现状形成鲜明的对比,这无疑使得她当下的生活显得更加暗淡。所以,暖几乎用极其粗俗的话来回应“我”对于家乡的惦念——
有什么好想的,这破地方。想这破桥?高粱地里像他妈×的蒸笼一样,快把人蒸熟了。[5]
我无比尴尬与不安,但话题总要进行下去,我于是问她有几个孩子,她说:
一胎生了三个,吐噜吐噜,像下狗一样。[6]
这些自贬的粗俗的毫无羞耻感的话,从一度美丽可爱但现在邋遢不堪的暖的嘴里说出来,我内心的不安变得愈发强烈,于是,我只能“缺乏诚实地笑着”。我和暖的初遇就这样结束了。随后,我造访暖家,她自己的家就在邻村王家丘子。
我很希望能够在桥头上再碰到她和白狗,如果再有那么一大捆高粱叶子,我豁出命也要帮她背回家。[7]
“豁出命”里面包含着丰富的意蕴,虽然“我”不能够分担她的不幸命运,但却渴望将这一捆沉重的高粱叶子背在肩上,也许对于多年生活在城市的“我”来说,背一大捆高粱叶有些力不胜任,但是“我”还是想借此表明自己内心对于暖的情感并未消失,同时也想减轻萦绕在心的愧疚和不安。然而,暖并没有出现在路上,“我”也就没有背高粱叶的机会了。当我走到暖的家,面对暖的哑巴丈夫的丑陋和粗俗,我的记忆迅速闪回到当年暖所心仪的风度翩翩的蔡队长。如果说这种对比有些残忍,那么,暖的小孩子的出现加剧了这种残忍的程度——
却见三个同样相貌、同样装束的光头小男孩从屋里滚出来,用同样的土黄色的小眼珠瞅着我,头一律往右倾,像三只羽毛未丰、性情暴躁的小公鸡。[8]
鲁迅《故乡》中“我”初回故乡,到了家门口,就“飞”出了八岁的侄儿,一个“飞”字带着孩子的天真与活力,给沉闷的家乡涂上一点亮色,这也正是鲁迅所希望的“亮色”。但在《白狗秋千架》中,暖的三个孩子是从屋子里“滚”出来的,而且后文中还描写,为了争抢我给他们的糖果而挤做一团,如果说,哑巴丈夫是暖在残疾之后无望的选择,那么,她所孕育的新生命也并未给她任何新的希望。看到这一切,“我”内心的负罪感更为强烈。离开暖家之后,在白狗的引领下,“我”见到了在高粱地特意等待我的暖,(值得一提的是动物书写是莫言写作中的一个重要元素,在《白狗秋千架》故事情节的开端处有一只眼神“遥远而荒凉”的白狗,后来我造访暖家的时候,面对客人,白狗用善良和温顺的叫声向主人通报,而暖的哑巴丈夫以及三个孩子却粗野蛮横,动物的优雅与人的缺少教养形成鲜明的对比,行文中溢生出一种“人不如犬”的悲哀。小说的最后,又是充满灵性的白狗将我引到了暖所在的高粱地——在莫言的文字世界,动物具有人性,甚至神性,从《红高粱家族》到《生死疲劳》,那些精彩的动物描写可以说是独特的动物风景。)暖告诉“我”,当年之所以在“我”进城后故意不给“我”回信,是因为觉得自己破了相,配不上“我”了。此时此刻的暖,非常认真地向我提问:你说实话,要是我当时提出要嫁给你,你会要我吗?“我”说:“一定会要的,一定会。”[9]
这句话,是“我”离开乡村十年之后的对于自己过去恋人的一种表白,是“我”始终不能够将自己与故乡分开的一种感情,这也是一个回到乡村生活中的知识分子,面对活生生的苦难所产生的良知的震动。正是这种表白,使小说中的“我”成为真正融入这片乡村土地的人。
《白狗秋千架》中的知识分子返乡,卸去了文学史中这一叙述模式的启蒙色彩,将知识分子的身心融进土地,与那片土地上的人一样,感受到贫困与艰辛对心灵的沉重压迫。这正是莫言“作为农民写作”的价值取向,它在这篇小说中已经初露端倪,此后更将其发挥得淋漓尽致——莫言让自己的写作与乡村生活成为水乳交融的一体。
莫言出生于底层,成长于民间,多年的农村生活经验使得他切身感受到了中国农民的悲哀与欢乐、痛苦与希冀,他通过自己个体的、具体的生活经验营造了他的高密东北乡世界。他小说中的人物,即使是远离家乡的知识分子,不管是隔多久,只要返乡了,就够深度融进家乡的土地,从而呈现出那一片土地上特有的生命意义。
二、苦难:直面乡土的残酷现实
苦难叙事是文学的永恒主题之一。“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杜甫《天末怀李白》),“文学是苦闷的象征”(厨川白村),都在说明一个共同的问题:最容易被文学作品选择的内容,往往就是苦难的生活。 苦难的来源有很多种,有来自个人性格的悲剧因素,有来自社会的动荡带来的灾难,有来自自然的艰险等等。从某种意义上讲,,苦难可以看作是人存在的本质困境,且往往带有一种深刻的悲剧色彩。
《白狗秋千架》描写了乡土现实中的苦难。一个社会学家完全可以从《白狗秋千架》的文本中看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城乡差异所形成的二元对立,农村作为一个贫瘠的、压抑人性的、让人感到窒息的地方,是被年轻人摈弃的。与之相反,城市则是富足的、文明的所在,做城市人、吃公家粮——这几乎是那个时代大部分农村青年的最高理想。《白狗秋千架》中的“我”无疑是幸运儿:离开了农村,成为城里人,而且成为知识分子。然而,暖却是不幸的,她不得不胶着在土地上承受生活的痛苦和劳作的艰辛:
她的头与地面平行着,脖子探出很长。是为了减轻肩头的痛苦吧?她一步步挪着,终于上了桥。[10]
从她“探”出的脖子和“挪”动的脚步,可以看得出所背负的重量几乎超出肉体的承载能力,所以她用几乎是变形的身体姿势承受那一捆巨大的高粱叶的重负。当她听到我喊她并且认出“我”之后:
她左腮上的肌肉联动着眼眶的睫毛和眶上的眉毛,微微抽搐着,造成了一种凄凉古怪的表情。[11]
“我”是暖旧日生活的见证人,是那些青春快乐时光的存留者。“我”的出现,毋庸置疑将暖的今昔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所以她在这种交互错杂的感情中,面部显出凄凉古怪的神情。除了劳作的艰辛,更令暖绝望的是承受家庭生活的困窘和粗俗,说起自己的境况,暖似乎没有什么表情地说了下面的话:
孩子落了草,就一直悬着心,老天,别让他们像他爹,让他们一个个开口说话……他们七八个月时,我心就凉了。那情景不对呀,一个个又呆又聋,哭起来像擀面柱子不会拐弯。我祷告着,天啊,天!别让俺一窝都哑了呀,哪怕有一个响巴,和我作伴说说话……到底还是全哑巴了。[12]
暖青年时期天生丽质,且善于歌唱,本来拥有足够的条件可以进城,即使那个蔡队长食言,还有一直喜欢她的“我”曾一度从城市向她发出召唤,然而,她因为残疾而自惭形秽,不愿意拖累我。最终,她嫁给了哑巴,也嫁给了苦难。
莫言的多部小说都触及到了现实中的苦难,甚至一些极其残酷的极端处境下的悲惨现状也被莫言描写了出来,成为惊心动魄的场景。比如《透明的红萝卜》中那个手中抓着烧红的铁钻的男孩;《枯河》中那个无意中闯祸而被父母爆打的男孩,都在行文中弥漫着一种令人窒息的残酷气氛。莫言之所以如此执着于乡村的灾难和痛苦,是因为它们是莫言乡村经历和乡村生活的写照——而他自己就是这些痛苦曾经的承受者。莫言多次在公开场合讲了自己少年时代的苦难。然而,莫言对于苦难的书写并非为了展示伤疤,更不是为了诠释人类种种苦难的必然性,其目的既是要表达一种直面现实的勇气,更为了完成一种灵魂的救赎与精神上的超越。
三、救赎:悬置道德审判的抉择
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有大量的关于苦难的书写。在关于诸多苦难遭遇的书写中,有一种来自命运的悲剧性力量常常被定格为人力所不能转圜的。比如莎士比亚经典作品中的俄狄浦斯悲剧,任凭主人公使尽浑身解数,也难逃命运的掌心——俄狄浦斯终究被弑父娶母的预言所击中,以至于自罚失明而远走他乡。至于现代意义上存在的悲剧性苦难,无论是卡夫卡的测量员还是搬运石头的西西弗斯所经历的人生,都代表了人类存在意义上的精神局限——这一切都必然存在,不可更改。
如果生命不得不在燃烧的烈焰中经历煎熬,那么如何完成对于苦难人生的拯救,是一切宗教与哲学寻求救赎学说的动力——基督教《圣经》将拯救的希望寄托给万能的上帝,而将幸福的希望寄托到来世,而佛教则将拯救的希望寄托给佛祖,深信潜身修行便可得因果轮回。但宗教并不能消除现实生活中的苦难,只不过试图对苦难进行释义和转化,让苦难变得有意义和有必要,从而在人的精神上实现自我救赎与超越。
从某种角度讲,面对苦难的态度,最能够彰显一位作家的精神追求。在西方小说中不乏苦难与拯救的经典文本,比如,《战争与和平》中的女主人公娜塔莎,在被安德烈抛弃之后,沉疴不起,后来在晨祷当中获得了灵魂的拯救;《喧哗与骚动》中的迪尔西带领班吉到教堂听牧师布道,并由此感受到了上帝的裁决——她说:“我看见了初,也看见了终。”这些小说都采用了经典的宗教拯救模式。当然,文学作品本身无需社会学意义上的论证,更不一定需要开出疗救的药方。但文学又并非独立于社会生活之外而存在,文学的文本总能够潜隐地告诉我们,一个作家在否定的什么、谴责什么,或者说希望什么。
在上世纪初,启蒙行动面对大众的愚昧与苦难,希望通过更广泛的精神引导来唤起社会的革命的力量:革去旧的疮疤,换来新生的肌体和灵魂。但是,若要完成真正的社会革新,除了作为先导的思想启蒙行动进行精神与文化的传播外,还需要依赖更为强大的社会力量的推动才能完成。因此启蒙者常常会产生一种目标的虚无感以及自我的无力感,这是鲁迅在一生当中感到“缠绕如毒蛇”的一种情绪,于是,他用一种“肩住黑暗闸门”的勇气来反抗绝望,并希望新生一代会有美好的生活。
莫言在《白狗秋千架》中同样面临着苦难与拯救的问题,“我”所见的故乡显然也流露出愚昧落后的气息(从大家对于牛仔裤纷纷指责就可以看得出),尤其是我所牵挂的暖的生活在一种毫无希望的苦难之中,“我”的愧疚之情日益加深。在此,莫言没有选择用宗教的方式去拯救或解脱受难者(即使在《丰乳肥臀》中有宗教的成分,但是宗教的影响毕竟比较薄弱),不会让暖在晨钟暮鼓的宗教精神中平息内心的苦闷;同时,莫言又不愿意站在启蒙者的立场上,给蒙昧者以虚饰的光明和无谓的承诺。
暖为自己选择了这样一条“看似实际可行的”拯救之路——她要求与“我”在高粱地野合,她期望因此而能够得到一个健康的孩子,从而使苦难的生活有拯救的希望。这一要求,虽然有悖于伦理道德,但又有其努力超越苦难的精神诉求——小说因此而产生出了巨大的张力。暖的这一要求对“我”这个大学里的知识分子来说是一个极其艰难的选择,因为无论“我”答应与否,都会遭受道德的裁判。
在《白狗秋千架》中,莫言悬置了答案,因而也就悬置了道德审判,给读者留下了想象的空间。正如布斯所说:“他早就确信,最‘富有人性’的主题是那些反映了生活的道德歧义的主题。”[13]当然,这种答案在他此后的多部小说中陆续给出——这一情节与在《红高粱》中“我爷爷”和“我奶奶”在高粱地野合的情节如出一辙,更是与此后《丰乳肥臀》中上官鲁氏不断为自己寻找生路异曲同工,当然也与《檀香刑》中的眉娘的价值取向相一致。
事实上,尽管莫言在他的诸多小说中描绘了乡村生活的残酷,但他并没有在小说中提出强烈而明确的社会变革诉求(从某种意义上说,揭示苦难本身或多或少地隐含着这样的诉求),在乡村苦难的书写中,小说家沿着乡土所氤氲出来的自然气息,书写了受难者所采取的反抗方式。这一方式既简单又原始——拒绝了宏大叙事的面孔,远离了道德说教的刻板,超越伦理道德的规约,直奔看得见摸得着的真实幸福。也许正因为这种寻求具有强烈的“在地性”,既是来自乡土的个体生命的追求,也是乡野生命力的自然流露和爆发,因而产生了一种摄人心魄的强悍力量。莫言曾经说:
作家千万不要把自己抬举到一个不合适的位置。尤其在写作中,你最好不要担当道德的评判者,你不要以为自己比人物更高明,你应该跟着你的人物的脚步走。[14]
实际上,在莫言的创作里,始终都在拷问故乡土地上存在着的灵魂和肉体,而最终表达的,就是生存空间的艰难与在艰难中的自我救赎和自我超越。
可以说,莫言的“高密东北乡”文学风景从《白狗秋千架》这里拉开了序幕,作家始终都没有把自己当做一个高高在上的启蒙者或者拯救者,而是将自己深深地融入高密东北部的乡土之中,成为其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参考文献:
[1]鲁迅.鲁迅全集[M].北京:中国致公出版社,2001:1517.
[2]莫言.我的故乡与我的小说[J].当代作家评论,1993,(2).
[3][4][5][6][7][8][9][10][11][12]莫言.白狗秋千架[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2:197,198,203,204,206,208,214,198,202,213.
[13][美]W.C.布斯,著.小说修辞学[M].华明,胡晓苏,周宪,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7:53.
[14]莫言.文学创作的民间资源——在苏州大学"小说家讲坛"上的讲演[J].当代作家评论,20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