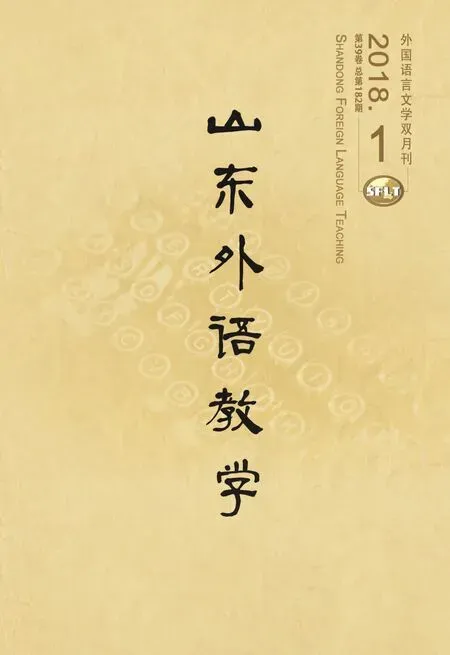乔伊斯文学批评思想中的非洲情结
张敏,谭惠娟
(1.浙江金融职业学院 国际商学院,浙江 杭州 310018;2.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外国语学院,浙江 杭州 310018)
1.0 乔伊斯非洲情结的根源
乔伊斯(Joyce Ann Joyce,1949- )是当今美国文坛才华横溢但饱受争议的非裔文学批评家,在非裔研究、美国文学以及女性研究等领域颇多建树。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非裔美国人的种族状况和经济状况的改善,众多美国非裔文学批评家倾向于运用白人主流批评理论来解读黑人文学作品,而乔伊斯则强烈反对这种做法,主张非裔文学批评理论一定、也必须秉持非洲文化和黑人历史。她通过专著、文章、演讲等各种形式铿锵有力地呼号非裔文学理论界坚持非洲情结,对作品无论是批评还是支持,都是对黑人名族的激励和鞭笞,都是在构筑黑人从中汲取力量的精神家园。乔伊斯浓重的非洲情结是融化在血液中的,是名族历史和个人经历的双重作用形成的。
1619年西班牙海盗船船长为了获取食物,把17名非洲人作为“人货”卖到了北美大陆的詹姆斯镇,这17名非洲人踏上北美土地的脚印开启了黑人在美国血与泪的历史,同时也将璀璨的非洲文明之种播撒到北美土地之上。这些来自非洲的黑人奴隶,在奴隶制中繁衍着、煎熬着、斗争着,随着时间的流逝渐渐适应了当地的生活环境。尽管白人社会并不愿意承认,也不把他们当人看,他们还是在残酷的环境下慢慢变成了非裔美国人。18世纪40年代后黑人奴隶的数量急增,他们带来的非洲文化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不少非裔美国作家比如詹姆斯·欧铁斯就指出“所有殖民地的居民都是生而自由的”(Bruce,2001:6)。在这个时期的非裔美国人创作了民间传说、劳动歌曲和号子、歌谣等民间口头文学,这成为非裔美国文学的重要源头之一。经过南北战争与马库斯·贾维领导的黑人运动的洗礼,非裔美国文学从萌芽阶段进入到成熟期,即20世纪20年代的哈莱姆文艺复兴。这一时期的非裔美国文学突出种族意识、黑人自我意识和非洲文化意识。到了20世纪30年代一种文化融合主义或者称作文化同化主义开始蔓延到非裔美国文学批评界,大多数这一时期的批评家认为非裔美国文学不是存在于美国文学之外的,而应是美国文学的有机组成部分。
60年代开始一批批评家以巴拉卡、拉里·尼尔为代表,开始主张“去美国化”的文学理论观,他们致力于追求探索非裔美国人作为黑人的文化独特性,这种思想成了60年代到70年代非裔美国文学的核心美学理念。此时也正值乔伊斯的青年时代,乔伊斯承认自己是黑人艺术运动中作家的“带有学者气质的学员,(我的)作品反映了黑人美学的理念和风格。①”倡导“黑人权力”的政治主张成为黑人追求自我定义的准则,挑战美国社会一切不利于这个自我定义的思想和行为。70年代,“黑人权力”运动和黑人艺术运动合二为一(庞好农,2013),后者是黑人政治意识的艺术表达,并强烈反对任何疏远黑人社区的艺术行为。 黑人艺术是“黑人权利”概念的精神姊妹(庞好农,2013),这两者对于乔伊斯批评思想的形成影响深远。
从70年代末期开始,以盖茨、贝克为代表的非裔美国文学批评家又倡导了一次理论范式的转变(周春,2016)。他们主张要真正发展非裔美国文学仅仅重视文学文本创作是远远不够的,一定要重视审视以往文学作品中的黑人美学。从而构建黑人文学的批评理论体系,而这种批评理论应该以后结构主义等西方主流文学批评理论体系为基础。他们在自己的文学批评实践中践行了自己的理论主张,开始用后结构主义等西方批评理论解读美国黑人文学,并建构理论体系。这意味着这一时期的非裔美国文学批评开始注意文本、语言和叙事结构等形式研究,对文本所反映的政治文化等的外围研究渐渐减少了。无疑,贝克和盖茨的这些理论和实践有利于非裔美国文学的制度化、学术化,因此也受到了主流文学批评界的推崇。随之,许多贝克和盖茨理论的追随者也进入了美国的主流教学和科研机构。
然而,非裔美国文学研究应该把政治意义放在首位,还是应该自由展现美学特点,非裔美国文学批评理论到底应不应该把所谓的西方主流批评理论奉为经典,这些几乎一直在美国非裔文学史和批评史上存在争议。贝克和盖茨的批评思想也受到了乔伊斯为代表的文学批评家的强烈质疑,引发了一场旷日持久、影响深远的文学理论论战。乔伊斯坚定地认为文学的主要功能是唤醒、教育、救赎同胞揭露白人社会对黑人的压迫、歧视和迫害。文学批评理论也完全没有必要讨好似的套用所谓的西方主流批评理论的框架,而一定要把非洲文化作为文学批评理论的原点和中心。
乔伊斯的个人生活经历也给她的灵魂系上了非洲情结。乔伊斯的出生地是美国佐治亚州朗兹郡的政府所在地瓦尔多斯塔市,佐治亚州是非裔美国人和黑人的主要聚集地之一,占其人口的比重将近三分之一。瓦尔多斯塔曾经是美国长绒棉花的种植中心,历史上大量的黑人被奴役从事棉花种植。乔伊斯1970年毕业于瓦尔多斯塔州立大学,这一年是瓦尔多斯塔实行种族隔离的最后一年,乔伊斯是该大学早期为数不多的几个非裔美国学生之一。大学毕业后她进入佐治亚大学攻读英语硕士学位,1972年毕业后回到瓦尔多斯塔州立大学任教,她是在该校执教的早期的几位非裔美国人之一。她于1974-1979年到佐治亚大学攻读美国文学博士学位,先后担任助教和讲师。1979年博士毕业后在马里兰大学帕克分校任副教授,1990年作为正教授任教于内布拉斯加大学。1992年在芝加哥州立大学的格温多琳·布鲁克丝研究中心担任副主任,后成为该校黑人研究所主任。从1997年到2001年在天普大学担任美国非裔研究所主任,目前在该校的女性研究中心任职。乔伊斯在佐治亚大学就学期间,给她上课的教授几乎清一色是南方人,许多是在瓦尔多斯塔接受的教育,是重农派或者新批评文学批评流派的后裔。受他们的影响,乔伊斯非常重视文本的细读。通过罗伯特·斯坦普多和德克斯特·费雪编写的《非裔美国文学史:结构重构》(Stepto & Fisher,1979: 45),乔伊斯了解到黑人作家批评中居于统治地位的社会主义学派正在被某个将语言与社会体制隔离的新学派所取代。通过对该书的阅读,乔伊斯开始理解阶级、文化和意识形态三者间的相互关系。
另外,许多非裔文学家和批评家对于乔伊斯批评思想也具有深刻的影响,其中尤以理查德·赖特和索妮亚·桑切斯为重。乔伊斯初次接触赖特的作品是在读博期间。一次偶然的机会她阅读了赖特的《土生子》,立即被主人公比格·托马斯所吸引,接下来阅读了佐治亚大学图书馆所有赖特的以及与其相关的著作。最后决定将赖特作为毕业论文的选题,从此开启了赖特的研究之路。“对赖特来说,生存的最高境界就是无所畏惧的批判思想与公平正义的政治责任并存”(谭惠娟、罗良功,2016:169)。乔伊斯也像赖特一样“敢于直言不讳地表达自己的文学思想”(谭惠娟、罗良功,2016:178),力求做一个自由思想家,由此可见赖特对乔伊斯的影响至深。乔伊斯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讲解和研究桑切斯的诗歌。她理解桑切斯艺术的复杂性,了解并深入研究了其作为一个诗人走向成熟的过程,以及作品的多样性。桑切斯作为一位女性,一位黑人女性,一位诗人,一位剧作家,她敢于挑战和摧毁针对黑人艺术、黑人女性、黑人以及其他有色人种的反人道主义观念。乔伊斯在赖特和桑切斯研究上成果颇丰,而她在文学批评思想上的左倾转向与二者的影响不无相关。
2.0 乔伊斯非洲情结的内涵
非洲情结是对非洲文明的溯源和回归,它贯穿于乔伊斯文学批评研究的始终,对于她的批评思想具有重要的影响。乔伊斯对于非洲传统文化的认同和维护体现了其浓厚的非洲情结。
乔伊斯对于非洲传统文化态度集中体现于其对于非洲中心主义理念的强烈认同。1994年由第三世界出版社出版的《战士、巫师和牧师:论非洲中心主义文学批评》是其非洲中心主义思想的集大成者。在该文集中,乔伊斯对非洲中心主义进行了界定,强调其对于美国非裔文学创作和批评的重要价值。她认为基于欧洲中心主义的西方美学批评标准对于美国非裔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毒害颇深。非裔文学作家和批评家应当回归自我和族群,以创造富有特色的黑人艺术,塑造健康的非裔美国人心理空间(Joyce,1986)。乔伊斯认为美国非裔文学源于非洲传统,美国非裔文学批评的功能价值也根植于非洲传统,艺术在非洲是种族性的,是黑人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乔伊斯通过作品不断证明非洲传统的独特,欣赏非洲传统的美丽,宣传非洲传统的价值。她把非洲传统视为非裔美国人(包括民众和艺术家)的精神之光,不断抚慰着他们的创伤,同时也锐利着、丰富着他们的思想。因此,“文学批评要与黑人美学保持一致,必须仔细考察美国非裔文化,寻找一直以来贯穿美国非裔文学传统的脉络,这条脉络可以是内容的,也可以是形式的”(Joyce,1986:31),这对于艺术家风格创新、读者欣赏水平提高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那些伟大而多元化的现代美国非裔文学批评家身上肩负着寻找、继承和发扬这种传统脉络的责任,“通过文学理论传播非裔美国人应该认知的价值观”(Joyce,1986:36)。美国非裔文学批评家不应该以任何方式或理由抹煞黑人性,否定被批评作品中的非洲传统。乔伊斯强调要颠覆白人至上的神话,使黑人艺术永葆生机,需要坚持非洲中心主义的立场,从灿烂的非洲文明中汲取营养(Joyce,1986)。
此外,乔伊斯的非洲情结还间接体现于其对于非洲文化和文学批评传统的维护。对于后结构主义在非裔文学批评中的应用,乔伊斯持否定态度。1987年乔伊斯撰文对非裔文学批评领域后结构主义的领军人物盖茨的后结构主义立场予以了抨击。乔伊斯认为后现代主义者要传递的价值观和许多读者体会到的价值观之间有一种固有的矛盾(Joyce,1987)。后结构主义者反对黑人美学,他们完全脱离美国非裔文学的固有的、重要的传统,自顾自地首先创造一种理论,然后再去书写文学作品来适应这种理论(Joyce,1986)。非裔美国人具有“双重意识(double consciousness)”(Joyce,1987:295),一层是对黑人和黑人的非洲传统的意识,一层是对自己美国身份的意识,“二者融合的媒介恰恰是语言”,而后结构主义者“把语言仅仅看成一种符号系统或一种游戏”,乔伊斯认为现在不是时候也几乎不可能这样做,因为许多伟大的美国非裔文学作品,无论是小说还是20世纪60年代和60年代后的诗歌都超越了语言,用价值观把一个民族团结在一起,公然挑战后结构主义。乔伊斯坦言自己厌恶专业理论术语,因为这些术语无非是源自现实再将其抽象化而已。有些批评家出于追逐名利的需要不得已而使用欧洲中心主义术语去批评美国非裔文学②。 总之,乔伊斯坚定的认为:“后结构主义情结”是不适合应用于美国黑人文学作品的(1987:296)。
乔伊斯抨击亨利·盖茨不应该否定黑人性(blackness)或种族作为分析黑人文学的一项重要成分。她指出“黑人批评家不论采取何种策略,贬抑或……否定黑人性都是阴险狡诈的”(Joyce,1987:292)。乔伊斯认为,黑人批评家就像黑人作家一样,传统上认定黑人现实和黑人文学之间存在着直接的关系。黑人作家和批评家的功能是在扮演引导和中介的角色,解释黑人与压迫他们的力量之间的关系。盖茨的文学与学术活动是黑人文学与欧美文学的合并体,盖茨等于自动放弃黑人作家和批评家传统上应该承担的中介角色,接受了基于欧洲中心主义的美国主流社会的精英价值与世界观,其文学与学术活动,向美国白人社会投降、靠拢,同时更扩大了自己与仍然饱受白人社会压迫的黑人大众之间的鸿沟。乔伊斯对于“黑人性”和批评家责任和立场的论述反映了她在文学批评中对非洲中心主义立场的坚持,体现了其浓厚的非洲情结。
3.0 乔伊斯非洲情结的彰显
乔伊斯在其文学批评实践中处处彰显着浓浓的非洲情结。她在进行文学批评时,注重把非洲黑人文化的元素纳入文学批评的范式和内容。乔伊斯认为美国非裔文学都源于非洲传统文化,而且任何对美国非裔文学、尤其是非裔诗歌的理论研究都必须把非洲语言、音乐、舞蹈和宗教置于整个研究的中心位置,语言包括城市、乡村、传说中的市井语言,音乐包括圣歌、民歌、布鲁斯、爵士乐(Joyce,1996)。
乔伊斯从非洲土著语言中汲取营养,建构其文学批评话语。乔伊斯认为对美国非裔诗歌的批评要使用黑人文化中的术语,尤其是那些黑人聚集区使用的语言,比如班图语。这些语言的使用可以维系强烈的团结意识,也能够保持文化活力,这是美国非裔文化发展的基础(1996:40)。例如其代表作之一《索尼娅·桑切斯和非洲诗学传统》(Ijala:SoniaSanchezandtheAfricanPoeticTradition)的题目就充分体现着她的这种情结。在约鲁巴语言中用不同的词来描述诗人朗诵诗歌时的音调,比如有艾萨调(esa)、奥弗调(ofo)、啦啦调(rara)等,而伊扎拉调(ijala)指的是一种音调较高的声音。书名中选用伊扎拉这个词,一方面因为桑切斯朗诵诗歌时往往音调较高,另一方面因为在约鲁巴文化中,伊扎拉调都是由猎人或约鲁巴铁血战神欧刚(Ogun)的信徒们使用的,暗喻桑切斯用声音唤醒自己的同胞,用诗歌反抗社会政治压迫。题目中伊扎拉一词的使用包含了乔伊斯将桑切斯等同于战神欧刚信徒的隐喻,刻画出桑切斯在非裔诗歌传统中无可比拟的地位。另外,桑切斯认为非裔解放诗歌需要具备六个特征以创造社会价值:功能性、激励性、教育性、引导性、意识形态性和政治性。非裔诗歌是应一种文化需求而诞生,因此与这六大特征密不可分。乔伊斯使用伊扎拉一词还意指桑切斯的诗歌具备这六大特征,凸显其对于各种压迫的斗争。
乔伊斯在探讨美国非裔诗学传统时,全文引用了草根瑞格音乐中最伟大的灵魂乐手彼得·汤士的一首歌曲《压迫者》(Joyce,1996),并将其作为范式,以此可见乔伊斯对于非洲音乐的热爱。这首歌曲有两层含义,一方面歌唱了世界末日,运用了圣经典故,另一方面抨击了种族压迫和预言了白人对黑人强权的毁灭。“这首歌体现的语言、政治、宗教和音律的特点把处于流散状态的黑人诗歌关联在了一起,并洋溢在整个美国非裔诗学传统中”(Joyce,1996:31),从菲利斯·惠特利到兰斯顿·休斯再到拉斯·巴拉卡。乔伊斯认为非洲音乐的主题与美国非裔诗歌的主题都具有积极向上的特点。当代欧美白人诗歌多是关于孤独和绝望,与此不同,美国非裔诗歌歌颂生命、肯定生活,这与非洲音乐的主题是高度吻合的(Joyce,1996)。兰斯顿·休斯把布鲁斯和爵士乐的节奏融入进诗歌,阿米力·巴拉卡、索尼娅·桑切斯等人与乐队一起表演诗歌。乔伊斯指出音乐不仅是他们诗歌主题的一部分,而且对诗歌的行文格式和诗人的朗诵表演都产生了很大影响。这种把音乐作为一种群体活动的方式本身就沿袭了非洲传统(Joyce,1996:36)。
乔伊斯还将非洲舞蹈的特征引入其批评话语。 虽然非裔美国作家不得不使用白人的语言写作,美国非裔文学批评家也不得不使用白人的语言去评析文学作品,但是乔伊斯呼吁“不管作家的文学作品如何具备欧洲中心主义色彩,一个非洲中心主义的批评家的工作就是利用自己的想象力去解读这些优秀作品中那些微妙的、被忽视的非洲中心主义特点” (Joyce,1986:111),因为不可能期待欧美白人批评家去发现“那些黑人风格与技巧的微妙和意义”(Fuller,1994:199)。如果说探索桑切斯等人作品中的非洲传统是明显的和容易的,那么发掘格温多琳·布鲁克斯诗歌中的非洲传统就变得很艰难了,因为布鲁克斯的诗歌深深扎根于欧洲中心主义语言传统。经过深入研读,乔伊斯把她的诗歌从欧美诗学传统的泥土移植到非洲中心主义的土壤中,发现了布鲁克斯诗歌与非洲舞蹈的关联。布鲁克斯的诗歌符合非洲舞蹈的七大特点:多旋律、多中心、空间感、重复、曲线形、叙事记忆和整体性(Joyce,1986:111)。她的诗歌始终将黑人置于主体地位,而不是客体,强调种族价值和形式的整体性。 诗歌就是语言的舞蹈,乔伊斯的解读是艺术的和理性的。
4.0 结语
综上所述,乔伊斯早年的生活经历、教育经历和工作经历从一开始就在其心中烙下明显的非洲印记。黑人权利运动和黑人艺术运动中所倡导的艺术功能、艺术基调和艺术理念对于乔伊斯批评思想的形成影响深远,奠定了其非洲中心主义主张的基础。许多非裔文学家和批评家对于乔伊斯批评思想也具有深刻的影响,其中尤以理查德·赖特和索妮亚·桑切斯为重。
她在文学批评思想上的左倾转向与二者的影响密切相关。可见,非洲情结是贯穿于乔伊斯的非裔文学批评理论和实践的始终的。一方面,乔伊斯认同非洲中心主义的理念,并专门著述对相关文学批评理论和实践进行介绍和探讨。此外,她致力于维护非裔文学批评的整体性,提倡文学批评家应尽的社会责任,对后结构主义文学批评持否定态度,彰显了其浓厚的非洲情结。另一方面,乔伊斯在其非裔文学批评实践中注重从非洲和非裔文化中挖掘适用于非裔文学批评的元素,将非洲土著语言、音乐和舞蹈等语言和文化元素应用于非裔文学批评,极大拓展了非裔文学批评的话语空间和纬度。
注释:
① 引自Joyce写给笔者的电子邮件(2017年1月22日),Joyce在邮件中这样写道:“I am a scholarly mentee of writers of the Black Arts Movement; thus my work reflects the ideology and style of the Black Aesthetic.”
② 同引自Joyce写给笔者的电子邮件(2017年1月22日),Joyce在邮件中这样写道:“... they use Eurocentric terminology because they think they have to in order to get a job, to get tenure, to be famous, etc.”
[1] Bruce, D. D. Jr.TheOriginsofAfricanAmericanLiterature1680-1865[M]. Charlottesville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Virginia Press, 2001.
[2] Fuller, H. W. Towards a Black Aesthetic[A]. In A. Mitchell (ed.).WithinTheCircle:AnAnthologyofAfricanLiteraryCriticismfromtheHarlemRenaissancetothePresent[C]. Durham and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4.199-206.
[3] Joyce, J. A.Warriors,ConjurersandPriests:DefiningAfrican-CenteredLiteraryCriticism[M]. Chicago: Third World Press, 1986.
[4] Joyce, J. A. The Black Canon: Reconstructing Black American Literary Criticism[J].NewLiteraryHistory, 1987,18(2): 290-297.
[5] Joyce, J. A.Ijala:SoniaSanchezandTheAfricanPoeticTradition[M]. Chicago: Third World Press, 1996.
[6] Stepto, R. & D. Fisher.Afro-AmericanLiterature:TheReconstructionofInstruction[M]. New York: 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 1979.
[7] 庞好农. 非裔美国文学史(1619-2010)[M].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
[8] 谭惠娟,罗良功. 美国非裔作家论[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6.
[9] 周春. 美国黑人文学批评研究[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