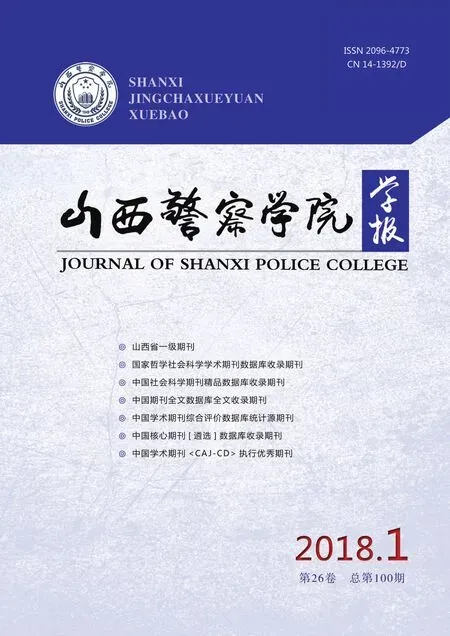值班律师担任合适成年人的合理性证成
□王瑞剑
(北京师范大学,北京 100875)
一、问题的提出
涉罪未成年人是刑事诉讼程序中的一个特殊群体,对其进行特殊、有效的保护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为实现与国际社会的接轨、切实贯彻“教育、感化、挽救”方针,2012年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对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程序进行了重大修改,其中首次明确了合适成年人制度:赋予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侦查讯问、审判等刑事诉讼活动中享有合适的成年人到场参与的权利。[1]作为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程序中的一项特殊制度安排,合适成年人制度的确立对保护被追诉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具有重要意义。然而,由于制度建构之初立法过于原则化,诸多制度运行上的问题并未得到解决。其中,尤以合适成年人的选任问题最为突出,成为制约制度发展的瓶颈。
在立法未予明确、实践尚无统一规范的情况下,各地针对合适成年人的选任展开了多样化的试点。一方面,多样化的制度试点为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实践经验,但另一方面,各种选任方案暴露出了诸多缺陷,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近年来,值班律师制度的实践探索逐渐成熟,并被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所吸收,落实于制度层面。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值班律师在保障权利、促进程序运行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从这一角度来看,值班律师为合适成年人的选任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值班律师担任合适成年人是制度进一步完善的契机。而要引入值班律师制度,首当其冲便是论证值班律师担任合适成年人的合理性。鉴于此,明确合适成年人选任的实践现状与困境,并在此基础上,论证值班律师担任合适成年人的合理性,便是本文所要解决的问题。
二、合适成年人选任的现状与困境
“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2]立法往往只是制度改革的第一步,如何适应于复杂的司法实践尚待进一步考查。在对值班律师担任合适成年人的合理性进行探讨之前,首先需要对合适成年人选任的实践现状进行一定梳理,以明确存在的制度困境。
(一)我国合适成年人选任的实践现状
根据《刑事诉讼法》规定,一般情况下,合适成年人由法定代理人担任,在法定代理人无法通知、不能到场或是共犯时,由其他人员担任。可见,合适成年人的选任由两个顺位组成,第一顺位是法定代理人,第二顺位是包含其他成年亲属、所在学校、单位、居住地基层组织或者未成年人保护组织的代表在内的其他人员。从实践中看,由于我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时期,外来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情况十分严重。*根据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1年的资料显示,2008~2010年,该院及辖区法院共审判未成年人犯罪一审案件1628件,涉及2214人,其中有上海户籍的仅有585人,占总人数的26.42%,绝大部分未成年人均为外来人口。参见上海市综治委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专项组等编.2011~2012上海市青少年事务社会工作调研成果集[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3:216.在这些案件中,因种种原因,法定代理人或监护人往往无法参加讯问、审判等活动,导致合适成年人的第一顺位缺失。*据从事实务工作的同志介绍,自新刑事诉讼法实施以来,其讯问时法定代理人到场的不足50%,大部分未成年人案件属于外地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作案,法定代理人因种种原因难以到场。参见冯磊,何梓桢.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具体问题研究[J].法治论坛,2014(1):216.而在法定代理人无法参与的情况下,如何有效地选任其他人员以充当合适成年人便是合适成年人选任的关键。
针对有效选任的问题,大部分地区均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形成了不同的选任模式。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有:
(二)我国合适成年人选任的制度困境
上海模式,依托上海相对成熟的青少年事务社工队伍,由专业的社工担任合适成年人。[3]专业社工大多具备教育学、心理学知识,善于沟通,对履行合适成年人的职责大有裨益。同安模式,主要由区人大法工委、关工委、团委、妇联干部、教师、律师等担任合适成年人。[4]这些人员往往本职工作就与青少年相关,在与未成年人沟通上有很大的优势。苏州模式,由热心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成年人组成“爱心妈妈团”,为未成年被告人提供善于交心、易被接纳的合适成年人。[5]律师担任模式,律师担任合适成年人在实践中争议较大,部分地区也曾将辩护律师或法律援助律师作为合适成年人的来源之一。*如北京市海淀区在合适成年人试点初期,曾将法律援助律师作为合适成年人的唯一来源;再如截至2012年,厦门市同安区聘请的合适成年人中有4名律师,占28.6%。
实践中各地自生自发的实践探索催生了多样化选任模式的产生,但另一方面也暴露出了各种选任模式可能存在的问题。正所谓“法律的生命不在于逻辑,而在于经验”。[6]合适成年人的选任绝非简单的立法选择问题,而是关涉实践中制度运作、职能履行的方方面面。在上述选任模式的作用下,合适成年人制度运行中存在着如下几点问题。
其一,参与程度不高。合适成年人制度要切实发挥保护未成年人利益的效果,必须要保证有效、充分地适用。然而,从实践中看,合适成年人在刑事诉讼程序中参与程度并不容乐观。上海市少年犯管教所曾于2003年10月对在押的103名未成年犯进行过“关于合适成年人参与首次讯问”的问卷调查。调查显示因犯罪行为而受到首次讯问时,没有合适成年人参与讯问的占100%。[7]2008年另有学者曾就“是否让合适成年人参与案件处理”的问题对207名公安一线的刑事办案警察进行过问卷调查。结果显示,经常让合适成年人参与的只有14%,86%的警察表示很少或者不让合适成年人参与。[8]近年来,随着合适成年人制度被写入《刑事诉讼法》,合适成年人的参与率有所提高,但仍旧未达到制度预期。江苏法院曾对2011年至2013年1月-3月合适成年人的制度施行情况进行统计。结果显示,虽然近年来合适成年人参与刑事诉讼活动的比例明显上升,但整体而言,仅占全部案件数的13.1%。*2011年度江苏法院未成年刑事案件收案3860件,合适成年人参与案件数213件,占5.5%;2012年度,收案数3449件,合适成年人参与案件数247件,占7.2%;2013年1-3月,收案数2200件,合适成年人参与案件数586件,占26.6%。参见陈晓钟.我国合适成年人制度实践路径的思考[J].南京大学法律评论,2016(1):219.合适成年人参与程度之低很大程度上源于选任模式不当,其中尤以侦查讯问程序的适用最为明显。侦查阶段的讯问对效率极为重视,要使合适成年人能够参与讯问,关键在于合适成年人能够“随叫随到”。然而,现有的选任模式并不能满足这一点,无法保证在侦查机关讯问时及时到场,缺乏系统化、常态化的选任机制,导致程序参与度不高。而若合适成年人在实践中难以及时参与,再好的制度设计也仅是“纸上谈兵”。
其二,职能履行形式化。从立法目的来看,合适成年人在场目的有二:一则,弥补未成年人诉讼能力局限的不足,保证刑事诉讼的正常开展;二则,进行监督,防止违法行为对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损害。[9]可见,合适成年人在诉讼活动中主要发挥着保护与监督作用。前者体现于向未成年人解释有关诉讼活动的意义、享有的权利义务以及可能产生的法律后果,促进未成年人与办案机关的沟通。后者则体现于监督刑事诉讼活动中是否有侵犯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行为,保障程序的合法性。而实践中,由于选任的合适成年人本身的局限性,导致这两项职能的行使往往流于形式。保护职能的行使,要求合适成年人必须具备一定法律知识,对相关刑事诉讼活动有一定理解。然而,实践中的选任方案,如上海模式、同安模式、苏州模式,无法满足这一要求,由此产生的合适成年人连自己都尚难以充分理解刑事诉讼活动的意义,遑论有效帮助未成年人。监督职能的行使,同样需要有相应的法律知识为支撑。由于大部分合适成年人没有法律知识,缺乏专业训练,除了一些十分明显的刑讯逼供行为,根本无法对隐蔽性较强的不当行为进行有效监督。可见,专业知识的欠缺是职能履行形式化的根本,而合适成年人具备相应的专业背景是有效履行保护职能与监督职能的基础。
其三,中立性难以保障。未成年人可能存在着理解与表达上的障碍,在诉讼中会遭受权益侵害,因此合适成年人的作用在于弥补未成年人能力上的缺失,帮助其有效参与程序。质言之,合适成年人是司法机关与未成年人之间沟通、交流的桥梁,而非诉讼一方的代言人。[10]由此可见,合适成年人的中立性地位在职能的有效履行上尤为重要。然而,现有选任模式难以保障合适成年人的中立性地位,主要存在两种不当趋势:其一,合适成年人过于偏向办案机关,监督作用不力;其二,合适成年人明显偏向未成年人,保护作用有余。前者主要体现在社工模式之中。由于社会工作者担任合适成年人的项目是以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运作的,社工与派出所之间难免存在利益上的密切关联。[11]基于利益关联所施加的限制,担任合适成年人的社工难以保持中立地位,更难以独立、有效地履行监督职责。而后者主要体现于律师担任模式中。辩护律师的职能具有明显的偏向性,与合适成年人的中立性不相符合。以辩护为己任的律师,很难要求其在担任合适成年人时能转换身份而保持中立地位。综合二者来看,合适成年人的中立性问题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三、值班律师的引入——解决问题的可能路径
现有的合适成年人选任模式在实践中暴露出了诸多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需要采取新的思路。值班律师制度在各地试点多年,积累了充分的制度经验,为合适成年人选任问题的解决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一)值班律师的实践探索
值班律师是指由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在侦查、审查起诉或审判等诉讼阶段免费为当事人提供法律咨询等法律帮助的律师。该制度最早起源于英国,近年来已成为域外各国法律援助制度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12]我国值班律师制度肇始于2006年河南省修武县的试点,制度初衷在于为低收入人群提供及时、专业、低成本、高效率的法律援助服务。[13]修武县首期选聘18名值班律师参与试点项目,在县法院、公安局、看守所、城关派出所分别设立一个法律援助值班律师办公室,每个工作日各有两名值班律师值班。在近两年的试点期间,值班律师的主要职能是解答来访者咨询、告知权利义务、代写法律文书以及引导申请法律援助等。[14]随着试点经验的成熟,值班律师制度逐渐推广,各个地区纷纷效仿。例如湖北罗田在看守所设置值班律师,其主要职能是法律咨询、受理援助申请、开展法制宣传以及履行告知义务。[15]再如,广州在市看守所与市中级人民法院均建立了值班律师工作站,负责提供法律咨询服务、指引申请法律援助和司法救助、参与涉诉信访案件化解以及法律援助案件诉前调解工作等。[16]
实践中多地自生自发的探索为制度构建提供了有益的经验,也为制度的全国推广奠定了实践基础。2014年,中央深化体制改革领导小组正式将“在法院、看守所设置法律援助值班律师办公室”列为司法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2016年,“两高三部”出台了《关于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意见》,其中明确提出了“建立法律援助值班律师制度,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法律帮助”的要求。诸多中央文件的出台既对值班律师制度提出了具体要求,也推动其落实于制度层面。随着速裁程序、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明确规定了值班律师制度,意味着值班律师制度正式落实于制度层面。
(二)值班律师的制度定位
对值班律师进行准确的制度定位,需要对值班律师以及值班律师制度进行全面的审视。从值班律师的实践探索来看,各地试点的经验大同小异,均赋予值班律师相应的法律帮助职能。法律帮助职能一般包括解答法律咨询、告知权利义务、代写法律文书等,而不会进行调查取证和出庭应诉。值班律师的职能仅起到基本的法律帮助作用,并无法发挥辩护的作用。可见,值班律师的法律帮助并不能与辩护律师的辩护职能混为一谈。后者直接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辩护,具有相对独立的诉讼权利;而前者仅是帮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现辩护权起到辅助作用。因此,从性质上看,与辩护律师辩护人地位相对应,值班律师仅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之辅助人。另一方面,从功能的角度来看,值班律师制度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发挥的作用是保障被追诉人自愿认罪认罚以及防止不当追诉。*参见《关于<关于授权在部分地区开展刑事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工作的决定(草案)>的说明》。通过指派值班律师,法律援助机构一则为被追诉人提供有效、免费的法律服务,二来介入刑事诉讼活动,起到有效监督。可见,值班律师制度在试点过程中主要体现了国家对弱势群体的权利保护作用。综合上述两点,值班律师既不受司法机关的指派,也不承担被追诉人的委托,而是作为第三方,中立地履行法律帮助职能;值班律师制度则是基于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利,防止其遭受公权力的不当侵犯而建立的一套制度,是法律援助的一种特殊形式。
四、值班律师担任合适成年人的合理性证成
值班律师制度为合适成年人的选任提供了一个独特的思路,为此需要明确制度引入的合理性。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言:“一切实践和选择,都应以某种善为目的”。[17]具体到合适成年人制度,值班律师担任合适成年人的合理性便是制度选择的基础。
(一)利于合适成年人参与常态化
要保证合适成年人能够有效参与,特别是在首次侦查讯问时介入,要求办案机关能够随时联系到合适成年人,合适成年人能够及时到场。而我国实践中合适成年人之所以参与程度不高,也在于合适成年人难以做到“随叫随到”。可见,要提高合适成年人的参与程度,必须要具备相应的人员保障制度。英国在三十多年的实践中形成了一支能在24小时内随叫随到的合适成年人队伍,这样一支队伍对于确保警察机构的讯问必不可少。[18]因此,要保证合适成年人参与常态化,需要建立一支常备的合适成年人队伍,以确保未成年的被追诉人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均能及时获得合适成年人服务。
从目前的司法现状来看,要想在短时间内建立起一支常规化、专业化的合适成年人队伍较为困难。值班律师制度的引入正好解决了这一问题,其在队伍建设上具备四点制度优势。其一,现有值班律师制度在人员配置上能够满足合适成年人队伍建设的需要。由于速裁程序、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吸纳了值班律师制度,各个试点地区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建立了相应的值班律师库,保证了人员的充足供应,*司法行政机关建立值班律师库,在试点法院、看守所设立法律援助工作站342个,共为17177件案件的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提供法律帮助20930人次,受委托进行调查评估3597件。参见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刑事案件速裁程序试点情况的中期报告[EB/OL](2015-11-03)[2016.7.19].http://www.npc.gov.cn/npc/xinwen/2015-11/03/content_1949929.htm.为值班律师担任合适成年人提供了人员上的保障。其二,值班律师制度基本上形成了日常值班的工作模式,能够满足合适成年人的即时性需求,保证“随叫随到”。*据统计,以杭州市中心、各基层以及铁路看守所、法院为例,16家看守所里,值班律师每天值班的有4家,占25.00%;16家法院里,值班律师每天值班的有12家,占75.00%。参见董红民,麻伟静.构建法律援助值班律师制度实证探析[J].中国司法,2016,(10):39.其三,值班律师的值班场所设置于看守所与法院之内,靠近侦查讯问场所与审判场所,有助于提高合适成年人的工作效率。其四,值班律师受法律援助机构指派,依托于法律援助机构,具有较强的人员资源储备,有助于合适成年人的队伍建设。综合上述四点可知,值班律师担任合适成年人能充分发挥现有的制度优势,促进合适成年人的常规化队伍建设,有利于合适成年人的参与常态化。
(二)促进合适成年人职能实质化
合适成年人履行职责需要相应的专业知识为支撑,其中最为重要的莫过于法律知识。这一点在实践中也得到了印证,有学者调查发现,绝大部分的办案人员、合适成年人和未成年人都认为合适成年人应当具备一定的法律知识,至少要有一般了解,最好能达到较为熟悉乃至特别精通的水平。[19]具备相应的法律知识是门槛较高的一种技能,而要较为熟悉法律、达到有效理解刑事诉讼活动的程度,必须要通过经年累月的研习。实践中部分地区也曾对选任的合适成年人进行过法律知识的简单培训,但往往收效甚微,难以促进职能的有效履行。可见,要具备专业的知识并不能通过简单的培训得到,而是需要专业的人员参与。
引入值班律师制度同样能解决这一问题,其合理性体现于如下两点。其一,值班律师具有更为专业的素养与技能,能满足有效履行职能的要求。值班律师一般由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其不仅具有专业的法律素养,也具备丰富的法律援助经验,有利于职能实质化的实现。其二,值班律师的职能与合适成年人的职能大致相同。实践中值班律师的职能有二,一是提供法律咨询等法律帮助,二是对公权力进行有效监督。再看合适成年人,实践中的职能履行形式化主要在于保护不当与监督缺位,因此要促进合适成年人职能实质化必须要重视保护职能与监督职能的行使。两相对比可见,值班律师的职能可以类推至合适成年人,两者相差并不大。另外,值班律师制度试点多年,在具体职能行使上积累了一定经验,对于职能实质化同样大有裨益。
(三)符合合适成年人的制度定位
纵观域外各国关于合适成年人的立法,无论是英美法系还是大陆法系,*关于英美法系、大陆法系立法模式的比较与评析,可参见张阳.缺失与规范:论我国少年刑事审判程序中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J].河南社会科学,2014(12):59.设置合适成年人都是为了体现国家对未成年人权利的保护。不同于法定代理人的监护职责,合适成年人的职责植根于国家亲权理论,反映了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原则的具体要求。因此,合适成年人是国家设置的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专门保护人,在刑事诉讼中应处于客观、中立的地位。[20]具体到制度定位上,合适成年人不仅要体现国家对特定群体的保护,还要具有相对客观、中立的地位。现有的现任模式之所以导致存在种种问题,其原因之一便在于合适成年人客观、中立的地位难以保障,从而偏离了原有的制度定位。引入值班律师担任合适成年人并不存在这一障碍,其符合合适成年人的制度定位,有助于制度运行回到正轨。其一,值班律师制度保障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利,防止其遭受公权力的不当侵犯,体现了国家对特定弱势群体的保护。其二,值班律师来源于法律援助机构的指派,其既不受办案机关的影响,也不承担被追诉人的委托,而是作为第三方,中立地履行法律帮助职能。可见,值班律师制度不仅在制度定位上与合适成年人制度相契合,在此基础上同样能够解决原有选任模式产生的不中立现象。
(四)有助于制度的有序发展
从少年司法百余年的发展历史来看,少年司法具有作为司法制度进步先驱者、司法改革试验田的特殊作用。[21]合适成年人制度作为少年司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样具有改革先行者的意义。合适成年人讯问在场一方面为未成年人提供了有效的权利保障,但另一方面也是律师讯问在场的制度模版,为其提供了发展契机。出于保护未成年人的目的,结合上述合理性,值班律师以合适成年人的身份介入侦查讯问在实践中或许并不会受到太大的阻碍。通过值班律师担任合适成年人,一方面可以促进律师讯问在场的进一步突破,使值班律师制度取得实质性发展,另一方面也可以推动合适成年人制度的进一步完善,落实监督职能与保护职能。综合二者来看,值班律师担任合适成年人不仅是制度有效运行的合理性要求,也是制度有序发展的应有之义。
【参考文献】
[1]姚建龙.论合适成年人在场权[J].政治与法律,2010(7):145.
[2]张居正.张居正奏疏集(下)[M].潘林编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233.
[3]蔡忠,杨峻,金璠.上海青少年事务社工在“合适成年人参与”工作中的实践与思考[J].青少年犯罪问题,2009(2):62.
[4]林志强.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的实践探索和完善进言[J].青少年犯罪问题,2007(2):59.
[5]史华松.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的“吴中经验”研究[J].常熟理工学院学报,2011(1):58.
[6]霍姆斯.普通法[M].冉昊,姚中秋,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6:1.
[7]胡骞骜.试论推进未成年人取保候审工作[M]//英国保释制度与中国少年司法制度改革.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2005:157.
[8]刘东根,王砚图.我国未成年人刑事司法中的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之完善[J].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5):144.
[9]郎胜.《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改与适用[M].北京:新华出版社,2012:469.
[10]谢登科.合适成年人在场制度的实践困境与出路:基于典型案例的实证分析[J].大连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3):111.
[11]王文卿,丁可欣.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的形式化:社会工作者的参与观察和反思[J].社会工作,2016(1):111.
[12]郭婕.法律援助值班律师制度比较研究[J].中国司法,2008(2):101.
[13]阮兰泉.中国法律援助值班律师制度初探[J].河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学报,2009(4):115.
[14]王淑华,张艳红.探索建立中国法律援助值班律师制度[J].中国司法,2009(5):90.
[15]刁凡超.值班律师制度的罗田样本[N].民主与法制时报,2014-12-15(6).
[16]邓嘉詠.论广州市法律援助值班律师制度[J].商,2015(23):249.
[17]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M].廖申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3.
[18]沈莉波,赵越.合适成年人到场制度的观察与反思[J].人民司法,2015(15):76.
[19]何挺.合适成年人讯问时在场的形式化倾向及其纠正[J].中国刑事法杂志,2012(11):77.
[20]何挺.“合适成年人”参与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程序实证研究[J].中国法学,2012(6):163.
[21]姚建龙.对少年司法改革之应有认识[J].青少年犯罪问题,2010(5):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