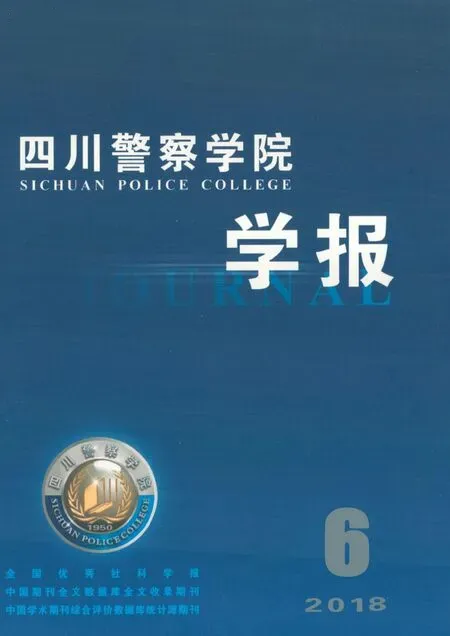刑事推定的合理性与价值
——兼对审前“推定方案”的证成
杨佶欣
(华东政法大学 上海 200333)
一、前言
“证据裁判主义”背景下,审前证据问题凸显出来,而如何搜集证据、认定事实,其主要的机制形态,对于审前检察审查证据以及侦查取证有着重大指导意义。当前有关客观证据认定事实的机制,在理论界(国内外)存在限制推定,尤其警惕“事实推定”可能对推论等证明机制侵蚀的论调“此起彼伏”时①,实务界或者务实的研究者,却对运用客观证据体系,以“事实推定”来认定事实持“乐观态度”,他们往往认为这是扭转“口供中心主义”、“言词证据中心”、不合理的认知证明思维(印证认知和证明的依赖等)的“一剂良药”②。同时,也有倡导“零口供办案”并且提出物证中心导向,进而倡导侦查专业化建设、尽力搜集证据、重勘察鉴定以及“善用推定”的进路[1]。
其实,以上表现的实务中审前司法人员追求“推定方案”推动取证、认知的完善,也有其现实因素。结合对上海市虹口区检察院、公安“电子证据的取证、审查工作”的调研,总结侦查取证乃至整个审前程序的证据问题的“症结”所在(在上海存在,在其他地域问题只会更明显),发现:取证的客观条件难以短期改变的前提下,欲使取证偏好、证据体系和认知机制完善,当前的证据类型、证明机制(事实认定)存在明显滞后;如可采性、证据相关程序、推定适用问题等方面,或许可以针对新形势做出一点调整。在此基础上,有必要对推定制度的功能、价值进行重读,从而回答几个问题:刑事推定在新时期是否合理?如何完善?有何具体价值和功能?
(一)“证据裁判主义”下的证明与推定
近年来,“证据裁判”、“庭审实质化”等字眼成为重点强调的对象;最集中、系统的莫过于“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及其文件了。中央近年出台一系列相关文件旨在推进证据裁判主义。政策指引不言自明,在于革除传统“以侦查为中心”模式下的弊病,旨在发挥证据裁判在预防错案、认定事实方面的作用。作为现代审判关于证据、事实认定的大原则,“证据裁判主义”语境应该呈现什么形态呢?又应该对我国刑事推定制度产生什么影响?应该进行重新思考和解读。证明与推定,都是“证据裁判主义”下认定案件事实的路径且在主流观点认为推定是“替代性方法”③;但也可以这样解读:推定也是证明的延伸,都统辖在“证据裁判主义”的精神下,没有根本区别和矛盾。推定制度也应当体现证据裁判与证明的理性化、科学化、程序化、公开化、规则化等基本特征,真正成为定纷止争、查明真实的有力武器。同时,不应有孤立考察推定的“削足适履”的教条思路。进一步讲,将推定制度统辖在“审判为中心”“证据裁判”的大背景下进行解读、规划,及将其规范化、程序化、理性化的方向,才是理论用力的价值所在。
(二)传统对推定的解读及偏颇
查阅了现今学界对推定的解读方向,大体分为三种:其一,是将推定进行不涉及价值判断的技术性解读,厘清推定的盲点、难点;其二,是对推定的评价,主要的论调都是对推定尤其是事实推定持一种谨慎的、限制的态度,认为这是侵蚀无罪推定的模式,不利于被告人权利保障;其三,是在诉讼程序中考察推定制度及其适用问题。在此,对第一、第三种不涉及价值和态度的内容抛开不谈,先谈谈第二种比较普遍的态度。总而言之,对于推定制度侵蚀无罪推定原则,造成事实认定过程不规范、不理性以及不利被告人权利保障等问题的担忧,是可以理解的;但由此就足以对司法实践中大量存在的“法律推定”乃至“事实推定”进行限制、压缩吗?恐怕理论不能如此武断。其作为法官理性认识事实的一种方式,与其仅“谨慎和限制”,不如将其“规范与完善”。这样对“以审判为中心”起到的是促进作用,并且还可能有力推动审前司法调查、认知模式有益的变革,最终间接支撑证据裁判原则的实现。
二、推定定位:“觉今是而昨非”?
推定的理论定位其实远远没有成熟化,且受“玄学化”的基础理论研究的“惯性”影响,被看成转移给被告方证明责任、降低控方证明难度、标准的工具,依然以此为纲、乐此不疲。同时,推定由于其本身的不成熟、不规范,而被看做一个需谨慎对待的对象,常常饱受鄙夷的目光④。但是,今天的探讨是否应有陶渊明“今是而昨非”的态度,批判中前进呢?
(一)比较法和历史视角中的真实图景
如果说前文笔者对于自己针对推定的态度还论证不充分的话,我们先从“别人的眼光”和“过去的眼光”来看看。首先,别人的眼光。总体而言,推定是从神判发展到机械证据和经验主义,再发展到现代理性、自由心证的必然产物;英美法系的推定制度,是一种平衡陪审团和法官之间权力构造,增强法官的心证对事实认定过程影响的制度;大陆法系的推定制度,其本质就是自由心证语境下,法官进行事实认定的方式和路径。综合来讲,推定在域外都体现为法官心证的一部分,也是现代庭审事实认定的关键机制,并且其也符合现代刑事审判“自由心证主义”和“证据裁判主义”两者的共同需求,体现着现代理性光辉、形式理性特征和对法律真实追求的价值取向;域外的理论态度也基本是将其纳入心证范畴进行规范和强化,而非给予其谨慎、克制的目光。
其次,过去的眼光。神判时期,证明困难的时候的最终事实认定机制往往交给神祗(上帝);中世纪用法律的明文规定来机械总结经验形成法定证据制度⑤;进入西方意义上的“理性时期”后,自由心证在立法和意识形态上被肯定,其中,推定制度逐步兴起,它既体现了自由心证的理性光辉⑥,也兼具了心证的模糊性、形式理性特征。总体而言,推定及其依靠的自由心证制度本身,就是对落后的神判体系、法定证据思维及其刑讯制度等历史“过去式”的批判、发展,本身的理性和科学化光辉不容抹杀。
(二)理论态度与司法实践需求的结构性矛盾
其实,针对推定制度的争论早已不绝于耳,甚至域外某些人主张废除这个提法⑦;但国内学者多用“无罪推定”原则的内涵和要求来否定和制约推定制度的适用。某些理论认为,推定制度的适用,是从一定程度上打破了“无罪推定”这种理念的统治地位;越是扩大其适用的范围和力度,就越是会压缩无罪推定的价值和功能,使得刑事审判成为一种刑事法律政策的工具,个人利益的保障将被压缩。现今对推定制度的谨慎态度甚至批判态度,认为会侵蚀无罪推定制度和造成司法的恣意性;其实说法是片面的。证据裁判主义从法定证据制度发展到自由心证制度,这个过程必然是伴随推定制度等的兴起和规范化,而没有推定等形式理性式、相对模糊式的事实认定机制的支撑,自由心证制度只能是空中楼阁。
再者,这种又一个“图腾式”批判不符合司法实践需求。其一,“证据裁判主义”下的刑事诉讼,是谈如何证据思维、情理推断思维(推定就是体现)在整个诉讼中占主导的语境;而不是继续让传统的侦查“印证认知、印证调查”思维继续占领主导;也应当是法院对“法律真实”认定的形式理性思维崛起的时候[2]。其二,证明的过程就是一个模糊的过程,并且对于疑难案件真实的若即若离,似乎形式理性化的模糊证明才是正确的司法实践选项[3]。其三,司法实践中越来越多的关于刑事推定的规则、解释、会议纪要不断出炉,进一步做推定的固化,将法律推定乃至事实推定的范围进一步扩展。
三、证据裁判语境中的刑事推定
“证据裁判主义”追求符合程序正义的“法律真实”,这种真实的依托是证据的取得,举证、质证和认证过程,以及依据证据的证明、说理过程符合程序要求,在此基础上得出的结论才能被视为真实。在这个意义上,推定正是符合了此种形式理性特征,也是符合自由心证的要旨,其发展方向更应是一种程序外观和程序正义的实现过程。
(一)推定制度与伪推定的区别
不容讳言的是,当前的推定制度适用程序存在不规范、不明确甚至乱象,但“伪推定”倾向不能否定推定本身。首先,不规范和不明确甚至恣意的“推定”本身就是对推定精神的背叛。以何家弘教授针对贪污罪推定的总结为例,总共有不提及、少说理、欠明确、不统一等缺陷,其实不仅是贪污罪;就笔者自己的裁判文书检索已经发现了几乎食品安全、环境污染、毒品犯罪等刑事案件中都存在这样的问题[4]。但是,这样的普遍问题只能说明,推定制度在我国还有待全方面完善,但是否能就此谈谨慎、限制推定,其实是有待商榷的;这种“这种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的态度在理论界时时呈现,但是态度本身除了将自身隔绝于实践之外,别无他益。
应着力如何将其完善、如何纳入程序的规制,如何可视化、程式化和规则化,而不是继续沉浸于玄思(证明责任、证明标准等传统理论领域)的泥沼或者是单纯挑刺(侵蚀无罪推定和现实不规范之批判)的旋涡中[5]。同时,现代意义上的推定,都是韦伯的科学程序的演绎,也是罗尔斯所谓的纯粹的程序正义的演绎,亦是对“法律真实”追求的精神演绎,也逃不出司法实践对诉讼效率和实体公正平衡的妥协智慧的范畴。这种符合现代自由心证、程序正义理念及其程序外观、形式理性和科学精神的推定制度,才是“真推定”,这也是理论和实践的追求理想,“伪推定”的以辞害意应警惕。
(二)推定符合“证据裁判主义”的本质——司法形式理性
进一步讲,“证据裁判主义”是在“法律真实说”的大框架下,进行形式理性化的司法认知的模式;其依托是程序正义和程序外观。可以说,越是现代化的审判,其事实认定机制越是呈现形式理性特征。推定制度,正是有这种精神气质。推定应闪耀着形式理性的光辉;其应当是由程序规则所制约,整个过程都被纳入诉讼尤其是庭审的程序中,以一种“看得见”的形式呈现在利益相关方的眼前,并且给予控诉方、辩护方同等的参与权;这种参与既表现为相关方对“基础事实”的举证、质证和辩论的可视化过程,也包括辩护方针对“推定事实”的反驳程序之规范化,更应该包含针对“事实推定”的基础事实与推定事实之间“常态联系”的质疑程序和相关表达。当然,裁判的推定释明、相关说理论证和心证公示也应该是有机组成部分。同时,“无救济无权利”,还应当赋予相关推定的程序以诉讼程序上的效果及相应制裁;否则推定这个事实认定机制的规范化也就如镜中之花了。
司法推定,即是一种模糊的事实认定机制,也是一种相对合理主义的体现,这本身就是体现了“相对合理主义”体现的实践理性[6]。既然司法人员不是全能神,那么给予凡人以凡人的程序(推定就是代表)来认定凡人的案件事实(从基础事实到推定事实),即使和时光隧道那端有出入,那也是现代司法形式理性化、证据裁判逻辑下的合理化选择。
(三)推定及其形式理性的依靠——程序外观与程序正义
没有程序外观的推定是镜中花、水中月。根据笔者调研上海高院刑庭法官,并不是说如此简单解释就能使推定站住脚——对社会效果的忌惮、对被害人家属情绪担忧以及工作压力、法官素质制约使法官不敢说明、谨慎运用推定以及怠于运用推定,甚至对此缺乏敏感度。笔者认为,实践当中存在的问题恰恰说明了推定的程序不清、规则模糊以及相关法律效果缺失,所带来的缺陷。推定制度没有专门的甚至相关程序规则说明、制约,也没有法律效果的规定,更没有针对法官说理论证的规定,同时司法人员对此意识不强、重视不够;上海市三中院管辖的就是毒品犯罪、食品安全、环境污染等判决书竟然几乎只字未提“推定”,更不用说针对其说明、说理论证,之前的程序外观能有推定的“一席之地”?很难令人相信。程序外观的缺失,很难保证推定制度的有效、合理、服众、理性地运行,便逐步成为实务界一个尴尬的存在。
“正义不仅要实现,而且要以看得见的方式实现”[7]是程序正义最经典的表述;但推定还没有以“看得见的方式”进行。笔者认为,程序正义是程序外观的核心精神和价值,并且其能够使实体认定过程可视化、程式化,多方看得见的参与的程序能够一定程度消解多方的误会、纠纷,同时赋予各方以程序性尊严,这本身就是推定制度应该具备的内容。关于程序正义,在上世纪末相关学者已经将美国主流理论译介入我国;但是很遗憾,时至今日在推定这个事实认定的重点机制中,实践中依然没有程序正义及其依托——程序规则规范的外观——应有的身影。一方面,让我们不得不反思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但更重要的是,如何让程序正义思维映入刑事法官眼帘,以及如何配套增强该机制的程序外观,成为应该着重思考的问题。
在“审判为中心”改革阶段中,无论是倒逼审前阶段改变事实认知机制(由印证式改为类似推定的情理式认知)、相关证据搜集方式,还是完善庭审的形式理性、程序正义,都有必要规定专门的推定释明过程、推定举证质证、认证以及推定的反驳权保障,及法官心证阐明、裁判文书专门说理,并且赋予相关规则以程序后果等。只有这样的改变才能使各方看到何为推定、如何进行的推定、推定有无瑕疵,才能保障司法的公正、权威,才能逐步让推定这类理性认知模式,逐渐被大家接受,并减少前文所说的司法实践尴尬境地。
(四)推定制度的另一种解读:自由心证思维
推定制度是同自由心证制度与意识同步成长的。从精神气质上看,其也是法官对“法律真实”认知的一种方式,并且体现了一种“情理推断证明模式”的基本特征——本质上,是自由心证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一,从制度上来讲,推定都是作为法官心证本身或者法官制约陪审团的机制而存在的,在此不赘述。其二,从历史上看,只在经过法定证据制度后,推定制度才开始逐步生发、成熟完善,而这几乎和自由心证同步成长。此一定程度印证了推定制度的讨论,应该放在自由心证的氛围中进行,也说明了其进步必须依靠心证思维。其三,自由心证受法官专业性、司法监督和内部形式理性制约,也是一种根据证据、依赖程序和需要说理表达的司法事实认定过程;其实,推定的完善只能通过这样的成熟心证思维的路径进行。最后,情理推断,也有助于逐步革除审前“印证认知模式”等思维,推动自由心证发展。虽然“印证证明模式”和“情理推断模式”同属于自由心证的范畴,[8]但是正如相关学者所述,印证证明和典型意义上自由心证还是存在区别。
四、刑事推定与证明模式的革新
虽然并不反对推定、证明二分的逻辑分类,但是司法实践正如霍姆斯所述“法律的生命不在于逻辑而在于经验”,逻辑二分不能掩盖司法经验上、法哲学上其与证明相辅相成的关系,以及对证明模式的作用和影响。
(一)推定的扩展作用:审前倒逼“证据裁判”意识
学界对于证据裁判意识、做法,如何有效深入审前,远未找到成熟答案[9]。笔者受此启发,结合推定的情理认知、情理证明的本质,认为:庭审“以供为王”的印证式证明和认知模式,起源于审前的取证和调查模式,是审前阶段证据意识——追求绝对真实、重视对口供等印证,以口供等言词证据为中心的证据搜集、认知和证明范式——对审判阶段“证据裁判”的一种绑架和侵蚀;这也是为什么刑讯逼供成为主要冤案的原因之一种解释。而庭审阶段如能形成规范化、程序化的有限推定制度,则可以形成审判阶段对客观证据体系的偏好,及其相应的偏“情理推断式”证明模式的导向,这样的变化长此以往,或许能成为审前程序,尤其是侦查取证和认知模式变革的一种倒逼力量。
当前的理论,往往忽略法庭的核心问题——推定等情理推断和说理论证程序——对审前证据“形塑”的引导作用。正如相关学者所讲:“近现代以来,刑事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刑事诉讼程序逐渐由人证为中心向物证为中心过渡……刑讯逼供(在依赖口供的时期,刑讯是合法的)、非法取证越来越令人难以容忍”[10]。推定背后的情理推断模式,及其对客观证据(尤其是物证)的偏好,对逐步减少印证认知模式及其对主观证据的偏好,将形成一种良性审判职能指引,指引审前的取证、认知、固定证据、整理证据体系等行为向形式理性化、程序性、情理推断型的追求法律真实的“证据裁判逻辑”上靠。
(二)推定与审前程序认知模式的革新
审判阶段的“证据裁判主义”声音孱弱、“明灭不可见”,并且一定程度上被审前认知模式、取证思维绑架。那我们就看看,侦查思维是如何绑架证据裁判思维的,如何破解?
“破案”(嫌疑人归案是核心),在侦查实务中是基本目标和理论导向⑧;当然这也是行政式、调查式、迅速型侦查模式下的必然产物,过多批判也无益处。但是,这种思维却影响了审前证据的搜集、固定保存、证据体系整理和相应司法认知的模式,在当前“三机关分工负责、相互配合、相互制约”的流水线式程序没有根本改变的情况下,这种模式、思维,及其形成的证据体系“半成品”,之后对审判阶段“证据裁判主义”的侵蚀是巨大的。查阅了主流侦查实务和学术著作,除“犯罪现场勘查”为搜集物证等客观证据以外,而“摸底排队”这一类查人的“由人到事”的机制占据了主流地位;并且,讯问犯罪嫌疑人、询问证人等主观证据取得行为,均进行了详尽的侦查谋略、技巧论述,都体现了以人以及“以口供为核心”的调查、取证、认知导向。但对审判和庭审的要求,侦查取证应该如何符合审判的证据裁判要求,如何完善证据体系,基本只字未提[11]。当然,“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不可期望一日扭转侦查取证及其思维,但是在审判中心之下,再不能有“抱薪救火”的不明就里了。
综上,应该明确推定机制的完善对于引导审前侦查,由纯粹“由人到事”的“破案、调查附带取证”为核心的模式,逐步向“取证与形塑证据兼破案”的模式转变的之可能的积极作用。当然,并不是说推定的程序化、规范化以及赋予其一定明确法律效果,就可以将侦查取证拉向“情理推断式”认知,这不可能、也不现实;但是推定至少可以在长期上,起到证据偏好的引导作用,对审前认知模式的改良、“审判裁判主义”的生根发芽,是有好处的。
(三)推定与刑事诉讼情理推断模式的崛起
推定体现的“情理推断模式”是一种较为高级的,以物证等客观证据为中心的诉讼证明和认知模式,这种机制体现了司法经验、智慧的总结,是程序过程中法律真实的得出方式。从言词证据的地位相对下降中,其实已经可见这种情理推断式(物证等客观证据为中心)司法事实认定模式崛起的可能:当前,主观化、印证化手段受到了限制,认可书面证言的传闻证据规则这一“英美证据法的基石”,例外情形越来越多,适用范围越来越小[12];同时,美国的所谓“传闻证据规则”这个保障言词印证证明模式的核心规则,在《联邦证据规则》中出现了大量的例外情形[13]。再者,我国证人出庭模式依然是“老大难”问题,在多种因素制约下,一时间难以实现从“文书中心”到“实质言词中心”的转变。
与其过度关注如何保障针对证言的对质、如何让证人出庭,如何保障口供真实性、合法性;不如拿出一部分精力,同时关注如何完善和规范推定——这类“情理推断式”事实认定模式——的适用,这也将对贯彻证据裁判主义,强调客观证据与法律真实对于诉讼的意义。
(四)推定的别样价值:司法推动主义的强化
司法推动主义更能起到长远、有效和深入基层的作用;而推定就是司法实践中重要抓手。西方经典的启蒙思想和司法理论,由霍布斯、洛克、卢梭、孟德斯鸠等构建和论述,在相关经典著作中都表达了立法理性的笃定,并且显示了对司法权和审判方式的立法限制思想;本质上来讲,启蒙思想家认为民主法治国家应当依据法律文本审案,同时立法理性是凌驾于司法理性之上的⑨。但进入现代司法实践,显然不能再如此概括。我国当前司法改革大背景下,中央的文件和立法对各地的、基层的司法实践能起到的“自上而下”的作用追究是有限的,只有各地、各层级“摸着石头过河”的司法实践(推定就是其中一个抓手),才能使立法精神逐步实现:以庭前会议和羁押必要性审查的司法实践为例。关于羁押必要性审查,各部门之间存在细化变通是常态[14];关于庭前会议制度,刑诉法第182条关于“了解情况、听取意见”留下了解释空间,实务中,对于效力问题,各地适用规定有所不同[15]。以上是基于“司法推动主义”相较于“立法推动主义”的几大优势:实践性而非超前性、避免法律文化冲突、方便法律效果评估、协调部门利益,等等。
推定制度如果能够逐步成熟,增强程序规则及其效果,加强相关的专业的司法经验积累总结,完善相关案件的整理、指导案例发布等工作,加强文书的专门说理,以及其他庭审中的程序权利外观等,则推定制度将可能成为各地方司法实践完善化、特色化、程序公正化以及公开规范化的一个制度标杆。“徒法不足以自行”,只有将事实认定机制、证据裁判精神融入到各地、各层级不同的司法实践与程序中,才能使看不见的立法精神、政策导向,以看得见的形式各放异彩、逐步成长。
五、结语
本文以上分析已经在一定程度证明了审前“善用推定”尤其是事实推定的合理性,这种“推定方案”在程序正义以及外观的保障下,将对侦查取证乃至“检察前置介入”引导取证、制约侦查,及其后续证据审查过滤,起到良好的引导和纠偏作用。进而言之,完善“推定制度”的程序外观、细化其效力规定,应该比单纯批判和警惕更有现实意义。整个刑事审前程序证据体系完善、取证偏好改变、认知和证明模式转型,实现从主观到客观,从单一到全面,从印证思维到情理推断等变革——推定制度,其价值证成和功能重读、程序发展,都是必不可少的一环。申言之,其进一步发展将一定程度“反哺”证据裁判原则的实施。为此,应当注意如下几个方面。
(一)进一步“解构”当前理论
当前对于推定的理论认识,呈现过于技术化的解读倾向,也有以及“无罪推定”等经典原则的机械理解对其进行限制、谨慎对待的声音,更有反复炒基础理论冷饭的做法;对于这些理论方向,笔者已经进行了或多或少的反思和批判。但是,“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对传统推定的理论解读远谈不上“解构”的程度,如果不能对林林总总的推定规则、理论解释和方向论证,以及相关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如证明程序、证明标准、逻辑分类、相关概念和制度、历史渊源、制度基础、实践状态等——进一步深入研究,则只能达到“隔靴搔痒”的程度,理论研究,不能由此“不求甚解”的态度。因此,这一点上,今后的研究在做好足够的“破”的基础上,才能据此做好足够的“立”。这一点,王敏远教授已经在《一个谬误》一书中充分体现。
(二)推定中程序的具体形态
前文反复强调推定的形式理性光辉及其程序正义价值,但是对推定中的程序的具体形态,却缺乏一个基本的认识和论述,这留下了一个缺憾。可以说,本文基本打开了“推定制度必须具备全方面、全流程、实实在在的程序外观”这一个方向性缺口,但是独木桥只铺到了一半,如果不继续进行下去,则这前一半的价值也就只能停留在法理性、思辨性的层面了。因此,接下来的任务如果要以推动司法实践中推定制度完善,这样一个“经世致用”的目标,则必须对推定制度在审前、庭审中、裁判文书中全流程应当是怎样的样貌,对推定在举证、质证、认证和说理论证中呈现什么具体特殊性,对事实推定的基础事实之反驳、所有推定的推定事实之反驳权以及相应程序权利、救济、效果,等等问题,有整体的构建和论证。当然,这个过程不是闭门造车,必须充分分析域外样本、经验,深入中国司法实践进行考察,而后才能得出成熟的结论。
(三)推定与司法改革背景
最后,司法实践的形态,一定程度上也是由司法体制、生态所决定的,因此,不能不考虑法官所处的制度环境和生存环境。推定制度,与法官的素质、法官任职保障、法官独立性、法官文书说理的后果等都有一定联系。因此,充分考量员额制改革、司法责任制改革、法官独立化问题及相关内部指导、学习机制等,就具备了现实意义。从更深层次讲,相关证据问题、证明问题乃至大的事实认定问题,都离不开司法体制及其改革,否则其研究将虚无缥缈。
[注释]:
①当前关于刑事推定的代表性文献,参见龙宗智:《证据法的理念、制度与方法》,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298—309页;Michael.H.Graham,Federal Rules of Evidence,Copyright@West Group,610 Opperman Drive.pp.52-53;陈瑞华:《论刑事法中的推定》,《法学》2015年第5期,等等。
②以审判为中心改革中,实务界隐含着众多对于“推动方案”的重视,但这种高看似乎缺乏理论证成,参见刘建中、蒋和平:《审判中心视野下“零口供案件”侦查取证问题研究》,《中国刑警学院学报》2017年第1期;牟静雯:《侦查阶段客观性证据收集工作研究》,《公安学刊》2017年第3期;蒋和平:《“零口供”案件侦查取证技巧》,《现代世界警察》2017年第6期,等等。
③传统层面对刑事推定的讨论,主要局限于理念层面和价值评判层面,未充分结合理论与实践,参见卞建林等:《从逻辑到法律:推定改变了什么》,《南京大学大学法学评论》2009年春季卷;陈瑞华:《论刑事法中的推定》,《法学》2015年第5期;龙宗智:《推定的界限及其适用》,《法学研究》2008年第1期;张家骥:《论推定规则及其适用》,《重庆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20卷第6期,等等。
④陈瑞华:《论刑事法中的推定》,《法学》2015年第5期;龙宗智:《推定的界限及其适用》,《法学研究》2008年第1期,等等。针对推定与证明责任、证明标准的关系,几乎成了当前研究这个领域的主流,在此不展开了。
⑤历史上自由心证形成的体制背景和现实因素,参见罗伯特·巴特莱特著、徐昕等译:《中世纪审判》,浙江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前言第2—10页。
⑥自由心证的形成也是历时性的、实用性的,而非共时性的、理想型的,参见王亚新:《刑事诉讼中发现案件真相与抑制主观随意性的问题——关于自由心证原则历史和现状的比较法研究》,《比较法研究》1993年第2期,第117页。
⑦域外理论界,亦有针对推定制度及其概念本身的非议,但这种非议正体现了推定的理论解读存在问题,而非需要废止这个说法,参见Greer v United States,245 U.S.(1918),p.559,561;Bohlen,The Effect of Rebuttable。
Presumptions of Law upon the Burden of Proof,68 U.Pa.L.Rev.(1920),p.307,310-312;肖建华:《再谈民事诉讼中的推定》,何家弘主编:《证据学论坛》(第10卷),中国检察出版社2005年版,第325—326页。
⑧关于主流侦查学研究中关于审前侦查取证的研究倾向,乃至类似的实务界关切,参见杨宗辉主编:《刑事案件侦查实务》,中国检察出版社2011年版;杨正鸣、倪铁主编:《侦查学(第二版)》,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毕惜茜主编:《侦查讯问学》,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等等。
⑨传统启蒙思想家对立法和司法的论述中,充斥了对立法的笃信和对司法的质疑,起源于理性主义、构建理性色彩,其也多规划了立法推动司法发展的理念、模式,但在现代社会纷繁复杂的实践样态中,这些经典著作中的内容有必要重新认识。参见霍布斯著、黎司复等译:《利维坦》,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133—142页;孟德斯鸠著、许明龙译:《论法的精神(上卷)》,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93、94页;卢梭著、何兆武译:《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22—2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