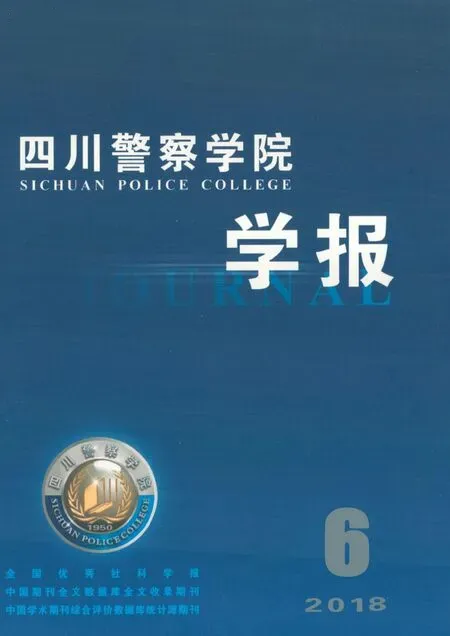刑法学与刑事执行法学的内在联动:由刑事判决到刑事执行的思考
曹 波
(贵州大学 贵州贵阳 550025)
一、问题缘起:刑事判决与刑事执行关系总览
刑事判决是人民法院依照刑法规定,根据查明的事实和证据,依法对被告人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构成何种犯罪、应判处何种刑罚的处理结论。而刑事执行,意指人民法院、公安机关、监狱等执行机关将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刑事判决所确定的内容付诸实施,以及解决实施中出现的执行变更等问题而进行的诉讼活动[1]。同属广义的刑事法学范畴,刑法学和刑事执行法学具有内在一致性和延续性,连接二者的桥梁和纽带即为刑事判决。作为刑事实体法和刑事程序法双向并进、综合作用之结果,刑事判决乃系刑事执行之根据,即刑事执行系刑事实体法和刑事诉讼法的综合适用的必然结果,相应地,刑事执行过程必须重现刑事实体法和刑事诉讼法的相关内容。即便如此,刑法学和刑事执行法学因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不同,而呈现相当差异性。刑法学是以刑法规范及其适用为对象,注重对行为人行为的评价,采用的是规范分析方法,可以通过研究者形而上的逻辑思维的演绎构建刑法学的知识谱系。而刑事执行法学是以各种刑事措施(包括但不限于刑罚)及其执行制度为研究对象,强调对实施犯罪行为的犯罪者的关注,采用的是社会学分析方法(其必然是一门包含法学、社会学、心理学、医学在内的综合性学科),其特征在于以刑事措施执行理念及目标的经验事实为基础,推崇实证研究,注重观察、归纳方法的运用。在这个意义上,刑法学虽然也具有一定的实践品格,但较之于刑事执行法学,仍不啻为一种“书斋法学”。以二者对死刑的研究为例,兴许可明晰二者的关系。刑法学主要关注刑法规定之死刑适用条件及执行制度,对死刑展开规范分析①。而刑事执行法学主要是对死刑执行的社会效果及死刑存在的社会基础的论述,二者的差别是显而易见。
或许正是二者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差异之故,由刑事判决所固定的刑法适用结果完全可能与实际执行的具体需求相矛盾。一般认为,这种矛盾体现在以下两方面:其一,由刑事判决所确定的刑罚已经执行完毕,但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并未实际消除,囿于刑事判决书的具体规定而不得不释放犯罪人的情形,即“刑罚不足”的情形。其二,在实际执行中,犯罪人在刑事判决书确定的刑期之前已经消除人身危险性,而使在人身危险性消除之后的刑罚成为“不必要”的刑罚的现象,即“刑罚过剩”的情形。由此本文形成三个问题意识:其一,“刑罚不足”与“刑罚过剩”究竟是相对于何者而言?其二,这种表面上并行不悖的“刑罚不足”与“刑罚过剩”是否真在实践中客观并存?其三,如何恰当利用现行制度消除实践中真正存在的矛盾?下文将就此展开。
二、“刑罚份量”的确定:刑罚正当化根据决定刑事判决
在主张“刑罚过剩”和“刑罚不足”论者的眼中究竟何种刑罚是既不“过剩”,也非“不足”呢?该问题必然涉及刑罚裁量,如此其便逸出刑事执行法学的领域,而成为一个地地道道的刑法学问题。在刑罚裁量过程中决定“刑罚份量”的因素属于刑罚正当化根据的范畴,亦即在何种意义上施以刑罚以及施以何种程度的刑罚才是正当的。不同发展阶段的刑法学对该问题做出了迥然有别的回答。
刑法理论上,关于刑罚正当化根据的主张存在报应论和预防论的对立。虽然在报应论者内部存在一定程度的分化,如有主张绝对报应刑,既有因侵害法益而主张刑罚,也有近来提得比较多的所谓的“正义补偿论”[2],但不论具体观点有何种区别,在报应论者看来,刑罚的正当根据是存在于过去的,是存在已然的事实之中的,对于适用刑罚所产生的预防效果,只是刑法适用者高兴见到的“附带效果”而已。与此相对,预防论者将刑罚视为社会控制的手段,将刑法正当化的根据求诸刑罚实际产生的预防效果,根据预防针对的对象的差异,预防内部又有一般预防与特殊预防的分立;另外,根据刑罚达至一般预防的效果是通过产生威慑效果还是通过激起人们的法忠诚意识的不同,又可以分为消极的一般预防与积极的一般预防②。值得注意的是,时至今日,绝对报应论或者单纯预防论都没有学术市场,两种学说之间正在实现某种调和,而致并合主义成为主流观点。
事实是,产生所谓的“刑罚不足”与“刑罚过剩”的根源完全在于刑罚裁量所采之标准与执行中所采之标准存在差别,这也是刑法学与刑事执行法学相当重大的区别之一。详言之,刑罚裁量标准在于刑罚的正当化根据,除了绝对预防论以外的报应论及并合主义均强调“报应”(罪责、非难)在刑罚裁量中的重要作用,而被告人的人身危险性(或“预防必要性”[3])在量刑阶段只是为追求刑罚个别化而考虑的次要要素。与此不同,刑罚执行中执行者虽在一定程度上要发挥刑罚的报应效应,但其更为关注的是如何最大限度消除服刑人员的人身危险性以使其尽快回归社会。一言以蔽之,刑罚裁量追求之目的在于报应及一般预防,特殊预防仅是考虑的次重点,而刑罚执行所执着的乃是特殊预防,报应与一般预防早已因在刑罚裁量中得以实现而退居次要位置。
如果认同上述论点,那么如下的论述便是理所当然的:报应思想(并非仅仅是绝对报应主义,还包括并合主义中的报应元素)将刑罚的根据委之于已经发生的客观犯罪事实,因而在某种意义上具有相当确定性,刑罚执行过程中出现的具体情况并不是刑罚裁量时法官应该考虑的,法官考虑的重心应该是犯罪行为对法益(社会关系)抑或规范有效性的破坏程度,故只要能够信赖法官可以依照既存事实公平公正地做出判决,那么判决中所裁定的刑罚便是正当且必要的刑罚,而不会发生所谓的“刑罚不足”或“刑罚过剩”的困惑。
之所以产生“刑罚不足”或者“刑罚过剩”的问题,完全是将预防效果(人身危险性)作为刑罚正当化的根据的结果,这是因为,“刑罚不足”与“刑罚过剩”皆是相对于罪犯的实际改造效果而言的,是将刑事判决书所确定的刑罚与消除罪犯人身危险性所需要的时间相比较而得出的结论。具体而言,刑事执行者在某种意义上扮演了预防论的执行者的角色,将刑罚当作消除罪犯人身危险性和预防(犯罪者或者一般人)犯罪的工具,只要能够消除罪犯的人身危险性的刑罚就是正当的、必要的,超出预防需要的刑罚也构成刑罚滥用。为此,法官在确定犯罪人刑罚时,应该着重考虑预防必要性(人身危险性),行为人的犯罪行为仅仅是其人身危险性的表征,法官正是通过对行为人犯罪行为及其后果的综合衡量来主观预测行为人的再犯可能性。但是这种将刑罚的根据求诸将来没有发生的“危险”的观点,是存在很大问题的。因为至少仅考虑人身危险性必然得出“不确定刑”的结论,其必然违背罪刑法定原则的规定,并进而违反法治国保障人权的要求,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才会得出所谓的“刑罚不足”或“刑法过剩”。
在本文看来,即便存在一个几乎不可能被质疑的观点——刑罚从来没有治愈任何一个被侵害的法益,也不足以将刑罚与一个可能出现的利益——预防犯罪——相联系。如前所述,预防犯罪包括特殊预防和一般预防③,其中特殊预防论的大前提是已经实施犯罪行为的人也存在继续实施犯罪行为的危险,正是在这样一个前提之下构建特殊预防理论的大厦。但是我不禁要问这样一个前提是必然存在的吗?众所周知,特殊预防理论是新派学者在对犯罪原因剖析的基础上,提出的犯罪对策。西方“犯罪学三圣”之一的加罗法洛对此就毫不讳言,“我们信奉这一点,即对犯罪必须施以损害仅仅是因为罪犯自身所引起的危险。特殊预防应是刑罚的直接目的。”[4]姑且不论特殊预防在实践中取得的效果,在犯罪原因(特别是再犯原因)的分析上就可以看出上述前提的缺陷。众所周知,犯罪原因存在龙勃罗梭的一元论、李斯特的二元论、菲利的三元论等的对立,暂不论菲利和李斯特都直接强调犯罪的社会原因(或者自然原因与社会原因),就是一元论的龙勃罗梭也没有将视野投向行为人事前的犯罪行为,而是注重遗传因素(隔代遗传、返祖现象)对犯罪的决定作用。过分注重犯罪人的生物因素固然存在其重大局限性,但是犯罪的社会原因的分析无疑具有相当的说服力,也为本文所赞同。特别是在目前正处于经济社会转型期、各种社会矛盾交织突出的中国,对社会原因的强调更能向我们展现犯罪的深层根源。由此可见,预防论建立的前提存在商榷余地,其所导出的结论必然是:“刑罚不足”与“刑罚过剩”都是存在商榷的余地的。
虽然根据不同的刑罚正当化根据有否认“刑罚不足”或者“刑罚过剩”之虞,但这恰好反映出刑罚正当化根据对决定刑罚量的重大影响,也反映出刑法学对刑事执行法学的内在制约。不惟如此,非但社会是流动变化的,罪犯个人不论其是在监狱里还是社会之中也都是不断流动变化的。在决定刑罚量的时候,很难设想在几年以后或者是几十年以后罪犯的改造或矫正情况,但是又不可能随时根据罪犯的改造表现而随时作出改变。一方面,人都有伪装自己以展现好的一面,其内在的人身危险性并未消除,在其趋乐避苦动机的推动下,为尽快、最大限度地摆脱当前的不利遭遇,而不得不伪装自己,展现自己被改造所取得的“良好效果”。要求法官裁量的刑罚能够真正对应于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是对法官的过度、甚至是过分要求。另一方面,其欠缺可操作性也是显而易见的。由于技术条件的限制或者根本不可能测定所谓的改造效果,不可能也不应该要求矫正人员随时随地检测出罪犯的改造效果或者人身危险性的消除情况。
三、“刑罚不足”的否定:罪刑法定制约刑事执行
罪刑法定原则是近代刑法最为宝贵的财富,其作为刑法之铁则,是不容撼动的。罪刑法定原则不仅在刑法领域必须贯彻,对行为的规范评价起着原则性限定作用,而且也必然随着刑事判决书而流向刑事执行领域,在刑事执行之中发挥不可限量的意义。以罪刑法定原则为根基的适用刑法过程,便是将刑法规范的内容固定于刑事判决之中,通过刑事判决体现出来。刑事判决书是刑法规范的自然延伸,执行刑事判决的过程其实是就是真正实现刑法规范的过程,是刑法规范从“书本中的法”到“行动中的法”的华丽转变。在刑事执行领域依然要贯彻刑法规范,依然要坚持罪刑法定原则,并且要保障坚持罪刑法定原则的刑事判决书在刑罚执行中能够得到强有力的贯彻落实。另外,又因近代刑法客观主义确立的罪刑法定原则之最大机能在于约束国家权力,保障公民权利,罪刑法定原则承认有利于被告人(罪犯)的形式侧面,所以允许在刑事执行过程中,可以依据改造的效果,在满足法定条件下,减少由原判决确定的刑罚量,或者变更原判决确定的刑罚执行方式。因此,“刑罚不足”与“刑罚过剩”中,真正成为问题的仅是“刑罚过剩”。
同作为刑罚执行过程中出现的刑罚实际需求与刑罚具体执行之间矛盾的“刑罚不足”与“刑罚过剩”,缘何仅“刑罚过剩”成为问题的争点?实则,“刑罚不足”无外乎有两个人们不愿见到或者不愿承认但又必须实际面对的原因,即刑事判决书所确定的刑罚畸轻,以至于不能真正为改造犯罪人提供适当的刑期,以及刑事执行的具体程序不能在刑事判决书所确定的刑期内真正改造犯罪人,消除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前者是量刑失当,后者是改造无力。
然而,本文并不认为存在“刑罚不足”的问题。首先,可以通过严格规范量刑程序,综合考量各种量刑情节,最大限度实现刑罚个别化;其次,如若在释放罪犯时,罪犯依然存在人身危险性,那么便可以根据人身危险性的大小,在有保安处分制度的国家对行为人施加一定期限的保安处分;在没有保安处分的国家或者地区中,也不必为保安处分制度的欠缺而懊恼,因为如果行为人真正具备一定程度的人身危险性的话,他一定会再度实施犯罪,进而重新置身国家的监控中去,回到监狱中来,这是人身危险性即再犯可能性之由;最后,“刑罚不足”现象既可以视为对国家权力的过度约束,也可以视为对犯罪人的一种“恩赐”。在现代法治国家要求限制国家权力的呼声下,以对犯罪人的“法外施恩”换取“不当”约束国家权力,是贯彻形式法治的必然成本。再者,所谓确定改造效果——消解人身危险性,在没有确切的科学仪器检测之前,其是并且仅仅是人们的一种假说而已。所以,“刑罚不足”不是一个问题,或者不应该成其为一个问题。
四、消解“刑罚过剩”:减刑假释制度
刑罚正当化根据在决定“刑罚不足”与“刑罚过剩”的同时,也深刻影响直接针对“刑罚过剩”的减刑假释制度的存在。具体而言,在绝对报应刑的时代,可能存在的只是基于统治者的“恩典”而缩短刑期的情况,减刑假释制度缺乏生存的价值土壤和理论空间。而在绝对预防论那里,也没有减刑假释制度存在的必要,因为如果彻底贯彻特殊预防论,根据实际矫正的效果而决定是否释放。对于没有矫正可能性的,就应该从肉体上消灭或者流放荒岛,对于有矫正可能性的,则实施矫正。其典型代表当属李斯特无疑,李斯特在犯罪原因二元论的基础上,将犯罪人分为机会犯和状态犯,其中状态犯又可分为可以改善的犯罪人和不可改善的犯罪人,对于前者应当适用教育性或矫正性处分,使其适应社会;对于后者则应将其从社会中剔除[5]。并且,预防论(不论是一般预防还是特殊预防)有一个不可回避的通病,即“在这个理论中没有包含刑罚期间的界限”[6],可以把一个被判刑人关押到其已经重新社会化为止,这就导致“不确定刑”,很难想象“不确定刑”的语境中有减刑假释制度存在的必要。由此不难得出,减刑假释制度仅可能存在于刑罚正当化根据采并合主义的场合,这也是当代各国所普遍坚持的立场。
必须承认,减刑假释制度具有消解“刑罚过剩”的重要机能。我国《刑法》第四章第六节和第七节分别规定了“减刑”和“假释”的适用条件和具体程序,《刑事诉讼法》第262、263条也对减刑、假释的具体程序做出规定,以与刑法的规定对应、协调。“减刑”和“假释”不仅仅是为鼓励犯罪人改造的制度,更是在一定意义上,根据实际改造效果,将“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的或者有立功表现的”和“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没有再犯罪危险的”分别通过减少原判刑罚或者附条件提前释放的形式缓解“刑罚过剩”的问题。所以说,即便存在问题的“刑罚过剩”,也可以通过减刑和假释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得以缓解。最后,还须提及的是,减刑假释制度的具体执行过程也必须谨守罪刑法定原则和法治原则,因为在一定程度上,减刑和假释都是对原判决书既判力的否定,这种否定在法治国家中只能由做出判决的法院或者是上级法院依照法定程序做出,这是在对减刑假释制度改革过程中必须引起重视的。
五、结语
加强刑法学与刑事执行法学的内在联动,必须以刑罚正当化根据和罪刑法定原则为主轴,实现刑事判决和刑事执行的衔接与贯通。在刑事司法实践中,理应清晰认识到由刑事判决所固定的刑法适用结果完全可能与刑事执行的实际需求相矛盾,即有出现“刑罚不足”与“刑罚过剩”现象之虞。不过,刑事判决是根据刑罚的正当化根据确定的具体案件中所需判处的“刑罚份量”,但刑事判决阶段追求之目的在于报应及一般预防,特殊预防仅是考虑的次重点,而刑事执行阶段追求的乃是特殊预防,报应与一般预防早已因在刑罚裁量中得以实现而退居次要位置。“刑罚不足”与“刑罚过剩”皆相对于罪犯的实际改造效果而言,是将刑事判决书所确定的刑罚与消除罪犯人身危险性所需要的刑罚相比较而得出的结论,完全是将预防效果(人身危险性)作为刑罚正当化的根据的结果。然而,从罪刑法定原则内含之限制公权力与保障人权的立场出发,“刑罚不足”是因量刑失当或改造无力所致,并不能成其为真正的问题,真正成为问题的仅是“刑罚过剩”。当前,我国刑法确立的减刑假释制度,可以根据刑事执行过程中被执行人人身危险性的消释情况,减少或附条件不执行刑事判决所确定的刑罚份量,从而消解“刑罚过剩”的问题,避免不必要的刑罚执行给被执行者权利带来不必要的剥夺。
[注释]:
①必须同时指出:在刑法学中对死刑更高层次的研究一般表现为“死刑利弊的分析与死刑存废的论证”。参见陈兴良:《刑法的知识转型(方法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7页。
②需要注意的是,刑罚正当化根据中报应论与预防论的对立是一直流传到现在的传统观点,而德国刑法学家雅各布斯教授提出了一种新观点。在他看来,刑法保护的不是法益,而是规范适用,犯罪是破坏规范有效性的行为,刑罚是对规范有效性进行恢复与确认(雅各布斯:《刑法保护什么:法益还是规范适用?》,王世洲译,《比较法研究》2004年第1期)。雅各布斯教授的主张逐渐成为一种有力的学说,在德国得到米夏埃尔·帕夫利克(有人称其为“雅各布斯第二”)的追随,在日本得到松宫孝明教授的支持,在国内则得到冯军教授的提倡。例如,冯军教授在《刑法问题的规范理解》(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一书中就表达了类似的观点:犯罪是对规范的否认,刑罚是对犯罪的实在法规范性报应。在没有否认实在法规范效力的地方,就不需要刑罚。刑罚的份量是与否认实在法规范效力的程度相适应的。
③一般预防论在当下面临最大的指责在于将犯罪人作为预防犯罪的“工具”,进而违背了在法治国理念下人只能作为目的而不作为手段的人权观念。不论是消极一般预防的威慑论还是积极一般预防的忠诚论都难逃上述诟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