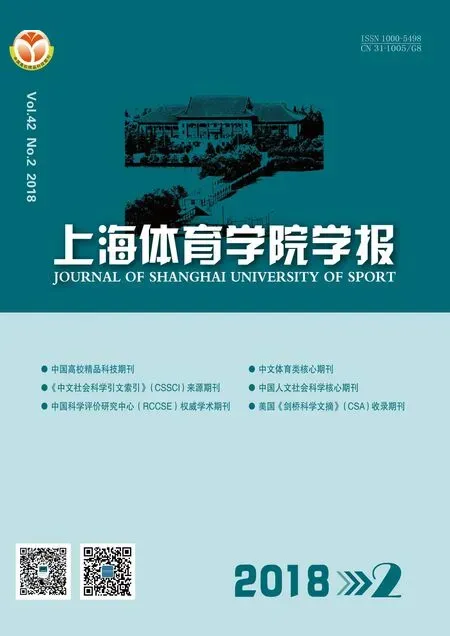体育自治的导向:体育自治权的属性辨析
李 智, 喻艳艳
(福州大学 法学院,福建 福州 350116)
近年来,国际足联腐败事件、俄罗斯田径队兴奋剂事件等一系列国际体育事件的发生,不仅使国际体育组织的公信力受到广泛质疑,而且导致外部司法力量的直接介入,严重动摇了体育组织的自治管理模式。这一系列事件表明:体育自治权出现权力化趋势,引发滥权、渎职、腐败等各种问题,暴露了目前体育自治管理模式的缺陷以及规制能力的不足,这也是导致外部司法力量介入的直接原因。外部司法力量的介入影响了体育自治这一体育领域的基石。因此,厘清体育自治权的属性,完善自治权行使的方式,协调与外部规制的关系,是实现善治的根本。
1 体育自治权的属性之争
“权利”与“权力”之争是法理学领域的一个基础性和历史性辩题,同样,对体育自治权在属性上是“权利”还是“权力”的界定,也影响着体育自治权的范围划定、行使方法以及规制方式的确定。一直以来,虽存有争议,但学界普遍将其视为一种行业自主治理权利。晚近以来,体育组织出现了较为明显的权力化扩张趋势。2015年,国际足联爆发腐败案件,国际足联对世界足球运动所拥有的绝对治理的绝对权力[1],是导致自治体系失控的重要原因。体育组织的自治管理已扩张出较大的权力内容,并形成了公共权力之外的一种新的形态,进而引发了体育自治权的属性之争。
1.1体育自治权的产生与发展体育自治权产生于体育活动参与成员的权利让渡和自愿认可,追溯体育自治的历史脉络,最值得一提的是阿诺德在拉格比公学进行的体育教育改革。他将学校内的运动竞赛组织工作委托给最有威信的学生,让他们管理运动场,按照自主原则组建运动队和俱乐部,举办比赛。这种自主管理的方式迅速从校园走向社会,从国内走向国际。虽然在阿诺德的改革中,指定管理者的改革手段使体育自治权的产生略带强权色彩,但在传播和发展的过程中,逐渐演变成现今体育领域的以自愿为核心的自治模式。因此,体育自治权的产生和发展包含着浓重的“契约论”和“自生自发”的理论色彩。
依契约论,人生而自由,但为实现权利,需要通过权利让渡的方式形成制度和规则,并自愿遵守[2]。哈耶克将社会秩序规则分为“自生自发”的秩序和“组织或者人造”的秩序。前者又称为内部秩序,这种秩序不具有共同的目的等级序列,所具有的是每个人的目的,但这些不尽相同的目的因行动者遵循规则而得到彼此协调[3]。分析国际体育自治的产生,其依赖于私人契约,进而体系化发展,形成自治秩序,应属“自生自发”的秩序。首先,体育运动是人类在发展过程中自然出现的一种行为方式,能促进身心健康,在产生之初与社会公共秩序并无牵涉。其次,人类自由地进行体育运动,而后产生了竞技体育,并逐步发展出职业体育。这一发展进程与业余体育并行不悖,只是这个“磁场”越来越大,吸附物与日俱增,参与主体实现了广泛性。为了更好地开展体育事务,需要有专门的人员、机构进行管理和组织,制订专门的规则予以规制。于是,参与者们将管理权、规则的制订权等基础性权利让渡出来。再次,在受让主体的选择上,基于业务熟悉程度的考虑,受让主体显然更愿意把权利交予了解并热爱体育的人。由此,通过“个人契约”的方式,体育自治权的权利让渡与交接顺利完成。最后,20世纪以来,体育运动国际化极大推动了国际奥委会、国际单项体育运动联合会、国家奥委会、国内单项体育运动联合会等体育组织的发展,在成员自主参与的基础上,体育自主治理权交由各体育组织行使,通过层层让渡和授权,形成了较为系统的国际体育自治权体系。
体系化的国际体育自治权的权属内容可以概括为3大类:①组织管理权,这是体育自治权最基础的内容。举办体育活动和组织体育赛事是体育事务的起点,包括内部建设管理权和外部组织管理权,即成员的接纳和取消、内部组织框架的构建、内部管理机制的完善,以及举办体育赛事和管理其他相关的体育活动。②规则制订权,这是体育自治权最重要的内容。体育组织通过制订自治规则,将体育自治体系固定下来,以此规范竞技体育,将体育参与者让与权利的目的通过统一的赛事规则体现出来。根据效力层级,依体育自治权所制订的规则可以分为自治章程和其他规范性文件;根据内容,可以分为技术性规则和非技术性规则。其中,技术性规则主要指赛事规则,非技术性规则包括内部运作规则、纪律规则、纠纷解决规则等。③解决争端权,这是体育自治权最具发展性和强制性的内容。体育自治权中的争端解决权主要由2个部分构成,一部分是各个体育组织对内部纠纷的解决权,另一部分是国际体育仲裁院对国际体育纠纷的解决权。二者分别依托体育组织的内部纠纷解决体系和国际体育仲裁制度,自主处理体育纠纷。
可见,体育的娱乐性、健康性、发展性以及公益性等原初土壤,滋养了底蕴深厚、发展良好的自主治理文明,这也是体育爱好者和参与者智慧的结晶,人类智慧在自发的构建治理制度创举中催生了体育自治权。即使晚近以来问题出现,但主流观点仍是呼吁以完善自治为核心,追求体育的良好治理。而且,一贯以来,行政和司法等外部力量对体育自治秉持审慎的干预态度,从侧面为体育自治权的发展提供了独立自主的现实环境,使得“私人契约”的产生基础和“自生自发”的发展秩序得以固化。
1.2体育自治权的属性争议与权力化趋势如上所述,以契约为基础,体育自治权自发成体系化,并得到了内部成员的高度认可和外部管制力量的尊重。以此为基础,体育自治权的形成、发展及内容体现了以下3个主要特点:①权源上的契约性。无论是竞技体育还是业余体育,无论是参加体育赛事还是参与其他体育事务,都体现了自愿性。通过自愿让与产生了体育自治权,是意思自治原则的契约化过程,也是外部力量审慎干预体育自治权行使的原因所在。比起外部强制力,植根于内心意愿的契约精神更能确保治理的成效。②权利形式上的发展性。体育自治源于个人创造,最初也是交由体系内的个人行使的,这一阶段的自治权可以归结为代表权。在体育组织产生之后,转由组织行使,发展成为团体自治权的一种。目前,尚无法断定这是否是体育自治权发展的终点,未来是否可能探索出的新形式,值得期待。③权利内容上的综合性。通常,可以根据某一权利或权力的内容对其进行类型化,例如管理权、审判权、处罚权、处分权等。体育自治权利的组织管理权、规则权以及争端解决权,既有实体的内容,又有程序的内容,既有决策层面,又有管理层面,既有规制性,又有保障性。可以说,体育自治权既有明显的权利发展轨迹,又具备权力的某些共性。因而,对其权属特征的定位,存在以下3种主要观点。
(1)社会权力说。该观点从体育自治权的权力性出发,认为这是一种不同于国家权力的社会权力。这种社会权力是社会主体运用其所拥有的社会资源对社会和国家的影响力、支配力,是全球公民社会中的治理权[4]。该观点在逻辑上的建构是可行的,先进行基础的定性,再运用比较研究方法将其归为社会权力,由此将其与国家权力、其他公共权力区分开来,充分考虑了自治的特殊性。但是这种观点易将体育自治权与其他行业的自治权混淆,忽略了体育运动的娱乐至上性的本质以及其他特殊性。而且,“支配力”的阐述放大了体育自治权的效力,也与体育参与者让渡权利的初衷相背离。寻求体育自治,其目的是让“体育的归体育”,并非是支配公共资源,甚至是公共权力,而是探索体育领域更好的治理方式和发展模式。
(2)权利说。依该观点,体育自治权在本质上仍是一种权利。所以,持此观点的学者常对体育组织所采取的某些强制措施的合法性和公正性提出质疑,例如禁赛、强制仲裁等[5]。诚然,权利说具有基于体育自治权权源上的契约性特点,体现了对体育精神和体育领域私人治理方式的尊重。然而,其对体育自治权内容的扩张性和影响范围的延展性,未做出关注和解释。一般情况下,类型化权利的内容指向往往较为明晰和单一,影响范围也常以其他权利或公共权力为界限,有时还受地域性的制约。体育自治权在内容上具有综合性,具体内容体系化,在影响范围上则具有国际性。体育自治权的扩张性和延展性已经突破了权利的请求效力和抗辩效力,具备了一定的类似于权力的强制效力。
(3)综合说。该观点不对体育自治权进行定性,认为体育组织的权具有广泛性,除了自治权之外,还有其他内容,强调自治权兼含权利和权力[6]。综合说采取了一种折中的方式,兼容并包,试图全面表述体育自治权的内容。但在基础问题上模糊定性,会给体育自治权的行使方式、规制方式以及改革导向带来摇摆不定的风险和困难,不利于体育自治权的结构化和法治化。
综上,有关体育自治权的权属争议主要在于:相比依契约取得的类型化权利,其又具有权力的内容,尤其在外部管制力量对其高度尊重的情况下,在规则制订、争端解决等方面,权力化特征更加明显。自治权利的权力化是晚近体育组织治理过程中最明显的趋势。
首先,体育自治权在性质上应该为“权利”,基于体育的特殊性,这种权利包含了部分权力的内容。例如:对运动员参赛权利的规定类似于行政权中的审批权;对运动员的禁赛处分、对管理者“禁止从事足球事务”处罚等纪律处分,则类似于行政处罚权,甚至可以类比为司法审判权对个人权利的限制。这些权属内容在国际体育领域已经实现了普及化,并且得到体育领域内外的高度认可。以争端解决权为例,它是体育自治权中最具发展性和强制性的内容,“权力化”趋势也最为明显。一方面,体育自治争端解决在效力上具有内外的强制力。目前,国际体育争端解决机制是递进式的3层结构:①体育组织拥有对内部争端解决的优先权,国际体育仲裁院及各国法院均对此予以尊重[7];②国际体育仲裁院通过各体育组织的章程及运动员协议,取得仲裁管辖权;③各国司法力量对体育争端的自治解决予以尊重,审慎介入。体育争端解决的实践表明,国际体育争端解决机制兼顾了效率和公正,不仅有效解决了各类体育争端,且得到了内外部的尊重和认可,兼具极强的内部强制效力和一定的外部强制效力。另一方面,体育争端的解决在形式上具有类司法权性。争端解决体系的构建是国际体育秩序得以维护的命脉,在争端解决过程中可能会出现管辖权、规则适用、裁决的承认与执行等问题,使争端解决权备受“准司法权”的质疑。
其次,“权力化”趋势并未改变体育自治权的权利属性。①私人意思自治的契约基础所奠定的内在权利属性未被改变。近代以来,权利本位思想占据主流,强调权力来源,并服务于权利,形成了“权力的权利性”的生成逻辑:权力的内在属性中包含了权利的价值指向与功能,权力的起源、运行与发展过程会受到权利的价值与功能的指导和规制[8]。即:权利是权力的内在属性,而非外在特点。体育自治权的发展轨迹恰恰相反,起点是权利,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若干被广为接纳的权力的内容与特点。然而,这种特点仅限于外部形式,其内在属性仍然是权利。②以内部自愿遵循和外部审慎干预为原则的权利行使方式未被改变。换言之,如果突破了权利的性质,内部强制力将不再以自愿遵循为基础,转而以权力的强制性为基础。根据权力的扩张本性,公共机关的介入随之成为常态,审慎干预模式将被“以权力制衡权力”的模式替代。
虽然在内部认可与外部尊重的作用下形成了程度不同的内外强制力,推动了体育自治权利的权力化,但这种“权力化”是一种“外在特点”,而非“内在属性”。而且,这种“外在特点”仍给国际体育治理带来了不小的冲击,不容忽视。
1.3体育自治权权力化趋势的影响“权力化”趋势最直接的表现就是体育自治权的内部强制效力日渐增强,并延伸出一定的外部强制效力,进而产生了正反两方面的作用。
一方面,体育自治权的权力化提高了体育组织的“自治能力”。比如,就争端解决来看,国际体育领域已经逐渐形成了由国内单项体育协会仲裁机构、国际单项联合会纠纷解决机构和国际体育仲裁院组成的具有层级结构的“类司法体系”。体育组织通过这一体系增强“体育王国”的自治能力[9]。自治能力提高后的国际体育组织顺应体育商业化的潮流,通过电视营销权、赛事举办权、商业赞助权以及媒体运营权等权利创造了巨大财富。以国际足联为例,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世界杯足球赛的营销利润逐年递增,收益已经占到国际足联财政收入的90%[10]。财政独立和自治能力的增强是一个双向的良性循环的发展过程,两者之间是互促的。财政上不依附于政府等外部机构后,体育组织自治权利的行使就更加独立;但这也容易使体育组织形成垄断,拼命逐利。
另一方面,体育自治权的权力化也导致了权利滥用,滋生了不当和违法行为,最终导致司法的强势介入,从而对体育自治权造成根本性冲击。在国际足联腐败案中,国际足联的数名高管遭到欺诈罪、洗钱罪、勒索罪等多项犯罪指控,严重损害了体育自治权最主要的行使主体——国际体育组织的公信力,还引发了民众对体育自治体系的质疑与否定。以契约为基础的体育自治权利在权力化趋势的影响下,沾染了权力的若干不良属性,在利益的诱导下成为钱权交易的温床。在管理上,权利行使存在缺乏透明度、问责机制等弊端,使得规则制订、组织管理以及争端解决的公正性饱受质疑。这些问题直接导致了近年来外部司法力量对体育领域活动干预的不断增长,从而使国际体育争端解决出现了崇法主义倾向。其中,最为典型的案例是德国慕尼黑地方法院于2015年1月15日对德国滑冰运动员Pechstein案作出的裁决,该裁决依托德国和欧盟的垄断法和竞争法,对体育仲裁协议的自愿性、仲裁庭组成的独立性以及裁决的公正性提出质疑,否定了国际体育仲裁院的裁决。虽然在上诉审理中,德国联邦最高法院撤销了慕尼黑地方法院的裁决,维护了国际体育仲裁院的权威,但慕尼黑地方法院的裁决给体育争端自治解决体系造成的冲击堪称“地震级”。
可见,体育自治权利的“权力化”趋势对国际体育自治的发展是一把双刃剑,在增强自治能力的同时也会造成权利滥用,引发外部干预,从而由内而外地削减自治成效。因此,分析体育自治权权力化发展的模式,厘清当下体育自治权的属性,方能准确定位体育自治权的基本功能,提出适应体育活动的治理方式。
2 体育自治权的权利发展模式
体育自治权利的权力化趋势是在体育的商业化、政治化以及社会化过程中,因内部认可和外部尊重程度日渐提高而促成的。因此,与公共权力、其他团体自治权以及体育活动参与主体的个人权利相比,体育自治权形成了一套颇具特色的权利发展模式。
2.1利与力:体育自治权与公共权力公共权力是指在公共管理过程中,由政府及其相关部门掌握并由其工作人员行使的,用以处理公共事务、维护公共秩序、增进公共利益的权力。基于权利与权力的本质差异,体育自治权与公共权力的区别显而易见,但二者的共性也较易窥见,即都致力于实现维护良好秩序以及实现更好发展的价值。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在建立了以主权国家为主体的平权式国际社会体系后,即代表对外独立权和对内最高权的最大公共权力——国家主权,树立了绝对权威,国际社会和绝大多数国家都维持了较为稳定的社会秩序,人类社会也进入了快速发展的阶段。同样,体育自治权产生伊始也是为寻求更好地开展体育活动的方式。而在其发展进程中,尤其是国际体育组织“遍地开花”之后,体育自治权内容得以丰富,权利得以充分行使,实现了国际竞技体育的组织化、规则化和制度化,建立了较为稳定的国际体育秩序。然而,权利是利,权力是力,毕竟是不同的事物[11]。
(1)在权源上,二者虽然都可以运用“社会契约论”理论进行解释,但是权利让渡之后,所形成的公共权力本身就有了发展和修饰,创造出“国家强制力”和“暴力机关”,以确保公共权力的实现。受让形成的体育自治权仍保持权利的状态,维系运行的也是成员的尊重、认可以及自愿遵从,所以在起初并无外化的强制效力,也并未产生体育自治强制机关。
(2)在公共权力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一套从人民到法律的权力认证范式,在现代社会,法律捍卫权力并使之合法化。体育自治权并不存在这样的论证模式,它不需要得到法律的认证,即得到承认,并维持良好的运作状态。即“法无规定皆禁止”和“法无禁止皆自由”的分别适用,只要不违反法律的规定,自治权的行使在权利让渡范围内是自由的。同时这种自由是法治下的自由,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也不能凌驾于国家主权之上。因此,不难理解在国际足联腐败案件爆发后,马上引发了公共权力干预体育自治的强烈冲动,并付诸实施,体育自治权并不能成为国际体育违法和犯罪行为的保护伞。
(3)公共权力,尤其是国家公权力,是公共产品的当然提供者,公共产品兼具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例如国防和立法行为等。体育自治权却并非体育公共产品的提供者,这也是体育自治权与体育行政权的最主要区别。体育自治权被权利来源方赋予了促进世界体育发展的使命,不同的体育组织的自治权内容和范围不同,提供的产品具有竞争性。在本质上,体育自治组织的义务之一是使权利让与主体的利益最大化。尤其是在职业体育领域,为成员创造的利益量决定了职业联盟或俱乐部的认可度,也直接决定了他们自治权利的大小。以转会制度为例,转会规则日趋复杂,考虑的因素不断增多,正是在市场经济供需杠杆的作用下,体育组织运用自治权完善规则以提高竞争力。再如体育赞助制度,它是体育自治权发挥调适作用,寻求体育运动与商业经济并行发展和利益平衡的产物。
2.2公益与共益:体育自治权与其他团体自治权团体自治权是指社会组织进行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发展的权利[12]。广义的团体自治权还包括民族区域自治权等因地缘、血缘因素形成的公共自治权。狭义的团体自治权仅指社团自治权,较为典型的如各行业的自治权。这些团体的自治权(也称行业自治权)在权源上都是产生于会员之间的契约[13],在利益追求上都是谋求行业成员的共同利益。体育自治权应归属狭义团体自治权的范畴,不过,凭借体育的特殊性,体育自治权较之其他团体自治权又具有以下3个明显特征,并成为体育自治权突破权利“栅栏”,日渐延展出权力强制力特点的内因所在。
(1)体育自治权具有更彻底的自治性。以争端解决为例,体育自治权的彻底性在国际体育强制仲裁制度上得到凸显,国际体育仲裁院仲裁制度使国际体育仲裁院的仲裁管辖权和仲裁裁决权威得以确立。相比较而言,商事仲裁制度虽也得到了广泛的运用和认可,但国际商事仲裁的广用性得益于仲裁解决商事纠纷的优越性,而国际体育仲裁体系的发展,除了延展了仲裁的优越性之外,也进一步推动了体育领域的自我治理。
(2)体育自治权具有更明确的公益性。体育是促进全人类身心健康的事业,竞技体育产生伊始就被赋予“停战”的和平使命,并产生了“奥运停战协议”。近代以来,体育在国际政治交往中更是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比如中美的“乒乓外交”,而“足球”等甚至成为某些民族和国家精神的象征。所以,即使受到商业化的冲击,体育所倡导的和平、共赢的理念,仍然是其最终的内在追求。所以,在体育自治权价值理念上,公益性和共益性是并列的,这也是体育自治权得到极大尊重和信任的原因之一。相对而言,其他团体自治权更强调共益性。尽管也提及社会责任,但这种社会责任的实现往往也是为了通过树立良好形象获得更大的经济效益,这与体育治理的公益性诉求相去甚远。
(3)体育自治权始终与公共权力保持距离。晚近,其他行业自治权与公共权力的关系出现趋同。公共权力通过委托或者授权等方式,将部分权力交予团体组织行使,将部分职能委托其履行,行业自治权和公共权力通过行使主体的趋同在某些领域实现了统一。反观体育自治权与公共权力,则始终保持相互独立的状态,近年来还时有冲突,冲突的解决过程均是在坚持体育自治性的基础上,不断明晰着二者的边界。哈耶克曾经指出:在一个传统和惯例使人们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都可预期的社会中,国家的强制力可以降低到最低限度[14]。以自治权行使为核心所建构的国际体育治理机制,凭借自治的优越性,弱化了国家强制力即公共权力的作用空间。
2.3集体与个体:体育自治权与其他体育参与方权利权利冲突是平等主体间法律纠纷最常见的原因,体育领域亦然。体育自治权来源于成员方的权利让渡,但伴随着体育利益和体育参与主体的不断增多,体育自治权得以扩展,也导致它与其他体育参与方权利之间的冲突频发。参赛资格纠纷、强制仲裁公平性争议、赞助合同纠纷等事件逐渐成为体育争端中的主要问题。明确二者的关系和边界,是解决争议的根本。
(1)自治权应遵从成员意志。体育自治权的唯一来源是体育参与方的个体权利,因而其权利边界以成员权利让与程度和范围为限。以体育仲裁协议制度为例,在国际体育争端解决体系中,通过3个环节确定了体育仲裁协议具有相当的强制性:一是仲裁协议的条款化;二是仲裁条款的格式化;三是格式化的仲裁条款在特定因素促成下,产生了强制效应[15]。分析此处的“特定因素”:当事人在选择参与某一国际体育组织或国际体育赛事时,已行使了自主选择权,自主将争端解决方式的决定权让与国际体育组织,国际体育组织行使受让的权利,制订了统一的“强制仲裁协议规则”,改规则适用于参与的成员。意思自治是启动仲裁程序的起点因素,这种得到认可的强制仲裁协议制度形式上是强制的,在实质上仍是意思自治。因而,即使国际体育仲裁院仲裁选择协议具有强制力,但其根本仍来源于成员意志。在上述德国速滑运动员Pechstein案中,国际体育仲裁院强制仲裁条款虽在慕尼黑地方法院的裁决中遭到质疑,但最终在德国联邦最高法院的裁决中获得了支持,说明权力化趋势不应动摇契约性权利这一基础。
(2)体育自治权应关注个体权利的实现。体育自治权是典型的集体权利,与个人权利具有发生冲突的必然性。比如:近期频发的运动队(员)赞助合同冲突问题。职业联盟对赞助商的选择往往基于全体成员以及联盟自身的考虑,但可能与某些个体运动员的利益产生冲突,尤其是一些商业价值较大的运动员。在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易建联球鞋”风波中,易建联以脚部不适为由,比赛中途更换球鞋,被认定违反联赛规则,处以禁赛和罚款的处罚[16]。无独有偶,林丹、孙杨等著名运动员的代言合同,也都与相应的国家队集体代言品牌协议产生冲突。在体育商业化背景下,个体权利与体育自治权的冲突更加突出,也更需要体育自治权做出相应的调适,通过完善规则,考量个案,既维护自治体系,又关注个体权利的实现,充分体现公平,实现其“更好地管理体育”的初衷。体育自治权与个体权利同处一个利益链条,不管是权力间的关系,还是权利间的关系,亦或是权利与权力的关系,本质上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利益的博弈。国际体育自治秩序的形成是以权利过渡为纽带,依赖于体育参与者这一数量庞大的利益主体的团结一致。体育自治权与体育参与者的个人权利,正是在追求共同利益最大化这一理念上得以协调的。
总之,体育自治权既区别于公共权力,又区别于一般的团体自治权和其他个人权利,在利与力、公益与共益、集体与个体等差异的共同作用下,形成了一套颇具特色的权利发展模式。在价值追求上,其权利来源于成员的让与,故而追求成员的共益。同时,体育自治权又依附于促进人类身心健康的体育活动而存在,因而又追求人类体育发展的公益。共益与公益同处于体育自治权所追求的同一价值链上,共益是基础,公益是最终目标。正因为如此,即使体育自治权出现了“权力化”趋势,仍被广泛接纳,并发展良好。在体育自治权行使方式上,体现为成熟彻底的私人自主治理模式。这一模式得以形成的现实基础是内部认可和外部尊重,而以组织自治、规则自治以及争端解决自治为核心的稳固的“三角架构”则是其制度保障。基于此,展望体育自治权的发展与完善:一方面,应在自治作用下与公共权力继续保持分离态势,依托“三角架构”,借助体育商业化、政治化和社会化的发展土壤,固化独立自主的权利行使方式;另一方面,应探索“权力化”发展带来的权利冲突、价值偏差等问题的解决之道,依托体育自治权的“权利”属性,以之为导向,完善国际体育自治体系。
3 权利导向下的国际体育自治
现任国际奥委会主席托马斯·巴赫指出:体育改变世界,但并非凭借一己之力[17]。毋庸置疑,在国内和国际层面,体育的价值都出现了多元化趋势。“良好的治理”是利益权衡的需要,也是体育发展的需要。厘清属性,分析发展模式,进而确立完善国际体育自治的导向,实现国际体育的良好的自主治理。
3.1权利导向:引导而非限制“善治”中的“治”包括两重含义:一是指一种治理的方式和模式;二是指一种秩序、状态、结果[18]。概括地说,其就是使社会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19]。体育本身就具有公益性,体育自治权在产生之初就被赋予维护良好的世界体育发展秩序的使命。不仅为参与成员的共同利益服务,而且追求全人类的身心健康,这是公共利益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所以,体育自治权利的最终目标与良好治理的追求在价值上具有一定的同质性。从权利属性出发,“良好的治理”关键在于以权利为导向,进行体育自治路径的优化和制度的变革以及体系的完善。
具体而言,权利导向包括2个方面的内容:一方面,体育自治权的权利属性必须被充分认识,同时该团体权利的行使应该服务于自愿让渡的私人权利,而不能反过来凭借团体权利的力量聚合,侵蚀处于弱势的私人权利。正如体育的商业化、政治化及社会化的发展不可逆转一样,体育自治权利的“权力化”趋势不可避免也无法改变,而且还有可能进一步增强。所以,应该强调体育自治权的内在权利属性,以此为基础,追求良好的国际体育自主治理。另一方面,在进行制度改革与优化时,应该适用对权利而非权力的约束规则,即应该是引导性的而不是限制性的。具体包括对权利行使方式的优化、对权利行使过程的引导、对权利行使结果的监督,以实现权利行使效益的最大化。
3.2自下而上的内部调适遵循“由下而上”的原则进行内部调适,优化权利行使方式,是从体育自治权的权利行使主体的角度,追求成效良好的国际体育自治的重要方式。社会契约理论下的权力的形成是“由下而上”的,但权力的行使是凭借强制力和暴力机关“自上而下”的。相比较而言,私人契约理论下的国际体育自治权作为一项团体权利,其产生和行使应遵循“由下而上”的原则。
(1)通过丰富权利行使主体增强权利行使质效。目前体育自治权行使主体主要有两大类:一是国际体育组织,主要包括国际奥委会、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国际体育仲裁院等;二是国内体育组织,如国家奥委会、国家单项体育协会、国家体育仲裁协会等。权利行使主体已经实现了从个体到集体的发展变化。在权利行使方式方面,各体育组织都在章程中规定了民主化原则,设立职能机关,分别行使规则性权利、组织性权利以及争端解决权利,以形成分工明确、相互制衡的机制。随着“自治权利”的膨胀,体育管理层权力不断膨胀后,出现了脱离体育参与者的倾向,导致体育自治权利的行使偏离轨道,发生了腐败、渎职等不当行为。过于集中的权利行使方式削减了行使效果,修正的要义在于“私人自治并非个人自治”。所以,可以考虑管理机关权利的下放,效率价值的实现前提应该是公正价值,集体权利较之个人权利最大的特点在于团体性,这一特点应贯穿权利行使的始终。
(2)对争端解决性权利这一出现“权力化”趋势的权利,应该适当采纳司法权的行使方式。在程序设置上,除了当前的正式裁决程序、上诉程序之外,还可以考虑增设其他申诉程序,通过丰富争端当事人的参与形式促实体正义的良好实现。在规则适用上强调可适用规则的多样性,在自治规则优先适用规则之下,考虑一般法律原则的替代适用和国内法的有条件适用,以弥补自治规则的缺陷[20]。在裁决过程中,要充分考虑体育事务的特殊性,但不能忽视当前国际体育的政治化、商业化及社会化发展趋势,在权益保护和利益分配方面应适当倾向于弱势方,尤其是运动员的基本权益保护。
3.3外部干预的适当引导引入适当的外部干预机制,引导权利的行使过程,监督权利的行使结果。这是从体育自主治理主体之外的其他主体的角度追求成效良好的国际体育自治,是一种外部引导。体育是全人类的事业,参与主体在国籍、年龄、职业甚至生理等各方面都具有广泛性,所以体育自主治理主体之外的其他主体有责任对国际体育自治权的权利行使加以引导和监督,以实现良好的治理。
(1)在规则性权利方面,强调立法权和司法权的引导。必须明确一点:自治规则不得剥夺法院对这些规则进行解释的权力[21]。通过保障立法机关或司法机关的规则解释权,一方面尊重体育规则的特殊性,另一方面在权益保护、制定技术以及价值取向方面引导体育规则更具公正性和规范性。此外,法院对规则的解释权应包括技术性规则和非技术性规则等各类体育规则。技术性规则是国际体育规则中的基础性规则,对运动员的影响最大,所以不应该以特殊性为由反对外部机关的解释权。非技术性规则以管理规则为主,对这类规则的解释会间接引导国际体育管理秩序的合理性。
(2)在组织性权利方面,强调行政权和司法权的引导。体育组织作为一种社团法人,其成立和解除都需要经过特定的行政程序,行政权应该在准入、发展以及退出等方面进行引导和监督。这里还涉及“体育行政权”和“体育自治权”的冲突与协调。从属性上来说,这是权力和权利的冲突在体育领域的反映,应该遵循“权利本位”的原则进行协调。体育行政权主要在宏观层面协调国内体育事业的全面发展,而体育自治权则是在微观层面促进体育运动的蓬勃发展,在可能出现的交叉领域,例如赛事的开展上,体育行政权应该发挥引导作用,让体育的归于体育,违反公共秩序时再强势介入。在组织性权利行使的监督上,行政权侧重于对体育组织及其管理人员“体育不当行为”的监督、惩戒及纠正,而司法权则是对“体育违法行为”的矫正。
(3)在争端解决性权利方面,由于这一权利的“权力化”趋势最为明显,应该通过构建完善的国际体育司法救济机制以解决当前国际体育争端自治解决体系中存在的显失公正、违反公共秩序等问题。事实上,在坚持“审慎干预主义”原则的前提下,效力在上位司法救济体系能够反促国际体育争端自治解决体系的发展。
可见,体育自治权的内在权利属性决定了国际体育良好的自主治理应该以内部调适为重点,而外在特点上的“权力化”趋势又使得能够实现有效监督和制约的外部干预成为必要。而且在私人自治领域,适当的公共权力介入和良好的外部监督体系可以倒逼自治体系的内部改革,增强内部自制力,以消解“权力化”趋势下自治能力增强后带来的权利滥用风险,实现国际体育的良好自主治理成效。
4 结束语
体育之所以能形成一个完善的私人自治体系,并不间断地发展到今天,源自于它在古代和现代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和不可替代性。利物浦足球俱乐部的经理比尔·尚克利曾言:足球不光是关于生与死的事情,它远比生与死更重要。尽管如今的体育包含了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丰富内涵,但在健康、热情、平等、和平、公正等这些最初被寄予的理念上,仍然是体育所能体现的人类美好的共同追求,甚至可以说是人类的自然权利。同样,根据私人契约形成的体育自治权发展程度的提高,不应该偏离“权利属性”这个既定轨道。当前,公域治理已经由单纯的国家垄断转变为国家与社会合作治理[22],但社会治理本质上还是一种公共治理,是权力导向下的自上而下的模式。国际体育良好的自主治理的实现,应该是权利导向的。在权力和权利的关系上,以权利为本位,发挥权力的引导和监督作用,实现权利行使的效益最大化;在团体权利和个人权利的关系上,以私人契约理论为基础,恪守团体权利的最终目标以促进个人权利的更好实现。
[1] HENK-ERIK M.Keeping private governance private:Is FIFA blackmailing national governments?[EB/OL].[2017-03-10].https://dspace.lboro.ac.uk/2134/12635
[2] 卢梭.社会契约论[M].科尔,译.上海:上海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0:1-2
[3] 邓正来.社会秩序规则二元观——哈耶克法律理论的研究[J].北大法律评论,1999,2(2):395-445
[4] 张文闻,吴义华.国际体育组织自治权的法理分析[J].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16,50(8):44-48
[5] PANAGIOTOPOULOS D.International sports rule’s implementation-decisions′ executability:The Bliamou case[J].Marquette Sports Law Review,2004,15(1):1-12
[6] 彭昕.我国体育自治建构的法理诠释[J].西安体育学院学报,2013,30(6):650-655
[7] 李智.体育争端解决法律与仲裁实务[M].北京:对外经贸大学出版社,2012:12
[8] 胡杰.论权力的权利性[J].法制与社会发展,2013(2):83-89
[9] 向会英.体育自治与国家法治的互动——兼评Pechstein案和FIFA受贿案对体育自治的影响[J].上海体育学院学报,2016,40(4):42-49
[10] GUILLERMO J.Fixing FIFA:The experience of the independent governance committee[J].Southwester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2014,21:165-174
[11] 漆多俊.论权力[J].法学研究,2001(1):18-32
[12] 李海平.论作为宪法权利的团体自治权[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1,51(6):141-146
[13] 汪莉.论行业协会自治权的权源及其性质[J].学术界,2010(7):75-82
[14] 苏力.法治及其本土资源[M].3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11
[15] 张春良.强制性体育仲裁协议的合法性论证——CAS仲裁条款的效力考察兼及对中国的启示[J].体育与科学,2011,31(1):19-28
[16] 搜狐体育.广东:接受处罚尽力解决阿联今后所穿球鞋问题[EB/OL].[2016-11-03].http://sports.sohu.com/20161103/n472209420.shtml
[17] Historic Milestone:United nations recognises autonomy of sport[EB/OL].[2017-03-10].http://www.olympic.prg/news/historic-milestone-united-nations-recognises-autonomy-of-sport
[18] 王利明.法治:良法与善治[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5(2):114-121
[19] 俞可平.全球化:全球治理[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10
[20] 乔一涓,李智.国际体育争端解决中的规则适用[J].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15,49(10):34-39
[21] 贝洛夫,克尔,德米特里.体育法[M].郭树理,译.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32
[22] 徐靖.论法律视域下社会公权力的内涵、构成及价值[J].中国法学,2014(1):79-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