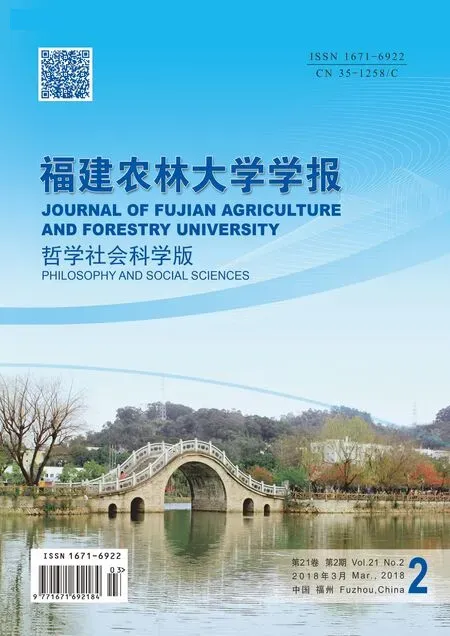村民公私观念与乡村社会治理
允春喜, 李 鹏
(1.中国海洋大学法政学院,山东 青岛 266100; 2.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江苏 南京 210023)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改革总目标,而国家治理的基础毫无疑问在基层。农村“乡土社会”的性质多年来并未发生根本改变,“熟人规则”“差序格局”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乡村社会治理,现代制度和乡土秩序之间的张力依然存在。公私观念直接“关系着社会结构的整合,关系着国家、社会、个人之间的价值取向和行为准则,关系着社会意识形态的规范和社会道德与价值体系的核心等重大问题”[1],规范着地方社会秩序,深刻地影响着社会治理的进程。
一、传统与现代交织下村民公私观念的复杂呈现
(一)公私范围的伸缩性
作为一对相反相成、相互依赖的概念,如果“公”和“私”其中一方范围发生变化,另一方也会相应地进行改变。人都有逐利和自我保全的私性,在处理个人与群体、社会以及国家之间的关系时,其行为准则和价值取向往往都会先“私”而后“公”。村民往往遵循自我主义原则,首先明确“私”的范围,以此来扩展和界定“公”的空间。在面临具体的社会问题时,村民往往会顾虑关系、利益等伦理义务要求,从而使得公与私关系呈现出“由近以及远,更引远而入近,泯忘彼此,尚何有于界划”的伸缩性表现[2],这种不忘彼此的义务联系也使得远近之间难以彻底定分,公与私之间成了辩证互通的存在[3]。在不同的话语情境下,家庭、家族、村庄等都可以成为“私”的范围,公私范围呈现出明显的伸缩性。
公私边界的伸缩性是伦理本位组织下的关系型社会中人际关系的重要显现。伦理本位消融了个人与团体间的界限,在不同情境中帮助村民确定相应的公私范围。乡土社会中传统家庭和家族的地位及其所要求的伦理义务对于村民的公私观念、村庄的内在运行秩序的影响是深刻的。同时,乡土社会中各种伦理义务的要求“始于家庭,而不止于家庭”[2],诸如师生之情、兄弟义气、同乡之谊、同窗好友等伦理关系也在帮助村民界定着“自己人”,而没有这些关系的他者集合便相应地构成了“公”的范围。由此可见,伸缩性显著的公私范围呈现出明显的内向化趋势,即私的逻辑主导作用明显。
(二)公私关系的层次性
费孝通认为,“差序格局”指的是私人与公共之间的关系,像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每个人以其所认定的“自己人”圈层为出发点逐渐向外围过渡,整体来看是一个推己及人、层次性明显的过程,“愈推愈远,也越推愈薄”[4]。中国古代是“伦理本位”的人伦社会,人的社会关系是亲情关系的放大,因此,家庭与个人联系的血缘伦理在不同层次中都最为紧密,在外层可看作命运共同体,在深层则是一个利益共同体。其他基于地缘、业缘、趣缘等的伦理关系也是一样,“自己人”的范围一旦确定,依照这种多样的伦理关系便可分出远近亲疏,关系之间的层次性较为明显。可见,“私”的范围首先界定在家庭、家族本位,再向外扩展才有村庄、国家、天下等“公”的概念,在传统社会中受到儒学熏陶的村民便践行着“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先后逻辑;其他伦理义务联系下的“自己人”模式则要求在推己及人的过程中能够先己后人。
“公私两个领域是具有高度相对性而不断开展的多层次的同心圆……个人处于这种多层次的同心圆的张开的过程之中,常面临多重身份与责任相互冲突的问题”[5]。这种公私关系的层次性是以伦理本位为原则同时呈现出明显的差序性。这种先后逻辑往往容易使村民“有家族观念而无国族观念”,在基层治理的过程中,这种观念依旧是家与村民联系的核心,村民往往受这种观念的影响,遵循先家后国的层次取向。在这两者作用力下的村民面临着“舍国为家”还是“舍家为国”的抉择困惑,使得基层社会治理存在潜在的张力。
(三)公私价值和实践的不对称性
中国古代的“公私”从春秋战国时期就逐渐开始具有价值判断属性,提倡“大公无私”“崇公抑私”的价值要求。沟口雄三在比较中日公私概念时指出“道义性的有无是突出两者差异的特征之一”,中国“包含着公正对偏邪的所谓正与不正的道义性”,而在日本则是“显露与隐藏‘公开’与‘私下’相对于‘公事’‘官方’身份的私事、私人之意”[6]。中国式公私观念的价值追求是“公”受到提倡和推崇,而相对的“私”一直受到批判和贬抑。但这种价值观念并未正确地处理“公”与“私”在实践中的关系,私的逻辑往往在现实中主导着民众的社会实践,人伦关系压抑了社会公德及公共利益,从而出现公私相悖的矛盾境况。这是由于传统公私观念对于“私”的绝对否定,使得无“公”可言,从而导致“公私两无”的情况。廉如鉴则从伦理本位组织的社会方式入手,指出崇公抑私的含义是“克己复礼”而非“发扬公德”,这种现实悖论与传统社会“高度耦合”,因此,这种矛盾本质上是一个“伪悖论”[7]。
公私观念在价值追求和行动实践中的不对称性,本质上还是由传统公私观念的自我主义和伦理本位原则决定的。在自我主义确定下的私域内,以伦理本位加以限制,防止私欲膨胀;在向外扩展的公域内,自我主义加以要求,防止破坏人际之间伦理关系。当这种道德诉求和现实生活对利益领域划分之间出现张力,自我主义的行为逻辑与集体社会对于公的价值推崇之间的冲突变得不可化解,从而使得现代基层治理过程滋生选择困惑。
二、村民公私观念对现代基层治理的影响
公私观念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村民在日常生活中对于公私关系的判断,同时还决定了其行动理念和逻辑,进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现代基层治理的绩效。
(一)自我主义和个人主义之间的难以取舍
传统乡土社会中村民的自我主义,是以乡土社会较少的流动性和社会资源有限为基础的观念[8],村民的“自我”取向逻辑出发点存在于伦理性义务范围内。伦理性义务要求村民遵守村庄秩序下的家规、习俗等伦理道德,这使得相互提携、互帮互助在村民中发展到了一个很高的程度[9]。这种基于血缘、地缘、业缘、趣缘的原则取向,可以保证村民在“自己人”模式下的伦理关系更加和睦融洽,但也在基层治理过程中产生了很多不合理的现象:在分配公共资源时,往往“肥水不流外人田”;处理社会争端纠纷时,往往是“自己人好办事”;面对公共利益的个人义务要求时,往往“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等。
与自我主义不同,个人主义是将自己利益作为出发点,理性认识他人与自己的关系,从而做出最有利于自己的判断并采取符合自己利益的行动。个人主义更加重视和强调的是人与人之间生而平等,以及在法律保护下个人权利神圣不可侵犯。在乡村,家庭、家族以及乡村内部,合理的个人主义倾向是符合人本理念的,体现了对个人权利的重视,村民不再受限于家族村规的制约,充分保障村民自身的权利不被传统的宗法秩序压抑。但是,过分强调权利而否定义务的个人主义往往会超越传统道德的界限,与伦理本位背道而驰,村民片面地追求私欲而忽视了传统乡村生活中互帮互助的义务关系,甚至造成村民之间“自扫门前雪”的现状,“原子式村庄”逐渐显现,村规乡约等义务性要求的约束力变弱。面临着二元价值选择的村民,在认识人际关系和处理日常事务时变得难以取舍,自我主义和个人主义之间的取舍与创造性转化,在不同层面上影响和制约着现代基层的治理。
(二)礼治秩序与法治精神之间的两难抉择
乡土社会得以稳定运行在于遵循一个“礼”字,从家庭内部“父父、子子”的尊卑观念到村庄内的乡约村规无不合乎“礼”的规范。“人无礼不立,事无礼不成”成为村庄内部的行为准则,这种礼治秩序塑造着村民的公私观念和行为取向。家庭中的等级秩序将个人利益居于礼之下,“礼之用,和为贵”指导着村民在人际交往中注重相互合作,按照礼的规矩办事,方能和气生财、皆大欢喜。而最简单的“礼”的外化表现为村民间的“关系”“面子”“人情”等,礼治秩序下的乡村成为一个情理型场域。村民遵循着礼治秩序,但正所谓“来而不往非礼也”,这就使得公共资源常常被有意无意地用于私人交换,使得中国人往往在情感性关系中没有明显的“公”“私”界限[10]。游移不定的公私界限被代表着“关系”“面子”“人情”的“报”与“回报”的交易活动所牵制,这种社会交易可以被视作“人情法则”下的活动[11],而这种所谓的“人情法则”在很大程度上便是情理型的熟人社会中强调礼治逻辑的产物。
现代基层治理越来越强调法治精神,明确公民的权利与义务关系。礼治秩序则以人情来进行价值判断和行为选择,这就使得法律下乡往往只是“停在嘴上、写在纸上、贴在墙上”而不能深入村民的价值观念和行为选择中。这并不是说,法律制度本身不适应乡土社会,而是传统礼治秩序和现代法治精神之间存在矛盾。在礼治秩序下,村民向来信任熟人要胜过信任制度,缺乏追求程序性价值的意识,不是寻求法律保护,而是以“打点关系,疏通门路”为主,从而出现“公事私办”或“私事公办”的奇怪现象。由于“村民的收入太低”导致“获得不了高昂的法律救济”[12],这可能是一方面的限制性因素;另一方面,村民惯于用“关系”解决社会矛盾的传统逻辑也发挥着深层的影响。村民在礼治秩序与法治精神之间的抉择成为现代基层社会治理必须正视的社会问题。
(三)乡治传统与现代自治的相互抑制
梁启超曾经指出,中西方在社会组织方式上存在“欧洲国家,积市而成;中国国家,积乡而成”的不同,使得“中国有乡自治而无市自治”[13]。在“皇权不下县”模式下,乡里秩序主要依靠乡绅、贤老的教化为主,同时遵守着家长制的家族法规。这样的乡村自治模式遵循着乡规民约、礼治传统,使得传统社会“讼狱极少”“与地方官府全无交涉”,村民遵照诸如乡规民约以及乡绅贤老的同意权力来行事,深处庙堂之上的皇帝与普天之下的村民达成了“无为政治”的基本政治共识[4]。村民对待个人、家庭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往往走向极端,儒家要求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便有了广泛的共识,这也使得村民往往更多扮演的是“顺民”角色,对于社会公共事务的参与相对不足,缺乏必要的政治组织能力,在某种意义上被描述为“一盘散沙”。
现代基层治理要求实现社会治理现代化转型,基层社会自治是其中的应有之义[14]。基层自治不同于传统的乡村自治,要逐渐重视村级在治理中的重要性。乡村治理在历经传统乡治到人民公社运动再到乡政村治阶段,越来越要求村民具备国家意识、集体意识,即“公”的意识。随着现代基层自治制度的实施和完善,村民逐渐成为“当家人”,个人概念和个人权利开始自觉。在实现自我治理的同时遵守公共规范,明确公权与私权、公域与私域,实现乡治传统与现代自治的创造性结合,这对于村民政治能力和基本素质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挑战。
三、现代乡村治理进程中公私观念的扬弃
传统是对以往生活经验的总结,而现代性因素的冲击又是全面深刻的。面对传统经验与现代实际的双重压力,应该摒弃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的解决方式。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传统并不完全是静态的,它必然要加以再创造[15],这种再创造并不是对现代性简单“超越”的片面追求,而应当是在尊重传统乡土社会特色的基础上实现现代化。
(一)在权利和义务关系下集体之公与个人之私的消解
乡村公私观念呈现出伦理本位、自我主义与个人主义并存,乡治礼治传统与自治法治要求并举的时代特征。立足于现代基层自治的实践过程,发掘并应用“现代传统”是有价值的,这样在公私观念理解和现代基层治理实践的互动中,现代基层治理过程才会合情合理[16]。传统与现代两种力量的内在张力在重塑着传统的公私观念,必须致力于实现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在社会治理进程中的消解,而这有赖于对村民权利与义务之间关系的重构。
公私观念推崇大公无私的价值诉求,强调个人对他人的伦理性的义务,村民出于这种伦理关系而往往自觉地忽略个人权利;而一旦超出伦理界限,扩大到“公”的范围,个人则往往更看重自己的权利。这是因为不流动的乡土社会人与人之间是相熟的,而在充满流动性的陌生人之间,便忽视了自己对他人的义务。乡村社会的个人既不是完全独立于社会的存在者,也并非是在群体面前毫无个性的存在者;在家庭作为“私”的基本单位中,村民既要遵守传统的义务本位,达到相互提携、帮助的要求,又应当尊重个人的基本权利,不能因此而忽略或压抑每个人的个性与诉求。而对于其他地缘、业缘、趣缘的“自己人”也是如此,彼此之间和睦相处并不意味着只从“经营关系”中考量。村民应该在创造性继承集体之公和创新性超越个人之私的基础上,实现权利与义务的对等一致,从而有助于实现基层治理中“发乎情、取乎法”的良性互动。
(二)理性基础上“公私”伦理与法律制度的互动
法治是现代社会行动的统一底线和乡村治理的保障,但法治解决的仅仅是“形式合理性”与“程序合法性”的问题。在公私观念影响下,“家庭成了所有道德行为的出发点”[9],村民往往会优先考虑家庭、家族的利益。因此,重视家庭在村庄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地位,有助于理解村民公私观念和行为逻辑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从而抓住乡村社会治理的核心。从某种意义上说,“乡村的、基层的、下面的治理难题只能用一种非司法甚至反司法的方式来解决”[17]。要在乡村社会治理中充分重视“合情”问题。因此,乡村治理现代化应该充分发掘和弘扬不违背现代法治精神的公私伦理资源,将理性的法治观念与情理的道德观念有机结合起来,在法治精神的前提下弘扬公私伦理所蕴含的公共性和内敛性。
因此,现代乡村治理要充分发挥家庭、家族在社会教化和合作方面的作用,将现代意义上的法律意识、组织意识以及公民意识等传递给下一代。“性相近,习相远”,习以为常的习惯往往从家庭教育中诞生;家族内部要求的相互扶持也是“先家后个人”的义务要求;在组织中将诸如婚丧嫁娶等社会合作的道德义务进行代际传承,进而过渡到涉及公共利益的事务中。这种跨越是有益的,也是非常必要的。同时,在应对家庭、家族利益瓜分公共利益的问题时,应做到充分重视和积极引导,以破除这种“有围墙的城堡”。
(三)公私融合主导下多元主体的情理共治
传统礼治社会往往易使基层治理过程陷入“一盘散沙”的人情困境,村民在社会冲突中往往倾向于谋求关系来解决问题,在非制度性参与下往往容易有失偏颇。我国传统社会中的村民讲求“情面”“关系”,这是维护乡村秩序的合情合理的规范。乡治礼治秩序下的村民讲求“情面”“关系”,这是乡土社会中合情合理的规范。现代基层社会治理仍是自治和法治精神的结合,既要尊重乡土之“私”的传统,又要符合时代之“公”的精神,才能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实现乡村振兴的和谐发展。中国的法律调解制度便具有传统乡土社会中乡治礼治的影子,过去的“评理”转身成为现代语境下的“调解”,不同于“西化论”下的法律制度,也不同于“本土化”下的传统法制,在处于变迁中的乡土社会,仍能够发挥其积极的作用[18]。
因此,基层社会治理应该适应乡土性的要求,使代表“公”和“私”的多元主体都能够在基层治理的大背景下实现融合,在完善乡镇政府、村委会等治理主体的基础上,增强现代村民的公民意识,同时以乡规民约等文化传统丰富乡村社会生活,并积极发挥新乡贤在乡村治理中的积极作用。在传统乡治与现代自治相结合的基础上,乡土社会的现代化变迁才会顺利进行。湖北恩施州2013年开始实施“优选村医村教进村‘两委’班子”,并在全州80多个乡(镇)开展[19];广东清远、河北辛集等地区成立村民理事会,并邀请德高望重、具有话语权的“乡贤”来参与治理……这些都是突出地方特色的做法,在认识到传统乡绅自治文化的合理内核下,实现现代社会自治的目标,如此的“现代传统”具有很强的“样本”意义。
公私观念为乡村社会治理提供了政治文化视角创新和再造的路径,村民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角色转型以及社会多元主体的共同治理,现代以理性为内核的制度架构和传统情理型社会的现代性转化,家国同构下的现代中国对于家国关系的再审视等问题,都可以从村民公私观念的继承与超越中重新获得解释,而基层社会治理与村民公私观念的互动也会合理有效展开并做到推陈出新。
[参考文献]
[1]刘泽华.春秋战国的“立公灭私”观念与社会整合(上)[J].南开学报,2003(4):63-72.
[2]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72-73.
[3]康建伟.公私之辩:从梁启超到梁漱溟[J].学术交流,2011(5):21-25.
[4]费孝通.乡土中国[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8:26,56.
[5]黄俊杰.公私领域新探:东亚与西方观点之比较[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88.
[6]沟口雄三.中国公私概念的发展[J].国外社会科学,1998(1):59-70.
[7]廉如鉴.“崇公抑私”与“缺乏公德”——中国人行为文化的一个悖论[J].江苏社会科学,2015(2):92-98.
[8]卜长莉.“差序格局”的理论诠释及现代内涵[J].社会学研究,2003(1):21-28.
[9]林语堂.中国人[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0:185.
[10]沈毅.黄光国的“人情与面子”模型及相关挑战[C]//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社会学研究所.中国社会心理学评论(第二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255-277.
[11]黄光国.人情与面子:中国人的权力游戏[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1-44.
[12]贺雪峰.公私观念与农民行动的逻辑[J].广东社会科学,2006(1):153-158.
[13]梁启超.梁启超论中国文化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99.
[14]周庆智.基层社会自治与现代治理现代转型[J].政治学研究,2016(4):70-80.
[15]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33.
[16]黄宗智.经验与理论[M].北京:中国人民出版社,2007:464.
[17]赵晓力.基层司法的反司法理论——评苏力《送法下乡》[J].社会学研究,2005(2):218-225.
[18]黄宗智.认识中国——走向从实践出发的社会科学[J].中国社会科学,2005(1):83-93.
[19]湖北省恩施州委州政府.优选村医村教进村”两委“班子提升农村基层组织服务水平和治理能力[N].中国组织人事报,2014-08-2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