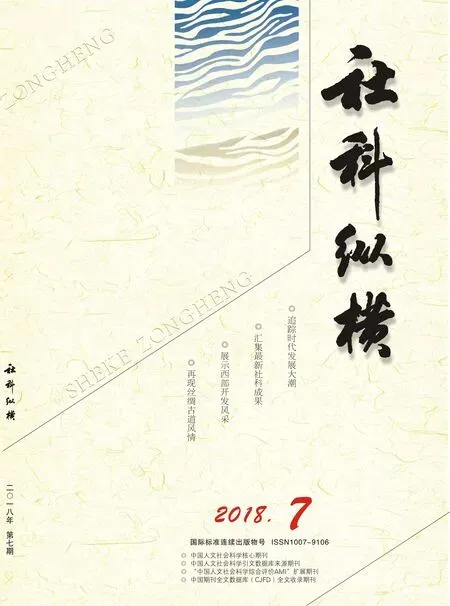论近代俄国外交决策机制的演变与特点
于宁宁 崔健伟 常 乐
(齐齐哈尔大学 黑龙江 齐齐哈尔 161006)
外交决策机制是指“以担负对外决策职能的国家政治机构为核心、在政治系统其他重要因素的影响下,按照相应组织结构运作从而将来自外部环境的要求与支持转化为一个国家对外政策的组织体系。”[1](P69)近代俄国外交决策机制的建立与俄国政体和内外形势有着密切的联系,无论是外交决策机制静态结构的构建,还是外交决策机制的动态运行,都呈现出典型的俄国属性和浓重的俄国特征。
一、近代俄国外交建制的演变
彼得大帝的统治开启了俄国历史的一个新时代。彼得一世改革前,俄国贵族影响力极强,王权正处于“等级代表君主制”向“绝对君主制”的过渡时期,贵族间经常发生内讧和战乱,政治机构中的衙门制度弊端明显。产生于15世纪末16世纪初、形成于16世纪中叶、于17世纪走向繁盛的衙门制度,是俄国16至17世纪实行的重要政治体制,在俄国中央集权化过程中起过重要作用。但至17世纪末,责权不分、分工杂乱、缺失监督、机构臃肿,成了衙门制度的象征,流弊严重,办事效率低,衙门制度中没有单独的纯粹的外事机构存在。
彼得一世亲政之后,锐意改革。1700年,在使臣衙门之外成立了使臣公署,负责对外事务,而前朝传下来的使臣衙门则管理国内的、地区之间以及经济方面的事务,直至1717年底被取消。使臣公署是近代俄国第一个纯粹的外事部门,被视为俄国外交部门的雏形。不过,由于处于北方大战之时,使臣公署的外交职能还不够稳定,内部外交机构的设置也不够完善,其功能上只是一个过渡性的机构。
1717年,彼得一世裁撤了使臣衙门和使臣公署,设立了各种使臣委员会,其中,外交、陆军、海军三个委员会最受彼得一世的重视,称为“一类”委员会。1719年起,使臣委员会改名为外事局。外事局的领导建制由局长、副局长、理事会构成。外事局下设彼得堡分局办公厅,由秘书、办事员、公证员组成。办公厅下设三个比较稳定的司局级单位:1.一司——对外关系司,下设四个处:一处负责处理北方战争前后盟国关系事项;二处负责处理北方战争前后敌国有关事项;三处负责处理北方战争战时中立国及其它国家关系有关事项;四处负责外交文件、翻译及人员组织等外交活动的技术问题。2.二司——财务管理司,主管行政和财务,不下设处。3.外事局莫斯科管理处,是外事局在莫斯科的代表和分支机构,至1781年裁撤。从机构设置和职能配置看,外事局主要还是为彼得一世的北方战争服务的,有较强的针对性和临时性。从功能上看,外事局仅是辅助沙皇处理对外事务的机构,有别于现代意义上的外交部。
亚历山大一世执政时期,近代俄国外交建制有了较大的发展。1802年9月,亚历山大一世开始推行部门制的方法管理国家,外交部位列中央八大部之中,负责遵循沙皇的对外政策方针施行俄国的外交。原有的外事局暂时得以保留,由统管外交部的外交大臣统一领导。在这种外交的双元系统中,外事局实际上主要负责国外侨民和国内外国人以及外交部的行政管理等事务。1811年,亚历山大一世在国内推行部司制管理体系,但外交部对外事局的改组却运作缓慢。尼古拉一世执政时期,沙皇于1832年颁布《关于成立外交部》谕旨,将外事局变为外交部下属机构,正式撤消了外事局。外交部下设立司局级管理体制,1819年设立特别亚洲司,主管外交部的亚洲事务,对外关系司是外交部最为重要的负责对外政治问题的部门,其下设立大臣办公厅、主管与国内各部协调的国内工作司、负责国内外干部配备的经营管理司等五个处级单位。
亚历山大二世时,随着俄国农奴制改革的推进,俄国中央管理体制也相应的有所调整。1861年,成立了由沙皇主持的旨在协调各部门关系的大臣会议。哥尔查科夫担任外交大臣后,根据命令对外交部进行了机构调整,成立了大臣主持的部委会,部长办公厅,三个业务司(亚洲司、国内关系司、干部及管理司)和地区司,两个部属档案馆(圣彼得堡中央档案馆、莫斯科中央档案馆)。亚历山大三世时期,外交部没有什么改进,只是随着俄国的对外扩张,驻外机构不断增加。
至此,近代俄国外交部自19世纪初成立以来,经过尼古拉一世和亚历山大二世时期的微小调整,直到帝国结束没有太大的变化。
二、近代俄国外交决策体系
根据近代俄国基本法,俄国外交政策的决策及运作是由一个复杂的外交决策体系完成的。这个体系的构建,以沙皇个人为中心,以绝对集权为主要特征。在遇到重大外交问题时,由沙皇、外交部、各部委及高官发起提议,由外交部和有关部委起草议案,由专门会议、国务会议、大臣会议商讨议案,最终由沙皇决策,由中央参政院一司颁布。
第一,沙皇掌握立法权和执法权,是俄国精神上的最高代表,掌握近代俄国外交决策权。沙皇可决定国家对外政策的总体方针和策略,握有宣战、签订、批准条约的决定权。此外,沙皇还控制着日常俄国对外交涉大权,可通过外交部及驻外外交机构呈送的专门报告了解俄国外交运作情况,并通过批示反映沙皇的意见。批示给驻外大使的指令、决定外交部的机构问题、驻外领事、军事、财政部门代表的任免均由沙皇决定。虽然在对外签约时,沙皇需要大臣的“陪签”。但由于”陪签“不是硬性规定,沙皇完全可以绕过外交大臣,指定其他顺从自己的大臣陪签。因此,沙皇处于近代俄国外交决策的最高层。
第二,国家最高政权机关,主要指国务会议、大臣会议、中央参政院,处于近代俄国外交决策体系中的第二层。以俄国基本法内容为准,国务会议是俄国立法机构,有权审理和裁定所有法律问题,包括俄国对外关系有关问题。但在实践中,国务会议的职权受到沙皇的限制,其对外意见和决定常常由沙皇来判定。因此,国务会议在近代俄国外交决策的实践中已经成为赞同大臣根据沙皇旨意形成的法律条文的机器。大臣会议,是近代俄国最高的执行机关。就其法定职权范围而言,与外交决策没有直接关系。
第三,中央涉外机关,主要指外交部、陆军部、海军部、财政部、内务部,处于近代俄国外交决策体系的第三层。这些部门在国外都派驻自己的常驻代表。其中,外交部是俄国外交政策决策的关键职能部门,主要负责处理俄国与其它国家的政治关系、为俄国海外贸易提供保护、为俄国侨民及其国外事业提供法律保护、为外国人在俄国实现其法律要求提供帮助。外交部没有专门的政策研究室,对外决策的有关职能主要由办公厅和亚洲司代行。办公厅是外交部的指挥部门,办公厅主任、帮办大臣(副大臣)以及外交顾问是外交大臣的咨议核心。办公厅通过汇总整理各部门的意见建议形成初步材料,然后交由上述核心研究形成最后的文件。亚洲司既是地区司,也是职能司。作为地区司,它的工作主要针对澳大利亚、北美太平洋地区、北非、巴尔干国家及东地中海地区。作为职能司,它与办公厅一起为外交大臣汇总整理有关材料和提出初步方案。外交部实行外交大臣一长制,形成外交部意见后,上呈沙皇阅批或提交其它部门商讨,对外政策的决策权只掌握在沙皇手中。
第四,边境省份的外交部分设机构。这是近代俄国外交决策体系中的最末端,作用甚微。
可见,受限于近代俄国绝对的中央集权体制,外交部仅仅是一个对沙皇负责、开展具体外交工作的执行部门,实际的俄国外交决策权由沙皇执掌。
三、近代俄国外交决策机制的特点
(一)沙皇个人作用突出
近代俄国外交决策中充斥着浓厚的沙皇个人色彩,甚至是个人情绪。外交决策、外交政策能否成功、外交风格的选择、外交大臣的任免,都取决于沙皇的外交素质、决策才能和行事风格。“俄罗斯一切的事情都要看沙皇是否高兴。外交政策仅凭沙皇的心情好坏,便由自由主义转向保守也是绝对可能的。”[2](P55)俾斯麦就曾抱怨说:“我们同俄国的关系完全要看沙皇亚历山大第三的个人情绪。”[3](P359)近代俄国外交中,彼得大帝果断而灵活的外交、叶卡捷琳娜二世狡诈而富有新意的外交、保罗一世的随性外交、亚历山大一世的神秘主义外交、尼古拉一世生硬而固执的外交、亚历山大二世坚定而多变的外交都证明:沙皇在近代俄国外交决策中起决定性的作用,俄国外交的成败与特点和沙皇的个人能力是密不可分的。
彼得大帝是一个务实的功利主义者,“他在方法与时机的选择上则是实用主义的。他从不迟疑地放弃失败试验,而改用新解决办法。”[4](P26)在组织超级使团出访欧洲诸国时,彼得大帝的最初用意是想建立反对土耳其的同盟完成南下计划,但受限于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造成的大国关系的变化,彼得大帝果断调整外交方向,改南下为北上,将俄国外交的重点由夺取黑海出海口改为夺取波罗的海出海口。“北方战争的结果对于欧洲和俄罗斯的历史命运来说具有巨大的意义。为夺回波罗的海出海口的艰巨而长期的斗争根本地改变了俄罗斯的国际地位。北方战争之前,俄罗斯在欧洲鲜为人知,其历史及影响被认为是微不足道的,把它拉入全欧事业是不可思议的。”[5](P45)北方战争的胜利使俄国从一个内陆国家成为一个可以从海路进入欧洲的强国,标志着近代俄国的崛起。“没有他的领导作动力,俄国也许不可避免地仍要朝它后来的方向走,但不会有这样一种一往无前的势头,而且,就外交事务而言,大概也无法取得这么大的成就。彼得一世的事业,或许最清楚地说明了沙皇在俄国外交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方面是起重要作用的。”[6](P4)
叶卡捷琳娜二世是适应俄国历史需要而出现的强权人物,不但扭转了俄国的困境局势,还极大的提高了俄国的声望,其外交具有强烈的个人色彩。叶卡捷琳娜二世自幼学习德语和法语,嫁到俄国后学习俄语,这种语言上的优势使得她在18世纪后半叶的欧洲外交舞台上不但可以通过与伏尔泰、狄德罗的书信交往打造自己的外交形象,还能比别人更迅速地与普奥君王密谋瓜分波兰。叶卡捷琳娜二世总能利用欧洲国家间的矛盾为俄国的外交决策服务。七年战争后,利用英法矛盾、普奥矛盾的发展,俄国积极倡导联合普鲁士、丹麦、英国构建北方体系反对法国和奥地利。巴伐利亚王位继承战争爆发后,俄国利用普奥矛盾成功入主德意志,不但调停普鲁士和奥地利的矛盾,还充当了普奥矛盾的仲裁者,最终促成《铁申和约》的签订。北美独立战争爆发后,利用英法矛盾,俄国发布《武装中立宣言》保卫中立国权益,并积极联合丹麦、瑞典、普鲁士等国家构建欧洲武装中立同盟,使得战争向有利于美利坚民族发展。在叶卡捷琳娜二世的外交实践中,欧洲大国——波兰、瑞典、土耳其、普鲁士、奥地利、法国——如走马灯似的一会儿成为俄国的交战国,一会儿成为俄国的盟友。对此。马克思曾深刻指出:“俄国经常玩他们的老把戏,唆使欧洲蠢驴们互相反对,一会儿做甲的伙伴,一会儿做乙的伙伴”。[7](P224)可见,叶卡捷琳娜二世正是巧妙的借力于欧洲大国间的矛盾,周旋于敌人与盟友之间,为俄国外交创造了成功的机会。
沙皇尼古拉一世继承了其兄长亚历山大一世在欧洲的辉煌胜利,借助在欧洲所建立的新秩序中俄国近乎欧洲霸主的地位和对于俄国非常有利的国际条件,俄国本应该获取更多的利益。但在克里米亚战前和战争中,尼古拉一世犯了三个错误:在涉及土耳其时,不应抛开法国;对奥地利会支待俄国的判断错误;错误地估计英国会接受他的建议。这些错误估计和判断导致尼古拉一世战略决策上的错误,最终俄国连本带息地输掉此前俄国在南部和黑海几代沙皇多年的积蓄。俄国从辉煌的顶点跌落下来,丧失了其欧洲霸主的地位。恩格斯曾对尼古拉一世有过深刻的评价:“沙皇尼古拉登基。外交界不能希望有比他更好的沙皇了,因为他是个只有排长见识的庸人;在他看来权力的外表高于一切,为了这外表他可以不顾一切。”[8](P38)尼古拉一世生硬而固执的外交使俄国遭受到近代以来最惨痛的失败,沙皇在东方问题中的一厢情愿和缺乏常识使得俄国失去了1814年以来获得的权力和影响力。由此可见,外交成功与否和沙皇的外交决策能力是息息相关的。
(二)秘密外交盛行
政治体制与政治文化对近代国家对外政策决策有着深远的影响,近代俄国是典型的封闭性政治体系,沙皇不仅是国家权力的核心,还是政策决策的轴心,社会大众、传播媒介等其它社会因素被排斥在政治决策过程之外,对外交政策决策的影响有限。“俄国的舆论(在19世纪30年代以前它几乎不存在)对帝国的外交关系和领土扩张的战争的影响比对它国内政策的影响要小得多。在开明专制主义的秘密外交和内阁外交的时代,人民不能够抑制彼得堡变化多端的帝国主义。沙皇政府在外交政策的决策方面行使了甚至比帝国主义时代欧洲其他专制的君主或立宪政策制定者更大的权力。”[9](P53-54)绝对君主专制决定了近代俄国政治体制的封闭性,外交决策中秘密外交较为盛行。
叶卡捷琳娜二世时期的欧洲国际形势对于俄国非常有利。七年战争后,欧洲大陆大国竞争的中心由西欧转向东欧,俄国、普鲁士、奥地利成为欧洲角逐的主角,这为叶卡捷琳娜二世在东欧扩张提供了机会。叶卡捷琳娜二世极度推崇阴谋和秘密外交,在与普鲁士、奥地利密谋瓜分波兰的过程中,秘密外交显露无疑。1764年,俄普在彼得堡签订了旨在反对波兰和土耳其的秘密同盟条约,宣称双方在必要时不惜使用武力,以反对推翻波兰共和国的制度及根本法。恩格斯在评论这一秘密条款时指出:“双方承担了用武力保护波兰现行宪法这个毁灭波兰的最好工具免遭任何改良的义务。这就预先决定了波兰在将来要被瓜分。”[8](P25)1772年8月5日,俄国、普鲁士、奥地利在彼得堡签订条约瓜分波兰,俄国根据条约得到西德维纳河及第涅泊河以东的9.2万平方公里土地,把俄国的西部边界推到了这两条河的东岸。对波兰的第二、三次瓜分是在法国爆发大革命之后,英国及欧洲封建君主联合反法,主要精力集中于西欧的情况下,俄国密谋组织并参与了对波兰的瓜分。1793年1月,在彼得堡,俄国与普鲁士签订了瓜分波兰的秘密协定,俄国获得共计25万平方公里的土地。1794年,针对波兰革命形势,俄国与普鲁士签订“联合行动”的秘密协定,俄普集中优势兵力扼杀波兰起义军,并于1795年联合普鲁士和奥地利达成了瓜分波兰的协定。通过三次瓜分波兰,俄国开始与普鲁士及奥地利有了领土接壤,叶卡捷琳娜二世将俄国西部边界进一步向西推进,奠定了现代俄国西部边界的基本走向。
亚历山大一世时期的俄国外交取得辉煌的成绩,但其成绩的得来与秘密外交不无关系。即位之初,为了调整保罗一世由联英反法到联法反英的急转弯对外政策,亚历山大一世先后与英国签订俄英海上协定、与法国签订《巴黎秘密协定》,以稳定俄国在欧洲的地位。1806年,第四次反法同盟与法国作战中,俄军败退至俄国边境的提尔西特。困境中,亚历山大一世选择与拿破仑谈判,并最终签订了《提尔西特和约》。从性质上看,提尔西特会谈是拿破仑与亚历山大一世的一次分配各自利益的交易。恩格斯曾经评价说:“虽然沙皇俄国在两次战役中都打败了,但是它却靠牺牲自己昨天的同盟者而获得了新的领土,并且同拿破仑结成了同盟来瓜分世界:西方归拿破仑,东方归亚历山大。”[8](P61)在维也纳会议前后,亚历山大一世将秘密外交的手段发挥到极致。通过密约,俄国得到了华沙大公国的大部分领土,建立了俄国沙皇兼任国王的波兰王国,从瑞典手中得到了芬兰。由此可见,政治体制上的集权性和封闭性导致近代俄国外交决策中秘密外交盛行,这一特点产生于近代俄国,并延续至苏联时期。
(三)外交决策受意识形态因素影响
在近代俄国外交史中,宗教意识形态和政治意识形态因素对外交决策产生过重大的影响,甚至在外交思想和外交政策的选择上占据了主导地位。作为基督教三大派系之一的东正教,具有扩张性和普世性,其教义和教会对俄国外交决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莫斯科公国时代,东正教思想家们将传播基督福音的善行与沙皇的东侵扩张结合在一起,主张“欧洲将宝贵的文化遗产经一个民族传递给另一个民族。俄国从欧洲手中接过了这一遗产,就应该成为这盏明灯的执掌者和向更为遥远的东方国家的传播者。因此,对于欧洲而言,俄国曾经扮演了学生的角色,而对于亚洲而言,俄国必然要发挥老师的作用。”[12](P1)同时,俄国东正教不但完全接受了原始基督教义中的扩张性,还发展出新的扩张性教义——“第三罗马”。第一罗马(罗马城)由于缺乏虔诚而被蛮族攻灭;第二罗马(君士坦丁堡)由于与拉丁教派媾和而陷落;莫斯科是领导全世界基督教的第三个中心,是伟大的世界首都,即“第三罗马”,是第一罗马和第二罗马的继承者,“已命中注定是这个基督教帝国的领导”[11](P357)。在这一教义影响下,沙皇开始以罗马皇帝继承者的身份不断对外侵略扩张,发动争霸战争。
19世纪上半叶,宗教意识形态和政治意识形态融合为一体,左右着俄国外交决策。亚历山大一世时期,沙皇对欧洲问题的看法中越来越多地增加了宗教因素的考量,浓重的宗教虔诚感和宽容观念在对待法国的态度中表露无疑。在拿破仑占领莫斯科后,亚历山大一世说:“莫斯科的大火照亮了我的灵魂,上帝在冰天雪地的战场上的判决,使我的内心充满了一种我从未经历过的深切信念……我充满着深刻而成熟的信心,相信应该为上帝,为增进上帝的荣耀,而贡献我自己和我的政府的一切。从那时起,我变成了另一个人;我感谢欧洲之从毁灭中得救使我也获得了拯救和自由。”[12](P238-239)在击败拿破仑后,亚历山大一世告诫军队:上帝不喜欢残酷,要有同情心,要有仁慈之心。沙皇深信他是上帝选择的布道者,是在神的指引下行事的。当然,亚历山大一世的道德观和宗教观并没有影响俄国攫取实际利益,沙皇将其理想与历史使命完美地结合在一起,通过战争和扩张获得了巨大的利益。在神圣同盟的缔结过程中,亚历山大一世明确提出,“根据圣经的训示,一切人要彼此以兄弟之情相待,缔约三国的将一致以一种真诚的与不可分的手足之情互相联系,并彼此视为一国同胞,无论何时、何地,均将互相救援;他们把自己看作臣民与士兵之父,又将以本身所秉有的同样的手足精神来引导他们,去保卫宗教、和平与正义。”“因此,力量的唯一真义,无论在上述各政府之间,或在其臣民之间,都应当是:为彼此服务,以永不变更的善良愿望来考验他们应有的相爱;人人都把自己视为同一基督教国度里的国民。”[13](P331)可见,神圣同盟议定书中弥漫着强烈的圣经的精神,亚历山大一世将政治问题看作道德问题,将自己的宗教信仰、宽大为怀和普遍和解融进保守主义同盟中,为其外交披上了浓重的宗教神秘色彩,这一特点对尼古拉一世等后世沙皇也产生了深刻影响。
尼古拉一世时期,意识形态因素对外交决策的影响更为直接和明显。尼古拉一世认为俄国与普鲁士、奥地利的合作是基于共同意识形态的友谊,是牢固而稳定的。正统主义原则在尼古拉一世看来是不可更改的,是维持欧洲秩序的根本。为了维持正统秩序的有效存在,就必须坚持镇压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政策,因而俄国镇压了1830年和1848年的欧洲革命。出于意识形态的原因,法国的共和制度使得尼古拉一世对法国极度不信任,禁止法国船只驶入俄国港口,严禁俄国青年赴法留学,完全排斥了从国家利益的视角审视俄国的大国关系的做法。最终,尼古拉一世对意识形态的一厢情愿和对形势的误判,将俄国引向了万劫不复的克里米亚战争。克里米亚战争的失败使得俄国意识到“国家对外政策不应建立在任何政治意识形态的基础上,而应建立在国家利益的基础上。”[14](P324)此后,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和亚历山大三世也长期受限于意识形态因素,将俄国、普鲁士和奥地利的保守主义王朝合作视为俄国外交的重中之重,纵使近代德国统一后欧洲局势已经发生了转向和调整,俄国依然积极构建三皇同盟的堡垒,以期实现外交转换。直至亚历山大三世统治的末期,俄国才超越了意识形态的束缚,突破了王朝联合的既定模式,选择与法国结盟,转变了俄国外交的不利局面。
(四)外交决策中“外国帮”的作用明显
俄国地处欧亚大陆东西方结合部,不仅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冲撞融合地带,也是人种混杂和交融地区,历史上形成了不同民族共处、多人种混杂的现状。此外,历史上拥有外国血统的沙皇不在少数,这使得在外交决策和外交执行领域里任用、信用、驾驭外裔外交要员成了一种常态化的存在,这也成为其外交决策中突出的特征。
任用外裔外交家主持外交部,由彼得一世开创。彼得一世的改革不但强行使俄国接受了西方的先进文化,还为俄国引进了西方的外交精英。此外,彼得一世处死独生子、外嫁女儿的做法也造成了俄国皇族血统的外化,彼得三世和叶卡捷琳娜二世就是典型的有外国血统的俄国统治者。叶卡捷琳娜二世时期,女皇忌讳自己的外国血统,但在任用外籍官员上却延续了彼得一世的习惯。至亚历山大一世时期,俄国外交界的“外国帮”已经成型。此后,历任沙皇都无所顾忌地任用具有外国血统的外交大臣,涅谢尔罗德、卡伯吉斯特利、吉尔斯都是拥有外籍血统的外交大臣的典型。19世纪末,恩格斯在《沙皇俄国的对外政策》中曾描述俄国外交中的所谓现代耶稣会,是一伙由“外国冒险家组成的秘密团体,把俄罗斯帝国变得现在这样强大”,“他们的作用超过了俄国所有的军队。正是这一帮人使俄国成为巨大、强盛和令人恐惧的国家,并为它开辟了称霸世界的道路”[8](P23-24)。这些外国冒险家热衷于扩张,他们将扩张视为保护俄国领土安全的利器,在外交决策中积极的推动扩张因素的膨胀,推动了俄国领土的扩张,使俄国的边界从第聂伯河和德维纳河扩展到维斯拉河以西,直到普鲁特河、多瑙河和黑海,从顿河和伏尔加河扩展到高加索以南,直到奥克苏斯河和亚克萨尔特河的发源地。
19世纪末,存在于俄国宫廷和政府中的“德国帮”对俄国对外政策的决策起到了重大的作用。沙皇兄弟弗拉基米尔、外交大臣吉尔斯及助手拉姆斯多夫的亲德倾向明显,在对外结盟的对象选择上,他们一向坚持保守主义结盟路线,认为俄德王朝合作对巩固沙皇专制统治具有重大意义,而与共和制的法国结盟将直接损害俄德关系,危及沙皇专制的安危。吉尔斯曾多次声明,和共和制的法国接近对于帝国政府来说是完全不可能的。因此,“德国帮”的强势和阻挠,导致了1887至1890年的法俄关系呈现出既友好合作但又不订立同盟的局面。1891年5月,法国建议沙皇开始法俄军事协定的谈判,以法俄合作应对德国力量的突变,但该协定直到1892年8月才草签,1893年底才获批准。这其中,与“德国帮”的作用不无关系。
近代俄国外交的不排外性,吸引了众多国外嗅觉灵敏的职业外交家,沙皇为他们提供发达的机会和条件,他们也为俄国外交作出了努力。历史上,俄国与这些外裔职业外交家之间形成了一种良性的互动关系,他们相互为用,各得其所。
参考文献:
[1]冯玉军.俄罗斯外交决策机制[M].时事出版社,2002.
[2][美]亨利.基辛格.大外交[M].海南出版社,1998.
[3][英]A.J.P.泰勒.争夺欧洲霸权的斗争(1848-1918)[M].商务印书馆,1987.
[4][美]拉伊夫.独裁下的嬗变与危机:俄罗斯帝国的二百年剖析[M].学林出版社,1996.
[5][俄]尼基弗罗夫.北方战争最后几年俄国的对外政策:尼什塔特和约[M].莫斯科,1959.
[6][美]巴巴拉.杰拉维奇.俄国外交政策的一世纪[M].商务印书馆,1978.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M].人民出版社,1974.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M].人民出版社,1965.
[9][美]赫坦巴哈.俄罗斯帝国主义:从伊凡大帝到革命前[M].三联书店,1978.
[10][俄]尼古拉.阿多拉茨基.东正教在华两百年史[M].广东人民出版社,2007.
[11][苏]克雷维列夫.宗教史(上卷)[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
[12][德]卡尔·施特林.俄国通史(第三卷)[M].格拉茨 科学院出版社,1961.
[13]国际条约集(1648—1871)[M].世界知识出版社,1984.
[14]姚海.俄罗斯文明与外交[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