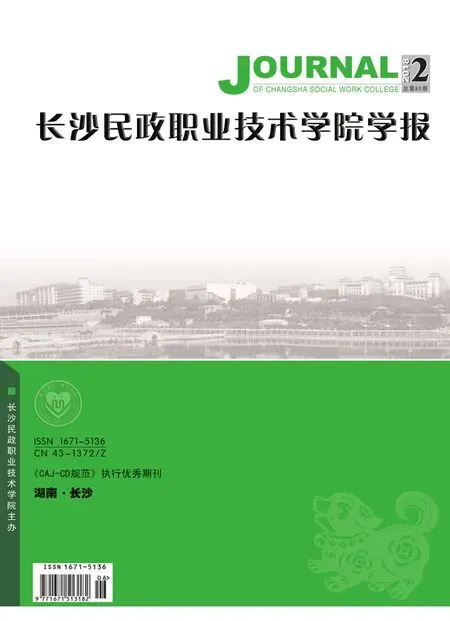网络版权中陷阱取证的效力认定
姚 远 董思薇
(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学院,上海 普陀区200063)
版权即著作权,是指各类艺术作品的作者享有的权利。根据《著作权法》第十条的规定,著作权人享有包括发表权、署名权等人身权利以及包括复制权、发行权等财产权利。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文学艺术作品更多以数字化的形式在网络传播,但是由于网络的快捷性以及便利性,侵犯版权的现象日益频繁,根据2017年度中国网络版权保护大会公布的《2016年中国网络版权保护年度报告》显示,全国著作权案件为66900件,其中60%为网络著作权案件,约4万件。但是知识产权案件因为其专业性极强,所以在取证中存在严重的缺项,陷阱取证也因此而生,但是其是否合法仍有待商榷。
一、网络版权中陷阱取证的合法性认定
(一)网络版权中的“陷阱取证”
陷阱取证一词最早在刑事侦查中出现,是指在一些特殊的刑事案件中为了取得犯罪证据或者为了抓获犯罪嫌疑人而采用特殊的侦查方式。其主要使用于贩毒、行贿走私卖淫等犯罪,由于犯罪行为具有极强的隐蔽性,侦查人员无法通过正常程序获取该证据,因此采用陷阱取证的方式。在刑事诉讼中,将陷阱取证分为犯意诱发型和机会提供型两种。犯意诱发型是指犯罪嫌疑人本来不具有实施犯罪的主观意图,但是侦查人员通过语言或者行动使得其产生了犯罪的意图,从而实施犯罪。机会提供型主要是指犯罪嫌疑人本身就存在犯意,而侦查人员只是提供一个客观的条件,即使侦查人员不提供机会,犯罪嫌疑人依旧会实施犯罪。两者之间的区别在于第一种情况即使侦查人员不提供这个机会,犯罪嫌疑人依旧可能对其他人实施犯罪;第二种情况是如果侦查人员不去诱惑引导,犯罪嫌疑人就不会犯罪。因此对于陷阱取证收集的证据,第二种完全可以用非法证据排除,而第一种仍然有待商榷。
网络版权中的陷阱取证是指在网络版权侵权案件中,使用陷阱取证的方式取得有效证据。版权具有无形性,因此在版权侵权案件中证据具有极强的隐蔽性、易于复制、删除。数字化时代的发展,不仅加速网络作品的传播,同时也导致网络版权侵权案件中证据的加速消失、不易收集保全。因此在版权保护过程中,陷阱取证的方式应运而生。与刑事诉讼中的陷阱取证相同,网络版权中的陷阱取证依旧分为犯意引诱型和机会提供型两种。
(二)陷阱取证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68条规定:“以侵害他人合法权益或者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的方法取得的证据,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因此陷阱取证中取得的证据能否被适用主要看两点:是否是法律明文禁止的和是否侵犯了他人的合法权益。
1.针对陷阱取证是否是法律明文禁止的问题。此时我们应当对该条文中的“禁止性规定”作法律解释,从广义上讲,法律不仅包括规则同样也包括原则,从狭义上而言,法律仅仅是包括明文规定的条文。在此我们对《证据规定》中的法律作狭义解释,因为法无禁止即允许,如果将该条文中的法律禁止性规定作广义解释,那么诚实信用、公序良俗等原则本来就需要法官自由裁量,如此一来以原则来衡量的证据就会处于不确定的状态。因此采用狭义解释后,目前我国并没有对陷阱取证作明文规定,所以陷阱取证取得的证据不存在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的情况。
2.针对是否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问题。对于犯意诱发型陷阱取证是侦查人员主观存在恶意去引诱他人犯罪,这足以使一个理性的人做出违背一般条件下的主观意愿而做出意思表示。这种情况从本质而言与教唆他人犯罪没有本质区别,因此应当被排除。而机会提供型陷阱取证是即使不向取证人也会向其他人侵权,因此取证人只是从客观上提供了条件,并没有对侵权人的主观意志产生影响,不存在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问题,因此不需要被排除,从全世界范围看,英国、德国等对诱发性取证进行严格控制,而对于机会提供型基本予以认可。
(三)国外诱惑侦查与网络版权陷阱取证的比较
在英国,上诉法院基本上采取从主客观两者处罚,即假定警察没有引诱犯罪嫌疑人那么他会不会犯罪,如果犯罪嫌疑人犯罪与侦查人员有关,那么根据《警察与刑事证据法》第78条的规定法官有权利排除有关证据。日本最高法院认为,机会提供型陷阱取证从实体看不会阻却犯罪行为人犯罪构成的该当性、责任性和违法性,从程序角度上看,即使实施陷阱举证的行为,公诉人依旧可以提起公诉,因此肯定该种陷阱取证的合法性。欧洲人权法院在“卡斯特罗诉葡萄牙”一案的判决:对于该证据是否排除必须区分两种情况,一种是侦查员向已经从事毒品犯罪的人购买毒品,则不构成对《欧洲人权公约》第6条“公正审判”权利的侵犯,另一种是侦查人向从未从事毒品交易的人购买毒品,则构成对犯罪嫌疑人人身的侵犯。
由于目前没有专门针对陷阱取证的详细规定,因此从英国、日本、欧洲法院对于诱惑侦查的规定可以对网络版权中的陷阱取证有如下借鉴:第一,明确将陷阱取证分为两种类型即犯意提供型和机会提供型,其目的在于区分取证人员在取证时是否存在主观故意,其实施违法行为与取证人是否存在因果联系,即如果取证人不采取行动,被取证人是否还会实施违法行为;第二,针对两种不同的类型采用不同的处理结果,如果针对犯意诱发型的案件一律按照非法证据予以排除,如果是机会提供型的案件由于取证人的存在对侵权人是否实施侵权行为并无联系,因此对于该种手段取得的证据可以直接予以认定。
二、从知识产权典型案例看网络版权陷阱取证
(一)北大方正、北京红楼诉北京高术公司计算机著作权侵权案
2001年7月20日,北大方正公司向高术天力公司购买KATANAFT-5055A激光照排机,并对安装盗版软件的照排机以及方正公司本身软件的机器进行证据保全。一审法院认为对于方正公司的行为是否违法法律没有明文规定,因此对方正公司取得的证据予以认定。但是二审法院认为:北大方正公司购买激光照排机真正目的是为了获取盗版软件,而这种方式并不是能获取该项证据的唯一方式,而且这种方式有违公平正义,破坏正常市场秩序,因此不予认定。
2006年北大方正公司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再审,最高人民法院认为方正公司的行为首先从主观来看没有不正当性,高术公司本就向其他人销售盗版软件,方正公司只是单纯地购买,并没有损害任何人的权益。而且知识产权案件由于其违法行为很隐蔽,权利人一直都存在取证难的问题,所以基于对知识产权案件的特殊考虑,认可该种陷阱取证方式有利于保护知识产权,维护知识产权人的合法权益。最高人民法院对方正公司的支持判决打开了民事诉讼采用陷阱取证的突破口。
互联网技术迅速发展,不仅加大了网络作品的传播速度,也扩大了网络版权侵权的影响范围,侵权证据难以保全的一部分原因也是由于计算机修改速度迅速,侵权内容很容易被篡改甚至消失,从取证难度而言甚至超过了一般的著作权侵权案件,从北大方正的案件中可以给网络版权侵权案件中的陷阱取证有如下两点启示:第一,取证目的必须正当。在侵权案件必须以客观的方式取得证据,在主观上不存在引发被取证人实施违法的主观意图,不能侵犯被取证人的意志自由权。第二,案件取证必须存在极强的困难性。陷阱取证上文已经阐述,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有边界模糊之处,因此在适用过程中必须特别谨慎,必须仅仅能够适用于一些难以取证或取证难度较大的侵权案件,或者说陷阱取证接近于是唯一取得证据的方式,如果是在一般的网络版权侵权案件必须严格控制。
(二)美国奥多比公司(Adobe)诉上海年华公司计算机软件著作权案
美国奥多比公司(Adobe)诉上海年华公司计算机软件著作权案是在知识产权领域著名的陷阱取证的案例。1999年8月,奥多比公司委托的调查人员向年华公司购得一台苹果牌“63/350 CD+17”、年华公司并随机附送一张光盘,并支付人民币22,000元,经检测年华公司的计算机软件中含有奥多比公司开发的软件。法院认为年华公司提出是在奥多比公司调查员的诱导下才安装、复制软件的抗辩未能成立,因此判令年华公司侵犯奥多比公司的著作权并予以赔偿。
该案对于网络版权中有关陷阱取证问题有以下几点启示:第一,取证人引诱被取证人实施违法行为。在该案中被告律师提出原告存在引诱被告安装盗版软件的行为,但是由于被告证据不足不予认定,因此该案的关键在于是否存在诱导性取证,这其实表明法院判决的态度,如果只是事实购买,不存在对被告主观意志的影响,那么所取得的证据是可以被采纳的,这变相支持了陷阱取证中的机会提供型证据。第二,证明责任分配问题。在本案中法院将被告提出的诱导性举证的证明责任给了被告,也就是说被告必须提供证据证明原告的行为存在诱导性,才最终导致被告实施犯罪。然而需要证明取证人实施该种诱导性行为,同时自己本身不具备任何违法意图和行为的难度极大,这样的证明分配模式其实有利于机会提供型陷阱取证取得的证据能更多地被采纳。
三、网络版权中陷阱取证的适用问题
(一)陷阱取证与利益衡量
从北大方正的二审判决可以发现,二审法院之所以对证据不予认可是因为其违反了诚信原则,在民事诉讼中诚实信用原则是基本原则之一,为维护市场公平正义,民事交易应当遵守恪尽诚信原则,但从陷阱取证本身而言,其实存在一定的欺骗性质,因为取证人明知道对方具有侵权行为而故意让其发生侵权行为,从而将证据保全,从某种角度看确实不符合诚实信用原则,因为取证人进行交易的目的并不是进行等价交换,而是获得对方的违法商品,从而为自己维权提供证据。另者,证据取得必须符合程序正当原则,民事诉讼一方当事人有取证的权利,因此在取证主体上正当,但是在取证方式上略带欺诈性质是否会构成证据瑕疵呢?但是如果考虑程序公正将该证据排除,则有可能影响实体公正,两者出现矛盾。
当陷阱取证出现与诚实信用原则、公平正义原则以及程序正当原则矛盾时,就应当考虑利益衡量的问题,平衡两者的利益,从而使得利益最大化。利益衡量理论认为,相互冲突的社会群体中的一方利益应当优先于另一方的利益,或者该冲突双方的利益都应当服从第三方利益或整个社会的利益。这时法院就应该从社会整体利益的角度对该项证据进行衡量,如果符合社会整体利益那么可以对该证据进行采纳,否则就予以排除,但是过分的自由裁量权容易出现滥用,因此平衡两者的关系依旧至关重要。在网络版权侵权案件中,由于互联网数字技术的特殊性,证据具有极强的隐蔽性和易消失性,为维护著作权人的合法权益,因此在取证过程中有可能适用陷阱取证,而且在某些情况下不使用陷阱取证无法获取证据。但是在取证过程中依旧不可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以及损害他人合法权益,否则应当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予以排除。
(二)对陷阱取证的两种类型区别对待
网络版权中的陷阱取证依旧分为犯意诱发型和机会提供型两种,具体内涵以及区别上文已经阐述。严格区分两种不同类型的陷阱取证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
第一,两者动机不同。机会提供型只是在客观情况无法取得证据的情况才创造客观条件取证,目的仅仅是保留侵权行为。而犯意诱发型是引诱侵权人让其从不想侵权到侵权,该种情况更多地有陷害的意味,动机不纯。
第二,两者方式不同。机会提供型只是提供客观条件,即使取证人不提供被取证人仍然会去实施,但是犯意诱发型是取证人通过语言、行为一层层引诱侵权人,让其产生侵权的意思表示,从而实施侵权行为。
第三,两者产生的影响不同。机会提供型只是创造条件,换言之侵权人即使不在取证人创造的条件时实施,总有一天也会实施该行为,而犯意诱发型是让侵权人从无侵权动机到有侵权行为,在本质上对侵权人进行引导。
那么对于上述两种类型的陷阱取证,需要对其做区分。由于犯意诱发型是不断对侵权人进行犯意引诱,从而让其产生侵权动机,再到产生侵权行为,取证人主观上的恶意已经不能证明其取证具有正当目的,而且损害了侵权人的主观选择权,因此应当作为非法证据予以排除。而机会提供型案件中,取证人不对侵权人作任何引导,侵权人本身就具有侵权的犯意,而且也考虑到网络版权侵权案件取证难度大,因此法官可以通过利益衡量予以接受。
(三)建立被取证人救济制度
虽然在网络版权的侵权案件中,取证一方收集证据难度大而采用陷阱取证的方式,犯意诱发型证据前文已经阐述作为非法证据进行排除。而机会提供型证据即使是被采纳但是其合法性与否仍然存在争议,如果过分地偏向于取证人,就会导致双方的权利义务失衡,不利于公平正义的实现,因此需要赋予被取证人以一定的救济权利,使得双方达到基本平衡。被取证人有权利为自己行为的合法性进行证明,同时如果取证人存在以下行为,被取证人可以因此免责:第一,被取证人本身不存在违法的意图,但是取证人通过欺诈、引诱、教唆等方式使得被取证人产生违法的意图,即诱发型取证所得的证据;第二,被取证方取证的方式已经违法了法律的禁止性规定,比如是通过损害被取证人人身安全的方式;第三,被取证方取证方式为社会带来严重不良影响,极大地损害了社会或者是大多数人的利益;第四,被取证方严重损害第三人的合法权益,造成其严重损失。
另外,被取证人能证明取证人恶意进行陷阱取证而对被取证人的人身、财产产生危害时,被取证人有权对取证人提出损害赔偿请求。在这种情况下,取证人不再受利益衡量说的保护,证据应当按照非法证据排除,同时其本人也应当按照违反诚实信用、公平等基本原则而受到处罚。
(四)陷阱取证与补强证据规则相结合
陷阱取证两种类型上文已经阐述,对于机会提供型的证据而言虽然不能算作是非法证据予以排除,但是由于取证人在与被取证人交易中实际上是采用欺骗或者隐瞒,因此证据在形式上存在瑕疵,是瑕疵证据。针对瑕疵证据,虽然具有证据资格即可采性,但是证明能力却大大下降,对于有瑕疵证据的证明大小,目前并无定论,主要是依赖于法官根据案情、社会状况、个人经验等方面进行衡量。笔者支持陷阱取证取得的证据不能单独作为定案的依据,而需要有其他证据加以补强,但是如同上文阐述之所以对网络版权中陷阱取证取得的证据予以采纳的重要原因是基于网络版权案件取证的困难性,所以针对该类证据的补强证据规则主要也体现在举证责任上。
在举证中,取证方在审判中应当证明自己进行陷阱取证在主观上具有正当性,不存在诱导或者引诱被取证人的行为,从北大方正一案中可以看出,最高人民法院之所以采纳有关证据,是因为认定方正公司主观上不存在恶意。其次取证人也应当证明取得该项证据的困难性。因为陷阱取证取得的证据本身就是游离在法律的边缘,只有当取证及其困难的情况下才可以予以采信。当取证人对上述两点能进行充分举证时,可以对该项陷阱取证取得的证据予以认定。
四、结语
网络版权侵权案件数量逐年增长,而网络版权侵权案件与一般知识产权案件一样均存在取证难的问题,那么陷阱取证取得的证据能否被采纳就极为重要。笔者认为对于网络版权中的陷阱取证问题应当严格区分犯意诱发型和机会提供型两种类别,法官在裁判时可以利用利益衡量说进行综合考虑,而不应该将其一并纳入非法证据一列予以全部排除。
——以《民法典》第1182条前半段规定为分析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