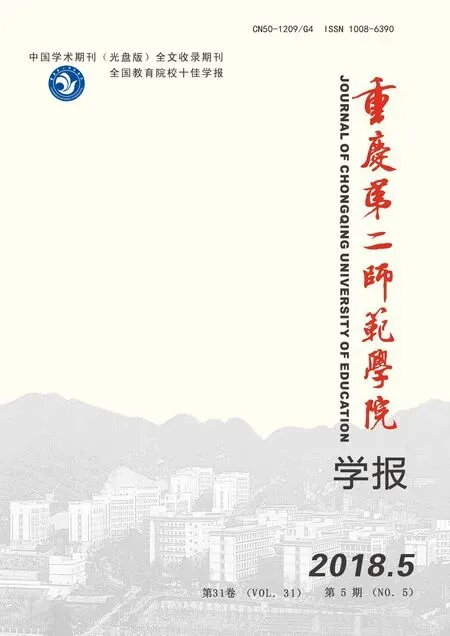近十年来汉语学习焦虑研究评述
徐婷婷
(浙江大学 外国语言文化与国际交流学院, 杭州 310058)
焦虑是一种面临挑战的威胁时自然产生的情绪反应,并且当人在无法达成目标或克服障碍时,这种情绪尤为明显,甚至会导致人的自尊心受挫,造成失败感、内疚感和畏惧感。1960年,Alpert、Haber[1]指出焦虑可分为一般焦虑和具体焦虑,而具体焦虑量表更能体现出焦虑与学术表现的关系。而后,Horwitz等[2]提出了外语学习焦虑这一概念,指一种从课堂语言学习中产生的自我感知、信念、感觉和行为,尤其强调外语学习焦虑不同于一般焦虑的独特性。他们设计了外语课堂焦虑量表[2](Foreign Language Classroom Anxiety Scale,简称FLCAS),发现焦虑对学习有一定的负面效应。而这一发现却与之前Alpert、Haber[1]提出的促进性焦虑(facilitating anxiety)和阻碍性焦虑(debilitating anxiety)的概念相悖。Spielmann和Radnofsky[3]表示紧张(tension)有时能带来对学业有利的效果,这种想法与Alpert、Haber[1]一致。更有学者针对焦虑与学习状态的因果关系进行了深入的探讨,认为Horwitz指出的“焦虑导致了学习困难”这一说法并无充分的事实根据,不能排除“学习困难导致焦虑”的可能性。直至今日,对于外语学习焦虑的探讨和质疑仍有不少,但多数研究已采纳该说法,并至少验证了焦虑与外语学习的密切关系。
相较于国外,国内的相关研究起步较晚。钱旭菁[4]利用FLCAS量表对来自欧美、日韩、加拿大等多个国家的在华留学生进行了汉语学习焦虑的研究对比,内容包括个体因素(如期望值、自我评价等)和背景情况(如年龄、国别等)。结果显示焦虑对汉语学习有一定的抑制作用,且国别、自我评价等因素都对汉语学习有一定的影响。其后,越来越多的学者投入该领域的研究,更深入和全面的研究结果逐年涌现[5-6]。随着中国的逐步发展和壮大,汉语的重要性也日渐显现,越来越多的外国留学生来到中国进行语言学习。焦虑作为影响留学生汉语学习的一个重要因素,应该受到更广泛的重视。本文集中梳理了近十年30余篇关于汉语学习焦虑研究的文献,对其进行了详细的归类和分析,旨在总结该领域的研究现状,并为将来的研究提出一些建议。
一、汉语学习焦虑的研究对象和主要方法
本文集中梳理了2007—2017年共37篇期刊论文,其中包含实证研究25篇,占67.6%,研究对象涵盖欧洲、美国、日韩、中亚、东南亚、蒙古等多个地域,但样本量普遍偏少,多集中在一两百人左右。这些研究大多针对来华留学生,仅有少数几篇例外。例如,唐进[7]对比研究了中国大学生学习英语与美国学生学习汉语的焦虑水平和特点。研究发现:中国学生的焦虑水平普遍低于美国学生,其中男生的焦虑多高于女生;中美两国学生学习外语焦虑的重点不同,中国学生对于考试、负面评价容易产生焦虑,而美国学生则更担心课堂环境和沟通交流。张钘铭等[8]在日本两个城市(东京和长野)进行了较大范围(390人)的问卷调查,研究关于日本学生汉语学习焦虑与交流意愿缺失的关系。结果表明,日本学生的焦虑水平普遍偏高,男生因焦虑导致的交流意愿缺失现象更严重。
这些论文的研究方法以问卷调查为主,多采用Horwitz等设计的FLCAS量表[9-10],并结合自制量表以求更贴合汉语学习的特点。其中,吴剑[11]根据自己教学的经验,设计了汉语课堂焦虑量表和汉语听力焦虑量表,在信度检验中有较高的分数,可信度较高。除问卷设计外,有的研究以课堂观察[12]和访谈[13]作为焦虑度调查的辅助工具。仅有一篇文献采用了个案分析的方式。王婷婷[14]研究了一位美国男生的焦虑水平,该男生在美国和中国都经过了一定时间的汉语学习,他在中国的焦虑水平高于美国,尤其紧张于同学的负面评价和沟通交流,而对老师的纠正持乐观和轻松的态度。
二、汉语学习焦虑产生的原因
(一)宏观原因
不少研究利用关于语言学习中的心理以及文化因素的理论来解释外语学习产生焦虑的原因。例如,杨馨[15]引用了Ellis的语言距离概念,并结合Tobias关于语言学习焦虑的三个阶段(输入、处理和输出)来讨论。语言距离即外语学习者在外语学习过程中面对不同语言文化的差异而产生的一种主观认知。这种认知的主观性时常会引起外语学习者迷茫、焦虑、畏惧的负面情绪。在语言输入阶段,学习者经历的主要是简单词汇的学习,而其母语与目标语的词汇并不是一一对应的(英语和汉语分属不同语系),语言距离就此产生,此时的距离感主要是基于语言差异的陌生;在语言处理阶段,学习者将面对不同难易水平、不同文化价值观的材料,如果学习者的本族文化与目标语文化差异显著,则会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学习者的迷茫和无措;最后一阶段是输出阶段,即要求学习者运用内化了的知识,如果学习者内心仍对文化差异的态度模棱两可,则会引发其自身身份认同的危机。以上三个阶段的情况都是导致学习者焦虑的原因。
陈柳羽[16]则借鉴了舒曼的文化适应假说,指出“第二语言获得是由学习者与所学语言的文化之间的社会距离及心理距离决定的”。心理距离包括语言休克和文化休克等。语言休克指在语言学习的某个特定阶段会产生语言水平停滞不前的现象,而实则是语言巩固和不断内化的过程。若学习者急于看到成效,则会起到适得其反的效果。文化休克则是学习者在跨文化环境中文化适应的一个阶段,在此阶段容易产生心理隔阂,从而导致焦虑的心态。
笔者认为,以上提到的语言距离和心理距离虽然属于不同的理论框架,但都介绍了外语学习者在学习中遇到的语言本身或文化差异问题,而这种差异容易导致学习者的心理问题,比如焦虑。
(二)具体原因
影响汉语学习者焦虑水平的因素有很多,每个研究也并非只针对某一种情况进行调查,因此本文将其分为三类进行讨论:背景情况(包括国别、性别、学习汉语时间等)、个体差异(包括性格、期望值等)和外在环境(包括材料难度、教学方法、教师态度等)。
1.背景情况
国别。在基于国别差异与焦虑水平的研究中,有的研究仅基于单个国家或地域进行分析,有的研究对比了多个国家。研究表明,美国(北美)、中亚地域的留学生焦虑水平普遍偏低,而日韩(东亚)、越南(东南亚)、泰国(东南亚)的留学生焦虑水平比较高[10][17-20]。基于单个国家的研究结果是否值得参考还有待探讨,原因在于虽然实验的评价大多基于FLCAS,但关于焦虑水平高低的评价并没有统一的标准,因此得出的结果值得商榷。
相较而言,多国统一研究中的对比就比较具有信服力。赵青[21]研究出欧美学生的焦虑度普遍低于日韩学生,这与刘文等[22]的研究结果相反;范祖奎[23]对日韩两国情况又有进一步的研究,发现日本学生的焦虑度高于韩国。张瑞芳和杨伊生[24]对比了韩国学生与蒙古学生的焦虑水平,得出了韩国学生焦虑度高于蒙古学生的结果。钟家宝和高静[25]对国别差别的研究比较全面,他们发现不同地域的焦虑水平如下:印度(南亚)>中东>非洲>欧美>巴基斯坦(南亚)>东亚。与以上结果相悖的研究也同样不少,例如周文华[26]表示国别(非洲、东南亚和南美洲)并不影响学习者的汉语学习焦虑。细看以上结果不难发现,同一地域的不同国家其焦虑水平可能大不同,有的研究结果甚至存在相悖的现象,这极有可能是由于调查人数不够以及个体因素差异大,因而使得研究结果不能达到普遍具有参考意义的水平。
性别。基于性别差异导致焦虑水平不同的研究也广泛存在。多数研究[19][22][25][27-28]支持女性的焦虑水平高于男性,但仍有少数[7][20]持相反意见,还有实验[24][26]表明性别因素不影响焦虑水平。
学习汉语的时间。与性别研究类似,学汉语时间的长短与焦虑水平的研究结果也各不相同。刘娟娟[19]认为学习汉语时间为三到六个月时学生的焦虑水平最高,因为该阶段学生对汉语的新奇感已经减弱,转而发现学习的困难,因而产生焦虑。何姗[27]也认为学习六个月时学生最焦虑。刘文等[22]的研究结果表明,学习时间越长,学生的汉语水平越高,而焦虑度逐步下降。笔者认为,学生的焦虑水平可能在短时间内有着细微的变化,如果以年为单位检测学生的焦虑度,可能无法得出可信的结果。
其他。其他背景因素造成的焦虑水平差异的研究还有不少,例如汉语水平的高低[13][27]、考试成绩[9][24-25]、年龄[19][22]、专业[25]、是否学过其他外语[27]等。但以上因素的相关文献较少,不足以进行有说服力的对比分析,因此不加以讨论。同时,这样的现象也足以说明这些背景因素是当前研究的漏洞,需要更多的学者加以考虑。
2.个体差异
个体差异包括学习者的性格、期望值、自我评价、自信程度、竞争意识等,本文收集的论文中对于每一点的研究都有,但都比较少,难以进行系统比较,因而本节主要分析性格因素与焦虑水平的关系。不少文献提出了性格因素可能会引起焦虑水平的不同[29-30],但将此猜想投入实践的研究并不多见。蔡德馨[10]认为外向学习者较内向和内外向特质兼有的学习者而言焦虑水平明显偏低,后两者焦虑水平的差异并不明显。段梅花[17]的研究却表明,性格因素并非影响焦虑水平的个性因素之一。
3.外在环境
纠错方式。仲清[28]专门针对不同的纠错方式进行了实证研究,通过对八个班的课堂观察和问卷调查,他发现在教师完全使用重铸方式对学生的错误进行改正的班级,学生的焦虑水平普遍较低,而在完全使用元语言提示的班级,学生的焦虑水平较高,教师结合使用两种方式尽心纠错的班级焦虑水平位于前两者之间。他明确指出了不同纠错方式对学生的焦虑水平会产生影响。
话题。不少研究发现,学生对于上课讨论的主题或话题非常敏感,如果话题为开放性问题(例如“你最爱的食堂是哪个?”),则学生反应积极,行为放松;如果话题比较陌生,或者需要学生根据课本的知识进行巩固,则焦虑感提升[29-30]。针对阅读时候的焦虑[23],学生同样认为,如果文章主题不了解或文章较长都会使其产生一定程度的焦虑。
其他许多研究发现,汉语本身的难度[17][23][31]也给学生造成了一定的压力,从而导致了焦虑(笔者将该因素归类为外在环境,因其与学习者自身状况无关)。另外,同学或教师的负面评价[14]、教师的体态与提问方式[22]等都也容易造成学生的焦虑情绪。
三、汉语学习焦虑的应对方法
(一)学生应对焦虑的措施
施仁娟[32]详细探讨了学生常见的各种应对焦虑的方式,其中乐观积极的方式包括查词典、与同学交流、放松心态(将学习视为兴趣)、预复习,而消极的则有回避考试(请假)。除上述提到的查字典和预复习的方法,高影和徐川[33]表示学生通常也喜欢使用团体合作学习以及用轻松休闲的方式(听汉语音乐、学唱流行歌曲或儿歌)进行学习以舒缓焦虑。Yan-hong[34]的研究与上述结果不谋而合,他发现通过合作学习,学生能对所学的知识加强理解,减少对负面评价的恐惧,从而大大减少了焦虑的产生。
(二)教师应对学生焦虑的措施
1.文化课程
从上述分析中可以发现,大多数研究结果表明,不同国家地域的学生焦虑水平不同。针对该现象,赵青[21]和齐飞[29]提出应该给留学生多普及中国文化,甚至增加相关的文化课程。因为在留学生来华的最初几个月到几年中,他们都经历着跨文化适应的阶段,该阶段不可避免。教育者能做的只有尽量缩短学生调整的时间,如果不能很好地将中国文化介绍给他们,很可能会延长学生适应的阶段,造成更长时间的语言休克和文化休克。
2.汉字教学
范祖奎[23]和邢尧[31]在对教师的建议中都提到了汉字教学的重要性。对于字母文字的国家来说(如美国、欧洲各国),汉字系统与字母文字系统截然不同,因语言书写天然的差异性,欧美学生对汉字书写的掌握较难;对于日韩等国家而言,虽然在各自的文字系统中存在不少的汉字,但这些汉字在发音、意义甚至字形上都有了一定的变化,这也导致日韩学生在学习汉语时易产生混淆。因此,无论是对于欧美等字母文字的国家还是日韩等同属汉字系统的国家,学生学习和巩固汉字都是非常重要的。
3.提高学生自信
不少研究发现学生在汉语学习过程中的自信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们的焦虑水平。邢尧[31]用心理学解释了自信的重要性:“如果一个人的自我评价比较高,就可以避免遭到许多应激源的全面影响。”他认为,教师应当实时地掌握学生的学习态度和状态,同时,多给予学生适当的鼓励和表现自我的机会,这对提升自信有重要作用。范祖奎[23]指出应当适度地让学生“品尝成功的机会”,例如在进行阅读时,可适当地解释生词和难句,这样一来,学生在自主学习时的困难就会显著降低。
4.科学纠错
仲清[28]发现纠错的方式对学生的焦虑水平有显著影响。对此,邓秀均[12]和刘娟娟[19]也对教师的纠错方式提出了新的要求。邓秀均[12]认为间接纠错能起到很好的效果,在学生回答错误时,大部分学生倾向于与同学们共同分析错误,得出正确的答案,部分同学认同请其他同学再回答一遍。由此可得,教师不直接纠正学生的错误,在一些情况下,对保护学生的自信心等有好的效果。刘娟娟[19]从口语的角度进行了解释,认为不少学生(尤其是年龄较大的学生或女生)在教师直接纠正自己发音时,会产生极大的焦虑感。为了缓解这样的焦虑,教师可以挑选合适的时机纠正必要的几处错误,从而既帮助学生提高,也迎合了学习者的心理。
5.合作式学习
陈柳羽[16]倡导合作式学习,将学生划分小组,在一种轻松愉快的氛围中学习,学生更容易提高自信、更加放松。Yan-hong[34]也认为合作学习的优点颇多。首先,合作学习可以使教师和学生更容易处于一种融洽的氛围中,同学们的相互帮助、观点的碰撞都能很好地帮助大家理解语言材料;其次,合作学习相对于课堂上的独自回答问题更能减轻学生的焦虑感,因为在该环境下,他们不必在意同学们的负面评价;再者,合作学习从侧面减弱了学生的竞争对立关系,在合作学习中他们不需要考虑考试成绩和结果,也就降低了紧张焦虑感。
6.多维度对学生进行测评
陈佳宜和刘慎军[35]对来华留学生进行了问卷调查,认为由于许多医学院校都将能否通过汉语水平考试与取得学位相关联,这样的考核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也造成了学生的焦虑情绪。对此他们指出,应根据多项考试成绩来综合判断学生的能力,例如将期末和期中的笔试或口试考核成绩按照一定的比例计入学生的最终成绩中,这样的考核更加可信,同时也可减少学生对某一特定考试的焦虑程度。
7.改变教师的角色
教师作为课堂的主宰,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学生对于汉语的感知和理解。多个研究[18][30]指出,教师不能仅仅“教书”,在对外教学的课堂上,他们也担任着示范者、心理辅导者和组织者的角色。示范者指教师对于二语学习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学生,汉语对多数留学生而言是一种交际的手段,学习并不是为考试做准备的。因此,教师就需要强调交流的畅通性,而较少强调学生的语调、语音上的错误。心理辅导者指教师应当承担引导学生培养良好心态的任务。学生在国外留学时难免会产生文化隔阂,如果处理得好,学生将很快适应异国的文化,找到身份认同感,反之学生则容易产生消极、不自信的心态。因此,教师需要及时地捕捉到不同学生的心态变化,加以疏导。组织者即课堂教学的主导人,课堂的氛围在很大程度上是因教师的表现而产生差异的,在对外教学的课堂中,如果课堂氛围轻松愉快,学生就更能培养出对汉语学习的兴趣,也学习得更有成效。同时,教师也应当适时地给学生提供机会表现自己,让他们更了解自己的能力,从而提高自信,降低焦虑感。
四、结语
外语学习焦虑是影响学业成功的一大因素,这一观念近年来已被多数学者接受。本文着重分析了汉语焦虑水平的影响因素以及应对措施,发现了以下问题:第一,近几年的汉语学习焦虑研究对象虽然较以往增加了不少国家的学生,但人数始终偏少,在一定程度上导致汉语学习焦虑领域指导性理论的发展停滞不前。第二,研究方法的创新性不强,多数研究基于FLCAS,但该量表是否适用于汉语学习焦虑仍有待验证。值得一提的是Luo[36]设计了一组可信度较高的汉语学习焦虑度量表(Chinese Language Learning Anxiety Scale),该量表针对汉语言的学生学习焦虑情况,对以后的研究有一定的借鉴意义。第三,许多研究都试图利用一次调查解决多个问题(学习者产生焦虑的背景原因、个性原因、环境原因等),事实上,这样的做法通常由于变量太多而无法在任何一个数据上达到非常可信的程度。因此,将来的研究应当针对单一因素进行更加系统的研究和分析,以求达到更好的效果。第四,Maclntyre和Gardner提出了具体情况焦虑(situation specific anxiety)[37],指学生在应对听、说、读、写等具体情况时的焦虑。由于留学生的国别不同,其学习水平与效果也参差不齐,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他们的焦虑水平,因此更多的实验研究需要在此方向上发展。
本文就国内近十年的期刊论文进行了分析,总结了关于汉语学习焦虑的起因和应对措施。不同于以往该领域的综述[38],本文对不同的因素进行了详细的分类探讨,因而有了更多具有启发性而全面的结果。由于汉语在国际上的重要性日益增强,越来越多的外国学生开始学习汉语,而焦虑是学习中不容小觑的问题之一,因而笔者呼吁更多的学者投入该领域的研究中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