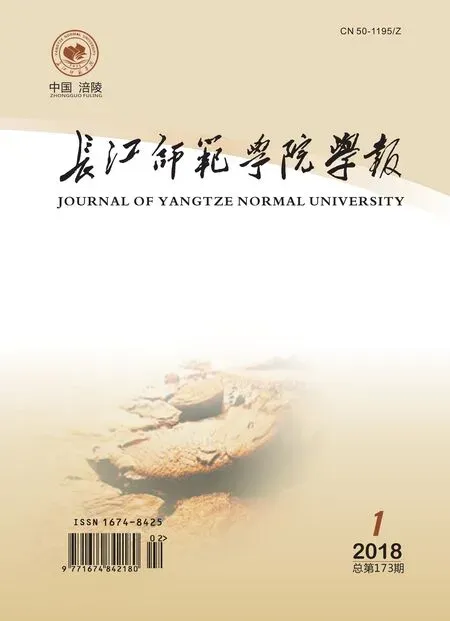先秦儒家礼教的当代价值
赵 胤
(河南省社会科学院 哲学与宗教研究所,河南 郑州 450002)
一、引言
由于在先秦,礼乐不分家,以此外生的乐教和礼教虽然在诸多方面都存在着差异,但两者均是一种教化的手段,且是相通并一起推行的,所以在具体回顾先秦儒家礼教思想之前有必要对“礼”与“乐”的关系进行澄清。
礼乐的功用,在《乐记·乐论篇》中有一段很是精辟的解读:“乐者为同,礼者为异。同则相亲,异则相敬。乐胜则流,礼胜则离。合情饰貌者,礼乐之事也。”[1]9《礼记·乐记篇》也云:“乐也者,情之不可变者也。礼也者,礼之不可易者也。乐统同,礼辨异。礼乐之说,管乎人情矣。”[2]1116由此可知“乐和同”而“礼辨异”,这是两者功用的差别。《乐记·乐论篇》继续说道:“夫乐者,乐也,人情之所不能免也。乐必发于声音,形于动静,人之道也。”[2]1143由此可知“乐”之“静”乃是源于人的生命本源的静,故其可使人心获得和易愉悦的感受,使人的内心趋于平和。在此种“自觉”地感受“乐”的过程中,人的生命本质即人的本心得以彰显、充盈,这样人就可以从喧嚣的尘世返回人的本质,从而克服内心的冲突和紊乱,达到与自身生命的和谐统一。故《乐记·乐化》中有言:“乐也者,动于内者也……乐主其盈……乐盈而反,以反为文。”[1]37所以“乐者为同,同则相亲”。“乐”作用于人心,使人产生与他人同宗同源的认同感,从而自觉地认同和维护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所以“是故,乐在宗庙之中,君臣上下同听之,则莫不和敬;在族长乡里之中,长幼同听之,则莫不和顺;在闺门之内,父子兄弟同听之,则莫不和亲”[1]39。“夫乐者,乐也,人情之所不能免也。”[2]1143“致乐以治心,则易、直、子、谅之心油然生矣。易、直、子、谅之心生则乐,乐则安,安则久,久则天,天则神。”[2]1139由此可见,在古人那里,人对音乐的需要是自然本能,是人的根本的生命欲求,因此音乐契合了人的本质,这也就是所谓的“乐化”,即“乐能化人,始至于善。乐可以正其心,则和易、正直、子爱、诚信之心油油然从内而生矣”[2]1139。故“乐”出自于人的心灵最深处,所以乐能感人,使善心生也,其功用在于和同。于此可见,乐教在国家治理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具体体现在圣王用音乐感人,使人们发自内心的安于本分,不做超越本分的奢望,促进人与自身生命的和谐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和谐,进而实现一个国家和谐。“礼”之功用在于“辨异”,也就是说礼教致力于区别差异、保证差异。由此可知礼乐之教本身就是为了达至一种“和而不同”的境界。“故乐也者,动于内者也;礼也者,动于外者也。乐极和,礼极顺,内和而外顺,则民瞻其颜色而勿与争也,望其容貌而民不生易慢焉。”[1]37“礼者,殊事和敬者也。乐者,异文者合爱者也。”[1]11接下来我们就从“礼辨异”出发具体来探寻一下“礼教”在辨异时所达至的那种和谐。
二、周代礼制
严格意义上的“礼”制萌芽自周代,主要有5种,即吉礼、凶礼、军礼、宾礼和嘉礼,此5种礼在《周礼》中有着详细的记载。周朝代商,并非只是简单的王朝更迭,如王国维在《殷周制度论》一文的开篇就说:“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3]231周人建国,乃是以制度为重,故王国维接着言“欲观周之所以定天下,必自其制度始矣。”[3]231周人一方面封土建君,创建一种人为的政治秩序,以取代部落酋长式之自然的政治秩序;另一方面确立宗法制度,将自然的血缘关系化入人为的政治关系之中,此即所谓周公制礼之说所代表之文化史意义。周人此一举措,就发生学角度来看,其本意乃是为了建立较有力之中央政府,但却透漏出一种以人为主的思想趋势,虽然此时这种人本主义乃是处在一种混沌的状态,属于不自觉而生,不过比起其“发生意义”,它的“本质意义”特别是其中对“人之地位的肯定”的那种人性自觉的精神成为春秋战国时期百家所以争鸣的一个重要条件。
在周代之礼背后所传达的乃是一种人本主义的精神,具体来说就是对人之地位的一种肯定。其实周代文化就是一种礼乐文化,故在现存的先秦文献中“礼乐”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周代的各种礼制主要载于《仪礼》《周礼》和《礼记》之中,故“三礼”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中国礼仪规范的渊源。“礼乐”背后所传达的那种人之自觉心和价值意识在春秋战国时期得以充分弘扬,所谓“礼辨异,乐和同”无疑是对“礼乐”精神内核及其功用的一种写照。
《乐论》所言及的“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群物皆别”[1]13,已将“礼乐”所要达至的目标清晰地表达了出来,而这一目标无疑就是诸子百家所渴望实现的目标。可由西周降至春秋,周公所建构的那一套礼乐制度却因社会经济的发展开始崩解,面对当时“礼崩乐坏”的时代大背景,诸子百家传承了周代以降的那种蕴藏在“礼”文化中的人性自觉意识,开始为寻求实现各自心目中的“乌托邦”而进行思想探索,其中对于“礼”的发掘和重新诠释最有建树的当属儒家,接下来我们就从孔子、孟子和荀子3个先秦儒家代表人物出发,以具体考察先秦儒家礼教思想的发展轨迹。
三、孔子释礼
周代被先秦诸子认为是一个礼乐文化的时代,孔子也不例外。他祖述尧舜,宗法西周,特别重视“礼乐”的社会功用,强调“礼乐”对于人们的“教化”作用。孔子指出:“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4]224这表明孔子已经把“礼乐”看作是天道的体现,正如他在《为政》中所指出的:“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4]15孔子认为,人君以法律及刑罚来约束民众,民众的遵从只是外在的,内心并未树立礼义廉耻的道德自觉性。以德治国,以礼教化民众则可以实现民众发自内心自觉地遵从及臣服,并且可以树立起全社会崇敬礼的风气。他还言:“不学礼,无以立”[4]230,“不知礼,无以立也”[4]]270……这些都足见“礼”在孔子那里的重要地位。
孔子致力于重建“周文”,但是支撑周礼背后的精神已然失去了其生存的土壤,故想要重建“周文”,并须重新诠释“礼”之内涵。基于这一点,他从新的时代精神出发对礼乐进行了新的解释:把巫师型的尧舜重塑为理性化的仁义之王,把宗教性的仪式加进理性化的内容,成为理性化的家(家族仪式)国(朝廷仪式)[7]。“礼”之观念实为孔子学说之始点。孔子处于春秋末期,深受周礼文化的影响,面对当时礼坏乐崩的社会现实,他以复兴礼乐文化为己任。他曾有言:“周监(鉴)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4]]36复兴与构建礼制社会是孔子的社会理想,而“以何立礼”则成为第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基于对人性的深刻洞察和对礼的形式化问题的反思,孔子援仁入礼、赋仁于礼[8]。孔子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4]30他以对人、对社会、对历史的高度责任感,努力构建起一个礼的意义世界,力图使礼成为人的终极信仰,鼓励人们超越自身的局限性去追求礼。因之,孔子提出的以“仁”为精神内核的礼“开辟了人的内在的人格世界,以开启人类无限融合及向上之机”[9]。
“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4]157由孔子所言的“为仁由己”我们可以知道,人的道德修养主要是靠自己来完成的,是个人的独立的自由意志的表现,并不受到别人或外界条件的影响。也就是说实践仁是无待乎外的,而是内在的,完全出于道德主体的自我选择。故孔子说:“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4]95“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仁矣乎?我未见力不足者也。”[4]49孔子的这些阐述足见“仁”并不远人,它是基于人的基本情感而建立起来的一套自省的切身的修养功夫,也是一种推己及人的胸怀。孔子就曾说:“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4]83
孔子在传统礼乐文化中发现仁,“引仁入礼、以礼释仁”赋予了“礼乐文化”一种新的内在价值。其思想系统乃是“以仁为本源,以礼为表征,仁礼合一”。在这个系统中,孔子承“礼”创“仁”,“仁是内在原则,礼是外在规范;仁是绝对的,礼是相对的;仁是常道,礼是变道”[17]。必须看到的是“仁”内在于人之生命体验,是道德主体的自主自由的活动,是人生境界不断提高的不竭动力。任何人只要愿意将其内化为自己生命的一部分,“仁”就实现了。“仁”作为修养工夫,包含“克己”与外在“复礼”两个方面,二者不可偏废其一,因为背后始终贯彻如一的乃是一种人性的自觉,故缺一不可,但孔子以降的儒家学派的继承人却逐渐偏离了“仁”之“礼”的原初轨道。
四、孟荀殊途
孔子以降的儒家学者将“仁”视为人区别于物的本质。当然,此处所说的人之本质并非是指人的身体或物欲,而是指人的道德理性。《中庸》引孔子的话说:“仁者,人也,亲亲为大。”[10]据此,我们可以这样说,“仁”就是“人”的社会属性。
从战国开始,“礼”完全毁坏[11],“礼乐”丧失了其本应具有的政治性和宗教性规定,而沦为享乐的代名词。当时的墨家就认为,在战国纷乱、百姓困苦的境遇下,统治者不应做礼教、乐教那种无用之事。墨子就曾言:“民有三患,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三者民之巨患也。然即当为之撞巨钟,击鸣鼓,弹琴瑟,吹竽笙,而扬干戚,民衣食之财将安可得乎?”[12]故其深信“乐”足以废事,而无利于天下,无利于天下之民,要提倡“非乐”。同时,“礼”也很自然地在其批判之列,单从墨家主张“节葬”可知矣。
在攻击“礼乐”作为外在享乐欲望的发泄途径时,战国诸家都在着力为礼乐文化重塑新的精神内核和外在形式,儒家更不例外,战国时期的儒家学者皆沿着孔子所开创的“仁”之精神的道路,同时发挥自己的个人想法来构建新的“礼乐”文化,为求实现儒家社会大同之理想,由此儒家内部出现了分裂,孟子和荀子为其典型代表,此二者虽源自同宗却最终走上了不同的道路。
孔子以“仁”释“礼”,孟子则提出性善论来补充此一学说。必须看到的是“无性善则儒学内无所归”[5]117。关于性善之说,具体乃见于孟子的“四端说”。“四端说”是对性善理论的重要阐释,《孟子·公孙丑上》有言: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由是观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有是四端而自谓不能者,自贼者也。谓其君不能者,贼其君者也。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达。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13]于此可见在孟子那里,价值意识内在于自觉心,人之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自觉皆为价值自觉,乃是德性之根源。仁义礼智皆根于心,孟子为道德之礼的内在性确立了心性论根据。由此我们可以知道,孟子所持为入学之重德精神,而不重视知识架构本身之问题,虽然也有政治思想,但是不难看出他所走的乃是“克己”之路,乃是要从礼制之内在精神出发,通过一种人心自觉来达至“礼”所要达到的终极目的,这一点从他的“民本说”以及“仁政”德治观念[5]136中可以得到进一步的证实。
荀子有别于孟子对礼教精神文化的阐发理路,对“礼乐文化”进行了一种新的归纳,并将之纳入社会秩序的规范、管理、分配的政治制度之中,并赋予其新的社会意义[7]。“礼者,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6]178故其之于“礼”的学说主要有两个方面:其一是性恶与师法;其二是君与礼,也就是他的政治思想。荀子认为人性本恶,他在《性恶篇》中说:“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6]434这似乎与孟子走向了对立,然事实上并非如此,二者乃是在不同的层面上所言,故孟子所言的性善与荀子所说的性恶并不矛盾。
不过,荀子从现实功利的角度来理解人性,自然更多的就会注意到人欲的泛滥,于是他接着说:“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然则纵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故必将有师法之化,礼义之道,然后出于辞让,合于文理,而归于治。”[6]434-435于此可见荀子要通过“师法”来克服人由于动物性所带来的祸端,故在他那里特别强调“复礼”,也就是外在的规范,“师法礼仪”皆生于圣人,由此礼制之用就是合于圣人之道以达至社会秩序的安定,具有强烈的现实意味,此一点在他的《礼论篇》中就可以略窥端倪:“礼起于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故礼者,养也。”[6]346于此处“礼”之“平乱”的要求可知荀子势必走上功利主义和权威主义的道路。这一点从其政治思想中亦可得到证实,特别是其“君”与“礼”的思想,在他那里“君”就是“道”,带有鲜明的权威主义色彩,他曾言:“君者,民之原也。”[6]234“道者何也?曰:君道也。”[6]238这些均可看作是其此一思想的佐证。然而也必须看到的是虽然荀子重法,但仍认为“人”重于“法”,其思想与法家仍有别,但是其实现儒家大同目标的途径却是主要从外在的“复礼”入手,突出“礼”的外在规范性,注重“礼”对社会以及个人的规范作用。
四、先秦儒家礼教的当代价值
由前面的论述可知先秦儒家的“礼乐文化”在原初状态所包含的具体内容,在时下人们的心中对其仍然存有相当的偏见,故首先的工作必然是“正名”,然后才能发现其合理的精神内核为当下服务。
综观历代以来对礼教的批判,皆带有“重破轻立”的倾向,在批判儒家的礼教之后,并未能在新的礼仪道德建设方面拿出独特的、卓有成效的方案来,未能建立一套新的礼教体系,未能建立一套规范人和整个社会的体系。有时候甚至导致这个领域的“真空”,旧的已被扫荡,新的尚未建立,使人们无所适从[14]。在为中国传统礼教正名的同时,我们有必要对其进行深刻的反思,考察它在内在精神和外在形式方面到底仍有哪些可以运用于当今社会之中,可以将之推行开来。
改革开放30年多来我国社会蓬勃发展,但同时也出现了利益分化、区域分化、阶层分化、领域分化、观念分化的态势,这种分化的态势影响着社会的和谐。而这又要归结到泛道德主义也就是主观主义的流行,由此而生的相对主义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社会道德的滑坡。当下的人们更多的是强调个人,也就是强调所谓的“异”,却忽视了“同”,在很多人的眼里,所谓的“同”更多的是和“专制”特别是泯灭“个性”联系在一起的[15],故在如何实现“求同存异”上,先秦儒家礼教思想的“礼乐文化”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实际上,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对国家乃至社会所要达至的目标,仍旧是一种未曾明晰、未曾统一的状态。尽管人类对自己的未来发展走向在认识上还不统一,但起码达成了对“人之地位”的充分肯定。但是当下的人们过于强调工具理性而忽视价值理性的内在发掘,同时又将价值理性空泛化,导致了价值理性成为无规定性的空洞言谈而使其走向了茫荡以至于无所归依。价值理性离开了现实,自然就会缺乏规范的建构,现实表现就是空谈心性和人文精神而不能落实。价值、意义本就不是能自存自明的东西,它必须发掘弘扬。
人的未来发展需要一种内在的精神支撑,否则久而久之,人性中固有的局限性必然会导致人们沦于欲念过多、身心涣散的状态,这种状态消解着一切礼制规范的严肃性和神圣性,导致对“礼”的僭越,社会混乱无序[8]。先秦“礼崩乐坏”就是这一状态的最终结果。故未来社会的发展必须与人文精神是内在统一的,但这一理想的实现必须要经过一个复杂的过程。
在当下,“礼”可以理解为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规范和准则,而儒家“礼教”背后的那种“仁”之思想可视作处理这些关系时表现出来的人格与价值追求,简单来说就是唤起人的道德自觉。这种唤起除了内心的情感共鸣外,“礼”制的外在形式也是必要的。在礼的内在的道德涵义(礼义)和外在的推行方式(礼仪)之间存在着这样一种关系:礼之为礼的根本在于其精神内涵,由内而外扩展开来,内心的情感自觉扩展至外在的符合于礼的规范的行为。但是,在这种道德自觉、情感自觉失落的情况下,如何唤醒人之内心的道德自觉呢?这仍是一个难以探讨到具体答案的问题。但不可否认的是,社会不能缺乏礼仪,人的言行也必须有一定的规范,在抛弃传统礼仪的同时,必须建立起适合国情的新礼仪,才能使社会得以平稳发展。其实,仅谈礼的内涵和价值,强调“仁”的内心自觉,在当代社会很难起到一种有效的规范作用。礼必须依附于一定的形式,这一形式就是具体的礼仪。礼仪是礼的载体,借助于一整套礼仪的长期推广和践行,礼在社会中起到一种规范和整合的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具体礼仪在推行过程中,必须防止其形式化。发展至近代的儒家礼教之所以失去了生命力,失去了其存在的土壤,之所以遭致近人的强烈批判,很大的原因就在于其形式化,在于其僵化的繁文缛节。在现代社会礼仪的推行过程中,必须以史为鉴,尽可能避免就礼仪论礼仪的形式主义倾向。在方法方式上,要注意避免强制性推广,尽可能以人们喜闻乐见的方式去传播、示范、教育,让人们自由自觉地把参与现代礼仪文化建设作为加强自身修养的目标。在道德人格的塑造上,当今社会应该有一个共同的标准,是与非、善与恶、美与丑的界限不可含混模糊。在具体仪节的实施方面,应充分尊重个人的主观意愿与各民族、各地域人群固有的风俗习惯,从实际情况出发。在仪式行为方面,朝着简便易行的方向前进,淘汰繁文缛节。在中国古代,学校是进行礼教的主体,教学内容根据年龄的不同而进行区分,具体包括“六艺”与“六经”。除此之外,还包括“六仪”:“一曰祭祀之容,二曰宾客之容,三曰朝廷之容,四曰丧纪之容,五曰军旅之容,六曰车马之容。”[16]现代礼教的内容应根据我国具体国情进行增减,构建起合理的教育体系。
此外,在先秦儒家礼教体系中,礼和法的关系一直很密切,尤其在荀子的思想体系中,更是一个礼法结合的完整体系。我国目前正处在社会转型时期,外在强行的法律与内在自觉的道德之间还存在一个宽大的空间,如何协调是当代社会治理和整合的一个关键。法律必须体现人文精神,成为引导人类未来走向的外在力量,这同时也是“法”未来发展的必然选择,故“法”必须契合人的内在道德要求而不能纯粹沦为外在的一种强制力,否则效果就会大打折扣。在当代社会的治理中,先秦儒家学者的思想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总的来看,先秦儒家礼教自身从开始就存在一定的缺陷,从而在后世的发展过程中走向形式化和极端化,以致遭到强烈的批判。但是,其蕴含的丰富的精神和内涵,为重建礼仪秩序而采取的方式,仍能为现世所吸取和借鉴,这也是礼教一直延续的一个重要原因——先秦儒家礼教确实在社会整合过程中起过相当大的作用。现代礼教的建立和推行,关键是与当代社会相适应,并有针对性地解决当代问题。在这个过程中,唤醒人内心的情感自觉与道德自觉仍是关键,但是礼也必须依附于一定的形式,依托于“礼仪”这一载体。具体礼仪的长期践行能够培养人的道德自觉。现代礼教的内容和形式应根据当代社会的具体情况,在扬弃历代礼教的基础上进行建构,以达到人格塑造和社会整合的目的。
[1]吉联抗.乐记译注[M].北京:音乐出版社,1958.
[2]郑玄注.十三经注疏(标点本)礼记正义[M].孔颖达,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3]王国维.观堂集林[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
[4]何晏注.十三经注疏(标点本)论语注疏 [M].刑昺,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5]劳思光.新编中国哲学史[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6]王先谦.荀子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1988.
[7]张法.礼乐文化:理解先秦美学特色的一个路径[J].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12):23-25.
[8]赖志凌,王江武.从《论语》中仁对礼的建构看孔子的仁礼关系思想[J].江西社会科学,2003(9):78-80.
[9]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1:61.
[10]王国轩.大学·中庸[M].北京:中华书局,2007:95.
[11]陈戍国.先秦礼制研究[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1:400.
[12]吴毓江.新编诸子集成·墨子校注[M].孙启治,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3:380.
[13]十三经注疏(标点本)孟子注疏[M].赵歧,注;孙奭,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93.
[14]顾希佳.礼仪与中国文化[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5.
[15]赵毅衡.礼教下延之后中国文化批判诸问题[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143.
[16]张自慧.礼文化的价值和反思[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8:239.
[17]颜炳罡.论孔子的仁礼合一说[J].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2):52-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