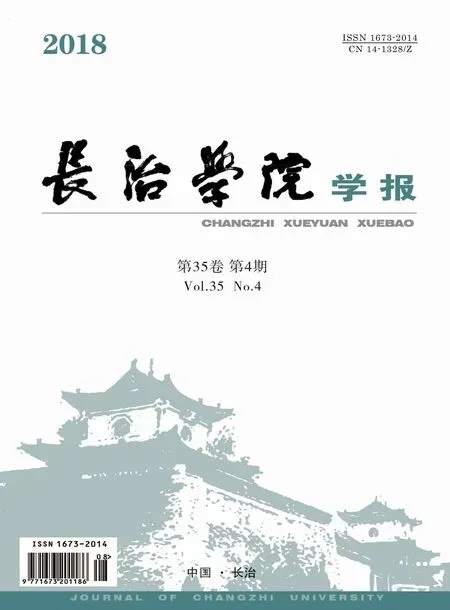论唐人小说之开山
——《古镜记》的艺术特色
谭力铭
(华中师范大学 文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9)
中国古代小说的发展史源远流长,自先秦庄子以来,“小说”名实历代变迁。唐代后,唐传奇逐渐形成,作为当时流行的文言小说创作形式,作者大多以记、传作为篇名,以史家笔法记奇闻异事。对于唐传奇的艺术成就和历史地位,鲁迅在20世纪初所作《中国小说史略》中说:
小说亦如诗,至唐代而一变,虽尚不离于搜奇记逸,然叙述宛转,文辞华艳,与六朝之粗陈梗概者相较,演进之迹甚明,而尤显者乃在是时则始有意为小说。[1]
这段评价至今已成为学界对唐传奇历史地位的定评。与六朝志怪相比较,唐传奇不仅在篇幅上更为恢弘,在故事情节上也比平铺直叙的志怪小说更加变化曲折。最重要的是,唐传奇的创作者开始有意运用虚构手法来创作小说,甚至在小说中主动添加自己思想,这正促进了中国古代小说向真正成熟迈出了关键一步。
作为唐传奇的开山之作,王度《古镜记》在整个唐传奇发展历史中都具有不可替代的特殊价值和举足轻重的地位。
古今小说纪镜异者,此为大观矣。其事有无,姑无论。即观其侈陈灵异,辞旨诙诡,后人模拟,汗流莫及。上承六朝志怪之余风,下开有唐藻丽之新体。洵唐人小说之开山也。[2]
汪辟疆在其校录的《唐人小说》中为《古镜记》作注,对《古镜记》给予了极高评价。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论及唐传奇时,也首述《古镜记》。这篇唐传奇“开山之作”虽然还没有达到盛唐唐传奇名篇的艺术水平,但是与此前的六朝志怪相比,已经前进了一大步,其中所包含的叙事艺术、意象塑造等艺术特色,都在此后更为成熟的唐传奇作品中有所留存,并对后来的小说创作发挥着重要影响。
一、新颖灵活的叙事艺术
作为叙事文学的一种,唐传奇盛行时期正是中国古代小说发展历史上叙事艺术得到快速发展的重要阶段,《古镜记》作为唐传奇早期的重要篇目,较之前代小说出现了新的叙事技巧。虽然叙事学在20世纪中叶才诞生于西方学界,但是其理论方法在唐传奇盛行时已经抽象存在于当时小说作品的艺术现象中,因此用叙事学理论分析这些作品应属可行。
(一)第一人称叙事视角
在《古镜记》诸多叙事技巧中,最为鲜明的叙事特色就是在中心人物叙事上大胆尝试第一人称叙事视角。在唐传奇之前的小说中,中国古代小说家大多采用全知叙事视角。而王度作为《古镜记》的创作者,将自己本人纳入到创作的故事中,用第一人称叙自己所见所闻,突破了前代小说全知叙事的樊篱。
在小说中,王度以古镜为经,时间为纬,依次叙述自己得到古镜后所经历的一系列奇闻异事。从古镜收服化为人形的老狐开始,历经神剑、胡僧、蛇妖等诸多异事。虽然在故事整体情节中,叙事者除了王度外,还有薛侠、豹生、张龙驹和王勣等人的第三人称叙事,但是以王度为主人公的第一人称叙事,仍是整篇故事的主体。
晋左军琅邪王凝之,夫人谢氏,顿亡二男,痛惜过甚,衔泪六年。后忽见二儿俱还,并著械,慰其母曰:“可自割,儿并有罪謰,宜为作福。”于是得止哀,而勤为求请。[3]
以《王凝之》为例,六朝志怪篇幅短小,作者在主观创作意愿上没有采用第一人称叙事的意图,而且篇幅也局限了数次更改叙事角度的创作空间。
王度之所以有意识以“我”的口吻贯穿《古镜记》始末,目的全在于使故事更具有整体感和真实感,将创作者放入故事世界中,易于使读者相信故事确出自于真人真事,这恰恰符合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唐传奇“始有意为小说”的评论。由于文学作品的叙述视角选择,能够直接影响到读者对文学作品的接受效果,因此王度用第一人称叙事视角将自己代入故事世界,使自己不仅是故事的讲述者,也是故事的参与者,并通过对故事细节的精雕细琢,实现了促进故事向真实事实靠拢的创作意图。
(二)复杂的叙事系统
虽然《古镜记》以贯通全篇的第一人称叙事视角为主,但是在第一人称叙事视角之外还存在一个复杂的叙事系统,构成《古镜记》复杂叙事系统的第一个方面就是叙事主体多元化。《古镜记》共有三类叙事主体和六个“讲述者”。第一类叙事主体即王度,第二类叙事主体即侯生、豹生、张龙驹和王勣,第三类叙事主体为镜精紫珍,其中以王度的第一人称叙事视角最为重要,全文正是通过王度才引出其他两类叙事主体。
多元叙事主体的运用体现出王度从容不迫、有条不紊的材料驾驭功力,也使小说比六朝志怪多出新的曲折情节,满足了读者阅读新奇曲折故事的心理。同时,《古镜记》从多人角度讲述古镜的神奇,每个主体的叙事都在相互印证,王度用他人叙事弥补故事本身的荒诞不经,进一步提高故事的真实感。
多元叙事主体除了拓展小说篇幅,也通过拓展篇幅带来了丰富情节,塑造出各个人物不同的性格,唐传奇以前小说并不具备这一点。如王勣执意游览山河大川前,兄弟二人的对话:
度止之曰:“今天下向乱,盗贼充斥,欲安之乎?且吾与汝同气,未尝远别。此行也,似将高蹈!昔尚子平游五岳,不知所之。汝若追踵前贤,吾所不堪也。”
便涕泣对曰:“意已决矣,必不可留。兄今之达人,当无所不体。孔子曰,匹夫不夺其志矣。人生百年,忽同过隙。得情则乐,失志则悲。安遂其欲,圣人之义也。”[3]
从中可见兄弟二人的手足之情,也塑造出王度的仁厚和王勣的洒脱,虽然着墨不多,但人物形象鲜活灵动,这也正是中国古代小说发展史上叙事艺术的一次极大进步。
构成《古镜记》复杂叙事系统的第二个方面就是全文具有多重叙事时序,基本颠覆了中国古代小说在唐传奇前习惯采用的连贯叙述。清代刘熙载在《艺概·文概》中概括叙事有“顺序”、“倒叙”、“连叙”、“补叙”、“插叙”等诸多叙事技巧,王度在《古镜记》中实现多重叙事时序的整体调度,正是通过灵活运用这些叙事技巧,主要是通过倒叙、顺序、补叙和插叙的巧妙变化。《古镜记》的叙事时序相较无明显时序的六朝志怪,显得更加复杂繁复,但是整个故事时间却又和谐统一,这也是《古镜记》的一大叙事亮点,也被唐传奇以后的中国古代小说所普遍借鉴。
(三)串联式叙事结构
《古镜记》还有一大叙事特色在于新颖的叙事结构,相较六朝志怪单调的叙事结构,全文围绕古镜这一中心,将独立的小故事串联成长篇。小说场景变换极快,一个故事结束立刻进入另一个故事,丰富的场景沿着时间不断转换,构成了《古镜记》的串联式叙事结构,迥异于唐传奇前的中国古代小说叙事结构。
虽然《古镜记》的叙事结构还未呈现出成熟唐传奇程式化、板块状的特点,也没有形成模式化的叙事逻辑,但是《古镜记》串联式叙事结构已经具备了依靠时间推进故事情节的简单逻辑。故事被串联起来后,不仅篇幅大增,而且不同角度、不同时间、不同地点、不同情节的故事被王度有机组织在一起,使得全文产生了连贯、对比、联想、衬托、悬念等联系,增强了对读者的吸引力。即使故事与故事之间缺乏必然联系,但鉴于故事中心始终存在,因此各个小故事并没有跳出小说整体框架,反而形成了类似于现代蒙太奇艺术的跳跃式美感,并且在故事与故事之间产生出大段留白,这些留白调动起读者对古镜已被叙述故事之外的联想,提升了《古镜记》的整体可读性。
对于《古镜记》率先使用的串联式叙事结构,因其具有开创意义的独特性而被后世唐传奇广泛借鉴,并由此生发出更多更复杂的叙事结构。唐传奇之后,串联式叙事结构仍被后世小说所借鉴,如《西游记》、《镜花缘》等代表了明清小说高峰的著名作品,细品其全书结构,依旧可以发现这些小说的创作者在布局全书结构时,运用到了串联式叙事结构。
二、含义深远的意象塑造
论及《古镜记》在六朝志怪基础上的创新,还必须提到其一大艺术特色,即全文中存在的大量意象,运用意象是《古镜记》超越六朝志怪相当关键的一点。在六朝志怪中,奇异事物基本只是被叙述对象,但是从《古镜记》开始,小说中出现的特殊事物大多包含有本身原义之外的特殊含义或情感。如全文最为关键的“镜”,又或是被古镜降服的妖物,这些都是寄托了创作者王度特殊思想或情感的意象,分析这些意象,对深刻理解《古镜记》的内在思想极具价值。
(一)“镜”意象
作为《古镜记》的故事核心,“镜”意象贯穿全篇,小说以“镜”为线索,串联起十余个与镜相关的奇闻异事。《说文解字》注曰:“镜,景也。景者,光也。金有光可照物谓之镜。”可见“镜”在东汉时期就已经具有“照物”功能,而将“镜”作为小说叙事对象,目前最早可见于托名汉代东方朔的小说《神异经》。在诸多小说之“镜”中,“镜”的功用包括了伴侣、信物、神器等不同类型,而《古镜记》就是借用了“镜”作为神器的功用。
“镜”作为神器,往往被用于祛除邪魅、降服妖魔,当镜面映照到妖物后,妖物就会现出原形,而“镜”的神器功用,就是由它“照物”功能附会而来。“镜”的照妖辟邪功用源自于中国漫长神秘文化,与早期巫术、原始宗教,以及后来的佛、道两教皆有密切联系。从功能来看,《古镜记》中的古镜是古代镜巫术的集大成者,既可驱邪除妖、治病救人,也可平定风浪、预测未来,甚至镜中还有镜精紫珍存在,堪称镜子神异功能的一次总结。在中国古代,镜子作为贵金属制成的生活奢侈品,普通百姓很少有机会接触到镜子,因此镜的功能在百姓口中被无限夸大。又由于在中国传统道教思想中,一直有着“剑”、“镜”、“印”的观念,三者共同构成道家传统意义中的常见法器,而佛家常用“镜”作为故事里人性善恶的试金石,在佛道两教的宣扬下,“镜”逐渐成为市井百姓口头讲述中常见的神异载体。而“镜”作为光的反射物,在道教朴素的辩证思想中,光与暗相对应,阳光更是至阳至正的存在,正是“阴”属性妖魅的克星,而能够反射光的镜子,自然成为了可以照妖驱邪的法宝,并最终形成了中国古代小说中的“神镜”。
镜横径八寸,鼻作麒麟蹲伏之象。绕鼻列四方,龟龙凤虎,依方陈布。四方外又设八卦,卦外置十二辰位而具畜焉。辰畜之外,又置二十四字,周绕轮廓。文体似隶,点画无缺,而非字书所有也。[3]
《古镜记》在对镜子的形制描述中点出了古镜上“麒麟”、“龟龙凤虎”、“八卦”等细节,“麒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瑞兽,“龟龙凤虎”是四方神兽,而“八卦”是上古圣人伏羲所作,这些细节更加证实了古镜就是可以照妖驱邪的神器。综述前文,“镜”意象在《古镜记》中依据中国传统文化中镜子作为神器的功用,表现出照妖驱邪的阳属性含义。
除了已有可以照妖驱邪的阳属性神器含义,古镜还因小说中的特殊形制和隐现的特殊时间,被王度赋予了“天命象征之物”这层含义。从形制而言,古镜造型独特,横径八寸,细节有“麒麟”、“龟龙凤虎”、“八卦”等,其形制与天地日月相对应,暗合天道。中国古代相信天象与人事关系紧密,天象变化可以预示人间吉凶。文中古镜与日食相连,正反映了古镜乃日月之光在人间物体上的投射,由此也可以引申为象征天道。同时古镜在隋炀帝大业七年五月被王度所得,到大业十三年七月十五日又从王度手上消失,根据故事中情节推断时间,第一次失镜为西魏亡国、北周建立之时,第二次失镜正值隋末乱世的开端,这些都预示着世运昌则古镜显,世道乱则古镜隐,古镜与国运相连,恰恰显示出古镜是天命象征之物的这层内涵。
(二)动物意象
王度在《古镜记》中运用到的意象除了最为核心的“镜”意象,还有在故事中作为“镜”意象对立面出现的一系列动物意象。这些动物意象包括狐狸、蛇、蛟、鸡、黄鼠狼、老鼠、守宫等,由于《古镜记》尚未脱离六朝志怪“谈鬼述异”的遗风,因此其中故事仍为神异之事,这些动物意象即是民间百姓口耳相传的妖怪。
道教思想中,存在有“物老则为妖”的观点,而各种动物自然就成为了妖怪原型的来源,将人的智慧和特性附加到动物的外形上后,就形成了“妖”。“妖”显出特异在于动物身体内拥有人的智慧和特性,又或添加一些奇特能力,但是究其根本,妖怪依旧脱离不了人的思想行为。就如宝镜最先除去的千年老狐,虽然作为妖怪,依旧难逃婚姻不顺、被人胁持等命运安排,无非是在封建社会中常见的被压迫女性的个人经历外再套上一个神镜降妖的故事外壳。又如猿妖、龟妖,则是一副山林隐士的形象,黄鼠狼、老鼠、守宫三妖也无非是乡间强占妇女的地痞强盗。
虽然《古镜记》照妖驱邪故事外壳下依旧是在讲述人事,但是加上“古镜降妖”的故事外壳后,考虑到“镜”意象,不管是从古镜作为阳属性神器的含义出发,还是从古镜是天命象征之物的角度出发,被古镜降服的妖怪只能位于“正”的反面,哪怕如从未害人的千年老狐鹦鹉,依旧未能逃脱被古镜惩处的命运,只能说明在王度的构思中,《古镜记》中的动物意象始终都是阴属性的反面形象,是天命笼罩下秩序社会的破坏者,动物意象所具备的含义,正是古镜意象的对立面,因而在面对古镜这一天命神器时,必然都会被降服,并受到惩处。
三、结语
《古镜记》作为唐传奇开山之作,正如汪辟疆先生所言,“上承六朝志怪之余风,下开有唐藻丽之新体。”如果将小说中单个小故事独立出来看,与六朝志怪的区别并不是很大。但是当王度以古镜为核心,将这些单个小故事贯穿起来后,《古镜记》的篇幅和情节就已远远超越了六朝志怪的传统模式。
在叙事艺术上,王度的大胆尝试让《古镜记》对于读者而言,拥有了更丰富的阅读趣味,而意象和思想的注入,使小说开始在表层故事拥有更深刻的内涵,这是对单纯“谈鬼述异”的六朝志怪又一新的超越。
从整个中国古代小说发展史来看,王度在艺术手法上为此后古代小说创作开辟出一条新的路径。从现代叙事学角度来看,王度创作《古镜记》时,虽然并不存在现代叙事理论和方法,但是他表现在小说中的艺术现象,已经可以证明《古镜记》具备了现代叙事艺术的某些特征,而这些艺术特征一直被中国古代小说创作者们所模仿和借鉴。
虽然《古镜记》的艺术手法相比盛唐时代已经成熟的唐传奇作品还显得有些浅陋,但是因它对前代小说创作的突破和在整个中国古代小说发展史上的地位,仍具有十分重要的文学研究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