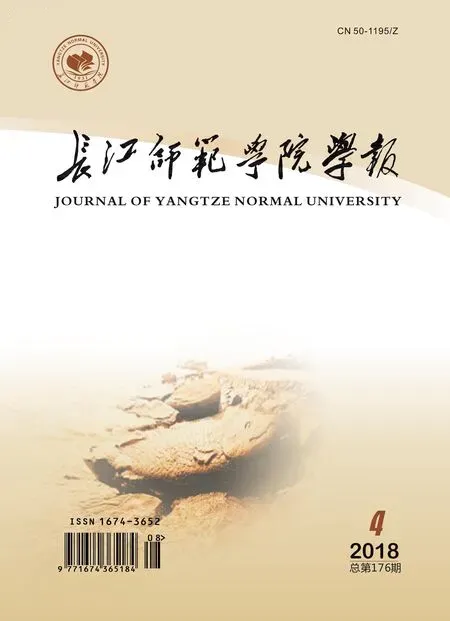天人合一视角下张载的成性论探析
姚军波
(陕西国防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思政部,陕西西安 710300)
张载哲学尤其是代表其晚年思想的《正蒙》一书读来艰深晦涩,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他所提出的一系列新的哲学范畴、基本命题和原理,这些哲学范畴、命题和原理的提出旨在整合“性与天道”,因此它们就同时关涉着天和人,这就使得张载哲学变得异常复杂。在中国哲学史上,张载首先明确使用了“天人合一”四字,他的思想也无不彰显着天人合一的思想,也就是说张载的整个思想体系都贯穿着将天与人看作是相即不离之关系的思维方式。本文拟在天人合一的视角之下尝试对张载的成性论进行初步探析。
一、成性论的宇宙论根据
汉唐以降,佛老异说大行其道,其形而上的思辨理论挑战着儒家学说的地位,儒者一方面“信其书,宗其道,天下靡然同风,无敢置疑于其间”[1]5;另一方面又“知人而不知天,求为贤人而不求为圣人”[1]386。面对此种形势,张载并没有“以遗言附会解之”,而是“自立说以明性”,以此对佛老异说的挑战进行了回应,并对“陋儒”之偏见进行了批判。
张载想要“自立说以明性”,就必须首先从宇宙论上对佛老的理论进行回应、批判,同时也必须从宇宙论的层面为自己所要重新建构的人性论寻找根据。质言之,人性论必须建构在宇宙论上。这里所说的宇宙论既包括宇宙本体论,也包括宇宙生成论。前者解决的是宇宙存在的原因及其根据的问题,后者解决的是宇宙的来源问题。
“形而后有气质之性,善反之则天地之性存焉。故气质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1]23张载认为人性可以划分为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两者并非是横向并列关系,而是一种纵向超越关系。只要“善反”,气质之性就可以变化为天地之性。人性论上的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反映在宇宙论上表现为太虚与气的关系,“合虚与气,有性之名”[1]9,“性其总,合两也”[1]22。“张载所谓‘合两’之‘两’,是就‘性’的内在结构分为两个层面而言,是指‘合虚与气有性之名’中的‘虚’与‘气’,或‘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而并非指物性与人性。”[2]“性的内在结构”就是指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两个层面,“虚”指太虚,“气”指阴阳二气。这就是说,天地之性根源于太虚,气质之性则源于阴阳二气的交感聚合。
太虚是指什么呢?“太虚无形,气之本体。”[1]7这里的“太虚”是指气的本然状态,还是指万物存在的原因与根据呢?张载认为“非有异则无合”,就是说同质的东西是不能够相合的。这就表明,太虚与气是一种异质关系,是两个不同的事物,“合虚与气,有性之名”[1]9。所以,太虚并不能等同于气,它并不是指气的本然状态,而只能指万物之所以存在的原因和根据。“由太虚,有天之名。”[1]9这里将太虚与天的地位相等同,更可以佐证太虚的确是作为万物存在的原因和根据的那种本源、本体。“虚者天地之祖,天地从虚中来。”[1]326这里明确地认为太虚就是天地万物存在的本源、本体。同时,张载认为太虚也是道德价值的本源、本体,“虚则生仁,仁在理以成之”[1]325。“天地以虚为德,至善者虚也”[1]326。清儒王植在《正蒙初义·臆说》中指出:“盖张子以太虚为性命之原,万物之本,故触处皆见此意。”王植不仅肯定了太虚作为万物的本源、本体,同时指出它也是道德性命的本源、本体。换句话说,太虚既是宇宙本体,又是价值本体。气则是构成万物的材质,“游气纷扰,合而成质者,生人物之万殊”[1]9。同时,气因为可以分为阴阳,故又是万物得以生化的动力所在,“其阴阳两端循环不已者,立天地之大义”[1]9。“立天地之大义”表明在张载的气化思想中也存在着现实的人伦关怀,这同太虚作为道德价值的本源、本体是一致的。这是宇宙本体论层面的太虚与气的关系,太虚是形而上的本体,气则是形而下的,前者是后者存在的原因与根据。
此外,太虚与气的关系还被张载表述为“太虚即气”,这又如何解读呢?由于太虚与气并不是两个相同的事物,这里的“即”字就不可能是“就是”的意思,它表示“相即”“不离”的意思。“其实,‘太虚即气’命题的意义并非隐晦不明,它显然是指‘合虚与气’、‘太虚不能无气’。”[2]也就是说,太虚与气可以相合,太虚不能够离开气而存在。这里的问题是,太虚作为气之本体,只能说气依赖于太虚,怎么可以说太虚不能够离开气呢?这岂不是消解掉了太虚作为本体的独立性了吗?“气之聚散于太虚,犹冰凝释于水,知太虚即气,则无无。故圣人语性与天道之极,尽于参伍之神变易而已。诸子浅妄,有有无之分,非穷理之学也。”[1]8-9原来,张载借助于“太虚即气”的命题是为了反对佛老的那种“有有无之分”的体用殊绝的理论。这个“太虚即气”的命题表现出了宋儒体用相即、体用不二的思维方式,那么太虚与气如何“即”呢?这只能在宇宙生成论的层面上讲。也就是说,在宇宙生成论层面太虚与气是一种相即不离的关系。不仅气不能够离开太虚,太虚同样不能够离开气。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太虚与气是一种体用关系,而非生成关系,张载明确否认了“虚能生气”说:“若谓虚能生气,则虚无穷,气有限,体用殊绝。”[1]8认为若如此则同老子“有生于无”之说无异,“不识所谓有无混一之常”。因此,虽然“太虚即气”是宇宙生成论层面的命题,但却不能将虚气关系径直视作生与被生的关系。那么,太虚又是如何化生万物的呢?由宇宙生成论层面太虚与气的关系可知,两者在化生万物的过程中应是伴随始终的。“太虚本体是宇宙的最高实在、终极根源和主导力量,而气则是万物得以生成的基质、材料和活力。”[3]这就是说,太虚与气在化生万物的过程中是缺一不可的,太虚为万物的生成提供原因和根据,气则为万物的生成提供形质、质料和动力。万物的生成是太虚与气共同作用的结果。
宇宙论层面的太虚与气的关系落实到人性论上则表现为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的关系。“太虚无形,气之本体”的宇宙本体论表明,对于气质之性而言,天地之性是一种体用、本末关系,亦即纵向的超越关系。同时,“太虚即气”的宇宙生成论则表明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同时是相即不离的关系。这就保证了气质之性向天地之性超越的同时不至于蹈虚,同时也确保了在相即的同时不至于滞着。这就为气质之性提升至天地之性也就是成性提供了宇宙论上的依据。
二、成性论的实践工夫
“横渠工夫最亲切。”[1]345张载不但在宇宙论上奠定了成性的根据,同时提出了使后学倍感亲切的成性的道德实践工夫。成性之“成”作何解呢?性不是人本来就有的吗?又如何言及成性呢?“是以此‘成’是工夫的成、彰著的成,不是存有的成,不是‘本无今有’的成。”[4]538所谓成性,并不是要否定掉固有的人性,而是指由气质之性向天地之性的提升。值得强调的是,在人性中,气质之性与天地之性是一种共存的关系,而非并列的关系。说其共存,是因为气质之性与天地之性同处于“一个世界”,它们是相即的关系;说其非并列,是因为气质之性是实然态的,天地之性是本然态的。因此,两者只能是一种纵向的超越关系。
张载的成性论来源于《易传·系辞》:“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其原意是说成道,在张载处则被转化为了成性①“太虚”一词最早见于《庄子·知北游》:“外不观乎宇宙,内不知乎太初,是以不过乎昆仑,不游乎太虚。”这里是在空间的意义上讲的。成书于西汉的《黄帝内经·素问》曰:“太虚廖廓,肇基化元,万物资始,五运终天。”“太虚”一词在张载处则既是宇宙本体,又是价值本体,论述详见下文。“太虚”的这一本体意义正是建立在空间义与本原义基础之上的。。张载说道:“性未成则善恶混,故亹亹而继善者斯为善矣。恶尽去则善因以成,故舍曰善而曰‘成之者性’也。”[1]23亹亹,作“勤勉不倦”义讲;舍,作“不”义讲。“恶尽去则善因以成”中的“成”字,依牟宗三先生校改为“亡”字,作“无”义讲。“善恶混”是就人性的现实状态而言,这种状态是实然态的气质之性的呈现,它既可为善,亦可为恶,意在强调气质之性非纯然至善。因此,成性并不是就性体自身而言,否则就成为了“本无今有”之成。张载认为,人在成性之前处于一种“善恶混”的状态,勤勉不倦地“继善”就会“恶尽去”。善与恶是一种对待关系,“恶尽去”则善之名也无以言、无以立。所以,不可称之为“善”而应称之为成性。这是理论地言之,落实到成性的具体实践则表现为“善反”和变化气质的工夫,也就是由气质之性向天地之性的提升、超越。
“天所性者通极于道,气之昏明不足以蔽之。”[1]21“天所性者”指的就是天地之性,它直接与道相通;“气之昏明”指的是气质之性,“禀气有昏明,则知能有偏全,而一曲之诚即天之诚,故‘乍见孺子’之仁,‘无受尔汝’之义,必发于情,莫能终蔽也。”[5]因此,气质之性并不能阻止天地之性的显现。这其实是在说天地之性相对于气质之性的超越性。“性者万物之一源,非有我之得私也。”[1]21“性则宽褊昏明名不得,是性莫不同也。”[1]330这是在说天地之性的普遍性,它非人力所能私有,气之“宽褊昏明”都不足以说明天地之性。天地之性根源于太虚本体,因此,“性于人无不善。”[1]22它是超越了具体的善恶之对待的纯然至善。相对于天地之性,气质之性则可善可不善。“有天生性美,则或能孝友廉节者,不美者纵恶而已,性元不曾识磨砺。”[1]264“天生性美”“不美者”均指气质之性。这里的“孝友廉节”“纵恶”应被视作一种可能、倾向,而不可以认为是一种实然的现实行为、状态。因此,此句意应为:人所禀之性美,就可能会孝友廉节;所禀之性不美,就可能会纵恶。气质之性的美与不美、善与恶只是一种潜质、可能,它并不就必然地转化、呈现为实然的善恶之行为。张载也把气质之性称为“习俗之气性”:“气质犹人言性气,气有刚柔、缓速、清浊之气也,质,才也。气质是一物,若草木之生亦可言气质。惟其能克己则为能变,化却习俗之气性,制得习俗之气。”[1]281人的气质之性有刚柔、缓速、清浊之分,而且它同时表现在“物性”上。也就是说,气质之性同天地之性一样,均为人性与物性所共有。
气质之性何以会有善与不善之分呢?因为它来源于阴阳二气的交感聚合。“天性在人,正犹水性之在冰,凝释虽异,为物一也;受光有小大、昏明,其照纳不二也。”[1]22“天性”就是指天地之性,天地之性存在于人,就像水性之存在于冰一样,人虽然有形体之别,就同冰与水有凝释之异一样,其天地之性却是一样的。每个人因形体的不同而表现出小大、昏明之不同,这就形成了气质之性。“形而后有气质之性,善反之则天地之性存焉。故气质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1]23气质之性是在人禀受了形体之后形成的,而君子对于气质之性是不以为然的。“大凡宽褊者是所禀之气也,气者自万物散殊时各有所得之气,习者自胎胞中以至于婴孩时皆是习也。”[1]329气质之小大、昏明不可以直接认作恶,善恶与否取决于人的“习”,因此它可善可恶。“盖人受形体之限,不能不有气质之偏。性体之不能呈现,或时有微露而不能尽现,皆气质之偏限之也。如是,遂有‘气质之性’之一义。”[4]这就揭示出了气质之性不可回避的性质,它限制着天地之性的显露。正是由于气质之性可善可恶,它就有可能向实然态的善恶之行为过渡、转化。气质之恶必然要被克服、转化,气质之善也要进行“变化”,因为它尚非纯然之至善。可见,气质之性正是人所要克服的。“人之刚柔、缓急、有才与不才,气之偏也。天本参和不偏,养其气,反之本而不偏,则尽性而天矣。”[1]23虽然气质之性有刚柔、缓急、才与不才之偏,但只要“善反”就可以“尽性而天”,也就是提升为天地之性。
在宇宙论上,万物的生成是太虚与气的共同作用,而非气的单方面气化流行的结果,万物还要以太虚作为终极根源;在人性论上,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是一种体用、本末关系,是一种纵向的超越关系,天地之性高于气质之性。所以,“善反”是沿着宇宙本体论的超越的向度,而非宇宙生成论的回溯的向度。“所谓‘善反’,也就意味着对实然气质之性的一种超越,正是在这种以‘反’为形式的超越中,天地之性才得以呈现。”[6]这个“善反”也就是变化气质的工夫。
“变化气质。孟子曰:‘居移气,养移体’,况居天下之广居者乎!居仁由义,自然心和而体正。更要约时,但拂去旧日所为,使动作皆中礼,则气质自然全好。”[1]265张载认为孟子所说的“居移气,养移体”就是指变化气质,人的行为均符合于礼的要求,“则气质自然全好”。“人之气质美恶与贵贱夭寿之理,皆是所受定分。如气质恶者学即能移,今人所以多为气所使而不得为贤者,盖为不知学。”[1]266又说:“但学至于成性,则气无由胜,孟子谓‘气壹则动志’,动犹言移易,若志壹亦能动气,必学至于如天则能成性。”[1]266人的气质之善恶,均是“所受定分”,此处之“善恶”,应该是指可善可恶的一种潜质、可能,而不是指现实地呈现为善恶的行为。而气质恶者通过学习就可以转化为善。张载进一步指出,“今人所以多为气所使而不得为贤者”的原因正在于“不知学”。这里,张载强调了“学”对于变化气质的重要性,认为学习就能够达到成性的目标。“为学大益,在自求变化气质,不尔皆为人之弊,卒无所发明,不得见圣人之奥。”[1]274为学的益处就在于变化气质,变化气质就是要改变所禀受气质的猵狭的一面。可以看出,张载将“学”作为变化气质的方式。“气者在性学之间。”[1]329“苟志于学则可以胜其气与习,此所以褊不害于明也。”[1]330他将“学”定位在了气质之性与天地之性之间,通过学习就可以克服气质之性猵狭的方面。这样,也就有了成性的工夫可言。
那么,所要“学”的内容是什么呢?张载认为需要学“礼”。“知则务崇,礼则惟欲乎卑,成性须是知礼,存存则是长存。知礼亦如天地设位。”[1]191成性必须学礼、知礼。“礼所以持性,盖本出于性,持性,反本也。凡未成性,须礼以持之,能守礼已不畔道矣。”[1]264张载想用礼对人的行为进行规范,以此达到成性的目的。学礼、知礼并不是要限制人的行为,他认为礼源于人之性,“盖礼之原在心,礼者圣人之成法也,除了礼天下更无道矣”[1]264。张载不仅将成性落实为变化气质的道德实践工夫,还指出了以学“礼”作为变化气质的方式。
三、成性论的目标指向
张载既在宇宙论上为成性的可能奠定了基础,又在具体落实上找到了切实可行的实践工夫。那么,张载为什么要讲成性呢?换句话说,成性的目标是什么呢?“君子之道,成身成性以为功者也;未至于圣,皆行而未成之地尔。”[1]27张载认为,君子之道以成身成性为目标,达不到圣人的境界,就只能说仍是行于途中而已。也就是说,成性的目标最终是要达到圣人的境界。张载居横渠之时,“学者有问,多告以知礼成性变化气质之道,学必如圣人而后已,闻者莫不动心有进”[1]383。知礼成性变化气质,最终还是以成圣作为归宿。
宋儒普遍有着浓重的担当意识,他们认为大道沦丧已经一千余年,“自孔孟没,学绝道丧千有余年,处士横议,异端间作,若浮屠老子之书,天下共传,与六经并行”[1]4。他们自觉地担起了“传道”的大任。张载就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使命自任。所以,他勉励人们要成贤成圣,并指出这是人之性分使然,“贤人当为天下知,圣人当受命。虽不受知、不受命,然为圣为贤,乃吾性分当勉耳”[1]310。
张载还指出了成圣的具体阶段,“由学者至颜子一节,由颜子至仲尼一节,是至难进也。二节犹二关”[1]278。颜子代表大人,仲尼代表圣人,这样成圣也就是一个由学者至大人、由大人至圣人的递进攀升的进程。“儒者则因明致诚,因诚致明,故天人合一。”[1]65“因明致诚”与“因诚致明”就是《中庸》所说的“自明诚”与“自诚明”,张载释之曰:“自诚明者,先尽性以至于穷理也,谓先自其性理会来,以至穷理;自明诚者,先穷理以至于尽性也,谓先从学问理会,以推达于天性也。”[1]330“因明致诚”是一个由穷理而尽性的过程,可以认为是学者和大人阶段的工夫;“因诚致明”是一个由尽性而穷理的过程,可以认为是圣人阶段的工夫。当然,这只是分梳地言之。其实,“因明致诚”和“因诚致明”并非独立的两个过程,而是双向并举的一个工夫。“天人合一”也正是成性、成圣的理想境界。
“天人异用,不足以言诚;天人异知,不足以尽明。所谓诚明者,性与天道不见乎小大之别也。”[1]20在张载的思想体系中,天人是同用、同知的,性与天道也是合一的。“天人不须强分,《易》言天道,则与人事一滚论之,若分别则只是薄乎云尔。自然人谋合,盖一体也,人谋之所经画,亦莫非天理。”[1]232所以,张载的宇宙论必然要介入现实世界,落实到人伦日用之中。由宇宙论到人性论,由太虚、气到天地之性、气质之性,这是一个由天道向人道下贯的路向。同时,张载认为圣人达到了“位天德”的境界,所以成性论是一个由人道向天道上达、超越的一种理论。在这种意义上说,张载的成性论是一个关于天人贯通、天人合一的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