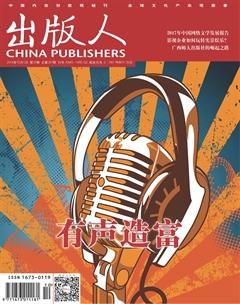“机长”村上春树
李婷婷
假如真有时光机,它的名字叫“假如真有时光机”,别名“旅行者专列”,机长叫“村上春树”。起飞前例行检查,谁来查呢,找个唱反调的老子。关于旅行,他最多意见,“不出户,知天下。其出弥远,其知弥少”,虽然“知少”未必不是好事,可是旅行途中有不少“令人目盲”的“五色”,“令人耳聋”的“五音”,“令人口爽”的“五味”,一路下来,岂不令人心发狂?
真的要“不见可欲,使心不乱”么?若不见,怎能修行?磨砺心志,反而要多见可欲,然后使心不乱。圣人不也西出函谷,骑着青牛去旅行了么,真是言不由衷的家伙。能周流万里,一路拥抱俗世的欢乐。假如真有时光机,可以重回往日,那就登机吧。
“机长”的名字真是万里通行的,走到哪都有人认识:村上春树。写书、长跑、听音乐,一身多能。会得多,还有共通性:专业。写书专业,长跑专业,听音乐专业。专业的习惯如流水一样扩散、融合,他成了诺贝尔奖的马拉松运动员,回回入选,次次陪跑。可惜啊可惜,可是他自己会不会可惜,谁知道呢。名人做“机长”,满载乘客,登机之后,就坐完毕,开始“绝云气,负青天”“怒而飞”了。
一路风景,仅仅是走马观花,也足令人兴奋不已。
因为与外界隔绝,冰岛的羊独立进化,没有尾巴,问问冰岛人,他们却回答说:“有生以来第一次出国时,看见羊居然长着尾巴,吓了一大跳。”
芬兰作曲家西贝柳斯不要在房间里装水管,因为施工噪音太大,怕影响作曲,“拜他所赐,全家老少都得跑到屋外的厕所去方便”。
到波士顿棒球场啤酒柜台买酒,每次都要求出示身份证,可能是看有无成年。可“我的一位熟人……已经七十高龄了,跟卖啤酒的人也很要好,互相以名字称呼对方,可每次仍然要勤勤恳恳地掏出身份证”。
搞不懂啊,搞不懂,可是没有这些搞不懂的人与事,怎么成就“世界之大”呢?
新鲜事物惊异我们耳目,又往往来去匆匆。
旅行者于风景地是过客,人生于天地间也是过客,假如一切只是匆匆,不知会错过多少美妙。
好在这个机长特别,赶路不着急,观光却投入。跟着他,我们学会看着查尔斯河水面发呆:“水面日日微妙地变化,改换颜色、波浪的形状与河水的流速。于是,季节确确实实地改变着河岸周边的植物与动物的模样。大小不同、形状各异的云朵不知从何而来,飘然现身后又不知所终……在这样一种伴随着真实感的流变中,我感觉自己只不过是自然那巨大的拼图中微小的一片。”体物之微,用心之细,自视之谦卑,一己与自然之相融,皆在默默凝视里流出。金圣叹想象王羲之在家看花,一定是静默谛视,一點一点看出花瓣里的曲折微妙,体物而察道,然后用之于书法。若然,机长的“非正常状态”是否也一脉相承呢?
在老挝琅勃拉邦寺庙漫步时,他又出神:“我们每天当然都会看很多东西,然而是因为需要看,我们才看的,并非因为发自内心地想看。”而在这里,“我们却不得不亲自寻觅想看的东西,花时间用自己的眼睛去观察”。他去观察寺庙里的塑像,发现“与其中的几座塑像虽然沉默不语,却能心心相通”。慢慢看,便能从容,体察微妙。听起来像怪力乱神,但这“如人饮水”的事,难以究诘,只好“存乎其人”了。
周作人的《上下身》里讲过一个故事:百余年前日本有一个艺术家是精通茶道的,有一回去旅行,每到驿站必取出茶具,悠然地点起茶来自喝。有人规劝他说,行旅中何必如此,他答得好:“行旅中难道不是生活么。”
行旅中当然也是生活,如同人的上下身一样,岂能一切为二。
旅程结束,终要“回归到日常的延长线上”。出行时不放纵,平居时不沉闷,而能从容自得,气定神闲,是“心向往之”的理想之境。
时光机流水线发车,《假如真有时光机》,那就“登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