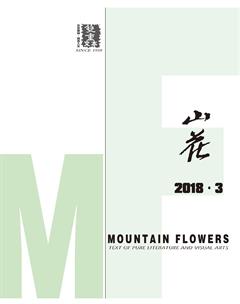鞑靼海峡
张承志
我和女儿作伴,来到北海道的最北端稚内。
她已经不是松户北部小学那个四年级的小女孩了。订旅店、查车次、问路和打交道我一律推给她。我听着她的日语,像一个不打分的老师。
人生总想尽力抵达自己的极限。
在野寒布岬,顶着冰冻的寒风,我们父女眼睛一眨不眨。传说的鄂霍斯克海怒涛滚滚,吞吐着寒冷,就在眼前喧响。
有时到达一个地点,望一眼就算大愿得遂。刚满五十岁那年我只想看一眼黑龙江。而此刻人在稚内,新鲜的地名和海风一块扑面而来,桦太、库页岛、鄂霍斯克海。
正面是东北的东北、亚洲的极东。鞑靼海峡,在视野的尽头。
1.貂皮路
以前,眼睛一直牢牢盯着蒙古。我从来对这一隅视而不见。它从来都是配角,远远躲在地球的东北角。它好像总是偏离历史中心,在边缘沉默,令人不在意它的蕴藏。
但是千真万确:一条像双叉子枪一样的路,缓缓地跨着大陆与海洋,藏在那片沉默的陆海之间。
我这个蒙古史的可悲“研究者”!……只是由于这次来北海道,到稚内之前读资料时,我才看见这张《元世祖狩猎图》。
忽必烈穿着一件点缀黑斑的白色大氅,样子不像帝王,看着有点怪。
在匪夷所思的稚内,肚子里的蒙古知识复苏了。我想起了铁木真——后日的成吉思汗小时候随父亲去相亲的故事。那故事很有名,细节记在秘史里:他未来妻子孛儿帖的翁吉剌惕部落,曾以一件黑貂皮大氅为信物。
后来他到了 “除了尾巴没有鞭子、除了影子没有朋友”的穷途末路,就靠这件貂皮大氅作抵押,借了军队去报仇。
我记着这个故事,却没想过那件黑貂氅的含义。在《蒙古秘史》里它的名字是“Kara Burugan”,马可孛罗说“它是毛皮中的王者。”[1]
对那张帝王图感到奇怪,是因为我不懂貂皮的价值。而忽必烈懂,所以画上的他一副满足的表情。大氅上的黑斑,是更罕见的银貂的黑尾巴,银貂更胜黑貂,是貂中的极品——我恍然意识到这种毛皮有多珍贵!
献上貂皮裘的,是极北之地的渔猎之民。
一条路,一条以能换铁骑三千的貂皮为极品、兼及毛皮海产杂货工具的交易路,缓缓绕过黑龙江,再绕过鄂霍斯克海和日本。间宫林藏探险后它在地图上被名为间宫海峡,但是文人喜欢“鞑靼”一语的质感,留下“蝴蝶飘过鞑靼海峡”的诗句。或者,学着丝绸陶瓷的叫法,称它貂皮路?
——再看去,视野里的北海道以北,景色滋味不同了!
它从辽东半岛开始绕一个大圈:
难怪为了遥远的航行,吉林境内建起了“船厂”……我到过船厂,眼界却只在清朝。我甚至在松花江里游泳,但却不知它的流向。
先沿着松花江,再借助黑龙江,水道一直入海。然后沿海南下北海道,最后从北海道南端的要塞松前城,指向日本列島甚至远指中国——或者从北方出发逆向南下:从乌苏里的密林,先西行再南转,一直指向山海关。
献给忽必烈那件银貂大氅,究竟沿弧线的哪一半送到元大都?貂皮氅只是川流不息中的一滴。物产和人无声地穿梭往来着。平凡或神奇的物资,鱼干或貂鼠,甚至官用的锦缎、铜雀台的板瓦——都向着朝鲜或日本、辽东或桦太,在鞑靼海峡的两侧涓涓分流。
瞥一眼地图,看一眼风景,原来视野里藏着一条古老的陆海通道……它几乎是秘密的,除了游牧或渔猎民族无人知晓。
它溢出了一般的常识。若不是到了这里,我会依旧觉得这条路难以想象。离开野寒布岬,到了宗谷岬,此刻,我身在知识边界的宗谷海峡。
对面的萨哈林(也叫库页岛或桦太),山影依稀可辨。消息随地点一起涌进,我看见了:路隐现于森林与海浪,鞑靼海峡是路的咽喉。
这里可能是我一生行旅的北限。隔着大海,左右南北一片静谧,静得宛如一个谜语。
2.蒲公英
从宗谷海峡对岸,沿着那条隐现的路,一种人,撑着独木舟渡过海峡,踩着石头上的苔藓,蹒跚走来了。
他们皮衣细目,背着弓箭,刷刷趟过枯萎的蒲公英。黑泽明导演的苏联电影《德尔苏·乌扎拉》,把这种人描写得出神入化。
他们的名字繁复,费人猜想。世界用各样称谓来称呼他们:通古斯人、爱斯基摩人、埃文基人、爱依努人、甚至印第安人。还有古代的称呼,翁吉剌惕人。
他们沿着黑龙江和乌苏里江向着东北、再向着更东更北,抵达鞑靼海峡之后和从南方北上的人群,以物易物,像水一样浸漫汇合。他们把东北亚密密的森林莽原里的貂皮、兽皮、干鱼和参茸,运往文明的彼岸,不用说也从其中获得了自己的生计。
成吉思汗的岳丈德薛禅曾自豪地表白说:我们翁吉剌惕部落的惯习是——向王族嫁女结亲,用这法子熄灭争战。这种不战的传统太罕见了,所以被《蒙古秘史》特记一笔:
我们翁吉剌惕的百姓
自古就有
——外甥女的容貌,处女的颜色
与别国之民不斗争
儿子守着营盘
女儿靠着姿色[2]
翁吉剌惕(Unggirad,词尾-d是复数),应该就是俄国的埃文基、中国的鄂温克。teme?id一词我有意不译“打仗”而译“斗争”,因为它在强调阶级斗争的年代,每天被人挂在嘴上,居然古今未曾转义。
他们生活在浩淼的密林水道之间,远离每一个中心焦点,从不掠地夺土。但他们视野广阔,也许人类中数他们跑得最远:不仅北海道,他们脚步的轨迹,一直伸延到阿拉斯加和整个南北美洲。
“不斗争”——也许,已经该强调他们的和平性格?
一种温和的性格,也沿着这条远岛冰海的路,从东北亚传到了南北美。无疑一种和平基因,也掺在血里一路南下,传给了美洲的原住民。
所以我们从墨西哥到秘鲁,一路到处都感到了这种血统。同样,由于太善良所以才失败,因为和平的传统所以遭受屠杀的雷同历史,也顺着这条路线比比皆是地重演。
在杀伐攻战为日常茶饭的北亚草原,这支渔猎部族,可能就是因为不喜欢恃勇斗狠,所以才默默无名?
时光如水,十几个世纪过去后,从北美到日本,他们消失了。没有留下墓冢,除了蛛丝马迹。也没有留下遗言秘史。顾盼整个地球,除了拉丁美洲,没有一个人群像他们:几乎不曾存在,残存得微乎其微。
在所谓证据——史料的缄默中,神秘的东北亚渔猎民族不见了。秘史传述的翁吉剌惕,那习惯把自己的女儿和外甥女嫁给强者成为哈敦(王后),再让她们成为防止冲突的盾牌[3]的以美人和黑貂自豪的古代倏忽消失了。
荒野上,只有点点的蒲公英,在不易察觉地摇曳。
日文网络上这样写着:
和人带来的天花等傳染病,使得爱依努人的人口变少了。1804年估计大概是2万3797人的人口到了明治6年(1873年),减少到了1万8630人。以后爱依努人的人口减少依然不能停止,北见地区到了明治13年(1880年),只剩下955人,而这一人口数字继而到明治24年(1891年),只剩下381人!
不仅在北海道,“这一种人”的人口减少,是一个瞩目的世界现象。
如今旅行在这块土地上,谁都会觉得爱依努人太少了,少得不可理解,少得几乎为零。
这一种人,被忽略了。
3.走马灯
记得满50岁那年,我头一次抵达了黑龙江。《北方的河》把黑龙江写成了梦,是因为我没去过。朋友为成全我的夙愿,把车一直开到瑷珲江岸。
那一天瑷珲就在眼底,黑龙江的波浪拍打着坍塌的城墙。古代的痕迹只见一座长满蒿草的寺,寺里没有阿訇,乡老无影无踪。同样,那时我也没有意识到:就在这里,隔一道黑水,20世纪之前,清朝与俄罗斯——两个帝国在对峙。
50岁那年我使劲瞭望过河对面的布拉戈维申斯克,它被中国人叫做海兰泡。我眺望它,漫无目的,像在新疆波马眺望对面的苏联集体农庄。我那次眺望和旅游大妈的观景台没有什么区别:虽然眺了望了,什么也没看见。
此刻从稚内北望,只隔37海里就是俄领的萨哈林。如今无论谁都知道:进入二十世纪以后,又是两个帝国——俄罗斯与日本的对峙。
在稚内的副港市场,能参观日本的桦太移民史展览。我可真是孤陋寡闻,不知道日俄战争胜后,日本帝国在桦太(即库页岛或萨哈林岛)的北纬50度以南,建成了一个殖民乐土。有港口有城镇有村庄——铁道交叉、市街繁华、中小学邮电局电影院一应俱全!
发生在布拉戈维申斯克的黑龙江大屠杀,是从石光真清自传里读到的。
这是一部明治帝国的间谍回想。二十世纪肇始之际响彻日本的民族主义呼声,使他选择了放弃警卫皇宫的近卫军官前程,不顾后路,“为祖国研究俄国问题”,跨过了鞑靼海峡,把一生抛在了黑龙江两岸的旷野。
对豆腐渣帝国大清,俄罗斯随时可以一刀剁了它的一条腿或一只手。1900年北京发生了义和团事变,宣示谁是老大的机会来了。石光真清手记的第二卷《旷野之花》里记载了这一惨剧:
俄国男人不问老幼都配发了步枪和弹药,在留守队长指挥下被布置在江岸以防备清军登陆。野炮阵地也加强了,上下游都派出斥候监视敌方的动静。同时,对住在布拉戈维申斯克的清国人的抓捕一齐开始。……
短时间里抓到中国街的三千清国人,又被拉到黑龙江边上惨杀,不分男女老少的死尸,像筏子一样被推入黑龙江的浊流。这是东亚有史以来最大的屠杀和最大的悲剧……从那天起,大东亚争霸的血斗史,就拉开了幕布[4]。
病入膏肓的大清,不再吹嘘大国崛起。康熙和乾隆都不能想象,他们开疆拓土把版图一直开拓至未知的远方,但在祖宗发迹的鞑靼海峡,堤防却呼喇喇地一溃千里。
用铁道高速推进远东的俄罗斯,是这块大地上后来居上的新帝国。他们毫不踌躇,把那些苦力和肮脏的人,简直充满快感地屠杀着,然后向着滔滔江水撮下他们的死尸。
可是曾几何时?只在5年后,傲慢的白种殖民大国到了1905年就遭了霉运。陆战败,海战败,岛战还是败。原来当享受屠戮别人的快感时,自己的地狱也建好了——从旅顺口到萨哈林,俄罗斯的大国崩溃,演出得更让人瞠目结舌。
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轮到日之丸帝国演出一场崛起戏时,历史又一模一样地重演了。发了痴的军事炫耀,拦不住的兵败山倒,熬到1945年,一切都化成了齑粉。
不用说,到了大国倾覆时,从稚内副港渡过宗谷海峡去桦太(萨哈林)殖民的日本人,就像满洲国的开拓团一样——森林铁道,撒手一空,人不分老幼,全体都舍了新家,逃回故里。
“大国”如走马灯,转得令人目眩。最后的一场角斗,演出在日美之间。一艘在下关击沉了几条日本船(其中有运送平民的船)的美军潜艇,功勋累累一路北行,走完了日本海。待它右转进入宗谷海峡时,等候良久的日本舰艇出现了,它无路可逃。
宗谷岬立着一块宣称“为所有死者”建立的纪念碑。当然从海浪中不能辨出哪儿埋着被击沉的美军潜艇,又在哪儿沉下了日本的驱逐舰。
我们父女站在宗谷岬。
心里似乎感触万千,其实什么也看不见。无论是大连和长春的繁华,无论从札幌到桦太的开拓,连同日本人的时代心理——祖国崛起腾飞中对他者的蔑视,都像空气一样流失了,像谎言一样消失了。
4.殖民者
在宗谷岬附近我们寻到了一处武士墓。女儿念着碑上的俳句:
たんぽぽや 会津藩士の 墓はここ
(蒲公英 及会津藩士的 墓在此)
除了会津藩外,东北诸藩比如津轻藩都曾派去戍边的武士,如今除了墓碑和徘徊的游魂,清冷的莽原上空无一人。“蒲公英”,是这一首的点睛之笔。宗谷岬一带遍生蒲公英,确实,人消失后,荒野上便只余蒲公英。
这也是一种人:
他们可能是日本的异类,是流放者、是穷民、是遭处罚的败军残兵;但他们也是带刀武士、是“文明人”、是殖民主义者。他们可能被命运抛到了僻荒之地,他们也可能渴望新的家园梦,但他们来到伊始,血液里流着一种歧视——对茹毛饮血的野蛮人,对未知的异俗。
我总在想,赤穗藩的四十七士若是到了北海道,会怎样呢?
对自己主公忠诚不二、一命可抛的武士,当面对的是野蛮人、是穿着不可思议的毛皮树叶、是唱着呕哑嘲哳难听怪曲的“爱依努”时,究竟残忍怎样被煽动、究竟欺骗怎么被选择,究竟杀人的刀被怎样举起?
武士戍边的早期,难以追究细节了。
到了1863年,《知床日誌》记载说:爱依努的女子到了年纪就被发派到国后岛,充当渔夫的玩物。土著妻子被公所的守卫拿去当小妾,男人则在离岛上被人酷使,动辄五年十年。
不用说,文明的“和人”(日本人)像一切边疆故事一样:一袋米换一头熊,一盆鲍鱼换一根针——
在超出经济学能分析的贸易掠夺中,原住民渐渐不能忍耐。有过两三次武力反抗:夏库夏因(シャクシャイン)、寇夏玛因(コシャマイン)、国后目梨(クナシリ·メナシ)。但是,就像今天毁灭中东的屠杀型战争一样,在绝对的军事优势下,“野蛮人”被打败、被夺走家园,最后人口剧减。
武士刀的征服之后,是商人算盘的搜刮。随着日本(和人)商人的渔场开发和残酷劳役,爱依努人被逼入了穷境。1789年爆发的国后目梨暴动,是最典型的一次。有意味的是:暴动的矛头,指向当时的承包资本家飞僤屋商人。他们杀死商人,烧毁商船,火焰一时烧遍北海道东部。
日本征服蝦夷地的桥头堡——松前藩出兵镇压。事件收拾的最后一幕,是对三十七名爱依努犯人的残酷斩首。日本网上有如是记载:
7月20日审问,当天立即宣布37人死罪。第二天21日,犯人被挨个从牢里拉出来砍头。到砍了五个人轮到第六个的时候,牢里开始喧嚣四起,众人唱起了叫做“抛坦开”(ペウタンケ)的咒语,企图弄坏牢房。于是镇压的军人向牢内开枪,用矛刺逃跑者,杀死了其中的大半。最后,把破牢的37人全部處死。然后割下所有首级,洗后装箱,用盐腌上。再把胴体一个个用席子包起挖了大坑埋了。在松前城郊外的立石野,对37个人头进行了验明。
在民族关系的处理中,有时模式是诱杀:
集武勇和儒雅于一身的“和人”武士,设下鸿门宴。他们像西班牙人在墨西哥一样,利用对方的淳朴,以酒引诱太缺心眼的爱依努人。然后席间拔出利刃,把醉倒的客人杀害。
从优越地歧视,到残忍地屠杀——其间只有一纸之隔。
《共同奏响——巴勒斯坦与爱依努》一书的逐年系列,是进步的日本知识人献给爱依努人的悼念。他们悼念和反省的方式,是把日本式殖民主义与巴勒斯坦发生的殖民暴行一起批判。板垣雄三在此书结语里写道:
假称和睦,设宴谋杀,手段恶辣——然而又搁置可耻事实、且使人不能直视它的作业,即美化武士精神性的“武士道话语”。……日本作为一个战斗的、不绝讨伐的国家形象,其亮相之处,即在东北及蝦夷地[5]。
板垣雄三的武士批判,还不间歇地发掘了暴力行径背后的文化。他俯瞰全球的殖民行为及其经济类型,一针见血地戳破了本质:
在基督教徒的《旧约》圣经、也是犹太教圣书开篇的《创世纪》中,讲到亚当的儿子们,该隐和亚伯的兄弟故事。亚伯是游牧民,该隐是农民,非常象征地显示了游牧(包括狩猎和采集)与农业的对照的生活方式。圣经中该隐杀死亚伯的兄弟相杀,是人类最初的杀人事件。……杀人犯是农民这一点,暗示着农业的攻击性。日本的农本主义也许觉得唯农业才是和平、而游牧和狩猎采集民乃是搅乱秩序者、换个时髦说法乃是恐怖分子;但圣经所说全然相反。占有自己的土地并总想扩张它的,是农民。唯因不改造和破坏自然,农业就不能成立。反之,若问谁是适应着生态和环境、与之共生并且存活的,毋宁说,正是从事采集、狩猎、渔捞、游牧生活的先住民族[6]。
对于我这个原牧民来说,这样的概括,一半如自身的切肤体验,一半是发蒙般的启发。对我这青春时代在草原奥深放牧,后来又企图咀嚼《元朝秘史》的蒙语原文、天真地想象着“和平的翁吉剌惕”的人来说——这样的认识,简直像撕裂着自己。
写那本关于日本的书时,对其中《四十七士》一章我曾有过不安的感觉。但我找不到解开的绳扣。也许在中国看腻了背叛的我,被那些殉死的故事掳掠了。没想到在这次旅行途中,我意识到了自己的肤浅。是的,写那本书时,我并无概括“武士”的能力。
我突然忆起2012年的上海。那次我只顾自己的宣泄,忘了把时间为板垣雄三先生留够。今天我痛感那一夜我很对不起上海的听众,因为他们更需要听的是板垣的思想。
我睁大着眼睛。北方的大海,在我面前洪波涌起。
人,若是他直到50岁才第一次见到黑龙江的波浪,他不可能奢望太多。见识的缺少和认识的浅薄是一对不幸的畸形兄弟,那一次我抵达了黑龙江,但什么也没看见。人的启蒙,连时机都有前定。
一条路,一个无声的古代,一种人——都消失了。病毒般蔓延的法西斯言论中,不是常见对异色他者的诅咒,说他们人口增加得太快么?
此时此地,没有谁再谈论爱依努人的被歧视、被杀戮和濒于绝灭了。但是 “不斗争”的翁吉剌惕,仿佛在视野的尽头,与我默默对视。女儿似乎也怀着心事思索。比我早很多年,她今天就有了这些常识。
在接续熄灭的走马灯中,在成串沉没在漆黑浪底的帝国中,一种突破地理的视野,一种返归朴素的原则,像一束光,穿过云缝照亮了海面。
吸引是真实的。从翁吉剌惕人的传奇到爱伊努人的消失,从被抹杀的人到被践踏的心情,在海天尽头的鞑靼海峡,远远地隐现。
海峡上寒风怒号,手冻得甚至无法按下快门。波浪空寂地冲响。乌云滚滚的海上,疾行着凛冽的萧杀之气。
baraan gar-ar,写完于2017年中秋
参考文献:
[1]见村上正二译注:《蒙古秘史》卷二,p.157注3。
[2]笔者据小泽重男对秘史第64-65节的蒙文拉丁转写及日译,再译为中文。小沢重男:《元朝秘史全释》(风间书房,1984年)上、p.260-261页。
[3]同注2,p.261
[4]《石光真清手记》之二:《旷野之花》p.35-37
[5]《響きあう パレスチナとアイヌ》,第一回反植民主義フォーラムin北海道,2005年8月28日,札幌市教育文化会館, P.95
[6]前引注5,P.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