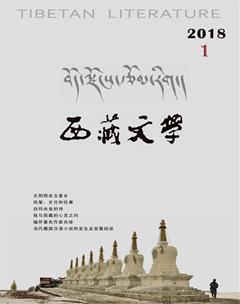今生与文艺缘起
平措扎西的创作在汉藏两种文字之间穿行,始终坚持从生活出发,面向群众写作,他的双语写作在新时期以来的西藏文坛占据一席之地。在文藝创作领域,平措扎西是个多面手,不仅在文学创作上佳作不断,在曲艺创作方面他更是显示出了出色的才华,创作的相声、小品,深受观众喜爱,常演常新。
普布昌居:格啦(老师),您好!非常感谢您接受我的采访。您是西藏当代作家中不多的能够用双语写作的作家之一,您在汉藏文两种文字的写作方面都有不俗的表现。请问您的双语写作的能力是怎样培养起来的?双语思维给您的创作带来了怎样的帮助?
平措扎西:我的家乡在后藏日喀则,我上学时大概是十岁。那时在我生活的周围会说汉语的人不多,人们交流以藏语为主,学校里的情况也差不多。那时日喀则地区的小学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公办学校,一种是民办学校。公办小学整个日喀则只有一所,另有八所民办小学,几乎一个居委会就有一所小学。我刚开始上学时读的就是我们居委会办的民办小学,民办学校里汉文老师奇缺,老师的教学语言以藏文为主,那时还年少的我对汉语文充满了好奇心,很渴望学习汉语文。当时,日喀则公办小学有这样一则规定,民办学校中最优秀的学生可以转进公办校。我小时读书很刻苦,虽然上学晚,但成绩不错,上学一年后我连续跳级,第二年就跳到四年级了,因为成绩突出,第三年我就通过考试转入了公办校的二年级,获得了进入教育资源更优越的日喀则公办小学的机会。
在公办小学里我才开始接触到汉语拼音,汉语课文,那时我已经是十二岁。初中三年里,这种情况没有得到多大的改观。当时因为师资缺乏,学校的课程安排里除了汉语文课,其它课程的教学都是使用藏语文,所以同学们的汉语整体水平都不高,很多汉语文的知识都是一知半解。初中毕业后我考入日喀则师校,你知道的,日喀则师校的藏文师资力量是很强的,三年的中师生活使我的藏语文水平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但是汉语文的提高不那么明显。一来自己的基础不扎实,二来学校安排的汉语文课程数量不多,学的课文也很简单。可以这样说,我接受的学校教育中藏语文的教育是系统、扎实的,而汉语文的学习就是断断续续的、粗浅的。
其实在初中阶段我对汉语文课就格外有兴趣,我的汉语成绩在班级里是最好的,也经常得到老师的肯定,这些鼓励让我获得了信心。读中师期间,我经常找汉文的课外读物来读,不断扩大自己的阅读量。谈到阅读,我最早阅读到的汉文长篇小说是《南海风云》、《高玉宝》、《闪闪的红星》这样的革命现实主义题材的作品,书中的情节我到现在都印象深刻。在读过的作品中我最喜欢的是当时不知道哪里出版的少年版《水浒传》。记得读中学时,每天晚上,我们居委会里的小伙伴们就围坐在煤油灯下,听我给他们用藏语绘声绘色地讲述白天刚读过的《水浒传》,大家都听得津津有味,临走都意犹未尽。《水浒传》里穿插了文言文,生僻的汉字让我的阅读变得艰难,现学现卖又很考验我的耐心与坚持,但那段经历之后我感到自己的汉语文水平有了很大的提升。
那个年代虽然拉萨和日喀则的交通还没有今天这么便利,但是我们也能经常接收、阅读到西藏文联主办的文学刊物《西藏文艺》,其中很多作品对我是文学的启蒙,比如朗顿·班觉啦的《绿松石》,记得当时是连载,小说传达出的许多新的文学观念,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因为我渴望能够继续深造,毕业两年后,我报考了西藏大学汉语系。大学期间我遇到了很多好老师,他们专业知识精深,有的老师自己还从事创作,有一定的文学造诣。我印象中有一位教写作的王远舟老师,他自己就是当时西藏“雪野诗”的重要成员,这些老师在教学中传递出的对文学的热情也激发了我对文学的浓厚兴趣。
因为选择了汉语文专业,我对汉语文的学习与运用就变得更加自觉,除了专业课的学习我还通过课余时间阅读了大量汉、藏文的文学名著、文学佳作,也接触了很多那个年代还很前沿的作品,像当时青年报连载的《第二次握手》,还有很多伤痕文学作品。
在两种文字的比较阅读中,我感觉到了不同的体验。我们阅读的藏文的经典作品多是古典的,遣词造句追求精致华美,而汉语的经典作品中很多是现代作家创作的,和现实的生活结合得更紧密,表达形式也更适合现代人的阅读,这与藏文的经典很是不同。汉语文学的这些特点让我感到新鲜,也使我开始有了写作的冲动,产生了用藏文书写现代生活、适合现代人阅读的现代小说的想法。在大学期间,我曾尝试着写过几次小说,给《西藏日报》投稿。当然,现在想起来这些作品确实很稚嫩,但那是我文学写作的开始。1987年我写了我的处女作,母语小说《索多和他们》发表在《西藏文艺》上,我在这篇小说中描写了八十年西藏青年的一些生活片段,写他们的思考,他们对时尚的追随,也写他们的浮躁,小说发表后得到了很多人的关注,也有人写评论肯定作品的价值。对于初出茅庐的我,这些关注与肯定是极大的鼓励,促使我继续写作。之后我又写了《斯曲和她五个孩子的父亲们》,顺利发表。最初的尝试所获得的成功让我对写作有了更大的信心,我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创作中,写作逐渐成为了我生活中十分重要的一件事情。1991年我调到西藏文联工作,写作真正成为了我的职业。
你提到双语思维对我的创作的影响,我记得有人曾说过双语写作者是“一手抓住两个世界”。我对自己的汉文写作有两个要求:一是体现汉语文字的美,二是表现藏文化内容的精深。当然我做得并不好,从文字上讲没能做到字句优美,从内容上讲,我的作品对藏文化的描述又做得过于深邃、浓稠,内容又太庞杂。对渴望深度了解藏地风俗的人可能有帮助,但对于浅阅读者就过于繁琐、细致了。
普布昌居:八十年代是西藏文学的一次高峰,出现了一批在国内外有影响的好作家、好作品。您的处女作《索多和他们》发表在1987年的《西藏文艺》上,并由此步入文坛。可以说,您是80年代西藏文学创作高峰的亲历者。那么,请问从文学的角度讲,那个年代给您个人最深刻的记忆是什么?
平措扎西:上世纪80年代,我正在上大学,强烈感受到了那个年代浓厚的文学氛围。那时西藏文学正在积蓄力量,无论作家的人数还是素质都达到了解放以来最好的状态。整个文坛也十分活跃,像秦文玉、魏志远、范向东、马丽华,蔡椿芳、叶玉玲、扎西达娃、色波、加央西热等作家,还有李佳俊、田文等评论家汇集一处。文学的不同流派、不同风格也竞相登场,交相辉映。除了《女活佛》、《高天厚土》这样传统的现实主义文学作品,还有扎西达娃的魔幻现实主义引领风气之先,他的《西藏,系在皮绳扣上的魂》打破了传统的写作模式,此外当时具有实验性质的“雪野诗”也风行一时。当然,这些文学的信息也引发我们大学生的阅读热潮。那时,在我们学校里也时常有朗读会,文学的氛围很浓,同学中不乏热爱文学的文艺青年,大家不仅读西藏文学的作品,还热衷读内地作家的作品,像张贤亮、梁晓声、路遥的小说,像《当代》、《十月》这样的文学杂志是我们最喜爱的读本。80年代,让我记忆最深的就是人们对文学的热爱,而我在那个年代激发起的对文学的强烈热爱持续到了今天。
普布昌居:八九十年代您在小说创作方面日趋成熟,出版了小说集《斯曲和她的五个孩子的父亲们》,1995年您还获得西藏10年文学成就奖,但是为什么在小说创作日趋成熟的时候您却把时间和精力更多地转向了相声和小品的创作?
平措扎西:1991年西藏文联的剧协搞了一个全区范围内的小品比赛,当时央视春晚的小品已经有很大影响了,我自己也很喜欢看。后来听说参赛的作品不多,剧协领导找到我让我写个作品,我也不好推辞,就写了两个小品《我们的女婿是个大学生》、《多干事的人》,后来又自己负责排演。因为是第一次,我的导演工作完全靠自己摸索,后来《我们的女婿是个大学生》在比赛中获得第一,当时阿沛委员长看后很喜欢,鼓励我们到工矿去巡演,巡演让作品获得了很好的社会效应。这样一来我的曲艺创作就一发不可收了。我写相声也是很偶然的。最早,我给从事曲艺表演的土登老师和米玛老师写了以保护传统文化、文物为主题的相声《逛议八廓街》,获得了很大的成功,之后又继续写了不少相声。应该说,是观众的热情和社会的好评让我对曲艺作品的创作有了更深入的认识,也有了更浓厚的兴趣。另外,我认为小说写作需要强烈的激情,而我自己随着年龄的增长,写作激情没有那么强烈了,所以这些年我的文学创作转向了写小品、相声了。但是我并没有完全放弃文学写作,只是更喜欢写散文了。我的散文写作更趋向于文化散文,我想把自己了解认识的藏族文化、藏地风俗、藏族名家用简洁朴实的文字介绍给大家。
普布昌居:2005年中国作家出版社出版了您的散文集《世俗西藏》,这本书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朴素的文风、丰富的民俗学知识、字里行间的幽默风趣,让那些在时间流逝中被淡忘的藏地风情习俗重新焕发出生机,将一个日常化的西藏深深刻画在读者的记忆中。能否请您谈一谈创作《世俗西藏》的初衷?
平措扎西:新媒体时代写西藏的作品确实很多,也有很多是区外的作家创作的。不能否认其中有一些作品是不错的,但也有不少写作者在写西藏题材的作品,更多是依据自己的想象来写作的。有的作品把西藏写得很神秘,有的又把西藏写成远离尘世的“最后的净土”,宗教生活被不断放大,缺少尘世间的气息,有的作品中西藏人的生活或者思想性格常常被抽空,这些都与现在的西藏是有距离的。西藏人并没有生活在真空中,俗世中的烦恼与缺憾一样不少。我写《世俗西藏》的初衷就是想通过写西藏世俗的人事人情,将一个充满了世俗气息,浓浓的人间味的西藏呈现给世人,即使写宗教也是世俗的宗教。
普布昌居:1992以来,您的创作在曲艺方面多有涉猎,先后创作了小品《酒鬼拉巴啦》、《这并非玩笑》、《银行之家》,相声《文物的呼声》等,这些作品成为历年来藏历年晚会中的精品节目。分析您的这些作品,我们可以归纳出一些共同的特点:与现实生活结合紧密,触碰到了社会热点问题。另外,在形式上多采用幽默、风趣以及轻微的讽刺,能否请您谈谈您这样的创作特色是怎么形成的?
平措扎西:习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到作家、艺术家应该成为时代风气的先觉者、先行者、先倡者,我在自己的创作中也是按照这个要求来做的。我在日常生活中注意观察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注重写接地气的作品,时时不忘保持艺术工作者的灵敏,积极发现社会焦点、热点问题。
比如,我写的系列小品《酒鬼拉巴啦》。我们藏族喜欢喜乐,也有很多人喜欢饮酒,有些人不懂节制,把时间和生命都耽误在了饮酒上,给个人生活和社会风气造成不好的影响,这种习惯甚至演变成为一种民族的劣根性,是一个社会生活的焦点。我想借用作品揭露、讽刺一下这种民族的劣根性。正好,有次去阿里参加社教,期间听当地的一个同志讲趣事,说当地有一个人喜欢喝酒。一次,他喝醉了酒后不小心被车撞伤了鼻子,被人送去医院治疗时,治疗他的医生也喝醉了。医生在缝合伤口时,差点把他的鼻子和眼睛缝到一起。后来我在进行创作时,采用了这个真实的素材,当时取名《这并非玩笑》。作品出来后,交给话剧团排演。后来的藏历年晚会上,演员们精彩的表演增加了作品的可看度,让这个作品获得了极大的成功。这之后,我们又应观众的要求,写了续集。第三集中已经戒了酒的拉巴啦娶了一个好赌的妻子,她的生活中最大的乐趣就是打麻将,即使怀着身孕还是放不下赌博。我采用荒诞的手法,借腹中胎儿之口,批评指责了做父母的失职。这个作品同样也是对我们民族的某些劣根性进行了讽刺,起到了很好的教育意义,上演后成为当年藏历年晚会最受欢迎的节目。
我写的相声《逛议八廓街》也是反映社会焦点问题。八廓街是藏族文化的中心,民族特色突出。过去有一段时间,八廓街的一部分文化遗迹没有得到很好的保护,我写《逛议八廓街》,呼吁社会相关部门、广大民众重视对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积极保护,这个观点当时还是有新意的,起到了发先声的作用。后来我写的相声《文物的呼声》是针对当时寺庙里文物被盗、遗失的情况比较严重的现实,作品启发了群众的文物保护意识,促进了文物造册、管理、保护工作。小品《书吧趣闻》讽刺了只懂得追求名牌,头脑里却空空如也的两个“老板”,让观众在笑声中懂得现代生活不只是物质的,也是精神的,重提阅读的重要性。今年我写了一个群口相声《健康是福》,又结合现代人的健康状况,提倡全民健身的理念。这也是触摸到了社会的热点问题。
我们知道讽刺是相声的主要功能,当然相声的讽刺更多的是“隔靴搔痒”。解放以來,我们西藏快步走进现代生活,但很多传统的陋习却还在影响制约着人们的思想行为,与时代的发展格格不入。一个民族、一个人要获得进步与发展,就要善于时时发现自身的不足,不断完善自己、建设自己。
说到幽默,很多人也问过我是不是与生俱来的?的确,我的天性中有幽默的细胞,但生活中我并不是处处搞幽默的人,我把这种幽默的气质更多地用于创作。另外,一个人性格气质的形成也和他的成长环境有关。我小的时候因为整个社会的文化生活比较单调,听故事是人们打发业余时间的主要方式。我很喜欢听大人讲故事,也十分留心。我的舅舅就很会讲故事,他讲的故事中有很多像“吉苏啦”这样好听好玩的故事,我喜欢这些故事,记忆深刻。另外,我所生活的后藏日喀则的地域文化相比西藏其他地方更具有幽默的特色,后藏方言中词语的表现力更强,一个现象可以用很丰富的词汇来表达。因为这样的成长环境,耳濡目染,幽默的、风趣的种子也就种在了我的心中。
普布昌居:新世纪以来,西藏文学新人辈出,像次仁罗布、尼玛潘多等,也有不少作品在国内获得大奖,并被翻译成多国文字流传向更广的地域。作为文联副主席,西藏文学的老作家,您如何评价当下西藏文学的发展状况?您对西藏文学的未来有什么样的期待?
平措扎西:八十年代西藏文学的作家队伍是以汉族作家为主,他们创造了西藏文学的辉煌。之后由于各种原因,这批作家中的很多人先后离开了西藏。这以后西藏作家队伍很长一段时间里都不太稳定。这几年这个情况有了很大改变,西藏从事文学创作的人一下子多起来了,而且很多还是本土的作家,他们成了主力。从作品影响来看,新世纪以来的西藏文学创作出了不少好作品,产生了较好的社会效应,这都是很让人高兴地事。
说到期待,习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要重视民族传统文化,要有文化自信。我认为这对我们西藏的文艺工作者很有启示,我认为我们的作家要注重从传统文化中吸取营养。就拿诗歌来讲,西藏有着悠久的诗歌传统,底蕴深厚。尤其是十一世纪《诗镜》被翻译到西藏,对西藏的诗歌创作起到了很好的指导作用,产生了丰硕的成果。今天来看,这些诗歌内容上主要以宣教为主,较为狭隘,但在形式上传统诗歌格式严谨,散韵结合,修辞丰富,音节优美,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我们可以取其精华,丰富深化自己的创作。当然我们更要善于学习、吸收国内外新的思想、新的方法技巧,与时俱进,让我们的作品散发出新时代的气息。
注:普布昌居(1968.10——),西藏拉萨人,西藏大学文学院教授。本访谈为西藏自治区哲学社会科学专项资金项目《新世纪西藏文学研究》(16BZW001)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邵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