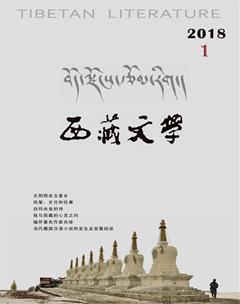亚东之行
平措扎西
本对亚东谷地,
没有抱怨可言。
卡达鸟的哀鸣,
碎了远乡孤心。
一首流传很广的歌曲,以寥寥几句,把一个外乡人在亚东的感受,非常传神地表达了出来。
这首歌,也让很多西藏人初次知闻亚东。我对亚东的认识,也来自这首歌。那时候的我太小,对歌词不明就里,根本无法理解卡达鸟的哀叫如何碎了外乡人的心。那时,亚东离我太远,遥远如天边,朦胧如梦境,更不敢想象有朝一日,自己能踏上这方土地。
亚东给现代人留下的最深印象,无疑是1962年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这场战役之后,中印边贸通道关闭,直到2012年恢复开通。此间,曾经的边境贸易和商道成为陈年往事,成为老人们茶余饭后的闲题。在我辈眼里,亚东仅仅是茂密森林的代名词,从那里运来的木材,建设了太多的房屋和桥梁。火热的运输事业,也让奔忙进出亚东的货运司机,成为令人艳羡的职业。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茶马古道”一词突然占据了媒体的重要位置,渐被人们忘记的人背畜驮的历史,因为空前的宣传力度,在人们的记忆中鲜活起来。各种官方和民间组织的重走茶马古道活动,试图与遥远的历史对话,还原这一重要的历史进程。
也是寻找茶马古道,探拾流年遗事的机缘,我在2004年盛夏,随一波文化人,在日喀则地委领导的带领下,来到茶马古道在我国境内的末端——亚东县采风。那是我第一次来到亚东。
从后藏干燥苍凉的高地,进入亚东谷地,植被渐渐浓密,山路每拐一次,像似下了一个阶梯,眼前的绿色便浓了一层。到了下司马镇,便有了置身绿色世界的感觉。无论山峦,还是平地,触目所及,尽被绿色渲染,还有花儿的点缀和轰轰奔流的河水。在干燥之地生活久了的人,一时有身临雨水之中的湿润感。
亚东这一名称,据说原指乃堆拉。乃堆拉形似牛颈,此山前面的地方,藏语称为娘东。英国人初到此地后,由于发音习惯,把娘字发音为“亚”。后来又从英语翻译成汉语,就有了“亚东”这个地名,以局部地区的名称涵盖了整个地方。其实,在藏语中,亚东称为“卓木”,卓是一种树,卓树树冠很大,一株能覆盖大地一片,使绿色在山巅浓密,“卓木”引申出绿色地带之意,一语破解亚东之特色。如今亚东县的地名,藏语和汉语相差甚远,就是这样造成的。
在原西藏地方政府时期,亚东隶属于帕里宗,由帕里宗委任两名贡堆官吏,代宗府管理亚东上下两村。贡堆的任职仪式,还遗留了原始的血祭仪式:在亚东地方神曲卧钦嘎神像前摆放供品,吹响颈骨号后,供上剛宰杀的牦牛心脏,让新选任的贡堆站在红色牛皮上发誓:“子与敌前不偏也不袒,拒做怂恿颠倒黑白事,扰民贪腐之事要远离。”发誓完毕,手指雏牛心,表达坚定决心。
此时,藏传佛教的种子在藏地已播洒了几百年,村前的山坡上,藏传佛教噶举派寺院东嘎寺也已矗立许久。而原始祭祀的遗风仍固执地存活在这个林海小镇,不能不说是件奇事。后来,据说是亚东的格西仁布钦阿旺格桑制止了血祭之举,认为其有违佛教教义。
1904年,英军第二次入侵中国西藏时,正式在亚东设立了商务馆,清朝中央政府在乃堆拉设立海关,汉藏军队共同守护边关。随后,西藏地方政府也在亚东设立了亚东总馆,处理亚东的地方事务及商务事。至此,亚东作为商贸重镇的影响得以显现,各路人马云集亚东,商业气氛比以往更加浓烈。商品交易的兴盛,促生了各种为之服务的职业。亚东本地人,也从农田里抽出身来,兼行商务相关行业。
从亚东前往印度等国,要翻越位于亚东西面的乃堆拉和则里拉山。这两座大山是考验商人和骡马队体力耐力的试金石,为了积蓄体力,前往印度的商人和马帮,约定俗成地要宿营亚东,为第二天翻山越岭做好准备。从印度归来的商人,也要在亚东整理清点货物,取回存放在商务关口的枪支弹药。另一个夜宿亚东的重要原因是,所有货物都要在亚东的海关接受检查。亚东的客栈生意自然红火起来,只要房屋宽裕的居民,都想开一家客栈。
“茶马古道”一词,让人们理所当然地把驮队想成了马帮。其实,西藏的驮队大部分是骡帮,因为骡的耐力强、劲大,过去西藏商贸通道上的主力是骡,其次是牦牛和驴。一组小骡队一般有八匹骡,称为一个“啦”,配一个骡夫,骡夫称为“赤巴”。一个大骡队,有几十个骡,十几个骡夫。不管骡、马或牦牛和驴,每匹颈上都挂大小不同、响声不同的铃,清脆的铃声和铁蹄踏在石头上的声响,响彻亚东宁静的山谷。
来来往往的商人驻足亚东山谷,带火了客栈生意。常走这条线的商人,都有自己熟悉的老客栈,一到亚东犹如回家,热心的店主早已准备好了房间、灯具、炉具和饲料。常走商道的骡子也很“专业”,每当骡夫走进熟悉的客栈,它们也主动配合骡夫卸下货物,悠闲淡定地吃着饲草。
随着商道上的驿站越盖越多,亚东渐渐有了城镇的规模,房屋也越来越有特色。亚东的民居一般为二层斜顶房屋结构,一层是客房或商店,二层是主人家居,二层房屋和房顶间留有通风空间,用来存放草料和容易霉变的食物。有条件的把一层完全封闭做存放物品处,房前或房后建放货物或圈骡畜的大院。在亚东,经济条件好的人家,基本上靠经营客栈或出租房屋来赚来往商人的钱;没有多少收入的穷人,只能加入到背夫行列。西藏的背夫,不是男人的天地,女人也同样能以这个职业谋生。
从西藏出口到印度等的货物,以羊毛为主。羊毛打包成坨,一坨约百斤,劲大的能背着二坨上路。背夫上路,必须随骡帮一起,路上若突发状况,一两个人势单力薄,难以应对。做背夫者,不光出卖体力,还能在替别人背货之余,自己顺带买些便宜货物,到藏地一转手,也是一笔不少的收入。跟驮队的骡夫关系搞好了,也会帮着把货物驮在骡上,可免劳苦身子。背夫中也不全是靠力气吃饭的老实人,也有人暗中从羊毛坨里挖一把,又用废料填充,害得商人交货时,背上以次充好的骂名。
乃堆拉山威严高耸,逶迤弯曲的山道像来回折放其上的布带。我们在一个晨雾弥漫的日子上山,权当是一次历险。而在昔时,弯曲的山路上,背夫们喘着粗气踏石而过的声音,是乃堆拉山谷的晨曲,也是晚乐。即便是在今天,沿着背夫走过的路,我仿佛能听到骡夫的喘息声和骡马的铃当声,甚至能嗅到他们散发的浓烈汗臭味。
古时的商道,艰险程度非现代人所能想象,徒峭的山崖,湍急的江水,窄小的狭路,时常考验骡夫和骡马,所以,没有一个有胆识、有毅力、有干劲的骡夫团队和强健、善跑的骡马,是很难在这条路上闯荡的,这是一条拿生命交换金钱的道路,是骡夫们靠着勇气和胆识,闯出的一种生存方式。
一个大的骡帮一般有十几个“拉”的骡马,其中有十几个“雪赤”。“雪赤”是指打头引路的骡,骡队的骡夫们每天要轮流作引路人,轮到谁引路,谁就把自己的“雪赤”骡带到最前面,让它带领整个骡队。在狭道上,两队骡马迎面而遇是经常的事,双方的赤巴要碰头协商,让谁先通过狭道,以确保双方安全。在此关头,“雪赤”发挥着重要作用,它必须不急不躁,以此安抚其他的骡马保持镇定。所以,培养一匹出色的“雪赤”,也是一个骡夫的看家本领。
作为商道,见证了很多商队的兴衰,也记录了难以复制的历史瞬间。上世纪四五十年代,亚东的商道上,走过一个特殊的骡帮。
那时,西藏地方政府看到了科技发展带来的便利,从印度先后进口了几辆小轿车。印度到西藏之间,尚没有公路可行,只好把汽车拆开来经过商道运输,能畜驮时畜驮,畜过不去的地方,以人背的方式运到亚东,然后在下司马进行组装。承担驮运汽车任务的骡队,不是一般的骡队,所有背夫头上盘着红辫,发尾露出的红缨在微风中猎猎飘舞,人们把他们称为红辫队。背夫们三五一组扛着庞然大物行走时,前后有腰插大刀的浪荡僧护卫,在狭窄的道路与别的商队相遇,再胆大的骡夫也要靠边让路。
最初的亚东是由上亚东四村落和下亚东四村落组成。而现在镇中心的下司马,是一片空旷的草场,下司玛的藏语本意就是东面草场,除了远乡的生意人偶尔驻足外,几乎是一片放牧草场。1904年,英人在亚东设商务馆后,凭借强大的经济力量,在下司马建造了供工作生活起居的洋房,现在亚东县中学的教学楼背后,仍能看到那时候的建筑,一幢房门上浮雕着1937年字样的欧式房。此后,英国人先后在亚东建起了邮局、电台、电影院、医院、网球场、小型足球场、马球场、蓝球场等,让一双双封闭于雪域深处的眼睛,看到了西方式的生活方式。
下司玛繁茂的市景,也吸引了各路人马,除了西藏各地商贩及他们的随从外,四川、云南等来自祖国各地的商人,也在亚东开设商号、餐馆。看着日益繁盛的亚东,英国人、印度人、尼泊尔人、不丹人,也纷纷到此寻找商机。亚东不大的城区里布满了各种商铺,矮小的商铺摆满各国的洋货,拥挤的巷道间,当地人把糌粑、青稞、荞麦酒、蘑菇、野菜甚至饲草都摆上摊面。一些沦落他乡的人,也选择在此定居,图的是这里好谋生。于是出现了这样的场景:头顶着“披莎”和面包盘的印度人,穿行在衣衫褴褛的乞丐中间;多彩的鸡尾酒在一双双惊异的眼神前闪过;留声机轮流播放着欢快的印度歌曲和沉缓的诵经声;西服和各种民族服装交相辉映;豆瓣酱、洋葱、咖喱面疙瘩和红茶的味道弥漫在下司马的上空。
商贸通道是不同国家、不同民族和不同文化间交流交融的大染场。交往久了,不自觉中接受了别的文化,不同民族之间通婚,繁衍子孙的例子也不少。我在亚东采访时,经常遇到叫张米玛、李卓玛之类名字的人,他们都是藏汉通婚家庭的后代,他们称呼家中的哥哥、姐姐,都是用汉语。而印度人和藏人通婚的后代,一般取名为阿达热·次卓玛、阿达热·多吉等等,家庭成员之间称呼毕直、阿巴热依等,明显有异域情调。我在阿桑村的一户家庭采访时,看到光亮的清漆墙上,贴着一组民国美人穿旗袍像,看畫面已有些旧了,想必是很早以前贴的,一打听,都说不清贴了有多少年,都说自己出生时就有这幅画,以此往前推算五六十年,当时在西藏的大城市都难得看到内地的时尚画,却在边陲小镇有安隅之地,可见当时的亚东小镇有多么繁华。
下司玛是个包容性很强的镇子,这里收纳了来自四面八方的人们,九分为商一分为民,几乎无土著。在文化、生活、语言、礼节各个方面,都相互影响,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情景。
文化的交融,最明显的体现在语言上,南来北往的人一多,谁也不能保持乡音不变,为了方便交流,说藏语时,大家都尽量往最权威的拉萨话靠,所以,今天的下司玛人说藏语,跟拉萨话相差无几,只是语气音调不同而已。细听亚东人说话,除了能找到熟悉的汉语词汇外,英语、印地语、尼泊尔语,乃至上、下亚东人的方言,无不掺杂在其中。如他们把市场称为巴杂,把商店称为多康,电影叫北斯古,手电筒叫毕几林,水桶叫卓莱,电话叫朋木,汽油叫白卓,电报叫达尔,酒精叫艾斯必仁,裤子叫巴都力等等,要是有人专门从语言上研究亚东,也许会有不小的收获。
在饮食习惯上,亚东人也深受西方人的影响。他们喜饮甜茶,甜茶的做法也保留英国人或尼泊尔人的做法,在缸子里调和,每次量很少,体现一种情调,和腹心地区大锅敖茶的习俗不同。在最艰苦的年代,没有牛奶没有红茶,他们就发明了一种叫必嘎的饮品,就是在清茶里放点糖精,过过喝甜茶的瘾。他们的菜大多咖喱味重,喜食豆类,光土豆就有六、七种作法,主食则以米饭为主,和腹心地区以糌粑、面粉为主食不同。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我国实行计划经济,粮食供应非常困难,但为满足边民的生活习惯,国家还专门为亚东边民每人每月供应五斤大米。
原西藏地方政府在亚东设置的总管府,承担着边境贸易的各种检查和审批工作,同时也管理着当地社会治安等,是原西藏地方政府一个重要的部门。总管府从1905年在亚东设置,到1956年关闭期间,西藏地方政府先后派去了九任总管官员,这些官员的任职年限不同,履职情况不一,有的一心只为工作,有的专谋私事,中饱私囊。其中最传奇的人物,莫过于总管米若佳巴其美多吉。他两次任亚东总管,分别是第三任和第五任。他办事公正不阿,性格果敢硬气,绝不屈从于英国人,只要在亚东违纪,无论国人外人,他都敢用同样的方式惩治。在他任职的十三年间,亚东社会平稳,边境贸易活跃,得到了十三世达赖喇嘛的赏识,慢慢地成了达赖喇嘛的宠信。据说他给达赖喇嘛写信,抬头就是“我的怙主老头”,并直接呈送达赖本人。
这个人时时处处喜欢显示总管的权威,早晨起床、晚上睡觉,都让卫师吹军号。平时巡游,一定要坐四人抬的轿子。逢年过节,总不忘用篮子提些碎钱,扔到佣人和卫兵中间,看他们抢夺取乐。倘若有人马过总府,必须下马而过,有些外国人不愿下马,他同样敢惩罚他们。有偷盗违纪出现,他会召集远近乡民,威严地坐在一张铺有虎皮的椅子上,亲自审讯。前面的桌子上放一把手枪,金碗里倒满酒,左右两边站着乐兵,让罪犯跪地受罚。他一边喝酒,一边审讯,吹着乐器棍打或鞭抽罪犯,让人闻风丧胆。
这个人任总管前后十三年。正当他威信如日中天时,突然接到了噶厦免去他总管职务的指令。这令他十分惊讶,绞尽脑汁不得其解。为什么让我如此紧急地交接总管职务?我尽心尽职维护边境安稳,功劳可谓不小。我又与十三世达赖喇嘛关系不一般,外界都称我为他的宠儿,为什么会遭遇如此下场?思来想去几天之后,他终于找到了原因所在。
原来,在此前几个月,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宠信贡培啦的父亲去印度朝佛,路经亚东时,米若佳巴热情迎送接待,还安排差巴负责路上的马匹等,可谓做得完美无缺。然而,在一次设宴招待时,米若佳巴得意忘形,说了这么一番话:“您的公子贡培和我一样是怙主的宠信,我还比他年长一些,但您的公子连一封信都不给我写。”言语之间,他把自己和贡培啦放在平等的地位,让贡培啦的父亲大为光火。贡培啦的父亲回去后,这话传到贡培啦的耳中,也是十分的不高兴,于是怂恿噶夏撤除了米若的亚东总管一职。很快,米若接到了噶夏的指令:“米若佳巴其美多吉总管任期已满,由次松平康格桑旺久接管,请速办新老交接,米若佳巴速到噶夏报到。”米若把工作交给继任者后,给噶夏呈了一封信道:“我米若佳巴其美多吉克服年老体弱之困难,服从指令,在边境十三年如一日劳役身心,甚至以命尽职。现已年迈,临踏入天葬台不远,无法履新,请免去我的职务。”他呈信后卸下官帽官服,回到他在南木林的庄园米若佳巴,一心归入佛门修行。
亚东也是最能体会新旧社会两重天的地方。1943年,原西藏地方政府在亚东设立的商贸关口,被一场洪水冲毁,几年时间都无力修复,只能借住在私人寓所办公。而2010年,印度锡金邦发生6.8级地震波及亚东,使亚东的很多民房毁于一旦,但政府出资兴建的一排排整齐漂亮的民居,很快在亚东山谷拔地而起。原西藏地方政府时期,背夫无止境地为商埠和来往地方政府官员支差,甚至一家几代人当背夫,也只能糊口罢了。一些边民羡慕大山外的生活,举家跑到国外生活。改革开放后,国家给边民的优惠政策力度越来越大,边民的生活一年比一年好,富起来的农民甚至超过了解放前的大富家。看到亚东发生的变化,印度边民都要求加入中国籍,过去离开亚东的都想回来。他们说:“在边境线看到五星红旗热泪盈眶,一种想回到祖国怀抱的温暖感油然而生。”
二
从亚东出来,地势越来越高,车子爬上弯弯的山道有些费力,就像一个不算年轻的人吃力地攀爬亚东的屋顶。
从亚东到帕里,不仅仅是两座小镇的距离,从海拔2600米到4600米的落差,是生命能量的检测点。但从常跑两地的老人们嘴里,几乎听不到地势高低,身体不适之类的话语。
我认识帕里也是始于一首童谣。这首歌这么唱道:
帕里草坪上的欧罗(小孩),
很乖很甜。
拉姆次仁不算漂亮的,
比她乖的还有普穷啊丽……
帕里在西藏的认知度,绝不亚于亚东。单论商贸地位,在昔日的商贸古道上,帕里是不折不扣的商品集散地,是来往商人必停的大驿站,它的声名也不在亚东之下。
到帕里交易的外商一般是印度锡金和不丹的商人,由于地理位置的缘由,在帕里经商的不丹商人,远远超过了在亚东经商的不丹商人,不丹人把帕里这个商贸中心视为最佳的谋生地。
帕里坐落在一个宽阔的草甸上。过去,这里除了宗府、公差府和几个贵族、大商人的邸府是石材建造之外,其它的房屋多是就地取材,以块状草皮垒造,草皮垒的平房随处可见,来往于印度、拉萨之间的商人,都要在这里驻足休整。为了抢商机,也有印度、尼泊尔、不丹人在这里开设商店,和那些没有实力到印度的小商人谈生意。
有句话说:“帕里是逃逸者创造的。”指那些支不起差的逃跑者、家破人亡的走投无路者,到这里给赶骡的赤巴做随从、给客栈当帮佣、为商人做短工,找到了谋生机会,成为帕里镇的主体,繁荣了当地的经济。
我的采访对象之一,80岁的强巴老人,也是逃到帕里后定居在此的。他出生在拉萨堆龙地方,17岁那年,作为仆人随主人到江孜经营庄园。八年后,一场洪水把富饶的江孜冲毁得面目全非,强巴当佣的庄园也未能幸免,就在他走投无路之际,想到了在帕里热振拉让的叔叔。于是,他来到帕里投奔叔叔,在帕里政府经营的一家藏纸铺帮佣,一干就干到了民主改革,成为了地道的帕里人。如果不是他自己说他出生在堆龙,从他的言语间根本听不出乡音。
商业繁盛时期的帕里,几乎人人经商,连宗政府也要参与其中。原西藏地方政府在这里设有纸铺、茶铺、米铺等,米铺主营不丹和印度的大米,除提供给政府所用外,还有一些可以对外销售。纸铺是从不丹进口藏纸,提供给政府写文件或做浆糊泥塑佛像所用,这些店子里除了主管外,还有不少穷人支役。
帕里能成为商业重镇,凭的是地理优势。从气候来说,它不占任何优势。这里海拔太高,一年中除了短短几个月的夏天外,大多数时间只能围着火炉而坐。如果你在冬天经过帕里,会发现这里没有几天是不飘雪花的,刺骨寒风更让人难以忍受。过往的人们留下了一句经典感叹:“想买夏天的帕里,想卖冬天的帕里。”
纵是最寒冷的天气,帕里的背夫们,还要背着一些死羊肉和骨头翻越旨木拉山,去不丹换一些粮食。不丹的背夫则背着大米和糌粑,翻过旨木拉山,到帕里换一些货物。在风雪弥漫的旨木拉山,常有背夫背著行李死在路上。但生存的艰辛,阻挡不了背夫,他们前仆后继,走出了这条商道的繁盛。“帕里店娘的生计,全靠旨木拉山。”说的就是大多数帕里人艰辛的生活场景。但在富家的客栈里,明亮的汽灯之下,也常常上演纸醉金迷的生活,醉客们飘飘欲仙,边歌边舞,挥霍着赚取的钱财。
高寒的气候,几乎让帕里与农作物绝缘,连遍布藏地的青稞在这里也成熟不了。到过帕里的人都说:“帕里如能长出青稞,大地将要饥荒遍地。”然而,每到春耕时节,帕里人还要和藏地其他地方一样,种植青稞,一到夏天,帕里满地都是绿油油的一片。帕里人收了这些未熟的青稞后,在屋檐垒成草墙,一到冬天,每家每户些微绿色的屋顶为荒芜的帕里增添了一丝绿意,但这些带点绿意的青稞不是冬天的点缀,而是卖给过往商人做饲料用。卖饲草也是帕里人的主要收入之一,连宗政府也要做饲草生意,和平民争抢白花花的银子。
责任编辑:邵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