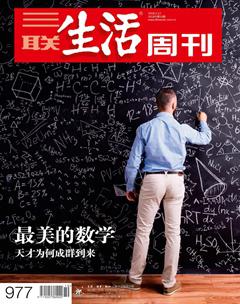新成都人的“蓉漂”生活
王丹阳

“蓉漂计划”
四川有句谚语——“川人出夔门是龙,不出夔门是虫。”夔门和剑门,是四川南北两大门户。北线剑门出蜀道,便穿行在米仓山、秦岭这些通往汉中的崇山峻岭中。南线出夔门,经长江三峡水道直达湖北和中原地区。都说“少不入蜀、老不出川”,是对天府之国富足安逸的最高褒奖。言外之意,成都的舒服和事业的进取似乎不可兼得。
然而,这种状况已经被反转了。安逸总是好的,安逸又适合工作发展,何乐不为?
“国际顶尖人才来蓉创业最高给予1亿元综合资助”“1.6亿元专项资金为市民提供就业创业培训”“本科以上青年人才可凭毕业证来蓉落户”“外地本科及以上应届毕业生来蓉应聘可在青年人才驿站免费住7天”……这两年,成都在人才政策上不断改革,各种组合政策令人眼花缭乱。目的只有一个,吸引各种高端人才入川。
目前,成都22个区(市)縣已经逐步构建了各自的青年人才驿站,计划每年可服务2.5万人。去年,成都开始正式执行“蓉漂计划”,并推举“蓉漂计划专家”。为了鼓励各类人才来成都创业就业,成都打开了落户闸门,实行全日制大学本科及以上毕业生凭毕业证落户制度,对于本市同一用人单位工作两年及以上的技能人才,可凭单位推荐、部门认定办理落户手续。对初来乍到者,政府提供7天免费的宿舍,帮助落脚。政府还提供35万套比市场价格更便宜的人才租住公寓,海内外正规研究生学历以上的人才都可以申请。
现在成都约有300名“国家千人计划”“四川省千人计划”及“蓉漂计划”专家,前两个层次的“千人计划”都在政府的带动下展开,而成都的“蓉漂计划专家”就是赋予这些海归高端创新创业人才的另一个称号。
从终身教授到电影玩家
罗健就是“蓉漂计划专家”之一,海外工作很多年后再度归来。他的办公室就在南三环外锦江区的创意产业园,其一手创办的冰翼数字技术公司在E座,大堂的正对面立着大学生创业基地的告示牌,上面写满了正在孵化的公司。
公司入口处的博古架上放着几个印着动画飞机模型的海报照。在这家技术范儿十足的公司里,员工喜欢叫董事长罗健为罗教授。罗健也是即将公映的动画大电影《扶桑岛》的艺术总监,这位曾经大学里的终身教授浑身洋溢着技术范儿,并不像电影圈的人。我们初到的时候,他在开一个长会,听说是拉片,浏览那部电影里1800个镜头。
罗健说这是一家做三维动特效的公司。他自己从一个成都飞机公司的自动化工程师,到一个电影的艺术总监,经历了多年的转型和蜕变。
罗健是成都人,但又是一个出走异国后倦鸟归巢的新成都人。说当时出国的初衷,他至今懵懂:“当时只是觉得身边的归国华侨多了,我就想我为什么不能做华侨呢?”对于一个军工企业的内培生来说,本来就很少看得到外面的世界,所以当他开始打听大洋彼岸的消息时,身边几乎没有同道。
罗健毕业后不久,在成都飞机公司工作。在人民南路的文化艺术宫边上的一家书店里,他淘到了一本出国留学指南,上面有美国各个学校的申请方法和期限。因自己小时候学过中国画,便把申请材料寄到了普林斯顿大学和耶鲁大学的艺术系,只因这两家学校的奖学金额度最高。没想到第二年开春收到普林斯顿的航空回邮,告诉他已经过了申请期限,不过倒给他推荐了三所还未截止申请的学校。“美国的学校挺有意思的,还帮助推荐学校,但我却傻到连申请期限都没有注意。”罗健说。他当时的心里只一味想着要出去,照样一式三份地发申请,最终全部收到了offer。
“当时只知道纽约是‘犯罪现场,而缅因州是总统度假地,那里的龙虾听说很棒,所以我就去了缅因州艺术大学。”罗健又一口气读了密歇根大学的艺术博士,“MFA学位就相当于理科的PHD了,60个学分,我只花了三年就读到terminal(终点)了。”他当时是没日没夜地读,后来再修了一个计算机硕士学位,在艺术设计的路上越走越远,也正是因为早年这个仅花了三年拿到的艺术博士,让他在2012年拿到了威斯康星大学终身教授的职称。
在威斯康星大学教书期间,罗健一直没有间断和美国各个电影工作室的合作研究,熟悉了好莱坞的电影工业流程。回国后,他带着200来人的团队按照好莱坞的电影研发与制作体系工作。“IP是制造出来的,不是买来的,我们要做的是designing film(设计的电影),不是film design(电影的设计)。中国的导演拍片感性得多,对错全靠运气,但是好莱坞电影是一个预测体系,是用很复杂的算法系统来制造IP,精确地预知市场。”罗健说。
冰翼业务集电影的策划、内容制作和后期动特效为一体,这样的公司在成都并不多。而像罗健这样,从艺术设计学教授到亲手操刀一部动画片更是特殊。《扶桑岛》脱胎于《山海经》,故事是罗健用半年时间写出来的。他认为关键不在于文学功底,而是怎样造出IP来,所以他要做的是那些仙人在现代的状态。罗健并不热衷在北京和上海这样的城市做原创电影,他认为那里只能获得前沿优势,距离宣发比较近,但同时环境也更嘈杂,往往“雷声大,雨点小”。换作搞内容,他认为还是成都最适宜,能让自己和团队踏实下来,把时间花在琢磨作品上。
罗健回国两年,从一个老成都人变成一个新成都人。他不停地观察着周围的创业环境和新兴产业,内心更喜欢这个不断求新、思想活跃的成都。罗健认为自己是那种不以安逸为目的,无法停下来的成都人。“其实,我最讨厌的事就是搓麻将,我也讨厌看美食节目,我不想把自己的追求降低到口腹之欲。”他喜欢成都,可以笃定做事,现在他就等着自己的第一部电影作品在全国院线上映。“影视行业一旦有了龙头企业,集聚效应就会显现,现在并不用担心成都没有完整的原创动画大电影产业链,有了作品和龙头公司后一切会水到渠成。”罗健自信地说。
归来依旧是少年
与罗健一样,高分子博士李进既是“省千人计划专家”又是“蓉漂计划专家”,他还是成都先导药业创始人。
李进是重庆酉阳人,高考恢复以来的第二届大学生,本科毕业于四川大学高分子材料系。酉阳位于渝贵交界处,要穿越800公里巴山蜀水,才能来到一马平川的成都。1985年,当李进作为国家第二批对外交流研究生被公派到英国时,他对西方世界一无所知。每次联系教育部,他都要走到市里的邮电大楼打长途,具体去哪个国家,由包办一切的教育部发派。1985年初,他得到一张2月9日飞伦敦的机票。那时,这个22岁的乡土青年也得到了生平第一笔几百块钱的制装费,买了套毛呢西装去了北京。“我跟北京一位农科院的兄弟说,我要出国,在你宿舍住几天,你要带什么东西吗?他说你给我带一箱青菜吧。”
李进带着一箱青菜离开了成都,一别就是20年,他进入了伯明翰的阿斯顿大学读高分子博士学位,三年就毕业了。“我们小地方出身的人没怎么见过世面,对未来也没有明确的计划,那时只想把博士读出来。博士毕业了看见大家都去读博士后,于是我也报了曼彻斯特大学的蛋白质化学博士后,等看见周围人在找工作、办长居了,我也跟着办长居。”李进说,他就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个目标接着一个目标地打拼,几乎没有想过要回来。直到2005年第一次回国,他突然惊觉:“中国怎么发展成这样了?”于是兴奋地回去告诉一些中国同事:“中国现在的变化很大哦!”
当时,他是瑞典阿斯利康制药公司的全球化合物科学总监,做前期新药研发。真正让他考虑回国发展,是后来在成都召开的一次行业研讨会上。有同行问他,成都的医科发展历史久,临床医学也相对齐备,为什么不来成都创业呢?李进认真考虑了这个建议后,回成都开了自己的原创药公司。
归来依旧是少年,说干就干,李进并不输年轻人。公司的天使轮融到了3000万元,他筹了个三人团队在高新区生命产业园的某幢楼占据了两层就开始干了。
回国第二年,李进自己申报了“国家千人计划专家”,翌年他又是省级的“千人计划专家”,如今被称为市级的“蓉漂专家”。“现在四川省级的千人计划专家有700来人,每年要评出200来人,最近更是加大了力度,落户安置的补贴也是水涨船高,从国家到省级、市级,每层都有配套资金。”李进回成都这几年,过得很舒服,他把妻儿留在英国,自己在成都买了一套房,周末有空就去打高尔夫。他还帮助自己招来的四位海归同事也加入了四川省“千人计划”。“一开始,这个计划只针对海归,我们认为非海归的也有人才,不能忽视,就去组织部提出建议,现在政策已经改了。”
成都始终以包容、体贴的姿态呵护着这群海归的“蓉漂生涯”,尽心尽力,润物无声。说是“蓉漂”,但李进和很多人一样并不觉得自己漂着。公司从最初三个人发展到现在的230人,大多数在顶楼的10来个实验室里做研发项目。公司所专注的肿瘤靶向药业务时间线长,从新药报项、研发到上市的平均周期是10年。但李进并不着急,他说在成都做事氛围宽松,做原创药的研发不应该急功近利,如果在北上广做公司,也许就是另外一种心态了。
李进的社交活动基本集中在各级医药类研讨会上。他屡次表达一个观点:“发展生物医药对于一个地区的竞争力非常重要,涉及了化学、生物学、计算机自动化等等,是多学科综合竞争力的体现。”在成都,像他这样的海归博士做新药研发公司的例子不多。“大概都去医院做临床医学了吧。”他笑笑,“既然成都市重视我们,说明他们充分意识到这个领域的价值了。”
中医博士迪亚拉
新成都人这个群体就像一面多棱镜,在这个有着独一无二的“巴适”气质的蜀都,折射出各种光芒。“蓉漂”的构成也是丰富多样的,有回流的科学家、高级经理人、年轻白领,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群体就是外国人。成都的领馆数量在全国排第三位,有3万多名外国人在这座城市如鱼得水。
来自非洲马里的迪亚拉是一位知名的外籍“蓉漂”,也是中国第一位外籍的中医学博士,和成都的缘分断断续续有20多年。现在,这位成都新都区中医院的外籍特聘专家,每天忙个不停,当我们见到他的时候,他正在住院部的走廊上探视加床的病人。他毫无违和感地周旋在人群里,“他講他的四川话,我讲我的普通话”,除了肤色,他已经全然地本土化。
迪亚拉的“前半生”说来话长。他出生于西医世家,1984年时,由马里公派到北京的北医三院深造,谁知道他被中医迷住了,把心一横“背弃”了自己政府的公派目的,弃西医改学中医。他先是去广州医学院从本科到硕士念了8年,再到成都中医药大学读博。“当时来成都是为了想拜著名的中医理论家杨介宾为师,为了见到他就四处打听,他知道我要考博后很高兴,但是在中国从来没有过外国人读中医博士的先例,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1994年,迪亚拉通过全国博士统考,破天荒地成了第一个外籍中医博士,那时的委培学费是一学期3000元人民币,他用多年来从牙缝里挤出来的奖学金付了学费。第三年时已弹尽粮绝,当时马里政府已经切断了对他的培养费支付。他永远无法忘记,那天在医院值完夜班后从口袋里掏出5块钱,这是他最后的财产。绝望中他打开医院里的信箱,却发现马里政府的一封电报:“经核查,我们还欠你3000法郎未付清。”这笔续命之财让迪亚拉感觉要起飞。

来自非洲的中医博士迪亚拉正在给病人看病
成都给了他太多的美好回忆。他在工作后曾跟随世卫组织和无国界医生组织去西藏和昆明工作过10多年,但最终还是选择了成都。“你会觉得,在昆明你一出门就见到很多外国人,但他们是来旅游的;而在成都,你也许很少见到外国人,但他们分布在各个角落经营自己的生活,他们就是这个城市的市民。成都这个城市很特别,既传统又时髦。”迪亚拉在成都过得很舒服。
迪亚拉选择来新都区中医院工作,是因为这家医院是“科研教育、医疗康复一体化示范基地”。他向我顺溜地背着这一长串名字。迪亚拉是一位孜孜不倦的外籍中医,每年都会创新一两项医疗方法。成都赋予了他这份气定神闲的心性,他自豪地说以药养医的行规跟他们医院无关。现在他是医院里的大红人,一些本地老人来看病,见他是外国人,就竭力转说普通话,可越急就越是说不出来。“每次我碰到这样的病人,我说好了好了,你就说四川话吧。”他装作不耐烦的样子敲敲桌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