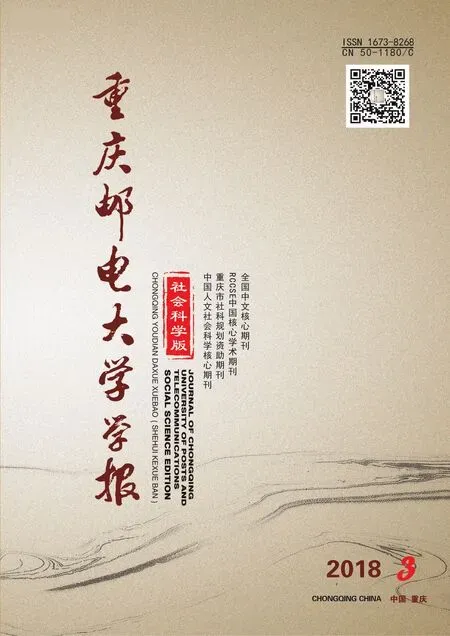“围城”中的“历史人”
——论李梅亭与霍华德·科克形象的伦理悖论及镜鉴意义*
张 媛,翟 哲
(1.江苏科技大学 外国语学院,江苏 镇江 212003;2.苏州大学 文学院,江苏 苏州 215123)
一、“围城”:李梅亭与霍华德·科克生活环境比较
人是环境的产物,从某种意义上说,李梅亭与霍华德生活的环境就是两座相似的“围城”。关于“围城”的涵义,《围城》的文本意义原来喻指婚姻:“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1]89杨绛女士在电视剧《围城》所题片头语中对其涵义有所拓展:“无论婚姻、职业、人生愿望,大抵如此。”有学者甚至将其提升至形而上高度,认为“围城”是人类生存形式的象征——希望与失望轮回的尴尬人生困境的隐喻。笔者在本文中借用“围城”这一概念,将其限制在形而下意义范畴内:“围城”意指李梅亭与霍华德生活及工作的环境。在人与遗传、环境的关系中,生物学家往往强调遗传因素的作用,而教育学家、社会学家更重视人的性格与环境之间的正相关性:环境往往决定人的性格。这里的环境既指涉人物生活的宏观大环境,如时代、国家、社会等,又涉及困囿人物的微观小环境,如家庭出身、职场氛围、社交圈子等。
(一)相似的“围城”
李梅亭与霍华德生活的宏观大环境(动荡的时代)与微观小环境(相对稳定的大学校园)都大致相同:李梅亭生活在20世纪30年代的三闾大学,抗战初期的混乱大时局与三闾大学相对稳定封闭的小环境构成了李梅亭们的“围城”;同样的,霍华德活跃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沃特摩斯大学,那个年代激进、动荡的社会历史氛围与沃特摩斯大学独特的“新式”校园环境构成了霍华德们的“围城”。李梅亭与霍华德生活在时空各异但社会、人文环境相似的“围城”中,这也是《围城》与《历史人》最为明显的相似点与环境基础。更为巧合的是,两位作家截取的人物生活断面也大致相同,都是一个秋季学期:李梅亭生活在民国二十六年(1937)的秋季学期,霍华德生活在1972年的秋季学期。钱钟书塑造李梅亭这一形象,主要将笔力集中在从上海到湘西的路上,借舟车劳顿的漫长旅途展现其生活时代的大环境,尽显人物高雅外表下的庸俗内在;马尔科姆·布雷德伯里塑造霍华德这一形象,主要将笔力集中在1972年秋季学期的两次聚会上,通过客观陈述霍华德一系列的谋划运作,尽显人物堂皇外表下的卑劣本质。
(二)不同的“围城”
虽然李梅亭与霍华德生活于其中的宏观大环境与微观小环境呈现某些相似性,但困囿他们的“围城”同样在多个向度上具有明显差异。
首先,从宏观大环境看,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英国不可同日而语。1937年的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全中国人民都主动或被动卷入了压倒一切的民族救亡战争中。李梅亭们离开十里洋场的大上海,赶赴偏僻湘西的三闾大学任教,一路的颠沛流离展现了战时的兵荒马乱、民不聊生,比如一行人在上海上船时遇到的空袭警报[1]147、宁波到溪口的泥泞小路、“古稀高寿”还在使用的汽车、“欧亚大旅店”的跳蚤、被困金华的无奈逗留、长沙被战火烧成白地的消息,等等。再如李梅亭代买船票的小算盘、把学校的旅费部分留在家里、随身携带一大箱子西药、吝惜新买的雨衣舍不得在旅行途中穿用,等等。作者真实地再现了那个时代政治的动荡、时局的混乱、经济的落后、物资的匮乏以及各阶层人士生活的艰难困顿。
与李梅亭生活的宏观大环境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霍华德生活的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英国,在政治上是激进与革命的先锋时代;在经济上相当富足:霍华德为了自己的个人目的不无挥霍地举行了两次盛大派对,丝毫没有李梅亭捉襟见肘的狼狈和猥琐;在思想文化上是史无前例的开放:“以‘石墙暴动’为标志的同性恋维权行动、‘垮掉的一代’以及伴随而来的摇滚乐与流行文化、毒品亚文化的兴起、性革命,形形色色怪诞而出格的现象泛滥、混杂。”[2]
综上,李梅亭与霍华德生活的时代环境迥异。任何人都是时代的产物,任何人都不可能自外于所处的时代,时代洪流裹挟着李梅亭与霍华德,从而使两个人物在经济上、政治上、思想文化上呈现出截然不同的景观。
当天晚上,3D的开奖号,是149。林小敏买的,是 148、149,各75组。买三百元,赢二万二千零三十元。
其次,从小环境看,三闾大学与沃特摩斯大学也迥然不同。虽然这两所学校同属新成立的高校,但在校园环境、人员素质、人际关系上的差异是显而易见的。
就校园环境而言,三闾大学偏安于僻远的湘西平成县,带有战时因陋就简的临时性质,缺乏像样的校舍建筑及硬件设施,更谈不上深厚的人文积淀和文化底蕴。而沃特摩斯大学按照英国先进的新式大学的标准模式而建,校园内各项设施先进,仅就一些堂、厅的命名看,就是“现代历史的缩影”[3]64,有“霍布斯和康德”大楼、“马克思和黑格尔”大楼、“汤因比和施本格勒”大楼[3]57,同时还是一个阐释“未来主义的地方”[3]66。
就人员素质而言,三闾大学汇聚着颇具假冒伪劣之嫌的学者、教授,有道德品质低下的训导长李梅亭,有毕业于子虚乌有“克莱登大学”的历史系主任韩学愈,有靠老婆谋得中国文学系主任职位的汪处厚,甚至还有为了汪太太而明里暗里争风吃醋的校长高松年。而沃特摩斯大学聘用的多是学识渊博的教员:霍华德出版过两本学术含量极高的著作,系主任马文、社会心理学家弗洛拉·本尼弗姆、亨利·毕梅思等都是拥有真才实学,在各自领域有所建树和坚守的学者。
就人际关系而言,三闾大学的人事任免带有中国特色的任人唯亲色彩,仅就从上海到三闾大学任教的李梅亭一行人看,赵辛楣是校长高松年的学生[1]129,李梅亭是高松年的老同事,顾尔谦是高松年的远亲[1]131,连方鸿渐和孙柔嘉都是通过赵辛楣引荐的;沃特摩斯大学则少见这种人身依附、帮派性质的裙带关系,人员来自五湖四海,只有“激进”与“保守”的政治与价值分野。
综上,从李梅亭与霍华德赖以生存的微观小环境(包括其日常运行与交互的环境生态)看,双方在文化氛围、人际关系、人员素质上有着云泥之别。在《围城》中,畸形逼仄的环境与病态知识分子群像相映成趣,真实再现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抗战时期特定的社会、政治与文化对校园生活无所不在的影响;而在《历史人》中,枯燥的会议,工作中的密谋,标新立异的课堂与学说,派对与性的聚会,直到最深层次的堕落与瓦解、冠冕堂皇下一本正经的无聊,无不折射了那个年代欧美的社会、政治与文化对校园生活造成的颠覆性影响。
环境为人物活动提供舞台,典型环境是塑造典型人物的物质基础。虽然同是描写动荡时代知识分子活跃其间的大学校园,但两个围城却是同中有异、异中有同。
二、“历史人”:李梅亭与霍华德·科克形象的伦理悖论比较
虽然生活的时代、国别不同,但李梅亭与霍华德形象在某种程度上说具有极大的相似性,他们都是生活其间的大环境与小环境——“围城”的产物,都已经成为了“历史人”——为历史存照的人物,或曰在历史大潮中脱颖而出的“弄潮儿”,其形象的伦理悖论具有极大的相似性。
(一)相似的伦理悖论
李梅亭与霍华德形象呈现的相似伦理悖论,主要表现为身份、地位与其扮演角色之间的矛盾。按照社会学的观点,“身份是一个人在系统中所占据的结构位置”[4],往往与人的地位相关;而“社会角色是指与人们的某种社会地位、身份相一致的一整套权利、义务的规范与行为模式,它是人们对具有特定身份的人的行为期望,它构成社会群体或组织的基础”[5]。而在身份、地位与角色的关系中,“地位与位置相关,角色则与行动相关”[6]128。就其身份、地位而言,李梅亭与霍华德都是他们生活时代的“成功者”。李梅亭在上海是中国文学系主任,在中华书局聚珍版精印名片上有一大堆唬人的头衔:“国立三闾大学主任”“新闻学研究所所长”。同样的,1972年秋季的霍华德“已经进入精英特权阶层”[3]24-25,“拥有了高级讲师的职位,还参加了许多个委员会。同时,他在城里的激进派事业中也表现活跃”,“在报纸上撰写文章”,“在当地新建的大学里讲课”[3]52。李梅亭与霍华德拥有他们所处环境中成功人士的一切身份和地位。但就其扮演的角色来说,无论是在日常生活中还是在职场生涯中,都与其身份、地位严重不符,两者分裂且呈现出明显的伦理悖论。
其一,在日常生活中的伦理悖论。“伦理身份是评价道德行为的前提。在现实中,伦理要求身份同道德行为相符合,即身份与行为在道德规范上相一致。”[7]无论是李梅亭还是霍华德,在日常生活的角色扮演中,身份、地位都与其呈现出矛盾与背离姿态,表现为言与行的矛盾、表与里的抵牾。以钱与色为例,李梅亭表现的是赤裸裸的粗鄙。在金钱问题上,李梅亭表面上主动为大家做好事——托人买船票、住两人舱,实际上是为了贪小便宜,把学校发放的差旅费省下来。其深入骨髓的爱财如命、锱铢必较,特别表现在赶赴三闾大学就任途中随身携带的大铁箱上:“一半是西药,原瓶封口的消治龙、药特灵、金鸡纳霜、福美明达片,应有尽有。”[1]153一路上挂念与关注的也是这只能够给他带来巨大利益的铁箱:“李梅亭依依不舍地把铁箱托付给店主。”[1]154动用所有心计与算计践行早已筹划好的发财之道:“他的药是带到学校去卖好价钱的,留着原封不动,准备十倍原价去卖给穷乡僻壤的学校医院。”[1]175-176在两性关系上,李梅亭对遇到的任何女性都怀有觊觎之心,如途中偶遇“带着孝”的“年轻白净的女人”,他言语中透露着体贴关心,而行动上却猥琐轻薄:
李梅亭四顾少人,对那寡妇道:“你那时候不应该讲你是寡妇单身旅行的,路上坏人多,车子里耳目众多,听了你的话要起邪念的。”李先生假装客套一下,便挨挨擦擦地坐下。[1]163
不仅如此,他在女性同事面前也异常活跃与轻佻,在赶赴三闾大学途中,“他向孙小姐问长问短,讲了许多风话”[1]149。到了三闾大学,笃定认为自己会做中文系主任,忘形之下非常露骨地流露出轻薄之意、觊觎之心:
“孙小姐,你改了行罢,不要到外国语文系办公室去了,当我的助教,今天晚上,咱们俩同去开会。”[1]184
与李梅亭的粗俗相较,霍华德表现得温文雅致。如在两性关系上,他总是利用时髦的社会学激进理论、教师身份的便利追逐女性,“四处拈花惹草,好多年以来他都是这样”[3]53。从同事到学生,从与弗洛拉·本尼弗姆的默契偷情,到来者不拒、不加选择地与学生费利西蒂·费依滥情滥性,不择手段地对清纯的凯琳妲小姐追逐、诱惑与威逼诱骗。无论是与妻子芭芭拉,还是与情人弗洛拉·本尼弗姆,以及与凯琳妲、费利西蒂·费依的相处中,一贯言行不一,与其交往的人都或多或少认清了这一点。弗洛拉·本尼弗姆更是一针见血指出:“我认为你喜欢撒谎”[3]180,“对你朋友来说,你是一个骗子,也是一种伤害”[3]189,“当事态顺应你的时候,你总能表现出一种优雅的正义感”[3]122,“你既不真诚也不公平”[3]141。这些无不彰显出冠冕堂皇的学者外表下隐藏着情场老手的真实内在及其“恶”与“丑”的本来面目。
言行不一、表里矛盾的实质是真与伪的对立。人们常常将“真、善、美”与“假、恶、丑”对举,不论东西方,“真诚”都是修身、为人之本。“子思以诚为宇宙之本,而人性亦不外乎此。”[8]13“真”是为人的基本伦理,而李梅亭、霍华德抛弃本真,一以贯之地以假面示人。“谎言总是有其根源的,即意欲在其他个体之上来扩展一个人自己意志的疆域……谎言就其本性而言,它是非正义的、恶毒的和卑鄙的产物。”[9]他们二位在日常生活中扮演的角色都是典型的“伪君子”,其伦理悖论无疑具有深刻的反讽性质。
其二,在职场生涯中的伦理悖论。在李梅亭与霍华德身上,既存在身份、地位与角色的悖论,也存在角色与角色的悖论。作为教师,传统的身份、地位赋予其定位是“传道授业解惑”的知识人角色。但在现代大学,人文知识分子的身份、地位或多或少使其身兼两种角色——政治人与知识人:教师的知识人角色是其“立身之本”[10]135,政治人角色要求其“经世致用”[10]79。但这两种角色其实在很多情况下是矛盾、冲突的,勉力扮演会让人力不从心、捉襟见肘。为此,韦伯告诫说“教师不应是领袖”[11]41,“在100名教授中间,至少有99名……不能要求做行动领域的领袖”[11]42。韦伯强调的是教师要扮演好知识人角色,而非政治人角色。在职业生涯中,李梅亭和霍华德更为重视的似乎是自己的政治人角色。
李梅亭与政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原先是“一个什么县党部的前任秘书”[1]154,到三闾大学后为中国文学系主任头衔落入汪处厚之手而耿耿于怀,后来总算谋得“训导长”一职。“训导长”是国民党推行党化教育的产物,带有人人讨厌的政治色彩。在金钱上深入骨髓的自私自利、在异性面前的种种失态,这与他专司维护学校风纪的训导长身份形成了深刻的反讽。不仅如此,“李梅亭一做训导长立刻戒香烟,见同事们照旧抽烟,不足表率学生,想出来进一步的师生共同生活”[1]212模式,一本正经中显示出一副小人得志后以势压人的丑陋嘴脸。
霍华德同样如此,他参加政治集会、定期举办聚会,都是为了巩固自己激进领袖的身份和地位。霍华德是“一位激进的社会学家”,“关于各类革命而开设的课程是这所学校著名的重点学科”[3]3,他将自己的激进政治偏见带入职场生涯中,为了达到政治目的,精心策划了“卡莫迪事件”,并无中生有制造了“曼格尔事件”,其中蕴含的多重职业伦理悖论,可参见笔者相关论述[12]。
李梅亭与霍华德作为教师,对超越职业身份的诸多私利的追求构成对教师操守及人格实质上的否弃,教师身份与其角色扮演出现严重错位,政治人角色压倒了“立身之本”的知识人角色。
总之,他们在职场生涯中道貌岸然的身份表象,与其庸俗无聊、滑稽可笑的角色扮演所形成的伦理悖论,无疑具有强烈的喜剧效果和深刻的反讽性质。
(二)同中有异的伦理悖论
虽然李梅亭与霍华德在日常生活、职场生涯中呈现出相同的伦理悖论,但由于时代、社会、文化等环境因素的差异,也由于素质和教养等个人先赋性因素的不同,其形象显示的伦理悖论又各具特点。
首先,环境差异导致的伦理悖论差异。“每一种阶级环境都产生不计其数的影响,使人形成具有持续性的人格,这种影响从一个人出生起就开始发生作用。”[13]李梅亭与霍华德生活在不同的“围城”中,这使其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宏大叙事领域和在私人生活、职场生涯领域都呈现出不同的伦理悖论。试以权、利、色为例。在谋求权力方面,李梅亭无论是即将就任自以为胜券在握的中文系主任时,还是实际担任训导长一职时,外露于行的都是小人得志后得意忘形的低俗;霍华德则是深藏不露地精心设计“卡莫迪事件”“曼格尔事件”,内贮于心的是自己在激进分子中的权威和个人利益的实现。在追求物质利益方面,李梅亭的谋利性本质决定了他对蝇头小利的斤斤计较,从而充分暴露出知识分子受制于经济的寒酸与猥琐;而霍华德“不崇尚财产”[3]51,并把“财产就是盗窃”[3]39挂在嘴边,这与其进入精英阶层衣食无忧不无关系。在追求异性方面,李梅亭赤裸裸的无耻近乎于流氓混混,霍华德则总是显得“高雅”,在新潮理论的粉饰下让他觊觎的女性主动投怀送抱。虽然在权、利、色方面二人表现形式有差异,但其存在的身份与角色、角色与角色的伦理悖论却是一致的。
其次,个人素质差异导致的伦理悖论差异。李梅亭大致可以归纳到我们通常所说的学术混混、政治混混之列,其内在精神的缺失、无聊使其伦理悖论显得猥琐而粗鄙;霍华德是随历史一道前进的人,与历史存在共生关系,其伦理形象则显出盗亦有道的理直气壮。
综上所述,李梅亭与霍华德的伦理悖论既具有相似性,也存在差异,且在知识分子中具有相当的普遍性和典型性。
三、讽喻:李梅亭与霍华德·科克形象的镜鉴意义
作为著名校园讽刺小说中的人物,李梅亭与霍华德都是其特殊“围城”的产物,其形象蕴含的伦理悖论带有强烈的谐趣与喜剧色彩。“喜剧是指通过呈现那种荒谬背理的人物及其行动,使人认清他们的存在是无根据的,通过笑直接否定他们的合理性。”[14]诚然,喜剧并不仅限于表层的滑稽,更要颠覆性地促使读者(观者)反思,努力寻找可笑情境背后的深层原因,从而在对人生和社会问题的严肃思考中由嬉笑转为严肃,甚至痛彻地进入悲凉之境。鲁迅先生对喜剧中的讽刺手法曾有经典论述:“迨吴敬梓《儒林外史》出,乃秉持公心,指摘时弊,机锋所向,尤在士林;其文又戚而能谐,婉而多讽;于是说部中乃始有足称讽刺之书。”[15]189钱钟书与马尔科姆·布雷德伯里两位学者型作家,长期生活在与李梅亭、霍华德相似的“围城”中,与吴敬梓“多所见闻,又工于表现……皆能在纸上见其声态”[15]303相似,在《围城》与《历史人》中动用了让对象变得滑稽可笑的矛盾、反语、夸张等种种艺术方法,以最具社会功利性和反抗性的讽刺笔法成功塑造了“类型化人物”李梅亭与“圆形人物”霍华德两类新儒林形象,其讽喻意义、镜鉴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作者“秉持公心,指摘时弊”,揭露了知识分子内在精神缺失的痼疾。无论在西方还是东方,对于大学、教师、知识分子都有很高的期许,“围城”中的知识分子身上或多或少笼罩着一种光环,如“知识就是力量”“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心和良知”等。许纪霖先生认为:“大学是要有灵魂的,这个灵魂一定是超越的,与凡俗不相干。”[16]蔡元培先生认为:“教员者,学生之模范也。故教员宜实行道德,以其身为学生之律度。”[8]166许倬云先生认为:“张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事开太平’的话概括对中国知识分子的期许,同时也是中国知识分子应有的四个方向或维度。”[17]李梅亭、霍华德具有“学为人师,行为世范”的教师身份,人们对其期许自然很高,不仅要求他们具有渊博的学识,更要求他们具有崇高的道德,“提高整个人类道德风尚是每一个人的最终目标,不仅是整个社会的最终目标,而且也是学者在社会中全部工作的目标”[18]。但无论是李梅亭还是霍华德,其身份与在现实中的角色扮演出现的伦理悖论,都与社会对知识分子的期许相去甚远。李梅亭在金钱、女色等日常生活中的粗鄙、轻薄,在职场生涯中乐于用政治角色取代学者角色的小人得志,其知识分子内在精神的缺失不仅是那个特定时代的历史缩影,而且在学界精英担当更多社会责任的今天同样具有镜鉴意义。霍华德凭借着自己掌握的一套学术话语谋求到了学术教职,并利用掌握知识的权力使知识话语转换为权力话语,并将其变成在私人生活和公共职场生活领域谋求权力的工具,其身份与其角色呈现的伦理悖论同样展现了知识分子内在精神的缺失,不仅为那个特定时代西方知识分子存照,在今天也同样具有鉴察意义。
第二,对知识分子形象的塑造带有省察自身的意味。作为长期浸淫学界从而洞悉学界内幕的学者、作家、文评家,钱钟书和布雷德伯里选取他们最熟悉最擅长的学界作为展露冰山一角的背景,用犀利的笔锋描摹出最能代表时代精神的知识分子世态百相。钱钟书在《围城》自序中透露作品是自己“锱铢积累”而成,通过对“新儒林”的描写和对一批归国留学生或高级知识分子形象的塑造,作家对学界的洞察与自身的体悟融为一体,多少带有自我反省的意味。布雷德伯里在评析自己创作的小说人物时也坦陈:“尽管在许多读者眼中霍华德也许完全是一个无耻小人,我却觉得自己离心目中的霍华德很近。”[19]李梅亭与霍华德在日常生活中的言行不一、表里矛盾,在职场生涯中的身份、地位与角色的悖论,特别是知识分子的知识人角色与政治人角色的混同,其实是在人文知识分子职业生涯中普遍存在的问题。中国从古至今以儒家学说为宗,士大夫(兼具知识分子与官吏身份)皆有入世情怀,历来缺失“‘为知识而知识的’传统。上焉者是为了充实自己的人格而知识,为天下国家而知识。下焉者是为了暖衣饱食而知识,为了升官发财而知识”[20]。李梅亭与霍华德为了蝇头小利和政治利益而游走在政治与学术之间,“学术精英”趋向庸俗化、反智化并非个案。“每一位个体的人生都是社会历史的一段插曲,后者为前者拉开序幕并会延续下去”[6]23,李梅亭与霍华德虽然已经成为“历史人”,但他们的幽灵还在今天的学界徘徊,这对于今天的学人如何为人处世、如何正确处理“知识人角色”与“政治人角色”之关系无疑能够提供警示意义。
第三,消解知识分子精英形象与精英文化为读者预设的神化效应,体现出作家自觉的现代忧患意识和批判精神。李梅亭与霍华德的诸多伦理悖论说明,文明与知识未必一定会塑造出真正的精英,高等学府这座“围城”也并非净土,无论是在动荡的时代,还是在改革开放的今天,都供养、庇护着大量表里不一、实用主义至上、以恶治善的李梅亭与霍华德似的“精英”。钱钟书与马尔科姆·布雷德伯里通过对李梅亭与霍华德在钱、权、色上的疯狂追逐,展现了“围城”里“精英”身上出现的伦理悖论——大度慷慨下的卑鄙自私,道貌岸然下的虚伪下流,故作高贵下的浅陋庸俗,貌似风雅中的粗鄙愚蠢,一本正经的乏味无聊——借此展现了他们堂皇华丽外表下可鄙、可恨而又可悲的灵魂与气质。这些“围城”里的“精英”,都像金漆笼中的小鸟和城堡内外的人群一样,茫然而卑琐地为自身名利和安乐在勾心斗角、巧取豪夺,由此,也消解了知识分子精英形象与精英文化为读者预设的神化效应。
更加难能可贵的是,作者并不专门着意于道德意义上的褒贬讽刺,讽喻的同时也体现出作家深深的疑虑:“围城”里的“历史人”能够真正走出“围城”而成为人格健全的现代人吗?知识精英能够不忘初心,固守本真,坚持自由自主思考,不随波逐流,不被严苛的生存环境异化,不为各种人为规则、制度所规训吗?知识分子能够克服李梅亭与霍华德的伦理悖论、不被历史潮流所裹挟而坚守知识分子的基本操守、坚守人文主义价值观吗?深具社会意识与公共意识的两位作家在诠释不同历史环境中的知识分子时,塑造的形象却有着惊人的一致性,都反映出不同时代、不同背景下知识分子需要予以正视的弱点与痼疾,表现出作家自觉的现代忧患意识和强烈的现代批判精神。“文学的现实价值就是历史价值的新发现”[21],虽然“围城”中的李梅亭与霍华德已然成为“历史人”,成为被历史唾弃的人物,但李梅亭、霍华德等人物形象所蕴含的伦理悖论,在知识分子中并非个案,而是带有一定普遍性,在当时和今天的社会语境下都具有相当的典型性。钱钟书和布雷德伯里勇于剖析自身所在的知识分子群体,揭露“知识精英”们的伦理悖论、学界存在的问题及大学体制内的弊端,既为历史存照,也对今天重塑大学灵魂、重塑知识分子健全人格具有一定的镜鉴意义。
参考文献:
[1] 钱钟书.围城[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
[2] 张媛.论《历史人》中芭芭拉·科克的悲剧人生——从女性性别角色层面解析[J].江苏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1):36.
[3] 马尔科姆·布雷德伯里.历史人[M].程淑娟,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12.
[4] 艾伦·G·约翰逊.见树又见林——社会学与生活[M].喻东,金梓,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90.
[5] 郑杭生.社会学概论新修[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140.
[6] 乔恩·威特.社会学的邀请[M].林聚任,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7] 聂珍钊.文学伦理学导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265.
[8] 蔡元培.中国伦理学史[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3.
[9] 叔本华.叔本华论说文集[M].范进,柯锦华,秦典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595.
[10] 胡金平.学术与政治之间的角色困顿——大学教师的社会学研究[M].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11] 韦伯.学术与政治[M].冯克利,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
[12] 张媛.社会学视阈下《历史人》霍华德·科克形象的伦理透视[J].广西社会科学,2016(5):161-166.
[13] 彼得·L.伯格.与社会学同游:人文主义的视角[M].何道宽,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94.
[14] 王一川.美学原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52.
[15]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
[16] 许纪霖.读书人站起来[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110.
[17] 许倬云.知识分子:历史与未来[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5.
[18] 费希特.论学者的使命 人的使命[M].梁志学,沈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45.
[19] LERNER L.Somebody’s best book yet[J].The Spectator,1987(9):30.
[20] 徐复观.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86.
[21] 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基本理论与术语[J].外国文学研究,2010(1):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