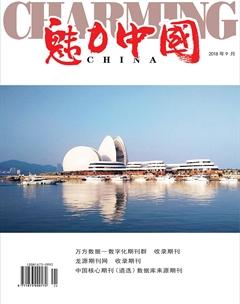论低保制度中的“福利污名”
尹婉霞
摘要:在我国,以现金补偿为主的低保制度极大缓解了贫困群体的生活压力,同时基于家计调查、具有选择性的低保制度又容易产生“福利污名”,继而延伸出社会排斥与瞄准偏差等社会问题。福利污名不仅来自“低保对象”的标签效应(身份污名)和认定受助者的家计调查程序(程序污名),更是由于“福利依赖”现象产生的刻板效应,以及低保制度非积极赋权型的救助模式。缓解福利污名需通过消除低保对象的标签歧视、重视就业救助、完善社会救助的递送程序、增强民众受助的权利意识等对策实现。
关键词:低保制度;福利污名;身份污名;程序污名
一、“福利污名”的研究缘起及其内涵介绍
随着我国经济和社会转型,贫富差距扩大、失业人数增加,贫困群体数量大增。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简称低保)应运而生,其是国家为生活在贫困线之下的社会成员,提供满足最低生活需要的物质帮助的一种社会救助制度[1]。以现金资助为主的低保对缓解贫困群体的生活压力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我国,低保制度遵循选择性原则,主要依靠家计调查制度确定受助者资格,福利污名常常被认为是家计调查建构与实施的结果[2]。许多研究已经表明,“福利获取”与“福利污名”间存在联系;如果贫困与羞耻感紧密相连,就有可能产生福利污名[3]。
美国社会学家戈夫曼最先使“污名”概念化:当一个陌生人所具有的特质使得他被归类到坏的、危险的、虚弱的类群时,他的形象就会从一个完整的普通人减损成一个玷污的人;当这个特质使得拥有它的人遭到贬损的影响越大,则这类特质就是一种污名[3]。“污名”是人们对群体或自己的刻板印象而导致的认知偏颇、消极情绪以及行为反映的综合结果。福利污名是受助者接受福利時遭遇的污名歧视和被排斥的过程,包括身份污名和程序污名[4]。一方面是社会对受助者存在贬低性、侮辱性的标签歧视,另一方面是部分严苛的申领条件有损受助者的尊严,受助者由此会产生羞愧耻辱心态,并导致社会对其不公正待遇的结果出现。
作为一个人口大国,2016年我国城市和农村居民低保人数已达6066.7万人,研究这一庞大群体乃至所有社会救助对象面临的“福利污名”具有深切的价值意义,旨为缓解受助者“福利污名”和完善现有的社会保护政策提供思路。
二、“福利污名”的延伸问题
(一)“福利污名”与社会排斥
回顾学者的研究,社会救助政策通过福利污名有导致社会排斥的风险。1974年,法国学者勒内·勒努瓦最先使用“社会排斥”概念来说明被排斥在就业岗位和收入保障制度之外的特定社会边缘群体的“被排斥”状态[5]。救助对贫富差距的调节作用有限,且可能带来福利污名和福利依赖,肖萌、梁祖斌[6]认为社会救助不但不能解决社会排斥,反而会加重社会排斥。社会排斥即是社会对被贴上污名标签的人所采取贬低、疏远和敌视等态度和行为,是污名化的结果,包括在劳动力市场、主流社会关系及主观层面的社会排斥。
社会救助的两大目标是:为贫困者提供物质帮助、消除对贫困者的社会排斥。本意是促进社会公平、缓解贫困者社会排斥的社会救助政策却在实际运行中因福利污名加剧了社会排斥,使得贫困者丧失了发展的机会和被剥夺参与的资格,在机会上被长期排斥在外。此为典型的福利悖论——在解决原问题的同时产生了更大的问题[4]。
(二)“福利污名”与瞄准偏差
部分贫困者由于羞耻感和污名感放弃了社会救助申请从而导致瞄准偏差现象的出现,这便是福利污名给贫困者造成的阻碍效应。当羞耻感和污名感被作为一种政策工具时(政府利用负面标签合法地阻止非贫困者申请社会救助,防止福利依赖),政策实施的意外后果往往是导致两种类型的瞄准偏差的产生,一是排斥性偏差:真正贫困者放弃申请低保;二是内含性偏差:非贫困者由于感受不到深刻的羞辱而积极申请低保,从而使瞄准偏差现象更突出[3]。
社会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中如何削弱福利污名、提升瞄准精度,让贫困者更有尊严地获取社会援助已经成为西方社会政策研究中富有生命力的重要话题。但目前国内学者还较少从福利污名角度分析瞄准偏差。
三、“福利污名”现象的产生原因
(一)身份污名:“低保对象”的标签效应
身份污名是指作为选择性救助的低保制度“认定身份”时伴随的耻辱感。受助者的身份认定与贫困状况有关,而贫困往往会带来羞耻感和污名化,“社会救助接受者”的标签会构成受助者的心理障碍并使得贫困者失去与其他社会成员的平等性[3]。贫困者在申请低保时就处在弱势状态,成为低保对象后,会被贴上困难户、拿政府的钱等标签,或会被周围人用异类眼光看待,人际关系上经受歧视和排斥。总之,“低保对象”是一个很明显的标签,需承受一定的心理压力。
(二)刻板效应:针对“福利依赖”现象产生的福利污名
处于劳动年龄具有劳动能力但宁吃低保不愿就业的“懒汉”,被归为不值得救助的低保对象,其依赖行为具有强烈的污名化。学者桑德斯认为,福利依赖具有文化上的驱动力,他将过去用于形容穷人的词汇,如自控能力差、好逸恶劳重新拿来形容福利依赖者,试图使人们相信受助者具有懒惰的生活习性和较低的自尊,形成了依赖文化[7]。当福利依赖风气盛行,人们在认知某一个低保对象时,便会产生刻板效应:该受助者是一个好逸恶劳、欺诈低保的“懒汉”,从而加剧了福利污名。
(三)程序污名:基于认定受助对象的家计调查程序
我国低保的申请程序是较为严格和复杂的,申请者需接受家庭收入和财产状况调查。程序污名是指受助者在接受救济时遭遇的“民主评议”和“张榜公示”等不友好的家计调查程序及工作人员的无礼对待等。大量学者在社会救助的申请程序、申请者与执行者的互动过程中发现了导致污名化的具体逻辑[3]。贫困者为了换取物质上的利益,需损害自尊承受一定的社会压力。同时,程序污名或会使贫困者产生退缩心理而放弃申请低保,这其实是低保制度的异化。
(四)低保制度:一种“基于回应的援助”救济模式
我国城市的低保政策主要是为了缓解当年下岗潮工人的生活压力而设立的,旨在维持社会的稳定。该制度与美国学者苏黛瑞提出的“基于回应的援助”模式类似,是消极回应而非积极赋权型的福利供给模式,以有限的物质救助为主,较少关注贫民的权利及精神需求[4]。然而我们应该意识到接受救助是贫困者的权利,是其生存权和发展权的重要体现,国家必须予以保障和满足。目前,社会各界包括救助主體、救助对象和普通群众对受助权利的意识皆相对模糊,这无疑是福利污名化的原因之一。
四、“福利污名”的缓解思路
(一)消除“低保对象”的标签歧视
1.加强受助对象的心理辅导
积极开展心理救助服务,加强受助者的心理辅导,鼓励其多与外界沟通交流,培养受助者在人际交往中的自信,增强权利意识,积极正面地对待标签歧视,增强心理承受能力。
2.营造良好的受助环境
落实政府层面对救助弱势群体的义务和责任,提升工作人员的素质,并做好受助宣传;鼓励普通大众多与受助者接触,充分了解他们的生活困境,感同身受,消除对贫困者的歧视心理。携手营造良好的受助环境,共建社会支持网络,消除“低保对象”的标签歧视[8]。
(二)重视就业救助,避免“福利依赖”现象
通过就业培训、就业补贴、岗位提供等方式积极开展就业救助,提升受助者的人力资本和自身素质使之摆脱困境。构建就业关联机制,减少“懒汉”数量,谋求独立发展。社会救助理应向发展型救助转变,除了要为贫困者提供满足基本生活需要的物质救助外,更应该为其创造发展机会,让其有机会有能力依靠自己的劳动不断发展自己,实现自我价值,进而消除在受助过程中的“污名感”。
(三)完善社会救助的递送程序,优化社会救助模式
加快建设居民家庭收入核对机制,运用高效的信息化手段强化瞄准机制,削弱不友好的家计程序带来的污名感。培育专业的社会救助机构和人员,充分发挥社会工作者的优势,为受助者提供社会融入、能力提升、心理疏导等专业服务。尝试以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引入市场力量,改变以民政部门为主逐级递送的社会救助方式。贯彻“人性化”的服务理念,优化救助模式,使社会救助真正满足受助者的需求。
(四)增强民众受助的权利意识
与西方成熟的福利国家相比较,东亚国家的社会权利意识还处于初步发展阶段[3]。我国的救助范式应向赋权型福利模式转变,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应该意识到消除贫困的途径在于赋予贫困者利益表达和实现自身权利的途径[4]。通过宣传教育,让公众认识到接受救助是贫困者享有的正当权利,突破传统的“施舍”和“感恩”心理,减弱贫困者申请低保时的污名感。民众受助权利意识的增强,将成为贫困者申请救助的“拉力”。
参考文献:
[1]刘娟、何少文.社会救助政策与实务[M].广州:广东经济出版社,2015:31
[2]祝建华、林闽钢.福利污名的社会建构--以浙江省城市低保家庭调查为例的研究[J].浙江学刊,2010,(3):201-206
[3]李棉管.技术难题、政治过程与文化结果--“瞄准偏差”的三种研究视角及其对中国“精准扶贫”的启示[J].社会学研究,2017:230-238
[4]王锦花.福利悖论:中国社会保护中的社会排斥--基于广州市的实证研究[J].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69(2):39-45
[5]熊光清.欧洲的社会排斥理论与反社会排斥实践[J].国际论坛,2008:14
[6]肖萌、梁祖彬.社会救助就业福利政策研究[J].社会保障研究,2010:96
[7]刘璐婵、林闽钢.“福利依赖”:典型与非典型的理论透视[J].社会政策研究,2017:4-6
[8]汪亦泓、柯仲锋.论“福利污名”及其应对策略[J]. 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13(58):3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