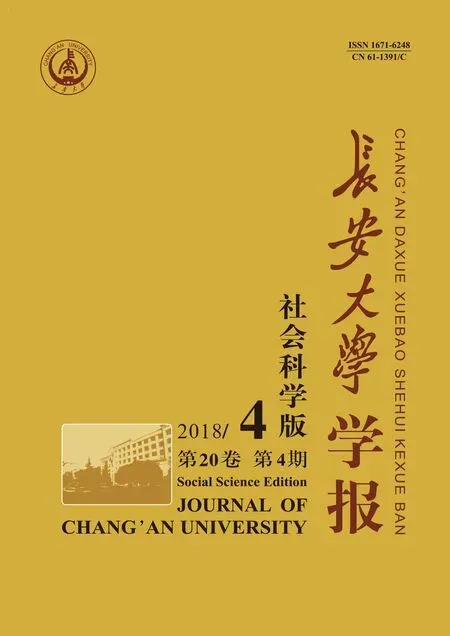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及其历史基础
张茂泽
(西北大学 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陕西 西安 710069)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总任务之一。实现这一伟大历史任务,不能不研究和解决民族问题。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们在新时代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全面贯彻党的民族政策,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坚决反对分裂祖国、破坏民族团结的行为。
一般地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两个显著特点:它不是人们主观设定的,而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它不是今天才有的,而是中华民族史、中华文明史长期发展的历史产物,有深厚历史基础、悠久历史传统。瞿林东说,在中华民族史上,民族关系有种种复杂情况,但“总的趋势是各民族间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历史文化认同的程度越来越深入,形成伟大的合力,共同创造了光辉灿烂的中华文明,共同推动了中国历史发展,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奠定了历史基础。”[1]我赞成这一历史论断。确实,中华各族在交往中互相交流,在交流中互相交融,逐步形成了有机一体、不可分割的密切关系。在生产发展、社会进步方面,各民族相互影响,携手进步;在近代民族危机、国家危亡时,各民族团结奋斗,共同抵抗外侮,维护国家的独立和稳定。这些不仅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历史基础,而且蕴含了兄弟般的平等交往精神,家人一样的团结奋斗、共同进步精神。渗透进各民族当中的这些因素,成为我们今天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源泉。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人们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意识。它作为中华民族的心理活动,既包括对中华民族身份的认同,有深厚的民族感情,也包括对中华文化传统的认同,对中华文化的自觉、自信,对美好生活的共同向往。它体现到每个中国人身上,就是大家的民族认同;民族认同中,也历史地渗透进了文化认同、国家认同等。在古代人文化成、文野之分等观念影响下,中华民族不限于以种族、血缘立族,而尤其以文化立族;中国不限于以种族、血缘而成的民族所居政治地域立国,而尤其以文化立国。文化,在根本意义即文明化。人们致力于提高自己的修养,并帮助家人、国人、天下人提高修养,使整个社会进化到文明程度,是中华民族、中国的本质特征。故中华民族共同体、中华文化共同体和中国这一国家共同体,三位一体。其中,中华民族是主体,中华文化为其本质内容,中国则是政治表征。
有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会认同56个民族一家人,认同大家都是中国人,都是中华民族的一员;就会感受到56个民族一家亲,兄弟同心,守望相助,共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宏伟目标;就会齐心协力,团结互助,努力提高各民族科学文化水平,奔向全面自由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
仅仅从中华民族史角度看,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中华各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中华各族兄弟一家的观念史,都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和丰富提供了丰厚的历史基础。
还要特别指出,几千年连绵不绝的黄帝文化,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比如,司马迁著《史记》,以黄帝开篇,并将北方匈奴民族描写为“夏后氏之苗裔”[2]。在此影响下,魏晋南北朝时期,入主中原的北方少数民族,如匈奴、鲜卑、羌等,纷纷被描述为黄帝的后裔。认定黄帝是民族始祖、多民族共祖,认定黄帝是中华文明的人文初祖,认定黄帝是华夏旗帜,就是历史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表现之一。今天,我们认同黄帝陵是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新时代的表现。
一、外来民族理论的中国化
“中华民族”概念,最早由梁启超在1902年《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3]的著作中提出,但中华民族共同体并非近代才产生。
大家知道,斯大林界定的民族概念,指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产方式、共同的文化特征而来的共同心理构成。有学者指出,这个定义主要指“近代民族”[4],在方法上主要是性质分析、列举,不是马克思民族观的全部;更不能用这个定义硬套古代,认为古代没有民族出现。因为民族本就是一定历史的产物,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变化。原始社会还没有民族产生,共产主义社会民族会随着国家的消亡而消亡。近代民族也不是突然产生的,而是古代民族的进一步发展。在历史上,从原始社会末期开始,氏族、氏族部落、部族,就是古代民族的起源。古代民族发展还不完备,未必有近代民族各方面的特征;但仍然不失为民族共同体。认识历史上的民族共同体,尤其是观察古代的民族共同体,不能以今律古。应从民族史实际出发,参照其他民族,如实认识中华民族的产生和发展,归纳中华民族特征,才是科学的。
在中国民族史上,各民族长期居住在中华大地上,共同创造了中华文明。他们在生产生活、语言文字、风俗习惯上都互相影响、水乳交融。比如,既有少数民族汉化,也有汉族少数民族化,从长远看前者是主流。因为互相影响,导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许多民族的特征都不很鲜明。
比如,汉族,因为各地方言众多,各地地理、气候差别很大,平原、盆地、山区、草原、沙漠、海滨、湖区等,经济产业大不相同,各地风俗习惯也有很大差异。汉族本就是历史上华夏族和众多少数民族交流融合的产物,是多民族融合的代表。汉族的民族特征不突出,许多少数民族也如此。
又如贵州穿青人。明初,朱元璋派遣江西、湖南兵征讨云南。战事结束后,一些兵将聚居于贵州西北部毕节、安顺、六盘水一带。他们租佃彝族的土地耕种,故他们既说汉语,也有一些彝族语言。风俗习惯少数民族化,但经济生产还是汉族的。他们说“老辈子话”,实际上是当时贵州本地的汉语方言,这是穿青人。明末,更多的汉人进入当地经商,他们说着另外的汉语方言,称为穿蓝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穿蓝人登记为汉族,穿青人要求登记为少数民族,得到国家承认。
又如,锡伯族,自称鲜卑人后裔,原来是游牧民族,主要居住在中国东北松花江中游和辽河流域,即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和内蒙古自治区。但现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也有分布,而且设立了察布查尔斯锡伯族自治县。原因是,乾隆二十五年(1760),锡伯人被抽调到新疆伊犁一带驻防。他们在当地定居下来,开荒修渠,娶妻生子,逐步转变为以农耕为主的民族。新疆锡伯族保留了锡伯语言,一种在满文基础上形成的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民族特点较鲜明,而东北的锡伯族却已使用汉语。
可见,我们可以从中国历史出发,根据中国民族史情况,提出中国“民族”概念,或对外来民族理论进行中国式理解。如20世纪30年代,吕思勉说:“在中国,民族观念,虽未见晶莹,然中国民族,则久经存在;而且从其演进之迹说起来,中国民族,真可称为民族之模范。”他根据中国的民族实际,提出民族的概念是:“民族,是具有客观条件,因而发生相同(对外即可称为特异)的文化;因此发生民族意识,由此意识而相团结的集团。”[5]这个概念强调文化特性和民族意识,我认为比较符合中国的民族实际情况。
20世纪50年代,中国政府展开了大规模的民族调查和民族识别工作,经自己申报和政府确认,最终确定了56个民族。在识别和确认民族身份时,许多民族的特征不那么显著,给民族识别和确认带来了困难。其中,有几个要素受到特别关注:一是族源;二是自认和他人称谓;三是语言、风俗等。这就重视了民族的文化特征和民族意识(自我意识和他族称谓)两个方面,可谓对民族概念的现实化理解,也是外来民族理论中国化的实践表现。
总体来看,中华民族是以汉族为主体,联合了其他少数民族在内的民族共同体,这种状况是历史时期形成的。白寿彝指出:“中国的历史长,幅员广,民族多,民族流动迁徙,交错杂居,在语言、风俗上互相影响,因而有相当多的民族,其民族特点不够显著,不易为人所确认。”[4]我们通常说中国有56个民族。其实1953年,各地申报民族400多个。1964年人口普查登记的民族有183个。其中,自认是少数民族但不被确认的,或自认是汉族其实是少数民族的有不少。有汉人进入少数民族地区生产生活,仍然保留汉族的文化特点,但并不知道自己是汉人,而自报为当地的少数民族,并得到国家确认。有迁居到少数民族地区生产生活,时间长了,和当地少数民族融合,与后去的汉人明显不同,自认为是少数民族,如穿青人。也有少数民族不愿表明自己的少数民族身份,一向自视为汉人。还有少数民族与汉族杂居,已经没有多少民族特点,少数民族身份得不到他人承认,却依然自视为少数民族。同一个少数民族,因为迁徙分散到其他地区居住,但保留了以前的民族特点,他们自己却不知道,于是登记为其他少数民族。民族身份难以确认,和中华民族与欧美各民族有别的历史特点关系很大。
二、中华各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主线
古代有以汉族政权为正统、以中原王朝作为历史上中国的情况。谭其骧指出,我们伟大的祖国是各族人民包括边疆各族共同缔造的,不能把历史上的中国同中原王朝等同起来[6]。同时,过去我们已经意识到,在阶级社会里,民族问题主要是民族压迫、民族歧视、民族不平等。现在我们以中华民族史为例,可以发现,各民族平等相处、团结合作、交流交融,是中华民族史的主线。
中国自古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而且至少在两千多年前,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国的疆域、历史与文化,都是中国这56个民族及其祖先在几千年发展过程中共同开发、创造出来的。今天的中国,是中华各族共同缔造的,中华文明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
我们知道,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决于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历史上中国各民族形成中华民族共同体,也有其生产、分工和交往的历史基础。各民族在社会生产分工基础上相互协作,共同发展繁荣,是民族关系真正友好互助的物质基础。
中华文明在世界上独树一帜,源远流长。它的渊源、产生和发展,都离不开各民族的创造与发明。例如,汉族首创了造纸、印刷、指南针和火药四大发明;维吾尔族和黎族最先学会了棉花的种植和纺织;回族建筑师亦黑迭尔丁规划并主持修建了元大都(今北京),为北京成为世界名城打下了基础;藏族保存的两大古代佛学著作《甘珠尔》和《丹珠尔》(即藏文《大藏经》),至今是中华文化宝库中的两件瑰宝;汉语普通话的发音特点,是受蒙古语的影响而形成的。凡此种种,不胜枚举。
纵观历史,几千年来中华各族的团聚和统一,始终以中原地区为中心,以汉族为主体而日益发展、壮大。
早在传说时代,在距今五千年前,在中原黄河流域,主要有夏族;在东部的淮河流域和泰山之间,有东夷;在南方的长江流域,有三苗;在西北地区的黄河与湟水间,有羌族;在北方的蒙古高原,有獯鬻。夏族与周围各族都有交往联系。
到了夏、商、西周和春秋、战国时期,根据文字记载,各族之间交往更加密切。在黄河流域有夏、商和周族,东方有夷族,东北有肃慎,北方和西北有狄、戎、羌、氐,南方有蛮、越等民族。在此期间,以夏族、周族和商族为主,吸收了夷、羌、狄、苗和蛮等民族的成分,演化成华夏族,并且相继建立了夏、商和周朝,国家的疆域越来越大,包容的民族越来越多。
秦、汉时期,华夏族吸收了更多其他民族的成分,形成了汉族。汉朝的疆域,东至大海,在西边一度包括了今新疆各民族,在北方越过长城,统一了南匈奴,控制了内蒙古,在南方,它的行政机构越过五岭(今福建、广西、广东)一直设立到海南岛。
到了隋、唐时期,中原王朝疆域进一步扩大。隋朝的鲜卑族大臣在朝廷中占有很大比重,隋朝皇后也多为鲜卑人。唐朝前期,中央政府官员几乎一半是少数民族。唐朝后期,军队中的高级将领有一半以上来自契丹、突厥、回纥、高丽等少数民族。唐朝政府主要依靠北方少数民族骑兵,控制了北到黑龙江和贝加尔湖,西到巴尔喀什湖和中亚两河流域的广大地区。
到元朝,其版图“有汉唐之地而加大”,人口“有汉唐之民而加多”,包括西藏的藏族在内,所有民族都统一在一个中央政权下。到了清朝,中国多民族统一更加巩固。
几千年来,中华各族日益密切的交往、团聚和统一的过程,也是民族大融合的过程。各民族经过不断迁徙、杂居、通婚,以及其他形式的交流,在文化上相互学习,在血统上互相混合、交融,使各民族、各地域间界限日渐淡漠,而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和心理特征则逐渐产生、形成。
中国的主体民族——汉族的形成和发展,就是各民族大融合的结果。早在先秦时期,中国存在着华夏、东夷、北狄、西戎和百越五大民族集团。古代就有舜为“东夷之人”、周文王为“西夷之人”[7]的说法,可知华夏族本就是在夷、夏融合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有人考证,齐国大臣管仲名夷吾,也是夷人。春秋时期,狄人部落大量散布于黄河以北,与华夏人通婚的记载很多。如晋国国君重耳的母亲就是狄人。南方的吴、越两国,就有大量越人。秦统一天下,原散布于中原的夷、狄、戎、越大部分融入了华夏族。
汉代以后,少数民族不时入主中原,也大规模融入汉族。如西晋末年,鲜卑、羯、氐、羌和匈奴5个少数民族乘乱进入中原,分别建立了十几个政权,史称“五胡十六国”。一百多年以后,这些少数民族都发生了汉化,成为中华民族的新鲜血液,推动了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
女真人建立的金国占据黄河流域以后,有“几百万口”女真军户迁徙进入河南,结果全部汉化了。原居于东北的满族人,随着清朝的建立,大部分迁徙进入关内。到清末,这些人完全丢弃了满文、满语,使用汉语、汉文,饮食起居和汉族差别已经很小了。
进入中原的少数民族,有的主动向汉族学习。如鲜卑族的北魏孝文帝拓拔宏进行汉化改革,发布命令要求鲜卑族学习汉语,穿汉族服装,改汉姓,鼓励和汉族通婚,加快了鲜卑人与汉族的融合。也有的少数民族统治者,反对汉化。如金世宗完颜雍规定:“禁女直人不得改称汉姓,学南人衣装,犯者抵罪。”[8]正式称帝、建立清朝的清太宗爱新觉罗·皇太极也发布过如下命令:不许“废骑射而效汉人”,“有效他国衣冠、束发、裹足者,治重罪”[9]。他们还禁止满、汉通婚,禁止满人经营商业、从事农业生产,甚至封锁东三省,不准汉人前去开垦等。
但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是进步的历史现象。特别是那些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低于中原汉族的少数民族,一旦进入黄河流域这个汉文化的摇篮,他们终究会融入先进文化的汪洋大海之中。正如恩格斯所说:“比较野蛮的征服者,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不得不适应征服后存在的比较高的‘经济情况’;他们为被征服者所同化,而且大部分甚至还不得不采用被征服者的语言。”中国历史上进入中原地区的少数民族统治者,大都经过了这样的发展过程。
元代的蒙古族也是如此。蒙古统治者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于1233年就在燕京设国子学,让蒙古子弟学习汉语、汉文。建立元朝的元世祖忽必烈也曾下令诸王子及近臣子弟跟随汉族儒家学者学习经典,皇子皆受双语教育。有学者考证,元朝科举前后十六科,共录取进士1 139人,其中蒙古人三百余人。曾经埋首汉文经籍、投身考场的蒙古子弟则数以万计[10]。元朝廷还加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加封屈原为忠节清烈公,改封柳宗元为文惠昭灵公,谥杜甫为文贞。元仁宗皇庆二年,朝廷恢复科举考试,以朱熹注解的《四书章句集注》为教材、考试内容和评卷标准。元仁宗对《贞观政要》尤其重视。《元史·仁宗纪一》载,即位初,“帝览《贞观政要》,谕翰林侍讲阿林铁木尔曰:‘此书有益于国家,其译以国语刊行,俾蒙古、色目人诵习之。’”大臣察罕翻译《贞观政要》,献给仁宗,仁宗“大悦,诏缮写,遍赐左右”[11]。元朝皇帝多命讲官进讲《贞观政要》,著名学者吴澄即为其一。可见,蒙古政权不仅不排斥,反而推崇儒学。到元朝末年,很多蒙古人已改汉姓,从汉俗。元朝灭亡后,蒙古人的身份已失去了等级上的优势,许多蒙古人很快融入到汉人之中。
自汉朝以后,历代都有很多西域的僧侣、商人、军人等来到中原。有学者曾对其中有文献可考的一百三十多人进行专门研究,证明他们都接受了汉文化。其中包括今新疆的吐鲁番人、和田人、库车人、吉木萨尔人等。还有来自葱岭以西的乌兹别克斯坦人、阿拉伯人、波斯人等。古代文献中也有西域人成百上千结队来到中原的记载。如汉灵帝时,一位叫法度的大月氏人,“率国人数百名归化”。又如,唐代的雍州醴泉县北,“有山名温宿岭者,本因汉时得温宿国(今新疆阿克苏)人,令居此地田牧,因以为名”[12]。唐代于阗国(新疆和田)曾派遣一支五千人的军队进入中原,帮助平息安史之乱,再未见其返回的消息,可见已融入中原。唐朝的将军尉迟敬德就是于阗人,至今仍是流传于汉族民间的门神之一。
几千年来,汉族人融入少数民族,汉族和少数民族相互融合,这类历史记载也很多。如秦始皇曾徙五十万中原人于当时的南越(今两广地区),其中很多人就融入了越人之中。隋朝末年,中原离乱,很多汉人北逃或被虏入漠北突厥为奴。唐朝建立后,唐太宗派人携钱币、丝绸去草原上赎人,前后赎回汉人数万。回纥、土蕃、粟特和突厥等族的很多商人、使节来到中原后娶汉族妇女带回的记载也很多。如贞元三年(787),唐朝政府在长安一次就查出娶了汉妇的“胡客”(西域商人)4 000人[13]。也有汉族人被抢掠或汉族地区被少数民族占领后,汉族人被少数民族同化的情况。
由上可见,中华各族在相互交流基础上走向融合,形成多元一体格局,是中国民族史发展的大趋势。中华民族是在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相互学习、交流中逐步形成的。在这个过程中,汉族本身也在和周围少数民族交流中不断充实自己、发展壮大自己,从而成为中华民族的主体力量。之所以能如此,是因为汉族掌握了各个历史时期的先进社会生产力,成为先进历史文化的代表,引导着中华文明的发展大方向。像鲜卑、氐、满等少数民族,他们在和汉族交往中,借助汉化,让生产生活从原来较落后野蛮的社会,迈入了较先进的文明阶段。
可见,各少数民族汉化只是表象,文明化才是实质。在各民族文化交往中,各族相互融合为多元统一的中华民族,并不意味着在这个统一体中,先进与落后、文明与野蛮之间完全平等。他们相互交往的结果,既不是一进一退,相互抵消,也不是如数学上两个数相加除以二获得一平均值,而是向着文明的方向不断前进的对立统一过程。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美好的文明梦想。在奔向文明的历史征程中,谁的社会生产力水平更高,谁更加文明,谁才可能抢占民族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高地;人们根于人性的、自然表现出来的文明风度,对其他文化而言,如君子德风,具有难以抗拒的吸引力和感染力。向先进文化学习,是一个民族的内在希望,也是一种文化的历史未来。
这也体现出关于民族文化交流发展的一个历史规律:即民族文化是不同民族文化相互交流、共同发展的成果;但只有那些历史发展水平更高、生产生活更加文明的民族文化,才具有对其他民族而言更强的吸引力。
三、中华各族交往交流交融是历史发展趋势
中华各族特性不鲜明,从根本上看,是因为各民族共性在漫长历史上得以熔铸、积淀,得以强化、凸显。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指出,近代以来,社会化大生产发展导致政治集中,形成各民族利益攸关的世界历史。“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愈来愈扩大,各民族的原始闭关自守状态则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此自发地发展起来的各民族之间的分工而消灭得愈来愈彻底,历史就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成为全世界的历史。”“大工业到处造成了社会各阶级间大致相同的关系,从而消灭了各民族的特殊性。最后,当每一民族的资产阶级还保持着它的特殊的民族利益的时候,大工业却创造了这样一个阶级,这个阶级在所有的民族中都具有同样的利益,在它那里民族独特性已经消灭,这是一个真正同整个旧世界脱离并与之对立的阶级。”“原先各自独立的、几乎只是由联盟关系联系起来的,各有其不同利益、不同法律、不同政府、不同税则的各个地区,现在已经结合成为一个拥有统一的政府、统一的法制、统一的民族阶级利益、统一的税关的民族了。”可见,民族特性逐步淡化,多民族交融的民族共性日益强化,最终直到人的全人类性得以自觉和实现,是近代以来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大趋势。
马克思说的主要是欧洲近代的情况。在中国古代就出现了民族特性淡薄,民族共性产生、积累,不断强化的现象,这就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中华民族史从先秦华夷之辨,到后来中华民族共同体逐步形成和发展,最终走向社会主义社会,可以作为这一历史趋势的案例。中华民族史是多民族统一的历史,形成了语言文字、共同地域、经济生产生活、共同文化传统、共同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等等。共性突出,个性自然会淡化。
夏商周,秦汉唐,元明清等国家统一时期,固然是中华民族共性得以强化的时期。即使在国家分裂时期,中华各族共同体依然在形成、发展中,中华民族共性依然存在,并不断成长、积蓄,厚积薄发。
中国多民族统一局面的形成,经历了几个阶段:单一民族内部的统一,如夏商周各族;地区性的多民族统一,如战国七雄;全国性的多民族统一,如秦汉隋唐元明清;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为标志,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国性多民族统一局面的形成。
中华多民族统一局面的形成过程,不是一帆风顺的。中间有曲折,甚至时有反复,在一定时期出现了分裂局面,几个割据政权并立。如秦汉以后,有魏蜀吴三国分裂;西晋短暂统一后,又进入五胡十六国之乱及南北朝的对立。在唐朝和元朝之间,有五代,有宋、辽、金、西夏的对立。但即使割据时期,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中华文明的发展也没有中断。其表现为:
第一,每次分裂后,就形成了更大规模的多民族统一,如唐代的统一范围超过汉代,元代的统一范围超过唐代。
第二,地方割据政权,为了生存,大量开垦土地,拓展农业生产地域。中国古代经济重心逐步南移,就是例子。江南成为经济重心,前有春秋时期吴越的开发,后有三国时期吴国的发展,南朝宋齐梁陈继续开发,江南经济由此发展到新阶段。这些都为唐宋以后江南地区的经济繁荣做了历史准备。
第三,地方政权在政治上,也能根据本地区特殊情况,创造一些治国理政的新做法,积累一些新经验。如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如春秋战国时期开始出现的郡县制,如曹魏的屯田制,北魏的均田制,隋唐时期都有继承发展。著名的三省六部制就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得到大发展,到隋朝才定型。
第四,在思想文化上,割据政权也都使用已有的汉语言文字,信奉以儒家为主的传统意识形态,而且他们也都自称是皇朝正统,将国家统一作为奋斗目标。三国时,北方的魏国自认是汉朝的延续,要恢复全国统一。西南的蜀国以自己姓刘,自称汉室宗亲,要统一全国,重振汉家天下。南北朝时期,北朝骂南朝是“岛夷”,南朝贬北朝为“索虏”。他们都自居为中国,要消灭对方,统一全国。辽、宋、金对峙时,3个朝廷也都自命为中国的主人,设想由自己统一全中国。
在中原文明面前,一些少数民族统治者从心理上也认为汉族政权是“中华正统”,“自古无胡人为天子者”,“自古以来,未有戎狄作天子者”[4]。这些都应是当时一些少数民族政权认同黄帝共祖的心理原因。
可见,国家分裂时,中华各族终究没有撕裂,反而在进一步融合,形成规模更大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中华文化没有中断,依然在吸收少数民族文化后,得以持续发展。如唐代贞观到开元一百多年的盛世局面,就是魏晋南北朝分裂时期,中华民族融合、文化交流的历史结果。可以说,虽然有分裂存在,从历史发展全貌看全国性的多民族统一才是主流。
中国发展不充分、不平衡。发展不平衡,在汉族和少数民族间表现尤为明显。多民族统一有助于汉族和少数民族同步前进,协调发展。
中国古代长期以自然经济为主。汉族地区主要生产活动是农业和畜牧业,而少数民族地区则以游牧为主。中原农业生产的粮食,纺织的布匹,和少数民族地区的毛皮、茶马等,可以互补。这种交易如不能进行,会迫使北方少数民族侵扰中原。而多民族统一国家,则为放开交易提供了必要政治条件。故“盐铁的贩卖,茶马、毛皮、药材的交易,植棉、纺织的推广,河防、水利跟工程和道路的兴修,还是多民族统一为社会经济带来的进步。”[4]社会经济因为民族交流交融而进步,反复彰显了民族交流、融合带来的好处,增强了各民族交流交融的吸引力,促进着多民族统一体的形成和进一步发展。著名的丝绸之路,正是古代汉族和少数民族经济文化交流之路,及其向国外的延伸。反过来说,周边少数民族对于中原有一种内聚的向心力。丝绸之路,也是这种吸引力和向心力交互作用之路。
中国幅员辽阔,各地自然条件不一,相互补充,正好构成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中原地区自然条件较好,经济文化比较发达,对少数民族有很大吸引力。粮食、布匹对于北方少数民族越冬必不可少。在中国古代,中原地区基本上有相同的农耕、定居生产生活,以及封建制度,而匈奴则处于奴隶制阶段,西南夷还处于氏族社会末期。到新中国建立前,中国既有买办资本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民族资本主义,也有封建制、奴隶制、原始共产制。但大家发展的方向是,汉族更加向前发展,各少数民族则“以不同的速度努力向汉族靠拢。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各族人民分别通过不同的形式,向社会主义迈进”[4]。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东部地区对口帮扶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已经取得很大成效。各民族友好相处,团结合作,携手共建祖国,共同发展,已经成为新时代的主旋律。
四、“中国”观念是核心
“中国”观念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核心,它本身就是中华各族多元一体关系发展的产物。在古代,“中国”一词并非国家概念,而是地域概念、文化概念,有文化中心的意思。从今天国家的概念看,古代“中国”所指的并不是国家的全部领土,而只是国家的中心区域。根据于省吾《释中国》一文所述,如《诗经·大雅·民劳》:“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毛传》:“中国,京师也。”也就是说,中国在商、周时期指商王、周王所在的王畿地区——国家首善之区[14]。
最初,“中国”和“四方”相对而言。作为国家的一部分,“中国”是国家抚绥控驭“四方”的中心地区,而“四方”则包括了周王分封的诸侯国和受周王管理的各边疆少数民族。如春秋时,中原地区的周王朝,以及晋、郑、齐、鲁、宋、卫等诸侯国,都自称中国,而将秦、楚、吴、越看成夷狄。秦汉时,秦、楚之地也变成中国了。魏晋时期,东晋人称十六国是夷狄。南北朝时,南北互相贬斥为索虏,为岛夷。唐朝时,他们都成为中国人。李延寿修《南史》《北史》,便一视同仁。两宋时,宋人将辽、西夏、金看成夷狄。元朝时,则将这些人都看成中国人了。这些历史事实反复说明,华夏文化不断拓展自己的地理空间,从中原到长江流域,再到华北、西北、西南、华南、东北等,形成了雄踞亚洲东部的文明共同体。
中华文明地理空间的拓展,是自然发展的结果。中华各族生活在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空间,有大致相近或相同的自然条件。居住相近的各民族间逐步接触、了解,甚至通婚、融合,进行经济文化交流,调剂余缺,取长补短,使双方的社会历史更加进步。交往交流交融,是中华民族史的主流。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是华夏族学习少数民族;北魏孝文帝改革,是少数民族学习华夏族。这种鲜活的事例很多,都是一个民族主动学习其他民族的先进文化内容。华夏族先后融合了秦、楚、吴、越、匈奴、鲜卑、羯、氐、羌、辽契丹、西夏党项、金女真、元蒙古、清满族等少数民族在内,形成了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这就是中国形成发展的历史过程。
随着各民族交流愈益密切,中原的汉族和周边的少数民族相互联系更为紧密,仅仅进行经济文化交流,已经不适应各民族自身的发展了。一些关系到双方的重大事件、思想、工程等,需要更高的国家统一政权来解决,如蒙古的马和中原的布帛、茶叶交换,女真人用自己的人参、貂皮交换中原的粮食、农具、缎布。国家没有统一,中原和周边地区互相禁止交易,双方都受害。相比起来,边疆少数民族更为需要中原的粮食、布匹。和向外发展受到林海雪原、崇山峻岭阻隔的艰难交通条件相比,北方南下,经过平坦广阔的草原,要更为容易。少数民族更愿意内倾,有对中原的“天然的内向性”;同时,较为发达的中原经济文化,对少数民族也历史地产生了“天然的凝聚力”[4]。少数民族天然内向倾向,和中原经济文化的凝聚力结合起来,成为维系中华各族联系的历史纽带。而国家统一后,中央政府借助其公共职能的发挥,有意无意地加强这种联系纽带。如经济上,双方自由交易,皆得其利,吸引力和向心力得以自然展现、加强。更不用说,还有共同对付洪水、干旱、地震、瘟疫等自然灾害的任务,近代以来,还增加了抵抗外来侵略的共同使命。各民族日益加强的联系纽带,反过来又成为多民族统一大国日益发展的基础。所以,从中国历史上可以看见,中国中央政权越来越成为多民族国家的政权。如秦汉、隋唐,大一统还时有间断,但到元明清,则成为连续大一统的世界大国,反映了多民族国家统一愈益成为各民族友好交流发展的需要。可见,中国作为世界性大国,中华民族成为世界性的伟大民族,中华文明成为持续不断自然发展的文明,乃是历史自然发展的结果。
结果就是,中国的统一越来越巩固,版图越来越大。中华文明是中华各族共同缔造的,中国历史是中华各族共同书写的,不是空话,而是历史事实。除了经济文化成就外,比如国家版图,元朝、清朝的贡献就非常大。秦朝统一,但版图北到长城,西到黄河,和青藏高原不挨边。汉朝统一,西边到玉门关,进入青藏高原的湟水流域。唐朝统一,到了中亚地区,但吐蕃等还在外,新疆、云南等是羁縻州,高度自治。两宋时,中国有好几个割据政权,南宋(长江珠江流域)、金(黄河流域和东北)、西夏(甘肃、宁夏、鄂尔多斯一带)、大理(云南)、西辽(新疆)、吐蕃(西藏),以及蒙古高原上的蒙古、突厥各部。元朝,从成吉思汗到忽必烈,才完全统一,建立起疆域辽阔的统一政权。明朝时,对东北辽东、北方鞑靼、瓦剌各部、西藏的统一,都不够巩固。清朝才完成了更为宏阔的统一,东北、新疆都建立起行省。
五、华夷一家观念是源泉
先秦时期是中华民族发轫和奠基时期。华夏族形成,华夏族和周围地区的少数民族,即东夷、南蛮、西戎、北狄的关系,即华夷关系,成为醒目的社会关系之一。儒家虽然重视宗法、血缘,但儒家的思想正着意于超越宗法、血缘。儒家华夷一家的民族观是集中表现。儒家华夷一家观正是古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概括,也是今天我们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源泉。
在民族观上,儒家完全没有种族观念,而是以天人合一的仁义道德为核心,以人性为基准,以文明为中心,以人类理想社会为引领,认识和调整民族关系。这里以儒家创始人孔子为代表,揭示儒家华夷一家民族观以人性修养、文明进步为基准的特质。儒家华夷一家观念也是对华夏族和少数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实际的历史反映。
民族是历史的产物,是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人类社会共同体形式。民族观的内容和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与民族史、文明史相联系。文化是一个民族、国家的灵魂。孔子的民族观和文明观交织在一起,司马迁等的民族观则和黄帝始祖观、黄帝共祖观等交织在一起。这两种类型的民族观念,在中国古代都发生了重要影响。比如,在秦汉时期,多民族统一的国家观念,多元一体的民族观念,就已经成为主导观念;这可以说就是当时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白寿彝指出,这种观念,结合秦汉时期得到空前统一局面和对外交通发展,正是司马迁等能够写出超越当时和今天中国国境范围的“包容广大的民族史”的原因。而邹衍大九州说,可谓这种观念的“地理形式”,《中庸》“舟车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载,日月所照,霜露所队,凡有血气者莫不尊亲”说,可谓这种观念的“道德形式”[4],司马迁《史记》所记录的民族史,则是这种观念的史学形式而已。
孔子的民族观,有以下几个要点:
第一,断定和肯定华夏和夷狄有相同的人性,遵循相同的道德规范、礼乐制度。孔子说:“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貘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卫灵公》)又说:“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子路》)在当时,比起中原华夏地区,周围少数民族地区发展不够,这是事实。但孔子断定和肯定少数民族和华夏族一样也是人,有人性,遵循忠信、笃敬等道德规范和礼乐制度。在孔子看来,这种以人性为内核的仁义道德、礼乐制度,正是人类文明的标识。
第二,孔子肯定诸夏创造了文明成果,夷狄等少数民族也创造了文明成果;双方的文明程度、文明地位并非恒久不变。若诸夏“礼失”战乱,夷狄可能更加文明。孔子说:“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八佾》)孔子在此的意思,究竟是夷狄不如诸夏,还是诸夏不如夷狄?学界有不同看法。朱熹引程子注解说:“夷狄且有君长,不如诸夏之僭乱,反无上下之分也。”[15]这说明,在孔子看来,诸夏礼坏乐崩,秩序瓦解,社会混乱,反不如夷狄社会平稳有序。比诸夏落后的夷狄,也创造了文明成果;本来比较先进的华夏,也可能因为社会动荡、战乱等,而野蛮化,文明程度反不如夷狄地区。后来顾炎武发挥说:“历九州之风俗,考前代之史书,中国之不如外国者有之矣。”[16](《日知录》卷二九《外国风俗》)顾炎武列举契丹、女真,还有匈奴、北魏、回纥等风俗材料作证。这说明,在孔子等儒家看来,诸夏比较文明,夷狄不那么文明,这种文明地位是总的看来如此,并非固定不变。
第三,孔子断定,有人性修养的人可以改变社会落后面貌,发展人类文明。孔子周游列国,郁郁不得志,甚至曾经表示“欲居九夷”。有人问:“陋,如之何?”孔子回答:“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子罕》)意思是说,有人性修养的君子,是能够创造文明,传播文明,改变落后、简陋环境的,不必害怕环境条件的暂时落后。
第四,孔子肯定管仲保卫诸夏文明的历史功劳,表明孔子民族观中,始终贯穿着文明观念,并将民众利益和文明程度作为比个人道德更重要的评价标准。管仲曾辅佐公子纠,与其兄(即后来的齐桓公)争国。齐桓公杀公子纠,管仲不能死难,反而为相,辅佐齐桓公。有人对此提出疑问。孔子说:“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祍矣。”(《宪问》)评价一个人的道德,不能局限于个人间的信义。让民众享受到实实在在的利益,保卫文明,避免野蛮化,是孔子评价一个人道德水准的重要指标;其重要性甚至超过个人道德。或者说,能否帮助民众获利,能否保卫和发展文明,本身就是衡量一个人道德与否的历史标尺。其实,在孔子那里,民众和文明紧密联系。所谓“民受其赐”,就是民众能享受到文明实惠。所谓“被发左衽”,就是文明被破坏,人类野蛮化。用道德修养保卫人类文明成果,维持文明先进程度,免遭外来落后文明的侵扰,就是民众最大的利益。保卫先进文明,免遭落后文明侵扰,实质上就是反对落后代替先进的文明逆传播,提倡先进代替落后,即“用夏变夷”(《滕文公上》)的文明正传播。
先秦时期,中原诸夏文明的建设和拓展,和西周封邦建国、制礼作乐相关。每个诸侯国实际上就是一个华夏文明单元,诸侯国的发展,就意味着向周围地区开垦土地,招徕民众,拓展礼乐文明范围,《鲁颂》所谓“戎狄是膺,荆舒是惩”是也。经过长期发展,一些诸侯国逐步强大起来,实际上意味着华夏文明终于发展壮大起来。管仲帮助齐桓公治理齐国,使齐国尊王攘夷,一匡天下,成为春秋首霸,正是华夏文明发展到新阶段的表现。
以文野之分,界定华夷之辨,是孔子民族观的要旨。不是看血缘种族的区别,而是看文明和野蛮的分野。这个思想,也是后来唐太宗华夷一家观念的理论来源。而黄帝作为民族共祖观念,则与其逻辑连贯。依照这种民族观念,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或者华夏族散居夷狄地区,都没有民族观念障碍。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华夏族和夷狄等少数民族,才逐步融合成为了汉族。汉族的民族特征不那么明晰,正因为汉族是历史上各民族融合的产物,也是中华民族各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历史成就。
第五,儒家的大一统观念,表现了人们对民族关系美好理想的向往。关于人类理想社会,即大同社会,也是天下一统观念,可以说就是民族关系的理想状态。这种理想状态的特征,很早就产生了。中国先贤曾经用“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17]来概括;《中庸》则有“书同文,车同轨,人同伦”的美好向往。这种理想状态的具体内容,《礼记·礼运》这样描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如何实现多民族天下一统?《诗经·小雅·北山》载“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表达了王权下的天下地理、族群的统一。孔子说:“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季氏》)是说礼乐制度的统一;孔子的学生南宫适说:“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宪问》)是强调道德修养的统一。战国中期的孟子,则要用仁义道德的仁政,即王道政治、良心政治“定于一”(《梁惠王上》)。战国末的荀子,则主张用虚壹而静的理性认识、诵经读礼的德操、明分使群的礼法政治统一天下。《礼运》则强调:“圣人耐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者,非意之也,必知其情,辟于其义,明于其利,达于其患,然后能为之。”在儒家看来,要达到天下一家、中国一统人的理想社会,就要认识到人的喜怒哀乐等人的共同性情,尽到父慈子孝等人伦,得讲信修睦之利。这些内容如果一定要用一个词表示,那就是道。于是,志于道,求道,闻道,行道,传道,让天下有道,就是必备条件。在王道政治基础上,就可以真正实现政治制度的统一、道路的统一、文字的统一、学术思想的统一等,而不会反复、曲折。人与人间,各民族间像兄弟一样平等、和谐,友爱互助,共同发展繁荣。
在华夷一家的民族观念影响下,中原王朝和周边少数民族关系的理想状态,就是子夏说的“四海之内皆兄弟”。在儒家这种观念影响下,中华各族交往交流交融、兄弟般地团结、家人一样的感情,越来越变成历史事实。历史上中原民族和少数民族关系,不能说一直和平相处、友好交流。事实上也有时闹矛盾、打仗,甚至战争规模大。但不管友好还是战争,历史发展的结果是,双方的经济文化联系越来越密不可分,越来越亲如一家。中华民族共同体在此基础上形成、发展,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这样铸造、凝练。
六、较高层次的民族意识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以人所共有的人性修养为基础,立足更广范围的民族共同体,是对民族片面性、局限性的克服,对民族全人类性、积极性的弘扬,是共产主义社会自由人联合体意识的初步反映。这是各民族间关系进一步发展、成长的表现。它反映了这样一个历史事实:单一的、孤立的民族,逐步成长为相互联系紧密、不可分割的更大的族群的一部分。
在意识上,民族个性的淡化,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看来,意味着“民族偏见、民族优越感”等民族心理的淡化;是对民族歧视、大汉族主义的反对和克服。在伦理上,这也是对民族自私的克服。因为这种民族心理,“归根结底不过是大规模的利己主义而已”。成长于这种心理基础的近代各种民族主义思想、思潮,不管是泛斯拉夫主义,还是泛日耳曼主义等,都会增加民族偏见、民族优越感等,导致民族歧视、民族纠纷等更多地出现,和近代世界各民族民主发展、民族解放、社会解放的历史方向不相应,和人类民族史上各民族个性淡化、共性强化的世界化的历史总趋势不相应,有其难以克服的局限。民族共性的增长,意味着在生产共同发展基础上民族团结有爱互助意识的增长,意味着民族成员人性意识的觉醒。《共产党宣言》指出:“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在理想社会里,“每一个民族都将有同一个统治者—— 劳动”。
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近代民族解放运动有其历史的积极意义。如中英第二次鸦片战争,恩格斯认为就是“为了保存中华民族”而进行的战争,这场战争的性质、内涵和结果,都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文明程度”。
同时,近代化也给工人阶级以超越民族狭隘性的世界意识和人性觉醒。恩格斯对英国工人说:“我确信,你们并不仅仅是英国人,不仅仅是单个的、孤立的民族的成员;我确信,你们是认识到自己的利益和全人类的利益相一致的人,是伟大的人类大家庭的成员。对你们作为这样的人,作为这个‘统一而不可分的’人类家庭的成员,作为真正符合人这个词的含义的人,我以及大陆上其他许多人祝贺你们在各方面的进步,希望你们很快获得成功。”事实上,“英国工人已经不再是英国人,不是像他的有钱的邻居那样的专会打算盘的拜金者;他的内心充满了丰富的感情,他那北方人天生的冷漠被奔放的热情所抵销,这种热情已经控制了他。智力教育已经如此有力地促进了英国资产者利己主义天性的发展,使他所有的热情都受利己心的支配,并把他的情感的全部力量集中在追求金钱这一点上。而工人缺少这种智力教育,因此,工人的热情和外国人一样强烈奔放。英国的民族性在工人身上消失了”。工人阶级具有了全人类的世界意识,这也是历史的产物。在中国历史上,民族特征的淡化早已开始,更高层次的民族意识早已萌芽并健康成长着,这就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在新时代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征程中,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能够确保我们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恩格斯指出,只有无产者在共产主义旗帜下,才能真正做到华夷一家。“在共产主义的旗帜下真正地结成兄弟。也只有无产者才能够真正做到这点,因为每个国家的资产阶级都有他们自己的特殊利益,而且由于他们认为这些利益高于一切,他们无法越出民族的范围。他们的少数几个理论家即使把他们所有那些美妙的 ‘原则’ 都搬出来也顶不了什么事,因为他们根本不触犯这些互相矛盾的利益和整个现存制度,他们只会说空话。可是全世界的无产者却有共同的利益,有共同的敌人,面临着同样的斗争,所有的无产者生来就没有民族的偏见,所有他们的修养和举动实质上都是人道主义的和反民族主义的。只有无产者才能够消灭各民族的隔离状态,只有觉醒的无产阶级才能够建立各民族的兄弟友爱。”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及其伟大成就,为各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形成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真正的华夷一家,提供了可能性和现实性。
七、结语
可见,在历史地位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是以自我民族为中心而罔顾其他民族利益的民族主义意识,而是对民族主义可能潜藏的利己主义自私意识、资产阶级剥削意识的克服,是对民族孤立性、狭隘性、片面性的克服,是对民族偏见、民族封闭、民族自负的消除。在民族思想史上,它是对民族主义意识的历史超越。它反对大汉族主义,也反对一切民族主义。它主张,每个民族都是平等的,都有生存和发展的权利,都应和其他民族友好相处,团结合作,共同发展。它认同中华文化,认同中国,认同中华民族,反对分裂祖国、撕裂族群文化;它又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内在一致。就其本质言,它是人性意识的民族化表现,是民族意识的成长和升华,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意识的中华民族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