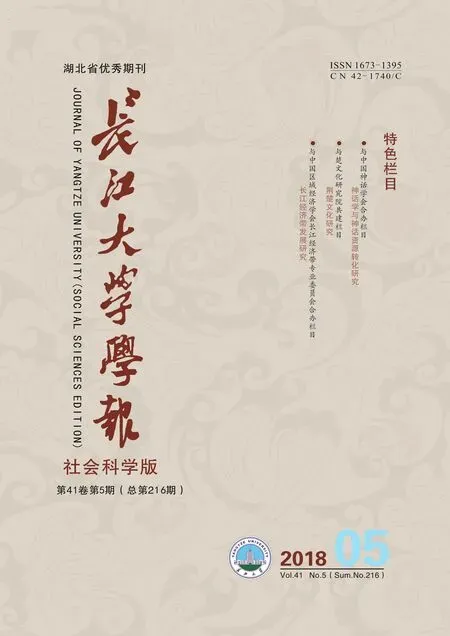百田弥荣子的中国神话研究
——以《中国传承曼荼罗》《中国神话的构造》为中心
刘雪瑽
(北京大学 中文系,北京 100871)
一、对中国西南地区神话的关注
百田弥荣子(1944-)于1970年毕业于庆应义塾大学文学系,现为日本中日文化研究所教授。她师从伊藤清司,并在其指导下完成了本科毕业论文《关于〈竹取物语〉形成的一项考察》。论文将日本民间故事《竹取物语》与我国藏族民间故事《斑竹姑娘》进行比较研究,认为两者之间有诸多相似之处,可见《竹取物语》的原型与中国西南地区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篇论文于1972年发表,也奠定了百田弥荣子致力于中国神话研究的学术道路。
百田弥荣子大学毕业后,曾在早稻田大学、东京学艺大学、大东文化大学等高校任教,并先后在国立民族学博物馆、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中日文化研究所等机构从事研究工作。自上世纪70年代至今,她共出版或参与编写、翻译了学术著作三十余本,发表了论文三十余篇,研究领域涉及到中国少数民族神话、中日神话比较、民俗学、文化人类学、中国儿童文学等。百田弥荣子通晓中文,早期翻译过一些中国作家的文学作品与中国学者的学术论文。语言上的优势,使她可以阅读中文文献,这在田野调查的过程中为她带来了不少便利。百田氏自20世纪80年代至21世纪初,曾多次赴中国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进行长时间的田野调查,访问当地民众和学者、采集民间神话与传说、查阅地方文献。这些赴实地进行考察的经历,使她更加贴近研究对象,并掌握了大量的一手资料。其著作《中国传承曼荼罗》的近百幅插图中,不少都是她在田野调查时拍摄的,如少数民族地区的传统剪纸、民间棺墓上的纹饰、祖先牌位旁的装饰、乡村小庙中的泥塑等,都是十分鲜活的论据。再如《中国神话的构造》一书中,为说明“公鸡雷神”站在桑树上是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共有的神话母题,百田氏在充分引用二手文献的同时,又以她先后赴云南大理的巍山县、贵州凯里的格细村、广西融水苗族自治县等地考察采集的一手资料为佐证,使得论证更有说服力。
事实上,百田弥荣子对中国西南地区神话的研究兴趣贯穿了她的整个学术生涯。受老师伊藤清司的影响,她在大学时期就对藏族民间故事《斑竹姑娘》与日本《竹取物语》的关系展开了研究,并将其作为毕业论文的主题。在此基础上,20世纪70年代初,她与伊藤清司联名发表了《竹取物语源流考》一文,在对二者进行系统比较研究后,得出二者应来源于同一祖型的结论。1981年,她发表了论文《浅谈传统中国西南少数民族的创造神:与雷神、龟神、天鹅、天狗相关联》,此时她已经关注到雷神在西南地区神话中的重要地位,为之后“曼荼罗”构造的提出奠定了基础。1999年之前,她还关注了侗族、苗族、纳西族等西南少数民族的神话与社会组织,并写作、翻译了一系列文章。这段时间,她不断思考中国神话是以一种怎样的结构进行传承的,并写成著作《中国传承曼荼罗》,于1999年由三弥井书店出版。百田氏认为,中国神话的构造应该是立体的球形,而球的核心就是“公鸡雷神”,即人类共同的创造神。2004年,作为前书的后续思考,她又出版了著作《中国神话的构造》[2]。这本书承袭了前书的曼荼罗神话构造,但与主要关注动物神不同,这本书的关注点是曼荼罗神话世界中的植物。这两本书分别于2005、2016年在中国翻译出版,在原著出版的1999~2004年之间,百田氏还关注到西南地区的来访神、观音与“公鸡雷神”的关系,射日与冶炼文化的关系等相关问题,并写作了一系列文章。2005年以后,她没有再出版过中国神话研究的专著,但相关论文却发表了不少,如2007年的《雷神与山神的关联》、2010年的《中国的三轮山神话》、2012年的《中国少数民族的创世神话:将彝族神话作为典型》、2015年的《传承曼荼罗的灾难物语:对丰饶的祈求》、2017年的《彝族诸支系的经典与神话传承》等。直到2018年2月,74岁高龄的百田氏仍发表了论文《云南省峨山县彝族的玛贺念神话》,可谓笔耕不辍,令人敬佩。
百田弥荣子对中国西南少数民族神话的兴趣并非是偶然现象,而是处于日本学界自20世纪以来对中国西南地区产生关注的学术潮流中。鸟居龙藏是这股学术潮流的先驱者,他于1896~1900年间在台湾进行“番人”的调查工作,1902年又赴中国西南地区进行了为期7个月的考察。[3]虽然当时的主要研究对象是苗族,但他的记录涉及到了彝族、布依族、傈僳族、藏族等。鸟居龙藏之所以将目光从台湾“番人”转向西南苗族,是因为他怀疑二者之间具有人类学意义上的关联。而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日本人类学界,流行着台湾“番人”属“高砂族”,与大和民族同根同源的说法。因此,探寻“高砂族”的祖先也就意味着探寻日本人的根源。这也是鸟居龙藏的研究成果为何会对日本学界产生深远影响的原因之一。鸟居龙藏根据这一次田野调查的成果展开研究,在《有史以前的日本》一书中提出了日本文化复合论的观点,认为日本民族构成之一的“印度支那族”来自苗族。在此基础上,20世纪70年代,中尾佐助提出了“照叶树林文化圈”学说,认为中国长江以南、台湾北部,日本西部同属共同的植物分布圈,因此生产活动与生活习俗也多有相似之处。这一理论问世后,日本学界对中国西南地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因此,1979年两国间的学术交流刚一放开,就有白鸟芳郎、伊藤清司等老一代学者奔赴云南、贵州等地展开实地考察。可以说,他们对中国西南地区兴趣的出发点,在于寻找日本的民族起源。学者们将在当地观察到的语言、神话、习俗、服饰、社会制度与日本进行比较,发现了不少相似之处。以百田弥荣子等为代表的新一代学者,则更加重视田野调查和对当地社会的整体性观察,而非仅仅立足于日本本土做研究。因此,新一代日本学者的研究不仅具有更高的学术价值,而且不少对于我国学界也颇具启发性。
二、中国神话研究的主要观点
前文对百田弥荣子迄今四十余年的学术路径进行了梳理,并简要讨论了她在日本中国西南地区研究学术史上的地位。前文已经提到,她分别于1999年、2004年出版了两部研究中国神话的著作《中国传承曼荼罗》与《中国神话的构造》,并分别于2005年、2016年译为中文出版。百田氏在对中国神话尤其是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神话的观察研究中发现,中国神话的结构并非是平面的,而是一个立体、浑圆的构造,她将其命名为“曼荼罗”。这两本著作都是围绕中国神话的曼荼罗构造这一主题展开论述的,只是侧重面有所不同,前者偏重动物,后者偏重植物。因此,这两本著作可以视为同一个论题的上下编,以下将放在一起进行讨论。
(一)曼荼罗构造
百田氏在研究中国神话时,发现不同的神话母题间总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彼此呈网状交织在一起。但是,她认为母题之间的地位并非平等的,而是围绕在一个核心母题的周围。对于中国神话而言,这个核心母题就是“公鸡雷神”。
在传承神话的世界里,绝非所有的话题形态都能平面地排成一列,保持着一个平等博爱的世界。几乎都是以“公鸡雷神”作了他们的核心,绝对地形成了一种立体的关系。倘若不是这样,这一切就没有一种可以结构起来的方式。当我们这样去思考这个问题时就会发现,这岂不就是传承的曼荼罗吗?因此我才把这种浑圆立体的神话传承世界称之为“传承的曼荼罗”。[1](P101)
尝试为中国神话寻找一个合适的结构,是百田氏试图将庞杂丰富的中国神话系统化的努力。她根据自己的理解,为中国神话找到一个容器,并将一个个神话母题置入其中。为此她也做了不少尝试。她在《中国传承曼荼罗》一书的后记中提到,她最初认为神话世界的形状是像绳子一般的线性结构,然而在画图时,在线条的中央就变得扭曲、混乱了。第二次尝试时,她将线条变为弧线,由“公鸡雷神”开始,由内向外画出与鸡相关的神话母题。最终画出的形状是一个立体的圆形,百田氏将它命名为“传承曼荼罗”。[1](P333)
关于曼荼罗的中国神话构造,首次以书面形式提出是在1999年,但早在1989年,百田氏就在研讨会上口头提出过。再向前追溯,在1987年时,她的脑海中已经有了关于这一理论的初步构想。[1](P339)此后,她花费了近十年的时间去思考、完善这一理论,最终写成了《中国传承曼荼罗》及《中国神话的构造》两本著作。
所谓“曼荼罗”,即梵文mandala的音译,中文又译作“曼陀罗”,意译则一般译为“坛城”。曼荼罗是佛教密宗所认为的世界,是佛陀生活的理想世界。曼荼罗是圆形的,这种形状也被称为“轮圆”或“浑圆”,有圆满的意思。如果将整个曼荼罗视为密宗修行的能量场,那么中央就是能量的核心,而四周则以某种对称的状态存在着,一层一层地由中央向四周延伸开去。佛教中的曼荼罗,中央是佛陀或众佛菩萨居住的须弥山,四周是佛陀座下诸弟子及随侍,或是佛教世界中的四大洲八小洲。在百田弥荣子的中国神话曼荼罗中,中央是“公鸡雷神”,四周是与它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猴、蛙、犬、鼠等动物,及扶桑、竹子、葫芦等植物。它们共同组成了中国神话的曼荼罗构造,并作为一个永恒的能量场,在民间代代传承下去。
(二)“公鸡雷神”的核心地位
在中国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的神话中,雷神的地位是很高的。百田氏发现,神话中雷神通常担任着以下几个职责:
A.世界最初混沌似鸡蛋,雷神诞生在其中,并开天辟地。
B.雷神发现大量金银,将其铸造成日月星辰,并创造万物。
C.雷神降下大洪水,并选择一对兄妹,让他们成婚,繁衍人类。
由此可见,雷神不仅担任着创世神的职责,而且也执掌着人类的生存与繁衍。当人间充满罪恶时,他惩恶扬善,选择了心地善良的兄妹作为人类的始祖。百田氏认为,雷神是丰饶神,也是铸造日月的冶炼神,同时具有公鸡的形象。雷神与公鸡之间存在关联,从职责A中也可以看出。
那么,百田氏是如何将雷神与公鸡联系到一起的呢?她先是发现西南少数民族对于公鸡十分崇拜。在《中国传承曼荼罗》第一章中,她使用《神异经》《汉学堂丛书》等文献资料、苗族地区柱顶上的鸡等实物资料,论证金鸡站在山顶、树梢上的传说古已有之。换言之,中国很早就产生了对金鸡的崇拜。在接下来的第二章中,她又举出河姆渡遗址中用于祭祀太阳的“双头三脚鸡”,联系贵州水族鸡上天讨要稻谷带回人间的传说,认为中国人很早就将鸡看作是促进社会富裕的神鸟了。此外,傣族还有向鸡祈求子嗣的传统,因此,鸡也具有司掌生育的功能。至此,百田氏的论证告诉我们,鸡对于中国人来说是十分重要的神鸟。而关于公鸡与太阳的关系,在第十章的射日神话中有所论及。西南地区的神话中常有这样的情节:多余的太阳被射落后,仅剩的一个太阳不敢出来,人们派公鸡去喊,于是每天清晨雄鸡鸣叫则太阳升起。因此,天上的雷神对公鸡既敬又怕,来到人间时就化作公鸡的模样。百田氏为了证明雷神的形象是公鸡,又以广为流传的洪水神话作为例证。她在第十一章中列出了十二则洪水神话的异文,其中雷神均为公鸡的形象,充分说明了在我国西南地区,普遍存在着“雷神是公鸡”的传统信仰。
那么,百田氏为何认为“公鸡雷神”在中国神话的曼荼罗构造中处于核心地位呢?这不仅因为“公鸡雷神”在西南地区神话中地位高,而且因为她发现神话中的其他母题,都可以“公鸡雷神”作为出发点延伸开去。我们以《中国神话的构造》一书为例。这本书的前三章分别围绕桑树、竹子、瓜这三种植物展开讨论,说明它们在中国神话中的重要地位与功能,并强调它们各自与雷神之间的关系。
首先是桑树。早在《山海经》中就有扶桑是太阳歇息之处的记载,且《神异经》中提到扶桑山上有玉鸡,玉鸡鸣则引起天下鸡鸣。百田氏由此认为,桑树就是“公鸡雷神”的宝座。在百田氏收集的西南神话中,不少都提到马桑树曾与天齐高,一些动物甚至能爬到树顶啃食日月。而如今马桑树之所以变矮,是因为雷神被兄妹搭救后逃往天上时,跳上马桑树把树压低了。百田氏注意到马桑树和雷神的纠葛,又列出了另一则贵州水族的神话:雷神千方百计阻止马桑树的生长,马桑树不服输,就生出了铜枝铁干,从此人们感佩它的不屈不挠,就不再用它做柴了。百田氏认为,桑树被人们赋予了不轻易屈服的骨气、高可通天的神圣性,同时还是“公鸡雷神”的宝座。
其次是竹子。与桑树类似,高大的竹子顶端也是“公鸡雷神”的宝座。百田氏注意到,西南地区普遍有“通天竹”的传说。贵州东南的布依族认为,古时候是雷神将九十九根粗大的楠竹撑在天地间,将天地分开的。百田氏从贵州黔南州水族一则《竹鼠怕雷》的传说中分析出,雷神就居住在长满竹林的山上;又从四川大凉山傈僳族的《蛐鳝报恩》中分析出,竹子是伴随着雷声长大的。但是,雷神与竹子的关系并非只有亲密的一面,百田氏也注意到了其互斥的一面。湖南土家族流传着这样一则神话:人间老妪想吃雷公肉,儿子就用竹笼捕获了“公鸡雷神”,因此雷神逃回天上后才会震怒降下洪水。由此百田氏判断,雷神对竹子是有恐惧情绪的,二者既关系亲密,又互相排斥。
最后是瓜。在广泛流传于南方地区的大洪水、兄妹婚神话中,瓜(葫芦)是承载着兄妹二人漂流于洪水中得以幸存的神圣容器。但是,由于二人之间具有血缘关系,成婚是违背伦理道德的。因此,要想顺利完成婚配,需要一些特殊的神迹。百田氏注意到,在此类神话中,往往是由“公鸡雷神”扮演促成婚姻的角色。成婚的过程往往曲折,在雷神的主持下,他们要经历合烟、绞发、种树、滚磨盘、穿针等仪式[2](P121),屡次证明兄妹成婚确实是天意之后,才能结合。
其实,不仅是植物,百田弥荣子在《中国传承曼荼罗》一书中也详细梳理了诸动物神与“公鸡雷神”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它们有的与雷神之间具有亲属关系,比如青蛙、马是雷神的儿子,老鼠是雷神的孙女等;有的与雷神有相似性,比如龙王与龙女也常被描述为鸡的形象;有的与雷神之间有力量强弱的对比,比如百田氏就曾归纳过鸡、蜈蚣、龙之间的力量对比:作为雷神的鸡﹥作为山神的蜈蚣﹥作为水神的龙。[1](P161)
总之,百田氏认为,这些神圣的动物与植物一起,围绕在“公鸡雷神”的四周,形成了曼荼罗的结构。她还提到,曼荼罗应由两部分构成,一个是以佛为中心的神仙群体,另一个是众神居住的宫殿和建有宫殿的须弥山。而在她所建构的曼荼罗神话世界中,既有以雷神为核心的诸神群体,也有雷神的宫殿。这个宫殿就是神树的树顶,是金鸡的宝座,当“公鸡雷神”化作太阳运行于天时,这个宝座也就变成了移动的宫殿。[2](P229)由此百田氏认为,中国神话正好能满足曼荼罗的两大要素,因此这个构造是十分合理的。
(三)神圣的螺旋纹
百田氏还特别关注到在中国神话及仪式中,螺旋纹所具有的神圣性。她在苗族村落中观察到,在祭祀仪式上,男男女女会排成两队,各自以相反的方向围绕着柱子转圈。她想象着自己处于柱顶“公鸡雷神”的视角俯看地面,这些民众走出的是太极图的队形。太极图的形状就像两条紧密依存、缠绕的鱼,百田氏由此联想到伏羲女娲的图画,他们的蛇尾是紧紧交缠在一起的,手中交换着规与矩,构成了非常明显的螺旋漩涡图纹。而在兄妹婚的神话中,雷神对兄妹的考验也往往与螺旋纹有关。比如合烟的考验,两股烟要交合缠绕在一起,形成的也是螺旋纹。再如绞发的仪式,二人的头发紧密相缠,也是形成了螺旋纹。此外,百田氏还认为,马桑树被雷神命令“长到三尺就弯腰”,因此马桑树也是呈螺旋形状向上生长的。倘若是两株马桑树对着生长,也会形成彼此交缠的螺旋形状。
其实,螺旋纹意味着彼此缠绕交合,象征的是合二为一。无论是伏羲女娲的交尾,还是兄妹婚的种种考验仪式,这其中的螺旋纹样也象征着两性之间的交媾和生命的繁衍。对此,百田氏也强调了,太极和螺旋的本质是呈旋转运行的中心轴,而婚姻仪式中的“顺利穿过”(如穿针仪式)就可以视为这个中心轴,用来表示阴阳之间的完全吻合。
螺旋纹虽然没有被百田氏直接纳入曼荼罗构造中,但是她强调了该图纹的神圣性,以及螺旋纹源自鸟纹的学界公论。由此出发,百田氏认为苗族的螺旋纹正是源于“公鸡雷神”,换言之,螺旋纹是属于曼荼罗核心的纹样。
三、对百田弥荣子中国神话研究的评议
前文已梳理了百田弥荣子的学术路径,并说明了她在学术史上的位置,也介绍了她在中国神话研究方面的主要观点。以下,将从三方面对百田氏的中国神话研究进行评述。
首先,要肯定她将中国神话结构化的尝试。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神话缺乏系统性就广受国内外学者的诟病。对此,前辈学者也试图从庞杂散乱的中国神话中理出一条线索,但是始终未能如愿。也有学者认为,不能用西方神话“成谱系”的特点来要求中国神话,这两种神话本就生长于不同的文化土壤。对此我们持赞成意见,但无法否认,将庞杂散乱的资料系统化、秩序化是人类的共同愿望。因此,百田氏为此付出的努力是值得鼓励与称赞的。尤其应该赞许的,是曼荼罗构造的立体性,它使神话脱离了二维平面,成为了更具延展性与包容性的三维空间。她将雷神作为结构的核心,并将其形象与公鸡相结合,由中心至边缘排列出一系列与公鸡相关的神话母题,以及由此发散开的其他动物、植物的神话母题。更有趣的是,佛教的曼荼罗具有能量,而百田氏的中国神话曼荼罗同样具有能量。她将这个能量视为神话得以代代传承的动力,这就在空间性上又增添了一层时间性,也使这个中国神话的结构转动了起来。
当然,百田氏提出的神话构造并不完美,其中仍然存在不少漏洞。比如百田氏颇具野心地将其命名为“中国神话的构造”,但中国地域辽阔、历史悠久、民族众多、文化多样,中国的神话绝不是出于同一个体系的。想要用一个曼荼罗的形状来囊括如此复杂的中国神话,恐怕不具有说服力。而且,百田氏在著述中引用的材料多为中国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的材料,她的田野经历也多集中在云南、贵州、广西等西南省份。因此,与其说她研究的是中国神话,不如说是中国西南地区的神话。西南众多的少数民族间虽有交流,但因地势隔绝不便沟通,也都在一定范围内形成了自己的文化,是否能将不同民族的神话打乱糅在一起讨论,也是值得商榷的。其实,这个以“公鸡雷神”作为核心的神话构造已经将不少神话母题排除在外了。就拿雷神的形象来说,是否只有公鸡一种形象?汉代画像中存在着大量的龙蛇型雷神,古代文献中也有雷神似猴、似猪、似人的记载,这些形象的雷神是否就无法进入曼荼罗构造了?由此可见,百田氏提出的中国神话曼荼罗构造,仍然具有进一步完善的空间。
其次,百田氏的论据是十分丰富的,不仅数量多,而且种类多样,地域跨度与时间跨度均很广,这与她一丝不苟的学术精神与精益求精的学术态度是密不可分的。作为海外学者研究中国的神话,不仅面临地理空间上的不便,而且还有语言上的障碍和文化上的隔阂。但百田氏曾多次赴中国西南地区做实地考察,深入少数民族村落进行或长或短的田野工作。在本文重点观察的两本著作中,她常用随笔式的语言穿插入自己的田野经历,有时为了弄懂一个问题,甚至不惜多跑几百里山路找当地人询问,这样严谨的学术精神令人感佩。百田氏使用的材料有传世文献、地方文献等二手资料,也有在田野中收集的神话传说、实际参与观察的祭典仪式等一手资料;有文字材料,也有图像材料,还有出土文物及田野发现的实物材料。可以说,她所采用的材料来源丰富,种类多样、全面,这也给她的论证带来了一定的帮助。不仅如此,百田氏对于论据的观察是十分细致的,这也是日本学者普遍具有的研究特点。尤其是在对神话异文的梳理上,她的阅读十分细腻且精准,总能敏锐地从文本中找到关键词,并与研究主题建立联系。
尽管百田氏的论证材料如此丰富,但她的研究方法在逻辑上不够严谨,最大的问题是忽略了反面证据。以中国神话的曼荼罗构造为例,百田氏在决定建构出这个模型之后,就花费了大量心血从浩瀚的神话资料库中找寻合适的“砖瓦”。被她选中的材料一定是符合已经预设出的模型的,而大量无法被装入模型的材料则被选择性无视。以《中国传承曼荼罗》的第三章为例,论证仙女与龙王公主可能是母鸡的形象,以下将梳理论证逻辑。文中首先分别举出一则日本与中国的“毛衣女”型故事,说明仙女拥有羽衣,穿上羽衣后就化作鸟的形象。继而列出两则苗族、瑶族的民间故事,说明这些故事中的仙女也是鸟类的形象。之后举出一则在广西上林采集到的壮族故事,当地的讲述人说故事中的仙女就是母鸡的形象。由此可以证明,在西南地区普遍存在着仙女是母鸡形象的说法。同样,在论证龙王公主的母鸡形象时,也举了仫佬族、壮族、彝族龙女变母鸡的民间故事,从而证明龙王公主的化身是母鸡。经过一番梳理后,我们很容易看出论证逻辑的漏洞。在千万条神话传说中,既有仙女、龙女化为鸟与母鸡的说法,也有化为其他形象的说法。事实上,民间故事中的龙女多是龙或人的形象。也就是说,从中国神话的整体来看,仙女、龙女化身为鸡可能只是一种偶然现象。而百田氏忽略反面证据的做法,是很容易把偶然现象视为必然现象,从而产生结论偏差的。
最后,我们谈一下对日本相关材料进行引用的问题。正如本文第一部分提到的,以鸟居龙藏为先驱的日本学者之所以对中国西南地区少数民族产生兴趣,是因为他们发现这里可能留存着日本人祖先的痕迹。尤其是苗族地区,被认为最有可能是日本人的发祥地。学者们纷纷前往当地进行考察,收集语言、民俗、神话、仪式、宗教、文化等各方面的证据,并与日本本土情况进行对比,寻找相似性,试图证明二者之间具有关联。这是老一代学者常常采用的研究方法,他们出于这样的立场与研究目的,目光也自然是朝向日本的。而对于新一代学者百田弥荣子而言,她的研究兴趣是中国神话本身,研究是脱离了日本本土立场的,也摒弃了为日本文化寻根的目标,而是将目光完整、彻底地放在了研究对象上。因此,虽然她的论证中常常出现日本的例子,但往往只是作为参照物或补充说明,绝非是论证的主体。比如《中国神话的构造》第一章,在论证马桑树是金鸡的宝座时,百田氏先举了几则中国文献的例子,来说明金鸡是居住在桑树树梢上的。继而补充了一则日本《今昔物语》的记载,是一个偷吃了鸡蛋的男孩遭到报应,在桑田中赤足疯跑最终烫伤双脚的故事。接下来又谈起日本NHK电视台播放过的一则新闻,讲在桑田中养鸡可以使鸡蛋品质更好。我们可以判断,这两则日本的材料只是用来补充说明桑树与鸡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而与材料的地域性关系不大。正是因为百田氏的研究中对日本本土立场的忽略,使得她的研究更加纯粹、客观。而她对于日本例子自然而然的选用,也使得她的研究视野更加开阔,角度更加新颖,论证更具趣味性。
总之,百田弥荣子对于中国神话研究的兴趣贯穿了她迄今为止四十余年的学术生涯。而中国神话的曼荼罗构造,是她在该研究领域中最重要的学术成果,也是其两部著作《中国传承曼荼罗》与《中国神话的构造》的主题。这两本著作尽管存在着诸多不完美之处,但是仍然可以引发后来者的种种思考,是很具创建性与启发性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