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对子的张禳关
◎小 米
写对子
张禳关是生产队记工员,给张家坝人写对子的,仅此一人。
谁家死了人或娶了媳妇,都得写几副对子。张禳关把要写的对子抄在一个揉得皱巴巴的本子上,他还给积攒的对子分了类。喜事类的,如:“百年恩爱两心结,千里姻缘一线牵。”丧事类的,如:“八秋耕耘,尽孝儿孙成大器;四方赞誉,合村邻里仰高风。”红白喜事写对子,主事那家就得烟酒伺候,但张禳关不吃烟不喝酒,烟酒伺候也白搭。白搭也得搭,这是礼仪问题。给张禳关预备的烟和酒,酒不能带回家,他转手递给别人喝了,烟得藏进口袋拿回家,等这一家的事毕了,再拿出来,给人吃掉。张禳关从不吃烟,从不喝酒,别人喝了该他喝的酒,吃了该他吃的烟,他心里也有一丝美滋滋的感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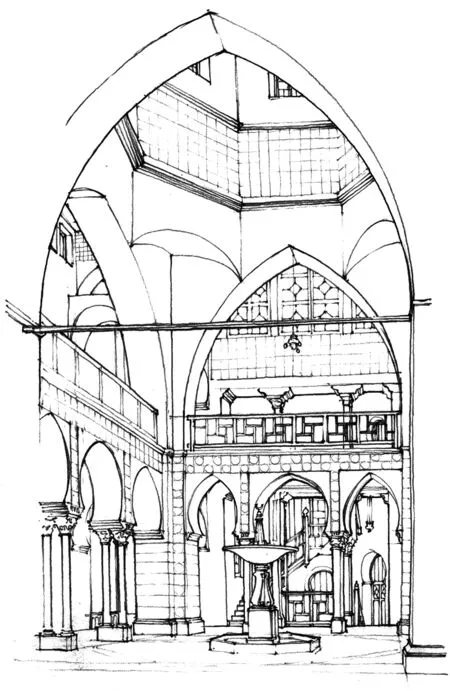
张禳关收集整理的对子,更多的,是春联类,如:“又是一年好光景,春满乾坤福满门。”“一年四季行好运,八方财宝进家门。”哪一类对子都可以二次使用,所以得积累起来,抄在本子上,以后要用,就不必为写啥而伤脑筋了。
张禳关最享受人们上门求他写春联的日子,但再咋样享受,他也有他的原则:给张家坝人义务写春联,只能是大年三十这一天。不到这一天,他要干这干那,不写春联;过了这一天就是大年初一了,用不着写春联了。张家坝户数不多,也就五六十户。一部分人家,年过得俭省,春联就不写了。需要写春联的一般也就三十来户,这三十来户里,多半只写一副春联,要么贴在大门门框上,要么贴在厅房门框上。贴在哪搭,全凭兴趣。只有极少数人家,比如祖佑家、队长家、会计家、老罗家……春联要写三五副、五六副,他们都是大队干部、生产队干部,张禳关不敢得罪他们。每年腊月二十九日夜,都是张禳关分头上门去问,问过了,拿上他们给他预备好的红纸,回家,当天晚上就把这些人的春联写好,把自家贴的春联也写好,把所有写好的春联和笔墨一起,藏在一个木匣子里。
每年过年,张禳关都给自家写五副春联。他家厅房一间、睡房两间、灶房一间,还有大门。只能写五副春联,多了就没地方贴了。年年过年,张禳关都给自家写够五副春联。他是生产队的记工员,大小是个干部,说话做事要向干部们看齐,不能向社员们看齐。
到了大年三十早晨,张禳关睁开眼睛,从炕上一骨碌爬起来,茅坑顾不上去,脸顾不上洗,饭也顾不上吃,他得分头送春联,越早越好,迟了就不好了,就显得不那么殷勤了。张家坝人家家户户都在腊月三十这天贴春联。队长家的、祖佑家的、会计家的、老罗家的,张禳关到了一家,听几句感谢他的话,再到一家,再听几句感谢他的话。他很享受这些话。春联送完了张禳关才回家蹲茅坑、洗脸、吃早饭,吃完早饭,假装要贴春联。年年都这样。张禳关刚要给自家贴春联时,求他写春联的人就陆陆续续进了门,这些人一来,他就用不着自己动手贴春联了,他们会帮他贴。张禳关不求他们帮他贴,是他们求他,非要帮他贴春联。他们帮张禳关贴春联,张禳关就可以腾出手来,给他们写春联了。
张禳关就爱张家坝人求着他,被人求的那种感觉,真不错。
在张家坝,张禳关字写得最好:大大的,方方正正的,一个顶一个。字要写得方方正正,人也要做得方方正正。张家坝人这么认为,张禳关也这么认为。张禳关的毛笔字写得更是不错,是标准的颜体字。张禳关并不晓得他写的字就是颜体字,他也不晓得颜体字是咋样的字,他只是这么写而已。张禳关写字,每一撇、每一捺,活脱脱都像一把刀,张家坝人已习惯了这样一种审美,他们把张禳关的这种写法,美其名曰“拉刀撇儿”,这是张家坝人对毛笔字的评价原则。在张家坝人心目中,“刀撇儿”拉得好,笔笔都像一把刀,毛笔字就写得好,“刀撇儿”拉得不好,哪怕只有极个别的撇和捺不像一把刀,毛笔字也就写得不算好:有毛病,有瑕疵。张禳关写对子写得极其认真,每一撇每一捺都必需拉出“刀撇儿”。张家坝没几个认得字的人,会写毛笔字的只有张禳关,但人人都有眼睛,都看得见撇和捺拉得像刀不像刀,所以,都会看看对子,都会谈讲谈讲。对子写好了,贴上了,人们就会逐字逐句,一边欣赏,一边谈讲,好听不好听,他都得接受。对子写好了,贴上了,就是改不了的了。
会写字也是张禳关当记工员的原因,他心里亮清。
大年三十这天,张禳关送完对子洗完脸,刚想坐下吃早饭,稀屎客就拿着一沓皱巴巴的红纸从大门进来了。
张禳关正打算吃早饭呢,听见来了人了,就给老婆使一个眼色,叫她先甭舀饭。
稀屎客一进大门就笑嘻嘻打趣说:“我的老孙子,你在忙啥到呢?”
张禳关没事,不忙。他今天在家,就在等人找他写对子。也只有在写对子的时候,张禳关心里才会泛起被人尊重的那种暖暖的感觉。按说,张禳关终于等到了这一年的这一天,终于等到了这一天的第一个“客户”了,心情应该很不错,可稀屎客只用一句“老孙子”就把张禳关的好心情破坏得荡然无存了。
张禳关看看稀屎客才摊开两手说:“你看看你这个人,老都老了,还是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找我帮你写对子,也不忘糟蹋我几句。”
“你就是我的老孙子嘛!你也是张家坝人的老孙子嘛,我莫非说错了?”稀屎客脸上,仍是笑嘻嘻的。
“你对!你对!你说得很对!你是毛主席,永远都对!”
稀屎客不笑了:“你也真是的,开不起玩笑。”
“你是爷,我是孙子,孙子没爷肚量大。”
“你看你这个人,开个玩笑的事儿,你还当了真了!”
给稀屎客这么一打趣,张禳关已没了帮他写对子的心情。老话说得好:高房出矮辈。张禳关的辈分确实低,屁大的娃娃,按辈份,张禳关也得叫爷。但辈份低似乎成了捏在别人手心里的把柄,这辈子都是摆脱不了的,张家坝人,也是人前人后,不求他写对子时,都叫他“老孙子”。平时这么叫,张禳关不想接受也得接受,因为这是事实。可今天不同。今天是大年三十,是人们求他张禳关的日子,在这一天,当着他的面,张家坝人从不叫他老孙子。
张禳关的心情就像腊月的天一样,一下子变得阴沉沉的,稀屎客再咋样低声下气求他赶快写对子,张禳关却是提不起精神来。
一动不动,张禳关就在火塘边。
稀屎客站也不是,坐也不是,就讪讪说:“快写吧,今天你是爷,我是孙子,我给你赔情道歉还不成吗?”
“我想不起句子来,你让我咋写?”
“你不是有一个本子呢嘛,你的本子上积攒了很多对子呢嘛,拿出来,随便写一个就成。”
“我的本子没见了,找了一早晨,还是没找着。”
张禳关说的,是假话。稀屎客晓得他在说假话。
“死人也得守住四页棺材板呢,你会丢了本子?哄鬼呢吧?”
“要不,你帮我找找?”张禳关冷冷说。
“这是你家屋里,我上哪搭找去?”
“要不你就给我编对子,我帮你写?”
“我没得那个本事。”
“你是爷嘛,木匠都能无师自通,编一副对子,还不是个简单事儿?”
“你甭挖苦我这个大老粗了,给个痛快话儿,到底写不写?一副对子的事儿,不写算球了,我就不信不贴这副对子,我还过不了年了。”
“不是我不给你写,是我找不着本子。要不,你还是把红纸留下吧,等我找着了再给你写,写好了,亲自给你送过去?”
“我不是干部,我享受不起。”
不想立即给稀屎客写对子,也就没打算进屋取抄满了对子的那个本子。张禳关当然晓得本子藏在啥地方。墨汁、毛笔、本子,包括已给自家写好的对子,都藏在那个木匣子里,夜个黑了才搁进去的东西,忘是不可能的。
稀屎客哼了哼,黑脸说:“纸我给你留下了,写不写是你的事。”
稀屎客说完,走了。
望了望稀屎客远去的背影,张禳关嘴里也哼了哼。哼完了,他还小声咕哝一句:“这个二木匠!”
木匠就是木匠,哪搭来的“二木匠”?二木匠当然是挖苦稀屎客的话,是说稀屎客的木匠手艺没哩正正经经拜师学艺,这样的木匠手艺再好,也只能给正经木匠打下手,是不能请来当掌墨师傅的。二木匠是张家坝人给稀屎客取的第二个绰号,跟“稀屎客”一样,都有瞧不起他的意思。
张禳关的话稀屎客当然没听着。对子,张禳关肯定也要给他写,不费事,不费墨,犯不着得罪了稀屎客。但张禳关想拿捏拿捏这个不会说话的稀屎客。拿捏了稀屎客,把稀屎客气走了,张禳关的心情,也就舒畅起来了。
张禳关再次坐到火塘边,示意老婆舀饭。
一边烤火,一边吃饭,一边等着下一个找他写对子的人。
腊肉的功能
老罗到张家坝的第二年就找队长,说是他要出门给生产队搞副业。老罗说:“一个生产队,没得粮食万万不成,光有粮食也不成,队里没得钱,你这个队长也不好当是不是?”
队长想了想,就答应了老罗。
老罗搞副业,干的还是他的老本行:石匠。老罗在外游荡了快一年,回张家坝时,满英已给他生了儿子罗思川。可这一年,满英因为怀孕坐月子,工出得很少。老罗回来后,虽说给生产队交了副业款,他自己这一年的工分有了,满英却因出了不足半年工,工分挣得太少,一家那么多口,只凭那点儿工分分口粮,吃一年是远远不够的。
老罗在四川老家时,有他的办法。
老罗把他在四川老家的办法又用了一次。
天黑了,天黑得啥也看不着了。
老罗提了一坨腊肉,悄悄摸到张禳关家大门口。除了大年三十那天,张禳关家几乎再无客人。听见敲门声,张禳关以为自己听错了。侧耳听听,真是有人在敲门,张禳关不晓得谁会来敲他家的大门,迟迟疑疑开了门,一看,来的是老罗。张禳关一怔。晓得老罗是来给他送礼的,张禳关更是吃了一惊,头摇得就跟拨浪鼓似的。
“我不是要你给我多记工,你给满英多记二三十天工,也就成了。”
“这不成,这不成,多记一天都不成。队长要是晓得了,还不免了我的职务?”
“一个破记工员,免了就免了,你又不会损失啥。”
想想,也是。会计在家休息,嘴上却说要记账,队长还不是给会计评了工分,让他这个记工员把工分给会计记上了?会计记账没记账,恐怕只有天晓得!再说队长吧,他明明是到金山镇赶场去,却非要说他是去公社开了一个啥子会,他这个记工员还不是乖乖地给队长把工分记上了?到底开会没开会,在张家坝,只有队长晓得!
作为生产队的记工员,张禳关就没得会计和队长的那种待遇。张禳关出一天工,就记一天工分,不出工,就没得工分。问题是,他这个记工员不出工还不行。他不出工就没人给社员们记工分。别人可以请假,在家歇气,他不成。张禳关给队长请过几回假,队长半天假也不准,队长说,你张禳关请了假,就没人给社员们记工分了。这是啥子逻辑?每天都是别人放工回家了,自己还跟队长摸着黑,给出了工的社员们一一记工分。当了多年记工员,队长没让给他张禳关多记一天工分,当这个记工员,捞到啥子好处了?
发觉张禳关不说话了,老罗就有了把握。
“生产队这么多社员哩,谁一年出了多少工,队长记得清吗?”
是记不清。当了这个记工员,除非查看记工分的本子,他也说不清谁出了多少工。
“当一个干部,不给自己捞一点好处,不如不当。”
老罗的话,不是没道理。
张禳关也不是没这么想过,但他年年出全勤,给自己,没法多记一天工。不能给自己多记,还不能给别人多记吗?张禳关突然感到豁然开朗,开了窍了。他想,我咋没想到这一层呢?
老罗又说:“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我不说你不说,队长就算怀疑你,也没得凭证。”
张禳关的脑壳先是低了下去,后来就搁在膝盖上了,他把脸埋在双腿之间,啥也不说,心里想的却是,那是一坨腊肉哩,就算不拿它当肉,当油来吃,也得吃上足足一个月。
老罗是啥时候走的,张禳关居然不晓得。张禳关从两腿之间抬起脑壳时,老罗已经不见了,回头看看吃饭的小方桌,腊肉还在小方桌上。
张禳关家已有几年不曾喂过猪了,杀年猪,吃肉,仿佛已是上辈子的事。
有了老罗送腊肉的事,张禳关就会当这个记工员了。谁对他好,谁帮了他,张禳关就悄悄给谁说:“我给你多记了三天工。”听话的这人,到了年底,在心里算算,果然不多不少,多记了三天工。多记了工,跟别人无关,当然要记着张禳关的好。得到好处的人,不对张禳关另眼相看当然不成。慢慢的,在张家坝,很少有人再在当面叫张禳关是“老孙子”了,即使背地里也不怎么叫,谁要是背地里还这么叫他,就有嘴长的人,说到张禳关耳朵里。张禳关晓得了,虽说不能把叫他老孙子的人咋样处置处置,但是,跟记工分似的,张禳关会把叫他老孙子的人,也记一本账。叫他几次老孙子,张禳关就给少记几天工。年底分红,你说张禳关给你少算了工分,但张禳关的工分本上,有据可查,谁也拿他没办法。
当了这个记工员,有人送腊肉,有人送米面,也有人送别的东西,还给人写对子做啥呢?给人写对子,一口饭也混不到嘴里,一口汤也喝不到嘴里,不是白劳神嘛。
当干部真是太好了。张禳关不想给社员们无偿写对子了。
一坨腊肉,改变了一个人。
仕途
在张家坝生产队,张禳关后来就成了一个受人尊敬的人,人们都拿他当干部看待。张禳关自己,却只尊敬队长。除了队长张有根,其他人,包括身为大队民兵连长的祖佑,包括会计、保管员,张禳关都不放在眼里,贫协主任、妇女主任,更不拿他们当干部看待了。
张禳关想,除了队长,谁也无权免了我的记工员。
在队长面前,张禳关始终战战兢兢,唯唯诺诺。
有了给人“送工分”这个生财之道,张禳关就不想替张家坝人写对子了。但不写不行。自己贴的春联,他还得写。队长家的、祖佑家的,他也写,仍是主动上门取纸,写好了,又送货上门。老罗家的、会计家的,他就不再上门取纸,写好以后又主动送货上门了。老罗和会计要写春联,也得和社员们一样,在年三十这天,拿纸给他,张禳关才帮他们写。其他社员,年三十这天拿纸上门求他,他才咕咕哝哝帮他们写,还是一脸不高兴。
“张禳关的架子,越来越大了!”张家坝人背地里都这么议论,当面却是啥也不说。
红白喜事有人请他当“大笔先生”,这是受人尊敬的事儿,张禳关也得写。红白喜事乃是人生大事,不帮人家写对子,也得帮忙干点儿别的。出力气的活,跑腿的活,不如写对子。
张禳关仅仅是不轻易动笔了。
张禳关主动写对子的名单里多了一个人,是住在王家山的王支书。
近几年,过年前,张禳关提前几天写好春联,托人捎到王家山,捎给王支书。给王支书的春联,红纸都是张禳关出钱买的,王支书从未拿红纸给他。
很平常的一天,王支书在队长面前说起了张禳关:“这个张禳关,人不错的嘛。”
“人是不错。”队长附和。
“他的字写得有模有样的嘛。”
“在张家坝,能够提笔写写毛笔字的,也就他一个。”
“是个人才嘛。”
“确实是人才。”
“人才就不能浪费嘛。”
“我让他当记工员哩。”
“当会计也不是不行嘛。”
“会计有人当着哩。”
“啥职务都是可以换的嘛。”
咋换?换了咋办?队长低头陷入了沉思。
队长抬起头来时,王支书已不晓得啥时候走了。
队长又低下了头,一个人,愣了很久。
队长没回家,去了会计家。队长想,会计准是啥地方得罪了王支书。
“你这个人,得罪王支书做啥?”
“我没得罪王支书呀!”会计看看队长,一脸无辜。
“真没得罪?”
“真没得罪。”
“王支书要我换了你。”
会计一听也急了:“我咋敢得罪王支书嘛!”
会计没做得罪王支书的事,队长就有些放心了。
从会计家出来,队长想了想,又去了张禳关家。
队长到家里来,张禳关有些受宠若惊的感觉,虽说队长爱串门,但队长串门都是有目的的,他从不曾到张禳关家串过一回门。
“你这个人,看不出来嘛。”
张禳关云里雾里,啥也搞不清,只好望着队长。
“你跟王支书到底是啥关系嘛。”
“没啥关系。”
“真没关系?”
“真没关系。”
“有关系你就给我明说。”
“那是,那是。”
“是我让你当这个记工员的,我也可以抹了你的记工员。”
“哄谁我也不哄你。我跟王支书,真的没啥关系。”
队长心里想的是,要是核实了张禳关跟王支书有个啥关系,就只能换掉会计,让张禳关当会计,就只能委屈会计,让会计当记工员。张禳关这么说队长就不想换会计了。队长和会计,有很多账目说不清道不明,他也不敢轻易换会计,队长也怕惹恼了会计,把不该说的说出来。
从张禳关家出来,队长原打算到会计家再做做会计的工作,张禳关这么说,队长就觉得没必要再去会计家说啥了。
后来,队长就把这事给忘了。
后来,王支书就碰见了张禳关,王支书问他:“你想不想当一个会计?”
“会计?”张禳关当然想当。
但张禳关转念一想,会计不是有呢嘛,当得好好的嘛。
“当倒是想当。”想归想,张禳关还是说了句实话。
“你等着吧。”
王支书说完,走了。他到公社开会去了。
莫非我能当会计?当会计比当记工员好多了。
更后来,王支书又碰见了队长。
“给你说的话,忘了?”
“啥话?”队长摸不着头脑。
“我的话你要是不听,也不是不行。”
队长一听又急了:“党的话我能不听?我真是忘了你说的话了。”
王支书笑嘻嘻说:“我也不晓得我说了啥话。”
队长后来就想起王支书给他说过的话来了。队长觉得不去一趟会计家,看来是不行的了。队长一进会计家的门,就冲会计发火说:“你这个会计到底是咋当的?”
“又咋的了?”
“你要明白问题的严重性,不是你的会计当得成当不成的事,王支书要是对我有了啥看法,我这个队长当得成当不成也成了问题。事情明摆着,是王支书对你有了成见了!”队长急赤白脸,接着说,“我们两个是拴在一根绳上的蚂蚱,你可不能拖累我。”
“不会吧?”
“你还是去一趟王家山,给王支书汇报汇报去。”
“汇报啥子?”
“你想汇报啥,就去汇报啥。”
“我一个人不敢去。要不,我们两个一起去?”
“你去,我不去。去了好好跟王支书说,亮明你的态度,表表你的决心。”
会计有些发蒙。
“事不宜迟。你今晚就找王支书去。”
天黑之后,会计捏了把手电,提着两吊腊肉,悄悄去了王家山。
后来,王支书问队长:“张禳关这个人,到底咋样?”
队长说:“张禳关我还不晓得?写个对子当个记工员,都能成。但他没啥大用处,狗肉上不得宴席。”王支书想了想,也就不说啥了。
后来,王支书又碰见了张禳关。
“我问你,你说你想当会计,队长问你,你又说你不想当。这个会计你到底想当不想当?”
队长没问过我呀!张禳关想,但在王支书面前,他不敢说队长的不是,他怕王支书把话说到队长耳朵里。在张家坝,张禳关最不敢得罪的人,就是队长。
“我没那个本事。”张禳关说。
“你这人,靠不住。”
王支书看了看张禳关,摇摇头,啥也不说了。
王支书本来也不是非要让张禳关当这个会计。他只是给自己找一个台阶,就坡下驴。
王支书再也没提让张禳关当会计的事儿。
张禳关的政治生涯就这么结束了。张禳关觉得,要是能把这个记工员一直当下去,也就不错了。
年年过年前,张禳关仍然托人给王支书捎几副春联。
张禳关觉得,王支书还是赏识他的。
有人赏识,他很高兴。
——《古对今》教学活动设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