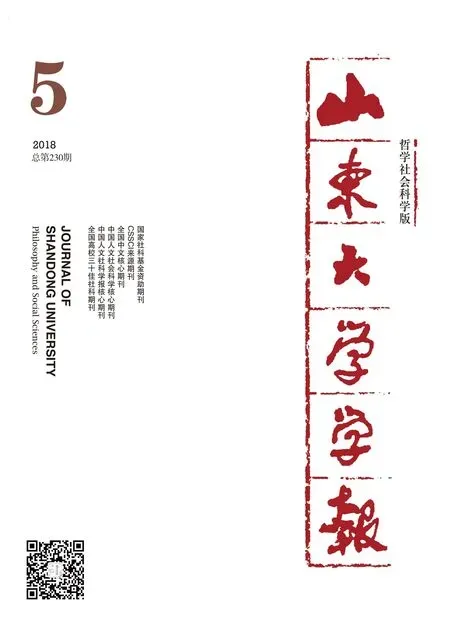欧洲民粹主义政党崛起的影响
郑春荣
2017年一度被认为是决定欧盟的命运之年,这主要是因为欧盟迎来了其三个创始成员国荷兰、法国和德国的国内大选,人们尤其担心右翼民粹主义政党荷兰自由党以及法国国民阵线会分别赢得荷兰和法国的大选,从而在这两个国家就是否脱离欧元区乃至欧盟举行全民公投,并最终可能会导致欧元区乃至欧盟的瓦解。
欧盟最终有惊无险地经受了荷兰与法国大选的考验,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并未像人们所担心的那样上台执政。虽然右翼民粹主义政党此轮冲击的势头有所缓解,但是,这绝非意味着它们会就此偃旗息鼓。而且,它们的此轮崛起,已经给欧盟各成员国的国内政治、欧盟的未来发展前景以及欧盟及其成员国的对外行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如果欧盟及其成员国不能对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加以“政治化”的议题做出有效应对,那么,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就很有可能在下一次危机造成的“时机之窗”到来时,利用“机会结构”,形成又一个“民粹主义时刻”*Lawrence Goodwyn, Democratic Promise. The Populist Moment in Americ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6.,给欧盟及其成员国造成更大的冲击。

一、民粹主义政党的概念、特征及其在欧盟内的崛起


总之,欧盟内的民粹主义是反建制的,尤其那些职业政客、代议制民主的机构、主流政党及其政策被它们树立为“敌对形象”,是它们抗议的中心目标。与拉丁美洲国家民粹主义的另一个区别在于,欧盟内的民粹主义都带有疑欧乃至反欧的诉求,结束由于持续欧洲化而导致主权的进一步丧失是其中心诉求[注]Cas Mudde and Cristóbal Rovira Kaltwasser, Populism in Europe and the Americas: Threat or corrective for democracy? Cambridg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由此,疑欧主义和移民问题成为了欧盟内变得日益脆弱的政党体制的新分歧线。

在2016年6月23日的英国脱欧公投中,“脱欧派”以51.9%的得票率险胜,在这个过程中,右翼民粹主义的英国独立党发挥了至关重要的、引导民意的作用;11月美国特朗普赢得总统大选后,欧盟内的右翼民粹势力再次得到鼓舞,欧盟及其成员国的政治精英也开始为欧盟内的每一次选举中右翼民粹主义政党是否会再次制造“黑天鹅”事件而提心吊胆。好在这些挑战都有惊无险地过去了:先是在12月初的奥地利总统第二轮选举中,右翼民粹主义的奥地利自由党候选人诺伯特·霍费尔——如果他当选,他就成为西欧国家第一个右翼民粹主义政党身份的总统——败给了独立候选人亚历山大·范德贝伦(Alexander Van der Bellen)。其后,在2017年3月的荷兰大选和5月的法国总统选举中,右翼民粹主义政党也未能取得此前民调所显示的胜绩。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此轮挫败与美国特朗普总统的执政表现以及英国公投脱欧后的乱局给选民带来的警示作用不无关系。
虽然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经过此轮冲击波之后,势头有所减弱,但就此作出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将由此沉沦的判断还为时过早。毕竟在荷兰大选中,基尔特·维尔德斯(Geert Wilders)领导的右翼民粹主义的自由党在议会中获得了20席,比上届议会选举多了5席,并由此成为了议会内最大的反对党;而在法国方面,国民阵线领导人玛丽娜·勒庞虽然在总统第二轮选举中输给了“非左非右”的“前进”运动领导人伊曼纽尔·马克龙,但是第二轮投票中35%的支持率远好于其父亲在2002年时的表现(18%)。在德国,在2017年9月大选后,德国另类选择党如期进入了联邦议院,而且,在基民盟/基社盟与社民党2018年3月再次组成大联合政府后,它成为了议会内的最大反对党。在2017年10月15日奥地利国民议会选举后的两个月,奥地利自由党也与人民党达成了联合执政协议,再次参与执政[注]郑春荣、范一杨:《欧洲右翼民粹政党的发展条件分析——以奥地利自由党为例》,《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7年第2期。。此外,在2017年10月21日结束的捷克议会选举中,“捷克版特朗普”安德烈·巴比什(Andrej Babis)创立的反欧盟、反欧元、反难民的民粹主义政党“ANO2011”党成为选举最大赢家,获得优先组阁权,并被任命为政府总理;而其政治盟友、总统米洛什·泽曼(Miloš Zeman)在2018年1月27日的总统第二轮选举中赢得连任。在匈牙利,维克托·欧尔班领导的执政联盟在2018年4月的选举中再次以三分之二以上的绝对多数获胜连任。而在2018年3月的意大利议会选举中,民粹主义的五星运动成为最强大的单一政党,经过一番波折后,五星运动与另一民粹主义政党联盟党(Lega,原为“北方联盟”)组成了联合政府。
由此可见,欧盟内右翼民粹主义力量的这一波冲击并未结束,它们只是在欧盟一些最核心的国家遇到了挫折,绝不能判断已经出现了趋势转折[注]郑春荣:《右翼民粹主义影响下的欧洲一体化会走向何方?》,《当代世界》2016年第5期。。实际上,民粹主义政党、尤其是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在欧盟内的普遍崛起已经给欧盟及其成员国带来了多重影响。
二、民粹主义政党对欧盟成员国国内政治的影响
民粹主义政党的崛起可以通过不同途径影响成员国的国内政治。一个可能的影响是,政党格局变得更加多元化、碎片化,组建(联合)政府经常变得越发复杂和耗时,并最终导致更为脆弱的政府的形成。另一个可能的潜在影响是对政府或主流政党政策内容及其话语方式的影响。最大的影响是,西方的民主政体可能因为民粹主义政党的崛起而面临挑战[注]Alberto Martinelli (ed.), Populism on the Rise: Democracies Under Challenge, Milano: ISPI, 2016.。然而,民粹主义也能起到警醒作用,它们把大部分民众关切的、但政治精英想要避免讨论的议题置于核心,例如右翼民粹主义政党提出的移民问题或左翼民粹主义政党提出的财政紧缩问题[注]Cas Mudde, “The Problem with Populism”, The Guardian, 17 February 2015.,由此迫使政府或主流政党的精英正视并采取措施来应对这些问题。
(一)政党格局多元化导致脆弱政府的形成

其次,民粹主义政党这些可能拥有联盟或勒索潜力的政党数量的增加,会使得政府组阁形势变得复杂,组成后的执政联盟也会变得更加脆弱,抑或主流政党组成的联合政府会面临强大的、作为反对党的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牵制或勒索。例如,在2017年3月15日的荷兰大选中,首相吕特(Mark Rutte)领导的自由民主党胜出,但是,由于基尔特·维尔德斯领导的右翼民粹主义政党自由党的议席上升,而其他主流政党得票分散,不仅使得自由党成为议会内最大反对党,也使得自由民主党至少需要组成四党联盟,才够执政所需多数。经过近7个月的组阁尝试,吕特才在10月中下旬组成了在议会仅拥有一席多数的四党联合政府。即使在政局算欧盟内最为稳定的德国,基于德国另类选择党在2017年9月的联邦大选后进入联邦议院,由此使得德国进入联邦议院的政党数达到6个,由于社民党在大选结束后当日就因糟糕的选举结果一度宣布成为反对党,使得唯一的组阁可能性就是基民盟/基社盟、自民党和绿党组成跨政党阵营的三党联盟,而经过四个多星期的试探性会谈,三党联盟的试验夭折,默克尔陷入了组阁困境,甚至一度不排除需要进行重新选举的可能性。好在德国社民党领导层“回心转意”,在联邦总统施泰因迈尔斡旋下,与基民盟/基社盟重启组阁谈判,并最终在2018年3月14日艰难完成组阁,这已经距离选举过去了171天,成为德国历史上组阁时间最长的一次。
(二)主流政党政策内容与话语方式受到民粹主义政党传染

主流政党应对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策略是多种多样的,从对民粹主义政党污名化、禁忌化或排斥在政治活动与讨论之外,到包容乃至模仿,直至与民粹主义政党合作,但是没有一种策略是灵丹妙方。就拿模仿来说,2016年在奥地利,在当时执政的社民党模仿右翼民粹主义的自由党的主张,转向实施更为限制性的难民政策后,社民党反而陷入了一场深刻的危机之中,并以联邦总理维尔纳·法伊曼(Werner Faymann)的辞职为顶点;但是,31岁的奥地利外长塞巴斯蒂安·库尔茨(Sebastian Kurz)领导人民党却在2017年10月的国民议会选举中取得了成功,库尔茨支持将难民进入欧洲的巴尔干通道关闭,并在穆斯林群体融入当地社会问题上推行强硬政策,在欧洲一体化上也表现出保守倾向,由此,其政策主张与奥地利自由党接近,也为选后两党的联合组阁创造了基础。又例如,在英国公投脱欧前夕,工党和保守党迫于独立党的压力,不得不采取类似于独立党的立场,却招致了党派内部的分裂和骑虎难下的决策困境[注]玄理、刘玉安:《边缘政党的主流化:探究英国独立党的崛起》,《新视野》2017年第1期。。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可以宣称,主流政党的“模仿”其实是证明了其主张的正确性,选民也很有可能更愿意把选票投给“原版”立场的提出者,而不是作为拷贝者的主流政党。
除了在政策主张和所采取的措施上,主流政党会向民粹主义政党靠拢,在话语方式上也会受到传染。民粹主义政党善于挑起极化的政治讨论,其魅力型领导人也乐于用简单化的口号或挑衅性的言论来赢得选民。例如,在2017年3月荷兰大选的最后阶段,土耳其官员意欲在荷境内开展竞选活动,首相吕特禁止土耳其官员入境,引发了荷土外交风波,但是,吕特对土耳其的强硬外交姿态,为他博得了部分右倾选民的好感,这也是他最终战胜右翼民粹主义的自由党的原因之一[注]陈博:《荷兰大选显现欧洲政治风向》,《经济日报》2017年3月22日,第9版。。
(三)西方自由民主体制受到挑战
民粹主义政党的出现与崛起,从本质上讲,也是由于西方的代议制民主存在赤字以及主流政治家缺少对此的有效回应。无论如何,“民粹主义运动和政党经常起到的是一场政治危机的警示信号的作用”[注]John Judis, “US v Them: The Birth of Populism”, The Guardian, 13 October 2016.。
但问题在于,民粹主义是一种“一元论者和道德论者的意识形态”,所以,它否认与“人民”有区分的利益与观点的存在,并拒绝承认政治反对分子的合法性。这一不妥协的立场会导致一种极化的政治文化的形成,使得非民粹主义者变成反民粹主义者[注]Cas Mudde, “The Problem with Populism”, The Guardian, 17 February 2015.。为此,有学者认为,基于民粹主义是一种“稀薄的意识形态”,它隐含着一种特殊的“非西方自由式民主”的愿景,具体包含有三个“非自由的”成分:首先,它按字面意思理解“民治的政府”并因此拒绝所有自由的制衡机制;其次,它憎恨人民与决策者之间的中介、尤其是政党,要求大众与精英之间有更直接的联系;再次,它所持有的对人民意志的整体性理解,使得多元主义和讨论没有存在的空间[注]Hanspeter Kriesi and Takis Pappas, “Populism in Europe during Crisis: An Introduction”, in Hanspeter Kriesi and Takis Pappas (ed.), European Populism in the Shadow of the Great Recession, Colchester/UK: ECPR Press, 2015, p.8.。这也使得民粹主义政党普遍要求引入全民公投等直接民主要素,作为“唯一真实的人民意志”的表达[注]Cas Mudde and Cristóbal Rovira Kaltwasser, “Exclusionary vs. Inclusionary Populism: Comparing Contemporary Europe and Latein America”, Government and Opposition, 2013(3), p.165.。

三、民粹主义政党对欧盟行动能力与方向的影响

欧洲民粹主义政党的崛起正是这一“政治化”过程的表现,而“政治化”也是欧洲民粹主义政党利用的一种有效工具。结合以上三个维度的冲突,民粹主义政党至少在以下方面对欧盟决策以及一体化产生了影响:一是总体上限制了欧盟内部的共识达成与集体行动能力;二是对欧洲一体化的原有模式提出了挑战;三是助长了欧盟内的“逆全球化”思潮,从而对它的对外行动产生影响。
(一)欧盟内部共识达成与集体行动能力受到限制
欧洲民粹主义政党的普遍崛起,不仅分散了欧盟各国政府及其主流政党的精力和资源,使它们没有更多的精力和资源投入到欧盟事务中,而且,由于欧洲民粹主义与疑欧主义紧密相伴,即使民粹主义政党还未强大到掌握政权,它们也能影响成员国国内的力量对比和民众对欧盟的态度。由此,欧盟层面达成妥协的余地变小了,尤其在高度政治化的议题上,例如难民危机的应对。

(二)“多速欧洲”无奈成为欧洲一体化的新路径
英国公投脱欧已经足以证明,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煽动的反欧情绪会带来何其深远的影响。与此同时,英国脱欧也表明,“去一体化”不再是不可能的。如果说右翼民粹主义政党传统的标签是排外,那么,在欧盟面临多重危机的背景下,它们也把疑欧、反欧主张写入自己的旗号里,例如,无论是法国国民阵线、荷兰自由党、意大利五星运动还是德国另类选择党,这些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原则上都主张本国退出欧元区,乃至就是否退出欧盟举行全民公投。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如果能够得到足够选民支持,进入政府乃至领导政府,就有可能会阻止进一步的一体化,或要求某些领域的管辖权“回溢”至民族国家层面。这样的背景至少带来了两方面的影响,一是除英国外的欧盟27国急需寻求巩固内部团结的路径,二是它们还必须为欧洲一体化的未来确立新的行动方向。
一方面,在英国公投脱欧后,在民粹主义势力的牵制下,欧盟27国在未来的行动领域上只能寻求“最小共识”。2016年9月16日欧盟27国有关欧盟未来的布拉迪斯拉发非正式会议,通过了《布拉迪斯拉发声明》,明确表示,尤其要改善与欧盟公民的沟通,并把欧盟公民的关切置于中心地位。这表明欧盟精英认识到了需要从根源上抵制激进或民粹主义势力的影响。从2016年9月启动布拉迪斯拉发进程到2017年3月的罗马峰会,这一政治反思进程暂告一段落。从这一进程来看,欧盟27国能够达成一致的行动领域主要集中在欧盟外部边界管控和反恐等议题上。但在移民等问题上的矛盾依然严重,例如,对于布拉迪斯拉发峰会,以匈牙利为首的维谢格拉德集团四国认为峰会并不成功,因为欧盟并未改变其迄今的移民政策;它们在一份共同声明中反对欧盟强制摊派难民,主张在移民政策上引入一种“灵活的”团结性[注]郑春荣:《右翼民粹主义影响下的欧洲一体化会走向何方?》,《当代世界》2016年第5期。。欧盟27国迄今依然无法消弭其在难民政策上的“东西分歧”。
另一方面,鉴于原先“日益紧密的联盟”这种欧洲一体化模式导致了欧洲民粹主义政党的普遍崛起,以及促成了英国公投脱欧,这就迫使欧盟27国寻找新的一体化路径。从欧盟委员会2017年3月发布的《欧盟未来白皮书》,到3月25日发布《罗马宣言》,欧盟内主张推行“多速欧洲”这一差异性一体化模式的声音渐涨,这些人认为,鉴于欧盟内的政治气候以及各个成员国在特定政策领域的巨大分歧,“多速欧洲”是更为现实乃至唯一可行的选项。“不求同步,但求同向”,是欧盟内拥欧人士在右翼民粹主义势力冲击下的无奈选择。但是,对于“多速欧洲”也有抵制的声音,例如维谢格拉德集团四国担心会因此被欧盟内的大国边缘化,警告不要出现欧盟的“去一体化”。其中,右翼民粹主义政党领导下的匈牙利和波兰政府,致力于实现“更少的欧洲,更多的国家主权”,它们要求限制欧盟的多数表决制,把管辖权从欧盟层面转回到成员国层面,增强部长理事会的作用而削弱欧盟委员会与欧洲议会的地位,使欧盟回归为一个更具政府间特征的联盟[注]郑春荣:《右翼民粹主义影响下的欧洲一体化会走向何方?》,《当代世界》2016年第5期。。由此可见,它们把灵活一体化不是视作增强欧盟团结与行动能力的出路,而是视作在某些领域重新增强民族国家主权的机会,2018年6月28日欧盟峰会艰难达成的难民协定也只能建立在成员国自愿合作及接受难民上[注]Almut Möller and Dina Pardijs, “The Future Shape of Europe: How the EU Can Bend without Breaking”, European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http://www.ecfr.eu/specials/scorecard/the_future_shape_of_europe, last accessed on 15 July 2017.。
(三)欧盟内“逆全球化”思潮暗流涌动

无论如何,为了把“全球化输家”从右翼民粹主义政党那里赢回来,主流政党必须就民众对全球化的恐惧作出反应。为此,我们可以看到,欧盟国家一方面公开反对美国特朗普总统所奉行的贸易保护主义和孤立主义政策,把自己表现为全球化的捍卫者。但是,在实践中,它们又迫于内部右翼民粹主义势力的压力及其搅动的“逆全球化”暗流,而采取一些带有贸易保护主义倾向的措施。例如,欧盟委员会在关于全球化的一份反思文件中表示,欧盟致力于全球化收益更好地分配,为此,欧盟可以通过抵制有害的和不公平的行为方式(如逃税、不允许的国家补贴或社会倾销),以敦促制定以建立平等竞争条件为目的的规定;动用有效的贸易保护手段和建立多边投资法院同样可以帮助欧盟坚定地应对那些采用不公平做法的国家或企业[注]European Commission, Reflection Paper on Harnessing Globalisation, Brussels, 10.05.2017.。由此可见,欧盟有以“公平贸易”之名,行“保护主义”之实的嫌疑。
欧盟的保护主义倾向最明显地表现在对我国的投资贸易防护机制的提升上。到目前为止,欧盟并未根据 2001 年欧盟与中国签署的《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议定书》第15条的规定,承认我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并取消反倾销中的“替代国”做法,而是引入了变相措施:2017年12月4日欧盟理事会通过的反倾销调查新方法修正案,虽然取消了所谓“非市场经济国家名单”,但引入了“市场严重扭曲”的概念,为此仍然保留了对中国实施“替代国”做法的可能性[注]Regulation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amending regulation (EU) 2016/1036 on protection against dumped imports from countries not members of the European Union and Regulation (EU) 2016/1037 on protection against subsidised imports from countries not members of the European Union,Brussels, 23 November 2017 (OR.en).。另一方面,鉴于中国近年来对欧、对德企业投资并购迅速增加,尤其是德、法、意三国积极推动在欧盟层面在现有的“安全性标准”外,引入投资审核的“经济性标准”。在欧盟内,法国新总统马克龙也是要求限制中国投资的积极支持者。他在2017年6月22日举行的欧盟峰会上,提出给予欧盟更多权力,在欧盟设置外资投资监管机构,以限制中国对欧洲关键产业的投资。由于希腊、葡萄牙和捷克等国的反对,德法意提出的升级欧盟投资防护机制的计划暂时搁浅。然而,2017年7月德国联邦政府通过了德国联邦经济部提交的《对外经济条例》第九修正案。该修正案扩大了投资审查的范围,把特定的关键基础设施和额外的军工企业纳入其中,旨在外国投资者收购德国具有战略重要性的公司问题上保留否决权。德国作为全球化受益者、捍卫者,单边率先提高投资防护机制,无疑将进一步激励欧盟内的“逆全球化”思潮。
四、结语
虽然在荷兰、法国与德国等国大选中,民粹主义政党没有再能制造“黑天鹅”事件,但是,它们并不会就此沉沦,而是会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构成对主流政党的挑战,其他国家内民粹主义政党的一次次得势也证明了这一点。这一方面是因为,从历史上看,目前欧盟内的民粹主义势力仍然处在高位。另一方面是考虑到欧盟面临的诸多危机如难民危机、暴恐危机、债务危机、英国脱欧危机、乌克兰危机等,中短期内都不可能得到彻底的解决。尤其是如何有效响应欧盟内“全球化输家”的关切,消除他们对全球化(臆想中)的恐惧,使全球化惠及更多的人,这也是欧盟内的政治精英面临的严峻挑战。当前,欧盟首先需要面对的是2019年5月的欧洲议会选举,欧洲民粹主义政党在何种程度上会进一步得势,尚不明朗。
必须看到,民粹主义具有警醒作用,它把大部分民众关切的、但政治精英本想避免讨论的议题提了出来,接下来就要看主流政党如何应对。排斥或“去政治化”的战略已经被实践证明并不有效[注]李明明:《欧洲一体化的政治化与欧盟成员国主流政党的应对战略——以欧债危机发生后的德、英、法三国为例》,《欧洲研究》2017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