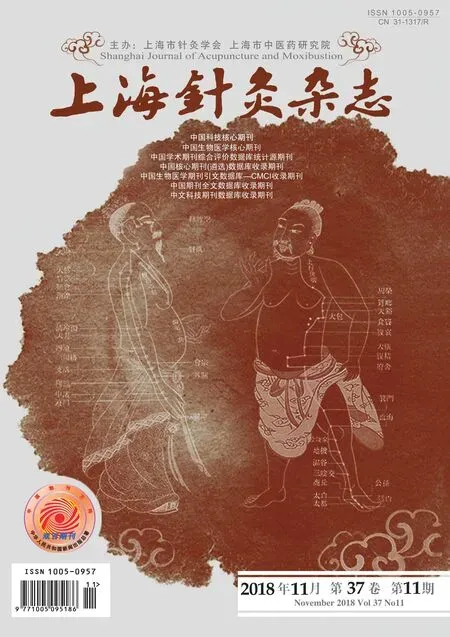不同电针刺激参数对镇痛效应影响的研究概述
付宏伟,阎丽娟,刘阳阳,郭义,郭永明
不同电针刺激参数对镇痛效应影响的研究概述
付宏伟1,阎丽娟2,刘阳阳2,郭义2,郭永明2
(1.天津市滨海新区中医医院,天津 300450;2.天津中医药大学,天津 300193)
该文通过整理、总结分析电针镇痛相关的实验研究及临床研究,从电针频率、电流强度、电压、波形、电针时间等方面,探讨影响电针镇痛效果的因素。研究发现电针参数是影响电针效应的重要因素,其频率为2~100 Hz,固定频率及变频均有选用;刺激电流0.1~3 mA,刺激电压2~20 V,以2~3 V为多;留针时间5~45 min。即使是相同实验设计,其电针参数的选择也未能统一。因此,电针参数需进行量化,才能为实验研究提供统一、客观的标准,更能为临床选择最佳电针参数提供理论依据。
电针;疼痛;针刺镇痛;综述
1996年11月召开的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意大利米兰会议,提出了64种针灸适应证,有32种与疼痛有关。电针就是在传统针刺手法上发展起来的,它可以替代人做较长时间的持续运针,使用方便,刺激参数稳定,可以进行定量和重复性操作,能较客观地控制刺激量便于定量分析,因此,电针现已广泛应用于临床和实验研究中。不同的电针刺激参数会产生不同的镇痛效应,影响电针镇痛效果的因素主要有电针频率、电流强度、电压、波形、电针时间等,笔者就近年来有关电针刺激参数对镇痛效应的研究做如下综述。
1 频率
1.1 不同频率电针镇痛作用于不同的中枢部位
针刺引起的传入冲动通过穴位深部的感受器及神经末梢的兴奋传入脊髓后,主要交叉到对侧脊髓腹外侧束上行,通过激活高位中枢发放下行抑制冲动来实现镇痛效应[1]。韩济生等[2-3]研究发现低频和高频电针镇痛由不同的中枢部位整合,即低频电针镇痛的重要部位在下丘脑弓状核,而高频电针镇痛的关键部位在脑桥臂旁核。张露芬等[4]观察到不同电针参数对不同中枢水平的体感诱发电位有不同的作用特点,其规律性表现为,低频强电针对皮层及痛成分效应明显;低频弱电针对皮层下成分效应明显。熊克仁等[5]观察低频(2 Hz)和高频(128 Hz)电针刺激大鼠合谷穴对尾壳核头部各区一氧化氮合酶(NOS)表达的影响,发现这两种频率电针均可使尾壳核头部各区NOS表达增强,而高频电针上调尾壳核头部NOS表达更为显著。
1.2 不同频率电针镇痛的神经化学机制不同
电针的镇痛效应是由许多递质或调质共同参与下实现的。Han JS[6]很早就证实,低频(2 Hz)电针刺激脑啡肽和b-内啡肽的释放,作用于m及d受体而达到较为缓慢持久的镇痛效果;高频(100 Hz)电针能刺激强啡肽的释放,作用于k受体而实现即时镇痛,中频(15 Hz)电针能引起三种啡肽的释放产生协同镇痛效应。Huang C等[7]发现2 Hz电针能介导正常小鼠脑内m受体促进内吗啡肽释放,发挥镇痛作用,而100 Hz电针则不能。谢国玺等[8]研究在2 Hz、15 Hz、100 Hz等不同频率电针刺激引起的镇痛实验中,2 Hz电针刺激主要促进脊髓内甲硫脑啡肽释放,100 Hz电针刺激主要促进脊髓内强啡肽A释放,而15 Hz的电针镇痛似乎是由甲硫脑啡肽、强啡肽A和强啡肽B共同介导的。王洪蓓等[9]观察两种频率(5 Hz、100 Hz)电针均能明显升高急性佐剂性关节炎大鼠痛阈,两者的作用无明显差异;这两种频率电针也都能提高血浆环磷酸腺苷(cAMP)和环磷酸鸟苷(cGMP)含量,两者对血浆cGMP含量的升高作用非常显著,2 Hz电针引起脑啡肽和内啡呔释放,100 Hz电针则可引起强啡肽释放,以达镇痛效果。田津斌等[10]研究表明,特定频率(2 Hz、15 Hz、100 Hz)的外周刺激可选择性地引起大鼠脊髓灌流液中生长抑素(SOM)和降钙素基因相关肽(CGRP)释放的增强或抑制,2 Hz电针对CGRP释放的抑制及15 Hz和100 Hz电针对SOM释放的抑制均可能有利于相应频率的电针发挥其镇痛作用。谢翠微等[11]给大鼠脑室或脊髓蛛网膜下腔注射去甲肾上腺素(NE)的直接前体二羟基苯丝氨酸(DOPS)来加强NE的功能,或注射a、b受体阻断剂来削弱NE的功能,观察其对电针镇痛作用的影响,结果表明脑和脊髓中的NE在电针镇痛中起着截然不同的作用,脑内NE主要通过受体对抗电针镇痛,此外兼有较弱的通过b受体加强电针镇痛的作用,而脊髓内NE则是通过a受体来加强电针镇痛的作用。
1.3 不同频率电针镇痛的分子机制不同
不同频率电针能促进或抑制中枢不同部位基因表达。低、高频电针分别引起下丘脑弓状核和脑干臂旁核大量c-fos表达,低频电针镇痛主要由弓状核介导,高频电针镇痛主要由臂旁核介导[12]。郭惠夫等[13-14]研究电针后不同脑区即刻早期基因c-fos表达的变化发现2 Hz主要引起下丘脑的蛋白表达,而l00 Hz主要引起脑干的表达,其区别以弓状核和臂旁核更为典型。
1.4 不同频率电针镇痛耐受性不同
连续或多次反复电针后,电针的镇痛效应会逐渐下降甚至消失,产生“耐受”现象,不同频率电针的耐受性不同。赵飞跃等[15]观察了5 Hz、50 Hz、100 Hz电针对镇痛效果和耐受性产生的影响,结果发现,5 Hz组的针效出现晚,针效弱,维持时间短;而50 Hz和100 Hz组的针效出现早,针效强,维持时间长。高频电针耐受现象比低频组出现晚,程度轻。孙少丽等[16]给大鼠低频(2 Hz)和高频(100 Hz)电针的交叉耐受试验,认为2 Hz电针可能在脊髓中释放内源性的d激动剂引起镇痛,100 Hz电针可能在脊髓中释放内源性的k激动剂引起镇痛效应。王韵等[17]观察不同频率(2 Hz、100 Hz)电针耐受对k阿片受体mRNA转录的影响,结果表明,不同频率电针可能具有不同的中枢效应,如2 Hz电针在第3天、第6天可引起中脑导水管周围灰质内k受体mRNA显著降低,而100 Hz电针则无明显改变。多次电针则在大多数情况下抑制k受体mRNA的转录,提示内源性阿片肽大量释放也可引起阿片受体下调,这可能是电针耐受的机制之一。梁繁荣等[18]发现电针能提高佐剂性关节炎大鼠痛阈并能维持60 min以上,同时发现电针能提高下丘脑b-内啡肽和脑干5-HT含量并维持30 min以上,降低炎症局部5-HT和多巴胺含量并维持此效应30 min以上,降低炎症局部NE含量并维持此效应15 min以上,说明针刺对慢性痛的后效应存在。王俊英等[19]研究认为电针对慢性神经痛大鼠的累积性镇痛效应与下丘脑POMC mRNA表达的上调和海马孤啡肽前体mRNA表达的下调密切相关。
1.5 不同频率电针镇痛临床效果不同
临床上,不同频率电针镇痛效果有明显的病种差异性。肖胜平[20]观察不同频率电针(1 Hz、4 Hz、30 Hz)对腰椎间盘突出症的治疗效果,4 Hz时治疗效果最为理想。孟庆越等[21]观察电针的不同波形(连续波、疏密 波、断续波)及频率(4 Hz、30 Hz)对腰椎间盘突出症(腰突症)的效果,4 Hz的连续波镇痛效果较好,能够在短时间内明显减轻疼痛,30 Hz的连续波镇痛作用次之,但两者无明显差异。但是,王乐等[22]研究认为治疗颈源性头痛时,高频(85 Hz)较低频(5 Hz)具有更好的止痛效果。郭锦华等[23]认为电针治疗三叉神经痛时高频组(电针脉冲频率定在每分钟300次以上)电针疗效要显著优于低频组(电针脉冲频率定在每分钟150次)电针疗效。Han JS等[24]第一个报道了2 Hz和100 Hz经皮穴位的刺激(TENS)可以分别诱发来自人的前脑啡肽原和前强啡肽原的阿片肽的释放,2 Hz TENS可以引起患者脑脊液中脑啡肽大量释放,而100 Hz TENS可以引起强啡肽的释放,为临床电针镇痛提供了理论基础。
2 强度
针刺所兴奋的神经纤维种类包括Aa、Ab、Ad和C纤维这4类[25]。低强度电针(非伤害性刺激)主要兴奋Ab类和部分Ad类神经纤维传入,通过脊髓节段痛整合作用实现小范围的镇痛,主要作用在局部;而高强度电针(伤害性刺激)主要兴奋Ad特别是C类纤维传入,通过激活脑内中缝大核痛负反馈调节机制,发挥广泛性的镇痛作用[26-29]。王跃秀等[30]观察不同强度、不同频率的电针参数对大鼠脊髓神经元伤害性反应的影响,发现在相同时间及波宽的条件下,强电针选用低频(5 Hz)较好,而弱电针时以选用高频(50 Hz)为佳。王友京等[31]比较两种不同强度(3 V、6 V)和频率(10 Hz、200 Hz)电针镇痛的即时效应和后效应,观察到低频(10 Hz)电针比高频(200 Hz)电针,强电针(6 V)比弱电针(3 V)的即时镇痛效果较好,而高频电针(200 Hz)镇痛后效应优于低频电针(10 Hz),弱电针(3 V)优于强电针(6 V)。朱丽霞等[32]通过测定坐骨神经损伤大鼠和佐剂性关节炎大鼠基础痛阈和电针后即时痛阈的变化,比较研究了强电针(2~3 mA,50 Hz)和弱电针(<1 mA,50 Hz)的镇痛作用,及对痛觉过敏大鼠的治疗作用,结果显示强电针和弱电针都可以提高大鼠的痛阈,但在炎症侧强电针的镇痛效应比弱电针强。
3 波形
目前,大多数电针仪可供选择的波形有疏波、密波、断续波、疏密波等,不同的波形产生不同的镇痛效应。方剑乔等[33]等认为镇痛可选用疏密波或连续波。疏密波是疏波和密波轮流输出的组合波,可对感觉和运动神经产生即时和延迟抑制,发挥较强的镇痛效应及维持效应,且组织不易出现适应性反应,故常被用来针麻镇痛。连续波的操作则需在治疗过程中调整频率及掌握合理的时间给予疏密波的切换。左芳等[34]观察不同电针波形对颈椎病疼痛的治疗,发现疏密波组比连续波组疗效好。蒯乐等[35]探讨电针治疗佐剂性关节炎(AA)最佳适宜的脉冲波形参数,发现治疗后不同脉冲波形电针组痛阈高于模型组,声电波是电针治疗AA最佳适宜的脉冲波形。金弘等[36]通过观察不同波形电针对实验性急性痛风性关节炎大鼠的疗效,结果发现疏密波电针组能使急性痛风性关节炎大鼠滑膜内HSP-70蛋白表达显著增加。
4 时间
4.1 电针治疗持续时间对镇痛效果的影响
低频电针出现镇痛效应需有15 min的潜伏期,45 min左右达到高峰;超过45 min,虽仍能维持镇痛,但其镇痛作用呈减弱趋势[37]。如果把电针时间限定在30 min以内,则仅能发挥强啡肽的镇痛作用,不能发挥作为镇痛主体的脑啡肽和b-内啡肽的作用。叶建红等[38]也认为电针15 min时大鼠端脑环磷酸鸟苷(cGMP)含量降低,电针45 min脑干含量升高明显,电针30 min端脑cGMP含量显著降低而脑干含量略升高,且痛阈明显提高,针刺镇痛以30 min为宜。方剑乔等[33]等认为运用电针治疗各类急慢性痛症时,应把刺激时间设置在45 min左右。
4.2 电针治疗频次对镇痛效果的影响
王贺春等[39]观察四种电针时间间隔(每日1次、2日1次、3日1次、4日1次)治疗大鼠慢性神经源性痛的疗效。结果表明,3日1次的针刺频度疗效最好。杜俊英等[40]对电针治疗骨癌痛的参数进行了深入研究,发现在同一频率不同频次电针治疗后效应的研究中,治疗前期(治疗2 d、4 d)后24 h,每日治疗组痛阈高于隔日治疗组,治疗后期(治疗8 d、12 d、14 d)后24 h,隔日治疗组痛阈高于每日治疗组,认为急性疼痛适合每日电针治疗,慢性疼痛适合隔日电针治疗。刘俊岭等[41]结扎大鼠坐骨神经造成慢性压迫性损伤(CCI)疼痛模型,对比不同强度、不同频度电针的镇痛效应,发现低强度电针时,每日1次、隔2日1次和每周1次3种治疗频度比较,每日1次治疗的镇痛效果最好,而较高强度电针时,每日1次、每周1次治疗均有明显的镇痛效果,两者之间无显著性差异。王文靖等[42]以佐剂性关节炎大鼠作为炎症痛模型,分别以3 h、6 h、12 h、24 h作为电针治疗间隔时间,观察累加电针对炎症痛大鼠模型不同间隔时间的镇痛效果,连续治疗6 d后观测大鼠疼痛级别、痛阈、下丘脑前阿黑皮素和前脑啡肽原mRNA的表达,结果显示电针组的疼痛级别明显低于模型组,间隔24 h电针组的痛阈高于模型组,各电针组下丘脑前阿黑皮素和前脑啡肽原mRNA的表达均明显高于模型组,在不同电针治疗间隔时间中,以间隔24 h治疗更能明显降低炎症痛大鼠疼痛级别并提高痛阈,促进下丘脑前阿黑皮素和前脑啡肽原mRNA表达。
4.3 电针日节律对镇痛效应的影响
罗非等[43]观察低频(2 Hz)及高频(100 Hz)电针在日节律不同时间(分别在0:00、6:00、12:00或18:00电针)镇痛效应的变化规律,发现低频电针镇痛效应在18:00最差,而高频电针镇痛效应在0:00最好。徐蕾[44]通过痛阈筛选的192只SD大鼠,将动物随机分为24组,分别于8:00(ZT0)、12:00(ZT4)、16:00(ZT8)、20:00(ZT12)、24:00(ZT16)、4:00(ZT20)这6个时间点的电针在昼夜节律方面的相关特征,发现正常大鼠痛阈具有明显的昼夜节律,其峰值在16点左右,谷值在24点左右,即暗期痛阈较低,明期痛阈较高,电针对正常动物及创伤痛动物痛阈的昼夜节律均有影响。
5 总结和展望
电针参数是影响电针镇痛效应的重要因素,频率为2~100 Hz,固定频率及变频均有选用;刺激电流0.1~3 mA,刺激电压2~20 V,以2~3 V为多;留针时间5~45 min。即使是相同实验设计,电针参数的选择都未能统一,电针镇痛效果都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故近年来有学者提出了电针参数需量化的观点,不仅能为实验研究提供统一的、客观的标准,更能为临床应用选择最佳电针参数提供理论依据。
[1] 刘乡.大脑皮层和皮层下核团对中缝大核的调控及其在针刺镇痛中的作用[J].针刺研究,1996,21(1):4- 10.
[2] 韩济生,王强.低频和高频电针镇痛分别由下丘脑弓状核和桥脑臂旁核转递[J].针刺研究,1991,16(3-4): 181-183.
[3] 王强,毛利民,韩济生.下丘脑弓状核在低频电针镇痛中的作用[J].北京医科大学学报,1989,10(5):430.
[4] 张露芬,程金莲,严洁.电针对中枢不同水平体感诱发电位变化特点的观察[J].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2000, 23(6):43-45.
[5] 熊克仁,马同军,杨解人,等.不同频率电针对大鼠尾壳核头部一氧化氮合酶表达的影响[J].皖南医学院学报, 2001,20(3):157-159.
[6] Han JS. Acupuncture: neuropeptide release produced by electrical stimulation of different frequencies[J]., 2003,26(1):17-22.
[7] Huang C, Wang Y, Chang JK,. Endomorphin and mu-opioid receptors in mouse brain mediate the analgesic effect induced by 2 Hz but not 100 Hz electroacupuncture stimulation[J]., 2000, 294(3):159-162.
[8] 谢国玺,韩济生.不同频率的电针镇痛作用由脊髓内不同的内啡素介导[J].科学通报,1985,30(5):388.
[9] 王洪蓓,董晓彤,王双昆,等.不同频率电针对急性实验性关节炎大鼠痛阈及血浆环核苷酸和皮质醇含量的影响[J].中国针灸,1999,19(3):170-173.
[10] 田津斌,沈上,韩济生.电针频率对大鼠脊髓灌流液中SOM和CGRP含量的影响[J].生理学报,1998,50(1): 101-105.
[11] 谢翠微,汤健,韩济生.脑和脊髓中的去甲肾上腺素在大鼠电针镇痛中起不同的作用[J].科学通报,1981,26 (20):1279-1280.
[12] Han JS, Wang Q. Mobilization of specific neuropeptides by peripheral stimulation of identified frequencies[J]., 1992,(7):176-180.
[13] 郭惠夫,方圆,王晓民,等.不同频率电针激活大鼠中枢神经系统不同部位的Fos蛋白表达[J].针刺研究, 1994,19(3):52-54.
[14] 郭惠夫.低、高频电针诱导原癌基因c-fos/c-jun和阿片肽基因表达及其关系的比较研究[J].生理科学进展, 1996,27(2):135-138.
[15] 赵飞跃,江帆,朱丽霞.不同频率电针对镇痛效应和耐受现象产生的影响[J].中国针灸,1989,9(1):26-29.
[16] 孙少丽,韩济生.低频和高频电针镇痛由脊髓水平不同类型的阿片受体介导:交叉耐受试验[J].生理学报, 1989,(4):416-420.
[17] 王韵,王晓民,韩济生.不同频率电针耐受对k阿片受体mRNA转录的影响[J].北京医科大学学报,1998,30 (1):1-4.
[18] 梁繁荣,罗荣,刘雨星,等.电针镇痛后效应与炎症局部5-HT、NE、DA含量关系的实验研究[J].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2001,7(11):52-55.
[19] 王俊英,孟凡颖,陈淑萍,等.电针镇痛的累积效应与脑内孤啡肽前体和前阿黑皮素基因表达的关系[J].辽宁中医杂志,2011,38(3):445-449.
[20] 肖胜平.不同频率的电针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的疗效分析[J].中国医药指南,2013,11(20):283-284.
[21] 孟庆越,王学新.电针的不同波形及频率对腰椎间盘突出症的效应[J].中国临床康复,2002,6(16):2370, 2375.
[22] 王乐,焦杨.不同频率电针治疗颈源性头痛临床观察[J].河南中医,2012,32(4):449-450.
[23] 郭锦华,张滨农,朱志义,等.不同频率电针治疗三叉神经痛[J].中国针灸,2006,26(12):903.
[24] Han JS, Chen XH, Sun SL,. Effect of low- and high- frequency TENS on Met-enkephalin-Arg-Phe and dynorphin A immunoreactivity in human lumbar CSF[J]., 1991,47(3):295-298.
[25] 江澄川,赵志奇,蒋豪.疼痛的基础与临床[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上海医科大学出版社,2001.
[26] He X, Zhu B, Liu X,. The extensiveness and specificity of analgesia of electroacupuncture (EA) at different points on the nociceptive responses of neuron in spinal dorsal horn[J]., 1993,18(4):271- 275.
[27] Xu W, Liu X, Zhu B,. The analgesic extensiveness and specificity of EA at different points on nociceptive response of trigeminal convergent neurons (TCN)[J]., 1995,20(1):24-30.
[28] Xu WD, Liu X, Zhu B,. The extensiveness and specificity of effect of electroacupuncture at different acupoints on nociceptive response of convergent neurons in trigeminal nucleus caudalis[J]., 1995,(2): 48-56.
[29] 何晓玲,刘乡,朱兵,等.强电针穴位对背角神经元镇痛效应广泛性的中枢机制[J].生理学报,1995,47(6): 605-609.
[30] 王跃秀,袁斌,唐敬师.不同参数电针对大鼠脊髓背角神经元伤害感受性反应的影响[J].西安交通大学学报(医学),2003,24(6):531-534.
[31] 王友京,王双坤.不同强度和频率电针的镇痛效应[J].针刺研究,1993,18(1):44-47.
[32] 朱丽霞,李文武,吉长福,等.不同强度电针对痛觉异常治疗作用的比较[J].中国疼痛医学杂志,1996,2(1): 26-32.
[33] 方剑乔,包黎恩.论电针镇痛的临床应用规范及其依据[J].浙江中西医结合杂志,1994,4(3):40.
[34] 左芳,何芙蓉,尹淑英.不同波形电针对颈椎病所致疼痛的治疗效果[J].中国临床康复,2004,8(20):4093.
[35] 蒯乐,杨华元,刘堂义,等.不同脉冲波形电针对佐剂性关节炎大鼠的影响[J].中国针灸,2005,25(1):68-71.
[36] 金弘,刘婷婷,陈英华,等.电针的不同波形对实验性大鼠急性痛风性关节炎滑膜组织中HSP70表达的影响[J].针灸临床杂志,2012,28(7):64-66.
[37] 李忠仁.实验针灸学[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2003:166-241.
[38] 叶建红,刘永莉,孔庆玺.电针不同时段对大鼠中枢cAMP和cGMP含量的影响[J].广西中医学院学报, 2001,4(3):44-46.
[39] 王贺春,姚磊,万有,等.不同频度电针治疗大鼠慢性神经源性痛的疗效比较[J].针刺研究,2001,26(3):227- 228.
[40] 杜俊英,陈宜恬,吴赛飞,等.电针治疗大鼠骨癌痛镇痛后效应的参数筛选[J].中华中医药杂志,2014,29(5): 1454-1458.
[41] 刘俊岭,陈淑萍,高永辉,等.不同强度、不同频度电针对慢性痛大鼠镇痛作用的比较[J].针刺研究,2006,31 (5):280-285.
[42] 王文靖,赵仓焕,谢步霓,等.不同间隔时间电针对炎症痛大鼠下丘脑阿片肽基因表达的影响[J].针刺研究, 2006,31(3):131-135.
[43] 罗非,韩济生.大鼠不同频率电针镇痛效果随日周期及动情周期的变化[J].科学通报,1992,37(12):1128- 1130.
[44] 徐蕾.电针对创伤痛昼夜节律影响的研究[D].成都中医药大学,2009.
Summary of the Study on the Effect of Different Electroacupuncture Parameters on the Analgesic Effect
-1,-2,-2,2,-2.
1.,300450,; 2.,300193,
By sorting, summarizing and analyzing the relevant experimental and clinical studies, this article discussed the factors that influence the analgesic effect of electroacupuncture from the aspects of electroacupuncture frequency, current intensity, voltage, wave form, and treatment duration. It is found that electroacupuncture parameter is an important factor that influences the effect of electroacupuncture. The frequency range was 2-100 Hz and both fixed frequency and variable frequency were selected; the current intensity was 0-1-3 mA, and the voltage was 2-10 V but 2-3 V was predominant; the needle retaining duration was 5-45 min. It is also discovered that sometimes the electroacupuncture parameters were not unified even if it was in the same experiment design. Therefore, the electroacupuncture parameters need quantifying to provide a universal and objective standard for experimental studies, and to offer a theoretical evidence to select the optimal electroacupuncture parameters in clinical practice.
Electroacupuncture; Pain; Acupuncture analgesia; Review
1005-0957(2018)11-1331-05
R245
A
10.13460/j.issn.1005-0957.2018.11.1331
2018-05-18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基金项目(81303022)
付宏伟(1988—),女,住院医师,硕士,Email:fuhongwei189@163.com
阎丽娟(1981—),女,讲师,博士,Email:18749050@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