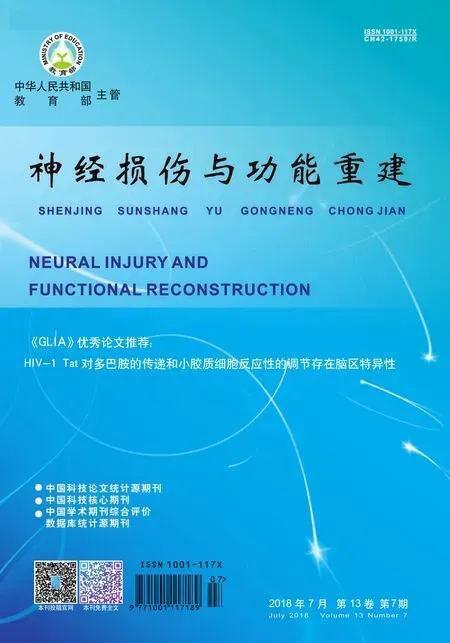创伤性颅脑损伤致阿尔茨海默病的研究进展
赵建伟,陈世文
作者单位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六人民医院神经外科上海200233
1 概述
创伤性颅脑损伤(traumatic brain injuries,TBI)的发生率在我国占全身创伤的第2位,目前达到每年100~200人/10万,其中交通事故是首位原因,颅脑外伤的死残率高居所有外伤的第1位[1]。对TBI的诊治,人们主要集中于急性期。但颅脑外伤可引起多种后遗症并能导致神经退行性疾病,据报道脑外伤与阿尔茨海默症(Alzheimer's disease,AD)的发生发展有关,但其机制仍不明确。
阿洛伊斯·阿尔茨海默在1906年首次报告现在以他名字命名的病例,记录了一位51岁的妇人奥古斯特·D的进行性痴呆症状[2]。此后,科学家们对AD的致病因素、临床分型、病理学、病理生理学进行了百余年的大规模研究,但其病因和发病机制迄今仍未完全阐明。很多研究表明,TBI是最强的AD的外在致病因素之一[3]。
2 TBI后AD的流行病学
1928年,美国新泽西病理学家Harrison Martland首次描述一种特殊类型的痴呆症状,经历反复TBI的拳击手会出现如震颤、运动减缓、语言障碍、思维混乱等表现,当时他称之为“Punch Drunk”[4]。此后,针对TBI后患者罹患痴呆进行了大量的流行病学研究,其中很多结果证实TBI和AD具有相关性。2000年,Plassman报道了一个由548例头部外伤史的实验组和1 228例正常人的对照组组成的队列,研究其罹患AD及其他类型痴呆的风险。结果表明,中重度脑外伤史是后期出现AD的重要危险因素[5]。2014年,瑞典的Nordström发表了一篇由811 622人组成的一项全国性队列研究,旨在探讨TBI与痴呆的关系,结果发现TBI与AD虽无显著相关性,但是TBI与其它类型痴呆(慢性创伤性脑损伤、额颞叶痴呆、帕金森病)有强相关性[6]。但也有些报道显示TBI与AD并无显著相关性[7-9],原因可能与回忆偏倚、随访时间过短、人群异质性等多种因素有关。这也提示TBI后神经退行性过程与TBI的严重程度、脑损伤部位和类型、个体基因易感性、基础健康状况、生活方式、生活环境等多方面因素有关。而TBI是造成包括AD在内的痴呆症状的最重要环境因素[10,11]。
3 TBI致AD的机制
AD是与年龄相关的常见的神经退行性病变,发病进程缓慢,早期常被误诊为正常的衰老,其典型的神经病理学特征是:大脑皮质弥散性萎缩、沟回增宽、脑室扩大、大量神经元丢失、神经元内出现神经纤维缠结(neurofibrillary tangle,NFT)和细胞间质出现β淀粉样蛋白(amyloid β-protein,Aβ)沉积,形成老年斑和淀粉样血管病。
急性脑损伤和AD有很多相似的病理学改变,比如Aβ沉积、tau蛋白磷酸化、轴突退化、突触损失、小胶质细胞增生[12,13]。神经炎症反应是介导急性脑损伤后继发性神经退行性病变的重要因素。TBI可引起神经细胞轴突损伤,而轴突-突触前损伤是导致AD发生的重要机制[14],TBI后轴突损伤可引起轴突球样变、肿胀、轴膜破坏从而引起轴浆运输损伤,继而出现神经细胞内淀粉样前体蛋白(amyloid precursor protein,APP)、衰老蛋白-1(Presenilin-1,PS-1)、β-分 泌 酶(B-site APP cleaving enzyme,BACE)聚集[12]。TBI还可诱发半胱氨酸天冬氨酸酶(caspase-3)表达,进一步引起细胞凋亡和APP产生,这些蛋白都是AD发生的关键蛋白,可诱发细胞内Aβ级联反应,促进tau蛋白磷酸化和NFT沉积。
3.1 TBI与Aβ
1984年,Glenner和Wong等首次从AD患者脑膜血管中分离得到一种淀粉类物质,其分子量为4 kD,约含39~43个氨基酸,由于其呈现β折叠而被命名为Aβ[15]。1985年,Masters和Beyreuther从老年斑中分离得到一种与Aβ分子量和氨基酸序列相同的蛋白质,从而证实老年斑的核心物质就是Aβ[16]。Aβ蛋白是APP经蛋白水解酶裂解后的产物,编码APP的基因位于第21对染色体,Aβ由APP经相关酶加工产生。其存在两种竞争的切割途径α分泌酶途径和β分泌酶途径[17]。BACE途径中APP依次由BACE和γ分泌酶切割产生Aβ42。α分泌酶途径不产生Aβ。PS-1为γ分泌酶的催化亚单位。Aβ42极易聚集,形成不溶性纤维,沉积为老年斑,导致神经细胞功能紊乱。Aβ沉积还能引发各种免疫炎症反应和神经毒性级联反应,形成瀑布效应,导致广泛的神经元变性。Aβ致病机理多样,其在形成可溶性Aβ寡聚体时即可具有神经毒性作用,且毒性作用最大[18],Aβ寡聚体是Aβ片层折叠过程中的一种过渡状态。研究证实,AD病情的严重程度与Aβ总量相关,但并非线性相关;但是与可溶性Aβ寡聚体呈线性相关[19]。Aβ的形成、沉积和降解贯穿AD的整个病理生理过程。Aβ假说是AD病因的主要假说之一。
在年轻TBI患者中,Aβ沉积在伤后2~4 h就可出现[20],TBI发生后立即死亡的不同年龄的患者中大约30%发现脑中Aβ沉积,研究者还发现TBI后轴突变性和轴突内Aβ沉积会持续多年,这提示TBI可诱发神经退行性疾病。免疫组化分析表明TBI后Aβ相关切割酶(包括PS-1和BACE)在受伤轴突中聚集[21]。Caspase-3是细胞凋亡过程中最主要的终末剪切酶,其过度激活可导致过度的细胞程序性死亡,Caspase-3过度激活在AD患者中常见,被认为在Aβ产生中起重要作用[22]。大鼠实验中,脑损伤后,Caspase-3阳性细胞增加[23]。APP小鼠经过控制性皮质撞击,使用Caspase抑制剂可降低Caspase-3介导的APP切割和急性Aβ的升高[24],Caspase升高Aβ的机制可能与其减少BACE降解有关,其机制还需进一步研究。减少Aβ的药物,如BACE抑制剂和γ-分泌酶抑制剂或许可用于TBI后的治疗。
3.2 TBI与tau蛋白
Tau蛋白是神经细胞中含量最高的微管相关蛋白,具有正常的生理功能。Tau蛋白形成微管束,对于形成轴突细胞骨架和细胞内蛋白的轴浆运输有重要作用。人类tau蛋白基因位于17号常染色体的长臂上,由单基因mRNA选择性剪切形成的,有15个外显子,外显子2,3和10可选择性剪接,得到六个亚型,主要在神经元内表达而少见于其他细胞。正常tau蛋白高度可溶。AD患者脑中tau蛋白过度磷酸化,称为异常磷酸化tau蛋白(p-tau)。P-tau形成成对的双螺旋纤维细丝(paired helical filament,PHF),最终在神经元或胶质细胞内形成神经纤维缠结(neurofibrillary tangles,NFTs)。P-tau蛋白不仅本身促微管组装活性低,还可与正常tau蛋白及其他大分子微管相关蛋白竞争结合,导致微管功能受损。AD患者脑中tau蛋白总量更多,但正常tau蛋白减少而p-tau蛋白大量增加。P-tau有两种构象,即顺式(cisP-tau)和反式(transP-tau)。TransP-tau是生理性的,可促进微管组装,而cisP-tau是病理性的,其不仅不与微管结合,反而可组装成PHF,导致进一步的tau蛋白病变[25]。
TBI发生后,微管tau蛋白裂解成30~50 kD的cleaved tau(c-tau)蛋白,随着损伤的轴突膜释放到脑脊液(cerebro-spinal fluid,CSF)中。研究表明,TBI后脑脊液中c-tau的含量上升1 000多倍[26]。CSF中c-tau含量增高提示TBI神经细胞微管损伤。
实验证实,TBI后的人类和小鼠组织中表达大量的cisP-tau蛋白。实验中,当小鼠经受TBI,神经元立即大量产生cisP-tau,扰乱轴突的微管网络和线粒体运输,并且可以传播至其他神经元,导致神经元凋亡[25]。Kondo等[25]发现了一种cis-tau蛋白抗体,在TBI小鼠中用此抗体能阻断顺式tau蛋白化,可阻止tau蛋白病进一步扩散,并且使许多TBI导致障碍的结构和功能恢复。因此,cisP-tau蛋白过表达是TBI发生后疾病进展的主要早期驱动因素,最终导致AD中的tau蛋白病。此顺式抗体有可能进一步开发用于检测和治疗TBI,阻止脑外伤后的神经退行性变。
3.3 TBI与神经炎症
近年来,神经炎症在AD发病过程中的作用逐渐受到重视。在AD患者与AD转基因动物模型中,神经胶质细胞和炎症因子周围的Aβ明显增加。同时研究表明,死亡的AD患者脑中抗炎分子减少[27]。流行病学证据也证实,神经炎症可能参与AD的发病过程:长期大剂量应用非甾体类抗炎药,可降低AD发病风险30%~60%[28]。神经胶质细胞增生、炎性因子活化等均可由Aβ异常沉积引起;Aβ还可激活胶质细胞释放促炎因子,而促炎因子又在神经胶质细胞、神经元和老年斑间相互诱导,诱发中枢神经系统炎症级联放大反应,进一步损伤神经元;炎症反应又能促进Aβ生成,形成炎症级联瀑布效应。
TBI发生后,脑内胶质细胞(小胶质细胞和星形胶质细胞)激活,发生免疫炎症反应[29]。同时,在剪切应力、压应力等外力打击的作用下,脑组织挫碎、血管结构损伤以及血脑屏障破坏,外周免疫细胞进入脑实质内也参与神经炎症的过程[30]。在TBI急性期,炎症反应可发挥保护作用,将急性损伤局灶化并参与神经元的修复。但如果炎症急性期未能充分消散,将会形成AD中常见的难以控制的慢性炎症,并可长期存在。此时胶质细胞的激活通常会加强神经元的氧化应激作用,并且推动脑内异常蛋白的扩散,导致神经元功能障碍进而产生退行性变[31]。
抗菌肽是具有抗菌作用的多肽,是人体天然免疫的重要组成部分。抗菌肽不仅有抗微生物活性,还具有许多其他生物学功能,如调节炎症反应、调节免疫、调控凋亡以及参与组织修复等。Kumar等[32]研究证实,在小鼠、线虫和培养细胞的AD模型中,Aβ表达可抵抗真菌和细菌感染。Aβ寡聚体具有类似抗菌肽活性,其抗菌活性与LL-37(人类抗菌肽)相似,在先天免疫中具有保护作用[33]。反过来,感染也会导致Aβ升高,过量Aβ沉积促进AD的发生。Aβ起到保护与损伤双重作用。需要进一步的研究证实,是否与炎症反应类似,TBI后急性期脑内Aβ的升高,对于外伤的免疫调节和组织修复起到有益作用。
研究者对如何减少神经系统慢性炎症已经进行了很多实验。代谢型谷氨酸受体(metabotropic glutamate receptors,mGluRs)的亚型mGluR5与小胶质细胞激活密切相关。激活mGluR5后磷脂酶C被激活,进一步激活MAPK及其下游信号通路,从而影响细胞的生理功能[34]。炎症刺激会导致mGluR5表达减少,激活mGluR5可以抑制小胶质细胞所诱导的细胞炎症[35]。2-氯-5-对羟基苯甘氨酸[(RS)-2-chloro-5-hydroxyphenylglycine,CHPG]是mGluR5的特异性激动剂。局灶性脑损伤1月的小鼠在给予CHPG后,可减轻神经炎症,保护大脑白质,改善神经系统的恢复,4月时可发现神经退行性变减轻[36]。类似的抗炎治疗如对液压损伤大鼠使用磷酸二酯酶抑制剂异丁司特6月后,可降低胶质细胞的增生并减少大鼠焦虑样行为[37]。
4 存在问题与展望
目前对于TBI后大脑具体的病理生理变化及其机制还不甚了解。国内外对TBI尤其是轻型TBI、慢性创伤性脑损伤(chronic traumatic encephalopathy,CTE)后致AD痴呆普遍认识不足。虽然急性脑外伤和AD有许多相似的病理学特征,但是TBI后大脑Aβ的产生位置与分布与传统AD患者并不相同。这提示AD相关的神经病理学理论有助于了解TBI后出现AD类型痴呆的机制。Aβ寡聚体的产生对于脑外伤急性期大脑是否也起到保护作用值得进一步研究。TBI后脑内即出现Aβ沉淀、CSF中出现大量tau蛋白,但许多疾病都有类似的病理变化,研究其具有特异性与敏感性的生物标志物对于判断患者TBI后AD具有重要意义。最近的流行病学及动物试验均提示神经炎症在AD发生发展中起重要作用[38],但哪些特异性炎症基因和通路可能导致TBI后AD的发生尚不清楚。TBI后AD与其他类型的神经退行性疾病存在相似的病理生理变化[10],理解TBI后出现AD的机制可以帮助我们更深入地了解其他神经退行性疾病的病理生理过程,对于衰老机制的研究也会有所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