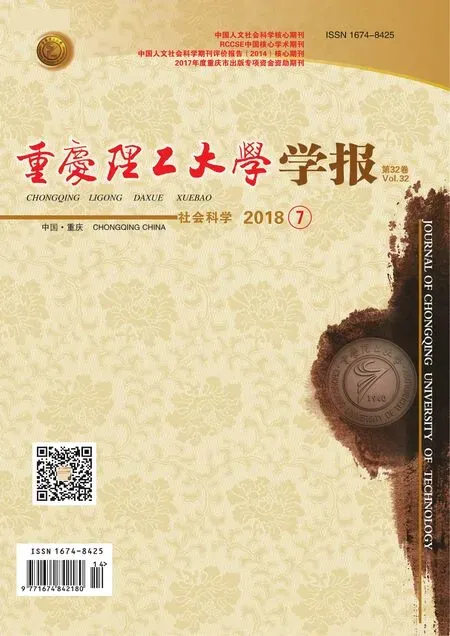韩非子的社会语言学思想
杨庆云
(北京师范大学 外文学院, 北京 100875)
一、引言
战国末期,合纵连横盛行百余年之久,当时的知识分子争相以自己的学术游说当权者,或建功立业,或博取豪名,或标榜学识,一时间说者纷纷、游者扰扰,鱼龙混杂。作为礼法思想的传承者,不甘寂寞的游说者,韩非子总结了当时的游说经验与说话技巧,成为先秦诸子中最为卓越的游说语言的研究者。《史记·老庄申韩列传》载:“韩非者,韩之诸公子也。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其归本于黄老。非为人口吃,不能道说,而善著书。”[1]2146在现存的韩非子遗著中,有游说秦王的《初见秦》《存韩》与《难言》,有总结游说经验的《说难》,有为应变游说状况或阐发游说思想而准备的语言资料,如《说林》《储说》等。这些资料十分丰富,总计有数百余则,其中蕴含着大量的社会语言学思想。
韩非子在《说难》中明确指出:“凡说之难,非吾知之有以说之之难也;又非吾辩之能明吾意之难也;又非吾敢横失而能尽之难也。”[2]60在韩非子看来,游说君王能否取得成功,不在于游说者的学识是否渊博,也不在于游说者是否拥有娴熟的口才,更无关于游说者是否有敢于直言的勇气。他从言者个体之外另找原因,从语言之外探求线索。他给出的结论是:“凡说之难,在知所说之心,可以吾说当之。”[2]60所谓“在知所说之心”,即从言语交际的对方寻找原因,而了解对方的心理,则离不开对语言的社会本质以及说者与听者所存在的社会关系及社会地位的分析与考量。由此,韩非子对游说的研究已经触破了语言学的藩篱,闯入了社会语言学的神坛。他独创了“说”体,用寓意深刻的历史典故、寓言故事阐释了“语言”和“言语”的区别。其观点与现代语言学奠基人索绪尔关于“语言”和“言语”的区分不谋而合。而且,他对语言的社会身份特征也有非常清晰的认识。他看到语言除了叙述事实,还传递着交际双方的“权势量”和“共聚量”等社会信息,是人们建构人际关系的重要媒介。同时,他的“在知所说之心”也证明他的语境观超越了语言内部的界限,扩展到了与语言相关的外部世界,这些观点都与现代语言学对语言和社会的研究非常契合。
二、“语言”与“言语”的辩析
现代语言学肇端于西方文化传统与学术脉络。早在古希腊时期,“语言”与“言语”大概就已经萌出了区别。逻各斯认为语言是“用一个单独的组织结构同时解释了人的言语和人的理性”[3]210,对语言和言语作出区别理解。此后,公元前100年左右的 Varro又提出语言的“个体自由”和“集体统一”的概念。他首次尝试并分解出了语言的个体性和集体性的矛盾与统一,为现代语言学家索绪尔区分语言和言语奠定了历史基础。
现代语言学奠基人索绪尔在1916年出版了《语言学教程》,其中对“语言”(langue)和“言语”(parole)的区分被公认为是语言学研究的里程碑。索绪尔认为:“不能把语言和言语混为一谈,语言只是言语活动的一个确定的部分,而且当然是主要的部分。它既是言语机能的社会产物,又是社会集团为了使人有可能行使这一机能所采用的一整套必不可少的规约。”[4]30这种语言系统同一切社会惯例一样,是一切社会成员共同遵守的、约定俗成的社会制度。此外,索绪尔又强调:“执行永远不是由集体,而是由个人进行的。个人永远是它的主人,我们管它叫言语。”[5]35对索绪尔来说,“言语”是“个人的意志和智能的行为”。索绪尔把社会性看作是语言的内在特性之一,是从大量的无序杂乱的言语片段中抽象概括和提炼出来的语言系统的各种规律。与语言相反,言语是指某个人说话的行为,是具体的,每个人说话的选词造句、发音方法以及语法句法都各不相同。因此,“言语”是以说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个人活动,所以它是个性化的,受说话人自身的社会、文化、语言环境制约的,它不能被群体同时共同使用,只能是个人的随机行为。然而,言语想要被人理解,又必须以语言作为基础。所以说,“语言”与“言语”是一对相辅相成、紧密联系的矛盾统一体。
西学东渐百余年之后,中国传统文脉逐渐复兴。关于“语言”与“言语”的辩析,早在两千多年前诸子百家争鸣时期,就已经有相当深入的研究与论述。荀子用“名无固宜,约之以命”潦潦八字破解了语言的社会本质,解释了语言从无到有遵循的任意性原则,又解释了语言强制性的根源在于“约之以命”的社会性,同时也诠释了“名可名,非常名”的语言发展动因[6]。此后,其学生韩非子因游说诸侯历尽艰难险阻,虽因游说未被采纳而身陷囹圄,但他对“语言”和“言语”的深刻理解却留存于《说难》《难言》《说林》及《储说》诸篇。《外储说左上》有“郑人得轭”一则故事:“郑县人有得车轭者,而不知其名,问人曰:‘此何种也?’对曰:‘此车轭也。’俄又复得一,问人曰:‘此是何种也?’对曰:‘此车轭也。’问者大怒曰:‘曩者曰车轭,今又曰车轭,是何众也?此女欺我也!’遂与之斗。”[2]207在此则故事中,“车轭”是套车时驾在牲口脖子上的器具的通用名称。而当郑人知道这个器具的名称为“车轭”时,便以为车轭是这个器物的专属名称。所以当他又发现一个被告知叫做“车轭”的东西时,则大为恼火,认为别人在欺骗他。我们对这个故事仔细分析会发现,故事中郑人和告知者的两种“车轭”造成的困境正好展示了“语言”和“言语”的区分。告知者的“车轭”是抽象意义的概念集合,也可以理解为这里的“语言”,它存在于每个社会成员的大脑之中。这个“车轭”无论由哪个社会成员以有声语言的形式说出来,它的本质并没有发生变化,仍然是表示对具体事物高度抽象概括后的概念意义。郑人指物提问,对方两次的回答都是“车轭”。在郑人的头脑中,“车轭”这个语音形式与其所对应的具体事物是一一对应的关系,第一次已经出现了“车轭”,以后就不应该再有“车轭”出现。但他却不知道“车轭”这个名称可以指代所有具备“车轭”性质的一类器具。也就是说,告知者脑中的“车轭”属于“语言”,而说出来的有声语言“车轭”则是他脑中这个概念的言语形式,也就是每个人说话时产生的形式各异的“言语”,可以是男性发出的语音,也可以是女性发出的语音,可以是含混的也可以是清晰的语音。正如索绪尔所说:“语言以许多储存于每个人脑子里的印迹的形式存在于集体中,有点像把同样的词典分发给每个人使用。所以,语言是每个人都具有的东西,同时对任何人又都是共同的,而且是在储存人的意志之外的。语言的这种存在方式可表以如下的公式:1+1+1+1+……=1…(集体模型)。”[9]41正是因为郑人无法真正理解“语言”和“言语”的本质区别,后来才会有“曩者曰车轭,今又曰车轭,是何众也”(先前说是车轭,现在又说是车轭,车轭怎么这么多呢)这样的疑问,也才误以为自己被人愚弄、欺骗。
三、韩非子的语言身份观
马克思认为,身份是指“人的出身、地位和资格,是人在一定社会关系中的地位”[6]18。 在一定社会关系中,身份是社会成员的社会属性标识和社会分工的标识,是人的一种社会归属,是确定人们社会地位高低、权利大小、义务多少的根本标准。从本质来看,身份确定了人与人之间亲疏、尊卑和贵贱,是人与人之间差别的总根源。可见,身份的本质是社会关系,个体的出身群体、政治与经济或其他地位,以及其在群体中所获取的某种资格,都是个体在社会群体中的社会关系,所以身份的社会性是永恒的,所有的身份都是“社会身份”。不同身份的人一旦进入社会,就会通过语言表达来建立和发展他们的人际关系,并在言语互动中相互构建身份的认同或排斥,语言选择则是社会身份建构的媒介。
语言除了叙述事实,还传递着交际双方的权势关系、亲疏关系等社会信息,由此促使人们保持或建构交际双方的人际关系,现代的功能语法称之为语言的人际功能[7]343。“权势量”(power)和“共聚量”(solidarity)则是人际关系中最为重要的概念,也是社会语言学中的两个重要概念,是1960 年社会学家Brown与Gilman首次提出来的。Brown等认为:“权势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行为进行控制的能力,是至少两人之间由于在同一领域不可能都有权势的情况下产生的不对等关系。”[8]“共聚”指人们之间的社会距离:包括共同经历,诸如宗教、性别、年龄、原籍、种族、职业、兴趣等的共同社会特征,表示友好的愿望等[8]。“权势量”标记着等级框架中交际参与者之间的社会地位距离或垂直距离。“共聚量”体现的是交际参与者之间的社会距离和交际双方的心理距离,相对亲密还是疏远。正确把握权势和亲疏关系,准确定位社会身份有利于实现交际目的,达到理想的交际效果。
战国晚期,部分诸侯国已经陆续出现了后来的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雏形,封建阶层开始孕育并初步显现出来。孔子提出的著名论断“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背后实际上是一整套封建的社会政治身份制度。君、臣、父、子这些社会身份在封建制度中都有明确的位置、权利、义务和行为规范。荀子提倡“分别制名以指实”,形成一套严格的封建等级制度,为的是达到“明贵贱”“辨同异”的目的。“明贵贱”实际上是区分尊卑贵贱,把语言作为“明贵贱”“治天下”的手段,强调语言在建立社会秩序中的政治功能[9]。韩非子生活在封建等级制度酝酿兴起的历史转折时期,他继承并发扬了孔子和荀子思想,认为语言交际的主体不是单一的独立体,而是具有不同身份的言者与听者。《难二》有云:“辨在言者,说在听者,言非听者也。”[13]279他认为言与听二者身份是不一样的,言语表达是否清晰明了应取决于说话者,而被游说者是否欣然倾听则取决于听话者的喜好。所以,在韩非子看来,语言交际是由不同身份的主体——言者与听者所共同构成的行为互动。
游说者与听者是何关系、具有何种不同的身份?游说者不是闲话者,不是表演者,更不是训教者,他是通过言语劝诱当权者而获取他授予的权利、财富与地位。所以,韩非子认为言者与听者存在着社会地位的巨大差别,这是作为游说者所首要考虑的。不同的地位,尤其是不平等的地位,且涉及有所求与有所予的双方相竞的差别,就会导致《难言》中所列举的情形发生:“言顺比华泽,洋洋纚纚然,则见以为华而不实;敦厚恭祗,鲠固慎完,则见以为拙而不伦;多言繁称,连类比物,则见以为虚而无用;总微说约,径省而不饰,则见以为刿而不辩;激急亲近,探知人情,则见以为僭而不让;闳大广博,妙远不测,则见以为夸而无用……故度量虽正,未必听也;义理虽全,未必用也。大王若以此不信,则小者以为毁訾徘谤,大者患惑灾害,死亡及其身。”[2]14
在《初见秦》《存韩》和《难言》等篇目中,韩非子都以“臣”的身份自称,向远在朝堂之上的君王进言献策。《初见秦》开篇中写道:“臣闻不知而言,不智;知而不言,不忠。为人臣不忠,当死;言而不当,亦当死。虽然,臣愿悉言所闻,唯大王裁其罪。”[2]1《难言》中也提述到“故度量虽正,未必听也;义理虽全,未必用也。大王若以此不信,则小者以为毁誉徘谤,大者患惑灾害死亡及其身”。这些言语都显示出韩非子尊君卑臣的权势观念以及对言语交际双方这种既定的不平等身份的认识。在这种权势关系中,被游说者是高高在上、掌握生杀大权的当政君王,进谏的臣子不可以随心所欲地畅所欲言,言者与听者的特殊身份就决定了进谏者必须消除君王的种种疑虑。即便如此,韩非子也没能成功地游说秦王,最终却死在了监狱中。当然,韩非子也不孤独,他在《难言》中也列示了因为游说而不能消除被游说者的疑虑而招惹祸患的先贤:文王被囚、鬼侯腊、翼候灸、比干剖心、梅伯醢,凡此种种,不胜枚举。
韩非子不仅论述了权势身份关系对游说的影响,还用很多故事阐释了共聚身份关系对言语交际成功与否的决定作用。他认为如果可以或被迫改变上述身份,且与听者建立良好的私交,取得信任,“周泽既渥,深计而不疑,引征而不罪,则明割利害以致其功,直指是非以饰其身,以此相持,此说之成也”[2]64,这样的言者就可以取得游说的成功。例如:“上古有汤,至圣也。伊尹,至智也。夫至智说至圣,然且七十说而不受,身执鼎俎,为庖宰,昵近习亲,而汤乃仅知其贤而用之。故曰:以至智说至圣,未必至而见受,伊尹说汤是也。”[2]1由此可见,谋权求财博取功名的,无论说得多么动人,都不会被信任而接受,而一个与功名利禄绝尘无干的厨师,其特有的身份就决定了其谏说是没有个人企图与私利的,因而君王是乐意听取并接受的。所以,在韩非子看来,如果不象伊尹、百里奚那样,降低自己的身份为厨师、为奴仆,是不可能达到“深计而不疑,引争而不罪”的信任程度的,其说辞虽好却是不可能被听用的。因此,身份强于说辞。
为了强化语言的社会身份,韩非子在《说难》篇结尾处又耗篇幅列举了两则故事。乍看起来,这两则故事与前文游说君王无关,但其阐发的言语者不同社会身份及或同一人社会身份转变后,相同言语或行为的不同社会后果,却恰恰揭示了社会身份对于语言交际的深刻影响。
其一:宋有富人,天雨墙坏,其子曰:“不筑,必将有盗。”其邻人之父亦云。暮而果大亡其财。其家甚智其子,而疑邻人之父。此二人说者皆当矣,厚者为戮,薄者见疑,则非知之难也,处之则难也![2]15
此例阐发了不同主体的同一言语,但因与听者的社会关系不一样,导致的后果却截然相反:与其关系深厚的“其子”,所言则被视为戮力同心,而与其关系浅薄的“邻父”,所言就被怀疑。可见,言语同,身份别,则意义迥异。
其二:昔者,弥子瑕有宠于卫君。卫国之法:窃驾君车者,罪刖。弥子瑕母病,人闻,有夜告弥子,弥子矫驾君车以出。君闻而贤之曰:“孝哉!为母之故,忘其犯刖罪。”异日与君游于果园,食桃而甘,不尽,以其半啗君。君曰:“爱我哉!忘其口味,以啗寡人。”及弥子色衰爱驰,得罪于君,君曰:“是故尝矫驾吾车,又尝啗我以余桃。”故弥子之行,未变于初也,而以前之所见贤,而后或罪者,爱憎之变也。故有爱于王,则智当而加亲,有憎于王,则智当见罪而当疏。[2]65-66
韩非子借此则故事阐明:虽针对同一事件,但因“色衰爱驰”的变化,导致弥子瑕由爱妾蜕变为弃妇的身份变异;而身份的变化,使得卫君的态度由爱变憎,由前称贤以至后降罪。共聚身份关系变化使得相同的言语和相同的事件却有了截然不同的理解:亲则爱,言则美;疏则憎,言则罪。
四、韩非子的语境观
所谓语境就是言语的环境,它对于言语的理解,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意义。在西方,公元前4世纪,希腊亚里士多德就曾注意到语境对语义理解的重要性,提出了一词多义的理解需要依赖其出现的不同环境的观点。19世纪初,美国语言哲学家皮尔士注意到“你、我、他”在不同条件下,其所指代的内容是不同的,识别它们需要依赖言语环境。文献记载的普遍观点认为,首次提出语境这一概念的是波兰人类学家Malinowski。他认为,交际中的话语与其所发生的语言环境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只有在“文化语境”和“情景语境”中才能对一段话的意义做出评价[10]306-307。
在中华古典文化中,虽没有“语境”这一术语,但语境对话语理解的重要作用却早为人所识。《诗·周南·关雎》所言“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并非字面上的爱情诗。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帛书《老子甲卷后本古佚书》认为:《关雎》是以思“色”喻思“礼”,比喻思求具有仁、义、礼、智、信的贤者,之后很多史学家和文学家都将此诗注释为求贤、迎贤、举贤的诗,其根据就是当时的历史文化语境[11]。现代修辞学家陈望道先生指出:“凡是成功的修辞,必定能够适合内容复杂的题旨,内容复杂的情境,极尽语言文字的一切可能性,使人觉得无可移易。”[12]338对此,孔子多次强调“慎言”,如《论语·学而》中的“君子……敏于事而慎于言”,《论语·里仁》中的“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论语·为政》中的“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等等。孔子的“慎言”并非不言,更非少言,其强调的是言谈辩论均需恰当得体,即“时然后言,人不厌其言”,根据交谈目的选择恰当的时机、场合、交谈对象,才能达到言谈目的。荀子非常赞同孔子的观点,指出“言有招祸也,行有招辱也。君子慎其所立乎”[13],强调谨言慎行是君子修身的一项重要内容。同时,荀子继承孔子立言修辞的“言必有中”以及“时然后言”和“择人而言”等主张,提出“言而当”,继而又提出“言必当理”前提下的“与时迁徙,与世偃仰”。韩非子生活于诸侯割据的战国晚期,对战乱频仍、动荡不安、民不聊生的社会状况体会更深。在这样一个人人自危的社会政治环境中,谨言慎行尚不足以保全自己,更遑论其他。而且韩非子自身口吃,多次进言进谏都不被采用,无法施展自己的政治才华又深感“以智说愚必不听”的艰难现状。因此,韩非子在《难言》《说难》中详细论述了自己关于谏说技巧的看法,并详细阐释了语言的表达和语境选择的重要性。他在《问辩》中说:“言无二贵,法不两适,故言行而不轨于法令者必禁。法令之不足备者,则臣慎言以尽其事,主采其言而责其实。”[2]301作为孔子的后学,他在《韩非子难三》中记载了一则孔子娴熟运用语境游说诸侯的故事,并对语境给予了解释:
叶公子高问政于仲尼,仲尼曰:“政在悦近而来远。”哀公问政于仲尼,仲尼曰:“政在选贤。”齐景公问政于仲尼,仲尼曰:“政在节财。”三公出,子贡问曰:“三公问夫子政,一也,夫子对之不同,何也?”仲尼曰:“叶都大而国小,民有背心,故曰政在悦近而来远;鲁哀公有大臣三人,外障距诸侯四邻之士,内比周而以愚其君,使宗庙不扫除、社稷不血食者,必是三臣也,故曰在选贤;齐景公筑雍门为路寝,一朝而以三百乘之家赐者三,故曰政在节财。”[2]284-285
针对三公的同一问题——如何为政,孔子却给出了 “政在悦近而来远”“政在选贤”和 “政在节财”三种不同的回答。问政人所处国家国情不同、民风各异,治政方略当然不同,恰与韩非子的“言会众端,必揆之以地,谋之以天,验之以物,参之以人,四征者符,乃可以观矣”同理。四征即地利、天时、物理、人情皆合。对于言论,韩非子认为要汇合各方面的情况,根据地利加以衡量,参照天时加以思考,运用物理加以验证,适应人情加以分析。这四方面的情况都符合了,然后是非善恶可断。康有为对此的论述是“言与不言皆无所失……失人则失机,失言则偾事,故不可不择人而言”。“择人而言”,涵括了言说对象、言说时机、言说地点、言说场合等多种因素[14]231。 可见韩非子对言语意义的使用和追问不是停留在字形、字面上,而是与言语使用的交际双方、社会政治环境以及具体的物理情景语境相校验,看是否得恰。韩非子的语境观超越了语言内部的界限,使语境包含了与语言相关的外部世界的特征。这与现代语言学对语境的研究不谋而合。对语境做出言语内部因素与外部因素区分的伦敦学派Firth指出:“人们的话语不能脱离它在其中起作用的那个社会复合体,每一段话都应该认为有其发生的背景,都应该与某种一般化的情境上下文中的典型参与者联系起来加以研究。”[15]227
在韩非子看来,语境是言语交际成功非常重要的因素。他在《喻老》篇中描绘了楚庄王一鸣惊人的故事:
楚庄王莅政三年,无令发,无政为也。右司马御座,而与王隐,曰“有鸟止南方之阜,三年不翅,不飞不鸣,嘿然无声,此为何名?”王曰:“三年不翅,将以长羽翼;不飞不鸣,将以观民则。虽无飞,飞必冲天;虽无鸣,鸣必惊人。”[2]123
这段对话,如果只从字面看,无从理解。Hymes认为:“要理解语境中的语言,其关键是从语境入手,而不是从语言入手。”[16]57听者楚庄王借助双方互明的历史背景语境已经辨识出右司马是对其莅政三年而无令发、无政为的责难,于是仍以鸟为题回答说“虽无鸣,鸣必惊人”,借以展示其政治抱负。语境知识将分属于两个看似不相干概念域的“鸟”与“治政”联系起来,使借鸟而论政的话语交际得以成功。可见,韩非子对话语理解与语境高粘合关系的感悟与西方最早提出“语境原则”(context principle)的弗雷格(Frege)关于语境的理解不谋而合。弗雷格认为:“不能孤立地追问一个语词的意义,要在一个命题的语境中询问词的意义。”[17]77-78
而且,在韩非子看来,语境的识别并非是静止的,是可以在相互言语行为中重新构建的,因而是动态的。《说林上》记载了一则“温人之周”的故事:
温人之周,周不纳客。问之曰:“客耶?”对曰:“主人。”问其巷,不知也,吏因囚之。君使人问之曰:“子非周人也,而自谓非客,何也?”对曰:“臣少也诵诗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今君天子,则我天子之臣也。岂有为人之臣,而又为客哉!故曰主人也。”君使出之。[2]128
在此故事中,因为周国不接纳外来人,所以温人否认自己是来客的身份而自称是主人,结果在盘问中因说不清里巷地址而被认为是说谎,最终被囚禁起来。声称自己是周人,则需具备知晓周国里巷地址情况而作为其被认可的语境,否则其言语就是不恰当。但当周国之君派人审问时,这个温人却依托《诗经》中“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而重构出新的语境,将周国追溯为周朝,将周国君比作周天子,则普天下尽为周人。现代语言学家认为语境并不是由交际参与者事先给定的,而是由交际双方在交际过程中共同构建的,Firth把这种共同构建的过程叫做“语境化”(contextualization)[15],韩非子早在 2 000多年前就能用故事阐释语境的动态性,实属难得。
五、结语
作为一部诞生于2 000多年前的思想名著,《韩非子》既蕴含着作者广博的政治哲学思想精髓,也展露出作者对社会语言学的深邃认知和理解。韩非子独创的“说”体和寓意深刻的历史典故、寓言故事,揭示了“语言”和“言语”的区别、语言的社会身份性以及语境的静态性和动态性,这些语言观与现代语言学研究不谋而合。尽管司马迁在《史记》中评价他是“知说之难,为《说难》书甚具,终死于秦,不能自脱”[1]2146,但在传末《太史公曰》又再次感慨道:“余独悲韩子为《说难》而不能自脱耳”,充分肯定了韩非子“说”体中所展示的高超的语言艺术和对交际话语的深刻思考。他的语言观为中国古典语言学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是中国社会语言学研究的启蒙经典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