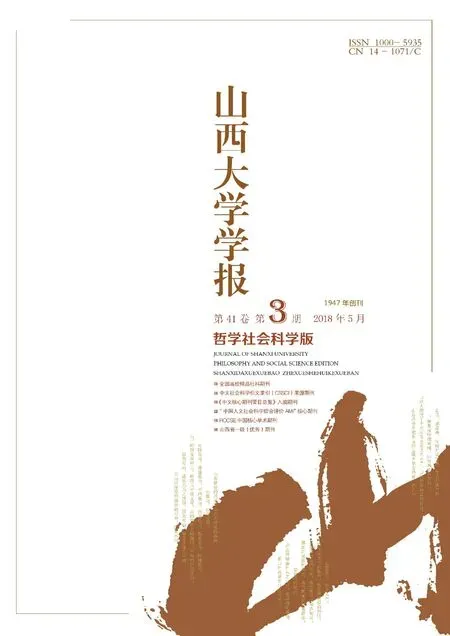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身份认同考辨
董琦琦
(1.中国社会科学院 外国文学研究所,北京 100732;2.北京联合大学 师范学院中文系,北京 100011)
“生态学”作为科学术语之一,由德国生物学家恩斯特·海克尔(Ernst Haeckel)于1866年在《普通生物形态学》一书中提出,旨在研究生物体和周围环境及生物体之间的关系。20世纪中期以来,工业化影响尚未消退,后工业时代接踵而至,自然环境生态和人类精神生态都面临危机挑战。在此背景下,一方面,生态学创立的生态思想基于自身内部的强大包容力和外部延展性被广泛借鉴到其他学科;另一方面,生态持续恶化,时不我待的危机意识促使各个学科积极寻找外部资源充实壮大其解决问题的能力。生态学与其他学科知识的交叉融合于是成为20世纪后半叶的重要事件之一,生态哲学、生态美学、生态文艺学、生态人类学、生态社会学、生态心理学、生态伦理学、生态经济学等一系列以生态学为中心的跨学科建设蔚然壮观。顺应时代潮流,生态学与马克思主义亦开启了深度对话与交流,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作为其交叉融合的标志性产物,将新兴知识的践行与经典的创新转化有机关联,在应对当代生态危机和身份认同危机方面作出重要突破,为现实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借鉴与参照。
一 知识谱系
在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产生的历史前提主要有两个:一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愈演愈烈的全球自然环境危机及由此引发的绿色运动,凸显了自然环境之于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极限问题;二是进入后工业时代,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同时引发人类自身危机,消费异化的见出和普及便是突出表征。在上述条件的共同作用下,反思自然与人类(社会)关系的呼声愈发高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应运而生。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自诞生之日起,便以生态关怀为己任,在揭示生态危机根源,寻找解决路径方面不断推陈出新。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作为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活跃生长点,努力将马克思主义与生态学结合起来,在传统马克思主义日渐式微,甚至备受质疑的情况下,肩负起为马克思主义作辩护的历史使命,创造性地从生态学维度挖掘并强化了马克思主义与当下现实的适应性。其理论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两点:一是针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态危机予以批判,并就危机根源进行诊断;二是提出生态社会理想,有关生态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设计及实施方案的拟定大抵属于此类。
20世纪末叶,生态危机持续升级,蔓延全球,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凭借问题诊断的切实性,赢得世界各国的关注与重视,并逐步在空间格局上形成了三大知识谱系:
一是以安德烈·高兹(Andre Gorz)、乔纳森·休斯(Jonathan Hughes)、泰德·本顿(Tedd Benton)、戴维·佩珀(David Pepper)、瑞尼尔·格伦德曼(Reiner Grundmann)为代表的欧洲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传统。欧洲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突出贡献在于将以批判性为特征的欧洲马克思主义与生态政治相结合,继承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唯物主义基础的同时,创造性地运用“经济理性”范畴解读资本主义社会的运行方式,解放了关于社会主义的生态想象。
二是以本·阿格尔(Ben Agger)、约翰·贝拉米·福斯特(John Bellamy Foster)、詹姆斯·奥康纳(James O’Connor)、保罗·伯克特(Paul Burkett)、约洱·克沃尔(Erhai Kvaal)为代表的北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传统。北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通过对传统的马克思主义与批判的马克思主义偏见的扬弃,实现了自然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有机融合。
三是以中国和日本为代表的亚洲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传统。亚洲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是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与亚洲本土文化联姻的产物,侧重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区域适应性。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在我国的传播与接受自此获得实质性进展,十八大报告之于生态文明的系统阐释充分体现了中国化的理论拓展与实践指向。继2012年“美丽中国”作为执政理念被首次提出以来,2017年10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进一步强调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设美丽中国的重要性及必要性。
二 学术争鸣
20世纪90年代,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在近30年的时间里,我国学者稳扎稳打,步步推进,不断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引向纵深,且见出基本形态。在我国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空间场域内,围绕概念范畴、视域现象,从来不乏学术争鸣和论辩,不同程度地折射出我国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动态与趋势。现以问题为导向,择其精要进行述评,据此归纳我国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30年主要观点、路径与方法。
(一)“Ecological Marxism”三种中文译法
1979年,美国大学教授本·阿格尔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一书中首次使用了“Ecological Marxism”一概念。自“Ecological Marxism”进入中国语境以来,关于“Ecological Marxism”的译法共有三种,即“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生态马克思主义”。
王谨教授在《马克思主义研究》1985年4期上刊文《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最早使用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译法。慎之教授1991年在翻译本·阿格尔代表作《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第七章时也使用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译法。2003年,詹姆斯·奥康纳的代表作被唐正东、臧佩洪译为《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
俞吾金、陈学明教授2002年在其合著《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流派新编:西方马克思主义卷》(下册)第八章中将“Ecological Marxism”译为“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同年,陈学明教授在两篇论文《评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及其主要代表人物高兹》《评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对立》中也使用了“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的译法。2008年后,陈学明教授转而采纳“生态马克思主义”的译法。
徐觉哉研究员1999年在《社会主义流派史》一书中同时使用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生态马克思主义”两种译法。段忠桥教授在《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5期上刊文《20世纪70年代以来英美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和“生态马克思主义”三种译法同时被使用。郇庆治教授于2005-2006年间针对国内外生态社会主义研究进行评论时使用了“生态马克思主义”的译法。何萍教授在不同时间分别采纳过“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两种译法。
2006年,当时身为中央编译局助理研究员的刘仁胜在《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3期上刊文《生态马克思主义发展概况》指出,以2003年为界,自己此前发表的文章采纳“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译法,之后转而采纳“生态马克思主义”的译法,所以变更的原因,他解释说为与“生态社会主义”相对应。
汤建龙在《江苏社会科学》2010年5期上刊文《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历史逻辑、理论问题和总体趋势》梳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产生发展的历史逻辑时指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主要表现为“生态马克思主义”“生态社会主义”“马克思的生态学”三种形态,可见其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与“生态马克思主义”关系的界定。
在此笔者不禁想要追问,“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生态马克思主义”译法上的殊异,究竟单纯只是一个语言文字问题?还是关涉着我国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深层阐释问题?如果属于前者,只能说我国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在概念使用上有待于进一步规范统一;如果属于后者,那么是否可以大胆推测三种译法代表了三种不同的学术立场呢?迄今为止,我国学界并未对“Ecological Marxism”译法的使用乱象予以足够关注,自不必说将其作为一个问题进行系统学理研究了,所以清理“Ecological Marxism”的译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二)如何界定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起点?
20世纪80年代,王谨教授指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保留原文采纳译法)的“异化”观受到法兰克福学派的影响,相对于法兰克福学派的悲观论调,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提出了应对性解决策略与方法,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的起点作用在相关来源考辨中被提及。[1]
陈学明教授认为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保留原文采纳译法)的理论观点最早见之于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和阿多诺(Theodor Adorno)合著的《启蒙的辩证法》,该书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对启蒙的辩证过程的揭示,对人追求支配和统治自然的知识形式的批判,开启了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的先河。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理论体系的真正形成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的事情。波兰哲学人文学派代表沙夫(Adam Schaff)、前东德共产党人鲁道夫·巴罗(Rudolf Bahro)、法兰克福学派的马尔库塞和施密特(Alfred Schmidt)是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成的真正起点。[2]
刘仁胜认为生态马克思主义(保留原文采纳译法)的理论观点最早出现在马尔库塞的《单向度的人》(1964年)和《反革命与造反》(1972年)中,形成标志在于莱易斯(William Leiss)出版《自然的统治》(1972年)和《满足的极限》(1976年),阿格尔出版《论幸福的生活》(1975年)和《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1979年)[3]。
汤建龙认为生态马克思主义(保留原文采纳译法)主要是在法兰克福学派对技术理论批判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霍克海默、阿多诺、马尔库塞均是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观点可以溯源的起点人物。威廉·莱斯的《自然的控制》(1973年)、阿格尔的《论幸福和被毁的生活》(1975年)和《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1979年)则是生态马克思主义思想趋于成熟的标志[4]。
(三)如何界定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的关系?
刘仁胜认为马克思的生态学理论是生态马克思主义(保留原文采纳译法)的四种理论形态之一。
汤建龙认为马克思的生态学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保留原文采纳译法)的三种表现形态之一。
张立影认为马克思主义生态观构成了生态马克思主义(保留原文采纳译法)的基本组成部分。
陈武认为马克思主义生态学思想是生态马克思主义(保留原文采纳译法)的主流思想之一。
(四)如何界定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与生态社会主义的关系?
王谨教授所撰《“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和“生态社会主义”:评介绿色运动引发的两种思潮》是我国学界最早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保留原文采纳译法)和生态社会主义关联起来加以比照的代表性文章之一。文章从西方绿色运动由来说起,引介两种思潮产生的历史语境,先个别阐释,后汇总合拢。王谨教授认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批判锋芒固然尖锐,但理论色彩浓重;生态社会主义由于被德国绿色组织采纳为行动纲领,所以影响较大。两者源起地域空间不同,然而经过初期发展大有合流趋势[5]。
陈学明教授在《评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及其主要代表人物高兹》的文章中区分了生态主义、生态社会主义、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保留原文采纳译法)三个概念,认为生态社会主义包含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在生态社会主义阵营中,唯有那些带有强烈的马克思主义倾向的人才是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者[2]。
郇庆治在《西方生态社会主义研究述评》文章中区分了广义的生态社会主义和狭义的生态社会主义,认为广义的生态社会主义包括生态马克思主义(保留原文采纳译法)、狭义的生态社会主义、“红绿”政治运动理论三个紧密关联的部分,生态马克思主义的研究重镇在北美地区,欧洲学者则在狭义的生态社会主义研究领域占据主导地位[6]。
曾文婷认为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保留原文采纳译法)试图通过观念变革实现社会变革的主观臆断,因为缺乏历史基础,所以决定了生态社会主义不过是其具有乌托邦色彩的一种理想愿景罢了。[7]
刘仁胜认为生态马克思主义(保留原文采纳译法)侧重理论分析,生态社会主义侧重社会运动;生态马克思主义必然指向生态社会主义,生态社会主义则不必然源于生态马克思主义;生态社会主义分为传统社会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两种类型,前者主要来源于生态马克思主义,后者主要来源于德国绿党政治纲领。[8]
汤建龙认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保留原文采纳译法)主要表现为“生态马克思主义”“生态社会主义”“马克思的生态学”三种形态[4]。
由上述典型可知我国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成果丰硕,基础扎实,为后续拓展深化无疑奠定了前提条件,然而就现有话语体系而言,一些疏漏与缺失正在走上前来,且日渐清晰,以下三点尤其值得反思:
首先,纵观我国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30年成果,前20年的很大一部分始于对西方理论的述评与阐释,近10年来回归中国语境的呼声明显,研究重心虽然有所调整,但却谈不上实质性突破,属于民族的、本土的独立创新不足。
其次,我国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未能有效关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与其他学科的交往事实。以生态文学及其对应理论形态的生态美学、生态文艺学为例,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或者作为态度立场,或者作为思想资源,已经不同程度地参与了生态文学创作实践及生态美学、生态文艺学的理论建构,然而从接受效果反观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延展性和影响力的成果却是凤毛麟角。
最后,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中文译法,到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出身由来,再到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衍生分支,针对概念归属、关系界定、现象解读,学术争鸣每每不绝于耳,缘何如此?关键原因在于我国学界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身份认同”问题上尚未达成共识。
三 探查省思
据词源学角度来看,英语“身份认同(Identity)”最早来自晚期拉丁语Identitas和古法语Identite,距离当代社会可以说是源远流长。尽管如此,“身份认同”并没有因为时移世易选择销声匿迹,而是摇身一变为当代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内不可或缺、无法逾越的关键词之一。直观而论,“身份认同”是对主体自我的一种认知和描述,整个过程需要文化认同、国家认同、民族认同、性别认同等众多因素共同参与完成,其间同时杂糅自我与他者、个性与非个性、同一性与差异性、稳定性与延异性等各种关系的博弈和对抗,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讲,“身份认同”本身便蕴含了鲜明的跨界视域。“身份认同”的胜出除取决于其内涵的多层次、多元化、多样性以外,也与当代社会身份认同危机肆虐蔓延不无关系。
20世纪60年代,全球化进程席卷世界,直接影响了人类生产、交换、消费方式,彻底颠覆启蒙时代以来确立的时空秩序,使得以此为基准定位的身份认同风雨飘摇,重新组合的无限可能随之而来。刹那间,整体的、同质的被碎片的、异质的,抽象的、普遍的被具体的、特殊的所替换。正所谓“当某些假定为固定的、连贯的和稳定的事物受到怀疑并被不确定的经历取代时”[9]259,“身份认同”成为一个问题。此刻适逢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崭露头角,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探索和社会实践与其说是生态危机向马克思主义寻求治世良方的一次尝试,毋宁说是传统马克思主义遭遇身份认同危机后的一次转型。就此而论,马克思主义与“身份认同”出于相同的背景语境和共通的心愿诉求产生了交集,一场以“验明正身”为名义的、关乎生存根基的思想运动就此开启。
这一阶段,全球理论爆炸,以先锋性、前卫性为标志的后现代主义逐步超越传统马克思主义成为“时代宠儿”,“你方唱罢,我方登场”,正当后现代主义在光怪陆离、热闹纷呈的审美革命中自我陶醉时,残酷冷峻的社会现实再次发出警告这不过“南柯一梦”尔耳。20世纪60年代并非像某些社会学家早先预言的那样,是一个富足安康的后工业社会,恰恰相反,是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就国际形势而言,资本主义国家几乎无一例外地敏感到霸权统治的难以维系,第三世界民族的崛起,阿拉伯产油国家的强大让他们终日惴惴不安;从国内情状来看,通货膨胀无法逃匿,失业率居高不下,迷惘彷徨占据人心。面对一系列危机,许多马克思主义者开始“重新研究马克思关于危机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不可避免的副产品的原本思想”[10]414。当代危机不仅保留了马克思发现的资本主义固有的内在结构矛盾,而且增加了消费异化、环境污染等新兴元素,这就为马克思主义的当代转型准备了条件。本·阿格尔判定“80年代的大规模的社会变革可能会表现为一种‘生态学马克思主义’”[10]414,缘其意识到现代生活的过度集中和现代组织的绝对规模是异化产生的根本原因,并针对性地提出解决方案,即通过对生产和消费控制权的分散来克服“过度集中、官僚化和分裂了的人的存在”[10]415带来的弊病与缺失。
美国马克思主义者埃伦·梅克辛斯·伍德(Ellen Meiksins Wood)、约翰·贝拉米·福斯特(John Bellamy Foster)合力主编《保卫历史: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主义》(InDefenseofHistory:MarxismandthePostmodernAgenda)一书,其间独具匠心地将后现代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加以并置,对比后现代主义的解构性和破坏性后,他们强调马克思当年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预见非但没有过时,反而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再度彰显其合理性、合法性,这与德里达在《马克思的幽灵》中所意欲表达的观点不谋而合。埃伦·梅克辛斯·伍德认为以“差异”为中心的后现代主义由于缺乏批判性,所以导致思想体系陷入僵化,倘若想要理解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本积累方式、竞争逻辑的话,必须依靠“马克思主义提出而后现代主义者们否定的一种‘整体认识观’”[11]导论P15。伍德宣称当代是复兴马克思主义的大好时机,在马克思主义众多理论武器中,历史唯物主义是“能以比当今思想理论和政治潮流更为有效、更具说服力、更不受传统思想束缚的方式论及不同倾向的理论”。[11]导论P18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作为传统马克思主义在特定维度的延展物,承接了对诸如“自然”“异化”“历史唯物主义”“资本”等关键词重新加以阐发的历史使命,在延续使用传统马克思主义关键词时,对其内涵作出了不同程度的修饰;另外,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在传播接受的过程中,也遭遇了异质文化的改造,相关话语转换的结果千差万别,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语境内的身份认同考辨不一大抵来源于此。
纵观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半个世纪以来的发展轨迹,无论其自身内部的理论建构,还是来自不同地域、不同国家、不同代表的外部阐释,围绕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形成的学术空间场域从来不乏魅惑力与挑战性兼备的范畴、话语、论题、知识碰撞交锋。究其原因在于,一方面,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话语建构受到“身份认同”概念本身延异性的影响而天然呈现出多元复杂的成长格局;另一方面,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自我明证也好,其之外的他者参照也罢,均存在一些悬而未决的知识盲点,导致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知识谱系何以型构的过程无法获得澄明性揭示。时至今日,一度存疑的知识盲点历经社会结构的调整与重组反而为新时代的学术探索提供了可能。
四 结论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缘何而来?表面看来,当代环境危机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兴起的直接诱因,然而“生态”并非单纯关乎自然,本质上是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综合性问题。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作为生态学与马克思主义的联姻产物,涉及内容广泛,学科边界难以被准确规定,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属性、特征进行描述。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为了摆脱现实困境,“向经典致敬”,在继承与改造传统马克思主义基础上,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形成了“有问题”“有论域”“有态度”的一种“理论”、一种“视角”、一种“立场”,在与不同地理空间、民族文化、国家制度、学科专业的结合中得以发展壮大,并被当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实践所广泛采纳。
参考文献:
[1]王 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J].马克思主义研究,1985(4):286-289.
[2]陈学明.评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及其主要代表人物高兹[J].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2002(3):145-148.
[3]刘仁胜.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生态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D].中国人民大学,2004:2.
[4]汤建龙.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历史逻辑、理论问题域和总体趋势[J].江苏社会科学,2010(5):79.
[5]王 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和“生态社会主义”:评介绿色运动引发的两种思潮[J].教学与研究,1986(6):39-44.
[6]郇庆治.西方生态社会主义研究述评[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5(4):89-96.
[7]曾文婷.西方马克思主义视野中的生态社会主义: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愿景[J].武汉大学学报,2010(2):196-201.
[8]刘仁胜.生态马克思主义、社会社会主义对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启示[A].马克思主义与生态文明论文集[C].2010:174.
[9]Kobena Meter. Welcome to the Jungle: New Positions in Black Cultural Studies[M].London: Routledge, 1994.
[10][加]本·阿格尔.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M].慎 之,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
[11][美]埃伦·梅克辛斯·伍德.何谓“后现代主义”[M]∥埃伦·梅克辛斯·伍德,约翰·贝拉米·福斯特.保卫历史: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主义.郝名玮,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