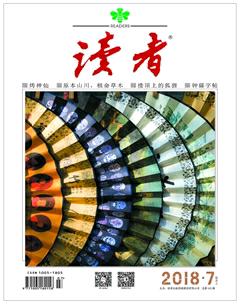冬日夜宴
张佳玮
以前被称为“江南乡间”的那片父亲的故居,如今已不再是那么纯粹的田园风景了——拓了路,修了楼,田野间建起了住宅区。然而到了冬天,乡间夜宴,还是要在家吃的。
乡下摆宴席,按惯例要请师傅上门,在院子里支起锅灶做菜,丁零当啷,喧腾热闹。父亲跟叔叔们聊天,母亲和阿姨们拉家常,嗑瓜子、剥花生、吃糖果。来探亲的远房亲戚中,年轻的姑娘红着双手,提着开水为长辈们泡茶,一被人夸貌美就红着脸,转身跑了。
黄昏时,狗吠声会传很远,各家的亲戚坐在大圆桌旁吃喝。凉菜先上,随后是热炒。大师傅们不断吆喝菜名,大人们喝酒说话,女人们把菜分夹出一些搁在碗中,任胳膊短的孩子们吃。乡间土菜,不甚精细,但肥厚重味、气势雄浑。霉干菜蒸蹄髈、炖整鸡之类,如不是大肚汉,看着就发怵。到了这时还有胃口下筷子的人已不多,更多的早已去拼酒叙话,或是自寻其乐了。大师傅们被请到桌旁,上酒上汤,吃自己做的饭食。别人敬烟,夸他菜做得好,他便將烟别在耳后,哈哈大笑。
然后,要开始喝酒了。我们那里的老式宴席,各桌有不同的酒。我小时候,家乡曾经流行一种乡下工厂酿制的东西,厂方将其吹嘘为香槟酒,乡人不买账,呼为汽酒。现在想来,多半是汽水兑酒的产物。气很足,像汽水,入口后才觉得略有酒味。酒量不大的奶奶、婶婶、阿姨、小妹妹们都可以喝,喝了也不醉。
年轻人或上年纪的女眷,喝啤酒或葡萄酒,再就是黄酒——南方人喝黄酒常用抿的,尤其是老人家,抿得唇间咝咝作响,然后吸个田螺或者吃口田鸡,眯着眼回味那股醇甜。
感情再好一点的,就得喝所谓“有力气”的酒了。每桌总有这么一瓶酒。白酒、保健酒,无所谓。总之,有力气的酒,少年不喝、女眷不碰。就是几个老爷们儿,尤其是长辈,碰了一杯又一杯;喝了几杯后,喝这些酒的人自发地组成一个小圈子,聊天、拍肩、大笑。天色暗下来,宴席吃完一巡,大家三三两两地散了。男人们喝得醉眼迷离,红着脸去隔壁串门。隔壁家还没吃完的,听见敲门声赶紧打开,各自拍肩欢笑,说起一年未见的想念。各家门前都挂了灯,怕喝醉了的汉子摔着。女人们在房间里收拾了桌子,便开始打牌。孩子们这时已有些累了,坐在妈妈膝上看打牌的也有,在沙发上睡着的也有,还有些不甘寂寞的,从后门跑去河边,惊起一片鹅叫声。
男人们半醉而归,一个个摔在沙发上,边聊边接着喝。他们就这样微笑着谈论生活里的琐碎小事,谈论生活本身。偶尔夹杂着一些对过去的回忆,仿佛只要就着酒,一切辛苦都能过去。
临近午夜,主人家把消夜摆上桌来。宴席没用完的食材,简单整治一下,端出淡一些的茶、用鸡汤下的粥,以及一些甜点和面食。小孩子们不知饥饱,看见甜点就扑上去。大人们则相当矜持斯文地喝起汤和粥,并且各自慨叹着。吃完这顿,大家或是各自散了,或是去主人家安排的房间睡了。
我记得那个寒冷的冬夜。我们一家三口到了客房,正待收拾床铺,却有人敲门。打开门,是我的叔叔和两位姑父。他们拿着酒,红着脸,对我父亲挤眉弄眼。我母亲叹口气说:“去吧。”我叔叔看着我道:“你来不来?”我去了。我们爬上屋顶,坐在屋顶的瓦楞上。我叔叔提了一个炉子上来搁在平整处,大家围着炉子,看着满天星光,哈着气,看见下面一片灰黄的田野和一路远去的萧疏林木。叔叔和两位姑父开了瓶酒,给我爸倒了一碗,给我倒了一点儿,叮嘱我:“别急着喝,抿一点点。”我哈着气、搓着手,不知道该期待什么,只记得他们四个人——在小时候的我看来,那时他们又高又大——说了些我听不懂的话,指点着这片他们生长于其间的乡土。我不记得他们说了什么,只是从未见过他们现出如此模样。大概,那天夜色下他们喝的,才是真正的酒。
(冥 谷摘自《新民周刊》2018年第1期,刘树勇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