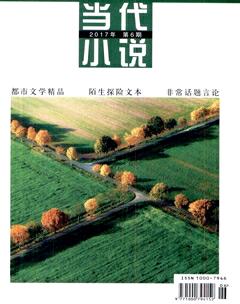外婆做的一个梦
王淼
1
风从窗外经过,忽然带起一些东西,飞一阵,又将它们放下,寻找别的东西去了。更多的风经过这个深秋的小镇、经过赤水河边的柿树林、经过垂死之人的窗前,没有迟疑、没有留恋,一往无前地飞。
只有秋天果子成熟时。才有这样明媚、浩荡的风。
我外婆躺在二舅家的阁楼上。她听着风声,或许没有听。她眼睑下垂,双手交叉搁在被褥上。一只苍蝇从她脑后的床板上绕过,飞到窗玻璃上,以头碰触,发出模糊而持续的嗡嗡声。
这只秋天的苍蝇显得硕大无比、笨头笨脑,徒劳地在透明的窗玻璃上飞。它大概已经很老了,老得只把窗玻璃当作出口。苍蝇的寿命最长两到三个月,或许,它很快就要死了。它的声音越来越微弱,最后干脆停在窗框上一动不动。我那躺在床上的外婆也已经很老了,老得只要略微动一动。就有可能像枝上熟透的果子忽而坠地。
往事如风,从外婆的窗外一一掠过。往事也如赤水河里的水,温暖与冰凉,都只是刹那错觉。
五个月前,外婆住在大舅家;五年前,外婆还住在老家芦花村的小屋里。外婆轮流躺在各位舅舅家的阁楼上已经五年了。这五年来,她哪儿也没去。
她没有瘫.还能下地走走。可自从那一次她在花桥镇上迷路后,他们就不让她走。舅舅们认为镇上车多、外来人口多,一个老年人到处乱走很不安全。而外婆想走,走回老家去,死也要死在自己家里。每隔一段时间,她的思家症就要发一发,但仅停留在口头表达上,舅舅们也从不当一回事。
“我要死了——你们的老娘马上就要死了,好送她回去了!”
“哼,你们这些不孝子,总有一天,我要自己走回去!”
沒有人理她,知道她走不了那么远的路。芦花村距离大舅和二舅所住的花桥镇约略十几公里.要经过的大概有赤水湖、梅村、樟树下村、采石场、福泉庵、岭上水库这几个地方。那个年代,货郎们一路插科打诨,走完它也需要近一个上午。外婆怎么可能凭一己之力走回去,简直是做梦!
没错,在那些白日梦里,我的外婆经常“走”回去。她神游般地走在那条路上。她总能听到锣鼓声。戏班子来了,好戏要开场了。她在自家屋里,慌得什么似的,双脚抽搐,拿了火钳跨出院门,又慌里慌张地跑回去。再次出门的时候,身上多了两个孩子,手里抱着一个、背上趴着一个。突起的门槛将她绊倒了,背上的那个摔出去,跌在门外,哇哇大哭起来。她赶紧放下怀里这个,去捞地上那个,却怎么也捞不起来。
疾驰而来的锣鼓声“咚咚咚”地催她快走,可她的孩子掉在地上,她的孩子不见了。她的孩子变成一条鱼,随着浑水游走了。
现在,我的外婆躺在床上,枯槁的双手在花绿的被褥上乱抓乱挠。她似乎抓到了什么,睁眼一看,是一朵干瘪的金银花。前几天,我表哥的小女儿在放学回家的草丛里看到它,将它采下献给我的外婆。
“婆婆,我把这朵野菊花送给你。”
“孩子,这不是野菊花,是金银花呀!”
“婆婆,那野菊花长什么样儿呢?”
六岁的小女孩不明白金银花和野菊花的区别。她凑近花瓣,使劲嗅了嗅,天真地说:“哦,金银花是不香的。那,野菊花香不香呢?”
小女孩抬头望着我的外婆,眼睫毛扑闪着。
外婆抬了抬手,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小女孩把那朵金银花放在外婆枕边,下楼去了。此刻,金银花散发的气味,让她忽然闻到野菊花那强烈的气味。阳光和大地混合而成的气味、青草生长时带出的气味。那气味在阁楼里盘旋,越来越浓。
而风已经不刮了。它们把所有野菊花的气味刮到我外婆的阁楼上后,忽然不刮了。外边静悄悄的。外婆将耳朵支起,对着窗那边聆听了一会儿,除了电线杆上麻雀的叽喳声,还是什么声音也没有。
世界很安静,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
外婆下了阁楼,走出二舅家,不忘将门带上。外婆的脚步是轻盈的,过分轻了,像踩在一个个棉花团里,身子有些摇晃,双腿颤抖得厉害,走起路来歪歪扭扭的。她绕过镇子,走在赤水湖边,身子一摇一摆。硬是画出一条曲折颤抖的波浪线来。
湖里的草鱼听见我外婆走近的声音,“砰”地一下跃出水面一秒钟,算是和她打了招呼。更多的鱼听见我外婆微弱而迟钝的脚步声,纷纷从潜伏的水草丛中游弋出来。鱼身跃出水面,发出水花溅落的声音。此起彼伏的声音交缠在一起,好像是珠子与珠子的碰撞。
外婆许久未曾聆听到这么天然、清脆的声音。外婆想起鸟羽击穿空气的啪啪声、深山里伐木的丁丁声。时隔三十多年,她对深山里的伐木声仍念念不忘。可她没有停下脚步,只要一停下,或许就走不成了。她慢慢地远离河岸,向着远处村落的方向走去。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在她的右手边,应该是梅村。可村口那株遒劲的老梅树却不见踪迹,这让外婆的记忆出现瞬间的恍惚。怎么回事呢?外婆在这个可能是梅村的村庄里东张西望着。村街两边出现倾颓的屋舍,一只大水缸里游动着孑孓,缸面上浮漾着绿色藻类。阴沟里沉积着乌黑色的淤泥,沟壁上爬着藤类植物,叶片上布满污垢。淡淡的臭味见缝插针,四处弥散。熟悉的村庄的气息扑面而来。
远远地,外婆看见一个穿红衣服的年轻女孩.坐在一株瘦橘树下。她吃了一惊,迟疑着向那红衣女孩走去。
红衣女孩也认出了外婆:“妈,你终于来了!”
外婆有些激动,去拉那女孩的手。她们的手如愿握在一起。外婆问:“那株老梅树呢?”
年轻女孩怔了怔,眼泪“啪嗒啪嗒”往下掉。“梅树早被砍掉了,村里很多大树都被砍掉卖钱了。我每天偷偷摸摸跑到这里,等外面的人来,一等就是好多年。”
外婆责备她,为什么不托人带信给她。女孩闻言,哭得更厉害了,“没有人会帮助我,他们都是德全的朋友,不是我的。”在说到“德全”这个名字时,年轻女孩的脸上浮现一层惊恐之色。
德全是外婆的女婿,原本只是个种菜的,自从成了远近闻名的阉猪匠后,就变了个人。
“既然你在这里过得不好,不如跟我回家吧!”外婆说。
年轻女孩环顾四周,略显迟疑地望着外婆,拿不定走还是不走。
“还等什么?我们快走吧!”
“好。别让他们看见了。”
2
重新上路的时候.我的外婆忽然进发出罕见的活力,不再那么老态龙钟,与刚才每走一步随时就要停下的样子判若两人。
一路上,她们絮絮叨叨,大都是外婆在说,说什么金窝银窝都比不上自家的狗窝。
她们走在那条通往芦花村的省级公路上,来往车辆不断。却没遇见什么熟人。年轻女孩喋喋诉说着在夫家所受的虐待,日子苦,过不下去,燒糊一顿饭、摆错一样祭品,都要被骂。“我恨他们,我更恨自己,当年为什么要离家……”她的眼泪像地摊上廉价的塑料珍珠,撒了一路。
外婆听着,身子微微发抖,说不出话来。两个人相拥着走路,也不知走了多久。动静忽然从马路对面传来,一个中年妇女大声招呼着外婆:“欺,大婶子,好久不见了。你这是要去哪儿呀?”
如果中间不是隔着一辆辆呼啸而过的汽车,那位妇女或许就会移步来到跟前。外婆发现妇女的眼神稳稳落在她的右手边,这让她惊慌不已,嘴上含糊地答应着,趁车子挡着的时候,早把步子迈得飞快。她丝毫没意识到自己在快速前进,所有腿脚不便的毛病统统消失了。
当一辆大型载重货车缓慢通过后,马路对面除了那排矮树,已空无一人。中年妇女消隐在飞扬的尘土中。外婆往尘土扬起的方向望了望,果断地说:“走,我们换一条路走!”
年轻女孩满脸疑惑地望着我的外婆,那神情好像已经好久不出来见世面,对这个尘世的禁忌和规则都忘得差不多了。
“我知道有一条山路通往芦花村,那里很隐蔽,没有人知道。”外婆手指远处的山峰,峰峦之上,云遮雾绕。
年轻女孩望望外婆所指的方向,一脸茫然。她们走到一处田埂上。田是荒田,植着几株瘦骨嶙峋的果树。果树与果树的空隙间,杂草足有半人高。田埂上长满蔓生的荆棘和芒刺,恶作剧似的,常常勾住她们的衣角,让她们别走。
外婆拉着年轻女孩,在荆棘和芒刺之间行走,如履平地。消失多年的汗液轻车熟路地回到外婆的体内,涣散的肌肉重新变得坚实,松弛的腿力得到持续加固。白发在隐退、黑发探出头皮,黑白交替,黑将取代白。
外婆瞬间变了个人,变成一个强壮的、能翻山越岭的人。她一阵激动,想起家里的母猪、兔子、鸡雏们,此刻正望眼欲穿地等着她回去饲养。“咱们快走!不然来不及了。”外婆大声说话,把步子跨得很大。年轻女孩跟在外婆身后,哼哧哼哧喘着气。
沿途,外婆看见兔子喜欢的爬树草、母猪喜欢的番薯藤,还有牛爱吃的黑麦草,她都没有止步去割。她归心似箭,一刻也不能耽搁。
脚下的路忽然变得柔软、顺从,一寸寸通向那个村庄,通向外婆屋外的篱笆墙。不知不觉间,她们已经进入山区,山路像直陡的梯子。
年轻女孩喘息着说:“真没想到这么难走。早知道,我们应该走大路。”
“难走点有什么关系?最重要的是安全。从山下看,他们只看见树,看不见我们。我们是安全的。”外婆振振有词。
“可我看得见他们,看得清清楚楚。”年轻女孩对此颇为忧虑。
“别害怕,很少有人能看到我们,一片叶子都能挡住他们的眼睛呢!他们什么也不知道,只有山知道。可山不会乱说。”外婆眨眨眼睛,微笑地望着那个年轻女孩,充满着只有在山中行走过的人才有的自信。
年轻女孩无奈地跟着走。她走走停停,她看山,山也在看她,不言不笑,静静地立在那里,千百年来,也不挪动一下。动的只是那些树叶、花草、灌木丛、山体表面的覆盖物以及拂过山体的风。
“多久才到啊?”
“快了,爬过这座山,下去就到了。”
“累呵。爬不动了呀。”
“我们慢慢爬,慢一点爬,就不会感到累了。”
她们靠在一块山石上休憩,女孩望着远山,忽然自说自话起来:“小时候,我听一个人说,山是飞过来的。它们总是在夜里,趁人不备,飞来飞去。那些山真的是从别处飞来的吗?那么,有一天,它会不会自己飞走呢?”
外婆听着有些奇怪,山怎么可能会飞?人都飞不起来,山怎么可能会飞?她到底想说什么啊?这个孩子的脑子里都在想些什么啊?从前可不是这样的!
外婆只好说:“别胡思乱想了。翻过这山,再过一个水库,就快到了。”
一说到水库,外婆不安地瞧着年轻女孩的神色,还好,她什么反应也没有,只茫然地望着远山与天空相交的地方,似乎那山顶的树木再长一长,就能碰到灰蓝色的天穹。那株最高的树将把天穹刺穿。刺出一个大窟窿来,然后另外的树继续长、继续刺穿,让天穹变成个大筛子。时间无穷无尽,只要它们愿意,可以一直长下去、刺下去。
外婆庆幸自己及时挽救了她,以后的事情就不会发生。那个曾淹死过很多人的水库最好不要让她遇见。可水库已经近在眼前,只要爬到山头,就能望见那一滴硕大的水。蓝绿色的水、不规则形状的水,被一道灰白色的大坝紧箍着,等着什么东西砸进去,溅出一点水花来。
“那是什么?”果然,年轻女孩的手指指到了那里。
“那……那是水库啊!”外婆颤抖的嗓音流露出了内心的惶恐。
“不是,我说的是那个,那里有人住吗?”顺着年轻女孩的手指,外婆看见一间茅草房,夹在一片杂树林里,烟囱上似乎还有青烟冒出……他还住在那里吗?都过去那么久了,不可能啊!
“那,应该是守林人的房子。”外婆略显迟疑地说。
那一年发生的事还横在外婆眼皮底下。她进山砍柴,天热,喝光了水壶里的水。去守林人老王的草屋里讨水喝。山上的水是甜的、山上的空气是甜的,山里人老王的身体上也有一股甜津津的汗味。老王的手那么宽厚、温暖,轻拂在脸上,如沐春风,让她想哭。最后一次,她真的哭了,像个十八岁大姑娘,满脸是泪,很伤心。
想到这里,外婆感到茫然,不能相信自己和老王真的好过。那种钝钝的痛楚,一点点重新从旧疮疤里渗透而出。
下山路上,外婆走得飞快,刹也刹不住。自入山后,她的体能已发生剧变,所有阻碍她腿脚前进的力量纷纷消退。年轻女孩的脚力则明显不够,有些跟不上了。
远远地,水库出现了。水位很高,不是往常寂静的蓝绿色,而是略显混浊的灰黄。还好,那么多水,竟然不发出一点声响来。
年轻女孩仍在嘀咕:我怎么觉得那屋里有人
外婆想,最好不要让她看见那个水库。没有这个必要。
走下坡路时,两人都有些失控,直往下冲。好不容易走到一条坦途上,卻还带着刚才疾走的惯性,双脚不听使唤地乱踩乱撞。
山脚下,外婆遇见了他。那个守林人,手里拎着一个米袋子,扁担扛在背上,蓝布衣衫敞开着穿,正慢悠悠地从桑树林那边踱步过来。
“发山洪,过不去了!别走了。”守林人举着空空的米袋,在半空中晃荡了几下,“你们过不去了!到我的草房子里歇歇脚吧!”
他仍然笑嘻嘻的,把她从头看到脚。
她告诫自己不要想,什么也别想。她艰难地从那个人身边挤过去,听见自己气呼呼地说:“怎么就过不去了?天塌下来,还是地陷进去了?”
“天塌下来喽,地也陷进去喽,洪水冲走了独木桥,没有路可走喽!”守林人的米袋子像一块破布。在空中飘了一会儿,又缓缓地回到他的手里。
“我们要过河!”
外婆拉着年轻女孩的手,头也不回地往山下奔去。
3
一条汹涌的黄泥河隔绝了两岸。黄水翻滚腾挪。如奔跑的走兽,前仆后继、昼夜不息。木桥已被冲走。水面上,一头死去的猪崽上下漂浮着,白花花的肚子,被巨大的水流撕扯着、席卷着、冲撞着,奔到下游去了。
河的对岸,麦田和芦苇荡的尽头,就是芦花村。她们望着那个暂时抵达不了的村落,流下了悲伤的泪水。
“水太大,根本过不去!”外婆扯着嗓门,近乎嘶吼。
年轻女孩挥动着胳膊,冲着水声喊叫起来,带着明显的哭腔。
“你说什么?”外婆大声问道。
“桥。去找下一座桥。”
“天快黑了。天越来越黑了!”
“桥!我要过桥!”女孩完全失去了控制,一心想过桥。
不知什么时候,守林人已悄悄来到河边,跟在她们后头。
“过不去了。真的过不去了。”守林人大声说。
年轻女孩一甩胳膊,沿着河岸奔跑起来。她大步大步地跑着、大口大口地呼吸着,好像要与洪流赛跑,看谁更快地跑过时间。
当年轻女孩奔跑的时候,天黑得更快了。年轻女孩奔跑的速度明显慢下来。夜色中,她的身影显得模糊,而那水声却更响了。
“去山上歇一宿吧。河水太急,过河危险。”守林人跟在她们后头,寸步不离。
外婆的眼神里忽然流露出久违的柔情。她想在守林人的草屋里住上一晚,就一晚。这个念头可耻而强烈。她不想过河了,河水那么急,肯定会出事的。守林人悄悄地扯了扯外婆的衣服,示意她留下。
一块巨大的木板从河的上游漂移过来。
年轻女孩扑向那块木板,可她还未来得及伸手,木板已被急流卷走。水花溅湿了年轻女孩的衣服,可她已经顾不上这些了。
木板给了她过河的灵感。她开始在河边东张西望地寻找着什么。外婆想,她的认真劲儿真像小时候在溪边捡鸭蛋。
从小,她就是这样一个认死理的孩子。
外婆终于说:“还是等明天再过吧。水实在太急了。”说完,她的眼神快速地掠过年轻女孩的后背,停在某个虚空的地方。
年轻女孩咬着唇,倔强地偏过头去。显然,她想马上过到河的那边去,一刻也耽误不得。
终于,她在废弃物中找到一块足够长的木板,看上去还算结实。不想,脚一踏上,只听得“咔嚓”一声,断为两截。木板断裂的声音让外婆心底一颤,她恍惚听到自己身上某处骨头发出的崩裂声。
女孩扑向洪流中的木板,就像饥饿的人扑向食物。她抱着木板,被洪流卷走。
她的身体随着裹挟而来的稻草、树枝、腐烂的牲畜,一路往前,在看不见的地方,被一阵猛烈的浪头击沉下去,消失在黑暗中。
4
草房子里,外婆躺在那张惟一的床上。夜。格外静,她已经不哭了。守林人老王靠在躺椅上。风吹着房顶上的茅草,发出细碎的呼呼声。
“睡了吗?”守林人的声音像风在窗户缝隙里呜咽,又似月光在草叶上徘徊。
“没睡,就咳一声吧!”过了一会儿,守林人又说。
草房子里随即传出一声咳,很轻、很轻的一声,戛然而止。
“我知道你没睡,我也不睡。我们一起不睡,好吗?”守林人激动地说。
好吗?
短暂的沉默后,那个声音忽然说:“那你,讲个故事吧。”
“好,”守林人答应了。
守林人大概在想那个故事该怎么讲,而她则做着长久聆听的准备。他们都共同期待着那个故事的降临。那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一个真真假假的故事里会有他们喜欢的东西吗?
万一,他在那个故事里向她表达心意,怎么办?刚才,她在为女孩哭泣的时候,他就乞求她留下。她该答应他吗?
这么想的时候,故事开讲了。
从前有一个人,独自住在山上,和他作伴的只有清风、明月和漫山遍野的树。山上的日子过得很快,日出、日落,年复一年。他很满足,没什么可遗憾的。有一天,他的草房子里来了一头受伤的老虎。看到老虎的第一眼,他就决定保护它。凶神恶煞的猎人要他交出老虎,被他果断地拒绝了。他说这个世界只要有他,就有老虎。除非把他先杀了,再杀死老虎。猎人想,这个人八成疯了,一个正常人犯不着和一个疯子计较.就丢下老虎,骂骂咧咧地走了。
在他的精心照顾下,老虎恢复了健康,并与他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他发觉自己越来越离不开那只老虎。
可那一天终于到了,老虎要离开了。他忽然失去理智,愤怒不已,骂老虎忘恩负义。老虎眼泪汪汪地望着他,说很感激他的救助,但不能留下来陪他。它要回到森林里去,森林才是它的家。
说着说着,老虎就流下了眼泪。老虎眼泪掉下的地方。长出一朵朵蘑菇来……
她不觉得这个故事有什么特别的地方,老虎的眼泪怎么可能变成蘑菇……想着都不可能。
“我喜欢那些蘑菇,我的房顶上就长有很多蘑菇。”守林人说。
对蘑菇,外婆既不喜欢,也不讨厌,说不出有什么特别的感觉。“不过,你要当心点,有些蘑菇可能有毒。”黑暗里,外婆告诫守林人。
“它们好吃得很,根本没有毒。”守林人兴奋地说著蘑菇,好像嘴里正在咀嚼着它。
外婆想着老家的房子上,从来没有长过什么蘑菇。那是水泥房子,怎么可能会长出这种东西来呢?她在黑暗里苦笑。她更想家了,恨不得立刻长了翅膀,飞回去。
守林人还在喋喋不休地讲蘑菇的事。有一天,他在林子里走着,看到一朵很大的蘑菇,像盆子那么大,采回家炒了满满一盆。
“那味儿真叫鲜美呢!”守林人嘴里发出啧喷声。
第二天,洪水依然咆哮,声若雷震。守林人说,别处还在暴雨,流到这里来的,短时间内停不了。
守林人再次力劝外婆留下,缓几天再走。可外婆已经等不及,伴随着年轻女孩的离去,外婆的心早已去了河的对岸。
“既然这样,那我为你造一座桥吧。”守林人艰难地说。
他开始伐树,一株株壮硕的松树慢慢倒下,被移到河岸边,成为新鲜的造桥材料。守林人忙了三天,从清晨到黄昏,孜孜不倦地敲打着。第三天午后,一座简易的木桥搭好了。
远远的,那桥横卧在洪流之中。除了桥面,其他各处都浸在水里。深而急促的水流,随时可能冲垮它.将它卷入洪流之中。
外婆见桥已架好,便急急地要上桥。守林人拦住她:“等等,让我先来。”守林人并没有马上过桥,而是燃起一支烟,慢慢吸着。
守林人吸完一支烟,望着外婆:“真的很想过河?”外婆使劲地点头。
守林人丢掉烟头,果断地说:“还是我先来吧。”
外婆想要阻止,已经来不及。守林人稳稳当当地走到桥的中间。回头一望,对着外婆笑。这一笑还未结束,忽然一阵剧烈的晃动,一截树干从上游冲下来,打在桥面上,溅起的水花漫过桥身,向着守林人的身上冲去。他摔倒了,跪在桥上,洪水瞬间漫过他的头顶。
水声过后,桥面空荡荡的。
四顾张望,没有守林人的影子。不太遥远的河的对岸,笼在一片水雾里,什么也看不清。外婆跪在河岸边,身体颤抖个不停,却忘了哭。
就在这时,洪流慢慢地、温柔地退去,退到桥身以下部分。水声也轻盈了许多,有鸟叫声从对岸传来。外婆稳稳当当地走上桥去,走到中间的地方,回头一望,好像在对着岸上的人笑。这一笑过后,桥身仍是稳稳当当的,什么也没有发生。
外婆平安地过了桥,向着暮色中的桑树林走去。她脚步飞快。有一个声音在耳边说:“快,快走啊!”在那个声音的催促下,她疾走如风,步履所至,尘土飞扬。
她进入芦苇荡,芦苇叶蹭刮在她脸上、手臂上,发出”哗啦啦”的声响。一阵风吹来,她忽然跑了起来,那“哗啦”的声音响成一片。
她跑得更快了,好像是被风刮着跑。她的手臂分开密集的芦苇秆子,像活力充沛的小船拨开浪花四溅的水面,锋利的叶片在她周遭发出凌厉的声响。
远远地,芦花村像一条破烂的小船,搁浅在混浊的水域。
她眼角一阵潮润,向着那小船搁浅的地方跑去。她的体力在奔跑的过程中,不断充实、壮大。
她意识到自己跑太久了。停下,不要再跑了,快停下!可双腿根本不听她的,它们好像被别的力量控制住了。
她跑过晒谷场、家族宗祠、小卖部,她的家在村子的最西面。她要跑过整条村街,她要看村子里的人端着饭碗、打着麻将、织着网、纺着棕榈线,多么热闹啊!她曾经也是他们中的一员,现在她回来了。她忽然热泪盈眶。
一个织网的老妪发现了她,“欸,你可终于回来了!”那人放下梭子,大声招呼她。
“是啊,我回来了!回来了!”她停下来,高兴极了,去握那老妪的手。她浑身颤抖个不停,想要说点什么。却嗫嚅着不能出声。
她哽咽着告别老妪,向家的方向走去。到处都是熟悉的脸、熟悉的房子、熟悉的气味,她必须马上找到自己熟悉的家。她在村子里转了两圈,没有发现它的踪迹。她冷静下来想,既然村庄都在,房子肯定还在。
她前前后后又找了一遍,终于在一堆瓦砾场中发现了它。房子一劈为二,一边已是废墟,另一边仍在苟延残喘.一条高速公路建在废墟之上。此刻,车辆穿梭,声响轰隆,她头痛欲裂。
走进残喘着的那一半家,绕过碎石瓦砾、荆棘杂草.她爬到屋顶上。她的屋子本来就是村里地势最高的地方,此刻她站在村庄的制高点上茫然四顾,有几家已经点灯了。星星点点的灯火从一片黑暗中渗漏出来。
她冷得发抖,没想到家里会那么冷。她使劲地抱紧自己,还是觉得冷。
刚才经过房间的时候,完全不认识了。墙体裂得厉害。缝隙里有隐隐的青苔滋生,椅凳被日光晒得失去原有的光泽,轻轻一碰就散架了。她站立的地方有些倾斜,这让她感到眩晕。
她忽然看到那朵蘑菇。在废墟般的屋顶上,那朵黑色蘑菇缩在拥挤的夹缝里,像报丧人撑在头顶的伞。她不能相信,水泥屋顶上也能长出蘑菇来。
扶着矮墙,她颤栗着,向那蘑菇所在的那片透明的亮光中走去。
5
这些,都只是外婆做的一个梦。
她醒了。由于梦里跑得太远,她脸色惨白、疲惫不堪,枯槁的手无意识地搁置在花绿的被褥上。
她想起了那些蘑菇,黑色的蘑菇、草房子上的蘑菇、老虎的眼泪。所有美好的事物在消失后,都会以一朵蘑菇的形式回来。
女儿已经死去多年。因与女婿发生口角,二十八岁那年跳了水库,再也没有回来。梦里,她再次被洪流卷走。
外婆的喉管里发出呜呜的声音。那低沉的呜咽声在房间里久久地回荡着。可她没有一滴眼泪。她的眼睛是干涩的。她多久没有流泪了,人老了,连眼泪也变得罕见。
在梦里,为了送她过河,守林人还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他竟然真的愿意这么做?想到这,外婆的脸颊上忽然飘来一片红云。草房子、飞扬的米袋子、林中的伐木声,一切是那么虚幻,却又真实存在过。
阳光透过林中缝隙,照在草房子前面的空地上,照在那一大堆散发着清香的木柴上。那个人提着斧子,嘴角叼着一支烟,从林子那边走来。
……可连那个人都已经下世多年了。
她觉得自己真的很老、很老了,老得已经没有同辈人了。
这天余下的日子,外婆都在床上躺着,嘴唇微微张开着,带着愿望被满足之后淡淡的笑容。一只苍蝇从她脑后的床板上绕过,飞到窗玻璃上,以头触窗,发出模糊而持续的嗡嗡声。
这只秋天的苍蝇硕大无比,又笨头笨脑,徒劳地沿着透明的玻璃飞。它在窗玻璃上持续地飞翔、打转,是将那里当成出口了。
在苍蝇的嗡嗡声中,外婆再次睡着了。
责任编辑:李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