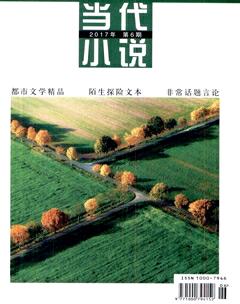十八岁的旷野
冯彩霞
1
小师傅叫细刻,只有十八,和我同岁,而我得叫他师傅。在我知道他的实际年龄后,我喊师傅就不大情愿了。我跟在他身后,看他将漆熟练地刷在门框上,刷子翻飞,漆薄而匀,没有流坠。刷完后他扭回头,脸上有得意之色。我撇嘴,有什么好得意的,不就是刷漆吗,用不了两天我就会刷得比你好!
他看我不服,又领我走到另一个房间。一扇未完工的木门架在工作台上。他拿起刨子,闭上一只眼。刨子在木门上轻快地滑翔,刨花像浪花一样翻卷,木头的清香塞满了我的鼻孔。他吹着口哨将刨子交给我。我整个身子俯在木门上方,双手端平刨子,然后向前推进,刚推了不足二十公分,卡住,拿起刨子再推,再卡住。我满头大汗地抬起头,将拎在手里的刨子甩在地上。他眉梢眼角里满是挑衅,好像在说,怎么样?服不服?
我当然不服。我从背包里拿出素描纸,对着他刷刷几笔,一幅肖像出现在纸上。他瞄了眼,不屑地说。怎么把我画成这样?我又朝画瞅了眼,哪里不对?你不就是这样吗?他连瞄第二眼的耐心都没有,接着说,再练个十年八年吧!他说这话时眉梢又挑了挑。再后来,他刨木门,我就在旁边看书,看《诗潮》,看《十月》。他偶尔看一眼封皮,嘴撇得能跨过鸭绿江。
他指着窗外的梧桐树说,诗人,你能为它做首诗吗?我瞧一眼那棵梧桐树,一棵破树有什么好写的?既没开花,也没落叶。我涨红了脸说,你也知道诗?那你背一首。他张口就背,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我笑得花枝乱颤,对他高高地竖起两个大拇指。
这叫实习吗?考进这个学校,而且学习装饰设计专业,全都是老梁搞的鬼,老梁专制的时候一点儿不含糊。老梁夫人也是怂包一个,看着自己的女儿伤心欲绝,居然使出“收买”的损招。我从西双版纳旅游回来,就进入了这个破学校。
刚人校两个月,学校就将我们扔到这个工地,美其名日:初步感知。
刚进工地,涂料味、油漆味扑鼻而至,射钉枪声、电锯声声声撞耳。我捂着鼻子四处逃窜,脚几乎不敢落地。正当我仓皇四顾时,被带队老师一把抓住,拎到小师傅的面前。见了我,小师傅发出“哧”的一声。
临走,老师还不忘留下一句话:遵守工地规定.服从师傅命令,否则,挂科。我问,师傅,你刚才为什么“哧”?小师傅说,丫头片子!我拿起根木棍,在他身后对着他比划了两下,他扭头,我正好放下。
我跑到别的地方去找同学。十三姨一脸苦瓜相.她的师傅矮胖,小眼一眯就像不怀好意,还胡子拉碴,鸟窝一样的头发白了一多半。我实在憋不住,跑到外边大笑三声,回来继续看十三姨的苦瓜脸。这时,她的师傅一扭身,松垮的裤带往下噜嘟了几分。露出半个包着花裤衩的屁股蛋。十三姨脸涨得通红.我捂嘴偷笑。忽然,我的小师傅背着手出现了。他指着我说,把老师走时交待的话背一遍。念在他年轻还算帅气的面上,我大声背了一遍。
小师傅个头足有一米八,我尾随着他英挺的背影回到阵地。想起十三姨的苦瓜臉,和她师傅包着花裤衩的屁股蛋子,我又笑出了声。小师傅不解地望着我说,生怕别人看不见你的一嘴龅牙!我忙捂住嘴.牙不好看管你什么事?你嫌不好看可以不看呀!但说出来的却是,师傅,我这牙不好看,就别在这儿恶心你了,我还是去看看十三姨吧,我怕她会阵亡。说着.又笑起来。小师傅从裤兜里掏出一张表,煞有介事地从其中一个框框里打上了“×”号。我敛住笑说,别介呀,那关系到我的见习评定。趁他扭身时,我又拿起木棍在他身后比划了两下。
2
第二天,十三姨跑来我这里,软磨硬泡非要跟我换师傅,她不惜冲着小师傅一个劲地抛媚眼。她对我嘀咕,自古以来都是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你校长的闺女就能跟黄晓明,为什么我就非得跟周伯通?小师傅不明就里,大方地冲十三姨咧了咧嘴角。他居然笑了,对我两天还没露出过一丝笑容。现在,对着十三姨的媚眼,他居然笑了。我严词拒绝了十三姨,并悄声表示我的师傅可能心术不正,有恐十三姨会吃亏.这么有风险的事,还是让我来吧!
日子就像窗外无精打采的梧桐。
小师傅今天对着块小木料雕刻。我坐在旁边的一块木板上,白色连衣裙无所畏惧地铺了一地。我大声朗读海子的诗:
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
喂马,劈柴,周游世界。
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
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小师傅的刻刀上下翻飞,偶尔他会将那块惨遭蹂躏的木块举到眼前,反复地看。他当我不存在可以,怎么可以漠视海子?小师傅只会背《咏鹅》,他也许根本不知道海子这个人。
百无聊赖,我又拿出素描纸,细细端详他。他的下巴硬得像角铁,脸上居然有淡淡的茸毛,嘴唇的线条也太分明,让我想到倔驴这个词儿。我憋住笑。继续欣赏。他的鼻子高挺,但并不顺直,山根下突然有个隆起,像刘德华。他的眉尖上扬,有点装模作样。
此时,他正全神贯注地雕他的木块,我看不到他的眼睛,画得并不流畅。这笔不对,走势有些失真,看不出倔;这笔好像也不对,弧度太柔和,无法表现他的坚硬。我自言自语,擦了又改。等我完工,发现他正盯着我看。我长舒一口气,师傅,没把你画丑吧?他点了点头说,太俊了,这还不是我。我急了,抓住他的双肩,让他面对着我不许动,准备对已经乌七巴黑的画再作修改。他皱皱眉,都说了你还得再练个十年八年的,别耽误我干活了。我不依,那你说明白,到底哪里不像了?他吹声口哨又拿起他的木块。此时,木块已初具龙的形态。我恼羞成怒,夺过他的龙摔到地上。他并没着急,慢声细语地说,你画的人在想什么?我一愣,我怎么知道?他说,你都不知道他想什么。怎么能画像呢?
我把嘴张得老大。这好像应该叫神韵,教画的老师曾说过。我指着他问,你懂画画?他轻蔑地一笑,不懂,我就是个木匠。
我想溜出去,刚转身还没迈步,他立马说,把老师临走交待的那句话再背一遍。我背着手立正,大声背:遵守工地规定,服从师傅命令,否则,挂科。他说.好。接着又指了指那块木板,大概意思是要么老老实实坐在木板上,要么跟着他干活。我冷笑着说。去厕所!他指着我的裙子说,从明天起不准穿裙子。这也要管?我白他一眼,转身去找十三姨。
十三姨和我同岁,她崇拜黄飞鸿,愣是取了人家太太的绰号。她正掂着把合尺发呆。她师傅憨厚地笑着说,你同学来了,说说话吧!看,人家师傅多好。
十三姨领着我出来,跑到工地大门外吃起冰淇淋。她冷眼看着我说,你还敢穿裙子,不怕别人用眼睛剜块肉去?唉,你真有福啊!
福从何来?我问。
十三姨咽了口唾沫说,你师傅没人敢惹,都没人去看你吧?这些工人,跟八辈子没见过女人似的。我都被看毛了,那些人走马灯似的来这里逛,这个说借个锤子,那个说借盒钉子。他们都在比徒弟,就我师傅不会护着我,光会傻笑。
我舔了舔嘴角的冰淇淋回到工位。小师傅抽了抽鼻子说,大小姐的待遇就是不错。
我说,师傅,十三姨那里可热闹了,每天人来人往的,你说你人缘咋这么差呢,咋没有一个人来跟你聊天?小师傅嘴角泛起笑意说,想换师傅了?可以呀。让你老师给我打个电话就OK了。我龇了下牙,认栽!老师和老梁是穿一条裤子的,我还是先忍忍吧。
我围着小师傅转来转去,心烦意乱。诗肯定是读不下去的。各种刺耳的声音,把诗都已牵到屠宰场。没有听话的模特,也画不下去。我说,师傅,我快抑郁了,跟你说话呢,听到没有?他“嗯”了声。我说,嗯是啥意思?你如果把我逼疯了,你是有责任的!我恨恨地准备抢他手中的木器。这时,我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一条龙的龙爪正努力张开着伸向我。龙鳞片片都微张着,龙头高昂,龙目奋睁,龙尾遒劲。底座是朵朵祥云。云的线条柔和,龙则恣肆张扬。龙嘴里还含着一颗龙珠。我看呆了,小心地伸出手指,拨转那颗木珠。木珠轻盈地旋转起来,像踮着脚尖跳舞的少女。我心花怒放,搂过那条龙细细抚弄。他说,大小姐,慢着点。我还得打磨呢。我有些疑惑,这还用打磨?小师傅说。不仅要打磨,还要上漆。我结结巴巴地问,师傅。你能雕小的吗?项链坠那么小。
小师傅看了我一眼,扭过身去吹了声口哨。
再回到家,看屏风,看摆饰,哪样都不顺眼。想象着屏风如果换成小师傅木雕的,那得是什么样?如果小师傅雕的那条龙放在老梁的书桌上,老梁会不会喜欢呢?今天是周末,我六神无主,转来转去。老梁夫人正在摆弄面食,她不跳舞,不美容,不逛街,整天弄个面团瞎鼓捣,还美其名曰:艺术。我转到老梁夫人身后,用手环住她的腰说,妈,这案板太小了,你这么大的本事也施展不开呀!我师傅能做案板,你想要多大就可以做多大。老梁夫人一听挺高兴,格外大方地拿出两张人民币,嘱咐说,别叫师傅白帮忙。
我捏着钱跑出了门。
小师傅看到我来,有些吃惊。我说明来意后,开始在周围找木板,相中一块大木板。小师傅说,那块板不适合做案板,遇潮会变形。我说,那你帮我选一块呗。我有一百块哟!我冲小师傅扬了扬手中的人民币。小师傅笑了。我忘了藏一张了,手里拿的是两张。
小师傅挑了两块榉木板,拿到工作台上。他锯、刨、合缝、镶边、杀角。一阵忙活后,案板嚴丝合缝、光滑平整。我闭上一只眼使劲瞅,竟找不到那条缝。小师傅将案板立我面前,催我尽快把案板送回家。没想到案板那么重,我抱着案板踉跄着向前冲了下,小师傅赶紧双手扶住,我竟然扑倒在他怀里,我整个脸都埋在他的颈窝里。小师傅愣怔了片刻,将案板抽出立到一边。我仰起头,正遇上他温柔的眼神。他突然狠劲地抱住我。一切都静止了。只是一瞬,我的心怦怦跳。他推我,我不松手。他的脸红红的,一声不吭地用力扳开我环着他腰的手。
天说黑就黑了,小师傅骑着三轮车送我回家。我扬着手里的二百元钱问,一百够不够?我将钱从他脖领子里塞进去,然后发出邀请,小师傅,还剩一百我请你吃饭咋样?小师傅咯咯地笑,狠劲地骑三轮车。
他将案板帮我提上楼。梁夫人大加赞赏。小师傅下楼走了两步,从怀里摸出那一百块钱塞给我说,好歹你也叫了我几天的师傅,就当改口费吧!我发现,他的脸又红到脖子根。
终于熬到了周一,我神清气爽地跑到小师傅面前.却发现小师傅比我更神清气爽。新理的毛寸,之前总是漆迹斑斑的迷彩服也换成了白T恤和帅气的牛仔裤。我凑上前一闻,他脖子里居然有淡淡的舒肤佳的清香。小师傅脸一红,忙将头扭到一边。师傅,你知不知道,你这一收拾,果真像黄晓明了!他也不回答。竟然跑了出去。工地外面是大片的旷野,绿草新鲜逼人。他铺了张报纸坐在沟渠边,信手摘了一朵淡紫的小花,双眼盯着小花发呆。
小师傅的背影在旷野里显得很小。
此后的很多天,他常常在旷野里独坐,或者抽烟,或者看天,或者叹气。他完全变了个人似的,不再和我说话。眼睛望着我总是发呆。忙活一阵儿后,就躲避瘟神般地跑出去,留给我远处的一个背影。有次,小师傅竟然主动要求给我换师傅。
这让我很是诧异。我当然拒绝了他。
3
有天晚上,我“如约”接到了十三姨的电话,蹦起来跟老梁夫人请假。妈,工地今晚培训。老梁夫人说,那去吧,好好学啊。
十三姨等在工地宿舍门口,说,怎么才来?
能出来就不错了,走,带我开开眼去。我跟在她身后进了宿舍区。
这是个不大的院子,院子三面都是两层的板房,院子里横七竖八地扯着很多晾衣绳,晾衣绳上各色衣服像各国国旗一样飘悠不定。再一看,一群光膀子的男人齐刷刷地盯着我。我一手捂着眼,一手牵着十三姨的衣角大叫,回去,不能去,这里都是光膀子的男人。让我妈知道了,得揍我个半死。
我的叫声引来了哄笑。有些本来穿着汗衫的男人也干脆扒掉了。我从指缝里看到小师傅,他显然很惊诧,慌乱之中。他从头顶的晾衣绳上摸过一件上衣就套上了。十三姨哈哈大笑,拨开我捂着眼睛的手指说,别装了,看看你师傅。我的小师傅身上居然穿了件女人的T恤,T恤的胸前隐晦地撑着两只软塌塌的“乳房”。师傅,你可够前卫的啊!我说。小师傅惊惧地倒退着,一边拨开我的手,一边向后逃去。
板房里热得坐不住人,人都在院子里闲扯。一个女人正撅着屁股洗头,我走过去,大姐,怎么不洗澡时一块儿洗啊?那女人白了我一眼。扭着大屁股进屋了。我小师傅可正在屋里换衣服呢!我大喊,小师傅,小心。小师傅出来训我,乱叫什么,什么大姐,小雕可比你还小仨月呢!
刚才那个大屁股女人叫小雕?我不依,我凑到小师傅脸前低声说,你换衣服,怎么可以让女人随便进屋?他也低声说,什么女人,咋这么不中听,是小雕。我说,是老鹰也不行,男女授受不亲。
十三姨拉我,别多管闲事了,快去看我师傅。我甩开她的手,你师傅有什么好看的?十三姨撇开我,自己去了。小师傅找了个板凳让我坐下,又用纸杯倒了一杯水递给我。我不接,他就放在我面前,然后自顾自地洗衣服去了。我不干,我说你就是这么待客的?小师傅好像很疑惑,那你还想怎么样?我低头俯在他耳边问,你是不是和小雕同居了?他好像很紧张。扭头往屋里瞅了瞅,紧张地说,你别离我这么近说话。
这时,屋里的小雕大喊,细刻,你进来。小师傅乖乖地跑进去,一会儿端着盆水出来泼掉,又接了盆水送进去。我跟着跑进去,恨恨地问,她是你什么人,能这么命令你?女人的头发还泡在盆里。嘴里发出“哟哟哟”的声音说,细刻,攀上高枝了,快成城里人的上门女婿了吧?我对着小师傅就是一脚,你是我师傅,你就看着别人欺负我?小师傅“哎哟”了一声,你就不该来这儿,你说你来干嘛?女人也急眼了,别人?我精雕和细刻一块儿摔泥巴长大的,你说谁是别人?我差点儿哭出来,小师傅,她到底是什么人?小师傅拽住我的胳膊往外送,别在这捣乱了,她是我师妹。
我扭身跑出去,去找十三姨。另一间房里有十三姨影影绰绰的身影,我犹豫了下还是闯了进去。屋里的情形令我大为尴尬。十三姨的师傅正端着一碗粥喂床上躺着的一个女人,而十三姨正为她师傅擦汗。我叫了声,十三姨。十三姨说,先等会儿吧,一会儿就好了。她师傅有点儿尴尬,十三姨,你跟同学走吧,天这么晚了,再晚我也不放心。十三姨说,没事,我同学有钱,我们打的走。我口袋里黑我老妈的二百元,被十三姨摸得门清。
我们一前一后走在院子里,打扑克的,打麻将的,喝啤酒的,抠脚丫子的,都拧着身子跟我们打招呼,这就走了,两个小美女,欢迎常来啊!院子里的水洼很随意,我不得不跳着脚走。刚出院子,想对着院子“啊呸”呢,发现小师傅讪讪地站在身后。我剜他一眼,拉起十三姨就走。十三姨拧着身子还招呼着。小师傅,不用送了,我们有钱,我们打的。我差点儿哭出来。想起那个女人的盛气凌人,我恨死小师傅了!
我要换师傅!
我给梁校长打电话,我说爹,明天给我换师傅吧。
梁校长说,好好学习,发什么神经!
十三姨瞥我眼说,咋啦,想看我师傅的花裤衩啦?告诉你,我师傅的花裤衩早就换成“欢迎品尝”啦!
我说,我现在一点儿也不想见他了,细刻这名字听着就砢碜。还有你那个武大郎师傅,没好东西!
别说这么难听,我师傅才不是武大郎呢。看见床上躺着的那个女人了吗?他老婆,植物人好多年了。我师傅够伟大吧!
小师傅再见我好像有点儿不好意思。
我不理他,自己坐在角落里生闷气。他从我身边一次次地走过。我嫌他木讷,嫌他不会主动打招呼,嫌他不会讨女孩子欢心。我气急败坏,你个色鬼。居然指使小雕欺负我!小师傅结结巴巴起来。我哪里色啦?我咋样指使小雕欺负你啦?
你还敢凶我?你说,你是不是在跟小雕鬼混?
什么叫鬼混?难听死了。小雕是我师妹,临出门时,我师傅嘱咐我要照顾她。
我不信,捂住耳朵哭起来。可恶的细刻,除了递给我张纸巾,居然不知道来哄我。
现在要跟小师傅说话,除了问他问题,其它他一概不理。我也变得很奇怪,总是死缠烂打问他问题。
短短一个月,图纸全部能看懂了,并且一看图纸,一幢装潢精美的大楼就立在眼前了。
我马不停蹄地跟在他屁股后刷漆,打排钉,弹线,刨木板,忙得不亦乐乎。他总是表现得一本正经,说,我干是因为我是工人,就得干,你得用眼看,你得动脑子,你得想想如果是你,这儿你想怎么设计,那儿你又想怎么設计。知道了吧?
我说,我学是因为你,我以后断然是不干这个的。
他说,如果有一天我再接到一套图纸,设计师的名字是你,你说会怎么样?说完,他好像还充满了遐想似的咂咂嘴。
老师来突击检查,看见我正在刷门漆,不禁啧啧称赞,这可是门面的活儿,一般人是不让干的,看来干得不错。老梁果真是爱女如命啊,见个习也得多方打听,不过看来,还真没白下的功夫,看你进步神速,我也好交差了。
春节将至,我每天都忐忑不安,生怕工地放假。
但工地还没放假,小师傅竟提前走了,连个招呼也没打。
有人说,他走前在工地前的旷野里,一个人坐了半夜。
4
春节过后,我拿出小师傅的肖像,左看不像,右看不像。果真不像小师傅。有股热血直冲脑门,我锁上门。支起画板开始重画。小师傅紧锁的眉头,抽动的嘴角,偷偷的笑,不屑,羞,窘。小师傅恨铁不成钢的苛责。小师傅轻快的口哨,躲避的眼神,狠劲的拥抱……我拿笔的手颤抖不止,泪流满面。
我决定去找小师傅,当面将这幅画交给他,问问他,现在像他了吗。
我打电话给十三姨,让她逼着她师傅告诉我小师傅的地址。十三姨说,她师傅不愿意说。她还学着她师傅的腔调告诫我,孩子,你可别去,去了会后悔的。
经不住我软磨硬泡,十三姨终于把地址要到了,并附详细的坐车路线和手画行走路线图。
坐了二天一夜的火车,又坐了五个小时的大巴,再转乘一辆当地蹦蹦车。蹦蹦车将我甩在大山的脚下,扬长而去。在这个层峦叠嶂的大山里,冬季的竹子略显疲惫,不知名的参天大树也显凋零之态。不时有一股清凉的泉水,出其不意地叮咚着奔到眼前,蜿蜒崎岖的山路上会有驮队经过。清脆的鸟鸣常不自觉地与驮队的铃声合音,新鲜的马粪味在清新的大山里飘荡。
我爬得气喘吁吁、汗流浃背,但往下看,才走了那么短短的一段距离,往上看,山顶隐没在缭绕的白云里了。我坐在石阶上,掏出路线图,估摸着到小师傅山寨的剩余路程。绝望之余,我伏在台阶上一动也不想动了。
我被一只手拽醒了,姑娘,姑娘。那只手执拗地拽着我,我醒过来,浑身冷得要命。一个驮队静静地立在山路上,所有人都直直地盯着我。
姑娘,你是想进山吗?坐在这里睡,多危险,会要命的。
伏在马背上的我几乎处于半昏迷状态。
我们是一个寨子的,有人说,精雕和她爸闹翻了。
为啥?
精雕不同意嫁给细刻了,说怕耽误他。她爸一着急,得了场大病,接着瘫痪了。细刻这孩子跟师傅亲着呢。也是,他亲爹娘也够狠心的,把这孩子扔山上,要不是他师傅,细刻早就冻死了,要不就被狼吃了。听说细刻灵光得很,什么都一学就会,城里人都看重他呢。他骨头里可能就是城里人!
在接近小师傅村寨的山头,我坚持下马。从山头上望下去,能看到几户人家零落在山坡上。我找到了小师傅家,精雕不在,小师傅正在喂鸡。这个院子和别的院子一样,都是石头屋子石头墙木栅栏,院子里有散养的鸡和狗。还有个木匠的工作台。
小师傅看见我,一脸的惊喜。他局促地用毛巾擦净凳子递给我,把水杯烫了一遍又一遍。
我对细刻说,这小院真温馨,要是再有两个孩子,就更温馨了。
床上的老人眼神复杂地望着我说,你看看,这个家就这个样儿。
我说,这个家挺好呀,放心吧老师傅,有细刻在,这个家会越来越好!
我要走了。
我说,再见,小师傅。
小师傅的喉节动了动,并没有发出声音,只是冲我挥挥手。
我没再看他。我早已满脸泪水。
5
开学后不久,我收到个包裹,打开层层包装,最后是一个小锦盒,红色绒面上静卧着一只精巧的小龙。这只龙晶莹剔透,它的眼睛有些无奈,似乎在看着我。我的眼睛潮湿起来。我的手指无法伸进去拨弄龙珠了,我用针拨弄它,它旋转起来,像快乐木马。
从那以后,我再没见过小师傅细刻。
多年来,我闭上眼睛,常看到一个男人的背影,在旷野里安静地坐着。
责任编辑:段玉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