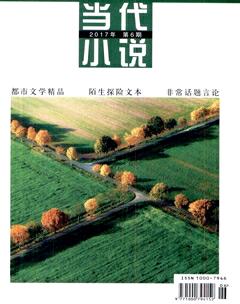当你们谈论爱情的时候谈什么?
冯积岐
是张峰把我约到这个茶秀来的。
我们刚落座,服务员刚把茶泡上,他就迫不及待地问我:你们谈论爱情的时候谈什么?我吭的笑了:我们谈论爱情?我和谁?他一听就发躁了:装什么装?难道你还和你老婆谈论爱情吗?我问你,你和她谈论爱情的时候说什么?我知道,张峰所说的“她”是我的一个红颜知己。我又笑了:我们在一起。就不谈论什么爱情不爱情,来直截的。他哼了一声:虚伪,你虚伪。服务员一扭屁股走了。我端起茶壶倒茶。他双手按住了:达诺,我看,今天这茶咱就不喝了。我一看,他满脸凝重的痛苦仿佛向下跌落,就说,有什么难言之事放不下?都这把年纪了,何必这样?他叹息了一声,身子紧贴住了沙发,头颅像一个巨大的问号,蹲在沙发靠背的顶端。轻松的茶秀里,充斥着他的沉重的疑问,气氛似乎也变了。
我和张峰相识于十年前。
那时候,省委组织部派我去关中西府的凤山县委挂职任县委副书记,我住在一幢小楼的二楼,张峰住在我的楼下,他担任县委宣传部部长。我们在一起共事三年三个月,后来我回到了省里的文化艺术中心,张峰从县委挪到了县政府,担任了常务副县长。他是从县人大常委会主任的职务上退下来的。退休还不到两年。
那时候,我之所以和张峰走得近,是因为,张峰是凤山县、乃至西水市一位有名气的散文作家,他的身份不只是官员。我和张峰在一起有谈论的共同话题。但是,我们从来没有谈论过爱情,以及有关爱情的话题。没有想到十年之后,他到省城来,要和我谈论这样的话题。我觉得蹊跷而可笑——这样的年龄依旧纠缠爱情,是很不合时宜的。
也许,张峰搁置在沙发靠背顶端的头颅经过短暂的思索之后,心情平静了。他喝了两口茶,点上烟,吸了几口,问我:凤山县政府办那个叫田小雅的女人你还记得不记得?我想了想:不记得了。他说,圆脸,短发,大约一米六的个子,雅致,文静。当时有三十岁吧,你不记得了?我很快打开了记忆的闸门,在记忆的库存里,怎么也拎不出来张峰所说的田小雅。我摇了摇头:确实不记得了。张峰说,那我就从头给你说吧——
他说,我给予她的太多太多了,可以说,改变了她的命运。
他说,我就不知道,女人在男人那里究竟要什么,男人给予女人什么样的东西,女人才能动心?
他说,张爱玲在她的散文中说,女人就没长良心。这句话我信。
他还要说下去,我打断了他:你不要激动,好不好?我不想听你的概括叙述,也不想听“心灵鸡汤”一类的话,你不是说,要从头说吗?那你就从头说,叙述具体的情节,用小说笔法。不要老是散文。
他说那好,我从头说。
我从县委到县政府没几天,有一个干事来给我送文件夹。她将文件夹放在我的办公桌上,迟疑了一瞬间,没有走,她小心翼翼地问我,张县长,麻烦你一下行不行?我说,什么事?你说。她说,我写了一篇散文,你帮我看看。我说,达诺书记在咱县挂职的时候,你怎么不去找他?人家是大作家。她说,我不敢去。我怕我进不了常委楼。她还敢说实话……我一怔,不觉抬起了头,瞄了她一眼。她端庄、漂亮,静静的样子。可我还是瞄见了她那双好看的眼睛里隐含的一团火,那是一团微暗的火,却在嗞嗞地燃烧。我放下了县长的架势,用谦恭的口气说,好呀,你把稿子拿来,咱们共同学习。
又过了几天,她给我送文件夹时把她的稿子一同给我送来了——她为什么不在当天或第二天给我把稿子专程送来呢?从这件小事上,我看得出,她是一个有心计的女人。晚上,我批阅完文件,开始读她的散文,我先看了看标题:《我的父亲》,然后,翻到最后一页。先看标题再看最后一页,然后通读,是我的阅读习惯。在文章的最后,她用钢笔写上了她的名字和手机号——显然这个名字和手机号是她给我送稿件时临时签上去的——因为不是用电脑键盘敲出来的。她为什么这样做?我心里很明白,我读过的写父亲、母亲以及亲情的散文可以说是马驮车载,我心里想,她不会写出什么新意的,就漫不经心地向下读。然而,她的这篇写父亲的散文我还是能读下去的。我被她文章中的真诚所打动,她在文章的结尾写道:“……我的父亲是伟大的父亲。我爱父亲胜过爱人世上的所有人。有句话说,父亲是女儿的前世情人。下一辈子,我还做父亲的女儿,不,做他的情人,名副其实的情人。”放下稿子,我按捺不住自己,按照她在稿子上留的电话号码,给她打了过去,我说,田小雅,你的散文我刚才读了,写得很不错。我真没有想到,凤山县政府还有这么优秀的散文作者。她显然有些激动,我仿佛能听见她兴奋而紧张的呼吸声,她竟然结巴了:感,感谢张县、县长。我和她的交往就是这么开始的。
你是小说家,你说说,田小雅有没有恋父情结?从她的散文中看,她对父亲的感情不一般。
咱先不讨论这个,你接着说。恋父情结是弗洛伊德的说法,是不是和中国人的情感有相通之处,我们是不是可以换一种说法表述,有待探讨。
好吧,我接着说。
我从县政府办主任那里知道,田小雅借调到政府办综合组三年了,她每年都试图正式调来,却没有办到,她原来的工作单位是田村镇中学。田小雅大学毕业后就分配到这个初级中学担任语文教师。她离婚后,被借调到了镇政府,一年后,從镇政府借调到了县政府。在此之前,我从来没有刻意了解过一个政府工作人员的生存状况。
其实,我没有必要给你说,把她调到县政府,是因为需要她这样能写材料的人才。你也知道.在六十万人的凤山县,能写材料的大学毕业生不是一个两个,我为什么选中了她?不瞒你说,我确实喜欢上了她,我觉得,这就是情感的力量——我不认为这是动用公权力办私事。因为,首先岗位上需要;其次,她符合条件。调动的难度在于,政府办的工作人员都是公务员编制,而作为初中教师只能进事业单位——公务员逢进必考。我和组织部和劳动人事局沟通了一下,将她调到了政府的下属的事业单位——县政府婚姻登记所。半年后,她就被任命为副所长(副科级待遇)。她暂且在政府办综合组上班。
将田小雅调到县政府之后没几天,财政局的田春光局长到我的办公室来谈工作,几句话说毕之后,他已经站起来要走了,但没有迈出步子,莫名其妙的嘿嘿一笑,好像很随意地问:张县长,听说你把田小雅调到县政府了。我说,怎么了?田春光说,不怎么,小雅和我在一个村,按辈分她叫我六爸。我说,我真还不知道,你们有这么一层关系。他说,我斗胆给领导说一句话。我说,尽管说。田春光说,我这个远房侄女,你还要有点警惕。作为长辈,我本不该这么说。为了领导好,我还是说出来了,盼领导见谅。我说,她人品有问题?田春光说,我不便说得详尽,相处时间长了。你就知道了。田春光撂下悬念就走了。我不能向田春光口中去掏话。我分明感觉田春光话中有话,却不能再多问,只能说,知道了。而田小雅以为,对我来说,调动一个人,易如反掌,她就不知道我背负着多大压力。县委于书记,组织部李部长,不可能问我为什么要调田小雅,不调王小雅,赵小雅。但是,他们心里是十分明白的。如果说,田小雅品质上有什么问题,以后有什么风言风语,就会使我很尴尬,或者说,给我抹黑。田小雅根本不理解,我调动她,把名誉压在了凤山县干部的嘴里。
果然,田春光的话不是瞎说,不知是田小雅出自什么目的,把一个秘密——除过我不知道以外,凤山县的干部可能都知道——自动告诉了我:田小雅在凤山县有一个情人,他是田村镇的党委书记常晓军,现任西水市卫生局的局长。
那年三伏天,我去雍山深处的林北县参加西水市的学习培训班。在我到了林北县的第二天,田小雅进山了。
在那个酷热的夏天里,我和田小雅在凉爽的林北县佳庆宾馆住了三个晚上。第三个晚上,我们折腾了一番之后,她偎依在我跟前,吞吞吐吐地说,峰,你对我是不是很了解?什么都知道?我说,那当然了。男人和女人一旦上床,对彼此就有了透彻的感觉,不只是了解。她说,你感觉到了什么?我说,什么都感觉到了,和你在一起,我就飞上了天,人在仙境。她说,你尽拣好听的说。你说,你还了解到了什么?我似乎感觉到了她想说什么,又欲言又止了,于是,我就说,在我面前你是透明的,像玻璃一样。她像小姑娘一样撒娇,趴在我的身上,用手搂住我的脖颈,说,有件事我全说给你,你可不要骂我。哪件事——什么事?我心里想,她肯定以为我知道了她的什么秘密。要不,她怕我以后知道了,使她处于很难堪的地步,提前告诉我,堵我的嘴,先发制人。而我却说,陈芝麻烂套子的事,我不想听。我越是毫不在乎的样子,她越想急于告诉我——她不想落一个欺骗我的“罪名”。她说,你听听嘛,我是爱你,才要给你说清楚。我说,那你就说吧。她重新依偎在我身旁,用手臂揽住我。她说,常晓军是她的娘姨的嫂嫂的儿子,小时候,她跟着母亲去娘姨家,认识了常晓军,常晓军大她十多岁,她将常晓军叫表哥。后来,她读了高中,读了大学,去娘姨家次数少了,两个人偶尔也相互通通信。你也知道。田村镇中学就在镇政府对面。我分配在那里当了教师之后,他一有时间就到学校来。我们就在那时候有了更深的感情,有一个礼拜六的晚上,他在我的房间里聊到了凌晨一两点,没有回去,我们就……她的一只手从我的胸脯上挪下去,平躺在我跟前,眼睛看着楼顶的顶灯。我心里未免有一股酸酸的味道,我不由得说,常晓军是你的初恋?她说,算是吧。在大学里,我谈过一个男朋友,但没有开过房,只是拉过手,接过吻。我侧过了身,揽住了她:后来呢?她说。这件事叫我表嫂知道了,我们就分手了。他舍不下他那个家。她说,我也知道,我们是不会有结果的,何况是很远很远的亲戚,我不可能撺掇他离了婚,另娶我。她侧了过来,再次搂住我,她说,峰,你能原谅我吗?我心里翻腾得很厉害,竟然不知道如何回应田小雅。达诺,我觉得,我那一刻是你的小说中的一个人物,我想起了你的小说中的一句话:谁的新欢不是他人的旧爱呢?我总以为,田小雅单纯,是一个很纯粹的女人,当然我不能说,她因为有过一段爱情就不纯粹了。可是,常晓军还是卡在我的心里,不,卡在喉咙眼里,想吐也吐不出去。我一句话没有说,我能说什么呢?突然,她潸然泪下了。我紧紧地搂着她,我说,小雅,别这样,我还能计较过去的事吗?我喜欢你,即使你是白骨精,我也喜欢,你不知道,我爱你有多深。她又哧的笑了:谁是白骨精?我说,那不过是个比喻,我的意思是说,我爱你,就爱你的全部,连你身上的汗毛、垢痂也爱。她说,峰,你真好。我这一生,能拥有你,是我的福气,除了你,我谁也不要的,你信吗?我说,信。她能把她和常晓军之间的事说给我听.说明她是坦诚的,她确实是爱我的。当她哭出了声以后,我有了宽容她的想法——甚至不只是宽容。我对自己说,那时候,田小雅刚大学毕业,我并不认识她,更不可能干预她。
后来,我才知道,田春光给我留下的悬念就是这件事。常晓军和田小雅的绯闻把凤山县几乎染红了。我却一点儿也不知道。在认识田小雅之前,我和她毫无关系,我为什么要知道这些烂事呢?
尽管,我去西水市政府开会,偶尔也会见到常晓军。他虽然不是我的情敌,但是,我一看见他心里总是疙疙瘩瘩,像塞了一团烂棉花。
很快的,我把这件事抛在了脑后,一心一意爱着田小雅,一心一意帮助她,给她创造比较好的生存环境。
我和田小雅的关系绝不是媒体上所说的“包二奶”,而田小雅也不是什么“小三”。因为,我们的感情很深。我觉得,只要有感情,什么都有了。局外人怎么说都无所谓的。
我鼓励田小雅好好地写散文。我给她买来了民国时期几个大散文家的书籍,以及世界经典散文家的作品,指导她认真阅读。她把她写的每一篇散文都拿来叫我批评。她发表的好多篇散文都是我给她修改过的,包括标点,也是我改过的。我将她的散文推荐到《散文》《散文百家》《今晚报》《新民晚報》等报刊发表。她在省内外的散文评奖中,几次获了奖。在西水市的文学界,她有了一席之地。她由衷地说,峰,我的成功就是你的成功。我说,你是我的自豪和骄傲。我们的爱情同时也在升温,几天不见,恍如隔年。
我就是在这种背景中,想办法把她调进了西水市文化局创作研究室。
那次调动我可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创研室只有一个编制,而想进市创研室的有五个人,和田小雅竞争的都是背景很不一般的,比如扶眉县一个80后的女教师,她的支持者是西水市纪委的马副书记。天兴县文化馆的一个女干部,也是80后,给她跑调动的是县委书记。你知道,现在办任何事都要人脉,为了田小雅的调动,我找到了省委组织部干部处的处长,找到了西水市政府的常务副市长郭健。郭健是我在古都大学里的同班同学,他半开玩笑地说,张峰,你为这个田小雅跑断了腿,她恐怕不只是你的女弟子吧。你可不要给我挖坑,等田小雅进了西水时,让我跌进泥坑。我没有腐败,也不想腐败。我说,老同学,你还不知道张峰,我什么时候求过你?我会叫你跳到坑里去吗?我从来没有利用手中的权力给亲人、亲戚办过任何事;从来没有为这种事情求过任何一个朋友、同学。这一次,我为了田小雅,弯下了腰,去求人。我给田小雅夸了海口:一定将她调到西水市的文化单位。首先,她确实是人才;其次,创研室也需要一个人。如果举贤荐才也是腐败,我能找你吗?郭市长觉得我说得也对,就答应了这件事。
田小雅如愿以偿了,这不是田小雅给我提出的要求,而是我心甘情愿地给她办好的。我觉得。爱就是奉献,既然我爱她,就要为她而奉献,奉献出我能奉献的一切。田小雅能走进西水市,我比她还高兴。
她在西水市,我还在凤山县。我们不可能每天都能见面。我和她每天晚上在电话上聊一个多小时.我再忙再累,也要给她打电话。我就是去省城开会。到外地出差,每天晚上的电话照打不误。两部手机,通向了两个人的情感世界。
这种“手机感情”还是有了危机。要么,她借故各种原因,敷衍了事几句就挂掉了;要么,她关了机;要么她不接——然后找理由解释。我明明听见。手机里静如银针,她却说,她在某个饭店吃饭;有一次,我一连打了二十三次,她一直在通话中,她却给我说.手机充电,她关了机。难道我连手机提示的通话和关机都听不清吗?我实在忍无可忍,在电话中质问她为什么骗我?她却说,我不信任她,我怀疑她。她越是在电话中敷衍,我越穷追不舍——一次又一次地打。她就抱怨,说我跟踪她。她质问我:难道我是你张峰的吗?我说,就是,你是我的,我也是你的。她说,我是我自己的,谁的也不是。我想怎么处置自己,是我的自由。我说,你不是很爱我吗?你不是说只爱我一个吗?她说,我爱你,不是叫你囚禁我,束缚我。我们的电话聊天变为相互指责。每次打电话,都是在很浓的火药味中挂断的。而且,她几次威胁我,如果再这样,她就和我分手。
西水市卫生局的一位副局长是我高中时的同学,他直截地告诉我:常晓军和田小雅在一起。我恍然明白,我千方百计把田小雅调进西水市只是给田小雅和常晓军提供了约会的便利。可是我不能相信这是真的,我宁可相信无,也不相信有。就像癌症病人明明知道自己是癌症,却在心里排斥着死亡的威胁。
我也几次想到了和她分手,可是怎么也下不了这个决心。因为,我发觉,我还是爱她,她就是身边有几个男人.也和我爱她无关。我们已经好长时间不在一起了,偶尔一次约会,也是不欢而散。我明明感觉到她的心不在我的心上,我却自己欺骗自己:她是爱我的。
我为什么要问你,你们在谈论爱情的时候谈什么?因为,我们在谈论爱情的时候,从不谈论性——虽然尽情地做爱,但不谈论。木心先生说过,爱情问题就是性的问题。我们不认可先生的这个论断。我们将爱情看得很高雅,很精神。尽管是婚外情,从来没有负罪感。我们曾经山盟海誓过,曾经赌咒发誓过,我深信。我们会爱到永远——尽管不知道永远是什么时候,但是没有怀疑过,有一天,爱的这条线会绷断,没有怀疑过,我们之间是不是爱。我猛然发觉我和田小雅相处了五年,原来,我不懂她,我不懂女人。达诺请你告诉我,女人的一生是不是只有一次爱?女人是不是只爱她的初恋?我就不明白,我给她做了那么多事。包括给她的父母亲、给她的亲戚们也办了不少他们办不到的事情;包括,她想什么,我就给她买什么。我付出的越多,她越不在乎我。于是,我只能加倍的付出。就像我刚才说的,我就不知道,她想要的是什么样的生活,什么样的人生?据我所知,常晓军给她没有办一件事,她却又投进了常晓军的怀抱,她对常晓军恋恋不舍,深爱着他。这是为什么?为什么?
张峰摁灭了手中的烟,不再说了。能看出他十分痛苦。
我说。不是你給她多少的问题。如果她不爱你,你给她金山银山也是枉然;如果,她爱你,她还会给你掏钱买东西的。
我淡淡地说,放下吧,该放下的时候一定要放下,何必自己折磨自己?
他说,如果能放下我早放下了。她依旧在我心中。
我说,这就怪你了,怪你不能面对自己,不能面对现实。一个人难就难在,不能面对自己的心灵世界,不敢面对自己的心灵世界,尤其是不敢面对自己的龌龊。
龌龊?我龌龊吗?他说。
依我看,你们之间从一开始就没有什么爱情可言,恕我毫不客气地说,只是苟且,只是相互需要。她需要你手中的权力改善自己的生存状况,而你需要的是她的年轻的身体。这和爱情无关。我问你,你相信爱情吗?
相信。曾经相信古典式的爱情,崔莺莺和张生那种爱情,很专一的爱情。
为什么说是曾经?
我现在已经不相信一个女人会爱上一个男人,她们给爱情里面赋予的功利太多,不纯粹了。我还是追求纯粹的爱情。
什么是纯粹的爱情?你的浪漫有点可笑。你怎么不检讨自己?连你对爱也持怀疑态度,还有什么爱可言?
我追求爱。追求不为房子、车子、票子、地位、权力而献身的爱。
你都这般年纪了,还是不合时宜的浪漫的诗人气质。你的追求不现实。世俗生活,包括爱情,总是和衣、食、住、行相关联的,总是和性相关。文学大师木心的话是对的。爱情这东西说透了和性分不开。你说常晓军给田小雅什么事也没办,她还对他爱得那么深。你以为你给田小雅解决了很多问题,她就很爱你?你的想法本身很世俗。人家田小雅就不需要常晓军给她办什么事,也许,她反过来还给常晓军办事。为什么?也许,常晓军给田小雅在床上带来的愉快,你根本不可能给予她。女人是一本深奥的大书,你没读懂书中的内涵。
照你说,我们只有一条路:分手。
这件事我不能给你决断,因为人的情感是非常微妙,你身在其中,也迷惑、懵懂,我一个局外人,更不可妄言。不过我要回答你一进茶秀就给我提出的问题,我和我的红颜知己在一起谈论爱情的时候,谈生活,谈做人,真诚地生活。在生活中做一个真人,才会获取真正的爱情。不然,你欺骗了爱情,爱情也会欺骗你。
责任编辑:王方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