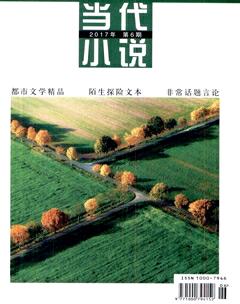还乡
何世平
可发空着手,走进家门时,圆子就发现他的脸色不对。
可发遇到麻烦时,那张刀子脸,本来就长,此时嘴巴却很不自然地嘟囔着,用圆子的话说,都能挂粪瓢了。今天圆子没有说他,圆子今天的心情也不好,圆子的心情不好,没有摆在脸上。可发肚里有丁点大的事,都挂在他那个刀子脸上,几十年了,没有丁点改变。圆子压着自己的心思,问他怎么了?可发说,没法活了,人力车都不让踩了。
圆子没有吱声,转身到门廊的灶间,拿起年前腌制的腊肉,拿刀剁了一块,打开水龙头象征性地用自来水冲了冲,就拿到一块塑料砧板上,开始切肉片。可发以为她又要用大蒜苗烧红烧,可发最不喜欢那样吃。可发看见圆子把一块一块很薄的有瘦有肥的五花肉,放在一个碗里,然后放进了还是生米的电饭煲里。可发的坏心情一下跑了许多。他就喜欢吃饭锅里蒸熟的腊肉,也不是有什么讲究,只因为小时候,娘就喜欢那样蒸给父亲吃,那个时候,不像现在家里有甚好吃的。先尽孩子吃,那个时候,家里有甚好吃的,娘都要背地里吩咐姐姐和他,要让父亲的筷子。姐姐一般老实地听娘的话,他也想听,可一到了桌上,他拿筷子的手,就不听脑子的使唤了,吃了一块,他还想着碗里的,又吃了一块.他还惦记着下一块。那一块一块咸生生的腊肉,丢进嘴里。他还没舍得用牙齿咬,可那散发着香气的肉片,就哗啦一下溜进了肚子里,香气顿时就没了。他于是就想著碗里的,小眼睛滴溜溜瞅着碗里的,往往这个时候,娘就拿眼睛示意他,他明明是看见了娘的提示,可他就是忍不住那一块一块香喷喷腊肉的诱惑,便不由自主地又伸出了筷子。
他是家里的幺儿,娘拿他没有办法,气咻咻地警告他,这样下去.讨不到老婆!
圆子把蒸腊肉端到桌子上时,可发还是与往常一样,喝起了小酒。与往常不同的是,他有一口没一口地吃着桌子上其他的菜肴,他就是不沾腊肉的边,好像压根儿他就没有瞅见桌子上还有那一碗菜似的。
圆子开始没当回事,当她扒完一碗饭,见碗里的腊肉还原封不动地在碗里时,她好像受到外人嘲弄一般,拿眼对着可发瞅。可发喝着他的小酒,他有意无意地避让着她像锥子一般射过来的眼光。
圆子问他,你啥意思?
可发说,我没意思,我只要你答应我,你不回乡下,你放我回乡下,行不行?
圆子说,人家贴心贴意为你在饭锅里蒸了腌腊肉,你依自己的心情,赌气不吃,你个晓得我现在的心情?
听了圆子的话,可发才忽然想起什么似的,抬头问圆子:你平常这个时候不是在饭店上班吗?怎么回家了?
圆子的眼里,有一团雾气在她的渐失光彩的大眼睛里盘旋。几年前,圆子还在饭店里端盘子,这两年,就自然而然地在后面洗碗洗锅了。
圆子说,我洗碗的事儿被人顶替了,我也没事做了。
可发用手薅进头发,想在头发里找到办法,当手从头发里出来的时候,还是没有办法,却把头发揉得像鸡窝。他想对女人说句什么,可是他不知说什么好,他急得脸上都暴青筋了,还是找不到合适的话安慰女人。
圆子看透他心思般地说,你也不要急,我答应你回乡下去。
可发瞪大小眼,不相信地问,真的?
圆子说,你也不要高兴得太早,还要答应我一个条件。
可发的心“咯噔”了一下,他脸上刚刚放松的肌肉,又紧张了起来,既然女人答应了回乡下,他也只好硬着头皮问她的条件。
女人说,你把这碗蒸腊肉吃光光,我明个就陪你回乡下。
可发听了,有那么两秒,有些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他想问圆子,刚才说的是不是真的?他又想,还是不问的好,他怕自己那么一问,圆子改口了,那就麻烦了,等圆子刚才的话,等了有十来年了,今个圆子终于放口了。他于是挥动手里的筷子,直奔桌子上的那一碗清蒸腊肉而去,起先几块像吃白萝卜一般,几筷子过后,碗里的腊肉,已经被他风卷残云地扫去了一半。到底还是感觉到了咸,从喉咙一路咸到了心里。他才想起杯中的酒,杯子里有半杯酒,他举起杯子,那半杯酒全部滑到了喉咙里。放下杯子,他又像吃萝卜样。开始往嘴里送腊肉。
圆子瞪大了眼睛,问,哪个跟你抢了?
可发又倒下半杯酒,只一口就干了。再瞧碗里,已经只剩下两块腊肉了。
圆子说,你能不能斯文一点?
可发没有听见一般,把那两块腊肉用筷子并成一块,再送进嘴里时,他没有咀嚼,却口含腊肉,眼睛盯着圆子。圆子幸灾乐祸,说你吞不下去了吧?圆子的话音刚落,那两块肉就被可发在没有咀嚼的情况下,生生地吞下了肚子。圆子说,你神经吧,哪个和你抢着吃还是怎么地?
可发又在倒酒,只倒了一点,圆子把酒瓶夺了。可发喝下杯子里的酒,对着圆子说,我明个去谢谢那个饭店的老板去!圆子不明就里地望着可发。待她明白可发的意思,说你要不去就不是人!
其实可发说到乡下的老家去种田,已经不是一天两天,更不是一年两年的时间了。每每可发说起,就被圆子呛了回去,圆子呛可发就反反复复一句话: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可发听了,无话可说。
可发在初中毕业那年,没有继续读高中,可发是一个没有远大理想的人。照理他的条件在当时的乡村,那是没有话说的,就凭父亲在县城酱油厂上班,就能猜到他们家的日子,在当时的草屋村,不是一般的。
这样的日子在可发十九岁那年,发生了变故。一贯好酒的父亲,在一天晚上骑车回家的机耕路上,摔倒在路边的水塘里淹死了。那是一个秋天的早晨,来送信的说出父亲淹死的消息,不但母亲不敢相信,可发上前就揪住了那个送信的中年人。扬起了粗壮的拳头。好在母亲冷静地拉开了他。
把父亲安葬后,可发天天背着扁担。到山里去砍柴。父亲没了,他家的一片天塌了,母亲天天以泪洗面,他不能像母亲那般哭泣,虽然他明显感觉村里人虽然口里安慰他,安慰母亲,那也是在送别他们之前的优越,这在同伴黄毛与他说话的口气里,就能明显感觉到。
感觉到,他又能怎样?
黄毛安慰他说,你爸死了,那是你命不好,别怄了!
黄毛安慰他说,现在我们扯平了,你那酒鬼爸爸不要你了!
乍听这话,可发掉过头去瞪着黄毛,可他发现,黄毛一脸真诚,他哭笑不得,只有安静地听。
黄毛看似安慰的话,在他的心里还在翻江倒海,灰心丧气之时,却意外地得到县酱油厂让他去顶职的消息。他簡直不敢相信,去了才知道,他这是搭国家政策的最后一趟顺风车,他上班不到一个月,这个政策就被取消了。
他回到草屋村时,黄毛拍着他的肩膀告诉他,他相信了《流浪者》电影里的话,贼头的儿子一定还是蟊贼。当工人的儿子一定还是个工人!
可发能听出黄毛心里的嫉妒,能感觉他语气里酸溜溜的味道。他却故意问黄毛,《流浪者》里台词是像你这样说的吗?
黄毛说,农民的儿子就是农民,我俩现在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上,难道还是假的不成?
可发发现,黄毛这次的话,的确是心里话,父亲死后,他们之间微妙的平衡,被他进城顶职,又一次发生了变化,而之前的自己,做梦也没有想到,居然不费吹灰之力,就进城到县酱油厂去当一名工人。虽然他明了自己现在的一切,是父亲意外死亡而得来的,他有时回家。真的就想到了“命运”的问题。命运是他后来想到的,他当时想到的,是自己的运气,自己的福气。
可发才上班的时候,每个礼拜都要骑着他的“凤凰牌”26型自行车回家一趟。父亲骑的是28型“永久牌”,父亲过世后,可发怕母亲睹物思人,偷偷将那辆自行车卖到了县废品站。到可发上班时,他第一件事,便是给自己买了一辆心仪已久的“凤凰牌”自行车。可发骑着这辆自行车回家时,黄毛的眼睛盯着自行车,足足地打量了好久。黄毛自然又对可发一通夸赞。
可发又一次骑着自行车回家的时候,黄毛告诉他一个秘密,说村支书的千金,圆子想见他,可发莫名其妙,说自己跟她不熟悉,她怎么想见自己?黄毛说,人家想见你,是给你面子,别不识抬举。可发被黄毛这么一激,还真的跟着黄毛去见了圆子,圆子的美丽一下就把他吸引住了。
后来才知道,村里的木匠小勇子那时候正在托人讲圆子。圆子做村支书的父亲没有话说,圆子要是答应,就没有可发的事了。可发知道这个事情,是他已经和圆子对上象以后。他心里还是“咯噔”了一下,凭条件.他家没法跟木匠小勇子比。与圆子结婚时,他问圆子,圆子笑而不答。黄毛一语道破天机,就凭你在县国营酱油厂上班的牌子。在农村什么样的女人讨不到?
听了黄毛的话,可发心里畅快,不管怎么说,娶了一个像电影演员一般的圆子做老婆,心里就是爽。这样的爽让他每天上班回家,都带着一份好心情。
这样的好心情保持到女儿出世,酱油厂的效益开始下滑,工资开始拖欠。第二年,厂里有人开始跳槽。跳槽出去的人,命运比留在厂里的人,好不到哪里去。又有人往外跑,这些人出去,不是去上班,而是去经商,有的人出去倒卖服装,或者去做别的买卖,几年下来,有的人发了,有的人变得一贫如洗。
那些年,可发一直在观望,一直在等厂里的效益好起来,直等到女儿已经上小学三年级,厂里在这一年宣布倒闭。那时候,可发觉得生活跟自己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
握着厂里一次买断的补偿款,他不知道自己还能去干什么?偏偏在这个时候,传来娘过世的消息。黄毛把电话打过来的时候,他问黄毛,我娘是怎么死的?黄毛说,回来就晓得了。
娘是在门前的明塘洗衣时,犯头晕,栽倒在明塘里。待村里人把她捞起来时,早就咽气了。十年的时间,村子里已经竖起好几栋楼房,黄毛告诉他,他也准备盖楼房了,苦于没有地基。安葬好娘,回到城里,可发已经空空如也,厂里买断工龄的补偿款,在娘的丧事里,用得所剩无几。
圆子到一家个体饭店去端盘子打下手,这之前,她一直犹犹豫豫拿不定主意,待到家里没有生活来源的时候,她却好像早已拿定主意似的。
可发没有选择,要么去工地上做小工,要么像厂里大多数工人一样。买一辆带马达的三轮“马自达”在县城的大街小巷载货拉客。可这两样可发都不愿意干,他觉得丢人带丢牲口,怎么着自己也是堂堂正正曾经的酱油厂里的工人,怎么去做那下三烂的行当?他才不干!自己是国家让他在乡村顶替父亲进县里的酱油厂做工人的,到工地去做小工,开“马自达”拉客,自己当初还不如在家里做农民。
黄毛来请他去乡下的新家喝喜酒,可发问他喝的什么喜酒?黄毛说,要死了,你把老家的屋基卖给我盖房子,你还装样?可发就更云里雾里了,说我什么时候答应把老家屋基卖给你盖房子了?黄毛说,你问你姐去。
可发安葬过娘,三天回家过一趟,一七回家过一趟,二七他就没有回去了。娘没了,工作也没了,圆子在饭店打工,请不动假,女儿在上学,还要接送,他走不开。姐姐是打过电话,可他没有办法走开。
也就是二七那天,黄毛跟姐姐商量,老屋没有人住了,不如把地基卖给他算了。姐姐没有马上答应,她说回家还要跟可发商量。黄毛说,不急,商量好了告诉我。
在姐姐回家做三七的时候,告诉黄毛,说她跟可发商量好了,房子和地基卖给他。黄毛喊来村里几个老人,与姐姐做了纸笔,把钱给了姐姐,不几天就开始动工盖起了楼房。
可发不信,打车去乡下问姐姐,住在邻村的姐姐说是有那么回事,是自己把房子卖了。姐姐说,父亲死了,你去顶职,到头来,娘过世,二七你就不回家了。父亲上班的时候,家里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是我跟娘做,你倒好,刚从学校回家,就去顶职,接着订婚结婚,家里所有的钱都为你准备的。你现在成了工人,成了城里人,我还在农村,还要苦做苦累,怎么挨,家里的老房子也要挨给我了吧?可发说。这么大的事情,你怎么着也要告诉我一声吧?姐姐说,钱就那么多钱,我家里儿女大了,我要钱用,你要钱没有,要命一条,随便你!
可发没有话说了,姐姐说到这个份上,他没有话说了。
回到家里,圆子跟他讨说法,他把姐姐的话拿来说,说钱我没本事要到,你要我的命,我马上给你!
圆子气得恨不能拿刀子捅他,说我怎么跟了一个窝囊废?可发受不了了,说你现在才晓得?你现在回头还来得及!圆子哭着说,你这样在家呆着坐吃山空,靠山山倒,不是窝囊废又是什么?
可发好像立马醒悟了,是啊,真的是靠山山倒。娘在世时,来过几次城里,厂里在要死不活的阶段.她虽然没有问过可发,凭父亲原来的老相识,她老人家应该心知肚明,可她就是不問,不说。她把家里的菜蔬,家里的白米,还有腌制好的腊鱼腊肉,往城里带,有时候,水都没喝一口,就回家了。假如娘还是依靠,现在娘走了,也就预示着,他的靠山倒了。
本来信誓旦旦不去工地,不去开马自达的可发,忽然之间买了一辆马自达跑起了拉客的营生。虽然圆子还时不时地提起老房子的事情,可发却打着哈哈装糊涂。他心里有时候觉得姐姐的话,不无道理。自己既然已经走出了乡村,干嘛还要跟姐姐争那老房子。有时候,他又恨姐姐,恨得咬牙切齿。不能怪圆子絮絮叨叨,自己做得不好,姐姐也没有姐姐的样子,他恨。
可发开马自达的那几年,城里的房子值钱,新住宅小区,遍地开花,几年下来,房价涨得让开马自达糊口的可发,简直瞠目结舌。县城一下子变大了,更变得豪华了起来。
原来还能说得过去的酱油厂宿舍,在四周新楼的衬托下,黯然失色,一下子就成了棚户区,贫民区。可发每天开着马自达从这里出去,开始还信心满满,可随着马自达数量的增加,交警开始管制,有时不走运,被交警拦住,罚单一开,就要几天白跑。可发遇见几回,回家牢骚满腹,有心无心地说,这样下去,还不如回乡下去种田。圆子呛他,说你回去窝都没有,怎么回去?
满街的马自达像蝗虫一般在大街小巷穿梭,既影响市容,也带来安全隐患,县里开始整治,分单双号上路,这样一来,可发的收入直线下降。他急,有天中午,趁交警下班,偷偷地上路,还没拉一个客人,却在路口被交警拦下了,车子拖到了交警队,几天后车子才拿出来,还罚了两百元的款。回到家,可发向圆子摊牌,我们回乡下种田去,这城里吃人,我们回乡下去吧!
圆子不理他,圆子说,你怎么这么没有出息?人家乡下人想着法子往城里钻,你倒好,一心一意要回乡下,你还是人吗?
可发没有办法,继续开他的马自达。不几天又被交警拦下了,他一不做,二不休,买上二斤苹果,尾随着那个拦他的交警,跟着到了他的家里。这次交警认真地打量起他来,问他什么意思?他说,你也辛苦,一年到头,站在马路上,就冲这点,我来谢谢你!这时.交警的妻子带着放学的儿子从楼道里上来了,可发就夸她的儿子长得帅。交警的妻子问男人,他是什么人?他自告奋勇地介绍,开马自达的。交警的妻子打量着他手里的苹果,开了门,热情地端来饭菜,喊他吃饭,他也不客气,拿起碗,就扒起了饭。
那天下午车子就拿出来了,并且,还一分钱没罚。那个交警再见到他,也不拦他了。可是,还有别的交警,他第二次故技重演时,被打了110,他被关了一个礼拜才出来。
这次回家,他回乡下的意愿愈加强烈,可是,圆子不答应,他没有办法。
县城美化环境,取缔了马自达,开始上人力三轮车,他只好把马自达换成三轮车。为了限制数量。从一开始就分单双号,可发就这么半死不活地蹬起了人力三轮车。这时的圆子,在饭店里,已经沦为洗盘子洗碗的角色,岁月不饶人,蹬人力三轮车,可发也觉得力不从心。这样的环境,也影响了读书的女儿.她读到初中毕业,就去读护理大专去了。
圆子没想到,自己洗盘子的事情,也竞争激烈,想想自己没打碎碗,没掉筷子,工作却无缘无故地没了,没了就算,明天再去找。回家好好烧两个菜慰劳男人,没想到可发的三轮车被扣了。
这叫祸不单行。
可发又要回乡下,回就回吧,女儿也不需要陪了,可发一再地要回,这次,圆子没有拦他。
可发回到草屋村,黄毛以为他是回来做客的,当听可发告诉他,他想回来生活时,黄毛怎么也不相信。要不是圆子在一旁帮腔,黄毛是怎么着也不会相信。黄毛相信之后,盯着可发瞅了半晌,先是满面愁容,然后,信心满满地告诉可发,你回来了,好!兄弟我有一口饭吃。绝对有你的。
黄毛当即表态,你乡下也没有房子了,就住在我家吧!一大片楼房,就黄毛一个人住,妻子儿子都出去打工了,黄毛吊儿郎当地在家里做着几亩田,过着饿不死、胀不坏的悠闲生活。
可发没有客气,就和圆子在黄毛家住了下来。他左看右看,发现村庄里没有小店,他想开一个百货店,带卖一些鱼啊肉呀豆腐之类的家常菜。黄毛提醒他,村子上面有这样的店,村子下面也有这样的店。可发说,对呀,草屋村几十户人家,不也能有这样的小店?
黄毛觉得开店不是小事,就说开店,只有小勇子家适合.因为他家在路边,位置处在村子中间。可发也是这么想的,可是,他一家人都在外面。黄毛自告奋勇,拿起手机就打,说了半天,黄毛把电话递给可发。都是从小在一起鸡巴拖泥灰长大的,小勇子当然没有话说,他半开玩笑地打趣可发,把他心目中的美人抢去了.可发说.你到现在还记着呢?小勇子在那头打哈哈。
小勇子门前,单独有一间瓦房,那是当年给他娘住的。他娘死后,那屋一直空着。黄毛把那间屋的木门撬开,一股霉味,扑面而来。
百货店开业的时候,生意好得让可发和圆子不敢相信。可发起早在县城菜市场批发肉鱼和乡下没有的菜蔬.摆到店里就卖掉了。那些日用品和香烟卖得也快,方圆几里地的人家,都来凑热闹,都来买一点鱼啊肉啊的什么的回家,就冲可发从县城回家这一点,也是不能空手回去的。
店里的生意虽然好,可发虽然起早贪黑,他还是拉着黄毛。出价每亩两百块钱,又包下了二十亩村里人不做的水稻田。开始种稻子。黄毛摇着头笑,说你回来不是过日子的,是来发财的。可发也笑,他没有回答他,他心里当然有他的想法。
小店的生意在好了一段时间以后。忽然间冷冷清清,没有顾客上门了。这还不算,就连本村子里的几十号人,也少有问津了。可发纳闷。把黄毛拉到店里喝酒,向他诉苦。黄毛也纳闷,想了半晌,他说你也不要急,我明个去打听打听。
黄毛走后,圆子就叹气,说这乡下的钱也不好挣,这叫条条蛇咬人。可发没有接话,一根烟接着一根烟,抽得屋里乌烟瘴气。
第二天中午,可发在田里回来,黄毛已经坐在店里等他了。黄毛告诉他,上面的店里和下面的店里他都去了,两家店像商量好了的,十块钱一包的红“黄山”,他们店里就卖八块五一包,拿一条八十二,猪肉比可发店里少一塊钱一斤。可发心里“咯噔”一下,他想他们是在照本卖,明着是在挤对他了。果不其然,黄毛说,他们公开地放大话,说城里跑到乡下来撒野,要你尝尝厉害。圆子的眼泪挂在脸上,说我们也没有得罪他们,这在做啥吗?
可发的菜是没法卖了,他告诉圆子,有生意来就做,没生意来就在店里呆着。圆子说,一天到晚卖不了两包香烟。这还叫生意吗?
可发说,这叫开店容易,守店难。
圆子说,你把田退了,我们回到城里去打工吧,绝对比这里强。可发瞪着她,他那有些凸起的眼睛,今天看上去有些凶巴巴的感觉。圆子是心里疼,自己的男人在城里不管是开马自达,还是蹬人力车,脸上都是白白净净的,像这样晒成古铜色,还从来没有过。
夏天到来的时候,黄毛和村里的一干人,喜欢到小店门前来乘凉,顺便唧唧喳喳地叨闲,晚上蚊子“嗡嗡”个没完没了,可发倒无所谓,圆子被蚊子叮上一口,要红上半天,越抓越痒。可发便背地里叫圆子呆在蚊帐里,圆子不答应,圆子说,那成么话了,我又不是娘娘!
有时候,黄毛他们聊到深更半夜才走,圆子坐在一旁,也坐到那个时候。可发觉得圆子跟自己太受苦了,圆子说,你说的什么话,黄毛的老婆带着儿子常年在外面打工,不也是受苦吗?我到乡下来,想通了,人生在世,都没有那么随心的,我答应跟你到城里,是准备去享福的,后来答应跟你到乡下,就是准备跟你来受苦的。可发浑身像被雷击了一般,颤抖了一下,这么多年的夫妻,他感觉头一次看清了圆子,一种叫做感动的东西,在他的周身,快速地流淌。
外面蛙声阵阵,可发发誓,一定要在乡下干出点样子来,不然,就对不起圆子。
田里的稻子收割后,稻子卖了三万多块,可发算了一笔账,虽然小店的买卖不是特别的好,但平时的小生意还是保住了家里的小用费,这样一来,卖稻子的钱就是赚的了。
好多年了,没有见过这么厚的一沓钱。可发觉得,他来乡下还是来对了。圆子却不这么认为,圆子说,这么多年,要是她和可发死心塌地地打工,一年照样也能存这么多钱。可发不服,说我来乡下才得到这么多钱,你还不承认!
圆子说,我说错了,是你的功劳,是你的功劳!
可发本来还有话说,圆子这么一说,他也不好说了,他下决心,一定要在乡下搞出点名堂。
第二年开年,他就打电话给小勇子,说他想养猪。电话那头的小勇子以为他就养几头猪,没说二话,就答应了。
可发把小勇子家门前的空地,利用起来,圈起了几间猪笼后,一次在县城买回几十头苗猪,放进了猪笼。黄毛来瞧热闹,村里在家的老老小小都来瞧热闹。
那些猪才到家还感觉不到什么气味,随着越来越大,味道也越来越重地飘荡在村庄的上空。猪们越来越大,草屋村上空的尿臊味猪屎的臭味也越来越浓重。小勇子家本来就住在村子的中间,这样一来,村子里的角角落落都弥漫着一股猪粪猪尿的气味。
小店的门前,是一条连接上面村庄和下面村庄的机耕路,走在路上和骑着电瓶车的外村人,在路过草屋村的时候,都愁眉苦脸地捂着鼻子。不久,草屋村得了一个外号,叫“猪屎村”。本来可发的小店还零零落落,多多少少地有一点生意,这样一来,一点买卖也没有了。没了买卖也好,圆子有时还拿着镰刀。到村后面的山上去割一担野蒿子回来给猪加餐。可发有一个计划,他养的是黑猪,不全吃饲料,平时吃一些野草野蒿子,这样,猪肉会带有农家自然的本色味道,价格一定不会低。
正当可发和圆子信心满满地料理着他们的猪宝宝时,黄毛走进了家门。可发见了黄毛,才想起来,黄毛有好长时间没有来他的小店了。可发连忙递烟。黄毛点着烟,面有难色,欲言又止的样子。可发心直口快,说你有话就说,没事。
黄毛就吞吞吐吐地说了,黄毛说,你养的这些猪,把我们村庄的名字都改了。可发不明就里。说没有啊。黄毛说,还没有,现在人家背后叫我们“猪屎村”了。可发莫名其妙,说自己还不晓得这事。黄毛说,你忙过了头,哪晓得呢?接着黄毛又告诉可发一件事,小勇子打电话给他,他马上就要回来盖楼房订儿媳妇,让他马上搬家。可发大惊,说这么大的事情。他怎么不打电话给我?再说,我盖猪笼养猪,是在电话里跟他说好了的呀?
黄毛说,他肯定要打电话给你,我是来先告你一声。
果不其然,黄毛走后不久,小勇子的电话就打来了。小勇子的说词与黄毛没有两样,可发央求他,就是搬,也得等他把这一朝猪养出笼,再说,这一朝猪,离出笼的日子,也就两个来月的时间了。小勇子说。不行,儿子已经把人家姑娘的肚子弄大了,没办法交差。
放下电话,可发像个傻子站在屋里发愣,马上搬家,他马上搬到哪里去呢?要是俩人还好办,这几十头猪,往哪里搬吗?
第二天,可发在村前村后转了一圈,没有找到能做猪舍的地方。回到家,小勇子的电话又打了过来,问他搬了没有?可发说,哪有这么快,正在找。放下电话,黄毛晃晃悠悠地又来了,黄毛说,你真要快点,小勇子现在怪我当初给你想了这么个主意。
那几天,可发焦头烂额,一边是小勇子穷追不舍的电话,一边是黄毛一天几趟上门的催促。他有时真的想把还在拔苗期的几十头猪卖了,可想来想去,这样卖了,不知要亏好多本钱。依圆子的主意。认亏也要卖,不能耽误了人家订儿媳妇。可发不舍得。圆子埋怨,小店开得好好的,你要养什么猪,这下怎么搞?可发说,你晓得个屁,我还不是为这个家好吗?圆子的眼泪在眼眶里打转,说你想好,我不想好吗?可发发现自己说漏嘴了,勾下头,低头一口一口猛烈地抽着烟。
黄毛来告诉可发,小勇子答应补偿他一些盖猪舍的损失。可发说,他在电话里也说了,关键是,我现在往哪里搬呢?
黄毛说他今天给他瞅了一个地方,养猪那是没的说的。可发问他在哪里。黄毛说,鸽子崂那里,不是有一大块空地吗?可发想了半天,想起来了,那里离村庄有三四里地,再说那里以前是坟场,这两年,修高铁,在那里取土,硬是把高低不平的坟山,推成平平展展的平地了。
可发犹豫,就算是平地,可那里以前是坟山,他记得的。黄毛给他算了一笔账,凭他离开村庄十多年了,现在哪里有他的一块地方?可发思忖了半晌,还真没有。黄毛又说,现在山上家家都栽了树木,哪个愿意把有树木的山地租给你养猪?可发想想,还真是困难。
没有办法的办法,可发决定搬到鸽子崂去。
黄毛给他张罗,没几天就盖好了一个简易的猪舍。就这样倒腾一下,可发算了笔账,这一朝猪是白养了。
他和圆子来到鸽子崂后,眼前除了几十头猪。一天一个外人也很难见到,之前这里的山崂里还有田.自从退耕还林后,这里山下和山上被茂密的树木连成一体,根本没有办法走路。听黄毛说,这块之所以是一块空地,是前面高铁取土修路,才来了推土机挖掘机推倒了树木,取走了黄土后,才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可发没有话说,他来乡下,本来就是想做点事情,才来的。这样一来,苦了圆子,他要是到田里去。他要是去镇上买饲料,圆子就一个人陪着几十头猪.怪孤单的。
圆子却说,我不孤单,有这么多猪陪我,我觉得热闹得很!
圆子在猪笼里捡猪粪,圆子在猪笼里用毛竹丫扎成的扫帚打扫猪笼,然后,拿着水管冲洗猪笼,圆子一个猪笼一个猪笼地清理,每一个环节,都做得有条不紊。这些都是可发在外面回家,亲眼瞅着圆子做的。这些原来都是可发每天做的事情,现在圆子做了,可发心里有些过不去,对圆子说,这些还是他来做。圆子手里拿着扫把,瞅着可发问,我做得不好还是怎么的?可发说,可好了,我是说,你一个女人家,做这个,体力吃不消。圆子听了,睁大她那好看的丹凤眼,说有你这句话就行了,你又要打扫猪笼,又要到田里去做庄稼活,吃不消的。
圆子又开始打扫另一间猪舍,站在那里的可发,望着她的背影,有些发蒙。
第一笼猪真的没有赚到什么钱,假如不是搬家,那是赚了,一笼猪,等于盖了两次猪舍,没有亏本就是好事了。卖了猪,可发到附近村庄的养猪户跑了一圈,那些养猪大户的投入,他望尘莫及,动辄几百上千头猪,不说管理,就是投入,他也望尘莫及。思来想去,他还是走农家养猪的路子,这样,投入不大,养好了,收效也还好。
养第二笼猪时,他胆子大了一点,一次买回一百多头猪崽,他要扩大一点了,他和圆子都或多或少有了一点经验了。
夏天到了,可發早晨起来,扛着锄头到田里转一圈回来,圆子一般乘着凉快,把一溜猪笼也打扫得差不多了,可今天回来,却发现圆子端坐在桌子边,在发呆。
可发走到她面前,她还是眼瞅着桌子。可发顺着圆子的视线,就见桌子上有一沓一百的红票子。可发心里晓得,家里没有这么多现金,他早晨才出去一趟,桌子上多了这么多钱,一定事出有因。可发这么想着时,就上前一步,将钱拿到了手里。圆子一惊。待她见眼前是可发时,才惊恐未定地捂着胸口说,吓死我了。
可发问,这钱哪里来的?
圆子说,这不怪我呵,是她硬要丢下来的。
可发愈加疑惑了,哪个她?他问。
圆子说,姐姐来了,刚走,你就回了。
圆子说,奇怪了,你早上刚出门,她就进门了.她拿来一万块钱,说是还当年她卖老屋给黄毛的那个钱。我不要,她强丢的。
圆子说,姐姐告诉她,她的两个儿子和小勇子一起做木匠,现在日子好得很,你回家的事,她一家人都晓得。姐姐还告诉她,你在小勇子门前养猪,是黄毛,还有村子里的人打电话给他,要他那么说的。说你的猪把村子的空气都带得臭不可闻,小勇子没办法才打电话给你。事实上,他家里的房子都不打算要了,准备在城里买房。
圆子说姐姐心里一直有愧,觉得对不起你。还说你要是在家门口不能呆了,就去她那里。
圆子说,她说着说着,就好像晓得你要回来似的,转身就走了,我还没有反应过来,她人已经不见了。
可发本来准备埋怨圆子几句,听圆子这么一说,他也有些发呆了。自姐姐擅自卖了家里的房子.他就再没有与她来往。这么多年了,想起这个事,他还有些生气,钱你要我给你,可是,你总要告诉我一声吧。
圆子想起什么似的,又告诉他,姐姐还说,她当年要房子的钱,一半是黄毛劝的,黄毛说可发已经是国家的人,吃香的,喝辣的。后来她听说你下岗开马自达,暗自哭过好多回。
可发说,不说了,打扫猪笼。
这时,太阳的强光,都已经跳进了猪笼里面。可发打开排气扇,与圆子打扫起猪笼来。他手里拿着扫把,心里还在琢磨着圆子刚才的话,他扫得心不在焉。
把猪喂好,夫妻俩到上午十点多才吃上早饭.圆子打趣地用筷子敲着碗对可发说,我都不晓得,我们现在吃的到底是早饭还是午饭。
也就是那天的晚上,圆子对可发说,你来乡下是来对了。来了我们才真正地认识了家里人,外头的人,我们要好好地吃苦,不然,人家会瞧不起我们的。
可发说,在城里我怕城里人瞧不起我。到了乡下,我现在又怕村子里的乡亲瞧不起我。真是左右为难!
圆子说,你说,现在村子里的人瞧得起你不?
可发支支吾吾,可发感觉,现在的村庄已经不是他当年在家里时的村庄,村庄里的人也不是当年村庄里的人了。他心里这么想,没有对圆子说。其实,他考虑这个问题,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他疑惑。
到秋天的时候,笼里的猪已经离出栏不远了。圆子早晨起来把猪笼打扫后,接着给它们喂食,然后骑上三轮车,到附近的山上去砍野蒿子给猪吃零食,拿可发的话说,这样能改善猪肉结构,卖得好价钱。
那天圆子砍好一三轮车野蒿子,准备回家,就见不远的高铁柱子上,一群建筑工人正在架桥。圆子开始砍野蒿子的时候,他们就在架,她砍好一三轮车时,他们还在架桥,看样子,是两头并拢。圆子好奇,来山上这么久了,从高铁筑柱子开始,现在都开始架桥梁了,她一次都没到近前瞅过,真的没时间去。今天她想到近前去瞅瞅他们怎么架桥梁,想自我放松一下。
圆子骑着三轮车,路边的秋阳从树上洒下,在她的肩膀上一跳一跳的。奇怪的是,她到了桥梁的下面,不到几分钟,桥梁就合龙了。上面的工人调侃道,没的母的来,还真对不上。
圆子笑,她为今天看到了稀奇,她为自己的到来,还能给那些出门在外的男人提起精神。
她回家把刚才的见闻说给可发听,可发说,等我们发财了,我带你坐高铁,出去玩。
圆子鼓起嘴巴,说你不发财,还不带我出去玩了?
可发顿了一下,连忙纠正,说,不管发不发财,都带你坐高铁。行了吧?
圆子笑。然后说,这还差不多!
第二天早晨,可发起来上过茅厕,准备去田里了,圆子还没起来,可发就大声地喊,没有声音。可发到床上去拉圆子,发现她浑身硬邦邦的。可发预感到了不妙,用手在圆子的鼻子旁试了一下,这才发现,圆子已经没有一点气息。可发圆子圆子地喊,可圆子像睡着了一般,就是不搭理他。
黄毛来了,村子里在家的人都来了。
把圆子送上山后,可发人瘦得认不出是可发了。黄毛劝他,村子里人劝他。黄毛号召村子里的人,轮流来可发的猪场打扫猪舍,给猪喂食。
可发的猪出栏,已经是中秋时节。效益是不错,可是。圆子没了。黄毛把可发拉回家,劝他好好休息一下。村子里像接春酒一般,在家里的人家,都排着队。接可发吃饭喝酒。
那一年,田里的收成也不错。可是,錢却揣在可发一个人的兜里。可发到圆子的坟前,对圆子说,好多年了,没有见这么多钱,现在有了,你却睡在了这里。
黄毛曾经神神秘秘地告诉他,本来那个坟场就不该去养什么猪,村里人都打过那里的主意,结果,都放弃了。黄毛又说,到坟场也就算了,圆子要去瞅什么高铁桥,听说,那些工人架了一个上午的桥梁,就是对接不起来,圆子去了,正好做祭奠。可发不相信他的鬼话,圆子的猝死,是急性心肌梗死导致的,他问过医生。可是,他懒得跟他辩。
可发对圆子说过,他要陪着她在这个山上。因为圆子就埋在鸽子崂对面的山上,他在养猪,就是等于在陪她。
开年后,他打扫猪场,准备去买猪崽回来,他正在忙乎,黄毛来了。黄毛问他,还能养猪?你总要去买饲料吧,家里哪个喂猪?你一个人要是有个头疼脑热,那些猪哪个来喂?
黄毛走后,可发觉得黄毛说得在理,一个人,做这个事实在没有办法。
不能养猪,可发打算就种那二十来亩田,能将就过日月,能每天陪着在对面山上的圆子,他就心满意足了。他于是打算今年该用什么样的品种。好提高产量,提高效益。黄毛又来了,告诉他一个消息,说村里来了种田大户,出价每亩六百,村里把田给他做的人很为难,让他带话,看在本乡本土的份上,可发要做,让他一百一亩。
可发说让他想想,过两天给他答复。
可发不要想的,种田大户哪怕田里不赚钱,就享受国家补贴一项,也是一笔不菲的收入,他怎么比?
黄毛过两天来听答复,猪场的门是开的,没有见到可发的影子。他到圆子的坟上,只见一堆火纸还没有散尽。黄毛大声喊可发的名字,没有回音,他打他的电话,电话已关机。
黄毛来了好多趟,一直没有可发的影子。他去了一趟酱油厂,那里的人说,可发没有回来过。黄毛想去可发女儿读书的学校,他怕找不到他女儿。
可发去哪里了?一直没有消息。
责任编辑:王方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