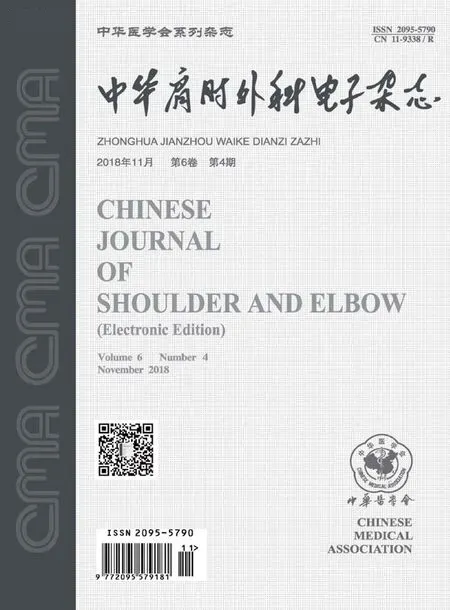单纯肱骨大结节骨折的诊疗研究进展
曾浪清 陈云丰 曾路路 蒋煜文 喻伟 詹鹏
肱骨近端骨折在临床上较为常见,约占所有骨折的5%,且常合并肱骨大结节骨折。然而单纯肱骨大结节骨折(isolated greater tuberosity fracture,IGTF)在临床上则相对少见,IGTF约占肱骨近端骨折的11%~19%[1-3],其中盂肱关节脱位合并大结节骨折约占15%~30%[1-2]。相比其他肱骨近端骨折,IGTF具有年龄较轻,男性患者比例高,常合并盂肱关节脱位及肩袖损伤等特点[1]。由于IGTF在解剖、损伤机制、骨折分型及治疗原则和治疗方法等方面均具有其独特性,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对该损伤进行了大量研究。本文针对IGTF的解剖、损伤机制及骨折分型、临床诊断和治疗进展等方面作一综述。
一、肱骨大结节解剖学
肱骨大结节为肱骨头外侧的突起结构,其顶点较肱骨头顶点低6~8 mm。包括上、中、下三个面,分别位于大结节顶部、后上及后下方,且分别有冈上肌、冈下肌及小圆肌肌腱附着[4]。与过去的认识稍有不同,Mochizuki等[5]的研究表明冈上肌肌腱止点位于大结节上表面的前内侧,有时还包括小节结最近端的一部分;冈下肌肌腱止点位于肱骨大结节上表面的前外侧及整个大结节中面部分。肱骨大结节骨折时,冈上肌与冈下肌上半部分的收缩力使大结节向上移位,而冈下肌下半部分与小圆肌收缩力使大结节向后移位。对上述结构的了解,有助于我们评估骨折损伤机制和指导术中骨折块的复位。
肱骨头的血供来源于旋肱前动脉和旋肱后动脉的分支。2010年,Hettrich等[6]的解剖学研究认为肱骨头的血供主要来源于旋肱后动脉分支(占64%)、其次为旋肱前动脉(占36%)。然而,2012年Maritsa等[7]的解剖学研究结论却相反,作者发现肱骨近端前半部分及大部分后半部分的血供来源于旋肱前动脉的终末支——弓状动脉,弓状动脉的分支经过冈上肌、肩胛下肌止点进入肱骨头,旋肱后动脉分支则经过冈下肌、小圆肌止点进入肱骨头。目前,尚无证据表明IGTF会引起肱骨头血供障碍。
IGTF常并发外周神经损伤,尤其是合并盂肱关节脱位的骨折[8]。神经损伤多为牵拉伤,大多数患者在伤后数月内恢复[8]。其中腋神经从臂丛后束发出,穿过四边孔、绕肱骨外科颈横向走行于三角肌深面,距肩峰下约6.3 cm、大结节顶点下约3.5 cm[9],是最常见外伤性或医源性神经损伤。这提醒我们在术中操作时需注意保护该神经,避免医源性损伤。
二、损伤机制及骨折分型
目前比较公认的IGTF的损伤机制:①肩袖肌收缩、牵拉导致撕脱性损伤,骨折向上或后上方移位;②向下的直接暴力,或外伤时上肢极度外展、大结节与肩峰撞击导致的压缩性骨折(骨折向下移位),Bahrs等[10]的研究发现多达25.2%的IGTF移位为向下移位;③盂肱关节前脱位时盂缘的剪切力导致大结节骨折[10-11]。由于肩关节本身结构复杂、活动范围大,患者受伤瞬间可能同时有肩袖的紧张收缩、骨性结构的撞击等多种暴力参与。因此其具体损伤可能由上述多个因素共同起作用,而非单一的损伤机制所致。
目前,临床常用的肱骨近端骨折分型包括Neer分型及AO分型。根据Neer分型,移位<1 cm的IGTF属一部分骨折,移位≥1 cm或成角≥45°的IGTF属二部分骨折(包括合并盂肱关节脱位的骨折)。根据AO分型,IGTF属于11A1型,进一步细分11A1.1(移位<5 mm)、11A1.2(移位≥5 mm)、11A1.3(合并盂肱关节脱位)。上述骨折分型均基于骨折的形态和移位程度,且均非专门针对IGTF的分型,对理解其损伤机制、指导临床治疗及判断预后的价值较为有限。Mutch等[12]于2014年总结了199例IGTF、其中55例(28%)合并盂肱关节脱位,并根据IGTF的损伤机制提出了新的骨折分型:I型为撕脱型骨折(占39%,77例),因肩袖肌的收缩暴力所致,骨折块较小、骨折线水平;II型为劈裂型骨折(占41%,81例),因盂肱关节脱位或半脱位时关节盂前缘的撞击所致,骨折块较大、骨折线垂直;III型为压缩型骨折(占20%,41例),因盂肱关节前下方脱位时关节盂下缘的撞击或肩部极度外展时肩峰的撞击所致,骨折向下移位、或伴有塌陷。其中III型骨折合并盂肱关节脱位的比例为46%(19/41),明显高于I型(21%)和II型(25%)骨折;III型骨折移位>5 mm的比例为7%(3/41),明显低于I型(35%)和II型(38%)骨折;III型骨折采取手术治疗的比例为7%,明显低于I型(20%)和II型(28%)骨折。Mutch等[12]认为对于骨折块较大的劈裂型骨折较适宜采用钢板螺钉内固定治疗,而对于骨折块较小的撕脱性骨折则更适合采用张力带内固定治疗。该分型系统对理解IGTF的损伤机制及指导临床治疗更为实用,但仍需大样本、多中心的临床对照研究结果来支持。
三、临床诊断
1.临床检查: 当患者因肩部外伤就诊时,首先应详细采集病史以明确患者既往病史和受伤机制。患肩主要临床表现是肿胀、疼痛、活动受限,有时可见瘀斑,伴盂肱关节脱位的骨折还有方肩畸形等。此外还需着重排除是否合并腋神经、臂丛神经及重要血管的损伤。其中腋神经损伤是最常见的合并伤,腋神经损伤可通过评估三角肌的等长收缩和其外侧区的皮肤感觉功能来判断。如果腋神经损伤3~6周仍未恢复,则有必要进行肌电图检查[11]。合并血管损伤较为罕见,但由于肩部侧支循环丰富,外周动脉搏动并不能排除肱动脉损伤,需要结合患肢是否存在感觉障碍、苍白或紫绀、血肿等其他体征来综合判断,必要时进一步行多普勒超声或血管造影检查[11]。
2.影像学检查:常规的影像学检查是拍摄肩关节创伤系列片(包括盂肱关节前后位、肩胛骨“Y”位及腋位片),但骨折移位情况往往在外旋位肩关节正位X线片更明显[13-14],而向后移位则在肩胛骨“Y”位X线片更明显[11]。CT检查对骨折的形态、移位程度及合并隐匿性骨折等情况更能准确地评估,更有助于术前计划,故目前应用越来越多。此外对于合并脱位、或肩关节正位X线片表现为“向下移位”的骨折,合并隐匿性肱骨解剖颈或外科颈骨折的比例较高,建议常规进行CT检查。Atoun等[15]的研究发现19例IGTF合并盂肱关节脱位的患者急诊镇静下进行手法闭合复位,复位后有5例出现医源性肱骨解剖颈骨折。吴剑宏等[16]对24例肩关节正位X线片表现为“向下移位”的肱骨大结节骨折进行分析及CT检查发现:10例患者肩关节正位X线片上发现轻微移位的肱骨解剖颈骨折,而CT检查却发现多达23例患者存在肱骨解剖颈骨折;作者认为此类骨折容易漏诊轻微移位的解剖颈骨折,实为外翻压缩性肱骨近端骨折(AO分型11B1.1型),并非IGTF。MRI非常规检查,但对于评估隐匿性骨折、非移位骨折或合并肩袖损伤较有意义。超声检查方便灵活、便宜,最大优势在于可动态下评估肩峰下撞击及肩袖损伤,也可评估血流、肩袖脂肪变性或萎缩[17],尤其适用于陈旧性损伤。
3.关节镜检查: 肩关节镜不仅可以镜下准确地判断伤情,还可以同时治疗骨折、合并的肩袖及关节内其他损伤。对于无移位或轻度移位的骨折,非手术治疗5~6个月后仍残留患肩疼痛及僵硬的患者需要进一步进行关节镜检查或治疗[18-19]。Kim等[19]的研究总结了23例此类患者,MRI造影检查仅11例患者有肩袖损伤的阳性表现,而术中镜下却发现23例患者均存在骨折部位、肩袖肌止点的部分撕裂。
四、临床治疗
(一)非手术治疗
无移位、轻度移位(<5 mm)的IGTF采用非手术治疗,患肩早期制动2~3周、之后进行被动活动、6周后进行主动活动及逐步力量锻炼,能取得良好的临床疗效。Platzer等[20]采用非手术治疗135例移位<5 mm的IGTF患者,平均随访3.7(2~20)年,97 %的患者功能恢复良好;作者发现移位3~5 mm的患者较移位<3 mm患者功能略差,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且合并盂肱关节脱位对功能恢复并无影响;女性患者功能恢复优于男性患者,年轻患者功能恢复优于老年患者。Rath等[21]回顾性分析69例非手术治疗、移位<3 mm 的IGTF患者,平均随访31(26~41)个月;作者发现患肩疼痛及活动受限平均持续8.1个月,但所有患者均获得良好的恢复、末次随访时平均Constant评分为95分。Rouleau等[17]回顾性分析43例、非手术治疗的IGTF患者,骨折移位平均为2.2 mm(-9~22mm)、平均随访2.4(0.8~6.8)年;作者采用超声评估肩袖、肩峰下撞击等情况,发现16%的患者伴有全层肩袖撕裂、57%的患者合并肩峰下撞击征,且大结节残余移位程度、肩袖撕裂或萎缩与功能呈反比。非手术治疗IGTF常见的并发症为肩关节僵硬、肩峰下撞击征[22],大部分创伤后肩关节僵硬患者可通过功能锻炼、理疗等非手术治疗治愈[11]。对于远期残留患肩疼痛、僵硬的患者,有必要进行MRI或超声检查评估是否合并肩袖损伤或变性,部分患者需要进一步行关节镜下松解等治疗[11]。
(二)手术治疗
1.手术指征:手术治疗的目的是解剖复位骨折、恢复肩袖的完整性及早期功能锻炼,预防畸形愈合、肩关节僵硬及疼痛、肩袖功能改变[11]。IGTF的手术指征存在争议,1970年Neer主张对骨折移位>1 cm的患者进行手术治疗[23];Platzer等[24]的回顾性对照研究证实对于移位>5 mm 的IGTF,手术治疗患者的功能结果明显优于非手术治疗的患者,因此作者建议采用手术治疗移位>5 mm 的IGTF;而Park等则建议对骨折移位>5 mm 的年轻患者、移位>3 mm的运动员或经常需上举肩关节的体力劳动者进行手术治疗[25]。Bono等[26]的生物力学研究表明大结节的移位会改变肩关节外展肌力的平衡;作者发现外展0°~90°,大结节向上移位5 mm时、三角肌外展肌力增加16%,大结节向上移位10 mm时、三角肌外展肌力增加27%,大结节向上、后移位10 mm时、三角肌外展肌力增加29%。目前国内、外学者较为公认的手术指征为移位>5 mm[27-30]。此外,手术治疗还需综合考虑骨折的形态、骨的质量、术者的经验以及患者的年龄、受伤前患肩的功能情况、合并伤等个体因素。
2.手术入路:IGTF的手术入路主要有3种:①传统三角肌-胸大肌入路:该入路切口较大、难以显露大结节后方,对于后上方移位的骨折,术中可通过牵拉穿过冈下肌及小圆肌肌腱止点的缝线或骨钩间接复位骨折;②肩峰下经三角肌入路:该入路需要在肩峰外取约4~5 cm纵行切口、纵行劈开三角肌显露骨折部位,该入路能够方便地显露大结节前方及后方,当骨折块较大、需要显露外科颈时,需注意解剖和保护腋神经(约位于切口远端、三角肌深面)[11];③经皮或关节镜下操作,手术创伤小、切口更美观,对于合并盂缘骨折或小结节骨折等其他损伤,关节镜具有可同时微创内固定治疗的独特优势[31-32]。切开复位时应注意保护周围骨膜等组织,避免为了显露骨折线而过多地解剖、剥离周围组织,以减小对肱骨头血供的破坏。
3.固定方式:IGTF的内固定方式多样,包括:肱骨近端解剖型钢板或微型钢板固定、松质骨螺钉固定、钢丝张力带及缝线或锚钉缝合固定,尚无金标准。(1)松质骨螺钉固定:松质骨螺钉固定是治疗IGTF的常用方式。对于骨折块较大、且非粉碎的骨折,可采用闭合复位或关节镜辅助下、微创经皮螺钉固定(尤其适用于年轻、骨的质量较好的患者)。对于骨折块粉碎、骨质疏松的患者,螺钉固定时存在较高的医源性骨折风险,导致大结节进一步粉碎或移位[11],因此应避免单独采用螺钉固定;对于此类骨折,可将螺钉与缝线相结合进行固定(螺钉固定大的、主要骨折块,缝线绕过螺钉尾部缝合固定小的、肩袖肌止点的骨折块),或将螺钉置于骨折线远端作为缝线的锚着点,进一步采用缝线张力带进行固定。(2)经骨缝线固定:经骨强力缝线缝合固定是较为理想的固定方式[11],对于骨质疏松、粉碎性骨折亦适用,且避免了金属内植物排异反应及二期取出等问题。缝合技术多样,如“8”字缝线张力带、经骨间断缝合及经骨“8”字缝合等等。术中应避免切除肩袖肌止点的撕脱骨折块,利于肩袖肌止点的愈合[33]。Dimakopoulos等[14]采用切开复位、5号爱惜邦不可吸收性缝线经骨缝合固定34例伴盂肱关节脱位的IGTF患者,平均年龄52.8(18~84)岁、平均随访4.8(2~10)年、盂肱关节脱位复位后骨折平均移位1.6(1.2~2.9)cm,其中16例伴肩袖纵向撕裂、3例伴冈上肌肌腱全层撕裂及2例冈下肌肌腱全层撕裂;末次随访时骨折残留移位均<3 mm,平均Constant评分88.4(40~100)分、优良率为96.9%,无复发盂肱关节脱位。Platzer等[24]则采用切开复位经骨缝线缝合固定治疗30例、闭合复位经皮空心螺钉固定治疗22例IGTF,骨折移位均>5 mm、平均随访5.5(2~11)年;末次随访时两组患者Constant评分平均分别为87.2分、81.6分,切开复位缝线缝合固定的疗效略优。上述研究表明采用切开复位经骨缝线缝合固定治疗IGTF能够取得良好的临床疗效。(3)钢板螺钉固定:近年来钢板螺钉内固定逐渐被运用于治疗IGTF,具有可有效压住骨折块、应力分布较广及固定稳定性强的优势,尤其适用于劈裂型骨折。Gillespie等[34]与Park等[28]均采用肱骨近端锁定钢板(Zimmer公司)治疗了11例IGTF,均取得了良好的临床疗效;但由于肱骨近端锁定钢板的体积较大且较厚、钢板放置偏近端则容易导致肩峰下撞击,远端置于肱骨外科颈及其下方,需要较大的切口、剥离多、创伤亦较大,因此此内固定方式并非理想的选择。而采用微型钢板内固定治疗则弥补了肱骨近端锁定钢板创伤较大的问题,是近年来的研究热点;微型钢板体积小而薄、低切迹、可用2.4~2.7 mm螺钉固定小的骨折块,能取得良好的临床疗效。陈强等[29]采用足部X形AO锁定钢板、经三角肌前中束间隙入路治疗19例IGTF,平均随访17.2个月、平均骨折愈合时间为9.4周,末次随访时Constant评分为(90.6f4.0)分、优良率达94.7%;作者认为该钢板可更加有效地固定粉碎的IGTF,也适用于骨质疏松性骨折。马骏等[35]则采用Y形微型锁定钢板内固定治疗6例IGTF,平均随访19.8个月,末次随访时Neer评分平均91.2(89~95)分。Popp等[27]则采用网格状的Litos跟骨板修剪成适应肱骨大结节外形的“Bamberg”钢板、治疗了10例IGTF患者,取得了良好的临床疗效,术后6个月Constant评分平均94.2(91~98)分。Bogdan等[36]则采用网格状钢板,修剪后用于治疗IGTF。上述学者所用微型钢板均非肱骨大结节解剖型钢板,足部X形及Y形微型锁定钢板较窄、对大结节骨面的覆盖有限,难于直接覆盖、稳定固定较为粉碎的IGTF;粉碎性IGTF合并冈上肌止点撕脱损伤的比例高达91%[28],上述微型钢板均无缝合孔,修复合并的肩袖肌止点损伤时,需在钢板固定前将缝线穿过钢板钉孔之间以利于缝线附着或者额外采用锚钉修复,术中操作不便。为了解决上述问题,上海第六人民医院陈云丰教授在总结国人肱骨近端骨骼解剖形态特点的基础上,设计了一款新型的肱骨大结节解剖钢板(图1),该钢板较薄、上缘低切迹设计呈斜形与肱骨大结节上缘的形态相匹配,且兼有缝合孔,利于术中克氏针定位或为缝线提供附着点;虽然章伟等[37]的生物力学实验研究表明该钢板固定IGTF具有良好的稳定性,但是其临床实用性及疗效仍有待进一步研究。(4)缝合锚钉固定:缝合锚钉治疗IGTF可在有限切开或肩关节镜下进行手术操作,尤其适用于撕脱型或合并肩袖撕裂的骨折。肩关节镜下手术学习曲线较长,但具有切口及创伤小、可同时治疗合并的关节内其他损伤、康复快及黏连发生更少等优点。常用的缝合锚钉技术包括单排锚钉缝合[38]、双排锚钉缝合、双排锚钉桥式缝合[39-40]等,均能获得良好的临床疗效;桥式缝合的缝线交织成网状,能够均匀将骨折块压向骨床更有利于术后骨折块复位的维持及愈合。2015年,McLaughlin-Symon等[41]介绍了一种新的锚钉缝合技术——Trapdoor技术:①骨折复位后,于大结节近端、肌腱骨交界处往肱骨头拧入2枚带Orthocord缝线的锚钉,②两枚锚钉各取一根缝线打结、使之横于大结节近端表面,形成一“桥式”结构,为大结节近端提供支撑压力,③再于大结节骨折线远端拧入Versalok固定锚钉(三个锚钉形成三角形结构),将剩余缝线卡入固定锚钉、拉紧固定;作者随访发现,85%患者术后6个月即可达到与健侧肩关节相当的活动度。Li等[42]于2017年介绍了一种新的、改良桥式缝合技术,即在常规双排锚钉桥式缝合的基础上,两枚锚钉间取缝线打结、使之横跨于大结节近端表面(类似Trapdoor技术),该技术优势是固定线对大结节的接触和固定面积更大。(5)各种固定方式的生物力学研究:近年来国内外学者针对上述各种IGTF内固定方式的稳定性做了大量的生物力学研究。Braunstein等[43]对3组IGTF的尸体骨标本(每组7例)进行生物力学测试,分别采用钢丝张力带、2枚松质骨螺钉及经骨缝线固定,结果发现力学稳定性依次为钢丝张力带、2枚松质骨螺钉、经骨缝线。Lin等[44]则通过生物力学实验比较了双排锚钉缝合、双排锚钉桥式缝合及2枚松质骨螺钉固定IGTF的力学稳定性,发现两种锚钉缝合技术在大结节移位3 mm、5 mm及内固定失效载荷均明显大于2枚松质骨螺钉技术;双排锚钉桥式缝合稳定性略优于双排锚钉缝合,前者在大结节移位3 mm载荷明显大于后者,但两者在大结节移位5 mm及内固定失效载荷方面无差异。章伟等[37]则通过生物力学实验比较了大结节解剖钢板、钢丝张力带及2枚松质骨螺钉固定IGTF的力学稳定性,发现固定稳定性依次为大结节解剖钢板、钢丝张力带、2枚松质骨螺钉。钟树栅等[45]的生物力学研究则发现可吸收线缝线与双锚钉缝线(均采用“8”字形固定)固定IGTF稳定性相当,均明显优于2枚松质骨螺钉固定。Gaudelli等[46]针对劈裂型IGTF,比较了“8”字缝线张力带、双排锚钉桥式缝合及锁定钢板固定的力学稳定性,发现锁定钢板固定的稳定性最佳、其次为双排锚钉桥式缝合固定、“8”字缝线张力带最差。Brais等[47]则针对撕脱型IGTF,比较了“8”字缝线张力带、双排锚钉桥式缝合及经骨缝线固定的力学稳定性,发现双排锚钉桥式缝合固定稳定性略优于经骨缝线固定,但两者均明显优于“8”字缝线张力带固定。上述研究表明:对于IGTF,钢板、双锚钉缝合及钢丝张力带固定具有较佳的力学稳定性,经骨缝线固定力学稳定性适中,而缝线张力带及单纯螺钉固定的力学稳定性较弱。上述研究结果为临床治疗IGTF提供了生物力学方面的参考,但由于上述研究的IGTF模型均为简单骨折,对于粉碎或合并肩袖肌止点损伤的骨折,临床医生还需结合个体实际情况采用合适的固定方式。

图1 肱骨大结节解剖钢板固定示意图 (A);该钢板固定肱骨标本的照片,其上缘与大结节上缘(蓝色虚线)的形态相匹配,兼有缝合孔(红色箭头)(B)
(三)陈旧性IGTF的手术治疗
无移位或轻度移位的IGTF,非手术治疗5~6个月后仍有持续性疼痛及活动障碍的患者,应考虑合并有肩袖肌止点的撕裂,需要进一步关节镜下清理、修复肩袖损伤及肩峰下减压等治疗以改善症状[19,48]。Kim等[19]采用肩关节镜清理、修复治疗了23例IGTF非手术治疗6个月后肩关节慢性疼痛患者,骨折平均移位2.3(0~4)mm、平均年龄39(24~61)岁;镜下发现所有患者均存在骨折部位肩袖肌止点部分撕裂,平均随访29(22~40)个月,术后疗效良好,其中有19例患者恢复至伤前的活动水平,平均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肩关节功能评分从术前的13(7~20)分改善至32(25~35)分(P=0.001),优良率86.96%。Park等[49]关节镜下桥式缝合固定治疗15例隐匿性IGTF(初次就诊时误诊或漏诊),外伤后肩部持续疼痛4(1.5~12)个月、经理疗6~12周症状无改善,复诊发现其中8例骨折无移位或轻度移位、7例骨折移位>5 mm;术后平均随访24(14~36)个月,患者功能明显改善,平均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肩关节功能评分从术前的15分改善至33分,优良率达93.3%。
畸形愈合或不愈合的IGTF通常移位较明显,后方移位影响肩外旋功能、向上移位则容易导致肩峰下撞击影响肩外展功能,此外还容易导致肩袖肌脂肪变性及萎缩、磨损或撕裂[50]。畸形愈合的治疗方式需根据骨折块的大小和移位程度来选择:症状明显、移位<5 mm的骨折可切除多余的骨质、锚钉重建肩袖肌止点或采用肩峰成形术治疗;移位>5 mm或骨折块较大则可采用截骨后复位内固定术治疗[51]。骨不愈合通常需要行骨折端清创、缝线或锚钉缝合固定等治疗。Martinez等[52]采用肩关节镜治疗了8例IGTF畸形愈合患者,骨折移位为5~10 mm、平均外伤致手术时间9(7~12)个月,患肩均有疼痛、活动受限及肩峰下撞击征;术中予肩峰下滑囊清理、分离大结节骨块附着的肩袖肌肌腱,然后刨刀重塑大结节骨面、使之新鲜及光整,最后双排锚钉缝合重建肩袖肌止点;经过平均18(12~24)个月的随访,患肩活动度明显增加,平均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肩关节功能评分从术前的11.1(9~14)分增加到30.2(25~35)分。Amroodi等[50]则采用手术治疗12例漏诊、骨不连的IGTF,骨折移位均>1 cm、平均受伤至手术时间5.3(2.5~10)个月;手术采用肩前上方切口、三角肌中1/3止点处肩峰截骨入路,骨面清创、松解骨块后采用强力缝线经骨缝合固定;术后平均随访36.2(25~51)个月,骨折均在术后6个月内愈合,患肩功能明显改善,平均Constant评分术前为29.83分、末次随访时为86.25分,平均VAS疼痛评分术前为6.5分、末次随访时为1.3分。上述研究表明症状明显的陈旧性IGTF采取合适的手术治疗能取得良好的临床疗效。
综上所述,IGTF是肱骨近端骨折较为少见的骨折类型,常伴盂肱关节脱位及肩袖损伤。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对IGTF的损伤机制及分型、诊断及手术治疗等方面进行了大量研究,取得了较大的进展。新的、基于损伤机制的IGTF分型系统对理解其损伤机制及指导临床治疗具有一定的实用意义。非手术治疗适用于移位<5 mm的骨折;对于移位超过5 mm的骨折宜采用内固定手术治疗,术式多样、尚无金标准。对于疼痛等症状明显的陈旧性IGTF采取合适的手术治疗亦可获得良好的临床疗效。临床上需综合骨折的类型、骨的质量、术者的经验、患者的年龄及自身要求等因素采取合适的治疗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