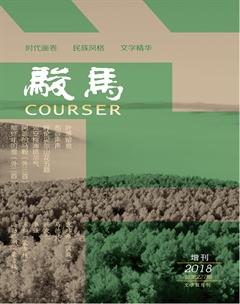冬夏
杨忠文
冬
1960年的冬天,特别寒冷。天总是阴沉着脸,整日不见太阳,空气中欲动非动、欲飘非飘、欲静非静地飘浮着一种灰白色的冰雾,地面上白毛风嘶嘶地吼叫着,卷起阵阵雪龙,翻江倒海似地旋转着,贴着地面闪电般地疾驰而过。
这是我全家人从山东到呼伦贝尔所经历的第一个寒冬,一来不知道酷寒的滋味,没有越冬经验,二来没有条件筹备越冬的物资。这个时候,还是物资计划供应时代,市场上是不能随意买到所需物资的,同时也没有资金购买生活必须品。
其实,“秋分”过后,我就感到了在这里过冬天将会是一个挑战。纷纷扬扬的雪花飘落在田野、草原、森林之间,时下时化,大地成了黑白相间自成图案的巨幅地毯。每日的早中晚温差较大,“早穿棉,午穿纱,围着火炉啃西瓜”的说法也适用于此。这时人们的穿着纷杂多变,一早一晚有穿棉衣皮衣的,中午还有穿夹衣单衣的,人们的穿着打扮会因年龄、工种、时间而异。市场等公共场合的人群衣着艳丽多姿。“立冬”之后进入冬季的严寒季节,冰封山河,一片银白,外出生产作业的人们,特别是一些老年人便头戴狗皮帽子,身穿反毛皮袄,脚蹬毡疙瘩,手戴棉皮手套,胡须眉毛凝霜结冰,俨然是一个个圣诞老人。
“秋分”节气一过,制砖生产只得停止,从事制砖工作的工人只好改行从事其他季节性生产的行业。厂部考虑我年轻,人口负担重,生活困难,从照顾我增加收入的角度考虑让我临时从事编织工种,主要是白日去河套割柳条,割小叶章草,晚上还可兼职业余文化教育,教职工汉语拼音,可多得部分补助工资。
“三九”天去河套里割条子割草,这可真是个叫劲儿的活。大兴安岭上的冬季是夜长昼短,夜间零下四十多度,每天早晨五点起床,吃完早饭后天还不亮,摸黑走十几里路来到河套,大地一片沉寂,只有被惊醒的野鸟从雪地中飞起,略显严冬之晨的生机。
河套里弥漫着大雾。远山近水融成白茫茫一片,树枝上草叶上到处都凝结着雪挂,银装素裹,静谧肃穆。这是一天之中最冷的时刻,人在河套里,有如步入雪窖冰天。八点左右,太阳从云霭中悄悄露出橙黄色的脸,空旷原野上的雪雾才渐渐变淡、变稀,显露出村镇和森林的轮廓。
大兴安岭河套里生长的红柳,多是在河边丛生,柳枝柔软易弯曲,适宜编织家具;小叶章草却喜欢生长在河边地上的塔头墩上,高一米多,草杆挺拔硬结,草叶有涩刺,刺手可破,柳条冻结硬如钢条,表面凝霜,手一握霜雪立即融成水,攥草和柳条的左手,握镰刀的右手相互交替揉搓,疼如猫咬。干这活不能戴棉手套,单手套一会就湿透,冻得硬如铁皮,只得干干停停。
这年没有供应棉鞋,我只好脚穿布袜,外用棉布缠裹,再穿上单鞋,在冰雪里每天站立八九个小时,冻得双脚疼痛难耐,只得两脚相击,以碰撞的方式以防冻伤。妻子每天特意给我烙上一个玉米面大饼子,早上出门时让我揣在怀里,中午充饥。可是每到中午,从怀里掏出大饼子,早已冻成了石头蛋子一般,在背风处一啃,一道白色碴口,又一啃又一道碴口……
夜长昼短的冬日,午后四点多钟已是落日余晖、晚霞涂红了西天的时候了。我们割了一天柳条子和小叶章的工人,回家时每人不会空手,每人捆上四捆柳條,打成人字形一个大捆,双肩一扛约有百斤重的负担压在自己身上。原本是冻得瑟瑟发抖的我们,不多会儿就会汗流浃背、衣衫湿透,待行十多里路回到家时已是大汗淋漓,像从蒸笼里出来一般,这才结束一天的劳动,每捆柳条可以获得一角五分的现金报酬,这是对编织工人的额外奖励。一般的工人到此就是一天劳动的结束,我每周一、三、五晚饭后,还要按时赴约去夜校辅导大家的汉语拼音学习。
领导对我的工作态度很满意,尽最大能力给予我生活上的照顾。优先分给了两间住房,虽然是简陋的土坯房,但为一家五口人解除了住宿安身之忧。室内盘上了火炕,垒了火墙,有了简单实用的取暖设备。在“三九”严冬的季节里避免了高寒地区的夜宿之苦。“冬至”过后,进入仲冬季节,交九才进入真正的寒冬。山东一带的“九九歌”到遥远的呼伦贝尔之后已经不完全适用,原先想象中的寒冷,与现实相差甚远,这里冷得邪乎。一阵寒风能把鼻尖冻白,把手指冻硬一层皮。老百姓冬季取暖主要是烧煤,这里是褐煤盛产地。附近多是煤矿区,煤的价格也相对较低,每户每月国家供给半吨煤,全年平均下来,基本够烧。
旧历腊月二十六日之夜,是一个难忘的夜晚。室外北风呼啸,房顶屋檐下传来阵阵狂风的劈啪声。半躺在床上,借着窗外远处铁路机务段信号灯的光束,隐约能看到铁路三角线的拐弯处,有两个铁路工人身上紧裹棉大衣,头上戴着皮帽子,扣紧了御寒的帽扣,棉大衣的下襟一阵阵地被狂风卷起,似是一对张翅欲飞的南极企鹅。
一天的劳累,又加寒冷单调的夜间生活,我和妻子谈了一些有关过日子的闲话,几个孩子已经睡着了。妻子向煤炉中填了些煤,使炉火通宿燃烧,以保证室温不会太低。
我正在睡梦中,突然被次子的哭声惊醒,听室外的风声已经停止,估计已经是下半夜了。孩子的哭声抽抽噎噎的,妻子醒后把他搂在怀里喂奶,他不吸奶,仍在哭泣,哭声断断续续地延续了一会。没哭声了,妻子从怀里把他抱出去,他已经不哭也不动了,放个什么样就什么样地躺在那里。我和妻子没有北方寒带生活经验,思想单纯,没有多想就要继续睡觉。就在这个似睡非睡的节骨眼上,妻子说她的头迷糊得厉害,她的话,一下子提醒了我,我的神经立刻紧张起来:是不是让煤烟熏着了?我爬起来问妻子。她低头不语,我已经意识到了事态的严重性,赶快去摸三个孩子,三个孩子也是一动不动。我用手去掐捏他们的屁股蛋,谁都没有反应。坏了,煤气中毒啦!说时迟,那时快,我推了推妻子,她哼了一声,再也说不出话来了。
一家五口之中,已昏迷四口,只有我还是清醒的,怎么办?我要是一个个地抢救已来不及了:喊人,时值下半夜,四邻都在熟睡中,更何况我们是新近为邻,只是萍水相逢,没有一定交情的邻人,患难相求是有难度的。懵懂中的我,干脆一脚踢开了窗子,抱起长子来到窗前,先做人工呼吸,然后再给其他的人继续做人工呼吸。
约十多分钟后,室内的温度已下降到零下,过堂风从破败的窗子里吹进来,屋子像个冰窖。妻子和孩子们慢慢苏醒过来,我极度的紧张惊恐缓解了一些,但我不敢怠慢。我赶紧把窗户封好只留一条缝隙通风。稳定下来,我才觉得浑身乏力,一屁股坐下去,心里后怕。这场灾难能够逢凶化吉,多亏了我家祖上积德保佑啊,不然,我携妻带子来到了异乡却让全家人遭此厄运,差点成了灭顶之灾,我如何向遥远的山东家人交代?如何面对祖宗先人呢?
但愿这一次血的教训能够成为我生活道路上的长鸣警钟。
邻居们知道我家的遭遇,已是早饭过后的时间。其中有一位邻居是我的寿光同乡,他三十多岁的年纪,懂得一些民间的保健知识,要是头痛脑热、感冒发烧、肠胃不适什么的他都可以对症治疗,给了群众很多方便。今天他特意来我家表示关怀慰问,看一下大人孩子有什么不舒服或后遗症没有。据当时一家人的自我感觉和他的观察都没有大毛病,他说这就是一家人的福气。外地人刚到林区生活,缺乏御冬防寒的生活知识,晚上压上一炉子煤后睡觉,要是室内空气不能流通,就容易产生一氧化碳,时间长了就会发生煤气中毒,这是高寒地区千万要注意的一件大事。今冬,全镇有两家发生过煤气中毒的悲剧了。我听到这些后,确实有些后怕,这个令人心惊肉跳的1960年的冬天啊……
夏
大兴安岭上的夏天来临了,才使人有了春天的感觉。河套里汇流着山谷间、森林里淙淙下泻由冰雪融化而来的桃花水。充满春的气息,万物复苏。北国独有的大兴安岭杜鹃,在一个阳光艳丽、东风和煦的早晨就可万山红遍,一簇簇一片片紫粉色的花瓣含笑迎人,似彩云飘落人间,如仙女抛袖起舞。杨柳松桦也已摇金吐玉,煞是壮观,大兴安岭特有的春天是如此辽阔壮美,让人心旷神怡。
河谷间碧水奔流,两岸繁花似锦,稠李子花簇如雪凝翠,蜂蝶嬉戏,鸟鸣幽谷,雉戏静林;山丁子花含翠吐玉,花瓣迎风微颤,如粉蝶落满枝头,花香鸟语,香气袭人,雾霭蒙蒙,满目花团若隐若现,似已进入人间仙境。
生产队农林牧副渔全面经营,要求社员必须是多面手,才能与之相适应,它又成了一个锻炼人、考验人、造就人才的大课堂。不到半年的时间里,我不仅经历了刨冻粪、打水井、打垅种土豆、赶牛四轮车拉粪送肥、铲地除草,还经历了上山包工计件打石頭,真是无所不干。
农村经历了三年大灾大难之后,处在一个相对稳定的经济恢复阶段,开始实行“三自一包四固定”的农村经济发展的管理办法,劳动实行男女同工同酬的计件工资,这大大提高了社员劳动的积极性,促进了农牧业生产的发展。这里的农业生产社最忙的季节,不单是春种秋收,最冷的冬天和最热的夏季才更是夺取农牧业生产丰收、为农业集体经济增产创收的黄金季节。冬季利用冰雪的有利条件,伐运深山里的木材:夏季抓住青草生长的旺季,打贮畜草,这两项任务,都是时间紧、劳动量特别大的体力活,没有一定的体力和毅力是难以完成任务的。
今年的青壮年劳力,我也是名列其中。打草是生产队的需要,也是青壮年劳力多挣工分增加个人劳动收入的一个主要项目,草场就成了强手如林的竞技场。打草有“马神”(即马拉割草机)和人工两种方式,大部分都是人工打草。我是初次上阵。
草场在六十华里以外的“二号”甸子上。吃住干活都靠自己,单独起伙,单独劳动,这对我来说真是一个大难题。首先是没有打草的刀具,别人打草用的是德国产“炮牌”或苏联产芟刀,我用的是夹把子刀;其次做饭用的锅碗瓢盆也没有,这在当时计划经济物资供应的情况下,是拿着钱也买不到的,更何况囊中羞涩,拮据无比。只好自己作瘪子东借西凑将就着干。
7月12号,队里用一辆四轮马车把我们四人一块送到了草甸子上,搭完草窝棚后,支下锅灶,就开始打草,褥子铺在草甸子上,身子底下阴湿流水。
打草的数量和质量,除因每个人的劳动态度有区别外,更主要的是由草场秧草生长的品种和高低决定的。这些之前我也不懂,他们三人分别占据了最好的草场,给我留了草稀而矮的一片。我是起早贪黑地干,每天早晨天蒙蒙亮就起来,趁草上没有露水先把前一天打的秧草垛好,然后再回窝棚做早饭吃。早饭后砸好芟刀再去打草,一直干到下午一点左右再吃午饭,下午又是打草。这期间是最好的打草时间,但也正是蚊子、“小咬”最猖狂的活动期,两只手只顾紧握芟刀打草,浑身上下落满了蚊子、“小咬”,要打蚊子、“小咬”就耽误了打草,若只顾打草就只能让蚊虫叮咬,那个又疼又痒的滋味真是难以用言语表达。
太阳西下之后,再用草叉挑草铺子,约五十斤左右一铺子,故意在夜间让夜雾凝成露,码成垛子后既能保持草香,又能保持草的重量和质量。入夜之后,才能回窝棚做饭睡觉。就这么拼死拼活地干了半个多月,队长到草场来给大家送粮,顺便检查社员的打草情况。当了解到我的干劲和打草的效果后,他一看我的草场秧草长得又矮又稀,全部是紫苜蓿和碱草,这草质量好,牲畜愿吃,奶牛多产奶,绵羊好增膘,但谁都不愿打这种草,这草有质无量,秋后点草时,按秧草重量计工资,谁打谁就挣不到高工分。生产队里愿意要这种优质牧草,但不能让一个老实社员吃哑巴亏。
队长看完我们的打草情况后,悄悄地在一边和我说:“这几个小子看你是外行,抓你的大头,分给你这样的甸子,累死你也打不出草来,后天我再来送你去一块好甸子,多打点草,多挣点工分!”回头他又对这三个人批评道:“你们太欺负老实人了,真是人老实了有人欺,马老实了有人骑,靠水近了好和泥!”
队长五天后把我送去了一个新草场。这里是小煤窑沟草场,秧草茂盛,又正是七月下旬草长花开的盛夏季节,一望无垠的草原,微风送爽,草波涟漪,给人一种“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心旷神怡的感觉。
在这么辽阔的草场上,我孤身一人在这里安营扎寨,目之所及一望无际,草场虽然无人和我争抢了,任我随处挑选割打,但确实有些孤寂、冷清,每到阴天下雨,更增加了林间草地的空旷凄凉。
做饭时,因为没有水桶,我只好端着小锅去附近的草甸子里取水。那是一个死水坑,孑孓不停地在里面翻着跟斗,烧水时,水温很高了,它们还在活蹦乱跳游泳呢!我只好眼瞅着把它们煮死。我本来就不会做饭,又因缺少炊具,没有面板、没有面盆,每天只好早饭是疙瘩汤,午饭是疙瘩汤,晚饭还是疙瘩汤,将近三个月的甸子生活,吃饭没换过样,也许是由于过于消耗体力的原因,吃着还挺香呢!
八月下旬,中午烈日当头,草场上风不吹草不动,就像一个大蒸笼,嫩绿的牧草已蔫头耷拉脑地没了生气。半个多月没有下雨,蚊虫特别猖獗,也应了“七月半,八月半,蚊子嘴,快似钻”的俗话。天气闷热,汗流浃背,又臭又硬的衣服贴在身上,如铠甲护身,但蚊虫还是能够叮透衣服,咬得如芒刺全身。炎热、饥饿、蚊叮、劳累使我筋疲力尽,每在这个当口上我就会不由自主地想起一大家子人来,是啊,他们在等着我吃饭哪!于是,我的全身就有了力量,我忘记了饥饿,忘记了蚊叮和疲劳,大芟刀一抡,唰,唰,唰——牧草横卧脚下,一行行,一排排,如尸骨遍野的浴血疆场……
一阵厮杀过去后,回首望去,战果辉煌,这一阵对牧草的拼杀,胜过半天的收获!精神毕竟不是万能的体力源泉,我累了,左手扶着芟刀,右手叉腰,背对太阳,迎着徐徐清风,想歇一会儿喘口粗气,肚子也确实需要饭吃了。
就在这时,背后的不远处,有一片高高的茅草,里面传来唰唰的爬动声,我机警地回头审视着,伴随着响声,茅草在不停地晃动。我的心一下提到了嗓子眼儿,我双手握紧芟刀,目不转睛地注视着。是什么东西呢?我壮着胆子向草丛里抡了一刀,草丛里传出了一声怪叫,像小狗一样。真的是一只小狗,不,是一只小狼!它已随着芟刀的惯力和一堆草躺在一起,草刀正中它的脖子。
我弯下腰仔细瞅了瞅,确实是只“小张三”,它头皮开裂,鲜血淋漓,死了。我害怕起来。听当地老乡们讲,特别是一些常年跑山的山油子们说,“张三”喜欢群居,恋崽心切,报复心极强,人或其它动物抓走或打死了它的幼崽,它就会向肇事者讨还血债的。我今天的后果,一定会引来一群母狼,先包围我的窝棚鬼哭狼嚎,撕破嗓子向它的同类哭泣报警求援,然后就是陆陆续续来些公狼,再就是要对我下毒手了……
我先仔細估量了一下自己的防范实力,觉得确实是势单力薄。藏身之地只是一个草窝棚,“老张三”一爪子就可以掏透,我便只能暴露在群狼之下,任其撕咬,想到不堪的后果,我不寒而栗,思来想去,三十六计,走为上吧。
我赶紧生火做饭,煮了一锅疙瘩汤吃,把行李家具收拾妥当后,奔着返家的方向启程上路了。走出了约五华里之外,碰上了先进生产大队的一位老社员,他听了我的陈述后立即摆手说:“这是好事,送上门的肥肉,我跑遍山林找还找不着呢!走,听我的,回去。”他看我迟疑,就把他多年跑山的经验说给我听。
原来他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山里人,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冬天上山下套子,专门套狍子套山兔,大雪封山之后,碰巧了还能套只犴达罕、黑瞎子什么的;有时也去河套里下夹子,夹“张三”、水獭水貂;夏天他就在河套里打鱼摸虾,凭这一本领,把这些活当成了主业,把生产队的活当成了有一搭无一搭的副业。
他说狼这个东西奸得厉害,人常说狼狈为奸,就是狼狈勾结干坏事。说着他又指了指背在肩上的布袋,里面有六盘铁夹子,要趁黑天以前下好,老狼要是真来,咱的夹子就会派上用场。他又摆了摆手里的猎枪,意思是确保咱平安无事,万无一失。
我半信半疑地跟着他回到了打草窝棚,主要是一种好奇感驱使着我。我跟着他下好了六盘夹子,之后我们就到窝棚里躺下休息,猎枪放在他的右手边,铁草叉放在我的左手边。
夏日的草原,夜色真美。上弦月挂在西天,如一把金黄色的木梳悬在高空。雾霭蒙蒙,月色朦胧,草丛中昆虫唧唧,树上宿鸟啁啾,如睡梦中的情人呓语,几棵松桦树影婆娑,似少妇出浴的黑发,风鬟雾鬓。时隐时现的夏夜景色,恰如镜花水月,虚幻美妙。
夜静后蚊虫也停止了飞动,只有湿地上的青蛙不时鸣噪,我们在静静的等待中渐渐进入了梦乡。不知过了多久,睡梦中的我俩突然被一阵急烈而凄惨的嚎叫声惊醒,我一下子坐起来,他按住了我,示意不要动。
我懵懂地靠在他的身旁,心里咚咚跳着。他却任凭狼嚎,稳坐不动,悠然自得地抽起了烟,时隐时现的烟火,使窝棚内弥漫着一片烟雾。
过了好大一会儿,狼的嚎叫声停止了。草原上恢复了往日的宁静。东方的地平线上已经泛白,我们走出窝棚,手执猎枪和芟刀,几十米外的草地上,卧着一只狼。我心里胆怯,只好跟在他的身后,“张三”看到我们后,猛地站了起来,但没有站稳,又趔趄着歪在那里,朝着我们呲牙咧嘴地干嚎,面目十分狰狞。他低声说:“没事儿了,这只张三被夹住了。”他把砂枪举起来,“啪”的一声枪响,草地里一下子又沉静下来。
这是只母狼,右前爪差点被夹折了,这一枪打得很准,铁砂都集中在头部,头被打成了一堆烂肉泥,面目全非。他又拿起刀子,用一个猎人特有的宰割技术,一会就如剥一只绵羊似地完成了剥皮剔肉的全过程,他把“张三”的两只耳朵装在背兜里,得意地向我夸耀:“这又能换几斤老白干啦。”
这时,已经是朝霞满天,雾霭使草原朦胧而沉静。他坐在一个塔头墩子上,卷了一只又粗又长的纸烟,深深地吸了几口,又掏出怀里的小酒壶大口地喝着,满脸焕发着胜利者的红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