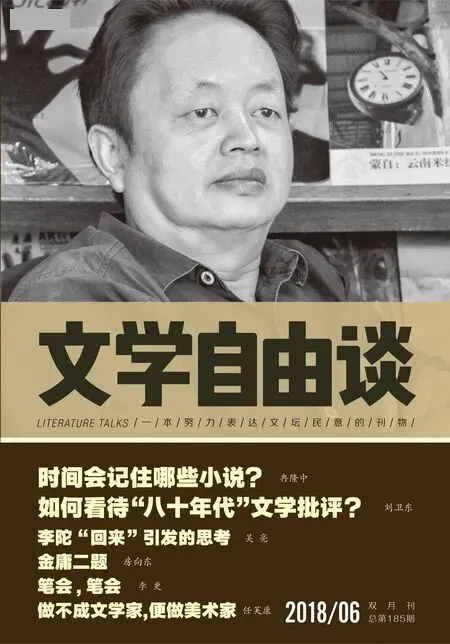诗歌形式问题的讨论是必要的
丁 鲁
中国白话新诗自1916年开始倡导。百年来,对它的评价论争不断。这些争论集中在诗歌形式方面。
在纪念新诗百年的时候,不少论者意识到诗歌的形式问题值得研究。比如2016年4月在中国新诗百年论坛南宁分会上,与会的谢冕、孙绍振、吴思敬等人都看到了中国新诗迫切需要形式方面的建设;这是难能可贵的。与此同时,也有人出来反对研究诗歌形式。2017年7月7日《文艺报》上叶橹先生的《流变的诗体,不变的诗性》一文,就很有代表性,值得加以研究。
由于叶文使用名词术语概念多变,逻辑表述往往不够清晰,我不得不先在这里简要说说自己的主要观点:
第一、“诗歌形式”主要是指诗歌的语音方面而不是专指文字的排列。它包括很多方面,句长句短、韵疏韵密等等都是,其中也包括“诗体”概念。“诗体”专指诗歌作品是否需要遵循特定的形式规范(即格律)。遵循某种格律者是格律诗,不遵循一切格律者是自由诗。二者之间的作品,可视其格律因素之多少称为半格律诗或准格律诗。
第二、内容和形式的关系是一个哲学问题。自由诗的形式研究并不涉及诗歌内容,因此所谓“内心世界的自由表现”在研究自由诗的“形式”时一般不加考虑;应该考虑的主要是自由诗的节奏处理之类问题,中国新诗界却很少有人对这些问题加以注意。
第三、新诗是现代白话诗歌(现代汉语诗歌),它是白话文运动的产物。五四时期保卫新诗的斗争主要是为了保卫用白话写诗的权利,而不是单纯为了保卫自由诗。
第四、白话的格律诗和自由诗都需要研究如何提高艺术表现力,都需要研究诗歌形式。其中的白话格律诗的艺术形式研究本来就需要作更多努力,过去又缺乏稳定的社会条件来做这件事,因此现在多作一点研究是必要的。不能认为提倡研究诗歌形式就只涉及格律诗,更不能认为提倡研究诗歌形式就是在和自由诗对着干。
第五、格律之要素有三,即节奏、韵、诗歌结构。其中节奏应有规范,以保证其流畅;韵应有规范,以保证其和谐;结构则应百花齐放,以保证诗歌的多样性。其中的某些通用形式(如古典诗歌的律、绝,西洋诗的十四行诗等),必然是在长期发展中形成的。至于某些人认为诗歌就是应该追求不流畅、不和谐,那不过是他们的流派主张而已。
现在我们来看看叶先生这篇文章吧。我们的讨论不妨从它的题目入手。
一、所谓“流变的诗体”和“不变的诗性”
叶文中说的“流变的诗体”,是指一种还是多种诗体呢?“流变”是指某种或某些诗体的特点呢,还是说“诗体”概念本身是变化不定的?这种有歧义的说法令人难以发表意见。如果叶文指的是多种诗体的嬗变,则无论中外,诗体的变化都只有若干种,数量是有限的。
以为一首诗多了几句、少了几句,或者诗行长了一点、短了一点,就是换了一种诗体,就是诗体在“流变”,这是过于简单的看法。所谓“诗体”,指的应该就是格律诗和自由诗两大类。而“诗体建设”,也应理解为“诗体”(包括格律诗和自由诗)的建设,而不是指诗歌具体结构形式的多样化。
应该承认,白话格律诗的倡导者中,的确有人在“诗体建设”和“增多诗体”的口号下搞出一些繁琐花样,往往起到束缚诗人的作用。因此,叶文提出的某些批评是积极的。但也应该说,叶先生对“诗体”概念的理解,与上述诸位格律诗倡导者并无差别,不过是指诗歌具体结构形式的多样化而已。
至于“诗性”,能说它是始终不变的吗?
诗,是文学的一部分;诗性,自然也是文学性的一部分。熟悉西方文论的人都知道,“文学性”概念是俄罗斯形式主义者提出的,而俄罗斯形式主义者,特别是后来西方的新批评家,对它也使用过“诗性语言”的称谓。自“文学性”概念提出之后,首先是形式主义者研究文学作品中的文学性,后现代主义又转而研究非文学作品的文学性,人们对它的认识就有变化。这是从理论方面来说的。从创作方面说,现代人恐怕很难写出像“小桥流水人家”那样的作品来吧?如果从欣赏方面说,按照欣赏美学的观点,现代人读“小桥流水人家”,和当时人的心情也不会一样。所有这一切,都说明对“诗性”的感受是可以变化的。
究竟什么是“诗性”呢?叶文说这里指的是“诗性语言”,似乎是赞成新批评家的观点,但语焉不详,只说“有的诗让人一读即眼睛一亮或心灵震颤,而有的诗读之则索然寡味或心存厌恶”,并认为我们在接触并进入作品的诗境和语境时,“首先是因为其语言的诗性内涵吸引并打动了我们的内心,使我们潜藏在内心深处的诗性因而受到激发引起冲动”。简言之,有无诗性,全靠批评家对作品好不好的个人感受,这就难以服人了。叶先生是把对重大理论问题的严肃的讨论,变成了一件可以各说各话的事,就像将一个需要靠“法治”解决的问题,依靠“人治”来解决,何时能有个结论呢?
二、关于诗歌形式
人们为什么老要提出诗歌形式这件事?难道真如叶文所说是“用旧体诗那一套规矩来衡量它”,甚至形成了一种“集体无意识”吗?既然“持‘诗体建设’论的人总是说,诗体建设并不是要制订一套模式,而是要寻找到一些使诗的写作不能过于信马由缰的方法和规律”,那么如果真能寻找到一些使诗的写作不会“过于信马由缰”的方法和规律,岂不是很好吗?应该说,过于信马由缰现在已经成了新诗界的一种通病。连这样“寻找”一下都要反对,岂不是叫人很纳闷?
内容和形式的关系,对于现代中国诗歌是一个多年没有解决的问题。对“内容决定形式”一语的错误解读,长期阻碍了文艺界,特别是诗歌界的艺术探索。
叶文一再强调自由诗符合追求自由的精神,说:“它的存在显示的真正意义在于,诗的追求自由的精神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这正是诗的本性之所在。”我不能不遗憾地说:以上这段话恰恰是一种混淆内容、形式区别的典型说法。历史上宣传新思想而采用人们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者,宣传自由精神而采用格律形式者,比比皆是,并不一定要改变文艺的形式。例子太多,无须列举了,还是请叶先生读读拜伦的《哀希腊》吧。
叶文还说到假诗、“非诗”泛滥的问题。什么是“非诗”,同样要从内容和形式两方面来看。从内容看,符合格律规范的假诗的确不少;可是从形式看,比如说一篇论文,内容再好,能说是“诗”吗?
至于叶文说到的回文诗、图案诗、藏头诗之类,不过是些文字游戏罢了,何足道哉?叶先生是太看重它们了。
叶先生还提到形式“包含内在的和外在的两方面”。这当然并非新论。“内在形式”(inner form)是德国人提出的。这个概念最早来自普罗提诺和夏夫兹伯里,但至今无人能将内在形式和外在形式的界限分清(勒内·韦勒克、奥斯汀·沃伦《文学理论》)。叶文虽然说“一首诗如果只有外在的形式,那就很可能成为诗的赝品”,但叶先生对“内在形式”语焉不详,同样没能说清楚。叶先生还主张“用‘形式感’一词来判断诗的形式的艺术含量”,而他所说的“形式感”就是指“艺术的‘形式’给了人们什么样的感受”,并认为“没有抽象的形式,只有具体的形式感”。我倒认为所谓“形式感”,总是人的一种主观感受,应该说是抽象的;至于“形式”是具体的,则是人们的普通常识。叶先生的创见若想服人,恐怕还需要有更多论证。
三、关于五四时期诗歌现代化的目的
叶文说:“现代社会的出现需要更为自由和多样的诗的形式,白话诗取代古典诗,乃是社会发展的需求和必然。”叶文还说:“近百年的现代诗前进的步履虽然彳亍艰辛,但在摆脱旧体诗的影响上却是取得了巨大成就的。”
这些话混淆了几个不同的问题:一、诗歌的语体(白话诗还是文言诗);二、诗歌的时限(现代诗还是古代诗或古典诗);三、诗歌的形式(自由诗还是格律诗);四、指诗体还是诗歌传统。
一些现代诗人往往将新诗称为“现代诗”。像以上引文把“现代诗”和“旧体诗”(即文言诗)作为相对应的术语,那么现代人写的文言诗算不算现代诗呢?
新诗是现代诗、白话诗,其中应该包括自由诗和格律诗(白话的格律诗),虽然至今还没有形成公认的格律规范。旧诗或古典诗是古代诗、文言诗;它们都是格律诗,虽然其早期形式在格律上要求并不严格。
如果承认以上说法,就应该看到:把白话诗取代文言诗(或曰古典诗)解释为“社会发展的需求和必然”和“现代社会的出现需要更为自由和多样的诗的形式”,并没有说明问题的实质。这种取代的原因其实很简单:就是为了语言的现代化,因为我们现在普遍使用的语体已经不是文言而是白话。法定的书面语言从文言改为白话之后,用白话写诗是必不可少的一步。叶文是用社会需求的空洞说法掩盖了语体变化的事实。
除了语体的变化之外,人们对诗体变化的目的就产生了两种不同的想法。一种想法认为诗歌现代化是为了解放诗歌作者手中的笔,任他天马行空地发挥;另一种想法认为这是为了读者能更好地理解诗歌作品。两种想法中哪个是对的?这件事我虽然着笔不多,却是一件最具根本意义的事。我们还是拭目以待吧。
至于叶文所说的“摆脱旧体诗的影响”,是指语体、诗歌形式,还是指诗歌传统?如果是指语体,即从文言诗变为白话诗,那是成功的。如果是指诗歌形式,就难说是“取得了巨大成就”。如果是指诗歌传统,是否应该“摆脱”,就值得好好研究一番。我希望这不是叶先生的本意,可惜叶先生说得过于笼统了。
四、关于社会条件对诗歌创作的影响
叶文说:“如果说现代诗存在着‘困境’,那么,这种困境绝对不是‘诗体’所造成的困境,而是我们的生存困境所造成的。把人的生存困境对现代诗造成的伤害,误认为是现代诗的诗体上的失误,实在是一种可悲的误解。”这种看法很典型,也很容易被人接受。有不少朋友就认为现在“不是诗歌的时代”。
可是在中国历史上,艰难困苦的时代不是很多吗?为什么中国古典诗歌会被叶先生评价为“超稳定”?“人的生存困境”真能对诗歌造成那么大的伤害吗?我们历来就有“国家不幸诗家幸”的说法。唐诗中的很多佳作,就是在安史之乱中出现的。历史事实反驳了叶先生的说法。何况诗歌一般远远短于小说、剧本等,既然生存困境对诗歌都造成了这么大的伤害,为什么还有人肯花更多时间去写小说和剧本?
如果说,诗歌在形式上还不成熟,而动乱的社会条件又妨碍它的建设,这就真有点像是诗歌的“困境”了。现在十年动乱都已结束了四十多年,经济发展,人民生活稳定,为什么不应该抓紧时间好好研究一下诗歌的基本建设问题呢?
五、叶文中的逻辑混乱
叶文在逻辑上问题不少,使用名词术语也很不规范。
叶文中强调,词、曲之所以丰富了诗的形式,是“基于对内心世界的更广阔的自由表现而出现的‘诗体建设’”;另一方面却又说:“我国的古典诗歌,从最早的四言、五言、七言的自由诗而发展到后来的格律体,从文化建设的意义上来说,无疑是一种进步。”既然格律诗不自由,为什么从最早的四言、五言、七言的“自由诗”发展到后来的格律体倒是“一种进步”?为什么这种进步又要加上“从文化建设的意义上来说”的先决条件呢?既然古典诗歌可以走向格律化,研究一点白话诗的形式问题为什么就不行?从这些表述中可以看出,叶文的主张是矛盾而不近情理的。至于认为我国最早的四言、五言、七言诗是自由诗,或者认为词、曲比五、七言诗更自由,不过是一些不熟悉古典诗歌的人们头脑中的主观想象而已。
叶文一再强调诗歌形式的所谓“无限可能性”,但文中又说什么“分行的无限可能性”。人们不禁要问:既有无限可能性,还要分行干嘛?在这方面,中国古典诗歌的不分行似乎更“无限”一点吧,因为它像文章一样排列,不需要以分行作为条件(当然这只是一句玩笑)。可见新诗界有些朋友并不明白,西洋诗之所以要分行,完全是出于实用的目的,因为它不分行往往就看不清眉目。
叶文中还说:“现代格律诗,其规模和格局是无法预设的,每一个诗人都会按自己的诗思实现其创作意图。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格律诗也是无法规范的。既然无法规范,实际上就存在着无限的可能性,注定了就是无体可建的。”此处将“无限可能”进一步扩展到了格律诗领域,就更加叫人感到奇怪了。既然古典诗歌可以有格律,为什么现代的格律诗就不能研究研究诗歌形式呢?
白话格律诗的“规模和格局”,一般说应该是指它的结构,比如全诗几节、每节几行之类。结构应该由诗人自由处理,不等于节奏和韵没有它自己的规律,怎么就“无法规范”?怎么号称是“现代格律诗”,却不可能有格律规范,反而“存在着无限可能性”和“无体可建”?既然“无体可建”,怎么叶文又承认有所谓“现代格律诗”?既然现代的格律诗也是“无限可能”的,那它和自由诗又有什么区别?总之,叶文首先错误地把诗歌形式等同于“规模和格局”(也就是结构),然后以结构需要多样化来否定格律规范,进而否定白话诗可以建立格律诗体,看起来这条路似乎走通了。可是首先,它的前提是错误的;其次,既然否定建立格律诗的可能,为什么一开始就明确提出“现代格律诗”这个命题?可见叶先生的逻辑在这里相当混乱。
叶文这一论断最大的问题,是它不符合辩证法。世界上从来就没有无限的可能性,诗歌也没有这种可能性,不论是格律诗还是自由诗。
至于名词术语的不规范,可以用“诗体”这个术语作为例子。比如叶文说到自由诗是“无体之体”,前一个“体”是指诗歌形式,后一个“体”却是指诗体。可是自由诗真的没有诗歌形式吗?自由,不就是它的形式吗?像“无体之体”这种说法,用在理论文章里就显得太不专业化了。
我指出这一切,只是为了用这个例子来说明我国当代诗歌界许多人在理论上,特别是在基本理论上的漫不经心。
六、关于双重标准与零和思维
叶文受到双重标准与零和思维的严重影响。
比如在批评伪诗的时候,叶文着重批评的就是“格律体的五言、七言诗”。其实作为诗歌作品中的一种普遍现象,伪诗在白话的自由诗中不是同样大量存在吗?
叶文还说:“本来,现代诗就理所当然地包含了格律诗和自由诗,只是由于每一个诗人都有自己的兴趣爱好和特长,因此我们只能让各人发挥其所长而不能用诗体来约束他们。”这句话一开始承认现代诗歌包括格律诗和自由诗,后来却说“不能用诗体来约束他们”;如果把“诗体”理解为格律诗、自由诗两大类,提倡写“自由诗”不是也会被算作一种“约束”吗?可见这里的“诗体”一词显然是专指格律诗。那么自由诗是不是一种诗体呢?要是那个诗人的所长就是写格律诗,又该怎么办呢?叶先生一方面说“在诗的形式的探索和试验中,不应当设立什么禁区”,另一方面却处处加以限制,这又该如何解释呢?
由此可见,叶文对自由诗和格律诗使用了明显的双重标准。
叶文承认,格律诗是现代诗歌的形式之一,“不存在它与自由诗的相互排斥的问题”,并且保证自由诗“绝不会威胁到格律诗的正常存在”。但马上又说:“如果一味地强调所谓 ‘诗体建设’,反而会让人感觉到自由诗的形式似乎是一种另类而非正统的。现代诗的格局,应该是真正意义上的百花齐放而不是厚此薄彼。”提到诗的建设,指的应该就是研究诗歌的形式方面,既包括格律诗,也包括自由诗。怎么就是厚此薄彼了?怎么就会“让人感觉到自由诗的形式似乎是一种另类而非正统的”?叶先生在这方面实在是过于敏感了!由此也可以看出,叶先生对研究自由诗的诗歌形式同样极为缺乏兴趣。
众所周知,格律诗的倡导历尽艰辛,在“内容决定形式”的口号下长期被批为“形式主义”,1958年新民歌运动中又受到莫须有的批判,直到今天,叶文还在用“何其芳们”的帽子把一些与何其芳先生毫无关系的主张硬扣到他的头上。叶先生在人家 “寻找”一些不让诗歌“过于信马由缰”的规律时也提心吊胆地生怕人们感到自由诗是“另类而非正统”,难道这也属于一种“集体无意识”吗?叶先生似乎对白话格律诗非常戒备,生怕它的发展会夺去自由诗的地盘。其实何必如此呢?各发展各的,相互学习,彼此竞赛,大家促进诗坛的繁荣,难道不好吗?为什么非要出来反对别人不可呢?心灵深处难道也像他所说的那样希望“用‘诗体’来一统天下的格局”?既然如此信心满满,为什么别人一提研究诗歌形式,叶先生就紧张?有什么可怕的呢?在这一点上,我和叶先生的看法和做法是不同的。我不仅主张诗歌形式的研究应该包括格律诗和自由诗两体,而且作为诗歌的实践,我自己既写白话格律诗,也写过自由诗。我的长诗《风之歌》,就是用自由诗体写的。
为了保卫用白话写诗的权利,五四时期进步的文化人作过艰苦的斗争。他们是生气勃勃的革命者。现在白话诗已经站稳了脚跟,迫切需要研究的是诗歌怎样在艺术上更进一步。我们不应该躺在前人开创的事业上不思进取。这是一个精神状态的问题,愿与叶先生共勉之。
2018年4月24日
《陈见尧诗词选》
陈见尧著 云南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