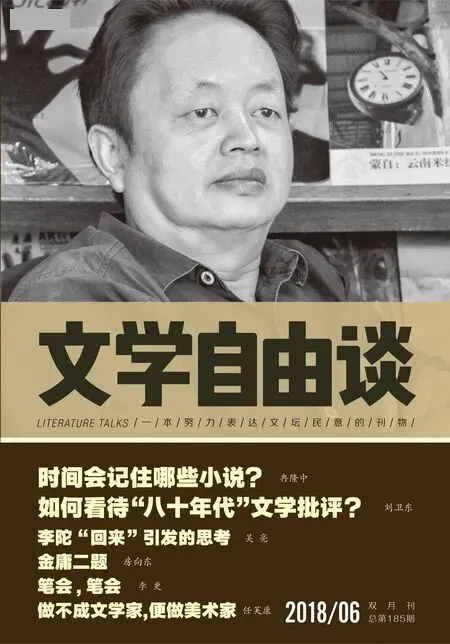笔会,笔会
李 更
每次看到父亲开始收拾行李,母亲就说,你爸爸又要吃好的去了。
和当时所有武汉人一样,吃饭是我们家最大的消费。吃什么,怎么吃,在哪里吃,天天都是一个重要问题。母亲每天除了到长江边上的第一冶金建设公司码头仓库上班,就是给全家五口人做饭。通常是晚上做饭,要够吃到第二天中午。我后来一直奇怪,那时没有冰箱,食物怎么保鲜?回忆了好久,才想起一件事:有一次,我从北湖农场学农回来,一个同学请客,拉我去他家,就是一个菜,榨菜炒肉丝,猪油炒的,好香,但是非常咸。原来盐能防止食物腐败——这是我学到的最实用的知识。如今想来,当年我们家吃的最多的,估计就是盐。
1979年,45岁的父亲李建纲由武钢调入湖北省文联,重要工作是参与创办《长江》丛刊。
听刘富道说,《长江》丛刊这个名字还是周而复起的。那个时候,全国几乎所有文学刊物一出版就可以发行十几万册,《长江》丛刊也不例外。除了盈利,还有有关部门的补贴。稿费标准按照当时物价来看不算低,每千字七元左右。《长江》丛刊也才一元钱一本。
几乎每个作者在发表作品前,都要先被刊物请来武汉,按照编辑的意见进行修改。这是最让作者激动的事情,特别是农村作者,他们有的几十年都没有进入过城市。
编辑部把作者的吃住行都包了。虽然也是招待所,但招待所的床铺就是比家里的木板床舒服;虽然也是食堂,但食堂的几个菜更是油泡出来的,人吃得精神旺盛,夜以继日改稿都不累的。饭菜份量很大,所以一些作者还呼朋唤友,一起来打牙祭。尤其是文联或者作协开会,连圈子以外的都摩拳擦掌找关系。现场往往摆了十几张几十张桌子,就像现在的河南水席,一道又一道的,肉是摞成金字塔的。人人都是饿牢鬼,开会时的虚心、诚恳、韬晦、礼让,种种温良恭俭让,此时都没有了,只是一阵又一阵“咬牙切齿”,大家都来不及说话了。
农村来的作者为了加快进度,湖北做法的牛肉之类懒得细嚼慢咽,直接就吞,因为你如果按照正常吃法咬那种牛肉,会有不少卡在牙缝里面。他们还解释说,吞下去的食物比吃下去的食物耐消耗。部队的作者有绝招,不知道在哪里搞到两个碗,先把看好的菜搛入自己的碗里。一个工厂作者看到大事不好,急中生智,拿瓢直接喝汤,假装烫嘴,噗嗤一下,面前几个大碗都中招了,女作者纷纷躲避口水,不再吃那些碗里的菜。可是这个方法对农村作者没任何意义,他们直接用筷子“夹”汤,一板一眼,顺时针,逆时针,一遍又一遍,耐心细致。武汉人说,他们连牙签大的肉都不放过;上海人说,他们不是用筷子“夹”汤,是在洗筷子。
后来流行开笔会,最让人津津乐道的还是伙食。不用带一分钱,但是得付粮票——计划经济,城市的粮食是计划到人的,而且开始时粮票也不能买卖。农村作者到武汉拉关系,就带了不少农副产品,干鱼、腊肉、辣椒酱、豆丝、霉豆渣、霉千张、糍粑,甚至粳稻米。
我因为在刊物上发表了一些诗歌散文,也被父亲的学生拉入笔会。本来,父亲对我非常严格,不让我去开会,因为一些会往往是他组织或者主持的,他要学习那些延安来的干部,不占公家便宜。他的一些学生经常来家里拉我去,直接就说吃饭去。母亲就喜欢这样的学生,夸奖他们懂事。如果遇到父亲阻拦,她就说:兴你吃不兴孩子吃?父亲就开玩笑:是你想吃吧?母亲说:我想吃怎么啦?父亲说:你哪瓣牙齿想吃啊?母亲说:我满口牙齿都想吃!我知道母亲没有说假话。她真的喜欢吃东西,但是在我印象里那时她几乎没有吃过什么像样的食物,经常是我们父子四人吃完她才动筷子;遇到父亲在家里请客,她连桌子都不上的。
有一次开会,在饭桌上和蔡明川遇到。他一口河南话:李更,你多吃点,看你瘦的。蔡老师是个老革命,南下干部,“文革”以前就是《长江文艺》编辑,后来又是《湖北文艺》编辑,经常跑红钢城找父亲约稿、聊天。有时父亲不在家,母亲就背着我小弟弟带他去找,我跟在后面。当时小弟弟很胖,像个肉坨子,不背他就不走;大弟弟就很瘦,我更瘦。蔡说我的特点就是老远看见一双鹭鸶腿,膝盖就是个大骨节。他说,你们家大概一天一个蛋糕,是老三吃的,老二吃包蛋糕的纸皮,你就在旁边认真看。他说的是武汉著名的香草蛋糕,当时一毛钱一个。
中学时,同学说我特别能吃。当时流行一本批判资本主义的连环画,主人公叫七把叉,因为能吃,被富人们拉去做活广告,后来在吃饭比赛中撑死了。同学就叫我“七把叉”。说来也怪,我是能吃,但一直不胖。直到大学毕业,我和黄学忠、何友胜配合张元奎在武昌首义路44号创办《书刊导报》时,我仍然骨瘦如柴,像非洲难民,胸前的排骨一根一根的,清晰可见,连心脏跳动都看得见。黄学忠老拿我的身材开玩笑:杨柳细腰啊。顺便说一下,我们创办了中国最早的民间报纸,有全国刊号的,还是胡耀邦批示的。招募了一大批生活无着的写作者,这些人里面,后来出了不少作家,白稚山、任蒙、黄晓阳、李德复等等。我们的报纸属于集体所有制的武汉书刊发行公司,池莉、黄自华从武钢出来后,都是先到这个公司。
把自己吃胖,是我的当务之急,否则都找不到女朋友。但是,上世纪80年代,吃饭是许多文学青年的头等大事,只要有饭局,都会呼啦啦聚集一帮人来。要知道,当时通讯联系可不容易,不像今天这样手机微信的。穷文人连固定电话都用不到,只能写信,而市内平信也得三四天,要想及时,就得靠文友奔走相告。
忽然流行起来的笔会,成为业余写作者最盼望的事情。谁参加了什么笔会,去了哪里、吃了什么,比写出什么更让人期待。一些大刊物的笔会尤其引人瞩目。在湖北,则以《长江》丛刊笔会最有规模。
通常,这些笔会是写作者向丛刊领导推荐自己家乡为开办地点。我记忆深刻的是熊召政家乡英山县桃花冲林场:大别山深处,满目林木,到处是燕子窝,到处是清澈见底的溪流;招待所对面的山上,已经是安徽的鸟儿在飞了。
我现在相信地灵人杰了。除了召政老兄,英山那个地方还出了刘醒龙、姜天民。三人都得过全国文学奖(可惜姜天民38岁就去世了,如果活到今天,文学成就会更大一些)。湖北三位茅盾文学奖获得者中,就有两位是英山县城出来的,并且,这两位先后都成为湖北文联主席;更传奇的是,他们都是花甲以后担任的,熊召政是60岁,接他班的刘醒龙是63岁。
英山笔会伙食非常好,好到大家后来都吃不下去了。是消化不良,还是这里的硫磺矿泉水影响食欲?
父亲组织这些笔会,先开始是坚决反对我参加的。其实,那时我已经在《长江文艺》《福建文艺》《芳草》《萌芽》等刊物发表了不少诗文,并且因为参与“朦胧诗”全国大讨论,观点上了《作品与争鸣》创刊号,而在圈子里面小有名声。后来去北京,顾城、杨炼都说,没想到李更你这么年轻,17岁。其实我17岁开始发表的这些文字,都是我十五六岁写的。
通常,我不用经过父亲同意,直接就去笔会。记得那次去英山,我迷路了,还是熊召政、王继走了十几公里山路来接我。那时的文友多么单纯、热情啊。有时床铺不够用,还有两个人挤一张床的。我就和野莽挤过一张床,就是那种单人木板床。野莽后来在北京请客,每次都要回忆那段时光,忆苦思甜。顺便说一下,当时湖北有“三野”:野莽、野牛、野夫。本来还有野墨,是我的一个笔名,事不过三,我就不凑热闹了。
那个时候,写作者的写作条件都很差,尤其是工人。农民还有农闲时间,而工人在工厂是一个萝卜一个坑,甚至不分季节三班倒;下班以后又忙于家务,根本没有时间也没有心情写作;城市里面还经常停电。(我一直记得父亲在煤油灯下读书写作的场景。)到了笔会,他们就非常刻苦,非常珍惜来之不易的机会,就是写作,没有娱乐,甚至连串门都很少,不像现在的笔会,基本上是麻将会。很多作者一天写上万字甚至几万字,把手都写肿了。今天想来,那不就是“双规”嘛——在规定的时间、规定的地点?
我是至今不能参与集体写作的。几个人在一个狭小的空间,像参加高考。本来我也想适应一下,但是一看那些正在刻苦的兄弟,脑子就走神了。一个人无聊,挨家挨户去看,想和谁说说话。还真的有这种一边写着一边和我聊天的兄弟,一天也是写一万字的;可惜那个兄弟后来对文学不感兴趣了。
后来很多兄弟说,感谢笔会,那种气氛就是让人文思泉涌。后来自家房子大了,独立写作了,反而不适应,甚至,再也没有写出超过以往的作品。
我去笔会,也不是白蹭饭的。父亲要求我干活,比如帮助作者整理文稿、记录日程、拍照留影、迎来送往,甚至做清洁。一些作者病了,我还得负责陪同去医院——这活儿今天叫“护工”。
有两次,正在写《长江三部曲》的鄢国培忽然发病,不省人事。我背着他去医院。招待所往往在荒郊野外,几乎没有正经路;有一次还是走羊肠小道,还翻个院墙。别看我瘦,但力气不小,一路小跑,堪称“人肉120”。乡下医院,也就是卫生所的水平,好在当时一同参加笔会的郑因在场。她是武钢二医院的护士,和我是朋友。她及时、准确地判断并帮助医院分析病情,最终总算是有惊无险。
老鄢是个很拼的人。他长期在宜昌轮船上当工人,一心想像我父亲那样调入省作协当个专业作家。我父亲就是工人作家出身,虽然工人的活儿他一天都没做过,但是他一直以武钢工人作家为荣。因为都是工人作家,父亲对老鄢特别欣赏,特别照顾,甚至几个笔会几乎就是为他组织的,在时间、地点上都考虑了他的实际情况,把笔会出作品的宝也押在他身上。
我是在高考前住在一个朋友家里“冲刺”时,读到鄢国培的作品的——说是复习,其实我整天就是看小说,看大仲马的《三个火枪手》《基督山伯爵》,钱钟书的《围城》,姚雪垠的《李自成》,以及李北桂的《贼狼滩》、鄢国培的《漩流》……常常是一天看一本。李北桂是湖南人,在黄石当宣传部长,是父亲的多年朋友。他的长篇小说《贼狼滩》一问世,就吸引了湖北大批读者。他写广西十万大山解放军剿匪的故事,比后来水运宪写同类故事早了十几年。鄢国培的《漩流》叙事宏大,场面开阔。按照他自己的设想,《长江三部曲》是全景型的,写到抗日战争结束,分三步走。但是他毕竟长期当工人,没有进行更充分的历史地理补课,《漩流》之后,功力不逮,虎头蛇尾。即使如此,也是湖北长篇小说的大制作了。
后来参加笔会,我得以与鄢国培朝夕相处,甚至和他讨论小说的谋篇布局。这是因为父亲给了我一个光荣而重要的任务:帮鄢国培抄稿子。那时可没有今天这么方便,你要一稿多投,必须多抄几份。我现在还是想不通,他的稿是首先在《长江》发表的,然后长江文艺出版社出书,为什么却让我用复写纸抄很多份?这让我痛苦不堪。我对自己的稿子都不会重抄,除非是编辑已经答应发表,之前还要修改一下,我才会一边修改一边重抄。
虽然我十分喜欢鄢的作品,但是,读和抄,完全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之前,为了学习,我抄写过很多作品,主要是诗作,大部分是外国作家的作品;中国作家部分,几乎把民国以来所有我喜欢的诗人的作品,都认真反复抄写过;湖北作家,我抄写过徐迟、曾卓、管用和的诗歌,还是诗人的作品。那时的抄写还有一个原因:买不到书。那完全是自觉自愿的。
抄诗歌和抄长篇小说,感觉完全不同。诗歌是点点滴滴,甚至抄写时有快感。给鄢抄长篇小说,居然还发现了不少叙述的毛病,没有读《漩流》的快感了——主要是拖泥带水,不断分行,可能是想拉长篇幅赚稿费。(他家里困难,极其看重稿费,他的小笔记本上写得密密麻麻,原来以为是灵感之类,其实基本上是收支状况,给哪个几十块,收到哪里多少稿费。当时我非常震惊,因为印象中的作家,除了姚雪垠,恐怕就属他有钱了。)还有不少错别字、语病,甚至还有历史、常识之类的错误,我都以商量的口气告诉他。他圆嘟嘟的脸庞充满喜气,用重庆方言说,李更到底是大学生,找你抄稿是李主席最正确的选择。我赶紧说,这是学习鄢大师的机会。
后来他为了赶进度,甚至直接用一些文史资料。他还用刘绍棠《蒲柳人家》那样的短句,但语言风格与他的作品不匹配。(顺便说一下,刘氏短句,在《蒲柳人家》里面是最精彩的,后来被刘自己用烂了。《长江》丛刊也发表过刘氏短句中篇小说。刘写作很快,几乎一个月一部中篇小说,一时,全国几个刊物几乎同时有他的中篇小说发表。)
当我提到《大波》,鄢国培惊讶了,说,你也看过李劼人?我说,文联图书室就有。鄢当时的表情,好像被人发现了自己的秘密似的,说,看来不能小看你。我笑说,我可是靠文学评论吃饭的;我的第一篇在省一级刊物上发表的文字就是文学评论,研究当代文学的。
鄢国培和李劼人有不少相似处,比如都是湖北人,都讲川东话。李劼人的“大河三部曲”(《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大波》)就是写长江,其中对民俗、地理、历史的体现,使得小说还有很高的社会学价值。鄢后来承认,他是受到李劼人的严重影响的;按照今天说法,是读着李劼人长大的。李劼人的意义,就是他的史诗性。民国作家写作三部曲的并不多,宣传得厉害的,当然是巴金“激流三部曲”。我个人认为,还是李劼人、老舍在这个方面最为成功——全景型,史诗性。
鄢国培加强了小说的香艳性。其实,如果李劼人在小说中也加入鸳鸯蝴蝶派的东西,就像食物加入一点糖,是可以把味道调得更丰富的。可能李劼人觉得鸳鸯蝴蝶派太过甜俗。这有个度的问题,加入的糖要刚好,不能让人觉得甜。
曾经,我专门到上海淮海路上的一栋有电梯的公寓楼拜访秦瘦鸥,和老先生讨论过鸳鸯蝴蝶派的得失。他也认可我的看法。他说,所以后来他写的是谴责小说了,比如《劫收日记》。这篇小说就是父亲找秦瘦鸥约的稿,在《长江》丛刊发表。现在对比一下《秋海棠》和《劫收日记》,风格区别就很大了,证明秦瘦鸥晚年转型的成功。秦老跟我抱怨说,上海文坛是某作家的“家天下”,他的文章在这里的媒体发表很困难,与他来往的朋友也不多,所以他非常感谢《长江》丛刊给他的文章一些出路。我在《珠海特区报》负责文学副刊以后,也经常发表秦老的小文章。记得有一次他说又写了一部中篇小说,和《劫收日记》同类型,想在我那里连载,说,主要是最近国外一些亲戚可以回国探亲了,他需要做个东,上海像样的饭局非常贵,特区报稿费高一些吧?可惜当时我的顶头上司是一个“文学中年”,心胸不够开阔,坚决不同意连载。
鄢国培就是在李劼人风格上尽量放糖,所以可读性非常好,写了很多女人,个个香艳,个个风骚,细节也十分生动,比如偷看女人洗澡、入厕之类。鄢说,其实这都是长江轮船上的水手生活,他把那些都放到袍哥身上了。我们都笑:是你的生活吧?他当然是否定的。以他的身材、脸庞,估计根本没有什么香艳之事。就是想象,无边的想象。就像最近有个作家说的,莫言从来不写猎艳的成功,而是写望女人不可得的痛苦,所以,他才可以把女人神化成超凡的美丽。
这其实涉及另外一个文学话题——怎么下生活的问题。有人说,你不吃猪肉,怎么知道猪肉的味道?“文革”以前十七年,以及“文革”期间,有关方面都要求作家深入生活,说,不到工农兵中间,怎么写得好工农兵的小说?所以,很多作家积极备战,甚至长期驻点,还要挂职。最极端的是柳青,一部《创业史》,让他当了那么多年农民。这还不说更多临时抱佛脚的。真的那么神吗?
其实,我认为“第二自然”更为重要。比如,石涛是“搜尽奇山打草稿”,张大千却是临摹甚至抄袭石涛(当然,张大千后来也是经常写生的)。现在,张大千的拍卖价居然超过石涛,说明一个道理,文艺创作中的想象是非常重要的,也是凸显创作者才能的地方。大家都知道,范仲淹并没有到岳阳楼,却写出了天下名篇。也许真的到了现场,就可能“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了。
事实上,大量历史小说,都是作家想象的结果。想象的水平,直接反映作家的才华,甚至,越是生活里面不能、无法触摸的,越是激发作家想象能力的动力,是绝对原始性的,就如鄢国培对于美女的想象,充满力比多压抑,充满荷尔蒙压力。
所以,体验,不是文艺创作的唯一手段,甚至不是一种重要手段。
父亲与鄢国培后来关系微妙,是在鄢当上湖北作协主席以后。本来,我以为他们的关系会因为父亲对他多年的欣赏、照顾而百尺竿头。父亲一直以自己是工人作家为荣,并且,一直坚定地认为老鄢也是一直认可自己的工人身份。结果,老鄢当了主席以后,再三强调:什么叫工人作家?作家就是作家!结果,父亲还是以工人作家身份与鄢拉关系,这不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吗?
在广东,也出现过这样的问题。有关方面一直推崇打工文学、打工作家,甚至在繁花似锦的深圳,宣传部门几十年如一日地花重金推出一个又一个流水线上出来的作家、诗人。尽管这些作家、诗人的水平存在明显瑕疵,但对比那些职业文化人来说,他们得到的组织关怀、资金支持要大许多。我曾经在一个研讨会上说,打工文学是需要帮助,但是你深圳作为一个世界经济大都会,更应该推出自己的精英文化,而现在这样的做法,却是深圳文化的自我矮化。当然,一些打工作家、诗人趁机声明自己属于精英,出现了几个开心可笑的人物,那是另外一说了。
因为父亲的关系,我当时还积极扮演一个牵线搭桥人的角色,就是为那些和我同龄的文学青年介绍发表的机会。而其实,一直到父亲离开《长江》丛刊,我也没有机会在《长江》上发表一个字——那个时候,我深受刺激,一定要冲出湖北,寻找发表、出版的阵地。
最近,诗人王家新在回忆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文章中,特别提到,当年北岛的中篇小说《波动》是他带回武汉,发表在《长江》丛刊上的。年纪大了,就是天才,记忆上“挂万漏一”也是可以理解的。这里我需要说明一下:当时的王家新不是《长江》的编辑,自己想在《长江》上发表诗歌都困难。他大学毕业时,被武汉大学“发配”回原籍丹江口。所谓“有志者‘誓进城’”,好容易从湖北最贫困的农村走到城市,怎么甘心再回老家?他极其向往北京,后来真的到了北京。这一点我非常佩服他。
有一次在沈睿家,我看到一本打印稿,就是《波动》,和《今天》一样,也是蓝色封面。我有阅读癖,拿起就读,一口气看完,大声叫好。署名很陌生。王家新说,北岛的小说。好像是沈睿解释,这个笔名是北岛为了纪念他的妹妹起的。我带回武汉给父亲看,父亲也非常兴奋,说写作形式像苏联小说《绝对辨音力》,马上推荐给编辑们传看,很快就拍板,决定发表。
当时,“北岛”这个名字还是很敏感的,于是通过王家新和北岛沟通,发表时用了北岛的原名——赵振开。
《波动》发表后,引起了文坛的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