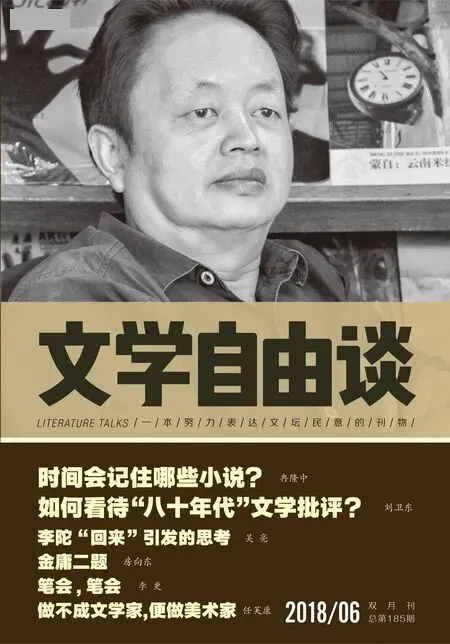曹文轩与安徒生有啥关系?
唐小林
在中国,只要上过学的孩子,恐怕没有不知道曹文轩这个名字的。尤其是2014年4月4日,曹文轩获得“国际安徒生奖”,国内众多媒体便一度出现了集体兴奋的状态。有媒体将曹文轩的获奖誉为“登顶世界之巅”,宣称:“来自中国的儿童文学作家曹文轩不负众望,顺利摘得这一世界儿童文学领域的至高荣誉,实现了华人在该奖上零的突破!继莫言2012年摘得诺贝尔文学奖后,中国的文学力量再次在世界面前展现了蓬勃的生机与无限的希望!”“国际安徒生奖为作家奖,一生只能获得一次,表彰的是该作家一生的文学造诣和建树。”曹文轩的小说,被众多的学校和老师推荐,被称之为“‘中国故事,人类主题’的完美呈现”“至珍绝美,典藏中的典藏”。但曹文轩的作品究竟是不是配得上这样高度的赞美,是否真正达到了世界文学的最高峰,学术界和文学批评家们却似乎很少去认真探讨和思考。
曹文轩在《读者是谁》中说:“我不是一个十分典型的儿童文学作家,因为我在写作过程中一般较少考虑我作品的阅读对象是儿童,更少考虑他们是我作品的唯一阅读对象。在书写的日子里,百般焦虑的是语言、故事、结构、风景、意象甚至是题目和人名之类的问题。我曾经许多次发表过一个偏颇的观点:没有艺术,谈论阅读对象是无效的。但我十分走运,我的文字引来了成千上万的儿童。当那些书以每年每种十万册的增长速度被印刷时,我暗自庆幸我所选择的文学法则。我要在这里告诉诸位:儿童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读者。”通过曹文轩的这段话,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儿童文学仅仅是曹文轩写作的一个外壳。曹文轩说“儿童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读者”,这样的话并不靠谱。儿童毕竟是儿童,他们因为年龄、知识、判断力等诸多原因,并不能对自己阅读的书籍做出准确的判断。事实上,儿童是这个世界上最容易被误导、最好“蒙”的读者。曹文轩的小说,虽然被冠以“儿童小说”,却未必适合儿童阅读,尤其是像《天瓢》这样的小说,其描写之“生猛”,更是令人匪夷所思。曹文轩在小说中毫发毕现、玩赏性的性描写,恐怕让许多学生家长都会大跌眼镜,感到崩溃:
彩芹清清楚楚地看到了杜元潮的小鸡鸡。杜元潮的小鸡鸡像一只没有长羽毛的还在窠里嗷嗷待哺的鸟。彩芹有心想用手去抚摸它,可是不敢,怕惊动了它似的。
朦朦胧胧之间,他看到了那口荷叶田田的大荷塘,看到了那棵老槐树,看到了赤裸的彩芹,看到了她的腿间:微微隆起的中间,是一条细细的缝隙。他依稀记得,她打开双腿时,他看到了一番景象,这番景象使他不知为什么忽然想起了清水之中一只盛开着的河蚌的壳内。
杜元潮仍将脸埋在彩芹的腿间,而两只哆嗦着的手,却沿着她发烫的腹部,慢慢向上伸去,直至高高举起触摸到了彩芹的乳房。
杜元潮泪水哗哗地亲吻着她的阴户,虽然面目全非,但他依然看到了它的过去。
曹文轩获得的虽然是安徒生文学奖,但在我看来,安徒生如果地下有知,恐怕也会气得再死一次。叶君健先生在谈到安徒生童话的艺术魅力时说:“他满腔热情地歌颂人民的优良品质,同时又尖锐地揭露出社会中形形色色的丑恶,以此来衬托人民的心灵美,使读者从感人的诗境和意境中发现真理,发现人类灵魂中最诚实、最美丽、最善良的东西,从而使人们的感情得到净化和升华。从这一点上讲,安徒生堪称是一位伟大的‘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与安徒生相比,曹文轩的作品题材狭窄、想象力贫乏、故事粗糙、文字矫情,弥漫着对“脐下三寸”的迷恋。曹文轩痴迷的,不仅仅是对人类的性行为的描写,更感兴趣的则是对动物交配淋漓尽致的描写:
最终,公鼠蹿到母鼠的脊背,一口咬住母鼠颈上的皮,以它沉重的身体将母鼠压趴在地上。母鼠企图挣扎,但这种挣扎似乎是为了激起公鼠更强烈的欲望。之后,母鼠温顺地矮下前爪,使臀部高高地翘起,并竖起本来遮盖着羞处的尾巴,将它清晰地暴露给正蠢蠢寻觅的公鼠。随即,母鼠的身体痉挛了一下,便发出了吱吱的声音。这声音是痛苦的,却又是快乐的。
——《天瓢》
其中一只绿尾巴公鸡,似乎兴趣并不在觅食上,常常双腿像被电麻了一般,歪歪斜斜地朝一只母鸡跌倒过去。那母鸡似乎早已习惯了它的淘气,只是稍稍躲闪一下,照样觅它的食。
——《草房子》
过了一会儿,公鸭拍着翅膀,上了母鸭的背上。母鸭哪里禁得住公鸭的重压,身体顿时沉下去一大半,只露出脑袋来。说来也奇怪,那母鸭竟不反抗,自愿地让公鸭压得半沉半浮的。
——《青铜葵花》
这种描写,让人感觉不是在读小说,而是在看“动物性交大全”的“毛片”。在曹文轩的笔下,“性”可谓泛滥成灾。水面上泛起的泡沫,是青鱼、草鱼、鲤鱼、鲶鱼、鳗鱼等等在交尾;东一家西一家的猪圈里,是母猪让人心头战栗的呐喊;田野上,公牛母牛叠成一座座大大小小的山,这些“山”在微微颤抖着……如此之多的性描写,究竟是出于艺术的需要,还是吸引读者眼球的需要?
作为一个儿童文学作家,其作品首先是要为儿童着想,就像《小王子》的作者安托万·德·圣-埃克苏佩里、《绿山墙的安妮》的作者露西·莫德·蒙哥马利、《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的作者马克·吐温、《山羊兹拉特》的作者艾萨克·巴什维斯·辛格等伟大的作家那样,写出适合于他们的心智、有助于他们的发育和成长的优秀作品,而不是像曹文轩这样,沉溺在卡拉OK似的自娱自乐,且放任无度、毫无遮拦的性描写中,甚至让人一看就非常恶心。
曹文轩小说人物的设置,并非是出于艺术的需要,而是出于哗众取宠的需要。在他的笔下,有生理缺陷的人,常常会成为其讥笑的对象。正因如此,“秃子”就成为了曹文轩小说中供人取笑的“道具”。在曹文轩的小说中,秃子之多之滑稽,可说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草房子》的第一章,干脆直接就用“秃鹤”为标题,并且从一开始就拿秃子来开涮:
秃鹤应该叫陆鹤,但因为他是一个十足的秃子,油麻地的孩子,就都叫他为秃鹤。……这个村子里却有许多秃子。他们一个一个地光着头,从那么好看的枫树下走,就吸引了油麻地小学的老师们停住脚步,在一旁静静地看。那些秃顶在枫树下,微微泛着红光。在枫树密集处偶尔有些空隙,那边有人走过时,就会一闪一闪地亮,像沙里的瓷片。那些把手插在裤兜里或双臂交叉着放在胸前的老师们,看着看着,就笑了起来,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我始终弄不明白,曹文轩究竟是在写小说,还是在故意建造“秃子集中营”,何以老是要拿“秃子”们的生理缺陷来博得读者的一笑?这种拙劣的表现手法,就像某些相声演员总是拿有生理缺陷的人来开玩笑一样,简直是把无聊当有趣。
曹文轩小说中的秃子,多是脸谱化的描写。他们不仅人长得难看,而且脑袋几乎无一例外地都很笨,蠢得像猪。在《流氓鸟》中,秃子干脆就被描写成为恶霸。《根鸟》中的小秃子,是一个不依不饶、带头“闹事”的人。《红瓦黑瓦》中,物理老师是一个秃子,他的帽子被一个造反的高三学生抓下来扔到了地上;打篮球的秦启昌总是秃着个脑袋在球场上奔跑,他在打鸟时,同样是丑态百出,连乌鸦都不惧怕他,不但不躲避他,还在他的秃脑袋上绕着乱舞乱飞,叫成一片,并将白色的粪便喷射在他的脑袋上;舒敏老师班上的二秃子,留了两次级,长得比班上原本最高的孩子还高出一个头;二秃子欺负女同学,在课堂上调皮捣蛋,不服管教,其母亲也是一个悍妇,她到舒老师的门口,破口大骂,用的是最下流的语言。《山羊不吃天堂草》里的秃子三和尚,为人刻薄吝啬,一分钱不是掰开花,而是数着格子花;人长得丑不说,还常年戴着个假发;其老婆公开出轨,明目张胆地跟村子里的川子睡觉。《拯救渔翁》中的捕鱼老人已经老了,不能继续在河上捕鱼,但他辛辛苦苦开垦出的一块荒地,却被邻村的马秃子占了;一只曾经被老人救过的鸟知道后,想方设法给马秃子捣乱,在播种时率领一群鸟不住地鸣叫,让马秃子心慌意乱,在长苗时引一头牛踩踏青苗,在收获时偷食其收割好的庄稼……
曹文轩的小说,人物脸谱化,故事程式化,人为设计的痕迹非常明显,写来写去,都是一些翻来覆去、陈旧雷同的故事。其中的景物和环境描写,往往都是大同小异,多读几篇,就会让人生厌。小说中的主人公,往往是一些家庭不幸、缺爹少妈,甚至先天带有残疾,或者生理缺陷的孩子;如果没有先天残疾,后天也会被故意“弄”成残疾,留下生理缺陷。总之,似乎不把这些人物弄得歪瓜裂枣、贫病交加,曹文轩的小说就根本无法书写下去。《阿雏》中阿雏的父母,坐船到邻村去看电影,小船超载而溺水身亡。《青铜葵花》中的葵花,三岁时妈妈就因病去世,父亲到小船上写生画画,不幸落水身亡。《灰娃的高地》中的灰娃与《红瓦黑瓦》中的二秃子一样,从小脑子就不好使,老师讲的课,他根本就听不进去,留两回级,坐在比他小两三岁的孩子们中间,高出一个头。《鸭宝河》里的鸭宝,脑子就像是进了水,常常受到孩子们的愚弄和欺负。《黑魂灵》中的傻子男,连话都说不清。《远山,有座雕像》中的达儿哥,是一个只有一只胳膊的独臂少年。《枫叶船》中的石磊,是一个连自己的父亲是谁都不知道的孩子,自尊的母亲受不了蔑视和耻笑的目光,在石磊出生不久,就将他交给了自己的舅父,去到了千里之外的漠漠荒原。《野风车》中的二疤子,八岁那年爬树,不小心从树上摔下来,被地上的瓦片划破,虽没有伤着眼睛,但视力却受到了影响,并且左眼的上方留下了一块淡紫色的疤痕,形状也与右眼不太一样;他看风车时,仰着的脸是扭着的。《细米》中的细米,调皮至极,六岁的时候,拿了把雨伞爬到树上,然后把伞撑开往下跳,摔在地上,把一只胳膊摔断了。《山羊不吃天堂草》里的明子,很大了还老是尿床。《天瓢》中的杜元潮,从小就是个结巴,《草房子》中桑桑的父亲桑乔,在二十五岁之前,也是一个结巴,而这两位结巴,都当上了教师,并且一个成为了油麻地的党委书记,一个成为了小学校长……
周作人在谈到儿童文学时说:“以前的人对于儿童多不能正当理解,不是将他当作缩小的成人,拿‘圣经贤传’尽量灌下去,便将他看作不完全的人,说小孩懂得甚么,一笔抹杀,不去理他。近来才知道儿童在生理心理上,虽和大人有点不同,但仍是完全的个人,有他自己的内外两面生活。”对于小说的写作,沈从文先生说:“要贴到人物来写。”而曹文轩儿童小说最大的致命伤就是越俎代庖,强作解人,常常脱离儿童的心理,大肆抒情和滥发议论,用一些华丽矫情的句子来营造一种虚无缥缈的“美”:
葵花很孤独,是那种一只鸟拥有万里天空却看不见另外一只鸟的孤独。这只鸟在空阔的天空下飞翔着,只听见翅膀划过气流时发出的寂寞声。
青铜很孤独。一只鸟独自拥有天空的孤独,一条鱼拥有大河的孤独,一匹马独自拥有草原的孤独。
却在这时,一个女孩出现了。葵花的出现,使青铜知道了一点:原来,他并不是世界上最孤独的孩子。
《青铜葵花》中,葵花的孤独和青铜的孤独,简直就像是同一个模具里批量生产出来的“孤独”。这样的文字,实在是太过于文艺范儿了,它与小说中的主人公,完全是两张皮。这样的心理,难道会是葵花这样一个年仅几岁的小孩所具有的?像青铜这样的乡村少年,居然能够超凡脱俗,如此“奢侈”地享受孤独,迎来葵花的出现,并且感悟出自己并不孤独,这实在太像一个失去爱情,而又重新获得爱情的文艺青年的做派了!它就像是在模仿张爱玲的经典之作 《爱》:“于千万人之中遇见你所遇见的人,于千万年之中,时间的无涯荒野里,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刚巧赶上了,那也没有别的话可说,惟有轻轻的问一声:‘噢,你也在这里吗?’”
投机取巧、移花接木,早已成为一些当代作家秘而不宣的创作“秘笈”。读曹文轩的作品,我们常常有一种并不陌生,似曾相识的感觉。《山羊不吃天堂草》中,对三和尚的老婆李秋云的描写,会让人想起赵树理《小二黑结婚》里的小芹;明子、黑罐和三和尚三人来到城里打工,傻呆傻呆地观望着城市,有时互相说几句傻头傻脑的话,然后故意把傻话说得特别的傻,然后傻乐,而明子面对城里公厕洁白的便池不敢撒尿,又让人不禁想到了刘姥姥初进大观园;明子他们捡到“外国钱”的一段,试图反映金钱对人性的考验,不就是对马克·吐温《百万英镑》的移花接木?
就故事的内容来说,曹文轩的小说常常有一种“程式化”:小男孩帮助比自己更需要帮助的小女孩,然后彼此产生一种朦朦胧胧的“爱”,构成一个凄美而又略带忧伤的故事。《青铜葵花》中的葵花,小小年纪就死去父母,无依无靠,被青铜的父母收养,成为异姓兄妹。兄妹俩从土中挖一点芦根吃,居然就成为了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他们不时地对望一下,心里充盈着满足与幸福,一种干涸的池塘接受汩汩而来的清水的满足,一种身体虚飘而渐渐有了活力、发冷的四肢开始变得温暖的幸福。
他们摇头晃脑地咬嚼着,雪白的牙齿在阳光下不时闪动着亮光。他们故意把芦根咬得特别清脆,特别动人。
你一根,我一根;我一根,你一根……他们享受着这天底下最甜美的食品,到了后来,几乎是陶醉了。
《山羊不吃天堂草》里的明子,本身还是一个老是尿床的农村孩子。他跟随三和尚来到城里打工,偶然遇到了患有不明病因、坐在轮椅上的紫薇,于是下决心要为她做一副拐杖,帮助她站立起来。这时,曹文轩在小说中的描写,完全脱离了一个农村孩子的心理和文化素质,显得极为 “小资”(以下引文中的着重号,均为笔者所加):
明子倚在铁栅栏上。明亮的天色下,他第一回如此清楚地阅读了紫薇的面容。她的脸色实际上比他原先感觉的要苍白得多,眼中的忧郁也要比原先感觉到的要浓得多。她的头发很黑,眉毛更黑,一挑一挑的,如两翼鸦翅。鼻梁又窄又挺,把两个本来就深的眼窝衬得更深。明子很吃力地阅读着,因为,他总是记不住紫薇的面容。
这些明显带有人工雕琢的文字,是明子这样没有多少文化的孩子能够感觉出来的吗?符合人物的身份吗?法国作家弗·莫里亚克在《小说家及其笔下的人物》中说:“如果某个主人公成了我们的传声筒,则这是一个相当糟糕的标志。”曹文轩笔下的人物,不管他们出生的环境和家庭、以及文化背景如何,都成了不可思议的“曹记”文艺小清新。他们一看到山水和天空,就想描写和抒情;一看到夕阳和星星,立即就像哲学家一样陷入无尽的沉思。《青铜葵花》中葵花,简直就是一个“女版”的哲学家庄子,她常常与一朵金黄的菊花说话,与一只落在树上的乌鸦说话,与叶子上几只美丽的瓢虫说话。
伊里亚·爱伦堡说:“任何小说,甚至幻想的或者乌托邦的小说,也都是以现实为基础的……任何艺术都不是也不可能超脱于现实。”而曹文轩的小说,往往都是对现实不管不顾,感觉良好地任性书写。《远山,有座雕像》里患上传染病的小女孩流篱,在城外大河边的草地上,遇见了放风筝的独臂男孩达儿哥。达儿哥的手臂是十岁时因为和小伙伴打赌,翻墙时被大石头砸得粉碎性骨折而造成的截肢。在曹文轩的笔下,达儿哥不仅是流篱眼中的英雄,而且无所不能:不仅会游泳,而且特别擅长打篮球,是队里的主力中锋队员。身体健全的对手,无论如何都防不住他。他满场飞跑,球到了哪儿,哪儿就有他。他奔跑时,不会失去平衡;他高高跳起时,就像空中飞人,长长的独臂,几乎就要碰到篮筐;在比分落后的情况下,他能在最后一分钟力挽狂澜,扳回败局,夺得胜利。达儿哥的心理素质特别超强,当发现流篱在注意他的空袖筒时,不但没有一丝自卑的神态,反而还露出了几分骄傲,好像那只空袖筒是什么荣耀的象征。就是这样一个达儿哥,成了流篱眼中的“男神”,并对其崇拜有加。达儿哥为了朦胧的爱,毅然将在比赛中获得的珍贵的球衣卖掉,为流篱买了一条乳白色的连衣裙。小说最后,达儿哥的妈妈去世了,他守在妈妈的墓前,一连三天,从早上一直坐到月亮消失在西边的峡谷里。于是,一段矫饰过度的文字,出现在了我们的眼前:
第三天的最后几个小时,达儿哥是动也不动地站在妈妈的墓前的。时间太久,他的双腿麻木了,重重地栽在地上。流篱跑过来,把他扶起来。星空笼罩着冬天寂寥的原野,世界一片混沌,远方起伏不平的山峦,像在夜幕下奔突的骏马,显出一派苍凉的气势。
这种看上去很美的文字,仅仅是为写而写,跟小说主人公的年龄、所处的环境和心境根本就不搭界。这种塑料花一样表面“好看”的文字,可说是曹文轩小说久病不治的沉疴。
曹文轩说:“小说不能重复生产。每一篇小说都应当是一份独特的景观。‘独特’是它存在的必要性之一。因为它独特,才有了读者,而要使它成为独特,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这就是求助于自己的个人经验——个人经验都是独特的。”但事情往往却很吊诡。曹文轩一方面强调小说不能重复生产,一面又在大量重复生产。其长篇小说《细米》完全就是对之前的《再见了,我的小星星》换汤不换药的重复书写。在后者中,主人公星星是一个让母亲头疼的、喜欢玩泥巴的孩子,被来此插队的苏州知青雅姐认为是艺术天才。雅姐的父亲是一个画家,她从小就受到艺术的熏陶。在她的辅导和关怀下,星星终于走上了通往艺术殿堂的崇高之路。在《细米》中,爱玩泥巴的星星“变”成了总是拿着刀子到处乱刻乱画的细米。细米这种“畸形”的爱好,令其父母伤透了脑筋,但被来此插队的苏州知青梅纹赏识。梅纹父亲是一位著名的雕塑家,她理所当然地受到过父亲的指点和熏陶,非常懂得雕塑。她毅然地对细米的父母说:“校长、师娘,将细米交给我吧”,“我来教他学雕塑”。在梅纹的辅导和帮助下,细米的艺术潜质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其雕塑作品很快就被送去参展……就这两篇小说的人物和故事来看,这完全就是一种大炒冷饭的重复写作。
曹文轩的创作虽然产量很高,但艺术性却非常令人生疑。他的小说中常常出现自相矛盾的硬伤。《红瓦黑瓦》中的马水清,三岁时母亲就去世了,在上海工作的父亲并未把他接到身边,而是以每月汇寄三十元钱的固定款项,作为他与祖父祖母一起的生活费用,将他永远留在了乡下。他的祖父开过木排行,有许多积蓄,根本不需要这笔钱,于是就把这些钱作为马水清的零花钱。令我们难以相信的是,在那样一个工人靠工资、农民靠工分,学生每月仅有一元五角钱菜金的计划经济年代,马水清父亲这么多的钱究竟从哪里来?
也许是为了追求“高产”,曹文轩在小说写好之后,似乎连仔细检查一遍的耐心都没有:
我不喊了。将铺盖卷放在甲板上,然后一屁股坐在上面,杲头杲脑地望着那一条条在眼前晃来晃去的腿。
我又重新回到了大烟囱下。我所看到的,依旧还是一张陷生的面孔。
这里出产的女人,似乎对他都不合适,因此,怏近四十岁的人了,依然还未成家。
这些一望便知的错别字,曹文轩在将书稿交给出版社之前,为什么不能静下心来,认认真真地检查一遍呢?曹文轩一面称儿童是“最好的读者”,一面又在将这样粗糙的文字兜售给他们,这种做法是否对得起那些正在成长、渴望知识、热爱阅读、天真无邪的孩子们?
国际安徒生奖,是儿童文学的最高荣誉,被誉为“儿童文学的诺贝尔奖”。尽管曹文轩已经获得了此项殊荣,但我们仍然坚信,曹文轩的作品,无论是在品位、艺术质量,还是写作追求上,都与安徒生有着天壤之别,而与安徒生奖之间,也只有半毛钱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