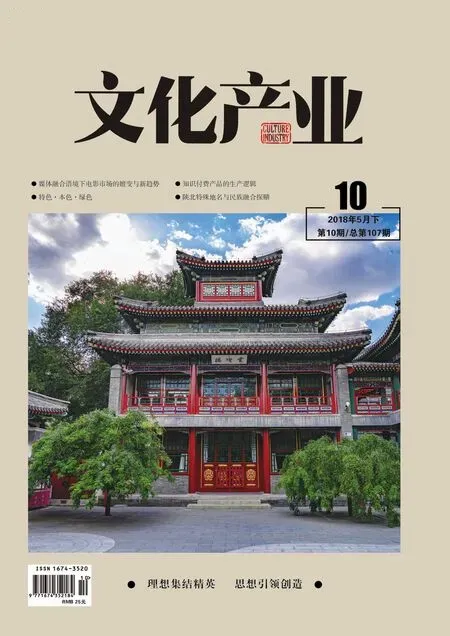从荒诞到真实:《局外人》中默尔索形象探赜
◎罗冠宇
(湖北大学文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62)
阿尔贝·加缪是存在主义文学的代表人物,尽管作家本人曾多次否认,但他和存在主义文学家萨特在当时法国文坛同样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加缪于1913年出生在阿尔及利亚一个普通的工人家庭,祖籍法国阿尔萨斯,其父死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随母亲一起住在位于贫民区的外祖母家。加缪生活在民族冲突、宗教矛盾非常激烈的地区,所以他常常会沉浸于人生、人类命运、道德伦理等形而上的理论。加缪于1957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评审委员会对其评价是“由于他重要的著作,在这著作中他以明察而热切的眼光照亮了我们这时代人类良心的种种问题”。
从创作思想来看,加缪的作品主题可以分为三类:荒诞、反抗和自由。其中,“荒诞”是加缪前期的重要主题,小说《局外人》、哲学理论著作《西西弗的神话》和戏剧《卡里古拉》都围绕着“荒诞哲学”这个哲学母题展开,以探讨荒诞产生的原因和如何面对。加缪在《西西弗的神话》中指出:“面对人本身不合人情所产生的这种不适,面对我们自身价值形象所感到的这种无法估量的堕落,正如当代一位作家所称的那种‘恶心’,也就是荒诞。”[1]这里的“恶心”指的是萨特的作品《恶心》,人处在不适的状态时会犯恶心。由此可见荒诞应该产生于人与自己以外的冲突和矛盾。例如看到冲洗好的照片不像自己,有种失真感。小说《局外人》正是讲述主人公默尔索是如何面对这种荒诞之感。为了更好理解文本,现简要陈述故事情节,并从默尔索的荒诞和真实两方面出发,分析默尔索的人物形象。
一、单线情节的荒诞
《局外人》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以默尔索的母亲去世为契机展开故事,再到他在海滩上杀死阿拉伯人为止。这里以第一人称“我”默尔索来讲述事情的经过:“我”在母亲下葬前后的表现比较平淡,甚至可以说是冷漠:不想看母亲的遗体、喝牛奶咖啡、抽烟、睡觉等,之后还和女朋友玛丽发生关系,和一个虐打情妇的邻居成为好朋友。这种叙述毫无抒情的意味,而是默尔索以一个“局外人”的身份平静冷漠地看待一切,给人一种莫名的荒诞感。打破这冷漠局面的是一件过失杀人案。因朋友的情妇而引起的一场血案,默尔索莫名其妙地杀了人:“我只觉得铙钹似的太阳扣在我的头上……我感到天旋地转。海上泛起一阵闷热的狂风,我觉得天门洞开,向下倾泻大火。我全身都绷紧了,手紧紧握住枪。枪机扳动了……”[2]在第二部分,牢房成为默尔索余下生命度过的地方,但他似乎仍比较冷静。律师希望默尔索说出有利于自己的事实,玛丽则安慰默尔索一定可以被法庭释放。而令人感到悲哀的是,审判法庭按照所谓的审判标准,利用默尔索过去的偶然事件将其异化为一个冷酷无情、蓄意谋杀的杀人魔。法庭判处默尔索死刑的原因并非因谋杀,而是其过去种种不合社会伦理规范的行为。柳鸣九评价:“如果说,从司法程序来看,默尔索是死于他作为当事人却被置于局外的这样一个法律的荒诞,那么,从量刑定罪的法律基本准则来看,他则是死于意识形态、世俗观念的荒诞。”[3]在默尔索被处决前夕,其本人发出最后的呐喊:“现在我面对着这个充满了星光与默示的夜,第一次向这个冷漠而未余温尽失的世界敞开了我的心扉……为了善始善终,功德圆满,为了不感到自己属于另类,我期望处决我的那天,有很多人前来看热闹,他们都向我发出仇恨的叫喊声。”[2]这是默尔索对生命和社会的真实体验,他虽置身于局外,但却一直观察局内的事情,而且十分明白这种没有真实的荒诞之感,因此最终选择以泰然的心态直面荒诞、 迎接死亡。
二、荒诞的局外人
对于“荒诞”一词,郭宏安指出:“荒诞并不产生于对某种事实或印象的考察确认,而是产生于人和世界的关系,这种关系是一种分裂和对立。一方面是人类对清晰、明确和同一的追求,另一方面是世界的模糊、矛盾和杂多。”[4]因此,默尔索之所以是荒诞的,不是因为他本人是冷漠无情而又荒谬的人,而是“世界报以不可理喻、神秘的沉默”,在法国当时的社会伦理规范中,若没有在母亲的葬礼上表现出大家所认可的“规则”,绝不会为社会所接受。默尔索身在“局外”,自然不会按局内的规则行事,但他又被抛掷在这个规则世界中,如不尽快熟悉社会规则就会被当作异类。默尔索被当成异类有以下几方面:
一是“不孝子”。故事开头第一句话就足以说明默尔索不是一个“孝子”:“今天,妈妈死了。也许是在昨天,我搞不清。”[2]这句话是默尔索的直观感受,对于母亲的离去用的是“死”,不是用敬语“作古”“驾鹤西去”,似乎仅是在陈述一个简单的事实,无任何丧亲之感。每一句都是短句,简洁平淡,字里行间读不出默尔索有任何情感。更可怕的是“我”连母亲逝世的准确时间都存疑。在后来母亲的朋友来守灵时,众人皆摆出守灵应有的状态,其中一位和母亲关系要好的女士还因难过而啜泣,而默尔索则有些不耐烦,没有掉一滴眼泪。在中国古代丧葬制度中,“卒哭为节哀之祭,此祭之前,服孝者‘哀至则哭’,朝夕无时;此祭之后,悲哀有所节制,‘朝夕哭而已’。”[5]默尔索的表现可被道学家称为毫无人性。而这些举动被局中人看入眼中,成为日后默尔索被判死刑的“证据”。
二是爱情“不忠者”。默尔索在海水浴场遇到昔日一起工作的玛丽,二人愉快地度过了一整天,晚上看完电影后来到默尔索家,默尔索居然在母亲刚去世后就和人发生关系,这种伦理和道德的冲突又一次让默尔索成为世人眼中的罪人。当玛丽问默尔索愿不愿意和她结婚时,默尔索的态度却显得十分模糊:“如果她愿意,我们就可以结婚。”但是玛丽在问及默尔索是否爱她时,默尔索如实回答:“如果一定要说的话,我可能是不爱你。”[2]此情此景,然而默尔索并没有按照社会规则说出约定俗成的话,而是诚实地表达自己的想法。
三是工作“不进取者”。默尔索从不会过多关注工作,但是对一些无关紧要的事,如公用的转动毛巾却极为关心,默尔索甚至告诉老板,公用毛巾在用一天后已经湿透了,以及默尔索在提出守丧时,可以清楚感受到老板生气的原因是自己可以休息四天,显然默尔索对这种细微之事体察入微。当老板表示准备在巴黎设立一个办事处,询问默尔索是否愿意去,默尔索却摆出了对一切事情漠不关心的态度,表示“都行”。
四是糊涂的“杀人犯“。全文在戏剧冲突上最荒诞的一部分就是默尔索杀死一个阿拉伯人。默尔索杀的确实是阿拉伯人,但他一直要对抗的对象却是太阳。面对太阳,默尔索的感受是“太阳晒得额头膨胀起来”“想逃避太阳”,这里的阳光不是柔和、普照大地,而是刺眼的,不是温暖,而是令人烦躁的。默尔索对这个阿拉伯人并没有起明显的杀心,但是炽热的阳光照耀在阿拉伯人的刀锋上,终于使默尔索失去理智,向阿拉伯人连开四枪,这便是默尔索被判死刑的导火索。
以上是默尔索十分荒诞的表现,在局中人看来,默尔索是一个没有人性、冷酷无情的杀人犯,对社会没有什么贡献,是毒瘤,其行为是荒诞的,但是,他在法庭的审判表现出的不是局外人的荒诞,而是局中人的道貌岸然:辩护律师希望默尔索收起天性说一些有利于自己的话、书记员执着于默尔索不信仰上帝的事实、检察官着眼于默尔索不符合正常道德规范的行为大声控诉道:“我控告这个人怀着一颗杀人犯的心埋葬了他的母亲。”[2]法庭把默尔索道德层面的问题强行作为主人公犯罪的依据,“把‘人性中或许存在的伦理道德上的可能缺陷’论证成了确凿的杀人倾向和杀人罪证。”[6]因此,如果用社会尺度衡量默尔索的种种行为,那将是毫无意义的。默尔索就是默尔索,他属于自己,他应该有自己的个性,而不应被束缚在局中,每日如局中人一般生活、工作,尽力要求自己符合一切“局中”规则。
三、真实的局外人
如果说默尔索是死于法庭的荒诞,那么他所表现出来的冷漠就是在对抗这种荒诞,甚至是积极地直面荒诞,哪怕是死于这种矛盾冲突。因此,默尔索并不是一个冷漠无情的人,而是通过自己的思考方式寻找着可能。这和西西弗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推动滚石有着一样的寓意,以一己之力对抗荒谬。滚石是我们每个人生命中必不可少的部分,因为人们每天也在做着重复的事情:工作、上学、吃饭、睡觉。最初进入这个陌生社会时,人们渴望并竭尽所能融入社会,并逐渐对社会规则轻车熟路。然而,人们终有一天也会产生疑问,究竟是人组织起社会还是社会规则控制着人?会认为重复的生活欠缺实感。如同一个演技拙劣的演员演着和布景格格不入的戏,局外的观众却看得十分清楚。《局外人》中的主人公虽然不是西西弗那样的荒诞英雄,但他却用自己独有的方式面对生活的虚无感,既不是用生理自杀来结束生命,也不是用哲学自杀来消极避世,而是直面荒诞,如鲁迅先生所说的“真正的勇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7]默尔索敢于直面人生荒诞,是一个真实的人。
(一)亲情的真实
默尔索没有用世人认可的方式表达对母亲的爱,但是他在处理完母亲丧事以后,不止一次地回想起母亲:妈妈在的时候,住的这套房子刚刚好,一个人住则显得有些空荡荡的;晚上睡觉听到朋友莱蒙的哭声后,不由得想起妈妈;甚至在临刑前想起妈妈对自己讲过关于父亲的往事。这些都足以说明母亲在默尔索心中的分量,母亲是潜移默化地影响着默尔索,默尔索是把母亲藏在心里,而不是做给世人看,认为自己没有必要符合社会所期待的样子。
(二)爱情的真实
默尔索之所以对一切事情冷漠,包括爱情,表现出“无所谓,我都行”的态度,是因为他用自己的方式诠释着对这个世界的观点。他不想欺骗玛丽,说自己有多么多么爱她,但是他又的确深爱着玛丽:在海水浴场遇见玛丽时默尔索就将玛丽的神态和表情记录下来;在海滩时默尔索不止一次想要亲吻玛丽;甚至在最后锒铛入狱,当玛丽来探望他时,默尔索没有把玛丽当作可以为自己洗脱罪名的证人,而是以男人对女人报以最原始、最纯粹的感情表现自己。绝不像洞悉社会规则般的男性一样对着爱的女性说着甜言蜜语,也不会玩弄对方的感情,而是真真切切地表明自己的态度。
(三)“我不信仰上帝”
默尔索的口头禅是“无所谓,我都行”,他对许多事情的态度都是模棱两可,没有明显的情感波动,哪怕是当年轻的书记员激动地拿着十字架问自己是否信仰上帝时,默尔索也平静地予以否认,由此可见,默尔索并不信仰上帝,或者认为上帝从没有尽职尽责。上帝虽然全知全能,但是上帝是否真实存在?加缪在《反抗者》中指出:“上帝的唯一借口就是他并不存在。”随后神父来劝导默尔索时,默尔索聚积已久的情感爆发,多次称自己不信仰上帝,认为神父说的虚无缥缈的话还不如女人的一根头发那样实在。上帝应该是不存在的,但是局中人几乎无一例外相信神真实存在,正如卡利古拉所说:“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消除人们内心中对于神明的渴望。”孔子直言“不语怪力乱神”“敬鬼神而远之”。人们努力探求世界的种种真相,而世界却报以无声的沉默,在这种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中,荒诞由此产生。人们追求真理,渴望找到世界的终极奥义,同时又被无情的现实打回,正因如此,人们永远在路上,永远在追求真理的道路上奋勇向前。默尔索是看清了这一点所以才坚称自己并不信仰上帝。
(四)充满人性的探求者
一个人是否热爱生活,其判断标准应该是对世界的态度,而不是把自己的社会角色扮演得多好。加缪在《西西弗的神话》中描述了这样一个场景:“起床,有轨电车,办公或打工四小时,吃饭,有轨电车,又是四小时工作,吃饭,睡觉;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星期五、星期六,同一个节奏,循此下去,大部分时间轻便易过。”[1]人们在这种现代化的生活节奏中迷失自我,就像汽车厂工人,每日按部就班上下班,没有真实感。而默尔索则是在这种荒诞中探寻出路,他虽然是一个局外人,但是却细致入微地观察生活并直观表达出来,默尔索感叹要不是因为妈妈,他现在应该可以散步而不是准备丧事,贯穿这部小说的“太阳”一直是默尔索所反抗厌恶的对象,这些感受都是默尔索最真实的体验。如果说谎言是对不真实的掩饰,那么默尔索给人们呈现的就是对世界和人最直观的看法,他不愿意迷失在荒诞中,愿从局中抽身离开,站在局外思考人生意义,默尔索不想被异化,要真正展现自己存在的价值。他比谁都要热爱世界,因为当别人被重复单调的生活所困扰而感到无奈时,默尔索始终观察着自己所属的社会,表达出自己的真实感受,与规则抗争。
因此,默尔索反而可以被视为头脑清醒、充满人性。他和西西弗一样勇敢,前者拒绝神父的布道,后者担负起永远推滚石上山的工作,蔑视诸神。默尔索则直面残酷现实,用自己的思想和“正义”的有神论者对话,坚持自己的信念,积极反抗荒诞带来的异化。他最爱说“无所谓”,但并不代表真的无所谓,反倒是默尔索认真体会人与社会关系的体现,在监狱时,默尔索在旧报纸上读到一则新闻:一个发了大财的男人带着他的妻子回到原来贫穷的农村,想给开旅店的母亲和妹妹一个惊喜,而晚上时母亲和妹妹却用锤子砸死了这个男人,事后母亲才知这是自己阔别多年的儿子,最后结果是母亲上吊、妹妹投井。默尔索读了许多遍却又觉得很自然,这说明他早已习惯了这个充满荒诞的世界,认为做人不应如“演戏”,而应该真实地展现自己的原貌。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当时的社会异化现象严重,最熟悉的人却成为了陌生人,以致于命丧黄泉。在这种无尽的荒诞中,默尔索仍能够保留本真,听从本心,思考社会背后的荒诞引发的种种矛盾,并积极地面对荒诞,反抗非人的社会以对抗世界的敌意,甚至希望别人在自己被判处死刑时发出仇恨的呐喊。所以,默尔索与“正常”社会中形形色色的人相比较,反而是一个敢于直面人生、正视矛盾、充满理性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