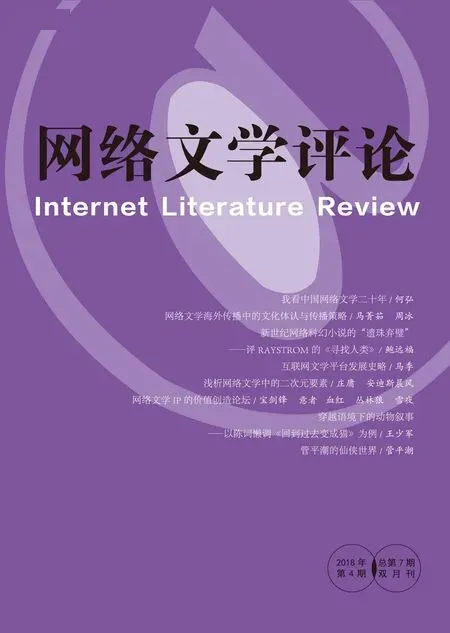论中国网络侦探小说的罪恶书写
侦探小说是反映社会现实的重要通俗小说类型,在法国文学理论家茨维坦•托多洛夫的理论概括中,被划分为“犯罪的故事”以及“侦破的故事”两个构成部分[1]。其中,“犯罪的故事”主要表现谋杀、抢劫、强暴、诈骗、偷盗以及故意伤害等一系列犯罪行为,是小说得以展开的重要基础。该部分提供了文本情节发展的“前叙事”内容,在时间向度上将侦探发生于当下的行为导向在此之前的过去,并在侦探将要完成的将来“解谜”事件中成为被还原的真相。基于此,从“犯罪的故事”层面切入,对侦探小说所涉及的罪恶书写进行分析,是研究侦探小说的重要路径。
新世纪之前的中国传统侦探小说,在表现“犯罪的故事”时存在差异,多数作品仅对事发过程以及场景进行概要描述,主要目的即为叙述“侦破的故事”提供重要动力,也暗示了“犯罪的故事”较之前者略逊一筹的真实地位。少数作品对罪犯心理进行描摹,虽对“犯罪的故事”有所侧重,但仍将其视为“侦破的故事”的附庸。诞生于新世纪之初的网络侦探小说,受开放且相对自由的网络创作环境影响,对上述创作倾向有所突破,趋向于重视“犯罪的故事”内容,并将罪恶书写作为小说文本的重要构成部分。具体来说,这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犯罪场景的恐怖化描写
在侦探小说中,“犯罪的故事”即是对人物犯罪行为的描写以及犯罪场景的展示。鉴于多数侦探小说是以倒叙的方式追溯人物的犯罪行为,犯罪场景成为“犯罪的故事”发生的初始呈现。多数网络侦探小说在对此进行描摹时,往往以直刺读者感官经验的文字,营造出一种“恐怖化”的场景氛围,亦展现其独特的美学追求。
由于侦探小说多以凶杀案作为主要案件类型,文本直接关涉了个体人的生死安危问题,其犯罪现场的重要指征自然是被害者的尸体。传统侦探小说在对犯罪现场进行描写时,往往采用精练简短的文字,对尸体状况以及现场其它物证进行介绍。网络侦探小说则反其道而行之,既对残破尸体以及残酷犯罪现场进行生动再现,亦以此暗示凶手的种种残忍且极端的犯罪手法,反映犯罪分子的凶残及其颇具暴力性的犯罪行为。雷米的“心理罪”系列中,主人公方木在形形色色的犯罪现场中,目睹过砍头、放血、分尸以及剥皮等极端犯罪手法遗留的血腥场景。秦明的“法医秦明”系列,则在描述案发现场后,让法医从专业角度,对护城河上漂浮的尸块、古井中倒吊的腐尸以及被野兽撕咬的残尸等,进行科学且有效的解剖以及分析。
较之上述作品,蜘蛛的“十宗罪”系列更以较长篇幅详尽描述具有“重口味”特质的案发状况,挑战阅读受众的心理承受水平:一座由四名学生肢体以及陌生女性头颅堆起的雪人出现在某大学宿舍楼下;野外探险的一群网友在某山洞中发现一口大锅,里面正煮着被开膛破肚的被害人尸体;一名年轻女性死在公厕中,身体上留下凶手所写的侮辱性字眼,胃中还有受到逼迫而吞食的粪便。除此之外,某些故事采取对比手法,在美好宁静的氛围中,以令读者猝不及防的方式引入血腥的场景描摹,使读者产生更为强烈的恐怖感受。“人皮草人”一案中,发生命案的武陵县即是中国古典名作《桃花源记》的故事发生地,亦被冠以“世外桃源”之名,尸体被发现时,“浓雾弥漫,蟠桃将树枝压成一道美丽的弧线,叶子滴着水,一个稻草人静静的伫立在果园里”[2],展现出的正是一派乡间的恬然景色。但这个“稻草人”正是真正的尸体,“那稻草人的头就是人的头,皮里面塞了稻草”,“整个头部从下巴底下整整齐齐割了下来,但是还连着一张皮,皮里面鼓鼓囊囊塞着稻草,没有穿衣服,手和脚也是稻草扎成的,看来凶手只割掉了头剥下了躯干的皮”[3],直接展现出行凶者的冷血以及残忍。
同时,部分作品刻意营造奇诡神秘的鬼魅氛围,以神鬼因素增添犯罪过程的离奇恐怖之感。校园深林中飘荡的白衣女鬼,怀中抱着婴儿,嘴里唱着“咝咝咝,白蛇仙活千岁,法无边飕飕飕”的童谣(《诡案组》);深山古寺中腾空跃起的无头鬼影,动作迅疾,在烟雾缭绕的背景中从一团黑影,幻化成没有头的人形(《凶画》);老屋阁楼中的破裂花盆中,一株铁树的根部包裹着已成白骨的骷髅头,在雨夜发出一声“你好”的问候(《十宗罪》)……种种关于“神鬼”的因素在文本中若隐若现,以一种近乎灵异的方式渲染常理难以解释的神秘玄幻,使得案件的发生以及侦破过程笼罩着令人“惊骇错愕,目眩心悸”[4]的色彩,亦使读者产生阴森恐怖的感受。值得注意的是,多数网络侦探作品,最终都试图对相应的“神鬼”影响给出科学解释,将文本从虚玄的想象产物还原为立足于现实的合理存在。
上述暴力、鬼神因素的使用,一定程度上被与网络作品的低俗化特质等同起来,成为网络侦探小说受到诟病的重要原因。但仔细审视这种文本处理方式,我们不难发现,其产生根源与网络平台具有密切联系。鉴于网络世界所提供的开放且相对缺失把关人的环境,创作者们会在作品中毫无保留地表达个人内心欲望,也借相应内容的表达,迎合大众阅读者的多重心理欲望,恰如法国学者雅克·拉康所言的“人的欲望就是他人的欲望”[5]。网络侦探小说的这种文字表述,首先即能帮助读者“接触到常人所无法触及的关于现代欲望社会的各种犯罪场景”[6],直接对其窥视和猎奇欲望提供代偿性满足。
在受好奇心驱使的旁观他者表层欲望之下,部分阅读受众的内心深处还隐藏着难以言明的暴力渴望。正如美国精神分析学家艾·弗洛姆所言,现实中仍然存在一类人,他们“嗜好残杀,并把残杀看作是超越生活的一种途径”,“对于这种人来说,血就是生活的本质;流血则是为了感觉到自己的存在,使自己成为独一无二的强者,从而凌驾于一切人之上”[7]。部分现代都市人仍持有这种原始嗜血欲望,但受制于当下社会法律以及道德规约,无法以具体直接的方式实现,却可通过文本中犯罪分子的极端残忍举动,获得一种替代性的宣泄。在这一层面,作品将读者心理深层富有破坏性的思想意识付诸想象中的现实,以虚拟化的方式对暴力冲动进行有效疏导。
更重要的是,通过对犯罪场景的表现,网络侦探小说的血腥以及鬼神要素描写也满足了读者内心对于恐怖刺激感受的获取诉求,使其产生“于一刹那顷,忽起异感而不能自制者也”[8]。生活于现代都市且沉浸于日复一日繁琐事务的受众,多数已为平庸、乏味的日常生活所累,部分甚至陷入麻木、空虚的精神危机之中。他们试图通过阅读获取一种心理刺激,进而从熟悉得近乎一成不变的现实中逃离,获得暂时的陌生化体验。恐怖感恰是这种体验的重要构成部分。但较之来源于现实的个人真实体验,这些文本提供的又是一种“他人代理的恐惧”,亦即“虚构的或实在的他者身陷险境”[9],使读者虽未直面险境,却仍处于虚拟的极端场景中,能够在自己的掌控中(成为小说中人却又随时可以抽身而出),体验罕见情绪,与恐怖感受保持一种若即若离且可以自我掌控的合适距离。
二、犯罪分子的立体化形象塑造
侦探小说往往将侦探人物作为主人公进行塑造,但在网络侦探小说中,罪犯人物也得到重视,成为多部作品的主要表现对象。不同于中国传统侦探小说多将罪犯处理为穷凶极恶、罪大恶极的单一人物形象,网络侦探小说试图将他们还原为日常生活中的普通人,审视他们的内心世界,剖析他们的犯罪动因,从多个角度进行人物塑造,使他们从此前刻板固定的扁平人物束缚中挣脱出来。在这些人物中,两类具有群体特征的罪犯形象颇具代表性。
第一类罪犯主要由生活于社会底层的普通人构成。于他们而言,物质条件匮乏以及精神世界压抑是个人日常生活需要面对的重要问题。基于此,在个人欲望驱使下,人物产生犯罪冲动却难以克制,最终付诸于实践,导致恶性事件的发生。网络短篇侦探小说集往往以这类罪犯形象作为主角,在相对较短的篇幅中直视人物的真实欲望,并探究其犯罪行为发生的心理根源。
在《十宗罪》一书中,“地窖囚奴”一案,犯罪分子从地铁站将富家小姐掳掠回家,囚禁在阴森幽暗的地窖之中,使其从此前风情款款、趾高气昂的优雅女性“变成了一具行尸走肉,一个眼神呆滞、浑身脏兮兮、脖子里锁着链子的女人”[10],其身心遭受的双重摧残令办案女警都心生惧意。故事中的罪犯被设置为养猪场老板,经济收入可观,但难以抑制对年轻貌美女性的强烈渴望,常采用窥视、尾随乃至骚扰的方式进行宣泄,直至最终采取绑架行为。这一切即导源于其年少的悲惨经历:被猪啃食脸部以致毁容,沉默寡言,生活在他人的歧视之中,迫使人物借助囚禁女性实现自身的控制欲,借以弥补个人尊严。与此类似,《尸语者》中的“沉睡之妻”故事中,丈夫体弱多病,与捡拾废品的妻子过着清贫的生活,在别人眼中一直是模范夫妻,却饱受自卑心理影响,受到妻子言语刺激后,一时冲动将妻子闷死,并教唆儿子撒谎掩盖罪证。这类人物长期承受来自外界或他者的压力,心理世界逐步扭曲,本身是相应问题催生的“受害者”,却因自身的暴力犯罪行为,成为旁观者眼中穷凶极恶的犯罪者。
同时,部分底层人物“之所以犯下不可饶恕的罪行,并不是因为他们的天生恶性,而只是因为他们遭遇了常人不会遇见的人生选择”[11]。秦明在《尸语者》的“大眼男孩”一案中,将溺死在池塘中的男孩父亲设置为杀死儿子的真凶,用竹棒将其按压在水下直至窒息,其动机正是经济窘困,兼之希望帮助儿子从多年难以治愈的疾病痛苦中解脱出来。而《十宗罪》中的“肢体雪人”,残杀四名女大学生并将其肢体拼接为雪人四肢的罪犯,是一名乞丐,因为心爱的姑娘被女大学生酒驾撞死,但对方只想出钱私了,却不顾自己的感受,只能采取极端手段为爱人报仇。
第二类罪犯则是具有专业知识的高智商群体。他们在现实中遭受不公待遇,对法律等手段丧失信任,决心依凭个人力量完成报复或“惩罚”行为。这些人物借助专业知识设计犯罪过程,并以缜密的思维逻辑以及过硬的心理素质与警方斗智斗勇。他们即是罪犯中的“翘楚”,与优秀的刑警具备“很多相同的特质:敏锐、缜密、冒险性、求知欲……他们相象得就如同是一个硬币的两面。而窥探对面的状态,永远是他们最想做却又最难做到的事情”[12]。这在一定程度上,淡化了小说的正邪对立色彩,也将侦探小说案件关涉的重点从人命安危转向智力对决。因为对决的内容需要以较长的篇幅进行展示,这些人物成为网络侦探长篇作品乃至系列作品所塑造的主人公形象。
紫金陈在网络侦探小说“谋杀官员”系列中塑造了一系列同类犯罪分子形象:《逻辑王子的演绎》中的数学天才徐策、《化工女王的逆袭》中的化学翘楚陈进,以及《物理教师的时空诡计》中的物理高手顾远。他们都曾面对过至亲好友殒命的悲惨现实,在深究事发原因之后,都将罪责归咎于以权谋私以及违反乱纪的部分政府官员,所以运用个人最为擅长的专业知识,以一己之力进行了数场打着“复仇”旗号的谋杀行动,最终又凭借个人才智从案件中全身而退。其中,顾远即为典型代表。他作为中学物理老师,将基础物理知识化用到杀人过程中:他计算出被害者的步行速度以及石板落地的自由落体运动情况,在其走进单元门之前将其砸死;他以滑轮和绳索组合,将被害人置于山崖之上摔死;他借助多部电话相互连通的声波传递,点燃案发现场并伪装自杀,成功制造出一起起接近完美的“不可能谋杀”。
同时,这类犯罪分子的心理变化过程也能与其犯罪活动形成重要对照关系。雷米的“心理罪”系列可被视为典型例证。在《第七个读者》中,吴涵杀害诸多借阅同一本书的学生,最初原因只是书中可能夹杂着泄露其个人隐私的重要物证,而部分事情的发生让他捕风捉影,认为其中有人知晓其秘密,所以必须灭口。随着事情水落石出,谋杀行为本该结束,但吴涵并未停止杀戮,反而沉迷于这场游戏,因为这让他产生了一种虚无的自我满足感,让他觉得“我发现了我的力量,我有能力把握一个人的生命。看到你们的恐惧,惶惶不可终日,看到警察费尽心思却找不到一丝线索,我感觉——”“我,我是神!”[13]《画像》中的孙普,本身是从事犯罪心理画像研究的高校教师,但因早年的严重刑侦行为失误,被迫远离自身擅长研究领域。其后人物一直生活于不得志的压抑环境中,内心对功成名就充满强烈渴望,后来本可通过侦破新的案件重返工作岗位,却被方木抢占破案先机。失去证明自身的机会后,人物本已扭曲的心理世界彻底崩溃,所以采用模仿世界知名杀手的方式制造凶杀案,向主人公进行挑战。在这些人物的认知中,本应具有重要价值的人的生命,彻底失去其原有价值,而沦落为辅助自己完成目的的工具,人物的心理世界呈现出一种趋向变态的发展态势。
上述两类人物形象的塑造,体现出创作者的共同创作意图:还原罪犯的本真面貌,将其视为一个具有七情六欲的普通人,而非单纯背负“十恶不赦”罪名的恶人形象。美国侦探小说作家雷蒙德·钱德勒曾对谋杀行为进行阐述,认为其体现出个人意志的受挫[14],这些犯罪分子的内心描写恰是其意志受挫的直接印证。这也与此前的中国侦探小说具有鲜明区别,并未如前者一样直接从道德和法律角度对犯罪分子予以抨击,而是真实展现出其重要心路历程,揭示其逐步走向犯罪的过程,借以完成相应目的。这在一定程度上,使他们成为E.M.福斯特提出的“圆形人物”,具有立体化的特质,而非多数类型小说善于塑造的“扁形人物”。这种处理方式,一方面给予罪犯以“言说”的权利,以他们个体的思想情感展现,拉近阅读受众与人物的距离,另一方面则以他们个人际遇的展示以及陈述,直指导致他们走上罪恶之途的不合理制度、现状等现实原因,从而使中国的网络侦探小说在借鉴日本社会推理派侦探作品的基础上,成为直刺社会现实弊病的重要文本。
三、犯罪结果的“正义化”性质探讨
与上文所分析的高智商犯罪分子形象塑造具有密切联系的,是网络侦探小说在处理部分人物的犯罪结果时,呈现出的一种重要倾向:对犯罪结果的探讨逸出了社会法制的范畴,从事实判断转向价值判断,并侧重从伦理学角度的善、恶两个维度进行研究,也对侦探小说一直秉持的“正义”主旨形成反拨。
紫金陈在多个系列的作品中都采取了相同的情节设置:小说开头讲述犯罪分子的犯罪动机,即人物的至亲好友被不公正对待后殒命,人物本着复仇的目的,运用种种计谋、机关,杀害相关责任人,多数情况下都实现了既有目标,同时自己也从案件中脱身而出,并未受到法律惩罚。以《逻辑王子的演绎》为例,文中的罪犯徐策本人已在海外生活,但家乡的祖宅忽被界定为“违章建筑”,以极为不合理的方式遭遇强拆。在阻止强拆的过程中,他的母亲被房梁的落石砸中当场身亡,却被认定为“妨碍公务造成的意外事故”,只获得少量赔偿金。涉事人员以及主管政府官员基本都未承担应有责任。这一人物遭际命运即为现实生活的直接映射,隐喻着种种不公的社会现实,即部分政府公职人员利用个人权力为非作歹、草菅人命,亦为罪犯的相应行为提供合理解释,使其获得阅读受众的同情。基于此,小说讲述了徐策的主要经历:以各异方式杀死上至局长下至办事员的所有涉事人员,最终成功嫁祸涉事的一位官员,将自己从案件中成功解救出来,并远赴美国。
徐策以及紫金陈笔下的部分罪犯形象采取了同样的行为方式,即打着传统的“血亲复仇”或相关旗号,以个人的特异方式向社会黑暗现实宣战,最终以一己之力实现了自认为的社会“公平正义”,即作恶者付出生命代价,自己也并未受到法律惩罚。这种结尾方式在一定程度上背离了侦探小说的一贯结局——凶手伏法、社会秩序得以恢复,对该类小说的既定正义主题形成消解。尽管罪犯凭借个人悲惨际遇以及内心真实心理活动,获得阅读受众的同情甚至认同,使读者从传统的追随侦探查找真凶阅读路径中走出,发展出一条新的追随罪犯躲避警探追寻的阅读路径。但审视人物的行为本质,读者不难发现恰是这些人物将所谓“正义”转化成为一种个体复仇,仍以最为原始的以牙还牙方式化解仇恨,在实现个人目的的同时也对侦探小说的正义主题形成解构。
近似的小说情节设置出现在周浩晖的《死亡通知单》作品系列之中。作品塑造了一个替天行道的罪犯“Eumenides”。他出于对种种社会不公现象的义愤,以“替天行道”的姿态惩治违法犯罪但并未受到法律惩罚的人。较之紫金陈笔下的复仇者,他更像是置身事外纯粹为受害者打抱不平的侠义人物,以那些违背法律却成功逃脱惩罚的人为对象,向他们发出“死亡通知单”,以私刑结束其生命。在马路上压死老人的女司机、收受贿赂的公安局长、横行全市的黑社会老大……无一逃脱其制裁。在他的认知中,“法律惩治不了所有的罪恶。权势高的人可以凌驾在法律之上,狡猾的人可以躲在法律照耀不到的阴暗角落中”[15]。正因如此,他将自己凌驾于社会法律之上,视自己为社会正义的化身,并坚持自己采取的方式才是惩治罪恶的终极方法,只是以一种“残酷的正义”方式实现最终目的。
不管是“谋杀官员”系列作品中的高智商犯罪者,还是《死亡通知单》系列小说中的“替天行道”者,小说中的罪犯行凶结果似乎实现了一种个人性的正义,即依循传统恩仇必报逻辑、满足个体“公平”诉求并惩治有罪者。但仔细考察这种犯罪行为的实质,其“伪正义性”不言而喻:一方面,心有不平者会在“行侠仗义”的“正义”观念感召下,竞相模仿该行为,纷纷采取以暴制暴的方式,惩戒被自己认定的违法者;另一方面,心有愤恨者会直接越过法律,以个人方式向仇敌复仇,因为缺少法律的规约,导致复仇行为在私人化的情感影响下,代代相传且循环往复。
基于此,保证“自由和机会、收入和财富、自尊的基础”[16]得到平等分配的社会公平正义自然难以实现,人物行为反而会彻底“激发起城市中的暴戾之气”,使其变成“一个巨大的垃圾箱,各种所谓丑恶宛如粘在箱底的腐臭秽物,被统统翻了上来”[17]。在这种情况下,“杀戮,似乎成为实现正义与公平的唯一手段”[18]。以此观之,他们的所作所为是一种凌驾于人类意志上的犯罪行为,虽以正义的名义进行,但实质上已触动人类最基本的公平信念与法制基础。更重要的是,他们的行为在本质上亦属于恶行的一部分,其动机正是美国心理学家罗伊·F.鲍迈斯特尔所提到的恶的四个根源之一——理想主义,即“当人们坚信他们站在正义一方,正在致力于改善世界时,他们经常觉得运用强硬手段来对付反对他们的恶势力是正当的。人们经常用目标之高尚来证明暴力手段的合理”[19]
诚然,上述行为有助于直击现代社会的丑恶现实,暴露现行法律制度的疏漏以及社会道德规章的失范,但与真正社会正义的实现南辕北辙。所以在《死亡通知单》结尾处,警察罗飞强调以法律作为执法人员行为的最高准则,还以受害者公道,亦是对“谋杀官员”系列作品中复仇者行为的最有效回应。正是通过上述不同小说创作意旨的展现,网络侦探小说以其对犯罪结果的描写,完成了“何为正义”的曲折渐进式探讨,以人物的相应行为引发读者进一步思考,并体现出创作者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亦呼应了传统侦探小说的一贯正义主题。
从对犯罪场景的血腥以及奇诡描写,到对犯罪人物形象的立体化塑造,兼及对犯罪结果的“正义化”性质探讨,网络侦探小说在犯罪书写方面实现了对传统作品的反拨。网络平台在其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恰对应着上述分析的三个方面。首先,网络世界提供了一个开放且相对缺失把关人的环境,使网络文学作品的创作毫无保留地体现出创作者以及接受者的内心欲望。这反映在网络侦探小说作品中,即是对犯罪场景及其隐藏的犯罪过程的恐怖化描摹,种种重口味且具有刺激性的内容展现,迎合的是大众阅读者的猎奇、窥视、冒险以及暴力宣泄欲望。其次,网络世界的多元性,意味着相应作品打破了传统文学的固有界限,类型文学创作也逸出其原有范畴,促进创作者思考全新的文学内容阐释可能。于网络侦探小说而言,罪犯形象亦从单一的平面化维度转变为具有丰富性的立体化存在,较之传统侦探小说即有所发展。再次,网络世界所提供给公众的互动平台以及对其参与感受的满足,在文学作品中也得到相应展现。网络侦探小说正是通过探讨犯罪结果的实质性质,对现实社会中的公众情绪以及认知进行直观再现,以“个体人”的生存境遇影射整个社会的重要发展动向,并通过解构以及重新建构正义主题的方式,完成了对传统侦探文本的突破。
[1]茨维坦·托多罗夫:《侦探小说类型学》,收入《散文诗学——叙事研究论文选》,侯应花译,百花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第5页。
[2]蜘蛛:《十宗罪》,湖南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第95页。
[3]蜘蛛:《十宗罪》,湖南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第97页。
[4]周桂生:《<歇洛克复生侦探案>弁言》,收入任翔、高媛主编《中国侦探小说理论资料(1902-2011)》,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8页。
[5][法]拉康:《拉康选集》,褚孝泉译,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625页。
[6]孙绍振:《城市与侦探文本》,收入任翔、高媛主编《中国侦探小说理论资料(1902-2011)》,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468页。
[7][美]艾·弗洛姆:《人心》,孙月才、张燕译,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21-22页。
[8]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收入任翔、高媛主编《中国侦探小说理论资料(1902-2011)》,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4页。
[9]拉斯·史文德森:《恐惧的哲学》,范晶晶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91页。
[10]蜘蛛:《十宗罪》,湖南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第92页。
[11]周浩晖:《死亡通知单》,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9年版,第248页。
[12]周浩晖:《死亡通知单》,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9年版,第85页。
[13]雷米:《心理罪之第七个读者》,重庆出版社2015年版,第209页。
[14]雷蒙德·钱德勒:《谋杀的简单艺术》,董乐山、石蓝译,新星出版社2008年版,第4页。
[15]周浩晖:《死亡通知单》,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9年版,第85页。
[16]约翰·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译者序言第7页。
[17]雷米:《心理罪之城市之光》,重庆出版社2012年版,第371页。
[18]雷米:《心理罪之城市之光》,重庆出版社2012年版,第371页。
[19]罗伊·F·鲍迈斯特尔:《恶——在人类暴力与残酷之中》,崔洪建译,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第49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