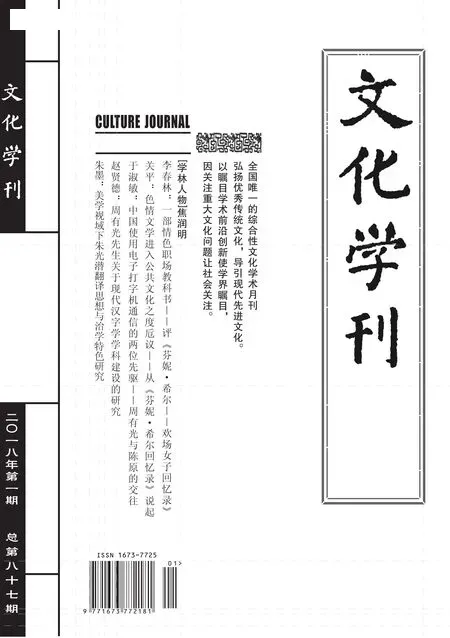地方性民间传统节日复兴的社会功能分析
——以广东省高要市“茶果节”为例
邓伟秀
(肇庆学院,广东 肇庆 526061)
“茶果节”又称“行村”“行社”,是高要市宋隆河流域的一个传统节日,以白土镇最为流行,其始于何时,尚无确切考证。高要市已把“茶果节”申报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本文主要以白土镇作为分析对象。
一、“茶果节”的来源与节俗活动
当地传说远古时代有一种瘟神(魔怪)为害百姓,使宋隆河流域不时发生水旱灾和瘟疫等。人们为了驱走瘟神,祈求丰收平安,便在每年的正月、二月选定某些日子举行“茶果节”。“茶果节”最重要活动是“放花船”。
“放花船”就是将瘟神捉入花船,放入江河,流出大海。道士手执铜锣,边敲边唱:“行滩锣鼓喜连连,敲起明锣就开船,读书君子讲书篇,耕田男女讲时年,……”一直唱到驱邪出外,引福归堂。[1]
在道光《高要县志》中,记载有“每岁冬月盛为法事谓之‘禳灾’,又谓之‘保境’,作纸船鼓吹送之江”[2]的风俗,与上述传说“茶果节”道士作法最后“放花船”相符,只是时间在年末。现时本地已没有这类活动(粤西茂名等地的“年例”也多在农历一、二月,大多还有“放花船”的类似习俗,可作参考)。在道光《高要县志》中还记载,春节后当地村民“罗设果酒粉饵,送香于坛庙。亲友相厚者携节物致敬,数日乃已。”[3]确是与现时“茶果节”的节俗相类似。白土镇“茶果节”现存的节俗活动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拜祭活动
拜祭包括神灵和祖宗两类。神灵主要是“社公”(土地神)、灶君,“社公”位于村外的一处空地,只有一块石碑,灶君在自家灶头拜祭;祖宗包括开村以来的列祖列宗、自家祖先,在祠堂进行拜祭。依现时本地风俗,春节典型的拜祭供品有一只鸡、一块长条状的猪肉、三碗饭、三双筷子、三杯酒,还有各类点心、水果、糖果等。与春节比,“茶果节”的拜祭活动已日渐简化,多数人家只是烧元宝蜡烛香,很少或不摆供品。
(二)煮“茶果”
“茶果”既非“茶”亦非“果”(本地不以产茶或果见长),而是以稻米粉(也有部分用面粉)为原料制作的各类点心,“茶果”是本地人的叫法,主要品种有煎堆、油角、各类糕等,还有本地特产裹蒸粽。村民们早早备好原料,节前一天就开始煮“茶果”,通常要忙通宵。“茶果节”当天,客人一进屋就能吃上还在冒热气的“茶果”,感受主人的热情。按习俗,客人离开时,主人要送上一袋“茶果”,感谢客人参加“茶果节”。
(三)午饭
准备一顿丰盛的午饭是各家各户在“茶果节”当天最重要的事情,原因在于,“茶果”是应节食品,没有当然不行,但不是主食。客人来到,主人会招呼吃“茶果”,吃与不吃,主随客便,但对午饭则极为重视。“茶果”可以吃过一家又一家,但午饭只能在一家吃。如果客人只是吃了“茶果”而没有留下吃饭,虽然也算走过亲戚,却留下某种疏远的感觉,即是否在某家吃饭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客人与主人的亲疏关系。过去“茶果节”一般是中午吃一顿饭就结束,现在越来越多的家庭会挽留客人吃晚饭。
(四)娱乐活动
白土镇各村都有自己的醒狮、武术队。“茶果节”期间(尤其是旧历年初)通常会有表演活动。笔者前年在横江村“茶果节”上,还看到过粤剧表演。
二、“茶果节”的社会功能分析
“文革”期间“茶果节”近乎停办,改革开放后,“茶果节”逐步恢复并日趋火爆。节日源于人们的需要,许多传统节日随着时代的变迁、社会的发展不再满足人们的需要而日渐衰落。“茶果节”这一乡村传统节日,没有官方的主动介入,经过农民的自发改造,今天发挥着多种社会功能,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本地农民多方面的需要,这是其古旧却能重新兴盛的根本原因。
(一)表达祈愿,调适身心
在生产力极为低下、科学技术不发达的古代,人们在面对各种灾害且自身无力抗衡时,不得不求助于某些超自然的力量。“茶果节”无论是起源于“纸船明烛照天烧”的禳灾活动,还是起源于春祈秋报的社祭活动,都反映了古人的这种心理。西江横贯高要,历史上经常发洪水,“肇庆有西水自广西来,每岁夏至后,淫雨暴涨”[4],白土镇位于高要市东南部,距西江只有约三千米,深受西江洪水与内涝之害。本地以种植水稻为主,稻田经常被淹浸,“除了山脚和堤边的少数高地以外,大部分是十年三收的大禾田”。[5]
解放后,随着水利设施的建设和完善,水灾问题基本得到解决。此外,农村医疗卫生条件的改善消灭了过去人们谈虎色变的瘟疫。这些变化,使“茶果节”的迷信色彩越来越淡化,“送花船”等仪式再也无人提起,但人们面对的依然是一个充满未知的世界。马林诺夫斯基指出:“人事中有一片广阔的领域,非科学所能用武之地。……不论已经昌明的或尚属原始的科学,它并不能完全支配机遇,消灭意外,及预测自然事变中偶然的遭遇。”[6]通过“茶果节”禳灾祈福,仍旧是广大农民达致心理平衡的一种熟悉的形式。
与此同时,“茶果节”对现实生活的心理调适功能日渐凸显。改革开放后,本地农村发生了巨大变化,青年人大多离开农村进入城市,父母子女之间因此多了一份牵挂。中国农民素有安土重迁、追求稳定的文化心理。虽然现在交通、通讯非常方便,但一年一度的“茶果节”家人之间的团聚,各个家庭仍然十分重视。本地习俗,清明节期间,男孩一般会从外地回家拜祭先人,女孩则基本不回。中秋节回家团聚的情况也不如“茶果节”。此外,春节是各家各户团聚,“茶果节”则有很多客人来。对那些长年在外打工,每天在规范化、程序化的流水线上忙碌的年轻人来说,“茶果节”是一年之中与亲戚朋友交流的最好机会,是摆脱束缚、释放身心的最佳时机。为了过“茶果节”,很多年轻人春节后推迟上班,或从工作的地方如广州、深圳等地赶回来,父母也不会因为经济上是否划算而有微词。在今天这个充满竞争的社会里,一家人与亲戚朋友隆重热闹地过“茶果节”,使各人的身心都能得到滋润。
(二)传承传统,延续认同
举办“茶果节”的单位,不是行政村,而是自然村,更确切地说是“门楼”。一个行政村里,即使同宗同姓,也不一定在同一天过“茶果节”;同一个“门楼”的人们,则一定是同一天过“茶果节”。所谓“门楼”,是指由村外道路进入村内巷道、具有代表本宗族意义的一个牌坊。本地农村传统的住房布局,最外面的一排房屋门口朝里,村内巷道不直通外面,“门楼”成为进出村子的唯一通道。“门楼”是一个人地结合的概念,既指“门楼”后的居住区域,也指居住在内的宗族。“门楼”与“门楼”之间有大路,水塘、山丘等自然分隔,如果紧靠在一起,巷道一般也是不相通的。同一个“门楼”的,大家是同祖宗的叔伯兄弟,彼此熟悉;而对于另一个“门楼”的人们,虽然看起来脸熟,也可能叫不出名字。同一个“门楼”的人们,有共同的祠堂,供奉同一个开村祖宗,用同一个姓氏,喝同一口井水。在“茶果节”这天,村里一派浓浓的节日气氛:从四面八方络绎不绝涌来的宾客;停满路边阻塞巷道的车辆;房间摆不下不得不搬到露天的筵席;主人客人脸上写满的笑意……置身其中,村民自然而然就会产生:今天是我们村的“茶果节”。同一个“门楼”的人们,在同一天以同样的仪式过同一个“茶果节”,对外把自己与别的“门楼”相互区隔,对内则守护、传承着共同的传统,凝聚、延续着对宗族的认同。
(三)维系感情,促进交往
参加“茶果节”的客人,包括亲戚和朋友两类。亲戚根据与主人的亲疏关系分成两个层次。核心层是至亲的血亲、姻亲,即丈夫的姐妹和姑姑,妻子的父母和兄弟姐妹,这类客人如果住在本地,主人是否发出邀请不具有实质意义,节期一到,他们自然就来。有的还会提前来帮忙,提供做茶果的米粉、请客的肉菜等;如果有客人因为某些事情来不了,会特别对主人说明,彼此间也容易谅解。第二个层次,是比上述关系疏远些的客人,如表姐妹等。有的会专门发出邀请,有的则具有随机性,如在路上遇见则会邀请他们参加,这类客人来与不来有一定的随意性,原因在于客人在举行“茶果节”的村子里可能还有其他亲戚。本地40岁以上的大多数婚姻是在方圆10里以内的村庄之间形成的(近年结婚的年轻人有较大程度的改变),且夫妻双方基本上都有三个或三个以上的兄弟姐妹,再加上父母辈的亲戚关系,客人在举行“茶果节”的村子里有多个亲戚的情况是比较常见的。
中国人重视人情伦理,尤其注重亲戚间的人情往来,“茶果节”体现了费孝通先生描述的中国人人际交往中的“差序格局”的特点。核心层次的关系,是与自身家庭最亲密、最重要的社会关系,是每个家庭必须尽力维持、不能割舍的关系,谁要是在这一重关系中出了问题,必为旁人侧目,每个家庭都会十分重视有着这种关系的亲戚家的“茶果节”。很多村子的“茶果节”紧紧相连或相差几天,姐妹们可能今天在兄弟家过了“茶果节”,改天又在自家迎接兄弟们。通常情况下,核心层次的亲戚间除了婚丧嫁娶等大事外,平常大多是父母子女、兄弟姐妹间一对一的交流互动,但婚嫁等大事不是每家、每年都会有,因而“茶果节”为亲戚间的交往,提供了一个固定的平台,起着加强联系、增进感情的作用。在第二个层次里,随亲缘关系的疏远,主客间“茶果节”的交往出现较大分化。影响彼此关系的因素,除亲缘关系外,还有主客双方以往的交往频次、深度。因而,即使是具有同等亲缘关系的不同亲戚,他们与主人家的关系也会有较大区别。乡村社会交往既基于血缘的亲疏关系,也讲究交往的对等性,即所谓的礼尚往来。节日是文化再生产的重要手段,年复一年的“茶果节”也再生产出乡村社会的交往文化。
“茶果节”在过去基本上是一个基于血缘、地缘的节日,参加者都是亲戚,住在本地。改革开放后,农民从事的行业越来越多,外出务工越来越远。被邀请来参加“茶果节”的,不再限于亲戚,职场工友、生意伙伴越来越多;除本地的客人外,来自“珠三角”其他城市的客人也越来越多,主人对这类客人比较重视,会预先做好安排。青少年是“茶果节”最活跃的群体,本地习俗中,未结婚的都不算“大(成)人”,他们到别人家做客,可以不带礼物,不需要有主人的邀请,这种交往文化与青少年的个性正相吻合。无论是在校学生还是已经参加工作的,只要找到一点关系,就成群结队去参加“茶果节”。
(四)活跃经济,交流信息
“茶果节”具有明显的经济效应。一是形成节日消费。每家每户“茶果节”的客人越来越多,消费的金额越来越大。年后各村陆续迎来“茶果节”,为本地春节后2~3个月的市场提供了较高的需求。每逢“茶果节”,不但本村市场卖菜卖肉的销量大增,圩镇也比平常更旺,越来越多的人家选择到圩镇上买菜。“茶果节”当天,各式小贩,卖水果的、卖玩具的等,摆满村道两旁。二是促进了农村住、用、行、娱等的消费升级。“珠三角”的很多农民对城市的生活非常熟悉,“茶果节”成为他们向亲戚朋友展现自己不断改善的美好生活的良机。有些客人来自城市,主人也会想办法让他们感觉舒适些,如一个去年参加工作的大学生,因为要邀请佛山的十多个朋友参加今年的“茶果节”,专门改造了家里的卫生间。
“茶果节”也是农民信息交流的重要平台。参加“茶果节”的亲戚,除彼此熟悉的至亲外,其他亲戚可能是一年甚至几年才见一次。有些亲戚,虽然没留下吃饭,也会抽时间来坐坐,聊聊天。随着农民职业的多样化、农村社会的分化,农民及其家庭彼此之间的差异越来越大。因此,即使同是农民,亲戚们谈论的话题也是很多的。“茶果节”的开放性使来自城市或其他地方的客人越来越多,这类客人有着不同的地域和职业背景,教育程度各异,每年的流动性比较大,其使主客间交流的信息含量较高,他们带来城市或异地的文明,对提高农村、农民的文明程度有积极影响。
[1]高要新闻中心.宋隆“茶果节”[N].高要,2010-03-08(003).
[2][3][4]夏修恕.高要县志[Z].刊本,1826.
[5]张盛炜.高要解放前后的洪涝旱灾[A].政协高要县文史资料委员会.高要文史(第七辑)[Z].整理本,1991.
[6]马林诺夫斯基.文化论[M].费孝通,译.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7.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