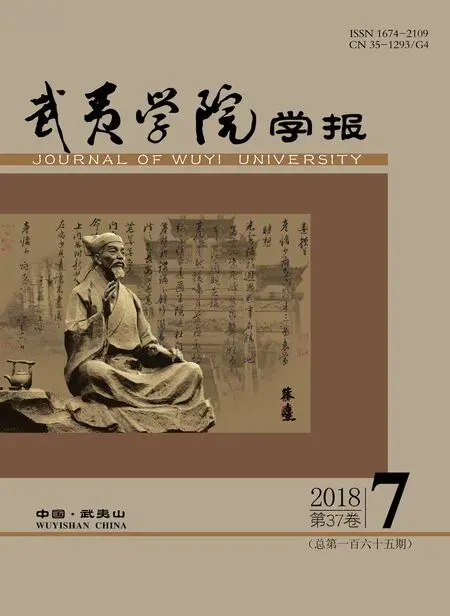义利之辨:传统义利观的嬗变及其启示
——从朱熹到康有为
许 彬
(1.武夷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福建 武夷山 354300;2.武夷学院 朱子学研究中心,福建 武夷山 354300;3.福建省统战文化武夷山研究基地,福建 武夷山 354300)
义利之辨是贯穿着历史与现实的重要话题。南宋朱熹在继承先秦儒家重义轻利观念的基础上,引理入义,赋予“义”以本原地位,在义利观念上主张重义轻利和以义制利的价值取向。时至清末,康有为在救亡图存的时代境遇之下,批判宋儒徒陈高义,忽视功利的倾向,并在此基础上提出重利兼义和以义生利的思想观念。义和利源于人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义利之间是辩证统一的,同时作为社会道德原则,崇尚道义又具有超越功利的普遍意义。
一、重义轻利,安贫乐道———朱熹义利观的主要内涵
众所周知,在义利之辨问题上,先秦儒家就已经形成了比较丰富的思想主张,这是朱熹义利观形成的主要来源。朱熹继承先秦儒家义利观念,并结合其理学体系,更加系统地阐发了义利观念。
(一)引理入义,重义轻利
在义利问题上,朱熹将理引入义中,赋予义以同属于天理的地位。他说:“义者,天理之所宜。”这就是说,判断一个人的心理和行为是否合宜,就看其符不符合天理。朱熹引理入义,并没有将“义”悬置于形而上的世界,而是将其纳入活生生的现实生活之中。他说:“义者,心之制,事之宜”[1],“义如刀相似,其锋可以割制他物”[2]。“义”就像一把利刃,裁制由于“人情之所欲”[1]而产生的种种功利。朱熹引理入义,将义与理相统一,在义利观的理论预设上,构建了“义”的本原性地位,目的则是确保义对于利的主导作用和优先地位。不过,对于“利”,朱熹并没有一概否定,正如他言:“利,谁不要”,“利不是不好”。[2]虽然如此,他对未经省思的欲望却表示出深深地担忧,因而他在论及义利之辨时,往往更加强调道义的衡量与裁制作用,总体上呈现出重义轻利,以义制利的价值取向。他说:“凡事不可先有个利心,才说著利,必害于义……盖缘本来道理只有一个仁义,更无别物事”,“义利,只是个头尾。君子之于事,见得是合如此处,处得其宜,则自无不利矣。但只是理会个义,却不曾理会下面一截利。小人却见得下面一截利,却不理会事之所宜”。[2]朱熹先义后利的观念与荀子“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荀子·荣辱》)的思路一脉相承。循着以义为先的主张,朱熹推出以义生利的效果,他说,“盖凡做事只循这道理做去,利自在其中矣”,“圣贤之言,所以要辨别教分明。但只要向义边一直去,更不通思量第二著。才说义,乃所以为利。固是义有大利存焉”。[2]言下之意,若是向义而行,利便不求自来,义中必有利。
(二)尚公轻私,安贫乐道
虽然说“利”是人人想要获得的东西,但朱熹更多论及的却是为人之公利。他在注解《孟子·梁惠王》篇中说:“梁惠王问利国,便是为己,只管自家国,不管他人国。义利之分,其争毫厘。”[2]即便如梁惠王是求一国之利,在朱熹看来也不值得肯定,因为这仅仅只是为一诸侯国之私利,与为天下之公利有根本性的区别。“义利之分,其争毫厘”,毫厘只差,恰在于公私与否。朱熹又言:“或问义利之别。曰:只是为己为人之分,才为己,这许多便自做一边去。义也是为己,天理也是为己。若为人,那许多便自做一边去。”[2]从功利的角度看,朱熹认为应该追求为人之公利;从恪守道义的角度说,他认为应该做好修身为己之学。相反相成,无非就是要牢牢把握道义的准则,对于这一点的强调,朱熹可谓是乐此不疲,不遗余力。他从内外之维加以阐明,他说:“大凡为学,且须分个内外,这便是生死路头……从这边便是为义,从那边便是为利;向内便是入圣贤之域,向外便是趋愚不肖之途。”[2]朱熹持守内圣之道,强调反躬内省的工夫论,这与永嘉学派向外务实的事功主义路向悬殊。
朱熹又从“存天理,去人欲”的角度,指出:“仁义根于人心之固有,天理之公也;利心生于物我之相形,人欲之私也。循天理,则不求利而自无不利;殉人欲,则求利未得而害己随之。所谓毫厘之差,千里之缪。”[1]朱熹认为人应当循天理、依仁义、持义心,这样便无往而不利,而判断君子与小人之别,关键就在于对义心与利心的领悟上,他说:“小人之心,只晓会得那利害,君子之心,只晓会得那义理。见义理的,不见得利害;见利害的,不见得义理。”[2]具体来说,“且如有白金遗道中,君子过之,曰‘此他人物,不可妄取。’小人过之,则便以为利而取之矣。”[2]可见,朱熹所肯定的利只是践行天理与仁义的自然结果。纵观其一生,大多处穷困潦倒之境遇,但是他却能够安贫乐道,怡然自得,这正是其坚守道义的真实写照。他说:“君子之于义,见得委曲透彻,故自乐为。小人之于利,亦是于曲折纤悉间都理会得,故亦深好之也。”[2]安贫乐道是儒家的价值理念和精神境界的追求,朱熹在注解《论语》“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时,说:“圣人之心,浑然天理,虽处困极,而乐亦无不在焉。其视不义之富贵,如浮云之有无,漠然无所动于其中也。”[1]圣人之心浑然天理,具备至高的道德境界,对于不义之荣华富贵,视作枉然,不滞于心。朱熹持守的淡泊名利,安贫乐道之精神,与箪食瓢饮的孔颜之乐一脉相承。
二、重利兼义,以义生利——康有为对朱熹义利观的批判与改造
清末民初之际,遭受西方坚船利炮的欺凌,康有为身处三千年未有之变局,肩负救亡图存的时代诉求,他批判朱熹等理学家重义轻利、以义制利的价值取向,主张自然人性论,强调人欲的合理性和功利的重要性,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义利兼顾和以义生利的价值观念。
(一)天欲而人理,“性全是气质”[3]
朱熹重义轻利、以义制利的观念与其“存天理,去人欲”的哲学思想相统一。康有为对朱熹义利观的批判就是从批判理欲观开始的,他甚至将天理和人欲颠倒过来,转而表述为“天欲与人理”。他说:“婴儿无知,已有欲焉,无与人事也。故欲者,天也。程子谓‘天理是体认出’,此不知道之言也,盖天欲而人理也。”[4]人欲在康有为这里得到了极大的肯定,乃至上升为天欲,他进一步认为,“凡为血气之伦必有欲,有欲则莫不纵之,若无欲则惟死耳。”[4]实际上,在朱熹“存天理,去人欲”的思想中,“人欲”指的是不符合天理的不良欲望,比如私欲、贪欲等,而符合天理的欲望,朱熹则是完全肯定的,如他所说的“饮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2]。康有为未加审视朱熹道德伦理学中“人欲”概念的真实内涵,他的“凡为血气之伦必有欲,有欲则莫不纵之”的“纵欲”言论,对于宋儒“绝欲而远人”[5]的批判,实有矫枉过正的局限性。然而,在“万马齐喑”的晚清社会,康有为对欲望的倡导,却又是有思想解放和推动社会发展的积极意义。
康有为“天欲而人理”的判断,与其自然人性论主张密切相连。他不赞同人性本善,认为“性全是气质”[3],进而批判“宋儒每附会孟子性善之说”[6],认为告子无善无恶论近于理。他说:“人性之自然,食色也,是无待于学也。”[7]在康有为的论述中,不管是“天欲而人理说”还是“性全是气质论”,其视角都是基于批判朱熹理欲对立、性有二分等的理论预设而进行的,其目的是希望通过强调气、欲、情等主体地位的理论阐发,将朱熹的天理论化为人理论。因此他批判“宋儒专以理言性,不可”[5],认为“‘性即理也’,程子之说,朱子采之,非是”[7]。他认为程朱理学中“以礼信为性,是不识性也”[7],理由在于“实则性全是气质,所谓义理自气质出,不得强分也”[3]。综上所述,康有为通过对朱熹理学及道德伦理学的批判,建立了天欲而人理,性全是气质的断言,为其宣扬重利兼义的观念打下基础。
(二)重利兼义,以义生利
康有为批判“宋儒不知,而轻鄙功利,致人才恭尔,中国不振”[9],这既是评价历史,更是希望汲取历史经验教训,改变社会“轻鄙功利”之弊,从而实现救亡图存的使命,故而他肯定“利者,人所同好”[9],对于富与贵,“人不能无取”[9]。为了论证人趋于私利的根源,康有为不惜放弃他先前肯定的自然人性论,进而强调人性之私及其在社会发展中的动力作用。他说:“人之性也,莫不自私。夫惟有私,故事竞争,此自无始已来受种已然。原人之始,所以战胜于禽兽而独保人类,拥有全地,实赖其有自私竞争致胜之功也。”[8]对于朱熹尚公去私的观念,康有为反其道而行之,在他看来,当面对有限的资源时,人性之私便油然而生,但恰恰是人性蕴藏之私,推动了社会的发展,很显然这其中是受到了进化论的一定影响。他说:“凡挟才智艺能之人,其下者,利禄富贵之欲必深,其高者,功名之心必厚……淡于爵禄、淡于功名之士,虽有德行志节,其于趋事赴功也必迟且钝。”[4]因此,“薄为俸禄,而责吏之廉;未尝养民,而期俗之善……盖未富而言教,悖乎公理,紊乎行序也。”[9]这与朱熹引理入义,重义轻利的观念形成了明显的反差。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康有为对先前“纵欲”的言论,已有所纠正,对于道义更加重视,如同朱熹严格划分义心与利心的区别,他也同样注重区分二者的不同。他说:“怀义心者,虽日为利,而亦义。怀利心者,虽日为善,而亦恶”,“若必怀利心,是乱世与平世之所由异,而太平终无可望之日矣”。[10]在这一点上,他与朱熹持守的重视仁义道德的价值观基本一致。平心而论,作为深受传统儒家文化浸染的康有为,并没有走到见利忘义、唯利是图的绝对功利主义的立场。他继承了“利者,义之和也”的道德命题,借子贡之口,说:“不欲人之加诸我,吾亦欲无加诸人,义之和也。如此,则利可也。”[10]他担心若完全以利为本,则将容易导致天下大乱,他又借司马迁之口,说:“利诚乱之始也。”[10]
三、传统义利观在近代的嬗变及其启示
康有为的义利观折射出中国近代思想家们对中国传统治理理念现代转型的思考,面对西方现代化的强势入侵,他认识到,中国只有走出传统义利观的束缚,重视功利,富国强兵,才能有力回应西方的入侵,这充分体现出近代救亡图存的时代任务,而朱熹的义利观则代表了先秦以降,传统儒家“正其谊而不谋其利,明其道而不计其功”(《汉书·董仲舒传》)的重义轻利的道德选择。进而言之,康有为通过对朱熹义利观的批判,是对义利之辨这一问题的理解和诠释,而在这样的创造过程中,义利之辨所蕴含的真理及其启示也得到更加全面和深刻的阐释。
(一)义利统一源于人的双重属性
人的双重属性指的是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一方面,自然属性决定了人对物质和精神的需求,如渴则饮、饥则食、安全之需等。在这一点上,可以说人同地球上其他生物没有本质的差异。康有为说人具备“求乐免苦”的权利,“爱恶仁义,非惟人心有之,虽禽兽之心亦有焉”[8],多是出于人的自然属性而言的。先秦儒家和宋明理学家不否认人由自然属性而带来的基本需求,如“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论语·里仁》),“饮食者,天理也。”[2]另一方面,社会属性又决定了人必须要遵守一定的社会道德规范和原则。秉承仁义礼智,是人之于物的根本区别。孟子说:“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舜明于庶物,察于人伦,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孟子·离娄上》)荀子把学与义比较后,得出“学数有终,若其义则不可须臾舍也。为之人也,舍之禽兽也”(《荀子·劝学》)的忠告。朱熹则以道学家的眼光,从德性纯粹与否的角度,指出:“物物运动蠢然,若与人无异。而人之仁义礼智之粹然者,物则无也。”[2]人受到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的双重作用,与此相应,也离不开对义与利的追求。无论是朱熹所持的重义轻利还是康有为所论的重利兼义,皆是源于这一双重属性。义利之间是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不是顾此失彼的冲突与对立。一味强调道义或功利,都失之片面,并可能会造成泛道德主义或极端功利主义的问题。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如果没有义利统一,人们的利益追求以至全部行为就不能得到有效的规范与引导,从而也会导致以合理化为特征的现代化破产。”[11]
(二)义利统一需要与时俱进
随着社会经济结构和思想文化的发展变迁,义与利的内涵也必然要适应时代的发展。“所谓‘义’亦即社会道德准则是一历史范畴,具有鲜明的时代性。”[12]朱熹重义的观念虽有合理性,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其自身所包含的局限性也逐步显露出来。康有为说:“朱子之学在义,故敛之而愈啬。而民情实不能绝也”[14];“盖天下义理,无非日新”[6]。在康有为看来,朱熹过度强调精神层面的道义,势必阻碍和限制社会大众对物质层面的需要和追求,这与社会实情和历史发展趋势相背,以至于造成“宋儒不知,而轻鄙功利,致人才恭尔,中国不振”[9]的历史结局。朱熹重义的价值取向具有可贵的道德意义,但是其重之“义”,最终指向的是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封建纲常伦理,其重义轻利的观念与维护宗法社会秩序的稳定紧密相连。他对功利意识和人欲追求的谨慎态度,在其理学思想被官方化后,逐渐对个体和社会求利的动力产生了消解作用,这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功利意识和功利原则对社会发展的动力和杠杆作用。当代学者陈来就曾指出:“儒家或理学面临的矛盾在于,它自身最多只能保持伦理学原理的一般纯粹性,而无法判定‘义’所代表的准则体系中哪些规范应当改变以适应社会发展,因而可能会把规范僵化。”[13]
康有为指出理学家的重义轻利观念已不能适应急剧变化的社会现实时,说:“夫以天地,不变则不能久,而况于人乎?且人欲不变,安可得哉?”[9]因此,康有为在对传统义利观扬弃的基础上,赋予义与利新的时代内涵。其“义”已经包含了求强求富,人人自主、人人独立等新的价值观念,对利的追求不再一味“罕言”之,而是推崇工商实业的发展。有学者已经指出:“在许多爱国的近代商人看来,最大的义已不是恪守封建伦理道德,而在于通过发展工商实业,为救亡图存,富国利民尽自己的一份力量。”[15]
(三)崇尚道义具有超越功利的普遍意义
“义”作为具体的道德准则,具有时代变化的特征,但是它作为社会道德原则,则又具有超越功利的普遍意义。“‘义’代表了社会性的道德要求,具有规范和引导行为的普遍意义。”[17]朱熹引理入义,重义轻利,尚公轻私的价值取向,具有超越功利的普遍意义。朱熹说:“义利之说,乃儒者第一义。”[2]孔子笃信:“君子义以为质”;“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论语·卫灵公》)。孔子、孟子甚至提出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道德追求。质言之,儒家倡导见利思义,反对见利忘义的道德观念,具有恒久性、普遍性,是跨越时代的,这不仅是超越功利,更是超越生死,是一种高尚的道德境界。平心而论,若是能够扬弃三纲五常所包含的落后性的一面,以义格利的价值观无疑具有伦理学原理的纯粹性以及可贵的理想维度。康有为重利兼义的主张,是对朱熹的重义轻利观念的完善,而不是绝对反对。他对理学家“徒陈高义”提出批评,但是在维护“义”作为社会道德原则的总原则上,却是保持一致的。他将人欲改为天欲,并非就是承认人欲的绝对性,在义利之间,他也屡次言及尊重道义的重要,他说“不可枉己求利”[4],“有耻心,则可使路不拾遗矣”[4],“利心不可怀也”[10]。就此而言,康有为与朱熹的义利观念是统合于儒家义利兼顾,反对唯利是图的道德伦理之中的。相对于“义”的普遍意义,人对功利的追求虽源于自然属性的内在要求,但是作为用来满足个人或组织需求的各种层次和类型的功利,离不开具体的对象。“‘利’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是个别的、特殊的,哪怕它是某个集体(家庭、部落、团体、国家、民族)之利,它总是与‘我’有关才能是‘利’。”[16]利的特殊性决定了人对功利的追求必然是要有限度的,而这种限度不仅需要道义的规约,亦需要尚义的超越性加以守护和升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