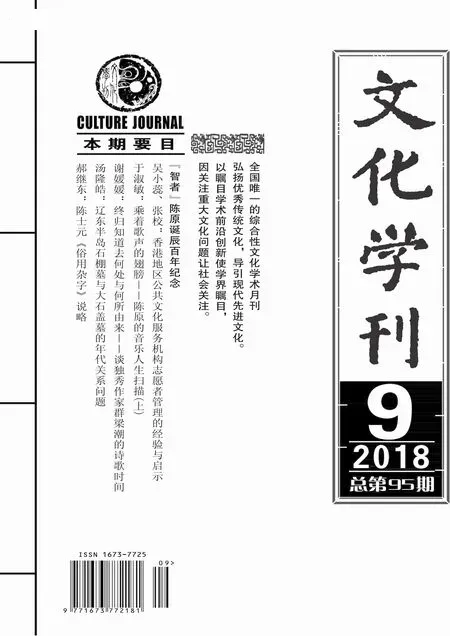何谓“真理”与“教师”何为
——有感于黄武雄《童年与解放》
王国东
(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7)
《童年与解放》是台湾学者黄武雄的代表作之一,在书中作者颇具创造性地提出人的“自然能力”和“文明能力”两个核心概念,使我们对如何面对一个具体而真实的人类存在,有了更深入的理解和把握。作者黄武雄曾是台湾大学数学系的教授,专业是几何研究,这个背景本身就颇让笔者惊讶。一个理工科学者并没有将自己所从事的专业的精髓,即以技术理性和工具理性所代表的“文明能力”视若圭臬,反而著书立说关心教育,且在书中倡导教育中“自然能力”的回归和儿童的自由解放。理由一,笔者认为是源于彼时台湾岛内的社会背景。黄武雄长于“白色恐怖”时期,该书完成于戒严之后,长期的封闭和压抑促发了黄武雄对自由和真的强烈向往,“人即目的”也成了作者全书的开篇之辞。理由二,笔者认为恰恰在于黄武雄注意到了教育的严重异化。教育变成了纯粹“文明能力”的传递,这种单一的传递禁锢了孩子的思想,扼杀了孩子的创造力。真正的教育需要呼唤“自然能力”的回归,而现实的教育恰恰忽略了这种“自然能力”。教育解放的过程,变成了教育压迫的过程,这是本末倒置的。有感于黄武雄在《童年与解放》中传达的深刻教育关怀,笔者也在思考——何谓“真理”?“教师”何为?
一、何谓“真理”
怎么理解作者所提出的“自然能力”和“文明能力”这两个重要概念?以皮亚杰(Jean Piaget)认知理论为例,认知理论对事物分析区辨和细微描述的能力是一种典型的文明能力。但除此之外,人还有一种整体认识和特征辨识的能力,这是一种在儿童时期即存在的能力,也就是自然能力。从语言的学习开始,儿童就表现出这种整体辨识的能力。但是随着儿童年龄的增长,社会变迁的加快,文明形式的愈发多样,社会化的过程也愈发讲求效率。为了快速将套装知识、客观真理、制度典章等文明传递给下一代,各种权威教条不断兴起,这也导致人的抽象文明能力在飞快提升的同时,自然能力不断下降甚至凋零。当自然能力丧失殆尽只剩下文明能力时,人类便逐渐受到奴役。而当文明变老之后,就会异化成为支配人类的工具,人真正成为了文明压迫和宰制的对象。法国思想家福柯(Michel Foucault)的研究有力地论证了这一过程。福柯认为,主体完全是由权力话语所建构的,当外在的政治经济力量、意识形态和文化控制所代表的文明能力无所不在时,人的主体地位就会逐渐丧失,直到主体完全成为一个客体化的主体。因此,当外在的文明愈发发达多样,人的主体精神便会不复存在,与生俱来的自然能力也将逐渐消失,人类终将陷入困境。所以,继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喊出“上帝已死”之后,福柯宣称“主体已死”——主体变成了真理和强权的奴隶!“主体已死”实则包含了福柯对传统真理观的强烈批判。
在传统认识论或实证主义哲学背后,有一个最基本的假定,即这个世界是可以通过逻辑理性去把握的,有一个实实在在的客观真理存在,这也就意味着,科学研究的目的就是为了发现这些存在的真理。但是这样的真理观发展到今天,我们发现它不再奏效,“哥德尔不完备定理”(Godel's incompleteness theorem)“海森堡测不准原理”(Heinsberg's uncertainty principle)等一系列理论的提出,让我们突然意识到,即便是以往被认为是最坚不可摧的自然科学的真理也是不可靠的,那些看上去极其纯粹客观的知识,也只不过是人类出于解释这个世界和宇宙的需要所构建出的一套能自圆其说的解释模型而已。什么是真理?当它能够解释我们身边的现象或者问题,它就是真理,当它不能解释这些现象或者问题,它就不是真理。例如,在古希腊,天文学家托勒密(Claudius Ptolemy)提出“地心说”,认为地球是宇宙的中心,其他天体都围绕地球转动,“地心说”数千年来被罗马教廷一直视为真理。中世纪以后,哥白尼(Nikolaus Kopernikus)《天体运行论》中提出“日心说”,后被伽利略(Galileo Galilei)论证,长期以来居于宗教统治地位的“地心说”才被视为谬误,太阳是宇宙的中心成为真理。但随着现代天文学研究的深入,人们又发现,太阳只不过是太阳系的中心,并不是宇宙的中心,“日心说”又被推翻。宇宙不是静止不变的,它总是处在不断的变化中,所以真理从来都不是绝对的,当我们提出的解释这个宇宙的模型不能被证伪,它就是“真理”,而一旦它被证伪,它就不是“真理”,所有科学的定义或者所谓真理都具有这样的基本特征。在这一点上,英国哲学家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著名的“证伪理论”(theory of falsification)一语道破:科学的理论或者命题,不可能被经验证实,而只能被经验证伪!因此,后现代主义哲学的一项重要内容就在于对传统哲学真理观的批判。福柯否定了真理的客观性和终极性,以及绝对性。在他看来,一切真理的产生来源于社会文化构架的策略,背后是权力!权力——多么有力的质问!真理背后暗含的是强权!
需要说明的是,质疑真理的唯一性和否定真理的存在是两回事,真理一定是存在的,只不过是流动变化的。事实上,黄武雄也探讨了知识和真理应有的掌握和传递方式。黄武雄认为,知识应该是主体经验的拓展,客观的知识如果没有经过体验和思辨,就永远不会成为主体的知识。只有经过主体转化的知识,才会成为人的一部分。非主体化的知识,也即客观的套装知识只会导致人的压迫和异化。因此,真正的知识来源于经验的拓展,教育的目的不是传授,而是促进的人的经验的拓展。这样的观点我们似曾相识,美国进步主义教育家杜威(John Dewey)在20世纪20年代即提出过类似的论述。杜威认为,教育是人的经验的改组或改造,学生只有将间接的知识与直接的经验相结合,并在自身的活动中建构出知识,这样的知识才是有价值的。因此,黄武雄在书中用较大篇幅强调“体验”对于调和人的自然能力和文明能力的作用。他认为,“体验”是人重要的原始创造特质。“人类文明的发展是人类共同体验的结晶,文明是亚当夏娃被逐出伊甸园,脱离了上帝呵护,才在人的体验中发展起来的。同样,人个体的成长也是通过不断而勇敢的尝试,无畏无忌地干扰并参与外在世界的秩序,才有了知识,形成智慧。等到一个人开始被灌输外加的知识,在吸收知识的过程中,被剥夺自身的参与及体验,那么他的成长、他的创造活动便告停止。他被送入文明轨道,吸收系列的文明知识,他可以被训练成一名熟练的技术操作员,但他没有创造,他的生命力在急速萎缩。”[1]《童年与解放》不断强调体验自然和真实生活情境的重要性,原因在于,作者认为当前的教育过于偏向文本的传授,以套装知识为主的教学固然提升了学生的文明能力,但长此以往也必将造成学生自然能力的消逝,这样的知性成长是扭曲的,学生也不可能在教育中获得真正的解放和自由。因此,我们的教育需要回归到学生最真实和自然的存在中,在获得、发展文明的同时继续葆有童年时代即存在的自然能力。
就像我们并不是否定真理的存在,我们也不是要否定文明,甚至我们需要拥抱文明。之前的文明是人类不断发展的结晶,是下一代发展更高文明的礼物,下一代也只有在打开自己经验世界,以融入自己的生活情境为基础,让上一代的文明与自我所存在的生活对话,在这样的借鉴对话中,我们才能对文明进行修正、创新甚至提出完全不同的诠释。如此以往,文明才得以生生不息。
二、“教师”何为
鉴于以上分析,笔者也延伸至教育教学交往活动中的重要主体——“传道、授业、解惑”之“师者”的思考。虽然黄武雄没有直接在《童年与解放》中对教学观、师生观进行探讨,但其对传统知识论的分析也有助于我们讨论今天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教师?
教师的作用是什么?教师的作用是教授课本上既定的公式和概念?抑或评阅学生的习题册和考试卷?如果教师的作用是完成这样的工作,那不少学生家长也可以承担教师的职能,何须教师?可悲的是,这依然是不少教师行业从业人员的工作状态。现实的学校教育,我们听到的最多的教师训诫口语是“认真听讲”,看到优秀学生的评价总少不了“乖巧听话”。对此,有学者也曾借中美教室内空间布局的差异做了一个颇有深意的分析。[2]在我国的课堂中,最为常见的桌椅排列是整齐有序的“秧田式”,学生全体面对教师和黑板。而美国课堂桌椅的排列却是五花八门,几乎什么样的排列方式都有。比较而言,中国课堂的空间布局有利于学生听讲、记笔记,而美国课堂的空间布局则更有利于师生互动、小组讨论和操作实验等。这种布局差异实则暗含师生关系和教育观念的不同,中式课堂容易使学生产生压迫感,教师也不自觉地会成为权威和“真理宣讲者”的角色,学生的学习相对是被动的;而美式课堂的教师往往会平等参与到学生的探讨和知识的建构中,承担的是一个教学活动组织者的角色,学生的学习相对来说是能动的。相应的,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我们的老师喜欢“认真听讲”的学生,而美式课堂的学生更喜欢质疑发问了。
但是,知识转型和知识大爆炸时代的来临提醒我们,过往的经验知识和客观真理是处于流动变化之中的,真理的恒常性和权威性已然被打破,真理的存在本身就应该是被修正和批判的,如果我们的教师在课堂上仍然以真理宣讲者的角色传递现成的知识甚至以此来压迫我们的孩子,后果可想而知。这里另要说明的是,知识转型容易造成教育领域常见的一种误导,即现有的知识因其更新日益迅捷导致其传递的必要性时常被讨论,实际上,潜在的问题仍然在于真理观念的另一种误解。知识转型和知识爆炸并不意味着知识的虚无,知识和真理的虚无观念往往导致一种教育无用论,这显然不合乎逻辑。因此,所谓知识转型就意味着教育变革乃是夸大其词。在弄清知识转型的应有之义之后,笔者认为,关键的一点在于我们应重视知识传授方式本身,即教师应以什么样的方式和态度去教学。
在黄武雄看来,童年的经验之所以可贵,就在于小孩子与身俱来的无边好奇、无限勇气以及没有偏见的宽容之心,这些可贵的品质是学生创造力生发的必要条件。黄武雄深刻洞察目前教育异化所造成的创造力丢失,对创造力的呼吁成为作者倡导葆有童年自然能力的逻辑起点。科技的飞速进步使得大量知识记忆和计算的过程被人工智能所取代,而且人工智能比人类更为精确迅速,倘若人类就此受困于人工智能,势必沦为工具的工具。这就相当于人类创造了一系列知识经验,再用这些知识经验去奴役自己,让自己变成机制的奴隶,这是可悲的。但实际上,人类之所以能够以主人的角色在大自然中存续至今,恰是因为人类作为高级动物所具有的一种特殊创造力,这是最先进的人工智能机器也不能取代的更高级的“智能”。因此,面对这样一个新的时代,如何摆脱人类自己的创造对自己的束缚,教育承担着重要的任务,即如何葆有和激发孩子的创造力。
教师之所以不同于其他专业技能人员,在于其不仅具备基本的“传道授业解惑”能力,还在于其经过诸如课程教学论、教育心理学等相关专业的培训之后所具备的“诱导”孩子的能力。好的教师一定是一个优秀的“诱导”者:“诱导”学生喜欢自己学习的学科,激发对未知领域的兴趣和求知欲;“诱导”学生不断追问“为什么”,敢于质疑课本上的定义和概念。即使教师是“传道授业”者,“道、业”也应该是最基本的学习符号和代码,这些最基本的符号和代码的教授主要在于帮助学生创造新的知识、推翻旧有的概念或解释新的问题,换句话说,“知识教学的真正目的是人的创造力而非知识本身”[3]。人天生爱好知识,更不用说这些好奇心和求知欲极强的孩子们,但是我们很难相信,长期浸染于“认真听讲”“乖巧听话”的训诫和评价方式下的孩子们,能充分发挥他们的创造力和想象力。此外,笔者补充另一点思考,眼下有关脑科学的研究对学习方式变革的探讨甚嚣尘上,加之20世纪行为主义心理学的余波未消,所以今天的教育仍然多多少少囿于应试之怪圈,教师在和学生主体交往关系中的作用也被削弱。但我们稍加思索便不难推断,不论有关学习科学、脑科学的研究如何发达,它在教育教学活动中能解决的也只能是如何让学生更加快速、更加有效地吸纳知识的问题,而如何激发学生对某一门学科的学习兴趣,真正通过教育培养出具有创新能力的人才,这不是某个科学或者主义可以解决的。学习兴趣和创造力的培养固然也受到社会文化等多方面的影响,但起码在教育方法的选择上,是每一个身处一线的教师可以思考并努力去实践的。
归根结底,好的学校教育其实是教师负责点起这把火,然后才是孩子们充分燃烧。
三、结论
很多读者都会将黄武雄提倡的儿童“自然能力”的发展和卢梭的“自然主义”教育思想相提并论,但稍作比较,我们也会发现其中的差别。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是一个彻底的自然主义者,在他看来,教育应该完全遵循儿童的自然天性,无需成人的任何灌输和压制,孩子应该完全归于自然并在自身的教育和成长中获得主体地位。但实际上,如果教育真的如卢梭所提倡的那样,完全由儿童自由生长,而不施以必要的引导,文明如何传递和进步?我们又与原始人何异?
黄武雄虽然认为教育应该遵循儿童生来就有的自然能力,童年应该解放,但他并不是要成为卢梭那样彻底的自然主义教育者。他认为,教育在强调立足自然的同时仍应该面向文明,但问题在于,既然童年应该解放,也就是说,教育应该将加在儿童身上的“文明”的枷锁全部都打碎,这才是解放,但他又提倡面向文明,是否意味着作者的前后逻辑是矛盾的呢?其实不然,黄武雄并没有反对我们去教授孩子这些文明能力而只需葆有自然能力,他反对的是我们利用这些文明能力(套装知识、唯一真理等)去压迫和奴役我们的孩子。黄武雄借此批判了现代社会虽创造了高度文明,但却让人类成为了文明机制的奴隶,变成工具的工具。因此,黄武雄表面上是在探讨童年的解放,实际上是在探讨整个人类的解放,在这个意义上,《童年与解放》是一本饱含智慧的著述。如此,笔者很赞同李丁赞先生描述自然与文明关系的一段话:“文明,是一种高度。只有面向文明,我们才能登高望远,开阔视野,神驰在浩瀚的宇宙之中。自然,是一种厚度。只有立足在自然之中,我们才能安然恬适、无惧无畏地与文明对话。”[4]